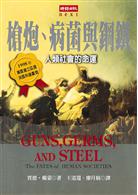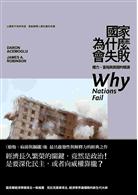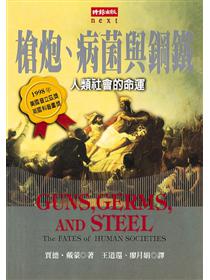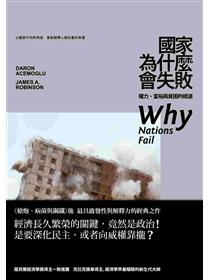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代序】下山家族物語
下山操子(林香蘭)
每當老爹酣醉時,便會淚涔涔地吟唱起自創曲〈夢的世界〉,然後,彷彿跌入回憶一般,對著兒女開始喃喃自語、嘮叨不休起來:
「你們的祖父,我的父親下山治平哪,是日本靜岡縣三島市人,他十八歲就入伍,隨靜岡聯隊屯駐到台中的干城營區。那時台灣的平地和大部分的山地,都已順服為日本的殖民地,惟獨歷來深居高山荒蠻,頑強凶悍的『生蕃』,被歷代政權視為『化外之民』,以隘勇線隔絕,因此從未與文明世界接觸,一直生活於叢山峻嶺,怡然自得悠悠自在地,過著最原始的生活。
這些高山驕子們的祖訓是:『看到外來陌生人,見一個殺一個。』『生蕃』傳承獵取人頭的習俗,常常神出鬼沒地下山出草。
若要完成全台灣納入日本殖民地的理想,必須大量無懼生死,願為國犧牲奉獻,投入征服台灣高山凶悍矯健生蕃的日本軍警。於是精悍愛國的父親退伍後,就轉考警官學校,響應台灣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蕃政策,參與殖民事業中最艱困的,征服中央山脈中部最強悍泰雅族的事業。」
他沉思片刻又說:
「你們的祖母,我的母親貝克‧道雷,是泰雅族最大部落馬烈巴社(Malepa)的大公主,聰慧手巧,十三歲便能織出巧奪天工的泰雅麻織品,於是依傳統於額頭上入墨(紋面),表示已有資格結婚,從此求婚者絡繹不絕,她卻誓死表示,除了雅烏依‧諾幹,她誰都不嫁。可這件事在當時其父母長輩絕不可能答應啊!依照泰雅習俗,額頭尚未入墨的男性不算男人,若沒有勇氣殺人,又將如何娶妻生子保護家人呢。雅烏依雖然已到適婚年齡,但是額頭尚未入墨,因此沒有人肯將女兒下嫁。他幼時全家人遭出草殺害成為孤兒,在其叔叔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所以寧願終身不婚,以免妻子兒女也被出草。他也自誓絕不出草殺人,以免害他人也過著傷痛孤苦的生活。
馬烈巴位居高山,想吃魚必須下到北港溪或合歡溪等去抓。常為反對出草與其父爭吵的母親,有次隨其母到西卡瑤社下面的合歡溪捉魚,不料在那裡邂逅了跟自己思想一致的雅烏依。彼此一見鍾情互生愛意,已到被族人譏為老女人的年紀,母親始終堅持非雅烏依不嫁。位極權高的泰雅族大頭目,也拿賢慧聰明、能幹又十分頑固的愛女完全沒有辦法。
後來父親被任命為馬烈巴駐在所警部主任,在理蕃政略婚姻的命令鞭策下,以頭目及抗日族人的生命相要脅,強娶母親。然而為他生了六個孩子的母親(冠以日本名字『下山龍子』),明明是先娶者,但戶籍上卻登錄為『內妻』(妾),反而父親後來又娶了故鄉的初戀情人勝又仲子,帶到台灣生了二男一女,其身分才是『正妻』(大老婆)。這對母親公平嗎?」
老爹無奈地搖頭嘆氣又說:
「我就讀霧社小學校四年級時,父親和仲子阿姨都返回日本,從此我恨透了拋妻棄子無情無義的父親。雖然他常來信,我被悲憤之心矇蔽雙眼,未曾看他的信。還好大弟阿宏和二妹敏子會回信。從國小四年級到師範學校畢業,八年間,我寫給父親的信寥寥可數,而且每次寫都是在我最傷痛、悲哀與氣憤的時候。直到師範畢業那年,霧社分室高井主任翻出最密件給我看,看到『政略婚姻』的內情資料、看到父親為安頓政略婚姻之下滯留台灣的妻子兒女,到處奔波陳情的一大疊檔案,才知自己的無知魯莽,想到那些指責謾罵父親的不孝信函,我至今尚覺得羞愧得無地自容。」
每說到此處,老爹便忍不住淚如泉湧。
好奇的我曾問老爹還記得那些信的內容嗎?他屈指算一算說:
「我父親娶雙妻共生九個兒女,其中他最疼愛的一直是敏子,父親歸日後,思父殷切的敏子得了夜遊症。母親為了工作出遠門無法回家睡覺時都交代我,萬一晚上敏子爬起來走向暗夜,絕不可驚動她,只要默默的尾隨保護,直到她自己回來睡進棉被即可。據說驚動夜遊者,會讓他猝死。看著星空下暗夜中敏子口裡唸著:『爸爸您在哪裡?爸爸您不要我了嗎?爸爸快回來。』往返於昔時仲子阿姨曾住過的警察宿舍。我實在心痛,因此,首次提筆寫信責罵害敏子得夜遊症的父親。
我們能住在警察宿舍,母親能以霧社分室所「囑託」(臨時雇員)之職,按月領取優厚的俸給,母親深信是高井主任和全體警察們同情我們的遭遇所賜。雖然她自稱是無知的蕃婦,但卻深明大義,知道受人恩惠不但要感恩,更該設法報恩。為了報恩,她借地種蔬菜瓜果,讓交通不便買不到新鮮蔬果的恩人們,能吃到她親手栽培的菜。
她無論大清早、下班後都到菜園忙碌。甚至重病時,仍挑糞尿到菜園施肥。尾隨而去幫忙的我,看到她在樹薯下累倒,但慈愛的母親發現我後還喘著氣說:『阿一,我沒有關係了。菜園之事不是你的工作,快去上課,不許遲到。你的本份是專心課業,將來覓得好職業,才是我的好兒子。』看到獨立持家的母親操勞受苦,我心裡十分酸楚,又寫信責罵父親拋妻不顧,害母親倍受辛勞。
在埔里高等科讀書時,同學們傳閱報紙竊竊私語,然後擁向我,指著報端七嘴八舌地交相指責:『你的父親是寡廉鮮恥的人口販子,誘拐台灣泰雅族女到東京的綠燈戶賣淫。』當我看到這份報紙,羞愧得期望有個地洞讓我鑽進去隱身。母親和弟弟妹妹也都為此遭受困擾。我怒不可遏,提筆大罵父親是罪大惡極的人渣、大壞蛋,為販賣人口上報,不單日本的下山家族蒙羞,也拖累在台灣的我們,受世人指責唾罵。
昭和五年的春假,佐塚愛祐伯伯從馬烈巴駐在所主任晉升為霧社分室主任,母親帶著我們全家去道賀時,正逢他們在拍全家福紀念照。亞娃依阿姨熱情的招呼我們兩家合照一張,正要拍時,佐塚伯伯站起來制止說:『照相洗相片要花很多錢呢。』還很不客氣地驅趕我們。他的孩子昌男、佐和子和豐子求其父讓兩家合照一張,他都傲慢地相應不理。父親曾擁有五台相機,佐塚家的那兩台相機,應該是父親離開馬烈巴前送給他們的。聽說那座比人高的昂貴精工舍立鐘,也是父親免費送給將繼任其職務的佐塚伯伯的。而今我們卻為拍一張相片而受屈辱,心有不甘的我,又提筆責罵父親,怨怪他當時為何不把那兩台相機留給我們呢。
我從台中師範學校即將畢業前夕,那一天我從校長室垂頭喪氣的走出時,對父親的憤恨升到頂點。我恨自己為何出生在這個家庭?我恨生而為人為何不能選擇自己的父親?校長的話不停在耳邊繚繞:『我剛接到總督府理蕃課的公文,不許讓你參加畢業前到內地(日本)的修業旅行,避免你見到父親後不肯回台灣,那樣的話你的母親就太可憐了。』我一再向校長保證,一定和師長同學同出同進,絕不滯留日本。但是校長說他不能違背總督府的指令。非常期盼到內地的我,竟為了『父親』的緣故臨行前被阻擋。此時我失去理性般地去信嚴厲責怪父親。」
說到此,老爹無奈地深深嘆了一口氣,掉下淚來。
接著他又叨唸:
「親眼目睹,親耳所聽之事,真的就是事情的唯一真相嗎?若不十分了解而斷章取義的話,那只是瞎子摸象罷了。那些喜歡探究日本時代台灣的文人墨客,常找上門看看父親留下的照片和我們家的照片,然後詢問我們下山家的物語。提到下山家族的日文書我看過四十多本,但是中文書從來沒看過。已出版的書中對母親被丈夫遺棄獨立撫養兒女長大之事,都寄予同情和頌揚;對於父親則千篇一律都只寫其享齊人之福,拋泰雅妻子兒女不顧之惡事。
我尚未看到霧社分室的最密件前,總認定父親是世上最無情無義的大壞蛋。但是目睹那些資料後很慚愧。平時常訓誡我們『右手所做善事不讓左手知道才是真善。』的父親,其實是個真心關愛我們的好父親。假如我能力夠的話,真想親手為父母親出一本書,順便為父親討回公道。」
老爹常以期待的淚眼對我們說:
「假如你們的爺爺是日本的落花生,他播種在台灣這塊泥土中,生出的我們就是土生土長的落花生了。我們下山家族的後代,生在台灣,生活、教育、工作都在台灣。假如日本是我們的生身父母,台灣就是養育我們的父母。養育之恩比生育之恩大,所以我們應該認定台灣是我們的家鄉,真心的愛台灣才對。因此我有一個心願,希望我的兒女能用中文寫下我們下山的家族史在台灣出版發行。不要在乎此書是否能暢銷,只要能留給兒孫們各一本,就是功德一樁啊!」
看我們相應不理,他含著淚,以孤獨淒涼的腔調吟唱起〈夢的世界〉。然後再度懇切地對我們說:「人生苦短似幻夢,轉眼一切成虛空。你們若不肯出手寫下山家物語,過了數代後,我們的後代將無人知曉自己的身家根源了。」
其實並非兒女不孝,而是當時雖然家中都以日語交談,但只受過中文教育的我們,對老爹喝醉時手寫的兩冊「自述」,以及寫家族史必然得熟讀的《台灣植民發達史》(東鄉實、佐藤四郎共著)、《台灣生蕃種族寫真帖》(成田武司編),彼時完全看不懂,就算老爹口述,我們都還是似懂非懂,要如何完成他的心願?
記得我國小四年級時,老爹為了生計,答應霧社電源保護站林淵霖主任,去鬧鬼最凶的高峰氣象觀測所獨守。大峰行雜貨店主陳春麟先生,請老媽當店員。當時日本敗戰約十年,霧社郵局尚未復業,居民都深感不便。陳先生知道老媽曾在東京自家郵局服務過,便申請在大峰行內設立郵政代辦所,郵務由她負全責,以此資助出身日本武士世家,不為五斗米折腰傲骨凜凜的母親。有一天我又被同學以日本鬼子、日本婆仔的話語凌辱,哭著跑回家找媽媽,追問我們的家世背景和同學們有何不同?當下她緊張地四下張望,答案卻依然是:「隔牆有耳,請不要拿這問題為難我。」為何雙親對這問題如此敏感呢?
這段時間,有位揹著大相機的日本青年到雜貨店的郵政代辦所來寄文稿到東京的讀賣新聞社,老媽表情突然變得很怪異,似興奮又不安,似哀傷又含期待地探問:「請問井上昌三先生還在東京的讀賣新聞社上班嗎?」那位青年追問母親和井上昌三的關係,並肯定地說媽媽一定是日本人。但是老媽緊張不安地回答:「我是高砂族。是泰雅族的高砂族,根本不認識井上昌三。只是前幾日也有日本人來寄信給井上昌三時談過他而已。」
我好奇興奮地靠近想告訴那位陌生人:「我們的確是日本人……」但是老媽正以凜冽的眼神凝視我,又以手勢比劃「隔牆有耳,請閉嘴!」制止我發言。
真是無聊透了,我就到外頭蹲著獨自玩佔地圖遊戲。那位自稱奧山的青年蹲到我身邊東問西問,我以父母的口頭禪回應:「隔牆有耳,請不要拿這問題為難我。」他保證不為難我,求我設法次日早晨將家人召集到我們曾借住過,日本時代的公共浴室前拍張全家福。聽到要幫我們照像,在當時全霧社只有農校李少白校長擁有相機的年代,我興奮莫名地答應了。
那張照片後來據說刊登在讀賣新聞上。原本以為我們都隨遣送艇葬身海底的日本親人和父母的好友見報後開始和父母互通音訊。好奇怪哦!當時就在讀賣新聞社當印刷部部長的井上昌三二舅,居然還是母親的家人中最後看到這張照片的人呢!
那張照片上所穿的衣服都是當時我們最新最好的,但從和代、典子和我的赤腳應可看出我們的貧困。從此仲子奶奶、外婆等常寄衣服、鞋子、食品、文具……等來。只要食品內含著海苔裹著的米果,絕對是外婆寄給母親的。
道雷奶奶在我未滿一周歲,就在台灣的高山過世了。人家都有長輩疼愛庇護,只有我未曾與長輩謀面。每次看到日本親友寄來的東西,就想用日文去信道謝,於是吵著雙親教我日文,他倆千篇一律地回答:「貧窮如乞丐的我們,不可能回日本了,戰敗國的語文就不必去學了。」
不肯教子女日文的老爹,隨著年邁,每醉卻必求兒女將其自述以中文在台灣出版。不是兒女不孝,不是兒女違背父親的心願,是不懂日文的兒女心有餘而力不足,實在愛莫能助呀!
青天霹靂,民國七十三年我罹患了血癌──急性白血球症的第三種變型。台中榮總的李方俊大夫說:「妳患了目前已知十九種血癌中最難纏的一種,治癒率只有百分之四。」血液科楊吉雄主任說:「若想多活些時日,必需熬過三年的間歇化學治療。」
因人生際遇坎坷,我曾竊喜自己因血癌即將從人間消失,對於家人和我都是最好不過之事。然當兩度病危戴上氧氣罩,已逝的親人似乎都來迎接我,突然傳來神莊嚴的聲音:「妳真的願意就此離開人世嗎?」腦中浮現出三個尚在求學的兒女,以及滯留台灣卻完全不學北京語、台灣話的雙親,出門辦事購物事事要依賴我。尤其成為耶穌聖靈教會牧師的家父,其聖經、奧義(講義)、讚美歌都是日文的,在台灣推展源自日本的聖靈教會,必須將讚美歌和各種資料翻成中文才行得通。為協助此生最疼愛我的父親,我毅然扛起翻譯的困難工作和協助傳教各種事宜。
於是兩度向主耶穌祈求:「為了我的父母和兒女請主救我!」兩度看到金鴿從天而降展開雙翅把我籠罩,我才能從死蔭的幽谷回到人間。
有一天,我的點滴瓶和垂下的藥袋中顯現出耀眼的十字架,不管從任何角度看,十字架都明顯地正對著我。我突然跪下祈求:「哦主啊!假如我能蒙祢相救,必勤學日文,期望在祢的庇佑下,讓我能達成老爹的心願,將父親的自述翻成中文,在台灣出版留給後人看。」
三年漫長痛苦的治療期,因為經常請假,年度工作考核都列入丙等。我卻善加利用這時間,由日語會話、童謠、懷念的老歌、國小一到六年級的教科書自習起,不懂的,向雙親請教。母親教我:「字典」是最好的老師。
說實話,在幫忙父親翻譯、協助傳教,每週末參加家裡的日語家庭禮拜之中,不知不覺我已經打下了日語文基礎。因此,當我的血癌被宣佈緩解,不用再住院治療的同時,我已能讀懂日文書,還能以日文和親友互通音訊了。
民國八十一年為了測試自己的日語文能力,我應徵長鴻出版社刊登於《國語日報》的翻譯工作。首先試翻中山光義所著「世界大搜奇」的第六冊《萬里尋主的忠狗》。接著翻譯《花之物語》,拿到兩本書的稿費時我告訴老爹:「我有自信能將您的手稿自述翻成中文在台灣出書了。」
欣喜的老爹在台中哥哥阿武家翻箱倒櫃,又翻遍埔里的弟弟阿誠家無數次。奇怪,其自述稿竟消失無蹤,不知藏身何處?動員家人協尋也都找不到,此事令老爹十分懊惱。
他跟我說:「隨著年邁體力日衰的我,也許將不久人世。趁腦海尚殘存些記憶,只能由我口述,妳記錄寫下來,否則我的心願可能就要石沉大海了。」
從此每週五晚上、週六家庭禮拜後和週日整天,我們父女倆開始進行口述與記錄的工作,歷經數月終於寫成《歸化人奇譚》。經鄧相揚先生熱心相助,介紹認識郭大衛先生。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們與釋覺映畫製作有限公司簽下長達十五年的契約,拿到三萬元簽約金,約定期內我祖父母和父母的故事若外洩,我將被罰五百倍罰金。
郭先生準備把《歸化人奇譚》改名《歐吉桑的回憶》,拍成十集電視劇,但是他們釋覺所拍攝的《又見福爾摩沙》記錄片,因牽涉版權問題,被重罰造成財務困難。郭先生極誠懇地向老爹和我致歉說:「連續劇無法如預期完成,但我立誓遲早會完成。」老爹要求郭先生《歸化人奇譚》書稿能盡快製作完成,並在他死前出版,郭先生滿口答應了。
八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父母八十壽宴時,郭大衛帶著未婚妻來參加,還執意以晚輩身份行跪拜禮。但是老爹十四日猝逝後,郭大衛和釋覺公司的工作人員好像從人間蒸發,怎麼也找尋不著了。
老爹臨終時曾慎重地委託我:「雖然妳是個血癌患者,請妳繼續為我們的後代完成在台灣出版下山家族史書而努力。不要顧慮暢不暢銷的問題,只要妳能完成,我在另個世界必能感受到,我會謝謝妳的。」
希望是支持人存活的動力,為達成對向來首重誠信的父親的承諾,我不斷祈求主耶穌庇佑。民國九十七年,以老爹口述的《歸化人奇譚》及後來找到的兩冊自述手稿為主,再參考老爹給我的數本日文書,我重新整理撰寫的下山家族第一代與第二代故事終於完成。透過東海大學日語系所古川ちかし教授與黃淑燕教授師生的協助,年底時,自費少量印製的《流與轉》終於出版。
民國一百年,透過幾位熱心朋友,玉山國家公園盧添登先生、台南黃俊邦先生的輾轉引薦,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長看過《流與轉》後,竟表示願意將此書重新編修,正式出版,聞此訊息,我喜悅地宛如中了人生樂透的頭獎。在下山家族墓園將此喜訊告知日本爺爺、泰雅奶奶與親愛的老爹時,彷彿看見愛哭的老爹慈顏上掛著兩行感激之淚。
得血癌後迄今我已存活邁進第二十八個年頭,蒙主成全,讓我終於達成了老爹所交託的遺願,親眼目睹下山家族故事的正式出版與發行。
感謝資林皎宏先生百忙中抽空協助修潤文稿。感謝遠流台灣館編輯團隊副總編輯靜宜、主編詩薇、企劃昌瑜,除細膩費心編輯設計與行銷規劃外,為深入體悟此故事,還特別移足故事發生的現場霧社、埔里、清流、中原、眉原等地考察。對於他們認真負責的專業精神,在此致上深深的謝意。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本書內容主要根據家父下山一的口述與自述日文資料譯寫而成,書中對原住民的相關敘述頗多使用「蕃人」、「蕃丁」、「蕃社」……等詞彙,此
乃時代背景所致,並非有歧視之意。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