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各界讚譽=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舞鶴 ──王德威 ──約翰.伯格
﹝作家葉石濤﹞
舞鶴是台灣文學史中的一個天才型作家。他熟悉台灣歷史的變遷,台灣庶民生活中的禮俗文化、政治、社會等背景,正確地掌握了台灣歷代民眾的生活動脈。
﹝評論家王德威﹞
舞鶴是台灣文學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他的寫作實驗性強烈,他面對台灣及他自己所顯現的誠實與謙卑,他處理題材與形式的兼容並蓄、百無禁忌,最為令人動容。論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
﹝作家朱天心﹞
舞鶴之於我們這一代的人,很像是淡水之於台北的存在,是一個可以逃遁、逃離的出口吧!我認為舞鶴在我們這一輩的創作者中,名列前三名。
﹝作家陳雪﹞
有評論家說舞鶴的文字是患有文字小兒麻痺症,但我在讀《餘生》、《鬼兒與阿妖》時卻可以看見那文字如水流瀑布般快意奔馳在紙頁上,而隨著文字的流動發出極好聽的音韻。
舞鶴的小說其實從未拒絕讀者進入,當我反覆讀著《餘生》,心裡突然明白身在島國的台灣小說家雖然許多人悲嘆「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寫了」,但舞鶴筆下的川中島馬赫坡展現了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筆下神祕詭譎彷彿奇詭瑰麗的故事垂手可得的馬康多小鎮(此處並非指小說技法或意識型態,而是可能性,世上還有那麼多故事可說可寫而我卻視若無賭)。
﹝中國社科院學者李娜﹞
舞鶴以「田野」的雙腳感知島嶼上的未知土地,以手工書寫人心對自由的嚮往,以最無羈的聲音,追問歷史、社會、人性、欲望及其之於個體生存的意義。以一種永遠的批判立場,對台灣社會發出聲音──這是舞鶴生命存在的形式,也是他的文學的隱喻。
【新版序】
舞鶴,與我們 /朱天文
他倆流放海外。在波爾多,西風吹起時聞得見大西洋。
每次我跟舞鶴一起時,難以名之,覺得只有這句話可以描述:「他倆流放海外。」
現在,《餘生》再次新版,欲收入我給大陸簡體字版寫的序文,除非舞鶴異議,我簡直滿懷願意,就像西風吹起時聞得見大西洋。
但何以是流放?何以是海外?
我非常,非常感激舞鶴的。在世間我能夠想像的人際關係裡,再不會有這樣一種關係了。一種我稱之為師兄、師妹的關係。
小時候眷村,孩子們愛在村邊墳墓山坡竄上竄下,凸凹頗具落差的墳座地形十分適合玩武俠輕功,大家樂此不疲搬演著邵氏黑白片《女俠草上飛》,于素秋、蕭芳芳、陳寶珠,時友時敵,殺個不休。玩不夠,放學一脫離糾察隊視線便豬羊變色,繼續把沒殺完的陣仗一路殺回家。女同學們互扮師兄師妹,從小已分出個性似的,有人天生當師兄,有人永遠做師妹,倒從來沒有過師姊。也沒有師弟。姊弟戀成為通俗劇偶像劇的內容,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古昔,那個沒有什麼公共空間可供女性活動的年代,人際網路僅及於親屬,表哥表妹一出場,即接受暗示的成了一對戀愛嫌疑犯。
師兄妹,卻複雜多了。
一言以蔽之,倫理。
不只是兄友弟恭、五常五倫的那種倫理,多了現代社會的職業倫理。不過職業倫理,離開職場,倫理就管不到。仍帶著前現代的氣質呢,師徒制的倫理。或更擴大一些,手工業的倫理。落在單獨個人身上,手藝的倫理。這樣的倫理,十分之嚴格甚至,嚴厲。比亂倫禁忌還約束人。並非誰要約束你,是你自己要約束。用一個含有負面意思的詞彙,制約,你受到手藝倫理的制約。
我兩次白紙黑字援引過普利摩.李維《滅頂與生還》裡的例子,講他在奧茲維茲集中營所見,現在我再寫一次。
化學家李維,另有一本好看極了的書《週期表》,卡爾維諾讚美他是同代義大利作家裡最好的一位。他記述奧茲維茲集中營,其中少數得以從事原本職業的人,如裁縫、鞋匠、木匠、鐵匠、水泥匠等,因為恢復了原本習慣的活動,而重拾某種程度的人性尊嚴。他記述一個痛恨德國和德國人的水泥匠,但是納粹派他去建防彈的保護牆時,他卻把牆建得筆直牢固,磚砌得整齊漂亮,該用的水泥份量一點不少。李維說:「我經常在同伴(有時候甚至我自己)身上,發現一種奇異的現象。把工作做好,這個企圖是如此深植我們心中,迫使我們連敵人的工作都想做到最好,以至於你必須刻意努力,才能把工作做壞。蓄意破壞納粹交代的工作,不但招致危險,還必須克服我們原始的內在抗拒。」
手藝倫理的制約,是的李維好驚人的觀察。此制約,經常恐怕是惹人厭的,頑固到令人生恨,可也幸虧這頑固,一門手藝保存了下來。也許華人世界裡歷經兩次政黨輪替的台灣,堪可苦澀體會這種頑固倫理的好處,因為看起來只有它,最能抵抗意識形態鋪天蓋地侵襲來的時候。台灣人學得了教訓,各種各樣的倫理制約,越多樣,越難收編。被誰收編?政客,當權者,民粹操盤家。倫理制約這裡那裡,錯綜搭鏈著,學會跟政治力說不。相對於政治力,那叫社會力,讓社會力把政治恰如其分圈入它事務的鳥籠裡吧。而手藝倫理,對任何想染指進來比東劃西的傲慢,一向總是說,請出去。
我見到舞鶴,已年近半百,人生過了五十大致是減法,譬如、朋友和友情,一路減。(一群跨過五十門檻的女人得到了一句新春開示偈語:東風吹,戰鼓擂,年過五十誰怕誰。)然而舞鶴,是我的加法。
如此之容易,如此之困難。
難在、啊難在人身難得,直信難有,大心難發,經法難聞,如來難值。
我高中一年級暑假開始寫小說,雖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之下的廢棄品,也至今寫齡快要四十,便任何一門手藝,亦老師傅矣。單單這寫齡,豈不已夠人身難得?我意思是,遇見舞鶴的時候,年歲已夠長,小說這門手藝已很老,在擠滿先賢先靈簡直再難塞進一名新鬼的堂奧之奧處,忽然見到,我們只能詫異驚呼:「你是誰?你在這裡?」
之於那十年在淡水的閉居生活,我有這麼一句話寫在〈悲傷〉:孤獨並生愛神與邪魔。這些作品,大約是邪魔的產物,都有愛神的質地。
邪魔與愛神,讓人想起誰?我想起舊俄巨匠杜斯妥也夫斯基。
巨匠乃日本語,偉大藝術家。但匠這個詞,在中文裡是貶抑的。作品匠氣,完了,不是等級之別,是根本未入級。古昔,這是一般知識界都明白的評鑑。入級意味著,穿透制約。
不說打破制約,說穿透,且看近三十年來國際樂壇最奇特風景的鋼琴大師波哥雷里奇(Ivo Pogorelich)怎麼說,他彈法大膽出奇,形象前衛叛逆,他說:「叛逆?不,我一點都不叛逆。事實上,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和音樂教育,都相當尊重權威。不向權威看齊,難道要跟無知學習嗎?」(去年蕭邦誕生兩百年,五月波哥雷里奇再度來台演奏,精彩的焦元溥寫了一篇精彩的採訪文章,我談到波哥雷里奇的地方,皆出自此文。)
彈蕭邦,聽眾覺得新奇,波哥雷里奇卻有所本:「我認為蕭邦詮釋中最危險的錯誤,就是以『浪漫』的方式表現他。蕭邦雖然身處浪漫時代,但他本質上是革命家,他的音樂在當時是全然的前衛大膽。如果不能表現蕭邦的革命性,卻把他和其他浪漫派作曲家以同樣的浪漫方式表現,那根本背叛了蕭邦的精神。」
那麼彈蕭邦最難在哪裡?難在、「我認為演奏者必須真心且誠實。蕭邦的音樂容不得一絲虛偽。這也是我永遠努力的方向,我從不演奏自己不相信的音樂或彈法。」
真心且誠實,什麼意思?在這個文字貶值,一切定義彷彿處於糊渾搖移的浮動定義的年代,這兩個詞語,出現在眼前,似乎只可能是反諷,諧謔,或kuso搞笑。那就確認一下這兩個詞語的本來定義,至少對於還願意耐心讀此文至此的讀者,真心且誠實,沒錯,一如它們字形的表面意思,全部意思。
波哥雷里奇說:「蕭邦和李斯特曾是非常親近的朋友,但他們也彼此嫉妒對方。蕭邦希望能有李斯特的超絕技巧,李斯特則羨慕蕭邦的創意和靈感。就所受的音樂教育而言,李斯特可說更『全面』,他的創作類型更豐富,寫鋼琴音樂也譜管弦樂作品。我們在李斯特身上也看到明確的貝多芬傳統,把貝多芬精神以新方式延續。」
李斯特是一呼百應的樂壇盟主,而始終抗拒人群的蕭邦,只活了三十九歲。波哥雷里奇說:「李斯特之後,沒有人能夠脫離他鋼琴上的影響,他是絕對的鋼琴皇帝。蕭邦之後,鋼琴音樂脫胎換骨,他是永恆的鋼琴貴族。」
才三十九歲的蕭邦!太嘆息了所以我們說,人身難得。是要到四十歲,舞鶴才離開淡水啊。才開始以平均一年一篇短中篇、中篇、長篇的寫作節奏,直到出版《餘生》,十年間寫出了獨一無二只有舞鶴才能寫的那幾本重量級小說。
且不管別人,我自己就好奇,四十歲之前,等量的十年光陰,舞鶴閉居淡水,他在做什麼?
按一般時間表,這十年是成家立業期,立功立德立言期,舞鶴呢?中篇〈悲傷〉裡倒有一句,「努力做一個無用的人」。舞鶴式黑色幽默的造句,凡使用中文者皆很明白,無用一詞,背後可是有位超級大師老子在壓陣,老子云,無用之用方為大用。說得出努力做一個無用的人,這樣的人,他當然自知,付出之代價是昂貴的。
昂貴。
譬如初見舞鶴,在我父親去世第五年舉辦的「紀念朱西甯先生文學研討會」,舞鶴爽快答應出席了最後一場發言,結束後穿越春寒三月的台大校園去吃晚飯,我與天心天衣參差走傍他身邊,杜鵑開得紛爛。我至今記得,他言語裡的柔軟微笑,彷彿無限嚮往,他說若他的孩子不是男孩,是女兒,當年他也許會駐足下來於家,若有三個女兒,他會像我父親一樣過著有家庭生活的寫作生涯吧。這我相信。他那本驚世駭俗因此吸引來不少「錯誤」讀者的長篇小說《鬼兒與阿妖》,扉頁獻詞云,「如果我有女兒,我送她這本書/和一隻可以抱在胸前的黑貓咪」。鬼兒窩裡,「肉體有她完整自足的生命」的女女們,朱天心說此書令她想到《聊齋》裡那些女子。而《餘生》後記說,「我寫這些文字,緣由生命的自由,因自由失去的愛。」
所以舞鶴,遠離(或放棄)婚姻家庭生活的舞鶴,這很昂貴。
然而整整八○年代,文壇不知舞鶴。說他埋頭墾讀,但飽讀詩書把腦子讀壞了的亦大有人在。說他寫一抽屜(並非形容詞而是事實的一抽屜因為十年間一篇也不發表)他自稱「主題逼壓、與形式實驗兩者切磋成類僵化了的東西」,大半他也當垃圾扔掉了。沒有目的的墾讀,寫作而不發表,這兩個,都很昂貴,舞鶴以一種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生活條件來支持。出家僧人還有廟可以掛單,他廟都不掛。
這樣很偉大嗎?大心難發,小說做為一種志業?但我已看見舞鶴在那兒蹙眉嘻呵,搖頭笑著了。
我們同代之人哦,同福,同禍,亦同其慧。七○年代我唸高中大學,辦《三三集刊》,舞鶴呢?「我自少年時代開始寫作,詩、散文、評論都曾嘗試,一度還迷上舞臺劇。這是一個文學青年的一般歷程。如今,我只留下〈牡丹秋〉一篇作為紀念」
〈牡丹秋〉是我們能看到的舞鶴的第一篇作品,寫於大學三年級,出手就高。那個年紀的一段愛情同居生活終至分開,寫實而詩韻,而辯證上升至存有處境的思索。詩韻與辯證,我要寫到《荒人手記》才有的,舞鶴開始就有了,並且一直是他日後的小說特質。
第二篇小說〈微細的一線香〉,舞鶴自己說,「一種『文學的使命感』在背後驅策,寫得坎坎坷坷,鑿痕處處,我年輕時一個龐大的文學夢想,寫作〈家族史〉之前的一篇試筆。我不喜這般所從來的小說,不過猶記得當時落筆儼然,是蒼白而嚴肅的文學青年立志寫的『大而正統』的作品。」
然後我們看到一個中篇,舞鶴說,「重校一九七九年的〈往事〉,難免疙瘩,政治社會意識直接呈顯在對話中,顯然其餘的鋪陳只為這『時代批判意識』而服務。反省這般作品,感想有二:每個當代都有其『意識強勢』,另外,作者無能逃離當時代的氛圍。其時,我二十八歲,就讀台北某研究所,居住淡水小鎮,處在『黨外運動』的暴風圈中。」
三篇發表的小說,然後,舞鶴就不見了。
一,二,三,跳級一樣,舞鶴用三篇小說就跳到許多小說家寫了大半輩子小說時候的心境:為什麼要寫,寫這些幹什麼,有用嗎,寫給誰看呢,不寫了。唐諾的新書《世間的名字》裡一篇〈小說家〉列出來一排這樣的小說家。而我三十一歲仍未寫出像樣的東西就侉言侉語倦勤了在《炎夏之都》自序說,「我心裡每有一種就此不寫了的衝動,因為再怎麼寫,也寫不過生活的本身。作者的一通篇文章,往往還不如平常人的一句平常話。那些廣大在生活著的人們,『不寫的』大眾,總是令我非常慚愧。」
廣大在生活著的人們,所以知識份子們且得「下生活」去了。何況那些大災難,說都沒得說—「奧茲維茲之後,文學還有未來嗎?」
英國小說家葛林的長篇《一個燒毀的痲瘋病例》,唐諾寫道,「有著世界級聲名的大建築師(儘管並不是大小說家)奎里一覺醒來,吃了一頓過飽的早餐,例行地拎起簡單行李到機場,卻遊魂也似搭上往非洲某地的班機,能離開多遠就岔向多遠的一逕往形狀如一顆人心的非洲大陸深處走去。最後『因為船只走到這裡』的停在麻瘋病人村,所有人(甚具隱喻的)都懷疑奎里是個躲避追輯的逃犯;小說最前頭的題辭裡葛林告訴我們,一個小說作家,終其一生,很難不長時間的心生一事無成的失望。很清楚,這懷疑的已不是自己而已,而是直指小說了。」
神隱的舞鶴之消失,就像奎里因為船只走到這裡,便停在這裡。
中國當代畫家劉小東,他說繪畫幾千年到現在,基本上你可以說繪畫已經是零,已經再無可畫,好好一塊畫布在那裡,多美啊,畫它作啥。這樣,你拿起畫筆,作畫。你就是你那麼一點點可憐的當下,當代,然後你得從頭開始自己走一遍。劉小東返鄉畫《金城小子》,在遼寧凌海市金城紙廠,我響應他的詩語唯只有學舌說,直到你自己也成為一條小徑。
「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淹沒,秋水連天。」哪位禪師的辭世偈,亦舞鶴淡水十年。
舞鶴當然是儘管調侃自虧,孤獨與寂寞對坐,不知寂寞為何物。直到一天孤獨吃著小雜鍋,自己吃一口,貓吃一口,寂寞發話了:「你看看,到了這步田地,再下去沒邊了。」孤獨頷首同意。
《十七歲之海》後記舞鶴寫,「海是在孤寂歲月中不斷凝視的自淡水、三芝到老梅的海。」
到得,歸來。
歸來的舞鶴這樣說,「十年間去掉了許多禁忌和背負。十年後出淡水自覺是一個『差不多解放了自己』的人,當然也解放了文學青年以來的文學背負,在我寫〈拾骨〉時才初次體會寫作的自由,其中源源流動的韻。這兩者,『書寫自由』與『小說之韻』,在隨後的〈悲傷〉一篇中得以確認。」
出淡水的舞鶴,生猛得!小說裡說屎說尿,道在屎尿,不是什麼新鮮詞了,那種生猛,我想著是巴赫金講的狂歡節(肉體性、物質性、社會性、宇宙性的緊密結合),小丑(公然推翻上下關係所引起的哄笑),荒誕現實主義,性與生之欲,死亡和再生。
《悲傷》後記寫,「肉體仍不自由嗎,何必花費這麼多文字來確定『自由』。生命仍不自由嗎,否則『書寫自由』怎會成為生之唯一完整的自由。」
由於書寫自由,由於生活方式,舞鶴堪稱惡名昭彰矣。他照舊不與文壇往來,任憑惡漢之名傳播。但我們說,到得歸來是餘生。既是餘生,又有什麼可損失的呢?
誠如舞鶴在《餘生》一再強調的,他的碑失去了史詩的、英雄的意義,充其量是「餘生」紀念碑。舞鶴的寫作實驗性強烈,未必篇篇都能成功。我卻仍然要說,他面對台灣及他自己所顯現的誠實與謙卑,他處理題材與形式的兼容並蓄、百無禁忌,最為令人動容。論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
向來與人為善的王德威,學術圈內人人頭上一片天卻都打心底歎佩最耐煩、耐操的王德威,好教養範兒的王德威,居然如此跋扈的點題舞鶴。
王德威一直被看成夏志清的接續者。半世紀前夏志清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為英語世界研究現代中國文學開了先河,至今仍沒有可與之並比的另外一部小說史出現。夏志清的功夫是,當年耶魯很少中國現代小說藏書,而哥倫比亞大學多,夏志清每月去哥大一次,就所能讀到的作家作品,一本一本,從頭到尾(沒錯,不是摘讀不是跳讀更不是只讀二手傳播的)仔細讀完。夏志清自許《中國現代小說史》有個好處,裡面每一位作者都不一樣,他率直謂此書:「是有個人觀點的第一本。」王德威繼承了讀原典這門功夫,每一本小說,從頭讀到完。他且讀得多,讀得廣。王德威在學院,我覺得他好處難得是,幾次不多的談話中,每看見他對自己身處學院的狀態忍不住會露出笑泡泡。我從未忘記他講此話時的語氣:「夏先生的英文好,有 personality,我們的沒有。」
所以王德威如此個人觀點的說出,「論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非同小可,我們得走進去考察,真的假的?
首先,文學。
噢我的當下和當代,文學二字,幾乎我們得像是《犯罪現場》(CSI:New York)影集裡邊亮出身份邊衝入淫窟毒窩的紐約警局把我們飽受殘虐的愛人搶救出來,洗淨她,療癒她,加倍護惜她。文學定義肯定是要再確認,以一連串不字為開頭的削去法把愛人從污傷裡清除出來。她不是臉書,不是推特,不是噗浪,不是部落格,不是微博,不是網路文學,不是
不是生與死的距離啊我的愛人,世上最最遠的距離,是我站在你面前,而你不知道我愛你。
這樣的我一再要確認手藝倫理並跟小學老師一樣為語詞再三定義時,這表示,手藝倫理已經在消逝而去。我們學國語算數,初高中習國文,大學有通識課大一國文,這是常識通才基本配備,但我的當代,國文將變成一門專才,一宗獨活,一件編織,一家打銀工坊了。
經常我被問,寫小說和寫劇本有何不同,夏天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講〈我對文學的黃金誓言〉,面對大陸讀者我換了個說法,寫劇本(寫一切實用的)我用橫寫無妨,寫小說不行,一定而且只能,直寫。
橫寫,寫有用的。直寫,寫無用的。舞鶴斯人,獨自提出「小說之韻」,我們聽過韻文與非韻文之別,小說也有韻?有得很噢,不直寫我就不會寫了(手藝倫理可惡的制約)。
看起來,中文橫寫,與直寫,分了兩岸的風流。
中文橫寫,小說家必須「下生活」。採最簡約以至於符號性的分類,這是魯迅系譜—然而同時,魯迅也是鮮明的文體家。
另一個系譜,好吧我們說,張愛玲系譜。
八○後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於大陸「首發」,當年阿城讀到納悶,哪個工廠裡女工寫的好小說,上海真是臥虎藏龍。阿城初來台灣大家唱KTV,英文歌都沒聽過,聽到一首說,這個有東歐風。兩岸分屬於冷戰時期地球的兩半,世紀末或改革開放,或低盪重建,兩側開始補修學分似的,把另一半陌生空白補上。大陸這幾年國學熱,台灣可是沒熱過,從小要考試的。「寂寞身後名」,張愛玲與「張學」橫掃小資,恐怕也是還在修學分。
小說之韻,舞鶴是這麼說的。這有韻無韻,也許平分了兩岸小說秋色之不同。
台灣延續民國以來從右到左的直寫中文,書法橫條也右邊寫起。小時候報紙標題、街上標語及各種文書,如果放橫了,一概右到左。報紙開始橫排,是一家報導影劇娛樂體育藝文民生新聞的報紙。九○後各報紙紛紛改橫排,台灣報紙特有的副刊,終於也橫排。我家訂三份報,兩報的正刊(A版)還維持直排,如果沒有錯,這兩報的凡是放橫的標題,改成從左邊讀起,彷彿兩報一齊約好的,是二○○二年秋末的事。記得世紀交替,或右讀到左,或左讀到右,「那時沒有王,人人任意而行」,人人自動切換系統運行無礙,雖然偶爾也將橫排的「王眼科」看成了「斜眼王」。
以書寫的便利,自左橫寫到右,至少一樁,不踐字,因此不會沾染字墨而把字紙寫髒。尤其暑熱天,汗如雨下,而仍右起直寫,那就像雨天走路不一刻工夫便濺得滿腳泥點,除非拿紙墊在腕下隔開寫好的字行。就我所知,還有非抽菸寫不出稿的,在咖啡館百分之九十九禁菸的台北當下,也許僅存那麼一家肯仁慈闢出一室臨街開窗因此沒有空調的讓抽菸人筆耕,因此夏若蒸籠,冬似冰箱,筆耕人一字一字寫出字。
以上,可視為一個手藝人的作坊圖像。評論稱之文字煉金術,也可。
而小說做為文字煉金術,大陸有誰,我只能就教之。在台灣,此系譜第一位,王文興。再有七等生。七等生啟蒙了我輩許多文藝青年(譬如舞鶴)相信,這才是文學。然後,郭松棻。他們皆屬於白先勇現代主義世代,連左翼知識份子郭松棻的參加保釣運動,也應放在現代主義脈絡裡來理解。郭松棻鍛鑄文字之精純,比諸台灣現代詩的最高成就毫不遜色,甚且超過(評論家黃錦樹有專文談郭,且說郭的繁複精工,也可能是五四新文學以來的最高成就之一)。文學的純粹度,止於郭松棻。然則二○○七年舞鶴出版《亂迷》第一卷,把這極限之極,又推進一隙隙。《亂迷》含金量之高,簡直在拒絕買家,舞鶴自己說,三百個讀者罷。
純粹到這樣,是要激怒人的,證實了王文興所言,「作者可能都是世界上最屬『橫征暴斂』的人,比情人還更『橫征暴斂』。」身為小說同業,我只有感謝。因為我不會這樣做,也沒有人會這樣做,唯舞鶴一人,把這種可能性做出了風景。
世間有純粹一詞,只是,有純粹之物嗎?
我知道威士忌有,蘇格蘭純麥威士忌(singal malt wisky)。歐洲某些個性小酒吧,甚至供應單一純麥(singal singal malt),這種威士忌不但來自單一釀酒廠,且是不再與同個酒廠其它酒桶的酒調配的單一酒桶陳年釀出,這意味,沒有一桶酒的口味是相同的。
舞鶴純粹。
只不過,純粹之人出現在眼前,大家倒不識。所以說,直信難有,如來難值。
所以台灣文學,止於舞鶴。亦所以為什麼王德威說,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在這個意義上,舞鶴是我們的師兄。
只有塞尚知道這究竟怎麼一回事。於是他懷抱著其他印象派畫家未曾有過的信念,單槍匹馬、焦急熱切展開一項劃時代任務:在繪畫裡創造一種新型態的時間與空間,好讓經驗最終能再次於繪畫裡得到分享。
純粹,似乎必得跟精工一起。但舞鶴讓我們看見,純粹可以生猛。
舞鶴的書寫自由,《餘生》之後,《鬼兒與阿妖》到《亂迷》,有謂他嗑了藥寫,有謂他起乩。我想到阿城講朱天心的小說〈去年在馬倫巴〉裡邊緣人最後變成一隻爬蟲類,「瘋得有條有理」。有邏輯的瘋,負責任的瘋,按馬奎茲的名言是,「我的小說每一行都有寫實的基礎。」舞鶴則說,「我的小說是亂民式的。」然後他加了但書,「亂民式,因為沒有美的、正的,如果有,人們還是喜歡看。」
若非高度專注和專志,寫不出舞鶴亂民式的小說之韻。若非頭腦清晰,不能自知自覺自己的是亂民。始終對自己刻苦苛求的波哥雷里奇(舞鶴?)說:「無論唱片錄音或音樂會演出,我的最高目標就是演奏的清晰明確。要達到清晰明確和靈感或天分無關,只能靠夜以繼日的努力。」無論前衛叛逆,無論亂民,靠的都是手藝和苦功。惡漢之名遠揚的舞鶴,但我沒見過有像他這樣閑在自在的人。他站在那裡,「昨日豆棚花下過,突然迎面好風吹,獨自多立時。」
我少少幾次聽他公開場合談論創作,和顏靜色,言語簡潔,有一股內力(內在的力量),優時甚至帶勢,並非強勢,而是生命之勢。我心想,這是舞鶴十年獨居能夠獨過來的功力了。
獨學無友,偏航至孤荒絕域至烏何有之鄉的人,沒能夠獨過來。舞鶴獨學,而能自我校正,聽憑內在的指針獨力導航,做為現代人,做為受現代主義啟蒙洗禮的小說家,他真的心智強健。非常強健。
三年前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舉辦「重返現代:白先勇、《現代文學》與現代主義國際研討會」,白先勇在此執教居住已近半世紀。兩整天從早到晚都圍繞這個題目說,黃昏時沿白玫瑰盛開如沸的河邊走去院長家吃飯,延續話題我問舞鶴:「現代主義者,常常是病體,也是文體。郭松棻說文學是嗜血的,要你全部人都獻上,還不保證能成功?」
舞鶴一貫的節約說:「這是不對的。這會倒過來影響你的內在,傷害到作品。」
啊這是不對的?我一向知道只有寫得好與寫得不好,什麼時候文學竟有對跟不對。我以為已經夠理解舞鶴了?
本來,現代主義在台灣,遲到又早熟的。遲到(《現代文學》創刊於一九六○年)是相對於歐美,早熟是台灣尚未到達資本主義中產階級文化的社會條件時已透過翻譯引進在大量閱讀著了。朱天心小學四年級讀到《羅麗塔》,至今納布可夫仍是她前三名鍾愛的小說家。我們,都是現代主義大氣候下長出來的花花樹樹,受它益,也受它害。藝術史上有印象主義,是現代主義的開端,「宛如一道凱旋門,歐洲藝術從它下方穿過,進入二十世紀。」人類不再是只能被描摹。人類亦不再是不言自明,而是必須在暗影的支離破碎中被發現。
對此,舞鶴因為強健,遂表現為嘲諷。看看他自己說的,「嘲諷是我書寫時的本能,因為低調,轉成幽默,也因為嘲諷背後有憤怒很快被察覺出這幽默屬於黑色。」然而嘲諷,是成立於原有德行還在的時刻裡,小說家既然無法、亦無能改變事情往虛假和腐敗傾斜去,那麼至少,揭露它。
這樣的舞鶴,永遠不會是自傷自殘,自毀的。不要被他筆下那些精神病患變態狂躁鬱症者廢人給騙了,他們是巴赫金「狂歡節」的變貌,是舞鶴稱呼的,亂民。他所以對自己知識菁英的身份也反叛,不喜文學腔。大家都笑「文藝腔」,原來文學也會有腔。朱天心是說,撲鼻一股小說腔,像從前上學帶便當(飯盒)蒸打開時撲鼻一股子的蒸便當味。任何一種腔,舞鶴忍不住要嘲諷。他當然不殉於文學。
他是行動的,也是有生產力的。端看他出淡水後,遠離台北,遠離文壇,去島上的魯凱部落、泰雅部落常居寫作,以至我們初讀到長篇《思索阿邦.卡露斯》時大吃一驚,誰是舞鶴?驚豔的程度,不輸阿城八○後始知張愛玲。
《餘生》,是一次集大成,寫當代泰雅族的霧社,日本殖民時期的「霧社事件」,事件在當代的餘生。此書獲得太多獎譽,舞鶴儲存了不少「信用額度」,就大肆揮霍到長篇《亂迷》,不用一個標點符號的詩小說。是的亂民,舞鶴已走離現代主義很遠了。
現代主義極至精品的名單,前三位早已經有人列出來:納布可夫,喬艾思《尤里西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華年》。也早已在這現代小說的完美句點上往後瞻看,提出來小說的可能之夢,夢想名單前三位,兩位在南美洲,一位在義大利,他們是馬奎茲,波赫士,卡爾維諾。
我們站在大人的肩上,又可眺望到什麼?但也許得先問,這個我們是誰?那就再引述一段柏格的話收尾:
將事件化為語詞,就等於在找尋希望,希望這些語詞可以被聽見,以及當它們被聽見後,這些事件可以得到評判。上帝的評判或歷史的評判。不管哪一種,都是遙遠的評判。然而語言是立即的,而且並非人們有時錯以為的,只是一種手段。當詩歌向語言陳述時,語言會頑固而神祕地提出它自己的評判。這評判有別於任何道德典律,但它承諾就它接收到的聽聞範圍,做出清楚的善惡區別—彷彿語言本身就是為了保存這樣的區別而創造的。
我們,是的我們都是相信語詞,使用語詞,並誓願為做出此區別而日復一日在那裡打造作物的文學人。
五月太平洋岸聖塔巴巴拉,到處是大片大片芥子花黃到天涯的黃。這裡曾是郭松棻和他的文學伴侶李渝的蜜月之地,是白先勇〈樹猶如此〉與摯友終生不失的相守地,我與舞鶴,我們呢?
舞鶴是這麼說的,柔和、低的:「長年走在山中部落,已安於大自然的不回應。」
他的慷慨大度,他的光明磊落到任何、任何時候都沒有一絲烏雲飄過,又再一次,解除了我的張力。如果我們之間有一點點張力,不論是基於禮貌,基於共處一星期,基於良辰美景,基於長途旅行像流放,基於五月千樣種玫瑰漫開得滿牆籬滿拱窗,他讓我放心的可以都不回應。一定要記下這個,因為唯有在舞鶴前面,土象星座的訥顏訥語才會靈光起來似的,我高興得如同一個師妹對師兄說:「那就把我當成大自然吧。」
很無厘頭的。也只有對舞鶴,才能揮霍一下這種特屬於師妹所坐擁的驕矜配額。不是嗎,師妹一向被允許刁蠻的,而忠厚的師兄永遠寬容她。
二○一一年二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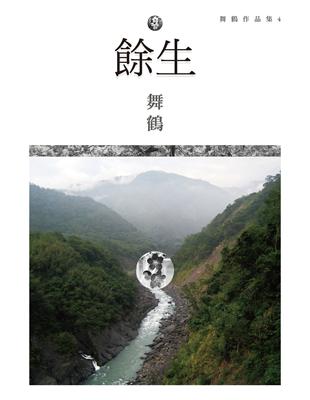












 瀏覽器,並以Chrome開啟我的電子書櫃後,點選『線上閱讀』,即可閱讀您已購買的電子書。建議使用 Chrome、Microsoft Edge有較佳的線上瀏覽效果。
瀏覽器,並以Chrome開啟我的電子書櫃後,點選『線上閱讀』,即可閱讀您已購買的電子書。建議使用 Chrome、Microsoft Edge有較佳的線上瀏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