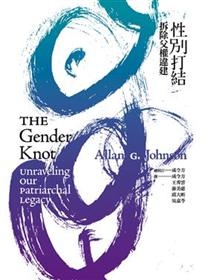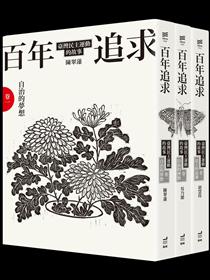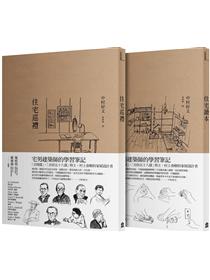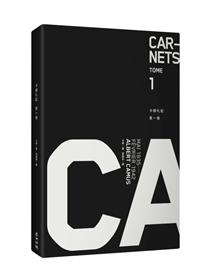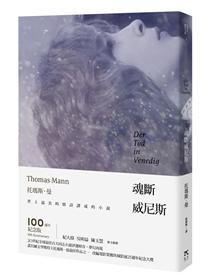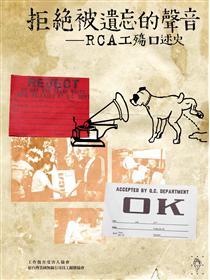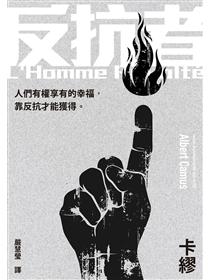Chalaw Basiwali《Polynesia》
知名樂評人 葉雲平
台灣。馬達加斯加。西班牙。
花蓮阿美族,非洲馬拉加西人,吉普賽佛朗明哥文化。
乍看之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幾組地域名詞或族群意涵,竟有什麼樣的因緣、能以一絲一縷緊緊串連,巧妙地,織就出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萬花圖像?唯獨音樂吧。音符與音樂,當是這股足夠跨界、跨越世間所有藩籬範疇的神秘力量。
相信熟悉或聽過 Chalaw作品的人,大都清楚,關於音樂上「跨」、「融」、「結合」之種種概念及作為,在過去兩張專輯《查勞‧巴西瓦里》(2007)、《老老車》(2009)之中,可說屢見不鮮,且驚喜迭起。Chalaw雖屬阿美族人,「樣貌」卻非意料之內 ── 所組樂團 Basiwali為南非+西班牙+漢族(+阿美)的大熔爐;歌曲除古調元素,尤大量揉現了 Bassa Nova、Latin、Reggae、Bluegrass……等各式同具「熱帶」或「熱情」性質的「外來」樂風,形成自己繽紛獨特、既世界又草根、「異國情調」濃厚的原住民在地鄉謠 ── 如此勇於嘗試的開放感,或源自居駐海濱的漁人本色:海納百川,魚網中大海賜予的漁穫,什麼可能性都有。
只不過沒想到,亟思突破的 Chalaw行至第三張專輯,竟將原本僅限土法煉鋼的「想像」,進一步大氣魄地「落實」:飄洋過海遠赴西班牙錄音,找來馬達加斯加傳奇音樂人 Kilema,以及西班牙吉他手 Isaac Muñoz Casado共同合作,打造出一張真切具國際化視野的世界音樂唱片。
素有「Soul of Madagascar」之譽、目前旅居西班牙的 Kilema,公認為當今推廣馬達加斯加音樂(文化)最力的代表性唱作人。長年巡演各地的他,曾受邀於2010年的台東「南島文化節」,由此與台灣音樂人結下緣分;此番擔起 Chalaw新作裡極重要的角色:不但負責主要編曲、參與合聲,精通多項(傳統)樂器的 Kilema,還親自演奏一些稀罕非常、甚至聽也沒聽過的非洲民族器樂。而另位舉足輕重的夥伴 Isaac Muñoz Casado,則是西班牙新一代頗具名氣的(佛朗明哥)吉他好手,同時操刀全輯的錄音及混音大任。
分別根植於亞洲、非洲、歐洲的原生音樂文化,彼此間會撞擊出怎樣的奇妙火花,是融匯或扞格?從開場曲〈藤〉就可獲致最精彩的答案:首先 Chalaw的聲音跟之前不一樣了 ── 隨著滿溢悠閒風情的曲調,變得…怎麼說…更慵懶、自由、遼闊起來……不知是否感受異地環境的影響?總之這有意思的化學變化,讓人讚嘆、難以想像是以台灣的邦查語在歌唱;待曲走中段,一陣像箏又似豎琴、清細透明的弦音搶出,那是 Kilema演繹的「Valiha」(竹管狀撥弦樂器),開始與佛朗明哥特有的女聲「呼喝」(Jaleo)及「拍掌」相互應和,上演一場殊異復絕妙的音樂對話。(另種樂音與 Valiha相近、但線條稍粗重的「Marovany」,則運用在〈安慰〉)。就像〈遠洋〉中急促唱著:「miliyas sado gami do lumaah daira e rumaay ah riyaarre mi fuding sado gami ah nini」(現在我們就離開家,前往未知的領域捕魚去),離開習慣的舒適圈,身體力行地實踐好奇的野心,才能享受不知將捕捉到什麼的興奮與成果。
而〈板模工人〉聽來歡快流暢,卻含精密複雜的編排,充分展現Kilema擅用多樣撥弦樂器(民謠吉他、古典吉他、烏克麗麗)去層層堆疊、製造節奏感 ── 旋律中有節奏,節奏又流露旋律 ── 的長處;裡頭除 Isaac Muñoz Casado高超的吉他獨奏外,也不忘利用大、小提琴增添曲式的豐厚度,堪稱內外雙全。此曲談的是 Chalaw(及許多原住民)早年上都市工作的親身經歷,滿不在乎的瀟灑唱詞,其實暗伏點點無奈;輕鬆的表達形式,悄悄反諷、提醒著我們反思社會底層的卑微與辛苦。
「玻里尼西亞」(Polynesia),希臘文的「群島」,意指佈於太平洋中、南部之大片島群,包括夏威夷、紐西蘭、大溪地、東加王國……等,也就是大洋洲 ── 專輯以此為名,自然指向台灣與大洋洲諸島,皆屬語言學中的「南島語系(族)」(甚有研究推定,玻里尼西亞人的遠祖為台灣原住民);而馬達加斯加,算是南島語系往西擴散得最遠的島嶼。即使眾多人類、地理學上的追溯理論,使得人與人、島與島、國與國之間,隱隱然產生了異族同源、一脈相承的文化網絡,但都比不上聽到由 Chalaw創賦骨架(詞曲)、Kilema與 Isaac Muñoz Casado填生血肉(編奏)的《玻里尼西亞》時,那些由音樂連結的「原來如此」的契合與置信感,那確實是一種遇見早已相熟的新朋友、既陌生又熱烈的親切;且三者不過分強調本體、節制中互顯自我特色的尊重,才謂真正世界一家。

角頭音樂 TCM
角頭音樂創立於1998年秋天,公司位在台灣首都士林的葫蘆島社區,由張四十三先生所創辦,那時他剛滿三十。「角頭」在台灣人的社會中,是指某個地方的「黑社會老大」。由於張先生的出生故鄉雲林,以出產「流氓」聞名,加上他從小就很憧憬於黑社會的傳奇神秘色彩,於是便取名為「角頭音樂」。
角頭做唱片的方式及態度,與一般的流行唱片公司相當迥異。角頭有著社會主義的理想性格,公司內部沒有階級之分,從不以合約箝制歌手的未來發展,給予歌手最大的音樂製作空間,且完全尊重每一個唱片環節的創意,如攝影、美術設計、文字..等等。希望能讓每一個階段的工作者,在唱片製作的過程裡,享受最大的創作喜樂。
Chalaw Basiwali《Polynesia》
知名樂評人 葉雲平
台灣。馬達加斯加。西班牙。
花蓮阿美族,非洲馬拉加西人,吉普賽佛朗明哥文化。
乍看之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幾組地域名詞或族群意涵,竟有什麼樣的因緣、能以一絲一縷緊緊串連,巧妙地,織就出一幅令人目眩神迷的萬花圖像?唯獨音樂吧。音符與音樂,當是這股足夠跨界、跨越世間所有藩籬範疇的神秘力量。
相信熟悉或聽過 Chalaw作品的人,大都清楚,關於音樂上「跨」、「融」、「結合」之種種概念及作為,在過去兩張專輯《查勞‧巴西瓦里》(2007)、《老老車》(2009)之中,可說屢見不鮮,且驚喜迭起。Chalaw雖屬阿美族人,「樣貌」卻非意料之內 ── 所組樂團 Basiwali為南非+西班牙+漢族(+阿美)的大熔爐;歌曲除古調元素,尤大量揉現了 Bassa Nova、Latin、Reggae、Bluegrass……等各式同具「熱帶」或「熱情」性質的「外來」樂風,形成自己繽紛獨特、既世界又草根、「異國情調」濃厚的原住民在地鄉謠 ── 如此勇於嘗試的開放感,或源自居駐海濱的漁人本色:海納百川,魚網中大海賜予的漁穫,什麼可能性都有。
只不過沒想到,亟思突破的 Chalaw行至第三張專輯,竟將原本僅限土法煉鋼的「想像」,進一步大氣魄地「落實」:飄洋過海遠赴西班牙錄音,找來馬達加斯加傳奇音樂人 Kilema,以及西班牙吉他手 Isaac Muñoz Casado共同合作,打造出一張真切具國際化視野的世界音樂唱片。
素有「Soul of Madagascar」之譽、目前旅居西班牙的 Kilema,公認為當今推廣馬達加斯加音樂(文化)最力的代表性唱作人。長年巡演各地的他,曾受邀於2010年的台東「南島文化節」,由此與台灣音樂人結下緣分;此番擔起 Chalaw新作裡極重要的角色:不但負責主要編曲、參與合聲,精通多項(傳統)樂器的 Kilema,還親自演奏一些稀罕非常、甚至聽也沒聽過的非洲民族器樂。而另位舉足輕重的夥伴 Isaac Muñoz Casado,則是西班牙新一代頗具名氣的(佛朗明哥)吉他好手,同時操刀全輯的錄音及混音大任。
分別根植於亞洲、非洲、歐洲的原生音樂文化,彼此間會撞擊出怎樣的奇妙火花,是融匯或扞格?從開場曲〈藤〉就可獲致最精彩的答案:首先 Chalaw的聲音跟之前不一樣了 ── 隨著滿溢悠閒風情的曲調,變得…怎麼說…更慵懶、自由、遼闊起來……不知是否感受異地環境的影響?總之這有意思的化學變化,讓人讚嘆、難以想像是以台灣的邦查語在歌唱;待曲走中段,一陣像箏又似豎琴、清細透明的弦音搶出,那是 Kilema演繹的「Valiha」(竹管狀撥弦樂器),開始與佛朗明哥特有的女聲「呼喝」(Jaleo)及「拍掌」相互應和,上演一場殊異復絕妙的音樂對話。(另種樂音與 Valiha相近、但線條稍粗重的「Marovany」,則運用在〈安慰〉)。就像〈遠洋〉中急促唱著:「miliyas sado gami do lumaah daira e rumaay ah riyaarre mi fuding sado gami ah nini」(現在我們就離開家,前往未知的領域捕魚去),離開習慣的舒適圈,身體力行地實踐好奇的野心,才能享受不知將捕捉到什麼的興奮與成果。
而〈板模工人〉聽來歡快流暢,卻含精密複雜的編排,充分展現Kilema擅用多樣撥弦樂器(民謠吉他、古典吉他、烏克麗麗)去層層堆疊、製造節奏感 ── 旋律中有節奏,節奏又流露旋律 ── 的長處;裡頭除 Isaac Muñoz Casado高超的吉他獨奏外,也不忘利用大、小提琴增添曲式的豐厚度,堪稱內外雙全。此曲談的是 Chalaw(及許多原住民)早年上都市工作的親身經歷,滿不在乎的瀟灑唱詞,其實暗伏點點無奈;輕鬆的表達形式,悄悄反諷、提醒著我們反思社會底層的卑微與辛苦。
「玻里尼西亞」(Polynesia),希臘文的「群島」,意指佈於太平洋中、南部之大片島群,包括夏威夷、紐西蘭、大溪地、東加王國……等,也就是大洋洲 ── 專輯以此為名,自然指向台灣與大洋洲諸島,皆屬語言學中的「南島語系(族)」(甚有研究推定,玻里尼西亞人的遠祖為台灣原住民);而馬達加斯加,算是南島語系往西擴散得最遠的島嶼。即使眾多人類、地理學上的追溯理論,使得人與人、島與島、國與國之間,隱隱然產生了異族同源、一脈相承的文化網絡,但都比不上聽到由 Chalaw創賦骨架(詞曲)、Kilema與 Isaac Muñoz Casado填生血肉(編奏)的《玻里尼西亞》時,那些由音樂連結的「原來如此」的契合與置信感,那確實是一種遇見早已相熟的新朋友、既陌生又熱烈的親切;且三者不過分強調本體、節制中互顯自我特色的尊重,才謂真正世界一家。

角頭音樂 TCM
角頭音樂創立於1998年秋天,公司位在台灣首都士林的葫蘆島社區,由張四十三先生所創辦,那時他剛滿三十。「角頭」在台灣人的社會中,是指某個地方的「黑社會老大」。由於張先生的出生故鄉雲林,以出產「流氓」聞名,加上他從小就很憧憬於黑社會的傳奇神秘色彩,於是便取名為「角頭音樂」。
角頭做唱片的方式及態度,與一般的流行唱片公司相當迥異。角頭有著社會主義的理想性格,公司內部沒有階級之分,從不以合約箝制歌手的未來發展,給予歌手最大的音樂製作空間,且完全尊重每一個唱片環節的創意,如攝影、美術設計、文字..等等。希望能讓每一個階段的工作者,在唱片製作的過程裡,享受最大的創作喜樂。

※ 二手徵求後,有綁定line通知的讀者,
該二手書結帳減2元。(減2元可累加)
請在手機上開啟Line應用程式,點選搜尋欄位旁的掃描圖示
即可掃描此ORcode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