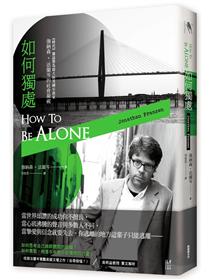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馬奎斯最喜歡的作家格雷安‧葛林的旅遊名作
一場宛如跌落地圖之外的旅程,處處驚險卻奇異無比!
非洲,被上帝遺棄的黑色大陸,
墮落、殘暴、卑微、晦暗、野蠻、荒蕪,是被深深烙印的符號!
幾世紀以來,多少探險家、文學名家都視她為冒險天堂,
他們用雙腳行旅,用心眼去凝視,也用筆書寫著她。
在這兒,永遠有未完的故事等待著被訴說下去。
二十世紀的文學大家格雷安‧葛林筆下的經典旅遊作品《沒有地圖的旅行》,訴說的是屬於一個沒有地圖標記的國度,賴比瑞亞的故事。
一場買不到地圖當導引的奇異旅程
一九三五年,格雷安‧葛林在表妹陪同下,徒步旅行賴比瑞亞。葛林對這趟旅程沒有絲毫概念,但他還是懷著忐忑恐懼的心情上路。
賴比瑞亞,位於非洲西南角,往上接鄰法屬幾內亞與獅子山,全境幾乎完全被森林所覆蓋,過去從未做過妥善的地圖測量,就連要找份資料概略了解這個國家的地理樣貌都是奢望。唯一市面上能找得到的兩份比例尺過大的地圖,一份由英國參謀部印行,這份可謂公開招認它的無知,地圖上賴比瑞亞多數領土呈現空白,上頭的虛線顯示僅屬臆測的河流走向;另一份由美國戰爭部印行,它則似乎在召告人類的想像力可以完全地天馬行空。
在這樣一個國家,旅行的唯一方式是查出下一個村莊或城鎮的名字。
下一個地方是哪裡?
在這兒,所謂的「路」,是濃密森林裡寬僅一呎的小徑,更具興味的是,一個人只要延著小徑走,就可以跨越一座大陸。西方文明的時間感在此地並不存在,腳程成了距離的量尺;只有旅行到這個村落,才知道下一個旅遊地是哪裡?對於葛林而言,他們跋涉過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從這個村落穿越那個村落,他發現山丘、溪流、集會堂、打鐵工坊、天黑時有人會提煤塊到各村民家供取火、在茅屋間走動的牛羊牲畜……是這些村莊共有的景象,然而,又沒有任何村莊是真的一模一樣。
此地的財富與快樂無需外求,屬於大自然的棕櫚仁遍地皆是,而他們的快樂和笑聲則似乎是大自然中最勇敢的元素;這裡的人對小孩非常溫柔,大人們之間也用一種低調且不言自明的溫和方式相互對待。
隨著旅程的推進,葛林訝異於西方文明的偏執與價值觀在這地方是多麼容易被放下。
回想在殖民保護地的獅子山市集眼見原住民的勞苦景象,葛林還犀利地批判:「當西方社會在吶喊”勞工大團結”的口號的同時,獅子山的鐵路工人每天卻只能領到六便士的工錢,連糊口都難,又有誰看到這些滿口勞工大團結的人士為此罷工抗議?在這裡,文明依然是以壓榨的形式存在。我們又憑什麼假裝自己是在談整個世界?」
然而,行走在賴比瑞亞的村落間,葛林那”旅人”的焦慮與不安,也慢慢轉換成隨遇而安。如書中有一段描述卡車從凱拉渾出發以後,原以為時間和行程的進行都能如預期順利,一路到達蒙羅維亞,經過四個星期的折騰,葛林人還在賴比瑞亞境內某個連聽都沒聽過的地方……事情開始變得複雜了……那是一種缺乏經驗的旅人感受到的焦慮,它造成的無謂的壓力也使得挑夫們對葛林失去了信任感。「後來我才學會對一切不要那麼在乎,就只要一直往前走,走夠了就停下來休息……」
沿途的旅程中,葛林撿拾各種線索,那可能是某種記憶,或某種痛苦……非洲好像在告訴葛林:「你無法逃避非洲,它無處不在,它爬在牆上,從門口飛入,在草堆裡沙沙作響,你沒法回頭也沒法忘記,所以,不如就好好凝視它吧!!!」
作者簡介:
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
出生於一九O四年。牛津大學貝列爾學院(Balliol College)畢業後,在《泰晤士報》(The Times)擔任助理編輯四年。他出版的第四本小說《伊斯坦堡列車》(Stamboul Train)使他聲名大噪,隨後他在一九三五年進行跨越賴比瑞亞的探險壯遊,並將所見所聞描繪在《沒有地圖的旅行》一書中。返回倫敦以後,獲《旁觀者》(Spectator)雜誌聘請擔任影評人。一九二六年時,葛林被正式接受為羅馬天主教會一份子,並在一九三八年赴墨西哥訪查報導當地的宗教迫害情況。他將探訪結果撰寫成《不法之途》(The Lawless Roads)一書,後來又根據那次的閱歷寫出著名小說《權力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葛林在一九三八年出版《布萊頓棒棒糖》(Brighton Rock),一九四零年他成為《旁觀者》雜誌文學編輯。次年,他開始為英國外務部服務,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間被派駐於獅子山。這個駐外經驗後來構成《物質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的背景脈絡,該小說的場景即設定在西非地區。
葛林除了出版過多部小說,還完成數部短篇小說集、四本旅行見聞錄、六部劇本、三本自傳——《某種人生》(A Sort of Life)、《遁逃的方式》(Ways of Escape)和遺作《我所獨有的世界》(A World of My Own)——、兩本傳記,以及四本童書。他也寫過數以百計的散文、影評及書評,其中一部分撰述集結成《思索》(Reflections)、《黑暗中的早晨》(Mornings in the Dark)等文輯。他的許多長篇及短篇小說都被拍成電影,而《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則是專為電影創作而寫成的作品。葛林以其傑出成就獲英王授予功績勛章(Order of Merit),並獲頒皇家榮譽勛爵(Companion of Honour)封號。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告別多采多姿的人生舞台。
譯者簡介:
徐麗松
台大外文系畢業,世紀交替之際旅居法國多年,陸續於巴黎第七大學、里昂第二大學及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修讀語言學及跨文化研究,並在法國及台灣從事英文、法文翻譯及跨界合作工作。
章節試閱
西賴比瑞亞
森林的邊緣
時值正午。我們跟著一位海關人員走進一間茅草寮,坐在又高又不舒服的扶手沙發座椅上抽菸。一個黃棕色皮膚的小個子男人坐在我們對面的吊床上,他也在抽菸,一邊抽一邊前後晃蕩。我朝他微笑,他也報以微笑;那是一種做樣子的笑容,裡面絲毫不含友善的成分。那人正在思考他可以敲多少竹槓;我則在衡量自己可以避免多少損失。一名婦女帶了一位小朋友進來看白人,小朋友看了以後尖叫了起來,無法控制地不斷尖叫。邊區部隊的士兵四處閒坐著,在垂直照射的火熱陽光中隨意吐痰。被烤成焦褐色的地面看起來幾乎就要龜裂。我點燃第二支菸。
然後拉米納衝了進來,像一顆充滿火爆氣息的小炸彈被投入百般寂寥、凝結不動的時空中。他那副模樣彷彿一隻哈巴狗被一隻亞爾薩斯牧羊犬欺侮了似的。有人告訴他,他得為他身上穿的那件有橡膠襯裡的白色理容師外套付關稅。海關人員後來還算客氣地在這點上讓了步,不過這件小事似乎釋放出一個信號:接下來我們還有得樂呢。我伸手拿出相關發票,德國佬打開一個小皮箱,付了兩先令半的稅;海關人員急著鎖定更大的獵物,於是德國佬很快就得以出關,他的身子在挑夫頭頂上晃動著逐漸遠離。接著,海關人員開始把焦點放在我的發票上,旁邊的士兵們邊吐痰邊露出詭異的笑容,我則是忙著拂去額頭上的汗水。
「這得花一整天處理呢,」海關人員說。「這些東西裡面除了愛生(Epsom)浴鹽、奎寧和碘藥水以外,其他都要付關稅。」他又說,如果我願意留下一筆保證金,我就可以馬上前往博拉渾,他們算清楚以後會把剩下的錢寄還給我;根據他的估算,留個四鎊十先令當保證金應該就夠了。我從錢箱裡取出一個裝六便士硬幣的錢袋,並小心地不讓旁人看到錢箱的密碼。不過事情到此並未完全結束。他們拿出八張表格,準備用來詳細填寫我的應稅物品,這些表格不是免費的,我每張都得付兩分錢。我買了兩張印花稅票,然後還得在每張空白表格下方簽名,證明表格所列物品全部屬實。我被迫將自己完全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想在表格上填甚麼就可以填甚麼。我的另外一個選項是在海關待一整個晚上,讓他們打開我所有的包袋和箱子,仔細檢查所有內容物。
結果我還是沒法輕易脫身。隔天,那個海關人員派了一名士兵到博拉渾找我,要求我再付六鎊十先令;我讓士兵空著手回去,結果海關那人親自來了,他坐在吊床上,讓四名挑夫從佛亞把他一路扛到博拉渾,另外還有幾個士兵陪著走這段漫長而辛苦的路。他的頭上戴了一頂骯髒的草帽,嘴角刁了一根嚼爛了的菸。他大搖大擺地走過門廊,整個人一副尖酸刻薄、貪婪無恥的模樣,他的笑臉揉合了憤怒、堅決,和一種造作的友善。他拿了錢,喝了兩杯威士忌,抽了兩根菸;我們無能為力,這時想用小錢賄絡他是不可能的,想必這種官員已經很習慣從他們詐取的保證金裡大肆抽成。
我非常喜歡進入賴比瑞亞以後第一天旅途的所見所聞,因為一切都很新奇。與黑夜爭時間的情景充滿快感,溫熱開水的味道相當有趣;甚至連挑夫的氣味也頗為迷人:那是一種不甜膩也不酸臭,不會令人不舒服的氣味;它有點苦苦的,讓我想起小時候有一次得胸膜炎之後所吃的早餐裡頭的一種東西,那東西說是可以增強體質、促進活力,不過我不喜歡吃。這種苦苦的氣息混合了挑夫從地上撿起來直接咀嚼的可樂果濃郁的李子氣味,偶而還隱約摻雜著從各種植物競相生長的雜亂綠野中飄來的不知甚麼野花的香氣。隨著溫度升高,那所有氣味都像蒸氣從潮濕的土壤冒出一般,逐漸鋪陳了出來。挑夫們除了在腰間掛了一塊布以外,身上甚麼也沒穿,汗水在他們油亮的黑色肌膚上留下彷彿蝸牛爬過的痕跡。他們的樣子並不雄壯,完全沒有拳擊手那種醜陋不堪的肌肉;他們的腿像女人的腿一樣修長,可是最底下卻是平板狀的典型「挑夫腳」,有如大大的空手套像蔥油餅般坦開在地面,讓人感覺他們身上背負的重量毫不留情地把他們的腳壓扁了。他們的手也是非常地纖細,跟小孩子的手差不多,而且當他們調整頂在頭上的五十磅重的箱子以求舒適時,手臂幾乎不會因為使力而膨脹,繃在那上頭的肌肉就跟鞭繩差不多細。
賴比瑞亞共和國幾乎完全被森林所覆蓋,一望無際的森林一路伸展到距離海岸僅僅數哩處。我們現在是位在這片巨大森林的邊緣;經過佛亞的邊界檢查哨和賴國境內第一座村莊,我們開始爬上陡峭的山坡,往回一望,我們看到在腳底下的村莊茅屋後方,濃密的森林像一道水勢凌亂的大瀑布般起伏不定地朝大海的方向流去,漸漸化成綠毯般的平原。森林彷彿綿延數百哩,高大的棕櫚樹突立於其間,彷彿矗立在城市天際線上的煙囪。這裡的茅屋跟在整個邦德地區一樣,都是建成圓形,尖尖的茅草屋頂覆蓋著斑駁的土牆,土牆下半部塗上了白漆。房子有一個門,有些也有一扇窗戶;室內只有一個房間,地板中央有一堆柴灰,日落時分,居民會從一塊社區共用的煤塊取火,重新點燃它;燃燒的煙氣有防蚊的效果,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驅趕跳蚤、蟑螂和其他害蟲,不過趕不走老鼠。這些村莊大同小異,都是分成好幾個層次建築在山坡上,類似歐洲的中世紀小鎮;林間小徑忽然陡降至溪谷,村民便是在那裡洗衣、沐浴或取水使用;然後小徑又驟然往上攀升,變成一條比較寬闊的硬泥路,穿出密林後,眼前出現另一座村莊的形影,尖頂茅屋聳立在正午的烈日下。村莊的地面彷彿乾燥的河床,有流水刻劃的痕跡。村莊中央是集會堂,村莊邊緣會有一間打鐵工坊,這兩棟茅屋都是沒有外牆的開放式建築。
我待過的所有村莊幾乎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徵:山丘,溪流,集會堂,打鐵工坊,天黑時有人會提到各個村民家供人取火的煤塊,在茅屋間走動的牛羊牲畜,有如一堆高大的綠色羽毛般聚積塵土的香蕉林。不過,沒有一座村莊跟任何其他村莊真的一樣。白天我們在雜亂無章、缺乏美感的森林中跋涉七個小時以後,在傍晚時分來到下一個村莊過夜;日復一日,我們經過的每一個村莊都讓我感到興奮。我可以感覺到每個村莊裡都住了一小群勇敢的居民,他們以幽微的方式存在於濃密的樹海之中,過於猛烈的陽光使他們難以正常勞動,可怕的黑夜裡充斥著惡靈;愛情化約為攀在頸邊的一隻手臂、煙霧迷漫之際的一個靦腆擁抱;象徵財富的是一堆棕櫚仁;老年就是一身病痛和痲瘋。至於宗教則是由一堆石塊、一叢林木和一個戴面具男人共同構成;死去酋長的靈魂飄盪在村落中央的石推中;禾花雀在林中築巢,牠們的長相有如黃綠相間的金絲雀;舉行葬禮時,面具男子會穿上椰纖裙跳舞。這些特性在所有村莊中都如出一轍,如同他們對陌生人的友善,他們的極端窮困,以及他們感受到的那種如影隨形的恐懼。他們的快樂和笑聲似乎是大自然中最勇敢的元素。我過去總是聽人說愛情是由中世紀歐洲的吟遊詩人所發明的,但在非洲,愛情無需文明的贅飾就無處不在。這裡的人對小孩非常溫柔(除了小孩看到白人時會哭以外,我從沒聽到小孩的哭聲;我也從沒看過小孩子挨大人揍);大人們之間也用一種低調且不言而明的方式溫柔地互相對待。他們從來不會叫罵打鬧,不會像歐洲的窮人那樣透過尖銳的言語和粗暴的舉動表達他們的絕望。一個人身處其間,無時無刻不會感受到一種責任,要求自己的行為必須符合當地的禮儀標準。
然而海岸地區那些商務代表和騙徒竟然跟我們說非洲人不可靠。「黑人老愛敲竹槓。」你再怎麼跟那些自命清高的人理論也沒用。事實上,在我們接觸到的僕役、挑夫,和內陸各地的居民中,沒有任何人對我們不老實;他們表現出來的親切、和善和誠實在歐洲甚至是找不到的,我們根本不敢妄想歐洲人能夠有這樣的特質。我在一個沒有警察管制的國家跟二十五個當地人一道旅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們都很清楚我的錢箱裡裝的銀幣對他們而言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我卻能平安順利地往目的地行進,這點讓我非常驚訝。我們現在畢竟不是在英國或法國的領土範圍內,要是我們失蹤了,海岸地區的賴比瑞亞黑人政府不會在乎,而且他們就算在乎,恐怕也無能為力。我們甚至不能算是有武裝;自動手槍藏在錢箱裡,既沒有裝子彈,也沒人看得到它的存在;一路上有許多用纖維繩搭造的橋,要是真有人打我們主意,很容易就可以在我們過橋的時候製造假事故。就算不採取那麼極端的手段,有心人士還是很容易故意把錢箱「搞丟」,或在森林中跟我們「走散」。
不用猜也知道,海岸地區那些白人心裡在暗想,「可憐的蠢蛋,他連自己是怎麼被耍的都搞不清楚。」可是我並沒有被耍。每到一個村莊,我所有的家當都會在我住的茅屋裡四處亂擺,肥皂(這對他們來說可是非常珍貴的東西),刮鬍刀,牙刷……一大堆村民隨時都會進出茅屋,可是從來沒有任何東西被偷。「你聘用一個僕役十年再說吧,」海岸白人又會說,「到時看你怎麼被敲。」說完他們會把喝完的空酒杯放下,走到外頭陽光刺眼的街上,回到他們店裡,看他們可以用甚麼辦法「敲」他們的客人。「不講感情,」他們又會說,「做了十五年,一點真正的感情都沒有。」他們只付給那些人那麼一點工資,卻指望從他們身上得到更多。他們只是付錢請當地人提供服務,但卻認為那些人應該大肆回報以真情。
我以為五點鐘應該會抵達傳教基地,結果五點鐘時,我們到的地方只是又一座山丘,又一片茅屋和石堆,以及下方濃密依舊的森林。棉捆被擱在茅屋外頭風乾,一棵小樹上有一朵花在風中抖動,嬌弱的身影映襯在天空中。有人指點出傳教基地給我看,那是一棟白色建築物,西斜的陽光把它的形影從林木間勾勒了出來。到那裡至少還需要走兩個小時,看樣子這會是旅程展開以來與黑夜賽跑最激烈的一刻,而經驗告訴我,黑夜總是要跑贏的。我們出了森林、蜿蜒在莫桑博拉渾山腳下的香蕉園中時,黑夜忽然就籠罩住我們了,我們走在小茅屋之間,天色已經很暗,空氣也冷起來了,身穿白色回教長袍的老廚師抓著一隻捆綁好的雞走在最前頭。茅屋裡都已經生了火,炊煙被風吹過狹窄的通道,刺痛了旅人的眼睛;但那些小小的火焰流露出家的感覺;這些非洲村莊裡的微弱燈火跟英國鄉村房舍的紅色百葉窗板後頭透射出來的燈光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莫桑博拉渾大概有將近兩百棟茅屋,這些房子簇擁在一座小岩山上,村莊缺乏整頓,散發一股邊陲的異教氣息,跟山腳下開發過的平原地帶上那個已經基督教化、花木扶疏的整潔村莊博拉渾兩相對照,幾乎可說是天壤之別。一條寬敞的硬土路往下穿過平原通往博拉渾,路上出現一批喧鬧的男人,是一群挑夫正扛著吊床搖搖晃晃地走上山來。一行人在我身旁停了下來,吊床上坐著的是一位年紀很大的長者,他穿著本土布料製成的長袍,留了長長的白鬍子,向我伸出一隻手。他是莫桑博拉渾的酋長,年紀九十歲了,他身體顫動著露出微笑,他的村民則站在他的四周聊天。他一個英文字也不會說,不過站我身邊那個帶槍的小伙子告訴我,酋長剛從泰拉渾回來,他到那裡參加另一位酋長的葬禮去了。急著下工的吊床挑夫很快又把他抬上路,他揮著乾癟的手,和藹地笑著,笑容中夾雜著好奇和迷惑。我後來發現,莫桑博拉渾之所以髒亂落後,多少是因為他的關係;他其實已經不再握有實權,只是年輕一代的魁儡。他大約有兩百個妻子,可是村民會把同樣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賣給他,反正他已經老得算不清楚了。他知道自己年紀太大了,所以他很想找個年輕人接棒,可是這個沒有章法的村莊不方便失去他這個傀儡。當他開始變得囉哩八嗦時,人們乾脆給他封個「主教」頭銜,他倒也心花怒放,樂在其中。
從博拉渾村出發往山上走兩英哩路,穿越一片青蛙叫得猛的林地,才會到達傳教基地。傳教基地隸屬於聖十字會,那是美國聖公會底下的一個修會。我把行李丟在長屋外面,等牧師結束祝禱儀式後走出來。我可以聽到裡面有拉丁文的低喃聲;一片漆黑中,我只看得到挑夫們的白色眼珠子,他們安靜地蹲坐在門廊前,累得不想說話。可是那拉丁文的音韻所代表的文明優於海岸上英國人開設的港埠和那裡的鍍錫鐵板屋,優於我在獅子山見過的一切;牧師們走了出來,其中一人把我帶到小賓館,他的白色袍子在凜冽的山風中飄盪,這時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可以不帶羞恥地在白人與黑人之間進行比較。在這個謠傳中充滿貪污與奴役的共和國裡,在這個偏遠的角落,至少存在著某種完全不具商業色彩的特質。我想這樣的讚美應該是再恰當也不過的了:這一小群白人男女牧師顯現的溫和有禮與誠實無欺,跟當地人達到了相同的標準。至於他們帶來的那種上帝被釘上十字架的意象是否比當地人的物品膜拜來得高明,這個問題就留待未來再做臆測吧。
那天晚上,在四壁如洗的小屋裡,水在過濾器裡不斷滴流,我付了錢把挑夫打發走以後,打開裝威士忌的箱子,然後走到外頭找梵谷——也就是生病走人了的C的合夥人。這個探勘員的帳篷就在我待的房子外邊,那裡頭有一盞防風燈點亮著。「那個梵谷啊,」稍早牧師告訴過我,「你會喜歡他的。」當我看到帳篷旁邊一堆箱子上頭放了一根虹吸管,我心想我可以請他帶他的蘇打水到我屋子裡一起喝一杯。我把遮簾拉開,看到梵谷躺在他的露營床上,身上包著毯子;我想他大概是睡著了,可是他轉動頭部的時候,我看到他正在冒汗。五個小時以前他開始發燒,那一整個晚上,被派到傳教基地服務的德國醫生都陪著他。他的情況非常糟;他一輩子都在熱帶國家度過,可是卻是在賴比瑞亞待九個月以後倒下了。隔天他被人用吊床抬著送到小小的基地醫院;他在戈拉森林的金礦場聘用的年輕工人過來打包他的帳篷和物品,然後把他抬下山,他病得重,虛弱的身子在烈火般的陽光下隨著吊床搖晃。
博拉渾的星期天
這天是博拉渾的星期天,這點絕對千真萬確。一個牧羊人把他的山羊群從岩石間趕出來,那情景簡直像是直接從聖經裡迸現出來的畫面。每場禮拜進行時鐘聲都會敲響,我看到五個修女排成一列走過村莊與香蕉田,她們戴著遮陽帽與面紗,手裡拿著祈禱書。她們是英國人;對她們而言,這裡的午茶時光(一大塊水果蛋糕,自製橙醬,被豔陽曬得憔悴不堪的巧克力餅乾,還有一種以棕櫚酒取代酵母製成的美味可口但難以消化的麵包)跟在英國任何一個主教座堂城鎮喝茶沒甚麼兩樣。那是一個屬於英國的角落,身為英國人,在那裡不禁會感到一股驕傲;那裡面摻雜了溫柔、慈悲、虔誠、稚氣與無私,而且身處其中的人對其間透射出來的堅韌與勇氣渾然不覺。我忍不住把這些大約生活在歐洲勢力保護範圍之外的修女拿來跟自由城的英國人做比較;自由城那些人享有電燈與冰箱,經常度假,瞧不起本地人,又成天自憐自艾。
關於傳教士,許多人寫過一大堆無稽之談。傳教士經常要不是被描述成帝國主義者或商業壓榨者的走狗,就是被抹黑為一群在性方面不正常的人,設法讓原本樂天知命的異教徒改信歐洲的宗教,從而受制於歐洲人的種種壓抑。一般人似乎都已經忘記基督教是源自東方的宗教,當年其實是西方的異教徒受到感化而皈依基督教的。傳教士甚至會被認為不具有邏輯思辯能力,因為如果一個人虔誠信仰基督教,他必然相信它的普世性真理;基督徒不可能在歐洲信仰某個神,在非洲又信仰另外一個神。發源於閃族地區的宗教傳統一直有一個核心概念,那就是它不會為東方認可某個神,為西方又認可另一個神。西方世界的新興異教流派以合乎科學自居,其實經常是神經質得離譜。這種新的信仰缺乏思想一致性,而且流於濫情,它接受回教徒用刀劍傳教的「歷史責任」,卻不認同基督教徒透過教導傳播信仰的責任,這樣的心態只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神經有毛病。
當然,在賴比瑞亞共和國內陸進行的傳教工作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它完全不受政治或經濟勢力所牽制。賴國黑人政府對傳教人員不信任,而沒有一家歐洲公司在該國內陸地區設有交易站。美國修士和英國修女如果選擇到博拉渾傳教,唯一的動機是他們對基督教的堅貞信仰。他們面對熱病、蚊蟲、老鼠的肆虐,但並沒有精彩華麗的冒險可以做為相應的補償;他們唯一冒的險,是被蛇咬和被疾病侵襲。他們不是那種以剛毛襯衣及束繩禁錮自己以獲得精神滿足的苦行僧;他們在博拉渾安頓下來以後,就盡可能把生活打點到一定的舒適程度。神父們蓋了一座小醫院,他們向福南梅森訂購食品,從法國屬地買進葡萄酒,蔬菜則是每個月從獅子山運來一次;他們甚至蓋出一座簡易式硬土網球場。他們沒有強迫當地人信基督,沒有要求那個赤裸著身體的快樂民族穿起衣服,沒有阻止他們跳土著舞蹈。西非所謂「土著」只要有錢,向來都會買衣服穿,如果有長袍可穿,他們絕不會堅持只綁一塊纏腰布,而任何外人只要待在叢林村莊中生活過一段時間,都會知道一件像樣的袍子就算用料再怎麼粗陋,都要勝過暴露出皺巴巴的乳房和流膿傷口的赤裸軀體。至於土著舞蹈和物品崇拜,傳教士就算希望當地人放棄這些習俗,他們也沒這個權力;在這裡,基督教畢竟還處於邊緣,歸依基督教的人口相對少,而且信基督也沒有甚麼物質上的好處;唯一的好處是精神上的,是可以從某些恐懼中獲得解脫,並得到某種無形的希望。
特別是在博拉渾,信仰基督教真的沒有任何物質上的好處。白種人在賴比瑞亞不被允許擁有土地,傳教工作受到政府的牽制,而且地區監委利弗斯先生就住在僅僅九英哩外的柯拉渾。利弗斯先生是個瓦依族人,也是個回教徒;在心理層面上,他還停留在十九世紀早期的奴隸交易時代。他痛恨基督教徒,痛恨白種人,尤其是痛恨英語。他那海豹灰的膚色,不帶情緒的深色眼睛,飽滿的深紅色嘴唇,頭上戴的菲斯氈帽和身上穿的本土布料長袍,在在都使他流露出某種結合了殘酷與感官質地的奇異樣貌,一種不是那麼地非洲、而比較有近東風味的神態。他粗鄙、無情而腐敗。他的妻子人稱「巴克萊小姐」,出身總統家族,根據當地人的說法,總統任命他擔任地區監委時向他承諾他可以終身享有這個職位。他先是被派到國土另一端的沙諾奎雷,在那裡發生過的一個事件如影隨形地跟著他來到柯拉渾;據說有一批曼丁卡商人在賴比瑞亞和法屬地之間進行走私被他逮到,結果他把他們關進一間茅屋放火燒死。這種傳言的真實性如何,在賴比瑞亞是不可能調查出來的,不過我倒找到許多證據,足以證明其他一些關於他透過殘酷手段進行暴力統治的事例,例如:他為自己蓋的房子是動用強迫勞力完成的,蓋房子的錢則是來自沒收老百姓辛苦種出來的食糧;他的隨從會任意毆打在路上勞動的工人;信奉基督教的博拉渾居民沒有人敢在他直接管轄的村鎮露面等等。有一天修女們看到他坐在吊床上經過,他的隨從竟然拿鞭子鞭打挑夫,令他們快步前進。許許多多這類故事陸續傳到辛苦徒步十天才到得了的蒙羅維亞,賴國政府終究沒法不予理會,而就在此時,總統本人正在前往柯拉渾的路上,到那裡聽取該地區酋長們的抱怨。
我們必須理解這樣的時空背景,才能知道那座醜陋的鍍錫鐵板屋頂教堂裡的祝禱儀式是怎麼一回事。高舉的聖物盒代表的並不是甚麼特別強有力的政治象徵:「信我吧,所有那些受苦受難的人,我將為你們帶來商業優勢,為你們在國務大臣耳邊說好話。」就像古代的早期基督教一樣,它提供的是一種掌權者的支持,殊知那些偶像崇拜的教士將施加甚麼樣的秘密壓迫。祝禱儀式沒有很多人參加:在這裡,基督教還算是一股屬於極少數人的革命力量,它吸引的不是老人,而是某些年輕人,而年輕人這時正在放假。一個身形嬌小的黑人小孩只穿了一件很短的透明襯衫,他一邊祈禱一邊抓癢,還把襯衫往上拉到肩膀,以便好好搔到後背的癢處;一個只有一隻手臂的少年跪在一幅難看的漆畫下方。(他在棕櫚樹上採果子時摔了下來,把一隻手臂摔斷了,後來他覺得手臂盪在那裡沒啥用,居然拿了一把刀,把它從手肘處斬斷。)
西賴比瑞亞
森林的邊緣
時值正午。我們跟著一位海關人員走進一間茅草寮,坐在又高又不舒服的扶手沙發座椅上抽菸。一個黃棕色皮膚的小個子男人坐在我們對面的吊床上,他也在抽菸,一邊抽一邊前後晃蕩。我朝他微笑,他也報以微笑;那是一種做樣子的笑容,裡面絲毫不含友善的成分。那人正在思考他可以敲多少竹槓;我則在衡量自己可以避免多少損失。一名婦女帶了一位小朋友進來看白人,小朋友看了以後尖叫了起來,無法控制地不斷尖叫。邊區部隊的士兵四處閒坐著,在垂直照射的火熱陽光中隨意吐痰。被烤成焦褐色的地面看起來幾乎就要龜裂...
作者序
這本書寫成六年以後,我居然成了獅子山的居民——作家真該小心自己在承平時期選擇前往什麼地方度假娛樂,因為一旦發生戰爭,他很可能會在因緣際會下回到那裡工作。飛機從拉哥斯起飛,在高空中沿著賴比瑞亞海岸前行。我俯瞰那綿延至天際的白浪拍岸景象,內心湧起一種奇特的感覺。我又看到那個由一堆簡陋小屋簇擁而成、名叫「大巴薩」的地方,我曾經在那裡解散與我同行的一群挑夫。飛機又飛過一座孤立的白色小建築物,那是英國設在蒙羅維亞的領事館。我的目光從蒼空往下尋溯我從自由城到凱拉渾的行旅足跡,看到同樣那種用燈泡照明的小火車,同樣那些供旅人歇腳的客棧,一股奇特感受又在心中油然而生。
當我回顧那一切,我不禁為自己當年描述自由城的苛刻字眼感到些許遺憾,因為現在的自由城已經成為我走過春夏秋冬、長期工作生活過的異鄉家園之一。當年我旅行到那裡時,曾經非常嚴厲地譴責周遭人們慵懶怠惰的劣根性,但當我自己在那裡待上一年以後,我竟也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同樣的特質。儘管一個旅人若只是路經某處,經常會落入一些謬論的巢臼,在當地住久的人在熟悉那個環境以後,倒也難免演繹出另一套謬論。然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澱,我們將不再留意許許多多的細節。若要現在的我再次提筆描述自由城,想必我描繪的畫面將美好得異常造作,因為我對自由鎮的記憶,已經開始主要只呈現在幾個詩情蕩漾的情景:燦爛的日落時分,所有紅土小徑在數分鐘時間裡驟然染上玫瑰的色澤;從前關奴隸的老碉堡前,一具大砲靜謐地斜躺在草地上;荒廢的鐵道,空無一人的殘破小火車站,雞隻在其間穿梭覓食;向晚六點,下班後第一杯粉紅琴酒的動人滋味。我開始忘記在偶然到訪的過客眼中清晰可見的一些事——無以言喻的骯髒污穢,疲憊眾生的不快樂及他們不由自主的造孽行徑。然而,由於這幅畫面終歸也是真實,我決定讓它繼續展現在讀者眼前。
倫敦,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這本書寫成六年以後,我居然成了獅子山的居民——作家真該小心自己在承平時期選擇前往什麼地方度假娛樂,因為一旦發生戰爭,他很可能會在因緣際會下回到那裡工作。飛機從拉哥斯起飛,在高空中沿著賴比瑞亞海岸前行。我俯瞰那綿延至天際的白浪拍岸景象,內心湧起一種奇特的感覺。我又看到那個由一堆簡陋小屋簇擁而成、名叫「大巴薩」的地方,我曾經在那裡解散與我同行的一群挑夫。飛機又飛過一座孤立的白色小建築物,那是英國設在蒙羅維亞的領事館。我的目光從蒼空往下尋溯我從自由城到凱拉渾的行旅足跡,看到同樣那種用燈泡照明的小火車,...
目錄
第二版作者序
第一部
1. 非洲之路
2. 貨輪啟航
3. 第二故鄉
第二部
1. 西賴比瑞亞
2. 總統閣下
3. 深入布吉人居住區
4. 黑色大陸的蒙帕拿斯
第三部
1. 傳教基地
2. 「文明人」
3. 大巴薩的獨裁者
4. 最後衝刺
5. 蒙羅維亞後記
第二版作者序
第一部
1. 非洲之路
2. 貨輪啟航
3. 第二故鄉
第二部
1. 西賴比瑞亞
2. 總統閣下
3. 深入布吉人居住區
4. 黑色大陸的蒙帕拿斯
第三部
1. 傳教基地
2. 「文明人」
3. 大巴薩的獨裁者
4. 最後衝刺
5. 蒙羅維亞後記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6收藏
26收藏

 50二手徵求有驚喜
50二手徵求有驚喜



 26收藏
26收藏

 50二手徵求有驚喜
5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