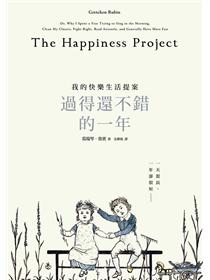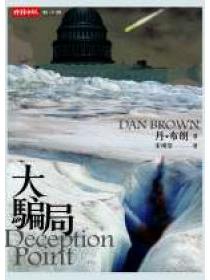保羅擁有雙性性徵,也就是俗稱的陰陽人。他從小被當成女孩撫養,取名為德妮絲。隨著年齡漸長,保羅自覺像是住在德妮絲體內的囚犯,他渴望掙脫身心的雙重枷鎖,成為真正的男人。《頭朝下》是真人真事改編的一本小說,以雌雄同體以及性別認同為主題,更是文學史上僅見的創作。本書已榮獲2002年DS期刊社會書卷獎。一個人頭朝下看的時候,會看到一片混亂,也會看到真實的場景……。──薇薇夫人(作家/畫家)夏特雷乃當代法國主要作家,她在《頭朝下》這部罕有的絕世精品級的作品裡,把當代「身體書寫」和「邊緣書寫」,帶到了一個非常成熟的水準。──南方朔(文化評論家)拿到文稿的那個晚上,是以帶著激盪又狂喜的心情一口氣看完本書,好久好久沒讀到這麼令我感受到情慾不斷在字裡行間挑動我的文字,透過天使保羅的開釋,《頭朝下》將為每個讀者開啟另一扇關於身體、情慾、性/別的大門!──陳儒修(政大廣電系副教授)夏特雷曾在舊作提及一位震撼人心的陰陽人。八年後,無限細膩感性的她,以這個別具風險的主題,寫下一則了不起的愛的故事。──《電視全覽》(Telerama)這是則令人驚歎的愛的故事。夏特雷文筆簡潔,句子重覆著離奇的格律,賦予這故事咒語般的魅力,及令人不安的迴音效果。在這裡,她告訴我們:所有事物皆具雙重性。 ──法國廣播公司(RadioFrance)兩個人如何生活於同一副軀殼之中?夏特雷以其才華接受挑戰文學上棘手的寫作難題,過去從不曾有人達到這樣的文字水準。──文學網站「Calou,l'ivredelecture」創辦人帕絲卡.阿居達斯(PascaleArguedas)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榮獲2002年DS雜誌社會書卷獎
章節試閱
6
「妳喉嚨不舒服嗎?」
「不,怎麼啦?」
「我覺得妳的聲音怪怪的。」
母親將咖啡壺放在舖白色桌布的桌上。今天是一個美好的星期天,陽光超棒,窗戶開得大大的,熱鬧的花園看得一清二楚,大自然似乎完美無瑕。我,十歲了。媽媽說得對:我聲音怪怪的,有種沙啞聲。
這不是一般的沙啞聲,我沒著涼,在學校操場也沒放聲大叫。它像一層蒙在我聲音上的紗,一種不知名的紗,一種輕霧,一種在清澈天際上的隱形披巾,沒通知就來臨了;也像一抹矇矓的蒸氣,無法捉摸,卻令我脫序,音色全變了。
我轉頭面向正在吞雲吐霧的父親。他聽見了嗎?
母親坐下來,並觀察著我。我則專注地往窗外看,好似解釋應該就在那邊可以找到我要的答案,完美無瑕的大自然那邊。
我不難想像母親的眼神。長久以來,在碰到她女兒不預期的、有點不適宜的言行時,她都是那種眼光,以沉默的眼神自問著一些問題,也不和我分享那個答案。
「妳要一顆方糖嗎?」
「……」
「妳要一顆方糖嗎?」
我跳了起來。我要不要一顆方糖?真服了妳,媽。真是服了妳。
母親都是一樣的,精通十八般武藝。東扯西扯的,當小孩要跌倒時,當小孩即將受苦時,因為她曉得她的小孩德妮絲會跌倒,她會受苦的。
嗯,我要,我要一顆方糖……我點頭示意,因為我擔心如果開口,我會走音的,聲音會像蒙上一層輕霧,一股不請自來無法捉摸的雲朵。
糖在我的舌頭上融化了,咖啡的汁液填滿了我的口腔和靈魂。我真想化為在我齒間嘎吱作響的小晶體。只是一粒亮晶晶的小糖塊而已。
還要什麼嗎?
還要這個十歲就變聲的非女孩。
非?
非女孩。非女孩。
三個字。這三個字再清楚不過了。我得花十年去弄清楚,而且把它變成一個指令、一項命令。非女孩。就需要有這麼一個美好的週日,我變聲了,它蒙上一層矇矓的披巾,讓事實也變成了渴望。
父親總是動也不動,好似迷失在他眼前的菸霧中。他聽見了嗎?他聽見那沙啞的聲音了嗎?他聽見我那無聲和義無反顧的沉默了嗎?他眼前菸的渦紋現在變成圈圈,分散並延伸開來的圈圈,越飄越高,好神奇喔。
我們三人都抬頭,像被白色菸霧般的龍捲風吸引住,這些美好的圈圈好似些難解的符號。我離開了地面,往上飄揚。我和爸爸的菸霧圖形在一起,跟它們混在一起,往上飄揚了。
在上面,我差點認不出自己。我看到一個大額頭、短頭髮和一副叛逆的神情。我看不見十歲的女孩模樣。我看到某個人。就這樣。
渦紋變稀疏了。我也盪下來了。父親熄了他的小菸捲。
「那我們去玩單槓?讓我看看妳是不是會玩單槓!」他活力十足地對我說。
7
經過多次猶疑不決,也失敗過若干次後,我的聲音似乎要固定在比較低沉和圓潤的音調上,有點兒像父親的聲音。
我喜歡我的新聲音,我聆聽它,就好像從確定變成渴望後的一種承諾。我沒法子發出女孩那種大聲又撒嬌、尖銳得刺耳的聲音。
奇怪的是,變聲這件事就這樣發生了,我什麼也沒做。畢竟,假如我留短髮,那是我想這麼做,但關於我的聲音,也沒人徵詢過我的意見。顯然地,我不會去抱怨它。顯然地,我很喜歡這聲音,不過我更喜歡先被告知,尤其是所有大事都是由我來做決定。此外,這件事若沒發生,我會知道我不再願意當女孩了嗎?
跟珍妮薇說?而且只對她一個人說。在課外活動時間,如果她轉過頭來,而且只有當她轉過頭來時。就算她坐在我前排,而且身體靠近書桌,只要我的眼睛直盯她的頸子或肩膀,她通常會有感覺。轉向我,珍妮薇,拜託。拜託,這很急,這很緊急。珍妮薇聽到了,她慢慢地轉向我,她的頭、下巴、嘴、雙頰、鼻子、額頭還有眼睛,都在和我的頭、下巴、嘴、雙頰、鼻子、額頭還有眼睛對話。在校鐘底下見?在校鐘底下見。
在課外活動中,女生玩女生的遊戲,男生玩男生的遊戲。然而,在校鐘底下,有兩個女生非常不同,她們什麼也不玩,站在和煦的六月陽光下,站在率直的話語裡。有個德妮絲在說話,有個珍妮薇在傾聽,接著是珍妮薇開口,德妮絲仔細聽。德妮絲說她不要再當女孩了,不再是德妮絲了。珍妮薇則說,她要當女孩,繼續做珍妮薇。
我認為我們兩個都對,而珍妮薇也這麼以為。珍妮薇是個完美的女孩。當她是完美的女孩,她想繼續當女孩是很正常的。假若我叫做珍妮薇,也許我就很完美,但明顯地,我是個失敗的德妮絲。珍妮薇卻不認為我是失敗的,恰恰相反,她很欣賞這樣的我。不過她明白我不再想當德妮絲了,她發現我的音色變低沉了,她覺得這樣很特別。
老師走近我們說:「要下課了。」
「那假使妳裝作好像……」
「像什麼?」
珍妮薇在我耳邊說悄悄話:
「好像妳是個男生!」
叮噹的下課鐘聲震動了「男孩」這個詞。它隨風飄散,在我耳際齊鳴。從來沒有人跟我說這些,而且,和我說這句話的,正是我所認識的女孩中最女性化的。我們四目相對。
鐘聲停止了,但對我而言,它並未停止。它的回音一直伴著我進入教室,直到我的課桌前,屬於女生堆那邊。
男生堆就在旁邊,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在男、女生座位之間,僅有一步之隔,很不起眼的一小步,很容易就跨過。「男孩」這個詞,繼續在耳邊響起。我想著我曾嘗試跳馬背、抓吊環、爬單槓、快速爬升等,所有危險的雜耍。然而這微不足道,小小的男女界線,對我而言似乎是如此浩瀚。真的很危險,就算爸爸將手放在我結實的大腿上,如機翼般堅固,我還是不確定我能跨過這個險阻。
我的眼睛又召喚著珍妮薇,拜託!這很急,很緊急!但是珍妮薇沒聽見。她披著完美女孩如長簾子般的秀髮。我焦躁不安,向老師舉手告知,就往教室外面走。老師帶著責備的眼神同意了。
操場空蕩蕩的,非常安靜。我看著上一堂課外活動結束時發出聲響、如今卻靜止不動的校鐘,想起剛才響徹我腦海的鐘聲,幾乎震耳欲聾,這是德妮絲的末日,在學校的德妮絲。我看著分為兩部分的操場:一邊是跳方格子的,另一邊是打球的,而我站在中央,像騎牆派,一腳跨在女生那邊,另一腳則跨在男生這邊。珍妮薇要我把兩隻腳都放在打球的那一邊,她覺得我想當男生是對的,而她想站在跳方格子那邊也是對的。我裝作很困擾,其實我真的很想屬於打球的那一邊。鐘聲減弱了,在操場上方六月的天空,我又聽到從教室傳來男女生一齊朗誦慶祝學期結束的讀書聲。
我更有信心地走向洗手間。在兩扇門前佇足:一邊標明著「女生」,另一邊寫著「男生」。又來了!難道一直都會是如此?一輩子?難道總要在兩扇門之間猶豫?這回,歸我做決定了,歸我,我自己。我很滿意沒人看著我,其他人都在朗誦,沒人會懷疑,也許除了珍妮薇,她看見我走出去,而且眼光跟著我。珍妮薇似乎比我還了解我自己,她替我在這兩扇門中做選擇,要我站在「打球的」那一方。
教室裡的朗誦聲結束了,我深信珍妮薇回頭了,她面向操場,望著我。
我大膽地推開「男生」廁所的門。
8
「妳肚子疼?」
「不……。」
一陣安靜。這是母親第二次問我這問題,也是我第二次看見她失望的表情,為什麼她孩子肚子不痛,她會感到失望?
我母親在期待某件事,一件關於我的事,而我卻一無所知。她似乎比以前更擔心,而我是她的大麻煩嗎?我感覺到她在窺伺,窺伺一種神秘的跡象。她最近常在我身旁轉來轉去,監視我。只要我表現得有點兒累,她就急忙跑過來,問東問西。這無謂的操心令我生氣,因為我別無期待,連暑假也不期待,因為學期一結束,就會帶走珍妮薇。
我父親似乎也因母親的侷促不安而心煩,我想他們一定為了我吵過架,因為爸爸也不期待什麼,我覺得。
我推開眼前標著「男生」廁所的門。幸好有珍妮薇,現在我是屬於打球這邊的,我覺得更有自信了,對於吞噬我雙頰的毒劑比較不敏感了。不當女孩很好,而當男孩又更好上十倍,這是我分秒都留意的事,如同一項全職的工作。譬如,女生和男生睡姿就不同,坐相和站相也不一樣。他們總是相異。在餐桌上也是如此,我爸大口地喝,我媽則小啜;我爸大口地吞食,我媽則細嚼慢嚥,嘴唇微翹。我偷偷地觀察,學習他們的不同,而且應用在自己身上。這是我的暑假作業,一個可以盡情打球的夏天,一個屬於男孩的夏天。
八成因為他是男的,八成因為她是女的,爸爸和媽媽,他們兩人都很疼我,而且疼我的方式也不相同,爸爸喜歡我玩單槓,媽媽喜歡我彈鋼琴;爸爸以我結實的大腿為傲,媽媽以我黑色的長睫毛為榮。可以說,他們愛的不是同一個人。只有珍妮薇喜歡全部的我,不管在單槓上或鋼琴前,不論是我的大腿還是我的眼睛。
事實上,當母親正為我們所不知道的那件事煩心時,我惦記著珍妮薇,但這讓我延遲拿暑假作業給珍妮薇看。除了她還有誰可以改我的作業呢?
在標明「男生」的洗手間門後頭,有個很困難的練習。我不願再像女孩般坐在馬桶上小便,我嘗試站著尿尿。這對我來說幾乎不可能做到。為了這件事,我又恨起德妮絲,而且我羞愧地哭泣,並尿溼了我的鞋子。女孩的尿液都是從身體下方流出來的,好噁心,男孩可不。我羨慕爸爸,他驕傲地灑尿在花園後的蘋果樹幹上,我夢想有一天我也會噴尿,我夢想用那光榮的標槍朝天際噴射。
9
我突然驚醒。
我別無期待,但有件事卻自然發生了,它不像母親所希望的,因為我沒有肚子痛。
我並未等待任何人,然而我卻聽見了。有人小聲地對著我的身體敲門,有人來找我了。他悄悄地、著急地來看我,我不敢點亮床頭燈。
有人在我裸露的肚子上輕輕地敲,不過我全感覺到了,可以說是一種輕撫。
在我身體門口,那道縫,我女孩的縫,早被遺忘多時而且幾乎看不見,但我知道它在那兒,像個污點,像條裂縫。
我假裝睡著。我不該看它,急切的神秘使者。別打斷它的魅力。
來訪者好似武裝好的騎士,而且他有翅膀,我確定。他在我床邊發出的輕微聲響,令夏末溫暖的空氣顫抖。我應該有點害怕吧,但我不懼怕。我只是靜靜聽著他對我訴說,對我一個人。
我非常注意訊息,因此沒能立刻感覺到他,不過現在,嗯,我感覺到了。我感覺到一支手指放在我女孩的縫口上,一隻輕飄飄的手指,然後我聽見一個字,剛開始我還以為是口哨聲:「噓……」輕柔的手指在我陰唇上發出:「噓……」就這樣,有人叫那兩片唇,那張嘴,叫那錯誤的開口閉嘴,再也別說話了,永遠。就這樣。我知道德妮絲被判終生沉默。
噓……!我的眼睛在我下垂的眼皮下微笑。翅膀的輕微聲響飛遠了,我在黑暗中睜大眼睛。我的手朝下探索剛被上天撫摸過仍微顫的腹部。就在禁忌的陰唇上方,我摸到一個硬硬的東西,凸起來的。我的信差留下一份禮物,他在我身體門口留了他光榮的長槍。
6「妳喉嚨不舒服嗎?」「不,怎麼啦?」「我覺得妳的聲音怪怪的。」母親將咖啡壺放在舖白色桌布的桌上。今天是一個美好的星期天,陽光超棒,窗戶開得大大的,熱鬧的花園看得一清二楚,大自然似乎完美無瑕。我,十歲了。媽媽說得對:我聲音怪怪的,有種沙啞聲。這不是一般的沙啞聲,我沒著涼,在學校操場也沒放聲大叫。它像一層蒙在我聲音上的紗,一種不知名的紗,一種輕霧,一種在清澈天際上的隱形披巾,沒通知就來臨了;也像一抹矇矓的蒸氣,無法捉摸,卻令我脫序,音色全變了。我轉頭面向正在吞雲吐霧的父親。他聽見了嗎?母親坐下來,並...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4收藏
14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