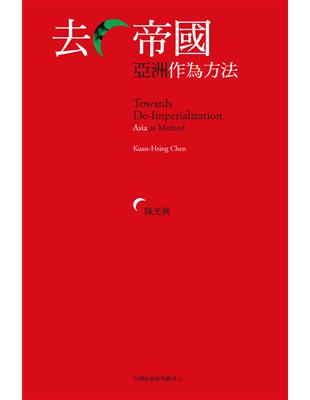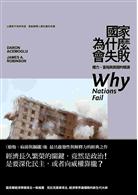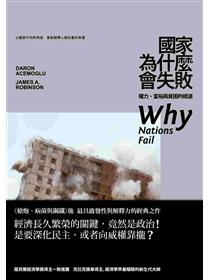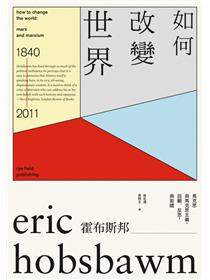本書是學者陳光興累積十餘年的思想與運動結晶。他以「去帝國」為武器、以亞洲為方法,帶領我們穿越讓人無法自拔的歷史纏繞。
在作者的理論想像中,台灣尚未脫離殖民、尚未脫離冷戰,我們全都籠罩在「帝國之眼」的領空,黑色的眼珠甚至也魅惑地閃耀出帝國的慾望。唯有認清歷史位置、感覺結構,面對自身的自大及自卑,面對亞洲,才是解放之道。
本書繼韓文版、台灣版之後,近日將陸續出版日文、中國大陸及英文版,可以稱之為東亞思想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這本不折不扣的「理論」書有許多值得一提的重要特色:
[不安的心靈]
在嚴格的論述片段中,我們會看到陳光興不合常規地在文章中穿插個人事件,讓嚴肅的學術論述呈現出個人生活、思維面向。這就是為什麼鄭鴻生先生如此評論這本書:「以其不安的心靈,尋求真正解放之道……」
[第二波亞洲運動]
這本書的第五章,也就是陳光興十年思想的總結〈亞洲作為方法〉,原本於2003年發表於愛荷華大學。如香港學者所言,這篇論文可以說繼一九五五年萬隆亞非會議之後,重新將眾人目光放到亞洲,開啟了亞洲為中心的第二波批判思想研究。
[運動的總結]
這本書不只是陳光興個人一段歷程的總結、台灣思想運動的一段紀錄,也是他亞洲活動的呈現。陳光興文章密集地在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中國等地造成深刻影響。陳光興主編、英國出版社Rouledge出資辦的雜誌Inter-asia,更是在短期內成為亞洲之間最重要的期刊。
作者簡介:
陳光興
任職台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任資深客座研究員、韓國延世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客座教授。著有《帝國之眼》(2003;漢城,韓文版)、《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主逃逸路線》(1992);編有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1996與David Morley合編)、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998)、《Partha Chatterjee 講座: 發現政治社會:國家暴力、現代性與後殖民民主》(2000)、《文化研究在台灣》(2000)、《後東亞論述》(2006,與白永瑞、孫歌合編,東京,日文版)。他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成員,台灣文化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國際期刊及書系的執行主編。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創新且有深度的「研究工程」…「去殖民」論述的重要大作。-----Stuart Hall(前英國Open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文化理論學家)
在本世紀,亞洲「作為思想的現代」與「作為歷史的現代」開始了交錯。本書正是這交錯中迸發出的火花。-----溝口雄三(前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無所畏懼而且不失嚴謹…陳教授的作品總是勇於處理當代最具挑戰性的評論,同時大膽地提出建議。-----Meaghan Morris(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東亞地區文化研究的里程碑。-----汪暉,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讀書》雜誌執行主編)
這本書是真正身為亞洲人的國際社會主義者,所播種的新亞洲理念種子,也是值得我們呵護的知性資產。 -----白永瑞(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處居於冷戰另一方的中國大陸的視角看,此書不僅對我們理解、進入東亞冷戰對方的歷史、現實有根本性幫助,而且對我們重新意識、評估自身的歷史和現實亦有重要意義。-----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這是一本作者以其不安的心靈,深刻的自覺,苦心孤詣,尋求真正解放之道的困思之作。作者企圖擺脫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桎梏,以及五花八門的西方理論框架,直接面對國族/帝國打造的致命吸引力,來為這災禍罩頂的台灣、危機四伏的中國大陸,以及百多年來陷入紛亂迷失的整個東亞區域,找出一條生路。但作者並不想刻意保持某種批判的距離,也不想從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來「超越」這時代的紛爭與難題,而是直接進入衝突核心,進到具體、分歧而多樣的生命欲望底層,包括作者自身的多重身分糾葛,來面對其內在的矛盾與本相。這裡進行的是一場以貼身對話、自我質疑與反復問難的方式纏鬥的肉搏戰,企圖從我們自身最根深蒂固的執著中殺出一條血路。讀這本書將是一步步心靈解放的體驗。 -----鄭鴻生,作家、《青春之歌》作者
名人推薦:創新且有深度的「研究工程」…「去殖民」論述的重要大作。-----Stuart Hall(前英國Open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文化理論學家)
在本世紀,亞洲「作為思想的現代」與「作為歷史的現代」開始了交錯。本書正是這交錯中迸發出的火花。-----溝口雄三(前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無所畏懼而且不失嚴謹…陳教授的作品總是勇於處理當代最具挑戰性的評論,同時大膽地提出建議。-----Meaghan Morris(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
東亞地區文化研究的里程碑。-----汪暉,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讀書》雜誌執行主編)
這本書是真...
章節試閱
后序
中華帝國的階序格局下漢人的種族歧視
當男/女、陰/陽、動/靜、上/下的配置關係繫之於乾/坤、 天/地時,人間秩序便被定義為宇宙自然的秩序。這個秩序,我們可以用杜蒙的階序格局理解。乾坤、陰陽都是關係性的、因著與天地自然宇宙整體的不同關係、配合成天地整體。它們是對立的,同時也是互補調和的。
——劉人鵬
如果去帝國化是本書指向未來反思運動的關鍵點,那麼放在中文世界來思考,這個方向將無法避免地指向曾經支撐中華帝國的內在理論邏輯,而這當中的一個重要線索,就在於分析以漢族為中心所建立出的中華帝國的文化想像。這套文化想像不僅牽涉到種族與族群之間的互動問題,而且涉及漢人內部的階序格局所引伸出的整體世界觀。清理中華帝國世界觀本身就是去帝國運動的理論工作的一部分,下面的分析只是有關此議題初步的嘗試性討論,尚且有待未來持續深化。
以下的討論還是透過具體的事件來展開。
事情是這樣的:1996年Martin Jacques (倫敦出版的Marxism Today前主編、現為資深的《衛報》〔Guardian〕專欄作家)為了替BBC2製作「西方的式微與東亞的崛起」(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East Asia)的電視專輯,透過霍爾的關係找到我替他在東亞介紹一些朋友接受採訪,在那樣的因緣中我認識了Martin,後來慢慢成為討論東亞問題的朋友。兩年後他舉家搬到了香港,著手寫書的計畫,想要處理東亞經濟及文化的轉化在全球變動中的意義。做為獨立的專欄作家,他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讓他到亞洲進行採訪及寫作,特別是住在香港那樣昂貴的生活環境,能夠來東亞研究的原因是他的太太Harinder Veriah——我們都叫她Hari——被倫敦律師事務所派到香港的辦公室工作,而會派她到香港正是因為她做為「亞洲人」的優勢:Hari是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的印度Punjabi人,從小因為生活周遭都是華人,所以也學會了說廣東話,派到香港來該是如魚得水。
1998年Martin來台北進行兩個月的研究及訪談,我們替他安排住在台北清大月涵堂;期間Hari帶著寶貝兒子Ravi來看望先生,全家團聚,Martin還特別安排她們住在陽明山,享受台北的山林之美。朋友的老婆來了,總要請客吃飯吧,就這樣認識了Hari。Hari長的瘦瘦高高的,大大的眼睛配上她常有的笑容,再加上她開朗熱情、心思細膩,特別是她還是那種處處都是替朋友著想、把自己擺在最後的人,所以非常討人喜歡。後來我們變成朋友之後,她就會開始講出在香港受到歧視的一些不快的經驗,原來認為有廣東話的便利,在香港應該很容易生存,然而不然,Hari南亞的深色皮膚及長相,讓她不論在辦公室、街上、市場,還是地鐵上,都感覺極不被尊重。爾後,不論是在她來台北碰面,還是路過香港借住在她們家中,我們三個人都會開始分析,以解釋香港種族歧視的形式。最後證明,我們家常式的討論並沒有能夠阻止悲劇的發生。
1999年12月底,我去北京開會,她們邀請我回程的時候過境香港,去跟他們的好友、頗具盛名的Eric Hobsbawm的一家人碰面,他們到香港過聖誕節及新年,也趁機理解南中國的變化。我很高興地去了,還在她們家叨擾了一晚,跟兩家人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我回到新竹的幾天後,突然接到Eric Hobsbawm大兒子Andy的電話,告知不幸的消息:Hari在2000年1月2日病逝於香港的一家醫院,死因不明,警方正在調查當中。這個事件後來在香港的外國人社會中引起相當大的回應,很多在當地曾經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有色人種都挺身而出,使得該事件從法律訴訟轉變成反種族歧視的運動。最新的消息是,香港政府正在草擬反種族歧視法。
這也正是我書寫的動力之所在,想要能夠跟Martin及天真可愛的Ravi解釋Hari可能是如何受害於漢人種族歧視的邏輯;雖然這樣的分析已經回天乏術,但是我們活著的人總可以逐漸去改變這樣的狀況吧!
很明顯的是,在法律的層次上來看,Hari的死跟種族歧視之間很難建立起直接一對一的因果關係,但是反過來說,大概也很少有人能夠斬釘截鐵的說,這個事件完全不涉入種族歧視問題。本文的目的不在於論證Hari是或不是因種族歧視而死,但是Hari的事件確實在香港開啟了外國人被歧視的討論,或許我們可以延續已經打開的討論空間,進一步展開漢人種族歧視的問題意識,在以漢人為主體的不同的華人社會中認真面對這個真實的問題。在港、台、新、馬等地各種形式的外籍勞工不斷增加,隱性/顯性的衝突矛盾處處可見,再加上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那種出頭天主義的情緒是很難克制的,也會引起多邊的焦慮以及引爆更為激烈的衝突。總之漢人的種族歧視將會是全球性的問題,進步的批判圈必須得開始嚴肅地面對這個無法逃避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要深刻地思考這個問題必須拉回到此前的中華帝國,以準確捕捉漢人的整體世界觀中種族歧視問題的位置。但是,中華帝國中漢人對待異族及外國人的問題,包括在具有批判意識的文化研究的研究領域,還沒有被充分地從理論及歷史的觀點加以解釋,而在這樣的研究廣泛缺乏的情況下,我此處只能初步提出如下問題:在現、當代以前,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帝國,他的種族觀跟其他殖民帝國主義的人種歧視有什麼不一樣?換句話說,漢人種族歧視的特定性(specificity)是什麼?
當然,從學理上來說,「漢人」及「種族歧視」都需打上引號,需要被問題化。漢人不具有同質的統一性,做為一個想像的群體,它在歷史中不斷地變化,除了中國大陸內部的民族分類,以及東北亞還仍然使用的「漢字」或是「漢語」等語彙外,在21世紀全球的語境中,漢人逐漸被「華人」或「中國人」(Chinese)的用法所取代;但是我此處還堅持使用「漢人」,是試圖藉此強調不論如何變動,它都確實在生活、思想、文化上有其傳承,並具體制約著我們的實踐。特別是政治上,在全球的範圍內,「漢人」確實是主導性的人口,因此我們必須把它跟其他包括在「華人」或「中國人」中有關的少數民族區分開來,以讓我們正面去面對、反省我們漢人自己的問題。而種族歧視之所以加上引號是為了指出,「種族」、「族群」與「民族」在華文及英文的系統中已經成為交叉重疊的用語,比如,我們說馬來西亞的三個主要「族群」是馬來、華族與印度人,但是彼此之間有「種族」歧視的問題;而在中國大陸的用法,漢人是民族的範疇,對少數民族表現出來的是「民族」歧視,而不是「種族」歧視。
另一方面,既有有關種族歧視的理論及社會科學相關的論述及分析架構,基本上是從經濟及階級差異來討論,或是文化主義式的詮釋,而華人社會的特定性並不能由此得到充分的解釋,用一般普遍主義的形式來解釋漢人的實踐,無法掌握其內在邏輯。但是這樣的講法卻並不意味著拉起特殊主義的旗幟來對抗所謂西方的理論講法,恰恰相反,歷史地來看,漢人的種族歧視不只是在與西方遭遇的過程中發生,在亞洲的內部也同時產生,縱使是在漢人本身生活的區塊中,乃至於在漢族內部,都展現有不同形式的歧視。我認為,如果能夠在我們自己生活的各種不同的社會空間中掌握種族歧視邏輯的特定性,或許能夠開啟新的討論視野,或是豐富化既有的討論,從而對於歧視的各種實踐形式提出更細緻、更有說服力的理解釋
在現階段要打開討論空間的一種可能性,是追溯早先漢人歷史中的各種時刻,看漢人是如何對待異己(學術名詞現在叫做「他者」或是「他者」),再來找出在後來不同的華文社會中,因應不同的環境所衍生出的不同歷史變化軌跡。由於我能接觸到的、具有啟發性的研究正好都是將焦點擺在清末民初之際,因此以下我基本上以此為討論與想像的時間點,不預設從古至今都是如此。美國奧瑞岡大學的Maram Epstein以及台灣清華大學的劉人鵬,近期從女性主義對於清末民初的研究,對我而言很有啟發,以下的討論從她們的論述向種族問題延伸,但正因本文的思考集中在帝國的種族問題,因此只能算是對於她們的研究進行抽離脈絡的挪用。
Maram Epstein的論文“Confucian Imperialism and Masculine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Novel Yesou Puyan(《野叟曝言》)”發表於1998年於台北召開的「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國際會議。這篇文章基本上是從女性主義的視角,處理《野叟曝言》文本裡中華帝國主義與漢人男性的認同。她對照了《野叟曝言》在1880年與1930年的兩個版本,主要在分析故事中男主角與異己互動中發生的性關係。與漢人互動的對象/主體包括歐洲人(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印度人,以及生活在中華帝國周邊地區的人種,如日本、苗、傜、緬甸、暹羅、錫蘭等。閱讀Maram論文的過程中,浮現了幾組漢人面對異己的論述(精神)策略。第一種是將陌生主體「鬼化」,異己被很有想像力地描繪成青面獠牙,有時長有尾巴,身體長毛。這一種基本上是對所謂「洋鬼子」的懼怕與著迷;在此範疇之下,又延展出不同種的階序位置,如洋鬼子與東洋鬼子的差別,後者是在指稱日本人,說日本鬼子的身材矮小,或說它們是倭寇。一般來說,將異己鬼化是漢人文化想像中較為熟悉的作法,異己是非人,是鬼,自身是人的位置。
不同於第一種方式,第二種策略在很多不同的場域中操作,就是將異己「動物化」。舉例來說,在幾場戲中,男主角到台灣旅遊,發現台灣島是一片荒野,在島上居住的不是人,而是人熊。在中國西南方,苗族聚居之地,他碰到六隻大蟒蛇,這些蟒蛇迫使苗人起來反抗中華帝國;這些蟒蛇長的像人,但是身體特長,長有白毛,鱗片包體,性器官冷感麻木。最後,到了印度,印度被描繪成佛教國家,「這些佛教徒一點都不努力,他們跟牛一樣笨,跟豬一樣醜,他們唯一做的事就是背誦佛經,而且可以念得超快」(p. 17)。有趣的是,縱使這些是被動物化的異己,也一樣能夠激起男主角的性慾,跟他們進行交媾,當然,交媾的目的正是在「化混沌為文明」(p. 12)。這種策略也是很熟悉的:殖民者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使這些動物化的異己能夠學習、從而進化成為我們——人,當然心裡也常常偷偷認為他們永遠也不可能真的跟我們一樣。
第三種策略,經常被用來對待鄰近的少數民族以建構另一種階序,即將異己(外人)進一步區分為生蕃與熟蕃,後者「雖然文化不同,但是可以很容易地被『消化』進入中華文化的勢力範圍」(p. 14)。所以,不像頹廢的日本東洋鬼子那樣,基本上沒什麼希望,苗人正在漢化當中,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還是跟我們有些不同,因為他們還沒有能夠真的進化成「人」,還沒有能夠成為人的具體表現是,苗人雖然男、女有別,但是在公共場合夫婦居然被容許相互擁抱,已婚的女性在懷孕前還被允許養漢子(「野郎」),這些都是不夠文明開化的表現。簡單地說,這種策略是企圖將他者人化,但重點是我們在階序關係中高於他們。
Maram Epstein的問題意識是用性別化的陰陽邏輯來解釋漢人(陽性)與他者(陰性)的階序關係,陽永遠高於陰,這是基本的女性主義批判的論述立場。但是同時,在上述的討論中,我們看到在根本上這幾種策略的共通統合性在於人與非人之間的階序區別,或是「人」到什麼程度的問題,這個階序邏輯是透過(看似超越、或是隱藏起來的)高於人與非人範疇的發言位置接合出來的,而這個發言位置通常是由具有最優勢文化資本及權力的(男性)主體所盤據。更具體地說,這裡所說的「人」,其意象是受到高度教化的主體,是經過長期的養成,一般的人雖然在軀體上可以說是人,但是並不能算是真正達到理想境界的人——四書五經的閱讀、修身養性都是通往這個境界的途徑,或許整個中國儒家的倫理/道德的思想之所以是實踐哲學,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簡言之,這樣的「人」超越了陰陽、男女的範疇及發言位置。
我認為這是理解漢人種族歧視內在邏輯的關鍵之所在,而問題在於:這個邏輯到底是哪裡來的?在漢人既有的種族歧視的實踐體系當中,這樣的邏輯早已成為面對異己不知所措時的基本反應。我的意思是說,與外來者的互動,預設了既有的實踐,在兩造相遇時,某些因子及原則被調動起來,以面對及處理自己無法理解的陌生異己。要特別強調以預防誤解的是,此處的討論不是在談什麼「亞洲價值觀」,而是在處理受到整套世界觀制約的具體實踐。
在思想的理論層次上,「內聖外王」的概念及歷史實踐,或許能夠初步地提供漢人種族歧視的解釋。這裡我依靠的是劉人鵬所發展出來的理論。
在她的重要著作《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一書的第一章〈傳統階序格局與晚清「男女平權」論〉,劉人鵬借用了杜蒙(Louis Dumont) 的經典著作《階序人:卡斯特體系及其衍生現象》(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1980)對於印度種性制度的分析,來理解中國階序邏輯的建構。雖然她的問題意識基本上是在性/別關係的軸線上,但是她的分析具有更為寬廣的抽象性(後詳)。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她認為杜蒙的階序理論是奠基在接合「含括者」(the encompassing)與「被含括者」(the encompassed)兩者之間的關係;亦即,在整體的系統關係中,高階者能夠包含低階者,而底階者不能夠包含高階者,就是男可以完全包女,女不能完全包男,所以在一個層次上男女之間有互補、互包的關係,而在整體結構中則不然。這個基本的方法論之所以稱之為借用,是因為它的理論主體是建立在對於我們自身的主體認識當中。
在第四章〈「罔兩問景」——「男女平等」之外的性/別主體〉,劉人鵬引用了莊子罔兩問景的寓言,重新思考主體理論,藉以理解不同發言主體之間的階序關係,以及在公共領域中不均衡、不平等的再現關係。罔兩問景揭示了三個不同的發言位置,這三個不同的發言主體包括:形,就是主體(形體);景,主體的影子(形體之影);眾罔兩,影子的影子(黏成一起,形象不明的影子餘陰)。如果說,主體是形,是身體,那麼影必須依附在主體身上/周遭才能存在;而罔兩作為影子外層的光影,則得依靠著影子的存在而存在。因為罔兩的存在曖昧不明,因此不能夠被辨識為具體的「個人主義」主體,也因此經常被當成一小撮主體性不明的群體/塊狀物來看待。
在罔兩問景的寓言中,主體從來不在對話的場域中現身,他的出現往往是在影子回答罔兩的問題當中,也就是在文本以及閱讀過程中出場。簡單地說,他是缺席的在場。有趣的是,在表面上,影子是在跟罔兩對話,然而她所指涉的往往是主體——形,所以主體雖然不在,但又無所不在。所謂形影不離,也就是主體與影子不能夠分離,其實這正是「包含」的運作邏輯,是在社會空間中實際操作的認識論架構。由於罔兩無法自我呈現,或者適切地用形(影)可以理解的語言、可以接受的方式、有禮貌地表達自身,她們的出現經常由影子在社會空間中來代言。
「罔兩問景」的寓言如此區分主體的差異,徹底質疑了像公共領域等理論的基本假設,認為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公共空間的假設。
我個人認為,「罔兩問景」必須分成兩個層次來對待,它的重要性基本上在於它的描繪分析性(descriptive-analytical mode),準確地掌握了客觀存在的主體差異/階序格局;這個層次必須跟規範策略性(normative-strategic mode)分開來討論,亦即,罔兩問影這個寓言是否能夠發展出培力(empower)弱勢主體的策略,必須回到運動主體本身的位置來討論。但可以確認的是,運動策略可以提出的前提,必須建立在客觀分析之上。本文的討論聚焦在前者,還沒有能力處理後者。
要將這個高度抽象性的罔兩問景的理論性的描繪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實踐當中,我認為可以用當代不同形式的認同政治來理解,不論是從性/別、階級還是種族/族群的軸線所構成的結構來看待:如果總體結構(太極)是父權異性戀體制,主體是男性,影子是女性主義分子,那麼罔兩就是女同性戀群體——後者無法自我呈現,常常得以女性主義的姿態來出場,或是扮裝成黏成一坨的女性主義分子、以團體的身分來現身;如果說結構是資本主義,主體是資本家,工人階級是影子,那麼罔兩就是(非法)外籍勞工,她/他們在所謂公民社會中沒有位置,而必須透過教會或是勞工團體才能發出聲音;如果說總體是人種結構的分類系統,主體是主導性的種族,影子是少數民族,那麼罔兩就是鬼、動物、生蕃、非人。上述三個軸線結構的關鍵在於:主體形成了結構性的整體世界,包含了所有發言的主體位置,在其間主體的真實位置是處於發言位置範疇之外的上方,主控了整個結構的動向。
討論至此,「人」已經出現了不同的光譜、程度與位置。
根據劉人鵬,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主體與客體不是像西方理論那樣以二元對立的方式來呈現,主客體的關係是陰陽邏輯,陰與陽的關係是互補的、協調的,是不同的分工。但是,劉人鵬認為這樣的共識其實忽視了兩者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她的核心論點是:太極其實正是結構性的整體,先於陰陽關係而存在,因此在分析時必須在兩個層次上操作,在高層次上,陰陽的統一是互補、和諧的,被包含在太極的整體秩序當中;但是在低層次上,陽高於陰,亦即陽支配、統治、包含了陰;更重要的是,陰與太極整體的關係不同於陽與整體的關係。劉人鵬是這樣論證的:
當男/女、陰/陽、動/靜、上/下的配置關係繫之於乾/坤、 天/地時,人間秩序便被定義為宇宙自然的秩序。這個秩序,我們可以用杜蒙的階序格局理解。乾坤、陰陽都是關係性的、因著與天地自然宇宙整體的不同關係、配合成天地整體。它們是對立的,同時也是互補調和的。然而,它們的位置並不是平行的,一是上際,一是下蟠,時間上也不是共時的,一是乾知大始,一是坤成作物。〈圖說〉此處要說的是「心之體也」、「人道之大」,事實上,是這個「心之體」、「人道之大」的假設、在天地乾坤男女之中之外並之上、作為那先在的整體秩序,這個整體,說話中的這個主體可以觀察到或者說出這個乾坤秩序,而這個先在的整體秩序,為這個說話主體所理解。在第一個層次上,陰陽共同成就整體秩序,只是在天地之間的分工不同,二者和合互補;但是在第二個層次上,天尊地卑。(2000:22)
劉人鵬費了很大力氣要論辯的是:晚清既有關於男女平等的論述,是以陰陽邏輯為基礎,實際上隱藏了內在於結構中極為不平等的位置,因此表面講平等其實是從根本結構上強化了不平等的關係。雖然,在一個層次上陰陽是互補的,但是在另一個層次上陽仍然是主體,陰是輔助的,也就是陽主因輔,陽包含了陰。因此:
上階的陽包含下階的陰;而「陰不得與陽擬」是說:下階的陰必然被排除於上階的陽之外。事實上,也正因為階序的關係,陽與陰必須分工,必須隔離,必須有別,同時也互補互依。陽尊陰卑的階序原則,在論述中要不斷導向天理或常道或自然之序,以回歸或通往和諧的天下整體。(2000:23)
將回歸天理、自然、天下整體的邏輯「下降」到社會層次來討論,這個造就了所有社會階序格局的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基礎,正是君子的發言位置,通過轉喻邏輯指向的則是聖王。根據劉人鵬的分析,這個發言位置暗示了一個具有包容性、同情他者的階級/階序的統一位置,盤據了道德與政治上高等的位階。相較於君子,聖人這個字眼更進一步預設了道德上的完美無缺。這樣的論述不僅能夠連結到社會政治體制的實踐,也包含了要求個人主體修養的情感模態。關鍵在於:這個發言位置正是「人」的終極理想之所在。在論述的實踐中,一串具有階序的等價鍵於是在社會場域中被建立起來:人、男子、中華、士大夫。一條生產這個包含主體位置的路徑是透過「內聖外王」來建立的,用當代的語彙來理解,就是內在的自我要求在道德上能夠成為聖人,如此才能夠外在於自身,以德服人,透過贏得民心的積極認可,才能王天下,平順地統治世界。
更明白地說,在晚清有關男女平等的論述中,聖人被認為是平等的根本資源之所在。如同梁啟超所言,「聖人之教,男女平等」(劉人鵬,2000:52),也就是只有聖人才能教導男女平等的真義,聖人的發言位置包含了男與女兩個範疇,聖人同時內在也外在於兩性關係,重要的是他高於這組關係。如前所述,聖人的位置終極指向的是大寫的「人」。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人」有很多種,他本身的多樣性是階序性的構成,聖人在最上,賤民可以是人的一種,不過是在底層,鬼、動物等則是非人,更等而下之。
於是,對我們處理漢人種族歧視的內在邏輯來說,這裡「人」的位置不只適用於性/別關係,也適用於階級與種族關係中的階序邏輯。「我們是平等的,但是你還不夠做為真正的人,來取代我做為聖人的發言位置」,這正是漢人與異己遭遇中經常啟動的精神機制,其得以確保自身(自保的)優越性的基本公式。
這正是中華帝國的基本認識論,帝國基本的階序格局,在心中運轉,也付諸實踐。
到了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具改革傾向的漢人現代化論述被迫要處理平等的觀念,特別是要面對與任何形式的異己進行互動時的平等關係。然而,整體的精神狀態、心理機制與意識形態實踐的常態公式——「我們是平等的關係,但是你還不完全是人」常常正是沒有說出的政治前意識,但在具體的互動狀態中被啟動。以人與非人的區別光譜來面對異己,不論這個異己對漢人主體而言,是有優越感(的白人)、是弱勢(的少數民族)或是只是肇始於彼此的陌生。這個普遍性的沙文主義(universal chauvinism)曾經在漢人面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時,發揮了龐大的精神抵抗作用(「這些洋鬼子可以用物質力量打敗我們,但是永遠無法征服我們的靈魂」)——這種阿Q邏輯,我們不能快速地否定它存在的積極防衛性。但是同時,正是這個種族歧視的理論邏輯,也戕害了不少中國周邊地區的善良人,Hari的不幸就是這一邏輯的結果之一。就像一塊周邊是鋒利的盾牌一樣,雖然可以擋住外在的攻擊,但是一不當心,隨手一揮,就變成了殺人的利器。
總結來說,雖然上述的兩個研究關切的主要是性/別問題,但是如果認真對待她們開啟的討論空間,那麼我們必須看到的是,她們其實正是在處理中華帝國的底層邏輯。在漢人過去的歷史中,多層次的歧視的內在邏輯其實來自於對於「人」的根本認知,而這個普遍性的「人」本身就是建築在歧視的階序邏輯當中。表面上來看,用現代的分析語言來說,「人」是一種境界,一種普遍主義的根本,能夠達此境界就能超越性/別、階級、民族與種族的差異。換句話說,性/別、階級、民族與種族的差異性階序邏輯,是「人」這個體制運轉中的自然表現。有點像個金字塔,「人」站在塔的頂端,其他還不完全成為人的半人或非人(影子或是罔兩)都張首向上仰望,慢慢向上爬,只有向下看的「人」能夠決定,你還差多少才能夠跟他一樣成為真正的人。這個沒有性/別、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超越一切的「人」,在面對性/別、階級、種族的異己時,他的高高在上,循循善誘,特別是他的告訴你:繼續加油,都是他歧視體現的具體時候。如果你想要跳出金字塔的運轉邏輯,跟他說這些都只是漢人、男性、知識階層所發明的想像,他會跟你說,你的慧根不夠,還沒有體會到「人」的真正境界,或是說你西化太深,中了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的毒。
我認為當前所謂「中國性」(Chineseness)的討論還不具爆破力,因為它沒有足夠深入內在核心問題,所以需要將矛頭指向前面所說的普遍性沙文主義。如果我們把這裡漢人對於「人」的討論當成是對「中國性」與中華帝國的討論,那麼在認識到所謂中國性在客觀的存在中,實際包含了如此看待「人」的意識與無意識之後,你如何能不支持去帝國的必要性?
我很確定的是,我們還無法掌握各種華人社會中,漢人對其他民族的特定歧視形式,例如,香港經過英國帝國主義的統治,台灣經過日本的統治,新、馬華人處於少數民族的位置,所以不同社會漢人歧視的形式可能極為複雜,因此也就必須經過更為細緻的歷史性分析才能充分把握。同時,我們更需要透過研究的對照與比較,在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乃至於中國大陸一起推動各地批判知識分子思考這個問題。以台灣當前對待原住民、外籍勞工、外籍女傭、看護工、外籍新娘、大陸新娘、外籍教師等等的總體表現來看,漢人歧視問題確實無所不在,並沒有因為所謂的民主化,就更為民主地對待異己。
很明顯的,我們離孫中山世界大同的境界還早得很,同志仍須努力,得開始認真的推動去帝國化運動。
2005年9月30日,丹麥《日蘭德郵報》(Jollands-Posten)刊登了12張極為輕蔑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引發了歐洲內部與伊斯蘭世界之間極大的爭議。2006年2月間,Martin Jacques在《衛報》撰文,反思歐洲種族歧視的問題。開頭的提要,替文章定了調:一個在過去200年間曾經使全球各地承受其殖民暴行的(歐)洲,實在沒有什麼好聲稱自己價值的優越性。他認為丹麥漫畫事件所引發的廣泛迴響中匯集了「自衛、恐懼、狹隘、自大」,其實意味著歐洲根本無法面對新的世界現實。這不是Martin初次在歐洲內部發表反思其過去殖民帝國主義行徑的文章,其實從90年代後期起,他就一直在「教育」歐洲人不能沈迷在自我中心的世界觀當中,必須要面對自己過去征服世界所遺留下來的問題,要面對世界的變化;Martin持續撰文關注亞洲(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的興起與變動,乃至於他長期投入進行的研究,都是在想要打開歐洲(特別是英國人)封閉的世界觀。
對我個人而言,最為難能可貴的是,Martin並沒有因為Hari在香港受到華人的種族歧視而喪生,就開始在情緒上反華、反中,恰恰相反,他希望愛子Ravi能夠學習中文,除了讓他學習孕育母親成長的印度音樂外,還送他去學二胡。或許,Hari的不幸,正是Martin反思歐洲帝國主義造就種族歧視的動力之所在。
在《衛報》刊出批評丹麥漫畫文章的第二天,Martin跟我說他已經收到兩百多封電子郵件,大部分都是不友善的,反應相當強烈,所以他對歐洲的內部反思過去殖民帝國主義歷史的能力非常悲觀,但這正是未來的一個世紀非得被迫面對的問題。讀完他的文章,我問他,如果同樣一篇文章,不用他的而是用我的名字發表,會有什麼反應?他說讀者根本不會理會你的意見,說你是中國人,根本不懂歐洲,或者說中國也曾經是帝國,也一樣有種族歧視,有什麼好質疑別人的。我猜想的也是如此,就像現在這篇討論華人種族歧視的文字一樣,如果是美國人或是歐洲人寫的,也不會被華人及中國人理會。
果真如此,這樣的現實狀況其實發人深省。認同政治沒有結束,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可能結束。進步圈不該只以政治正確的方式對待認同政治,而且還需更看清事實,以進而善用綁在我們身上、甩不開的身分認同,從內部發言,讓自身所屬的群體能夠積極面對問題。本文寫作的動力正在於此,套句老話,一切該從自身做起,要批評別人得先學會自我省視、自我批評。
本書在此劃下暫時的句點,並不意味著我認為當前世界的問題,都能夠化約到去帝國(以及所牽動的去殖民與去冷戰)的問題意識中來理解,好像只要解決了這個問題,天下就太平了。當然不是,然而當前世界的許多紛爭,乃至於一國、一地內部的衝突,確實又很難脫離殖民帝國主義與冷戰的歷史來找到解釋。歷史過程的本身是相互糾纏的,盤根錯節,交叉聯繫,因此平面地、抽象地、概念地理解紛爭與矛盾,客觀上往往就是搭配帝國主義推卸責任的知識生產方式。就像說種族歧視哪裡都有,而不去追究其中的特定性,或是說歷史本來就是帝國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沒有可能、也不需要去改變這樣的認知。本書要挑戰的就是這種強勢、自以為是的知識狀況,把學術生產單一化、扁平化,剔除批判關切、立場與思想才叫做專業,這樣一整套思惟、習慣透過帝國機器與帝國嚮往向全球擴散。承載第三世界被殖民地區歷史經驗的我們,不能再次跟風,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經形成的力道隨波逐流。
我們當然會期待歐、美也跟日本一樣,開始反思其自身去帝國化的迫切性,但是,事不我予,我們在自己有限的工作範圍內要做該做的事,在不斷的實踐、不斷的積累,以對世界走向真正的民主與和平發揮積極的作用。如果不能捲起大規模的運動,也得持續堅持去帝國、去殖民、去冷戰的開展,以「亞洲作為方法」推動在知識生產層次上的批判性區域統合。
后序中華帝國的階序格局下漢人的種族歧視當男/女、陰/陽、動/靜、上/下的配置關係繫之於乾/坤、 天/地時,人間秩序便被定義為宇宙自然的秩序。這個秩序,我們可以用杜蒙的階序格局理解。乾坤、陰陽都是關係性的、因著與天地自然宇宙整體的不同關係、配合成天地整體。它們是對立的,同時也是互補調和的。 ——劉人鵬如果去帝國化是本書指向未來反思運動的關鍵點,那麼放在中文世界來思考,這個方向將無法避免地指向曾經支撐中華帝國的內在理論邏輯,而這當中的一個重要線索,就在於分析以漢族為中心所建立出的中華帝國的文化想像。...
目錄
序言
導論 全球化與去帝國
第一章 帝國之眼
南進論述的次帝國文化想像
第二章 去殖民
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
第三章 去冷戰
大和解為什麼不∕可能?
第四章 去帝國
51俱樂部與以帝國主義為前提的民主運動
第五章 亞洲作為方法
超克「脫亞入美」的知識狀況
后序 中華帝國的階序格局下漢人的種族歧視
參考書目
序言
導論 全球化與去帝國
第一章 帝國之眼
南進論述的次帝國文化想像
第二章 去殖民
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
第三章 去冷戰
大和解為什麼不∕可能?
第四章 去帝國
51俱樂部與以帝國主義為前提的民主運動
第五章 亞洲作為方法
超克「脫亞入美」的知識狀況
后序 中華帝國的階序格局下漢人的種族歧視
參考書目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