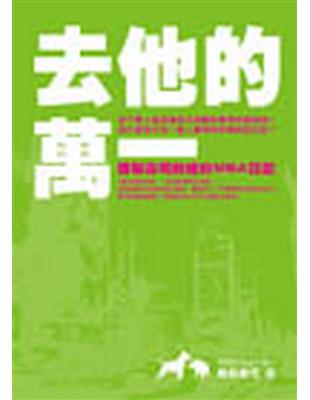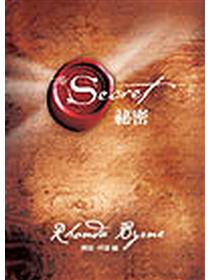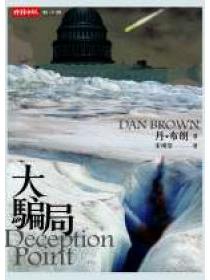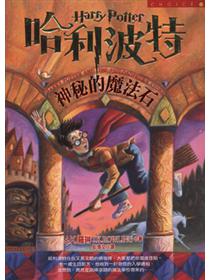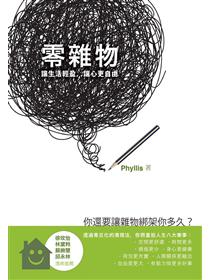萬一先生
在大部分朋友眼中,我是個說話大剌剌、愛耍寶、敢為了菜市場裡的三十塊青菜蘿蔔殺價,在餐廳也能理直氣壯拍桌子說:「請你們經理過來!」的惡女。
但只有一個人知道,我骨子裡是個膽小的孬種。
那就是萬一先生。
認識萬一先生是七歲那年,國小一年級的我第一次上福利社。福利社阿姨是我的敵人,她們總是面無表情的坐在深不可測的櫃臺後面,我怕死了。眼看離上課鐘響只剩一分鐘,兩顆一元的沙士糖在透明櫥櫃裡向我招手,想解饞就得開口。
就在這個時候,萬一先生出現了。他在我耳邊悄悄說:萬一你記錯價格錢帶不夠怎麼辦?萬一阿姨很兇不賣妳糖果?萬一她賣妳糖果卻找錯錢,妳敢跟她要嗎……
肥短的小手裡兩個銅板熱的燙手,我連耳根都紅了。
「要買什麼?」阿姨不耐煩的探頭問我。我一溜煙兒跑回教室,整堂課都想著沙士糖口水直流。
十二歲以前,電話是我的敵人,萬一先生則是我的好朋友。每當不得已要打電話給老師或同學,我總哭喪著臉在電話前猶豫半天,左手握著事先花半小時擬好的「演講稿」,上面從「喂」到「再見」一字不漏、鉅細靡遺,只差沒把我在讀者文摘裡看到的笑話也寫進去,以備化解可能面臨的僵局。
「王媽媽您好,可不可以請美麗聽電話?我想問她今天的數學習題。」我拿起話筒前小聲複誦三遍,確定舌頭不會打結、語氣像個有禮貌的乖小孩。這時,萬一先生說話了:「萬一不是王媽媽接的,妳怎麼辦?」
我搔搔小腦袋,在便條紙上用小括號補上「王伯伯/王大哥」,深呼吸準備撥最後一個號碼……
「等等,萬一美麗不在呢?」
我又加上「請問她什麼時候回來?」「可以請她回來後打電話給我嗎?」兩句。
「萬一妳打錯電話?那不是很糗?」
我補上幾個道歉詞、心砰砰跳,直到掛掉電話,確定自己耳朵沒被咬掉,才鬆了一口大氣。感謝萬一先生的細心。
從十三歲到十八歲,數學一直是我的敵人,幸好有萬一先生與我同一陣線。上了高中,我找了各種藉口逃避數學週考,因為過去每張考卷的分數都是紅字。有時候就算已經努力準備,到最後一秒還是決定請假不去考試。因為萬一先生警告我:「萬一考砸了怎麼辦?老師一定會處罰妳!」
最後,點名簿上一次又一次缺考的註記反而讓我安心,反正不嘗試就無所謂失敗。我只讀國文和英文,因為這兩科我最有把握。
高三甄試選填志願時,過多的選擇是我的敵人,萬一先生立刻表演英雄救美,以刪去法解決我所有困擾。萬一先生在法律系上打了個大叉(萬一法條太多妳背不起來怎麼辦?考不上律師怎麼辦?);接著又劃掉企管、金融、財管、會計等商學院的所有科系(妳不是做生意的料,萬一身陷數字地獄,會不會瘋掉?)、又對教育和各種語文相關科系搖搖頭(妳這麼沒耐心,萬一當老師後誤人子弟怎麼辦?)。結果只剩下傳播學院,既不用背書也沒有數學,更不用當老師,那就讀新聞吧!
十九歲上了大學,當同學們不惜拉低平均也要選修充滿挑戰性的法律、金融、政治當輔系,我捧著原本就很熟悉的希臘、羅馬神話和莎士比亞,悠遊在西洋古典文學的天地裡。
大四那年,我報名GRE補習班,補完了卻沒去考試,因為萬一先生說:「萬一妳考不好怎麼辦?萬一妳臨時反悔不想出國了怎麼辦?還有,妳出國想念些什麼?萬一改變主意,不是白考了……」
二十二歲從新聞系畢業後,我理所當然進了平面媒體當新聞記者,因為萬一先生嘟噥:
「電視新聞要拋頭露臉,萬一吃螺絲或長痘子怎麼辦?被批評的一無是處怎麼辦?去跑時尚娛樂或社會八卦或許很有趣,但萬一學校老師從此看不起妳怎麼辦……」
於是我選了家正派經營的老公司,領一份令人安心的薪水。我在洗頭時津津有味的咀嚼精彩刺激的壹週刊「踢爆」標題,回家繼續寫無關痛癢的產業前景。
我交男友,偏好長相中等、笑容陽光燦爛的好男人。瀟灑多金的帥哥對我沒有吸引力,因為他們笑吟吟的臉上寫著:「小心我一口吃了妳!」
「萬一他們有了別的女人怎麼辦?萬一我受傷怎麼辦?」萬一先生在帥哥出沒的方圓十里內都貼上「危險勿近」警告標語。
就連吃東西,萬一先生也幫我想得很周到。我故意忽略餐館的新菜單,極度不信任便利商店貨架上的新產品,因為「萬一很難吃那就糟了」。早餐土司我只買7-ELEVEN的「好土司」,因為它最便宜而且至少我吃過味道還能接受;到美而美我只點鮪魚蛋三明治加冰奶茶,上川菜館子點宮保雞丁麻婆豆腐,客家菜吃薑絲大腸和鵝肉,日本料理等於豬排飯、炒烏龍麵、花壽司或鮪魚沙西米。
這樣很好,做什麼事都有萬一先生陪著,我覺得很安心。
直到25歲那年,我才赫然發現,走在安全地帶,不代表不會有意外。天上都可以掉下禮物,這世界上還有什麼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所謂的「好男人」,也可能說謊、劈腿、背著妳在外地跟別人同居,遞給鄰居不會丟臉的名片不保證工作快樂,還有,壽司裡面竟然可以包酪梨這種怪東西。
生平第一次,我有解開繩索的念頭,想到安全網外的世界闖一闖。
我沒考慮萬一,就開始準備留學考試,還妄想挑戰過去二十五年來絕對沒想過的科系:MBA。我還是對金融沒興趣,只想做行銷,但天知道我有沒有天分,行銷工作會不會成為我的新歡。我辭職、申請相關文件、寄快遞,兩個月內,一切搞定。信箱裡躺著一個又一個好消息,喔,我錄取了!喔,我要去紐約!聽說那是個慾望城市。
就當一切都塵埃落定,萬一先生又回來了。
「萬一妳花了大把銀子回來找不到工作?」「妳什麼基礎也沒有,萬一跟不上進度怎麼辦?」「萬一去了才發現不對味?」「萬一妳在紐約的五光十色和MBA的交際生活中迷失自己?」「妳男友怎麼辦,萬一遠距離戀情行不通?」
我二十六歲,在日漸鬆弛的肌膚和圓滾滾的游泳圈肚皮後面,還藏著那個抓著兩元銅板瑟縮的七歲女孩,每當遇到抉擇,就像一隻手伸進「恐怖箱」的綜藝節目來賓,碰到鳳梨就驚聲尖叫,以為是會咬人的非洲蜥蜴。過去二十六年來,我用盔甲城牆重重武裝自己,假想敵是這世上所有無法預測的事情,結果失去的比得到的多。每次唱國旗歌唱到「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頭都低的很心虛。
二十六歲的我,第一次鼓起勇氣冒險。我想起偶然在一本雜誌裡讀過王文華寫他的史丹福MBA生涯:「我是詩人,將要在MBA課程中,尋找新的詩意。」(註)
我不是詩人、不懂詩意,但若不打開恐怖箱,怎麼會知道裡面不過是顆鳳梨。如果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連我最害怕的都能克服,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好怕的?就算敗陣下來,打道回府也很好。至少我知道自己不適合什麼,又嘗試過什麼。
去他的萬一。
註:史丹福暱稱那些沒有商管背景的MBA學生為詩人(poet)。
打包人生
要瞭解一個人的個性,只消看他打包行李。
有些人什麼鬼東西都往行李箱塞,留學如八年抗戰,維力炸醬麵、魷魚絲、康寶濃湯、廣達香肉醬罐頭、香菇、髮菜、蝦米……各種南北乾貨一應俱全,只差沒派娘親駕直昇機到米國空投白米,行李超重罰金足以直接升級頭等艙;也有人只帶護照和學生簽證就殺去機場,一張金卡闖天下,一開學就穿當季名牌,足蹬新款球鞋,多過癮啊!
在有限的空間內,選擇裝哪些東西,也能看出這人最重視什麼。有些人行李箱裡除了衣服還是衣服;有的人以食物為導向,人在異鄉,舌頭卻緊繫祖國;也有人恨不得把整個光華商場搬去美國;更有人忘不了陪伴他二十八年的填充玩偶和沾滿口水的髒兮兮小棉被,帶它們環遊世界,義氣十足。
我呢,或許是遺傳了老爹怕麻煩又不拘小節的個性,國內外旅遊一向以「輕裝簡行」自豪,人家帶了N個大箱子去瞎拼,我只拎個小背包,也甚少帶一堆有的沒的保養品化妝品伴手隨行,打包不用半小時。
正因為有往例可循,我一直信心滿滿,自以為出國打包這小事不過是塊蛋糕(piece of cake),難不倒打包界的天才──壽司。拖拖拉拉直到最後一週,開始進行時才發現,我、太、天、真、了。
「美國又不是無人荒島,妳去的又是慾望城市紐約,有錢什麼都買得到。如果妳高興,天天學凱莉蹬著三百美元一雙的高跟鞋上學,也沒人攔妳啊!」朋友甲看我這麼煩惱,建議我少帶些,到時候再買不就得了。
問題來了:我沒錢哪。
留學不比出國旅遊,這一趟至少兩年,出門在外買什麼都得花錢,我數學再怎麼爛也無法假裝白花花的銀子隨風而逝。加上我其實不是個愛瞎拼的人,需要買的東西越多,只會讓我加倍心煩氣躁。於是右腦想瀟灑成行,左腦又想省點錢把現成的傢私扛去,以免浪費資源。
這是「斤斤計較能塞就塞絕不吃虧歐巴桑首則」和「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徐志摩哲學」的拉鋸戰。
經過一個禮拜的掙扎,歐巴桑打敗了徐志摩。我列了一張鉅細靡遺的落落長清單,可惜任憑我使盡吃奶力氣死命的塞,家裡那兩口箱子加起來,只裝得下三十公斤(註:美國航線的行李托運上限是兩件各三十二公斤,合計六十四公斤)。拜託,郵局隨便寄件包裹都要幾千元,有免費的數十公斤空運額度怎能輕言放棄!不甘心吃虧在眼前,我當機立斷將行李箱換成兩個二十八吋的大箱,外加一個十八吋小登機箱,還用真空袋將陪伴我幾年的棉被、枕頭、被單、毛巾,全都一股腦兒塞進去了。
接著,為避免行李箱爆開,我冒著炎炎日頭,將幾件冬天大外套裝箱後,走了十幾分鐘的路到郵局寄陸空聯運,四公斤多就花了我一千元台幣。一位東方哲人說得好:「打包如人生,有捨才有得。」果然沒錯,捨不得的後果,就是把自己累死。
終於結束打包大業,電子磅秤公佈成績:兩箱分別重二十八和二十六公斤,外加一個八公斤的登機箱和電腦包(根據嚴格的新規定,得幫她們減重到七公斤以下)。雖然離一件三十二公斤的上限還有些距離,但已經結實到連抬上體重計都得小心閃到腰,我不禁懷疑,那些塞到超重的大俠們是否都有報名參加今年奧運的舉重項目。
結論是:如果打包可以看出人的個性,我應該歸在假瀟灑、真龜毛的那一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