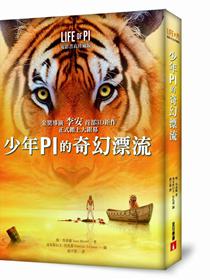我想靠幻想打發時間,不過我不知道該幻想什麼,每部幻想列車都走進死胡同,
因為我並不是自己以為的那個人,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這是一個關於曾祖母艾禾身世秘密的故事。
索爾的曾祖母艾禾是一位著名的演唱家,個性活潑開朗,隨性不羈,可是自己的女兒不願跟她說話長達十四年,而她在德國還有一位姊姊病重不久於人世,期盼再相見,但她常常巡迴世界各地演出,卻是六十年沒再踏進德國一步,一旦回到童年故居時,竟無故開始出現失憶……
故事分成四個部分,由這個家族四代的四個六歲小孩分別敘述,描述他們眼中所看到的世界與上一代。隨著一趟祖孫四代前往德國的家族之旅,曾祖母的身世之謎開始如拼圖般漸漸顯露輪廓,終至完全清晰,但也進一步殘忍地揭露隱藏在背後更可怕的秘密,而這個秘密帶來的傷痕,就像斷層線的裂縫般,一道一道藏留在下一代的心裡。
作者簡介:
南希‧休絲頓(Nancy Huston),1953年出生於加拿大,6歲時與家人移居德國,15歲時又搬到美國新罕布夏州,之後在紐約上大學,她在1973年,大二時申請以交換學生身份到巴黎唸書一年,從此定居巴黎,並進入高等社會科學學院就讀,主修語言學、符號學與心理分析,在羅蘭‧巴特指導下,完成碩士學位。
1980年代休絲頓開始創作生涯,以英文及法文寫作,並自己翻譯(英法對譯),出版過20多部小說與非文學類著作,曾入圍並獲得不少文學獎項,包括高中生鞏固爾獎、法國國家電台書獎、ELLE雜誌最佳年度小說、費米娜文學獎、加拿大總督總文學獎等。2005年則獲頒法國藝術及文學勳章及加拿大官佐勳章,著作有《黑暗樂器》與《天使的印記》等。
最新作品《斷線》是休絲頓第11本小說,法文版榮獲2006年費米娜文學獎,英文版則入圍2008英國柑橘小說獎。
譯者簡介:
陳蓁美,政大廣告系畢,法國Poitiers大學電影博士候選人。一九九六年至二○○四年,旅居加拿大蒙特婁、法國Poitiers、Laval等地求學。回國後從事翻譯,譯有《花的智慧》、《藍色圓圈之謎》、《夜》。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國際媒體推薦★本書的敘事自2004年回溯至1944年,每個句子都有其高明之處……南希‧休絲頓的最新作品是一部成功、詼諧、感人的小說。-觀點(LePoint)雜誌★南希‧休絲頓感興趣的不只是祕密,更是這些祕密存在的理由:記憶的承傳或抹煞記憶的方法——失憶,大戰後有失憶的必要,但就長遠眼光看來,失憶卻危害深遠,因為它切割了真實。-快迅雜誌★南希‧休絲頓以細膩的手法,生動地將童年無言的悲劇呈現在我們眼前,她極為含蓄地令讀者為了這些日常瑣事落淚,而這些日常瑣事卻讓童年的期待與幻影破碎,它可能是一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作者想要探討記憶的不可靠性與難以抹煞的童年經驗。★「我們只是我們能夠成為的那個人,我們難以是我們相信可以變成的那個人。」
得獎紀錄:國際媒體推薦★本書的敘事自2004年回溯至1944年,每個句子都有其高明之處……南希‧休絲頓的最新作品是一部成功、詼諧、感人的小說。-觀點(LePoint)雜誌★南希‧休絲頓感興趣的不只是祕密,更是這些祕密存在的理由:記憶的承傳或抹煞記憶的方法——失憶,大戰後有失憶的必要,但就長遠眼光看來,失憶卻危害深遠,因為它切割了真實。-快迅雜誌★南希‧休絲頓以細膩的手法,生動地將童年無言的悲劇呈現在我們眼前,她極為含蓄地令讀者為了這些日常瑣事落淚,而這些日常瑣事卻讓童年的期待與幻影破碎,它可能是一特別收錄 / 編輯的...
章節試閱
當我們抵達慕尼黑時,空氣裡瀰漫著令人無法理解的語言,我既反感又鬱悶,所以緊緊抓著媽媽的手臂,盡全力聽她跟莎荻奶奶的對話。我雖然全知全能,不過處在偌大的現代化機場裡,我應該繼續表現得像個正常小男孩,看起來一副無所適從的樣子。當我們好不容易踏出機場大門,爸爸已經在等我們,他傻笑著,意味他真希望不用過接下來的日子。他帶我們走向他剛在機場租來的車子,一隻手推著母親的輪椅,一隻手提著行李,一隻耳朵聽妻子,一隻耳朵聽母親,一隻眼睛注意他的小兒子,另一隻眼睛留意深愛的外婆有沒有走失。
我坐在後座,夾在媽媽和曾祖母之間,莎荻奶奶則坐在前座,把地圖攤在大腿上,因為爸爸完全看不懂路標。
「快,我該怎麼辦?左轉?」
「右轉!右轉!」莎荻奶奶用很流利的德語說道。
「他媽的,」爸爸說,他在最後一刻把方向盤轉向右邊。媽媽說:「哦,杭達,你說的是哪國話?」不過她的玩笑話並沒有達到笑果。
「他媽的!」爸爸又說了一次,「妳來開,黛絲?」
媽媽紅著臉,陷在後座裡。
我也不喜歡德文路標,它們就好像一道道大門在我面前關上,讓我碰得一鼻子灰,我拒絕問莎荻奶奶,我不想承認自己的無知。從現在起到我長大成人,地球上所有居民都必須開始說英語,如果他們不說,等我稱王,我第一個要實行的法律就是大家說英語。這個國家陌生的文字讓我起雞皮疙瘩,我的疤還是很難看,戴著猶太圓帽遮醜。我試圖重振雄風,提醒自己是地球上最厲害的六歲男孩,不過要在這部充滿著大人緊張情緒的車子裡,提高士氣不太容易。但至少媽媽緊緊握住我的手,鼓勵我。
我們終於抵達慕尼黑。我們開始找旅館,莎荻奶奶用足以震動全車的嗓音,介紹建築物的歷史,以及哪些地區曾被聯軍炸平,不過我們因為眼前乾淨、現代化的街景而不敢置信。我看著曾祖母一直揮舞雙手,她不斷彎曲瘦骨嶙峋的手指,我發現自從回到故鄉後,她再也沒說過一句話。我偷偷注視她,她兩眼盯著空處,很茫然的樣子,一時間變更老了。
「妳還認得出來嗎?」莎荻奶奶中斷下來,突然問道。她一定是在問她的母親,因為車內其他人都不曾來過慕尼黑,不可能認識這個城市。不過曾祖母沒答腔,她依舊直視前方,絞著雙手,瞬間又變老。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旅館睡覺,我不太喜歡。莎荻奶奶想節省旅費,儘管是她說要招待大家,但她一再提醒我們,她花了一大筆錢,所以她選擇的旅館很便宜,我們必須三個人擠一個房間,莎荻奶奶和曾祖母共住一間,這該是蠻特別的經驗,不過我不想知道特別在哪裡。我們在飯店餐廳吃了很難吃的飯,菜單列了許多最worst(糟糕)的菜,不過卻寫成wurst,莎荻奶奶說wurst指的是香腸(讓媽媽覺得好笑),卻讓我倒盡胃口,我只能吃一塊去了麵包皮的白麵包。莎荻奶奶又說,德語的「我無所謂」,就是「我不把香腸放在眼裡」,讓爸爸覺得好笑,我卻覺得很愚蠢。接著莎荻奶奶轉向曾祖母,曾祖母除了點菜之外,還不曾開口說話。
「媽媽,」她說,這句話出自像莎荻奶奶這樣的老太太口中很滑稽,不過她試著討好母親,想贏得她的歡心,因為大家都不得不注意到,她變得好安靜。「媽媽,妳還記得妳教我的那首和強尼•伯別克有關的歌嗎?那個掉到絞肉機把自己絞成肉醬的傢伙?該怎麼唱呢?」
「拜託!」媽媽說,她認為這樣的歌曲會讓我做惡夢或消化不良。
不管如何,艾禾並沒接腔,只是盯著餐桌啜飲啤酒。沒人知道她怎麼了。
「然後,妳問我:Bolognaise是什麼?妳記得嗎?」
仍然沒有回應。
「小索爾, Bolognaise是什麼意思?」莎荻奶奶轉向我,又問了一次。
「我不知道。」我說。
「是一種義大利麵醬。」爸爸邊笑邊說,他應該聽過這個笑話。
「蠢蛋,答錯了,是住在波隆尼的女士!」莎荻奶奶說,他們兩人哈哈大笑起來,接著莎荻奶奶又問,「小索爾,什麼是Hamburger?」
「在麥當勞買得到的玩意。」我說,不太相信會答對。
「蠢蛋,答錯了,是住在漢堡的先生。」她和爸爸又是一陣暴笑。
「還有……幫幫我,杭達……第三個是?」
幸好我父親也忘記第三個笑話,他們才放棄這個話題。
用餐期間,艾禾一直沉默不語。
我睡得很沉。
第二天早晨有了另一個問題。這家廉價旅館只有白煮蛋(冷),而我只吃不熟的蛋(熱),媽媽到廚房試著跟員工解釋這個問題,不過她不會說德語,沒法讓他們了解,她要莎荻奶奶幫她翻譯,不過已經開始吃早餐的莎荻繼續大快朵頤,聲如洪鐘地說:「別寵壞您的兒子,黛絲!如果他餓了,他什麼蛋都吃,如果他不餓,發牢騷也沒用。」
媽媽一邊走向我一邊聳聳肩,很難過的樣子。我恨那些侮辱她的人,我氣得熱血沸騰,幾乎可以把蛋煮熟。
不幸的,一隻腳已經跨到棺材裡的曾祖母姊姊並不住在慕尼黑,她依然住在她們小時候所住的小鎮,離慕尼黑兩個小時的車程,令人氣餒。
「好遠!」我哭哭啼啼地對媽媽說。
「沒辦法,我的小天使。」
「兩個小時,」爸爸說,「每天早上我也花兩個小時去上班。」
「你不能這麼比較,杭達。」媽媽說,「對小孩來說,兩個小時好像無止無盡。」
「你錯了,」爸爸說,「對我來說也好像無止無盡。」。
我們坐在和昨天相同的位置,曾祖母在我左邊,媽媽在我右邊,我們都坐在後座。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開出慕尼黑,行駛在兩旁都是綠色原野的大馬路上。
「我們現在往東部開,」莎荻奶奶說。「開往奧地利的國界,你們知道的,大名鼎鼎的巴伐利亞堡壘,希特勒最愛的藏匿地貝希特斯加登就在那裡。他在山區挖鑿極其複雜的迷宮,做為自己和朋友的藏身之地,他們在那裡屯積了幾十年也用不完的菸草、香檳、點心和衣物!現在則改建成高級飯店。」
「也就是說,我們離史瓦辛格州長的出生地只有幾步路的距離!」媽媽說,很高興有機會展現自己曾研究過地圖。
「嗯,是的。」莎荻奶奶說。「是可以說只有幾步路遠……但得是巨人的腳步!史瓦辛格出生在格拉茨附近,位於貝希特斯加登西南方兩百五十公里處。」
「啊!」爸爸說,「幸好在這輛車子裡有人那麼清楚!」
「不是,不是。」莎荻奶奶試著讓步,「老實說,黛絲指出這點很對,史瓦辛格的家族與納粹極為友好。」
這是媽媽最不願意碰觸的話題,因此她轉向曾祖母,問她:「再看到這些景色應該有很奇特的感受,不是嗎?」然後突然小聲說:「啊!她睡著了!」
曾祖母頭往後仰,嘴巴張開,小聲打鼾。我沒法拋開她每分鐘衰老一歲的念頭。在這麼近的距離下,她的皮膚好像透明的羊皮紙,上面覆蓋著數以千萬的細紋,她看起來那麼嬌小,那麼孱弱,我從未注意到她是那麼脆弱,好像鬼魅或是死去的麻雀……如果她死了?不,她打著呼,所以她不可能死了,不過我離她遠一點,挽著母親的胳臂,心裡想著:「求求上帝,我不要媽媽變老,求求上帝,讓她永遠年輕美麗……」
我問媽媽還很遠嗎?媽媽教我從瑜珈、佛教等課程學來的智慧:「別一直想要馬上到達,我的天使,告訴自己你已經到了,當下才是你生命中真正的一刻!好好的品嚐!看看美麗的景色。」
我強迫自己欣賞這些景色,高低起伏的田野、翠綠的草原、母牛、農耕機、麥倉、農舍。又是高低起伏的田野、又是母牛、又是麥倉,看起來好像模仿實物的小模型,就好像在動物園偶爾看到的愚蠢小農舍,為了給都市小孩一點鄉村的感覺。高速公路也比加州的高速公路小氣可笑。
到目前為止,這趟旅遊真是超級無聊。
當我們到達曾祖母小時候住過的小鎮時,她剛好醒過來。她跟我一樣清醒時就像打開電燈開關,沒有過渡狀態,眼中沒有倦意,瞬間完全甦醒,注意四周動靜。
她的沉默似乎感染全車的人,沒人說話,十片靜止不動的嘴唇。我的父親把車緩慢開到鎮中心。
突然,莎荻奶奶做了一個出其不意的動作,她從背後探出手,抓住艾禾的手,更出人意料的是,曾祖母握住女兒的手,輕柔地撫摸起來。
說話的是她:「這裡,杭達,你可以左轉然後停車,是的,是那棟大樓,就是那裡。」
接著又是同樣的馬戲表演:從後車廂內拿出輪椅,協助莎荻奶奶坐上輪椅,鎖住車門,諸如此類。路人盯著我們看,把我們當成街頭藝人。我非常清楚我們這群吵吵鬧鬧、花花綠綠的、操著英文口音的人有多麼怪異:一位頭戴假髮的殘障女士、一位白髮巫婆、一個戴著星際大戰猶太圓帽的小男孩,我想對著他們的眼睛射出雷射光,迫使他們看向別處……好不容易,我們終於走進大樓裡。
從外面燦爛的陽光走進室內,陰暗的走廊顯得格外漆黑,不過坐在輪椅上的莎荻奶奶衝到最前方帶路。就在我們手牽著手走在後方時,媽媽彎腰輕聲告訴我:「你也許最好脫掉帽子,我的天使。」
曾祖母挽著爸爸的手臂,她平時從不這麼做,不過今天她走得很緩慢,落後我們一段距離,最後,她完全停住腳步。
「怎麼了?」莎荻奶奶叫道,她已經在走廊盡頭的電梯口等著。
「她的心臟跳得太快。」爸爸叫道,「她要吃藥,妳能不能等一下?」
「當然可以,我們當然可以等一下。」莎荻奶奶說道。「好,我們等一下吧。」
曾祖母從手提包拿出一罐藥,搖動罐子讓藥丸掉到手掌心,再把藥丸放到張開的嘴中。過了一會兒,她點一點頭,再度抓住父親的手臂。
我們聚集在標著3W的大門前。為了讓這個隆重的聚會顯得更為隆重,莎荻奶奶帶著沉重的目光掃視每個人一眼之後,才按下門鈴。
過了一會兒,我們聽到幾道鎖轉動的聲響,接著出現一個龐大女人的身形,在門洞裡形成黑色的剪影。莎荻奶奶用德語問了一個問題,那個女人身影用德語回答,我想如果我整個下午都得聽德語,我會死掉。不過接著莎荻奶奶翻譯說:「她說她的護士碰巧休半天假,留她一人在家,她的病情不容許她善盡地主之誼,不過午餐已經準備好了,等我們開動。這位是桂荷塔。」她加了一句多餘的廢話。
桂荷塔又說了幾句德語,不過曾祖母打斷她。「今天,」她的聲音清澈響亮:「大家都用英語交談。」
她用戲劇化的手勢鬆開父親的手臂,向前走一步,大家讓出一條路。
這對姐妹面對面站著,相隔五十公分,彼此注視著,我們起碼可以說她們長得完全不像,桂荷塔的輪廓粗枝大葉,深深的皺紋把她圓圓的臉頰和下巴切成紅咚咚的肉塊,灰白的長髮編成一條寬鬆的麻花辮盤在頭上,龐大的軀體在粉紅色休閒衣褲下搖晃起伏。
「克莉絲汀娜!」她喃喃說著,並向曾祖母伸出雙手。對我來說,克莉絲汀娜是個陌生的名字,不過我好像是唯一覺得驚訝的人,它應該是曾祖母住在德國時的舊名。「克莉絲汀娜!」她又說了一遍,我看到她滿臉油光上的眼睛邊角閃著淚光。
曾祖母並沒有投入桂荷塔的懷抱裡,她抓住桂荷塔的手腕,把她拉向自己,輕聲說話,說得簡單俐落:「我們進去吧?」
「當然,」桂荷塔帶著德語口音說,「請原諒我,請進,進來,進來,請脫掉鞋子,路上的灰塵很多。」
莎荻奶奶為大家做介紹。桂荷塔跟每個人握手,當她看到我的疤痕時,她皺著雙眉,鑿出W形。
「發生意外?」她指著太陽穴問道。
「啊,沒什麼。」四個大人異口同聲說道,他們都笑了起來,而且又是異口同聲,所以他們又笑起來。不過我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好笑。
餐桌上放了十多種我不能吃的東西:裝飾著肥肉紋路的香腸、酸黃瓜和小蘿蔔、蛋黃沙拉、發臭的乳酪、洋蔥馬鈴薯沙拉、硬綁綁的黑麵包……幸虧媽媽經過廚房時發現一盒玉米片,她問桂荷塔能不能給我一碗玉米片,因為她知道爸爸不會在陌生人面前抗議。
媽媽要大家圍著餐桌手牽著手,她開始做餐前禱告,感謝上帝讓分散六十年的姐妹難得重逢,不過沒人顯得特別高興,包括把大家拖來的莎荻奶奶。祈禱完畢,大家忘了為我鼓掌和親吻我,我開始告訴自己,這次的旅遊是個天大的錯誤。我用最緩慢的速度吃完玉米片,因為媽媽不准我離開餐桌:「我們不是在自己家裡,因此今天要像圖畫般安靜一點,好嗎?」我只好左顧右盼。我好像被關在娃娃屋裡,觸目所及都有擺設,都是裝飾:傢俱和古怪的裝飾品、抱枕和蕾絲小桌巾、水晶碗、雕像、貼著印花壁紙的牆壁、掛在牆上的照片和圖畫。我想變成忍者龜,拳打腳踢,左右開攻,一走了之,轟!啪!砰!碰!或者變成超人更好:只要高舉雙手,就能夠像火箭一樣射到空中,衝破屋頂,急速飛到蔚藍的天空。空氣!空氣!
「所以,妳留在這裡。」曾祖母說。
「是的。」桂荷塔說。「我在這棟房子裡把小孩帶大。」
沉默。曾祖母顯然不想打聽這些孩子的下落。
「學校關了?」過了一會兒她又問道。
「啊!很多年前就關了。這棟大樓後來變成單純的住宅區,自從……六○年代起,我想,就在母親死後不久。」
曾祖母固執地不吭一聲。她為什麼要來?我納悶著,如果她不想來看自己的姊姊,不想重溫兒時的回憶,她為什麼投同意票?她對桂荷塔提起的家人並不感興趣。
「我後來知道是誰檢舉我們,妳知道嗎?是鄰居韋伯恩太太,妳還記得嗎?她的丈夫是共產黨員……是她向那個機構檢舉我們,他們才派那個女人把妳帶走……」
曾祖母沒回答。
「父親,他一九四六年回來,」桂荷塔繼續說,莎荻奶奶興奮點頭,鼓勵她說下去,未留意曾祖母執拗的沉默。「他在蘇俄坐了一年牢後回到家裡,母親告訴他妳和喬安都走了,他哭了一整夜。他還是這裡學校的老師,後來升到校長,最後在六○年代當上鎮長,一直當到退休為止。不過祖父,他就再也沒離開……妳知道的……那家醫院。」
我聆聽這位粉紅色胖女人所說的每句話,小心地把她所說的每句話放在腦袋裡的某個角落,以備未來之需,因為我得通曉宇宙的萬事萬物。不過目前,我聽不懂她的話,而她的說話對象(也就是曾祖母)甚至沒在聽。現在,她做出一項驚人之舉,她在餐桌前點菸,而其他人還沒吃完。不過沒人敢數落她,連媽媽也不敢,因為我們在別人家裡。
寂靜。爸爸打了一個小嗝,自從到達德國後,他不停喝啤酒。我看到媽媽在桌子底下踹他一腳,責備他粗魯的舉止。
「我一直很關心妳的歌唱事業,克莉絲汀娜。」桂荷塔又說道,試圖融化她姊姊眼裡讓人無法理解的冷漠。「我幾乎收藏了妳全部的CD,看!」
她指著CD櫃,大家都轉過頭朝CD櫃看,除了曾祖母。
再度沉默。
莎荻奶奶決定說話,緩和氣氛。
「荷塔桂妳好壞,準備這麼多的豬肉香腸火腿折磨我!」
「啊,上天可以做證!我不是有意的。」
「沒事,我開玩笑的啦,我有一堆東西好吃。」莎荻奶奶一邊說一邊再裝一盤堆得如山高的馬鈴薯沙拉。
「再吃一點肝香腸,克莉絲汀娜?」桂荷塔說。曾祖母用雪茄做作了拒絕的手勢,而桂荷塔為了逗我們開心,大聲說:「你們相信這個瘦小的女人以前想成為馬戲團的胖女王嗎?」媽媽和爸爸笑了起來,即使他們已經聽過這個笑話千百次,我也是。「而我,」莎荻奶奶不顧滿嘴食物說道,「我現在幾乎可以應徵這個工作,嗯?」引起哄堂大笑。我必須要說,看著莎荻奶奶龐大的身驅,實在很難想像它來自艾禾瘦小得跟精靈一樣的身體。
「擺鐘不見了?」曾祖母突然說。「以前有個很漂亮的擺鐘,就在角落……」
又是寂靜。我和媽媽相互看了一眼,因為這次的沉默很詭異。
「妳忘記了?」桂荷塔不敢相信的樣子。「祖父把它砸爛……」
「啊!他把它砸爛?我忘了這件事。」
「妳怎麼能……妳怎麼……那一天是……他砸爛一切和……妳真的不……?」
「不記得了,對不起。我大概經歷太多事,所以這件事的記憶變成……空白。別忘了我年紀比妳小,戰爭結束的時候,妳有……十歲吧,我只有六歲半,差了好幾歲。」
「這倒是真的。」桂荷塔說。她推開餐盤,困難地站起來。「黛絲,」她向媽媽?,「麻煩您為您的家人煮咖啡?現在我得睡一會兒。」
她搖搖晃晃,走了兩步路後,還是不停地搖晃。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莎荻奶奶不能幫她,而她對我們來說是陌生人,我們不敢碰她的身體。艾禾終於起身。
「讓我扶妳吧,桂荷塔。」她說,於是兩個老女人蹣跚地離開房間。
「好精美的瓷器!」媽媽從廚房的碗櫃裡拿出印花杯盤時,讚不絕口地說道。
「是啊,很精緻,不是嗎?」莎荻奶奶說。「一定是來自德勒斯登。」
她們繼續讚賞。我不知道女人怎麼可以整天吱吱喳喳還能沒發瘋;很精緻不是嗎,很嬌脆不是嗎,沒完沒了。現在是喝咖啡的時間,我不必待在餐桌上,我走在走廊上,想找到廁所送出輸入的資料。
我的便便完美,狀如飛彈,結實卻不乾硬,在排出的時候,我不斷自言自語:「我好想念Internet啊!我好想念Google啊!」我打賭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一定沒聽過Internet!
當我在走廊上,輕輕踩著繡著花朵圖案的厚重地毯回客廳時,我看了一下電子錶,已經三點十五分,太好了,媽媽說過我們大約四點離開,所以,半個鐘頭後,我可以開始拉她的袖子,假裝發脾氣:「是妳說的……妳答應我的……」
正當我想像著自己說這些話時,我聽到曾祖母用一樣的口氣說出相同的話:「是妳說的……妳答應我的……」
桂荷塔用德語回了幾句話。
房門半掩。我透過門縫看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我不敢相信:兩個老太太為了一個娃娃吵架。曾祖母抱著一個模樣很蠢、穿著紅色天鵝絨洋裝的娃娃。她氣得五官都變形了。
「它是我的!」她怒斥道,「它一直都是我的,不過就算撇開這一點,就算它不是我的……妳也答應過我的,桂荷塔!」
桂荷塔又用德語回答她。她看起來很疲憊,走到床邊任自己沉重地倒下,彈簧被壓得嘎嘎作響。接著她長聲一嘆,再也不動。
一直把娃娃抱在懷裡的曾祖母,走到床邊注視著她的姊姊許久。不過很不幸,她背對著我,我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
當我們抵達慕尼黑時,空氣裡瀰漫著令人無法理解的語言,我既反感又鬱悶,所以緊緊抓著媽媽的手臂,盡全力聽她跟莎荻奶奶的對話。我雖然全知全能,不過處在偌大的現代化機場裡,我應該繼續表現得像個正常小男孩,看起來一副無所適從的樣子。當我們好不容易踏出機場大門,爸爸已經在等我們,他傻笑著,意味他真希望不用過接下來的日子。他帶我們走向他剛在機場租來的車子,一隻手推著母親的輪椅,一隻手提著行李,一隻耳朵聽妻子,一隻耳朵聽母親,一隻眼睛注意他的小兒子,另一隻眼睛留意深愛的外婆有沒有走失。我坐在後座,夾在媽媽和曾祖...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