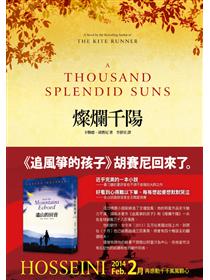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悲傷,雖然輪廓、大小、重量各異,但是悲傷的顏色對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當瑪格麗特打開通往過去的大門時,她面對的卻是自己的命運。
瑪格麗特自小在父親經營的古書店幫忙,個性內向,平時喜歡讀傳記,也嘗試過替古人寫傳。一天,她突然收到知名暢銷女作家薇妲‧溫特的來信。溫特一直過著隱居的生活,非常神秘低調,從未明白道出自己的出身背景,反倒編造了很多離奇故事來唬弄採訪的記者。但是,由於年事已高,加上病痛纏身,她決定說出自己真正的人生故事,於是寫信請瑪格麗特來為她寫傳。
出於好奇,同樣深居簡出的瑪格麗特來到約克郡見溫特。按照溫特的敍述,她的母親美麗而任性,父親、哥哥都聽從於她,而母親的一對雙胞胎女兒則是行為怪異。她對女作家的故事既著迷,又疑惑,無法完全相信。於是她開始著手調查這個家族,依照自己的調查結果將這個家族的故事拼接起來。
然而,尋找真相的過程令人膽戰心驚,並徹底改變了瑪格麗特自己的命運……
作者簡介:
戴安‧賽特菲爾德(Diane Setterfield),1964年生,主要研究十九、二十世紀法國文學,是紀德研究專家。原本任教於大學,1999年辭去教職,開始專心從事寫作。本書是她的第一本小說,卻獲得英美兩地超過260萬美元的簽約金,是同年度新人作家最高金額。戴安現居住於英國約克郡。
譯者簡介:
呂玉嬋,生於台北,藝術碩士。喜愛戲劇、文學及旅行,譯有《偷書賊》等書。
章節試閱
信
事情發生在十一月。我拐進隆德斯巷的時候,時間還不算晚,但是天色早就變黑了。父親已經打烊,關了店裡的燈,拉上百葉窗板;但他留下通往家裡樓梯上的那盞燈沒關,免得我一回家就是一片漆黑。那盞燈穿透門上的玻璃,在潮濕的人行道上投射出一頁紙張大小的蒼白四方形,而我就是站在那個四方形燈影的中間,正準備用鑰匙開門的時候,才第一次看見那封信。信──另一個白色的四方形──擱在下面倒數第五個台階上,我一定會看到的地方。
我關了門,把店鑰匙放回貝里撰寫的《幾何學進階原理》後面的老位置。可憐的貝里,已經三十年沒人想看他那本灰色厚重的書。我偶爾倒是很想知道,他的書變成了書店鑰匙的看守者,他自己會有什麼感想呢?我認為他大概從沒想過,自己花了二十年光陰寫成的代表作,最後會是這般的命運吧。
一封信,給我的,真是稀罕。信封堅實平整,裡面折疊得厚厚的信紙,使得信封都顯得膨脹起來了。收件地址的筆跡採用了老式風格的筆法,有著繁複裝飾的大寫字母與波浪紋狀的花體字,肯定讓郵差吃了不少苦頭吧。我第一個印象認定那是個小孩寫的字跡,筆法似乎沒有受過訓練,字母上不均勻的筆劃不是逐漸消失無蹤,便是沉重地刻印進紙張裡。拼出我名字的那行字母一絲流暢感也沒有,每個字母都是獨立寫成的,彷彿寫我的名字是一個可怕又困難的新計畫──瑪.格.麗.特.李.雅。但是我又不認識什麼小孩,於是我才想到,這是殘疾病患的筆跡。
這封信讓我渾身不對勁兒。當我昨天或前天正忙著自己事情的時候,有位不知名的人士,某個陌生人,靜悄悄地,費了一番功夫把我的名字寫在信封上。到底是誰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留意到我了呢?
我來不及脫下外套和帽子,立刻就一屁股坐到樓梯上讀信。(我從不讀東西,除非確定自己坐在安全的地方,這是我七歲時養成的習慣。那年我坐在一堵高牆上看《水孩兒》,書中描繪的海底生活深深吸引著我,使我不知不覺放鬆了。我腦海裡滿是海水環繞我的生動畫面,但海水不但沒有托起我的身子,我反倒是一頭栽到地上昏了過去,瀏海下面的傷疤現在還摸得到。閱讀也是有危險的。)
我打開信封,抽出一疊厚達六頁的信紙,全是同樣生硬的筆跡。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對於字跡難辨的手稿,有著豐富的閱讀經驗,訣竅只在於耐心與練習,再加上努力,就可以培養出品鑑的眼光。要閱讀一份受過水災、祝融、光線等傷害,或因歲月而磨損的手稿時,眼睛該注意的不光是字母的形狀,還有其他書寫過程中展現出的特點:下筆的速度、紙張承受的筆力、行筆間的頓挫收放。你必須放鬆心情,什麼都別想,等你進入出神境界以後,你就會化身為一枝在羊皮紙上揮舞的筆,而羊皮紙上頭的筆墨則輕輕搔弄著你。到這個境地你才能看出作者的目的、思想、躊躇、期待、意圖,清楚得好像你就是作者振筆疾書時,照亮紙張的那盞燭光。
這封信其實並不像有的手稿那麼具有挑戰性,它以簡短唐突的「李雅小姐」四個字為開場。接下來,鬼畫符般的筆跡很快就自動轉化為字體,然後化為單字,組合成句子。
信的內容如下:
我曾接受《班布里先鋒報》的採訪,改天我得找出來,好收到我的傳記裡。他們派了個奇怪的傢伙來,其實還只是一個孩子,雖然與大人一樣高,但仍有著青春期那種嬰兒肥。他彆扭地穿著一身新西裝,那種難看的棕色西裝是給年紀比較大的男人穿的款式,領口、袖口、布料都不適合他,但是一個做母親的卻會為了小孩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而買一套這種西裝給他,以為小孩總有天能成熟到適合這身衣裳。然而,當小男孩脫下學校制服之際,並不因此就脫離了孩子樣。
他帶著某種特質,一種熱切的態度。見到他的那一刻我心想:「啊哈,他想做啥?」
我對於熱衷想找出真相的人並沒有不滿,只是覺得他們很乏味,只求他們別開講有關「編故事」與「坦率」這兩種話題,這樣會惹毛我。不過,只要他們別來煩我,我也不會礙到他們。
我的不滿並非針對熱愛真相的人,而是對於真相本身。與故事相比,你能從真相裡面獲得什麼援助、什麼安慰呢?當你午夜夢迴,身處黑暗之中,而狂風像是一隻困在煙囪中的熊那般狂亂呼嘯之時,真相又能有什麼幫助呢?當閃電掠過,竟然在臥室牆壁上照出了黑影,雨滴像長長的指甲一般敲打著窗戶時,又能怎樣呢?真相幫不了你。當你在床上被恐懼與寒冷籠罩而無法動彈時,別期望沒血沒肉的真相會跑來拯救你,你需要的是故事帶給你的安慰,你需要的是謊言能帶給你如搖籃般讓人寬心的安全感。
當然,有些作家不喜歡接受記者採訪,想到採訪他們就生氣。「老掉牙的問題,」他們抱怨著。唉,他們想期待什麼呢?記者不過是受聘的寫手,我們作家才是真材實料。記者提出的問題永遠相同,但這不表示我們就得提供相同的答案呀,對不對?我要說的是,編故事正是我們討生活的本領啊。因此,我一年接受數十次採訪,這輩子已經做過幾百次了,因為我從不相信,人必須離群索居才能讓自己的天分發揮。我的才華洋溢,才不會因為記者卑劣的文字而無法展現!
以前他們老想找出我的把柄。他們做好了調查,把一小段真相藏在口袋裡來找我,選個適當的時候掏出真相,以為我會嚇得透露更多的事情。我必須小心謹慎,慢慢讓他們朝著我要他們前往的方向走,利用我的誘餌,神不知,鬼不覺,輕柔地用一個更精采的故事吸引住他們。這是件精巧微妙的工作。他們的眼睛會開始閃爍,不再緊握那些微不足道的真相碎屑,直到最後,真相從他們身上掉落,散在路邊,無人在意。我從來沒有失敗過。一個出色的故事永遠比一段破碎的真相還令人更眼花撩亂。
後來我成名了,訪談薇妲.溫特成了記者們某種階段性的儀式。他們大致知道該期待什麼,若沒有聽見故事就離開的話,那他們會失望的。他們迅速問出標準問題(妳的靈感哪來的?妳的人物是根據真人發展出來的嗎?妳的主角帶有多少自傳成分呢?)而我的答案越簡短,他們越喜歡。(在我腦中。不是。完全沒有。)接著,他們等候的固定節目、他們來訪的真正目的出現了,他們的臉龐悄悄流露出做白日夢的期盼表情,他們就像是臨睡前的小孩子。那麼妳呢,溫特女士,他們說,把妳的事情告訴我吧。
於是我就把我的事情告訴他們。其實只是簡單的小故事而已,裡面沒多少內容,只是幾縷絲線編織成的漂亮圖案,這裡放一個值得懷念的常見基本花樣,那裡放幾片小金屬亮片,只不過是從我破布袋底下拿出的碎片。這些瑣碎小故事多得很,有如從小說故事切下的布邊,又像沒有完成的情節,流產的角色,以及一些我從沒想到要如何利用的美麗場景。零零星星,東湊西拼,接著只需要修剪邊緣,縫合末端,就完成了。又一篇全新的自傳。
記者開開心心地走了,像是在生日聚會終了拿到糖果的小孩,使勁地抓緊筆記本。將來他們會告訴子孫後代:「有次我採訪了薇妲.溫特,而且她跟我說了一個故事呢。」
總而言之,班布里的那個小伙子說:「溫特女士,告訴我真相。」噯呀,那句話有什麼感染力哦?已經有不曉得多少人想出各式各樣的詭計來哄騙我說出真話,我大老遠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意圖,可是這句話呢?可笑。我的意思是,他究竟指望什麼?
這問題問得好。他指望什麼?他的眼睛因為熱切的興奮而閃耀著光芒,他仔細觀察我、探求我、偵測我,他所追求的是明白確實的事情,我很確定。他的前額因為流汗而濕了,也許他正在生什麼病吧。告訴我真相,他說。
我的心底感到某種奇妙的情緒,像是往事甦醒了。一段從前的生活在我胃裡像流水般攪動翻滾,使我血管中湧起一陣浪潮,傳送一波波清涼的微波,在我太陽穴輕輕拍打。這句話多麼刺激人啊:告訴我真相。
我思索他的請求,在心裡反覆考慮,估量可能的後果。這小伙子讓我心神不安,他那蒼白的臉龐,他那燃燒的雙眼。
「好吧,」我說。
一個小時之後,他走了。一聲微弱、恍神的再見,沒有回頭張望。
我沒有告訴他真相。我怎麼能告訴他呢?我告訴他一個故事,一個沒有創意而且情節貧乏的小故事。沒有閃亮亮的東西,沒有圓形小金屬片,只有幾片黯淡褪色的布塊,隨便粗略地縫在一塊,布邊的磨損任由它留著。我告訴他的故事,是看起來像真實人生的那種故事,更準確的說,是我們想像中的真實人生應該發生的故事,但其實人生是另外一回事情。像我這種天份的人,要製造出很像真實人生的故事,還真是不容易啊。
我從窗戶看著他,他拖著腳步,沿著街道走遠,垂著雙肩,低著頭,每一步路都筋疲力竭。他所有的精力、衝勁、氣魄,都已經被我扼殺了,我不會承擔指責的。他早就應該清楚知道,最好不要相信我的話。
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我的那股感覺,胃裡的浪濤,太陽穴,我的指尖,後來伴隨著我好長一段時間。它隨著小伙子那句話的記憶升起下降。告訴我真相。「不行,」我說,一次,一次,又一次。不行。但是水流不止歇,它讓我分心,更糟糕的是,它使我感到威脅。「還沒呢。」它發出嘆息聲,煩躁不安,最後安靜下來。安靜到我幾乎忘記了它。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啊,三十年?四十年?也許更久以前。時間飛逝得比你想像的速度還要快。
那個小伙子最近一直出現在我的心中。「告訴我真相。」而且最近我又再次感覺到那股內在的攪動。我的身體裡有種東西在生長,分裂又增生。我可以感覺到它在我的胃裡面,又圓又硬,大概是葡萄柚的大小。它吸走我肺裡的空氣,啃咬我骨頭中的骨髓。它經過長期的休眠,已經起了變化,從一個柔順服從的東西變成了一個惡霸,不肯與我妥協,阻撓討論的進行,堅持一己的權利。它不肯聽到「不行」這個答案。真相,它重複著小伙子的話,它看著他離去的背影。接著,它轉向我,緊緊抓住我的內臟,扭轉一下:我們有過約定,記得嗎?
時候到了。
星期一搭四點半抵達的火車過來。我會派一輛車子在哈洛格特火車站迎接妳。
薇妲.溫特
讀完信之後,我不知道自己在樓梯上坐了多久的時間。因為我失了魂。文字有種魔力,高明好手的生花妙筆會把你囚禁起來,如同蜘蛛絲纏繞人體的四肢,而且讓你沈浸其中無法動彈,文字會滲入你的肌膚,進入你的血液,麻木你的思考。在你的體內,它們操弄著戲法。等我終於回過神來,我只能臆測在我神昏意亂的幽晦之中,到底出了什麼事情。這封信給我招來了什麼?
我對薇妲.溫特所知甚少。不用說,我當然知道她的大名及種種稱號:英國最受喜愛的作家,本世紀的狄更斯,當今世上最出名的人,現存名聲最響亮的作者,諸如此類。當然,我知道她極受歡迎,可是我後來調查出的數據依然使我吃了一驚。五十六年中,她出版了五十六本書,翻譯成四十九種不同的語言;溫特小姐曾經二十九度獲選「英國圖書館借閱次數最頻繁的作者」;十九部劇情電影改編自她的小說。在統計資料中,最常爭辯的問題就是:她的著作銷售量到底有沒有超越《聖經》?要計算出她的著作銷售量(不斷以幾百萬幾百萬在變動的數字),不會像計算《聖經》那麼困難:不管人們對於主的話有什麼看法,但是大家都知道聖經的銷售數據不可信。我坐在樓梯上,讓我最感興趣的數字大概是二十二:前後已經有二十二個傳記作家宣告放棄挖掘她的真相,不再撰寫她的傳記。這些作家放棄的理由包含缺乏資料、欠缺支持,或受到溫特女士本人的勸誘或恐嚇。不過,在讀信的那個當下,我對這些數字一無所知。我只知道一項數據,這個數據與我當下的情況有關:我,瑪格麗特.李雅,讀過幾本薇妲.溫特的書?零。
我在樓梯上打了個呵欠,伸伸懶腰。一回過神,發現自己的思緒已經在失神時重新整理過了,而且從我的潛意識裡出現了兩件零星片段,引起我的注意力。
首先是跟我父親有關、發生在書店的一個小場景。我們從藏書拍賣會上買回來一箱書,其中有幾本薇妲.溫特的作品。我們的店並不販賣當代小說,所以我說:「等下午餐的時候,我把書拿去二手慈善商店,」並且把這些書放在桌子邊上。不過,一個早上還沒過去,四本書中有三本沒了,賣掉了。一本賣給一位神父,一本賣給一個製圖師傅,另一本則賣給了一位軍事歷史學家。我們的主顧(有著愛書人常見的蒼白面容與內心蘊藏的熱情)發現平裝封面上的鮮豔色彩時,臉孔似乎亮了起來。午餐過後,我們完成了拆箱、編目與上架的工作後,沒有客人上門,我們如往常一樣坐著讀書。時值晚秋,外面下著雨,窗戶濛著霧氣。背景是暖氣的嘶嘶聲;我們對那個聲音置若罔聞,因為我們肩併肩,人在一塊,心神卻相隔數哩遠,各自沉浸在我們閱讀的書本當中。
「我來泡茶好嗎?」我回到現實中,問道。
沒有回答。
我還是泡了茶,放了一杯在他旁邊的桌子上。
一個小時過後,茶涼了,一口也沒喝。我重新沏了一壺茶,在他身旁的桌上又放了個熱騰騰的杯子。他完全沒注意到我的舉動。
我輕輕把他手中的厚書往側邊傾斜一點,好讓我看得見封面。那是第四本薇妲.溫特的書。我讓書回到原位,端詳父親的臉龐。他聽不到我,他看不到我;他正在另外一個世界裡,而我是個幽靈。
那是第一個記憶片段。
第二個是個畫面。四分之三的側影,光與影交刻出一張巨大的輪廓,這張臉龐矗立在等車的通勤者上方。雖然只是一張貼在火車站廣告看板上的宣傳照片,但在我的回憶中,那張照片無情而莊嚴,有如古文明國家為了紀念多年前的女王與神祇所雕刻的石臉。弧度細緻的眼睛,寬廣平坦延伸的頰骨,線條與比例完美無瑕的鼻子。看著她的五官,會讓人驚訝於人類外貌的差異竟然是這麼大,居然能出現這般超自然完美的臉龐。如果未來的考古學家發掘出這樣的骨架,那看起來一定像是人工製品,是一個藝術造詣已達顛峰的作品,不可能是出自大自然的產物。肌膚散發著雪花石膏般不透光的明亮,潤飾了底下精細的骨骼;頭髮精準地排列在纖細的太陽穴附近,沿著強健優美的頸部而下,膚色在精巧編盤的紅銅色頭髮襯托下,顯得更加白皙。
彷彿這般華麗又任性的美麗還不夠,那臉龐上更有一對眼睛,經過某種靈巧的攝影技巧,將這對眼睛的色澤增強到幾乎不屬於人間的色彩,那是教堂窗戶上的綠玻璃,或者是祖母綠寶石,或者是糖果綠。這對眼睛在通勤者頭頂上方凝視,毫無表情。我不知道那天其他旅客對這張照片的觀感是否跟我一樣;他們讀過她的書,因此可能有不同的觀點。但是對我來說,注視著這對綠色的大眼睛,我忍不住想到那句老掉牙的說法:眼睛是靈魂之窗。我記得自己盯著她那綠色、視而不見的眼睛,我是這麼想的:這個女人沒有靈魂。
信送來的那個晚上,我對薇妲.溫特的所知就這麼多了。不多,不過想想,也許別人知道的也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薇妲.溫特,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的長相,知道她的書,但同時也沒有人認識她。她的祕密與她的故事一樣有名,她本身就是一部完美的神祕小說。
照這情況看來,要是這封信裡所說的是真的,薇妲.溫特想說出自己的祕密,這件事本身就夠古怪了。但是更古怪的是接下來我想到的:她為什麼想把祕密告訴我?
信事情發生在十一月。我拐進隆德斯巷的時候,時間還不算晚,但是天色早就變黑了。父親已經打烊,關了店裡的燈,拉上百葉窗板;但他留下通往家裡樓梯上的那盞燈沒關,免得我一回家就是一片漆黑。那盞燈穿透門上的玻璃,在潮濕的人行道上投射出一頁紙張大小的蒼白四方形,而我就是站在那個四方形燈影的中間,正準備用鑰匙開門的時候,才第一次看見那封信。信──另一個白色的四方形──擱在下面倒數第五個台階上,我一定會看到的地方。我關了門,把店鑰匙放回貝里撰寫的《幾何學進階原理》後面的老位置。可憐的貝里,已經三十年沒人想看他那...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74收藏
374收藏

 84二手徵求有驚喜
8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