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職業是護士
生命像一本書,你能讀透多少就有多少不同層次的認知和詮譯!
也許是我「幸運」,第一天實習就遇到了大家最忌諱的「屍體護理」,護士長叫我時,我還楞頭楞腦的跑著去,昨晚剛擦上白粉的護士鞋,被自己匆忙、紊亂的腳步踫得黑斑點點。我惶恐的看著她毫不友善的表情,緊張的等她吩咐,她看了看醫囑,慢條斯理的說:「 Miss林,四十九床的王造平已經死了,你去做屍體照顧!」我懷疑的問:「現在?」
「是啊!你是學過的,而且學校規定必須你一個人完成。」我心想,學歸學,以前是假病人,現在可是真人!想到這,站穩的雙腳突然輕飄飄起來,頭緊跟著蹦了起來,心窩部一陣苦楚,不用診脈我也估量得出,它已經是一百次以上了!
我看著護士長冷酷的眼神、無所謂的態度,只好硬著頭皮往治療室準備用物。
「妳沒問題吧!」一陣輕柔的聲音傳來;我怎敢說有問題?無論如何現在我代表學校,更代表我自己。對於 Miss蕭的問話,我回以一個微笑。她是第三組的組長,也是學姐。
「一定會害怕的,如果妳實在忍不住時,就奪門而出,我會在門外和妳做伴的……不過,據我所知,來這裏實習過的學生,從來沒有人辦不好這件事的,妳一定可以做得無懈可擊!」明知她是安慰我,卻覺這些話很管用。心緒純然是受思想支配的,這一次尤其是。
端著治療盤,壯起膽子,進入了第三室,這兒只有兩張病床,一張是空的,另一張也即將是。我看著那一層白布單,從頭到腳,迎面襲來一陣冷氣,傳遞著生命的孤寂,他尾椎骨部分的床單,留著一攤汙血,我放下治療盤,看看四周,墨綠色的長窗簾隨風搖曳,它好像把我拉近了死亡,於是迅速地拉開它,失望的是,天空依然灰黯,為一具軀殼──沒有生命的軀殼,它也參與了哀悼。
我抓開了白布,定神的去看他的臉龐,不但沒有我預料的可怕,相反的,他安詳而鎮定的走向死亡,從他下彎的嘴角,更可看到這位身經百戰的榮民,從戰場上得來的堅毅和勇敢,無形中,強烈的責任感震撼著我。我帶上手套,取出氣管處的鋼管;雖然他已經沒知覺,可是我卻像在對一位英勇的戰士致最高的敬意,我拿起縫針,很慎重的縫著每一針。每碰一次他的下頷,就憶起他生前講那句話的表情,「我死後要給醫學『用』!」這句簡單而勇敢的承諾,竟成了他唯一的遺囑!
不知不覺的眼鏡卻模糊得看不清縫線,忽然,門開了, Miss蕭走了進來,注視我良久,拍拍我的肩:「妳哭什麼?是害怕啊,真沒出息。」她一說,我竟理直氣壯的嚎啕大哭起來。
Miss蕭不解的看看我:「多做幾個就不怕了」;說著,她協助我取走臀下的那塊「尿布」,擦去血跡。
淚眼滂沱中,護理長站在我的前面:「 Miss林。我知道妳哭什麼。」微笑一下,「我想你絕不是為自己而哭吧!我看過妳以前的見習心得。」停了一下,「妳還年輕,我像妳這種年紀時,在軍醫院工作,為了憐憫、感動、欽敬……我曾認過三位臨死的乾爹,其中一個卻只叫了一聲就沒機會了;後來,我長大了,也學會了克制自己,因為那些都是感情用事;要保持鎮靜,在需要我們的病人之前做最真實的救助。埋藏了那份『婦人之仁』之後,妳會對眼前的難題更有信心,更具衝勁,套句俗話──化悲憤為力量!」我抬頭看到她潤紅的雙眼,閃爍著愛的光芒,卻怎麼也想不透,她會是這所大醫院中最有名的「凶神」!
對於我的遠道來訪,唐嘉不露些許驚訝,連句客套話也都省略了:「嘿!你來得正好,看我女兒表演大便,她會按時大便哦!」
「嗯!就是這個時候……」她從床上跳下來,拿了些衛生紙,墊在小女兒臀下,嗯了好久,她的寶貝女兒才被誘出一小團大便,「今天怎麼這般洩氣,不給媽面子!」她拍著女兒的小腿。突然外面傳來拉圾車的聲音,她緊張的叫道:「阿鳳,趕快!幫我倒垃圾,快點!除了那個筒子,還有那一袋,椅子上的!」我毫無選擇的餘地,拎著袋子,往下奔,聽到「少女的祈禱」又想起內江街的唐嘉。
新生訓練時她曾因為宿舍裏的小蟑螂,花容失色的跑到教官室把教官請來「處理」而名揚全校;第一次見習接生,她也因恐懼而昏倒;第一次實習打針,她顫動的手冰冷無力,緊張得拔針時只拔出針筒;第一次看屍體解剖,她吐得要小吳架著回學校,一個月不敢吃肉;第一次……太多了!
但是誰都沒料到,三年後她選擇的竟是每日與血肉為伍的開刀房工作,她那敏捷、幹練、細心的協助,竟成了許多大夫所樂道的話題,不過那時的唐嘉仍然是享樂派的,她的休閒活動走遍了台北各個角落,她一直強調單身的好處。
直到她遇到了意中人,第一次當媽媽,她才是自己理論的推翻者。看,她為了孩子所做的努力,客廳像嬰兒的遊戲間,輕音樂飄送,小玩具滿箱,有條不紊的白尿布,舒適清爽的嬰兒床……我記得他信中的那段話:「有兩種身分使我覺得不虛此『行』──護士、母親,真的,如果妳是我,妳就會贊成這句話『不學護理,憾為女人;不當人母,更憾為護士』。」
在清涼水果室,等了十五分鐘,都不見小李子的影子,數一數,有兩年不見了她,那守時的習慣不知怎麼丟棄的,正埋怨時,服務員走過來,問了幾句,要我去聽電話,「阿鳳,實在對不起,今天雖是星期天,我接到任務馬上要下高雄,那兒有好多大專的義務工作人員等著,人家幫我買了票,這一去大概要三星期,反正游牧民族的生活,妳知道,嘿,我又黑了!不過沒關係,有空給妳信,厚厚的,向妳工作報告!」從那急緩的口氣,不連貫的字句,我覺得它遞給我公共衛生特有的忙碌!那串日子又重在腦際回響。
那年,我當輔導員,奉命分配三個護士在桃園縣復興鄉,駐鄉任務是做山地家庭計畫工作及配合做溪口專業區之衛生改善。小李子的腳剛開過刀,不適合山裏的徒步,可是十二個人中,她卻是第一個自願下鄉的,她說了許多理由推翻我的拒絕,拗不過她,只好讓她去!
她們駐在復興台地的一個原住民家中,第一天除了蚊子還有跳蚤「歡迎」她們。首先她們還不以為意的繼續工作,直到傷口被抓得皮破血流,小李子才利用下班時間趕回局裏拿了瓶胺水去擦,在風雨中我目送小李子微跛,但穩定、踏實的腳步,一股為人服務的熱誠,直逼而來!
兩星期後,家庭計畫的問卷調查完畢,台地的養豬專業區「開訓」,我隨地方首長,乘會裏的車前往,先繞到小李子那兒,聽到她正用簡單的原住民話,摻雜著國語和原住民交談,民政局長告訴我,有個空位,我叫小李子來坐,她堅持不肯,還懷著感謝的語氣──「林姐,你們先走吧!那條路雖平坦卻要花很多時間,我走這吊橋過去,說不定比你先到達,而且公共衛生工作本來就要和群眾打成一片的!」一位女性原住民走過來,拉著她的手,就嘰哩咕嚕的說了些話,然後用生硬的國語說:「沒關係,她走不動時,我會背她的!」那一刻,我突然的好羨慕小李子。
結訓典禮上,小李子帶他們唱「再見歌」,巴陵區來的一位原住民也回過來教我們唱山地歌,我聽到一個小孩問他媽媽說:「肩膀上有紅叉叉的(紅十字臂章),是不是都是好人?」媽媽點點頭說:「她們叫做白衣……哦!不是,她們是『藍』衣天使。」
「什麼叫天使?」媽媽笑著指教堂的十字架:「就是上帝派來的好人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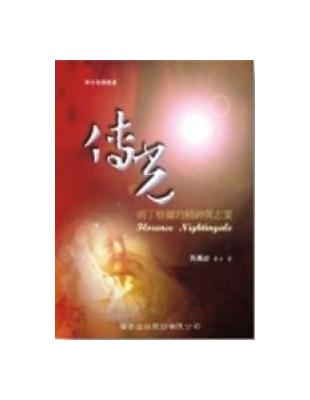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