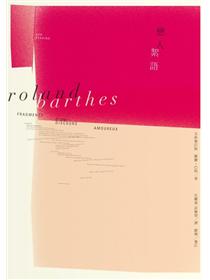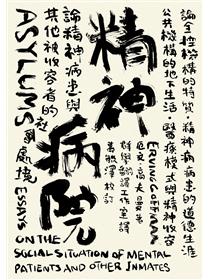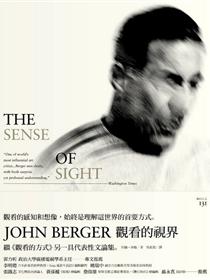《一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學之序論》是康德於1783年出版的一本小書。他撰寫這本書的動機可以直接追溯到他於兩年前出版的大部頭著作《純粹理性批判》。他經過十多年的沉思與醞釀,在1781年初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這部畫時代的鉅著。儘管康德花了極長時間來構思《純粹理性批判》,但他卻是在年歲日增的壓力下,於短短四、五個月內倉卒完稿。只是,這部著作篇幅太過龐大,所探討的問題又極為複雜,還使用了不少新的名詞與表述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根據康德自己的說法,《純粹理性批判》是「一部離開了所有常走的道路、而走上一條我們無法立刻熟悉的新道路之著作」。可以說,他自己早已預見到《純粹理性批判》不容易為一般讀者所理解。而事實上,《純粹理性批判》出版不久後,康德也確實感到有必要另寫一部較為通俗的著作,來闡明《純粹理性批判》之要義。因此,本書可說是康德為了使外行人理解其《純粹理性批判》而特別撰寫的一本書。
作者簡介:
伊曼努埃‧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生於東普魯士科尼希貝爾格(Konigsberg),1804年逝世於該城。他於1740年就讀於科尼希貝爾格大學,1746年至1755年迫於生計而終止學業,擔任家庭教師。1755年他在科尼希貝爾格大學完成學業後,留校任教,直到1797年因年老力衰,才終止授課。在哲學方面,他繼承啟蒙哲學之傳統,綜合歐陸理性論與英國經驗論,形成其批判哲學,開啟從菲希特到黑格爾的德國理念論;就其原創力及影響力而言,誠為近代西方哲學家第一人。其主要著作有《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道德底形上學》、《單在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未來形上學之序論》等。
章節試閱
中譯本導讀:
一、《序論》之成書始末
《一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學之序論》(Prole- 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以下簡稱《序論》)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於1783年出版的一本小書。他撰寫這本小書的動機可以直接追溯到他於兩年前出版的大部頭著作《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他於1770年發表其教授就職論文《論感性世界與智思世界之形式與原則》(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之後,經過長期的沉思與蘊釀,終於在1781年初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這部畫時代的鉅著。儘管康德花了十餘年的時間來構思《純粹理性批判》,但他卻是在年歲日增的壓力下,於短短四、五個月的時間內倉卒完稿 。這部著作之篇幅龐大(共856頁),它所探討的問題又極為複雜,而且康德在書中還使用了不少新的名詞與表述方式。但更重要的是,根據康德自己的說法,此書是「一部離開了所有常走的道路、而走上一條我們無法立刻熟悉的新道路之著作」 。職是之故,他自己早已預見到此書不容易為一般讀者所理解。在此書第一版之〈前言〉中,他便承認:此書是為「學問之真正行家」所寫,而「決無法適合於通俗的運用」 。
果然不出所料,此書出版之後,德國哲學界之反應頗為冷淡。在第一年(1781年)僅出現了兩篇不具名的簡短書評 。連康德極為看重的好友孟德爾頌(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對此書也毫無反應。康德在一封寫於1781年5月11日以後的信中向他的學生黑爾茲(Marcus Herz, 1747-1803)訴苦說:「孟德爾頌先生將我的書擱在一旁,這使我極不愉快,但我希望:這種事不會老是發生。」 他甚至在1783年8月16日致孟德爾頌的信中直接表達了其失望之情:「〔……〕僅致力於探討那座建築〔按:指形上學〕之地基的《批判》〔按:指《純粹理性批判》〕無法吸引您機敏的注意力,或是隨即又使您的注意力移開,這令我極為遺憾〔……〕。」
有證據顯示:就在《純粹理性批判》剛出版不久,康德便已感到有必要另寫一部較為通俗的著作,來闡明《純粹理性批判》之要義。就在康德寫給黑爾茲的上述信函中,康德於談到《純粹理性批判》時寫道:「這種探究總會是困難的,因為它包含形上學之形上學,但我還是想到一個計畫,按照這個計畫,這種探究也能取得通俗性。但是在開頭時,由於要清理地基,通俗性不會得到妥善的處理,尤其是因為這類知識之整體必須按其全部結構被展現出來。」 康德底同鄉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 1730-1788)在1781年8月5日致函康德早年的學生赫德爾(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30)時也提到:「康德準備也為外行人編寫其《批判》底一個通俗的摘要。」 六天之後(即8月11日),哈曼又在寫給出版商哈特克諾赫(Johann Friedrich Hartknoch, 1740-1789)的信中提到:「康德談到其《批判》之一個具有通俗趣味的摘要。他答應為外行人編寫這個摘要。」 同年8月18日康德曾致函哈特克諾赫,可惜這封信並未保存下來。但是11月19日哈特克諾赫回覆康德此函時表示:「如果《批判》之摘要已完成(這我並不懷疑),請將它寄給印過偉大著作的哈雷(Halle)印書商格隆內爾特(Grunert)。但一旦手稿寄出之後,懇請通知我。」 由此或許可以推斷:康德於1781年8月18日在寫給哈特克諾赫的信中可能提到了他為《純粹理性批判》編寫一個通俗摘要的計畫,甚至已著手編寫。其後,哈曼在1782年元月11日致函哈特克諾赫時又提到:「康德正在撰寫道德底形上學──我不知道是為哪個出版社而寫。他還想在接近復活節時寫完他的小著作。」 這裡所提到的「小著作」顯然便是指《序論》一書。但康德並未如期完成此書,因為此時出現了一段插曲,使康德改變了寫作計畫。
1782年1月19日在《哥廷根學報》(Göttingische Anzeigen von gelehrten Sachen)附冊第1冊刊出了一篇對於《純粹理性批判》的不具名書評 。這篇書評之原作者是加爾維,後經《哥廷根學報》底編輯費德爾之大幅刪節與小幅修改,而以目前的形式發表(以下簡稱〈哥廷根評論〉)。加爾維出生於布雷斯勞(Breslau),曾擔任萊比錫大學哲學教授,是18世紀德國「通俗哲學」(Populärphilosophie)底代表人物之一 。
這篇書評引發了康德與加爾維之間的第一次辯論。日後,加爾維在他於1792年出版的《試論道德學、文學與社會生活之各種對象》(Versuche über verschiedene Gegenstände aus der Moral, der Litteratur und dem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 Breslau)一書中批評康德底批判哲學及其方法論。康德於次年9月出刊的《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第12期(頁201-284)發表一篇長文〈論俗語所謂:這在理論上可能是正確的,但不適於實踐〉(“Über den Gemeinspruch: 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 taugt aber nicht für die Praxis”),在其中的一節回應加爾維之批評 。
在〈哥廷根評論〉中,評論者將《純粹理性批判》視為「一套高級的(或者如作者所稱,超越的)觀念論之系統」 ,並且將它與英國經驗論哲學家柏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之觀念論相提並論 。不但如此,評論者在書評之最後一段對《純粹理性批判》總結道:「但對我們而言,作者似乎並未選擇在無節制的懷疑論與獨斷論之間的中道,亦即縱非完全滿意、但卻放心地回歸最自然的思考方式之真正中道。」 而此處所謂「最自然的思考方式」便是訴諸「通常的人類知性」(gemeiner Menschenverstand) 。
在康德底用法中,「通常的人類知性」一詞往往與「通常的人類理性」(gemeine Menschen- vernunft)、「健全的人類理性」(gesunde Menschenvernunft)、「健全的人類知性」(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互換其詞。它們均相當於英文中的common sense 一詞。這是以里德(Thomas Reid, 1710-1796)、歐斯瓦爾德(James Oswald, 1703- 1793)、比提(James Beattie, 1735-1803)、史蒂瓦爾特(Dugald Stewart, 1753-1828)等人為代表的蘇格蘭「常識哲學」(common sense philosophy)之核心概念,而為加爾維底「通俗哲學」所繼承。接著,評論者指出脫離此一「中道」後可能導致的流弊:
而以理性思考者如何脫離此途呢?這是由於他將兩類的感覺──內在感覺與外在感覺──相互對勘,並且願意使它們相互融合或轉化。當內在感覺底知識被轉化為外在感覺底形式或者與它相混雜時,由此便產生唯物論、擬人論(Anthropomorphismus)等。當外在感覺得以與內在感覺並列的合法地位,亦即其特點,被否認時,由此也產生觀念論。懷疑論一下子這麼做,一下子那麼做,為的是將一切弄得亂七八糟,並且動搖一切。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的作者也是如此。由於他想要將實體與現實性底概念視為僅屬於外在感覺,他誤判了內在感覺之權利。但是他的觀念論更加反對外在感覺之法則,以及由此而產生且合乎我們的本性之表象方式與語言 。
換言之,對評論者而言,康德底「觀念論」可能會導致唯物論、擬人論、懷疑論等觀點。
康德對這篇書評極為不滿,因為評論者完全誤解了《純粹理性批判》之真正觀點。但這種誤解並非這篇書評之作者所獨有。例如,哈曼在讀了這篇書評之後,在1782年4月22日寫信給赫德爾,在信中表示:「我愉快地讀了對於《純粹理性批判》的哥廷根評論。〔……〕作者〔按:指康德〕一定不會對它滿意;他是否有理由不滿,我不知道。在我看來,這篇評論是深刻的、坦率的與合宜的。可以確定的是:沒有柏克萊,就不會有休謨,就像沒有休謨,就不會有康德。」 在這封信中,哈曼還提到:康德正在撰寫「一套尚待撰寫的形上學之序論」(“Prolegomena einer noch zu schreibenen Metaphysik”),而它是「龐大作品之精粹」(“Kern und Stern des großen Organi”)。這似乎是指康德原先計畫為《純粹理性批判》撰寫的通俗版。
然而,這篇書評卻促使康德改變了原先的計畫,而在這部計畫撰寫的新書中針對〈哥廷根評論〉加入一些釐清與辯解的文字。在《序論》底〈附篇〉中便有一節題為〈在探討《批判》之前就對它作評斷的樣例〉。在這一節中,康德直接反駁評論者在〈哥廷根評論〉中對《純粹理性批判》提出的批評。康德以罕見的辛辣口吻寫道:
他〔按:指評論者〕似乎根本不了解在我所從事(無論成敗)的探討中真正的問題之所在。無論是對於透徹思考一部長篇著作之不耐,還是由於一門他認為早已得到全面澄清的學問面臨改革而產生之惡劣心情,抑或──我不願作此猜測──一種實際上有局限的理解力要為此負責,使他從未能在思想上超越其學院形上學;簡言之,他猛然瀏覽一長串的命題──我們若不知這些命題之前提,就根本無法思考任何東西──,偶而發出他的指摘,而讀者不知道其理由,一如他不了解這種指摘所要針對的命題,且因此,他既無法為讀者提供訊息,也無法在行家底判斷中對我造成絲毫損害。因此,若非這種評斷給我機會去作若干闡釋,而這些闡釋能使本書底讀者在若干情況下免於誤解,我完全不會理會它 。
因此,康德斷然否認「《純粹理性批判》是一套高級的(超越的)觀念論之系統」這項評論。他以嘲諷的口氣回應說:
一看到這幾行文字,我立刻知道這裡會出現什麼樣的評論。這約略像是一個對幾何學從無所見所聞的人發現一部歐幾里德底著作,而被要求對它下判斷;他在翻閱時偶然見到許多圖形之後,或許會說:「此書是關於繪畫之一種有系統的指示;作者使用一種特殊的語言,以提出晦澀難解的規定,而這些規定最終所能達成的,不過是每個人憑一種良好的自然目測就能完成之事」云云 。
康德特別強調他自己的觀念論有別一般的觀念論。他將從古希臘伊里亞學派到近代英國經驗論哲學家柏克萊之觀念論概括為一句:「凡是藉由感覺與經驗而得到的知識均無非是純然的幻相,而且唯有在純粹的知性與理性之觀念中才是真理。」 反之,他將自己的觀念論建立在另一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原理之上,此即:「凡是僅出於純粹知性或純粹理性之關於事物的知識均無非是純然的幻相,而且唯有在經驗中才是真理。」 他還將自己的觀念論特別稱為「形式的或批判的觀念論」,以有別於柏克萊之「獨斷的觀念論」與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7-1650)之「懷疑的觀念論」 。
在《序論》§13之〈附釋二〉及〈附釋三〉中,康德也特別說明他自己的觀念論(「批判的觀念論」)之意涵。他強調:他自己的觀念論並不否定外在世界之存在,故正好與一般的觀念論相反 。他將自己的觀念論稱為「先驗的觀念論」或「批判的觀念論」,以別於柏克萊之「神祕的且狂熱的觀念論」與笛卡爾之「經驗的觀念論」或「夢幻的觀念論」 。他甚至意有所指地說:
〔……〕我對觀念論底一切過分要求的抗議是如此簡潔而明暸,以致若不是有不夠格的裁判,這種抗議甚至似乎是多餘的。這些裁判情願為一切與其雖然常見、但卻顛倒的意見不合者冠上一個舊名稱,而且決不對哲學稱謂底精神下判斷,而僅執著於字面;因此,他們準備以他們自己的幻覺來取代明確的概念,且藉此扭曲並破壞這些概念 。
此外,《序論》中的若干段落顯然也是針對〈哥廷根評論〉而發。例如,康德在《序論》一書之〈結語〉中討論「純粹理性之定界」時,在§57及§58論及休謨底《自然宗教對話錄》(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一書中有關「理神論」(Deismus)與「有神論」(Theismus)的辯論。依康德底理解,「理神論」底觀點是將上帝視為「一個包含所有實在性的事物」 ,而否定其人格性;反之,「有神論」則肯定上帝之人格性,因而預設一種「擬人論」。在這個脈絡中,康德指出:休謨對理神論的批駁是無力的,因為它所涉及的「只不過是理神論主張之論據,而決非其命題本身」 。反之,康德認為:休謨對有神論的批駁是非常有力的,因為它涉及有神論所預設的擬人論 。康德自己將理神論的「上帝」概念視為「一項必要的假設」 ,由此可以過渡到有神論 。康德所主張的有神論固然也預設一種擬人論,但這只是一種「象徵的擬人論」,而非「獨斷的擬人論」,因為它並未將任何我們藉以設想經驗對象的特性加諸上帝,因而未逾越純粹理性之界限 。最後,康德總結道:
在此,理性底批判標示出在休謨所反對的獨斷論與他所要採納的懷疑論之間的真正中道;而這種中道並非如其他的中道──人們建議彷彿機械地(從一邊取一些,從另一邊又取一些)為自己決定這些中道,而且無人由此得到更多的教益──一樣,而是人們能根據原則精確地決定的一種中道 。
這些說法無疑是在回應〈哥廷根評論〉中關於「其觀念論可能導致擬人論」的質疑,以及「康德並未選擇真正的中道」之批評。
康德在《序論》底〈附篇〉中回應〈哥廷根評論〉之餘,最後他還要求評論者現身 。這項要求得到了積極的回應。加爾維於1783年7月13日寫信給康德 ,承認這篇書評與他有關。但是他特別說明:
如今以這篇評論目前的樣子來說,我固然決無法承認它是我的評論。如果它是完全出自我的筆,我會遺憾萬分。我也不相信:這份學報底任何一位其他的編輯若是獨自作業,會產生如此亂無章法的東西。但我的確多少參與其事 。
根據加爾維在信中所述,這篇書評目前的形式是經過一位「哥廷根學者」(指費德爾)之删節與修改。加爾維並且解釋說:
您可以相信:在看到這篇評論時,您本人所感受到的反感或不快不會像我這麼多。我的原稿中之若干語句事實上被保留下來,但是它們的確不及我的評論底十分之一,且不及〈哥廷根評論〉底三分之一 。
但是阿諾德(Emil Arnoldt, 1828-1905)在詳細比較了加爾維底評論與〈哥廷根評論〉之後,發現加爾維所言不實。根據阿諾德之統計,〈哥廷根評論〉之全文(共312行)可分為四類:1)抄錄加爾維之評論而完全未加修改者(共76行);2) 抄錄加爾維之評論而僅在措辭上略加修改者(共69行);3) 摘錄或濃縮加爾維之評論而未改變其意義與用語者(共55行);4) 費德爾自己的補充及他對加爾維底觀點的闡述(共112行)。前三類(共200行)可視為出自加爾維之筆,佔全文篇幅將近三分之二,而非三分之一 。此外,加爾維之評論在篇幅上是〈哥廷根評論〉之三倍有餘。以此推算,〈哥廷根評論〉約保留了加爾維底評論之五分之一,而非十分之一。
後來加爾維取回其原稿,並且將它寄給尼可萊(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 1733-1811),尼可萊便將全文刊登於他所創辦的雜誌《德意志萬有文庫》 。在比較過加爾維底原稿與〈哥廷根評論〉之後,波洛克(Konstantin Pollok)總結如下:
費德爾之介入加爾維底文本誠然留下了明確的痕跡:事實上,〈哥廷根評論〉比原先的版本較少連貫性,而特別是其語氣為費德爾所大為加強。加爾維原先的評論顯得較少傲慢與自負,也未與柏克萊及休謨相比較,關於觀念論的爭論被表述得較為溫和,而且完全沒有關於懷疑論的爭論。但無論是在個別的評論還是整體的評斷當中,這兩個文本之間幾乎無所出入 。
此外,康德早期的學生蘇爾茲(Johann Schultz, 1739-1805)在其1783年8月28日寫給康德的信中也談到加爾維底原稿,並且提出如下的評斷:
它〔按:指加爾維底原稿〕比低劣的〈哥廷根評論〉好得太多了,而且在事實上顯示:加爾維先生花了許多精力詳細研究過您的《批判》。然而,它對您如此重要的作品卻不太公允,以致就整體而言,它毋寧還是對您的作品不利 。
總而言之,加爾維在信中的說辭似有推卸責任之嫌。在信函之末尾,加爾維特地請求康德不要公開他在信中所言,以免令費爾德難堪。
康德隨即於8月7日給加爾維寫了一封回函 。康德在信中表現了極大的善意,一開頭便表示:「現在我享有更純粹的愉悅,即是在大札中見到明確的證明,顯示您那種一絲不苟的耿直與通情達理的體貼心態,而這些特質賦予您那些精神稟賦以真正的價值。」 接著,他表示接受加爾維之解釋:「可敬的先生!您可以堅定地相信我,甚至隨時到萊比錫博覽會向我的出版者哈特克諾特探詢:我從未相信他的一切保證,說您在這篇評論上參與其事,而如今我極其高興由您善意的報導證實了我的揣測。」
不論康德是否真的接受加爾維底解釋,〈哥廷根評論〉之出現顯然改變了康德底作計畫。1782年8月25日哈曼致函赫德爾時提到:「〔……〕我今天聽說:康德已請人謄寫他的新論著,它可能涉及哥廷根的評論者。其標題似乎不同於我告訴您的標題――『一套尚待撰寫的形上學之序論』。」 但即使哈曼在此所言屬實,他所提到的「新論著」仍非《序論》一書之定稿。因為在《序論》之〈附篇〉中有一節題為「建議先探討《批判》再作評斷」,而康德在此提到艾瓦爾德(Schack Hermann Ewald, 1745-1822)在《哥塔學報》(Gothaische gelehrte Zeitung)第68期(1782年8月24日出刊)以匿名對《純粹理性批判》所作的評論 。因此,《序論》一書不太可能在8月25日以前定稿。除了康德底改寫之外,印刷商格隆內爾特之延誤也延遲了此書之出版時間 。此書係在1783年春季出版,正好趕上復活節年市 。
二、關於《序論》之撰寫與版本的爭議
由於相關資料之不足,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後如何形成撰寫《序論》之計畫,在康德研究者當中始終有爭論。其中最著名的是艾爾德曼(Benno Erdmann, 1851-1921)與阿諾德之爭論。針對《序論》一書之形成,艾爾德曼提出所謂「雙重編輯假說」(“Hypothese einer zweifachen Redaktion”) 。根據此一假說,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出版之後原先有兩個關於此書的寫作計畫:一是為外行人撰寫一個通俗版,二是為行家撰寫一個簡明的摘要。但是最後康德僅完成了後一計畫。而在撰寫此一摘要的過程中,康德又受到〈哥廷根評論〉及其他批評――如來自哈曼、蘇爾茲、希培爾(Th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 1741-1796)、克勞斯(Christian Jakob Kraus, 1753-1807)等人的批評――之影響。因此,在以目前的形式出現之《序論》一書中,這兩個動機交錯在一起,而出現兩種不同的文本。艾爾德曼在他所編的《序論》版本中,以小字排印他認為康德針對各種評論而插入的段落,以資區別。然而,阿諾德卻強烈質疑這個「雙重編輯假說」,認為這只是艾爾德曼之猜測 。阿諾德認為:雖然康德起初計畫為《純粹理性批判》撰寫一個「通俗的摘要」,但是後來(1781年10月)卻放棄了這項計畫 ;因此,這個胎死腹中的「摘要」與日後完成的《序論》根本是兩回事。他推斷:康德是在1782年2月上旬開始撰寫《序論》,而於同年9月中旬完稿 。
關於這場爭論之細節,懷興格(Hans Vaihinger, 1852-1933)與佛蘭德爾(Karl Vorländer, 1860-1928)均已有所評述 ,筆者在此無意續貂。儘管相關的文獻不足以確定事實之真相,但筆者在比較各家之說後,認為佛蘭德爾之推斷較為合理,故引述於次:
康德於1781年8月要讓哈特克諾赫出版的《摘要》與日後的《序論》決無法(如阿諾德所言)嚴格地區別開來,而是後者由前者發展出來。但我願意比艾爾德曼走得更遠,即是甚至在簡明的摘要與通俗的摘要之間也不明確地加以區分 。
在〈哥廷根評論〉出版之前,康德已在撰寫日後的《序論》,這在我看來,即使不是確定的,但卻是可能的。他的計畫受到〈哥廷根評論〉之影響,或者不如說,因它而修改,也是可能的 。
如果佛蘭德爾之上述推斷無誤,我們便不難理解《序論》一書在編輯上的錯亂。撇開小問題不談,最明顯的錯亂出現在§2與§4中。針對這兩節中的文字錯亂,懷興格提出所謂的「錯頁假說」(“Blattversetzungs-Hypothese”) 。懷興格猜測:或許由於康德本人之疏忽,再加上排版工人之誤判,原屬於§2的五段文字被錯置於§4。懷興格建議將這五段文字移到§2之末尾,並為其中的一段「依本義而言的形上學判斷均是綜合的……」(“Eigentlich metaphysische Urteile sind insgesamt synthetisch…”)補上標號 “3.”。這樣挪動之後,的確使§2與§4這兩節文字在邏輯上較為一貫,而不致顯得突兀。因此,儘管有人反對懷興格之「錯頁假說」 ,佛爾蘭德與馬爾特(Rudolf Malter, 1937-1994)在其各自編輯的《序論》版本中均採納懷興格之建議。
在懷興格「錯頁假說」之基礎上,庫爾曼(Georg Kullmann)進一步提出兩個調整文本的建議 。首先,他將原版中被置於§4中的第二及第三段(如今已被懷興格移置於§2)――自「純粹數學的知識所以別於所有其他先天知識之主要特點在於……」(“Das Wesentliche und Unterscheidende der reinen mathematic- schen Erkenntnis von…”)起的兩段――再度向前挪移到「首先必須注意的是……」(“Zuvörderst muß bemerkt werden...”)一段之後。其次,他將原版中屬於§2的「幾何學家所預設的若干其他原理……」(“Einige andere Grundsätze, welche die Geometer voraussetzen...”)一段之前後兩部分對調,而成為以「在此,我們通常相信……」(“Was uns hier gemeiniglich glauben macht…”)開頭的一段文字。這進一步的調整使§2中的文字在邏輯上更為一貫。因此,波洛克所編的《序論》版本便同時採納懷興格與庫爾曼之建議。本書也採納此一調整方案。
中譯本導讀:一、《序論》之成書始末《一切能作為學問而出現的未來形上學之序論》(Prole- 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以下簡稱《序論》)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於1783年出版的一本小書。他撰寫這本小書的動機可以直接追溯到他於兩年前出版的大部頭著作《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他於1770年發表其教授就職論文《論感性世界與智思世界之形式與原則》(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之後,經過長期...




 6收藏
6收藏

 21二手徵求有驚喜
2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