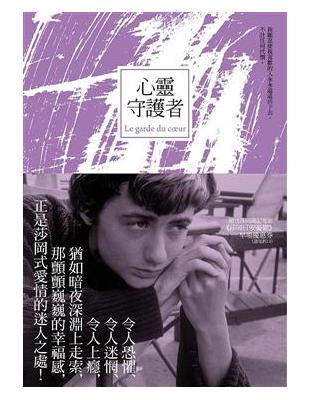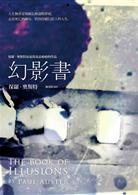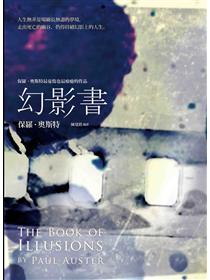我名叫朵荷蒂.西蒙,今年四十五歲,容貌有點憔悴,因為我生活中沒有一件事能好好預防這點。我是很成功的劇作家,還非常討男人喜歡,或許是他們也討我喜歡的緣故吧。我是讓好萊塢蒙羞的少數特殊人物之一:二十五歲時,我在一部充滿哲理的電影中擔綱演出,名噪一時;二十五歲半,我和一名左傾畫家遠赴歐洲,大肆揮霍賺來的錢財;二十七歲時,我再度回到故鄉好萊塢,沒沒無名,身無分文,還訴訟纏身。因為我毫無清償債務的能力,原告只好撤銷控訴,又因為我從前響亮的名字已讓無情的觀眾忘得一乾二淨,便雇用我編寫劇本。我對此甚感高興,因為我一向就討厭簽名、拍照、榮耀之類的事。我變成了「原本該當如此的人」(就同某些印第安酋長一樣)。感謝我愛爾蘭祖父的遺傳,我擁有健康的身體、豐富的想像力,我終於在編寫愚蠢膚淺的彩色電影劇本上逐漸享有聲名,令我吃驚的是,這類劇本的酬勞似乎很高。雷開比影業公司的歷史劇情片通常都是我編寫的,有時候我還夢見埃及豔后克麗奧佩特拉向我走過來,痛苦地對我說:「不可以,女士,我不可以說出『原諒吧,啊,我心靈的主宰者,我心已屬凱撒』這句話。」
那一晚,保羅.布萊特該是我心靈的主宰者。最起碼是我身體的主宰者。為此,我已呵欠連連。
保羅其實是個很俊美的男子。他是雷開比以及許多影業公司的代理。他風度高雅,和藹可親,相貌美得猶如彩筆畫出來似的。因此,和我們同輩的兩位影壇妖姬,也就是十年來經常在銀幕裡扮演蕩婦,叼著長菸斗,騙取男人錢財與愛情的帕美菈.克莉絲以及露易菈.史倫普,皆先後如痴如迷地愛上他,和他分手之後,也傷心欲絕,以淚洗面。保羅有個光輝燦爛的過去。然而那天晚上,儘管處境特別,我看著他,卻覺得看到的是個金髮小男孩。一個四十多歲的金髮小男孩。很令人洩氣,不過我也不能不屈服:八天以來,不斷獲贈他送的花,接到他的電話,聽他的言下之意,和他一起出門,像我這種年齡的女人,最起碼屬於我們圈內的女人,就應該讓步。該來的日子終於來臨了,深夜兩點,我們以一百四十的車速回我簡陋的小屋去。性生活對人是如此重要,我第一次感到非常悲哀。我當時很睏。可是前一天和三天前的晚上,我也很睏,所以我沒有權利再說睏了。我感覺到保羅以前那句體諒話「當然嘍,乖寶貝」將無可避免由另一句話「朵荷蒂,不管什麼事,你都可以對我說……」所取代。我得取出冰塊,拿出一瓶威士忌,輕晃酒杯讓杯裡的冰塊噹噹作響,然後把酒遞給保羅,躺在起居室的大沙發上,如寶萊特.歌達
我嘆了一口大氣,而保羅悶叫了一聲。
燈光下,一名男子像瘋子一樣,或者說像我在法國鄉下見過的四肢脫臼的稻草人一樣,往我們衝過來。我不能不說我的金髮男孩反應出奇靈敏。他死命剎住車子,把車連同他美麗的女友(也就是我)一起拋向右邊的壕溝裡。我眼前似乎出現了一連串幻影,之後,我明白自己正躺在地上,鼻尖埋在草堆裡,手裡還抓著皮包:很奇怪,因為不管在哪兒,我老是忘記我的皮包(什麼反應令我在可能發生死亡車禍之際抓住這個小錢包呢,我永遠無法知道)。我聽到保羅嗓音異常焦慮地叫我的名字,我知道他安然無恙後,如釋重負,再度閉上雙眼。那個瘋子沒被車子撞著,我沒受傷,保羅也沒事。接下來會有些形式上的事要處理、心情會很激動等等,晚上我獨自一人在家睡覺的機會很大。我有氣沒力地說「保羅,一切都好」,然後爬起身,擺個舒服的姿勢坐在草地上。
保羅大聲說:「謝天謝地!」他總喜歡以激情無比的老套成語說話。「謝天謝地,親愛的,你沒事。我剛剛以為……」我不知道他剛剛以為什麼,因為這時響起了一聲可怕的爆炸聲,我們互相摟得緊緊地撲在地上打滾,一直滾到離壕溝十公尺遠的地方。我耳朵幾乎震得半聾,雙眼無法視物。我情緒有點焦躁,掙開他的手臂,好看看正在燃燒的捷豹跑車。車子燒得如一把火炬,一把保了險的火炬,但願如此。保羅也跟著坐起身,說道:「天啊……是汽油。」
我有點懊惱,問他道:「車上還有沒有什麼東西會爆炸的?」
我頓時想起那個瘋子。也許此時此刻他正給烈火燒著。我立刻往前衝,往馬路上跑過去,站起身時還發現絲襪抽了絲。保羅跟在我身後。一個身影躺在柏油路上,沒讓火燒到,但是靜止不動。我起先只看到火光照得發紅的棕色頭髮,輕而易舉將那人扳過身之後,我看到一張如同孩子般的男人臉孔。
有件事情必須解釋明白:我從來沒喜歡過、現在也不喜歡、將來也絕不會喜歡很年輕的男子。這些男子在歐洲被稱作「小貓」。令我驚奇的是,擁有個年輕情人這回事似乎愈來愈風行,許多我的女朋友正是如此。這幾乎要歸咎到佛洛伊德所說的情結上了。乳臭未乾的小伙子不該投身在酒味沖鼻的女士懷裡。然而,火光下躺在地上的這人的臉孔,如此年輕、完美無瑕、卻已顯得很冷酷的臉孔,讓我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情感,令我既想逃避,又想擁有。可我沒有任何戀子情結。我心愛的女兒住在巴黎,婚姻美滿,兒女眾多。每當夏天我到蔚藍海岸去度一個月的假,她就想把孩子託給我照顧。還好,我很少獨自一人旅遊,因此之故,我可以把未盡母責的事歸咎於對社會禮節的顧慮。再回頭談談那天晚上和路易的事吧。那個瘋子,那個田野裡的稻草人,那個昏迷不醒的男子,那張俊美的臉孔,叫作路易。我在他面前靜止不動地待了一會兒,也沒摸摸他的心臟,也沒察看他是否還活著。我看著他,他是死是活似乎對我一點也不重要。這種情感也許無法理解,而且我後來不得不為此深感懊悔,但這並非一般人所以為的意思。
保羅嚴肅地說:「他是誰?」
好萊塢人士之所以令人佩服,就是因為他們總想認識或認出每個人。保羅感到不愉快,因為他無法直接以某個名字來稱呼這個在三更半夜差點被他撞死的男孩。我惱起火來。
「保羅,我們現在可不是在雞尾酒會裡!你想他是不是受傷了?哎唷……」
從陌生男子的後腦勺和手上淌出來些許紅褐色液體,那是血。從溫度、黏糊糊的觸感、以及可怕的光滑感,我辨識出那是血。保羅跟我同時看到血,說道:「我沒撞到他,我很肯定。一定是汽車爆炸的時候,車子的碎片擊中了他。」
保羅站起身,嗓音很平靜,很穩定。我開始有點明白為什麼露易菈.史倫普要哭泣。
「朵荷蒂,不要動,我去打電話。」
他大踏步往遠處黑乎乎的屋影走過去。我獨自一人留在馬路上,蹲在這個也許會死去的男子身旁。突然,他睜開雙眼,看著我,對著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