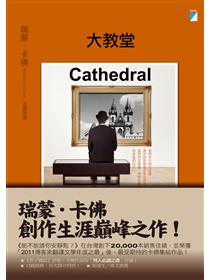沒有瑞蒙.卡佛,我們將看不到今天的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推崇卡佛是他寫作的啟蒙導師,他曾說:「我的寫作,多數來自瑞蒙‧卡佛的啟發。」
★卡佛被譽為自海明威以降,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小說家!
★《倫敦時報》評譽卡佛為「美國的契訶夫」
★2011年三月號《聯合文學》專題巨幅介紹
★(知名文評家)南方朔 專文導讀
★各大文學教授、藝文界、報紙媒體 齊聲推崇!
有一種小說很奇特,讀著它,你還不覺得血脈沸騰,但之後,當你開車、吃飯、行走、與人聊天,進行一切日常活動時,卻一再地想到它,這時你才驚覺,它已滲透了你;原來,它的力量不在於書寫出偉大,而是寫出了你所有的生活--瑞蒙.卡佛的作品,正是如此﹗
卡佛曾說過︰「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生不是什麼冒險,而是一股莫之能禦的洪流。」在這本《能不能請你安靜點》所收錄的22則短篇小說裡,我們所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人生片段。寫的完全不是冒險奮戰的英雄人物,而是我們身邊毫不起眼卻終日陷在生活瑣事、人際關係難題裡的小人物。
〈他們不是你的丈夫〉
描寫一個丟了工作的業務員,靠老婆在餐廳端盤子維生。一日,竟因為目睹客人在老婆身後指指點點她肥胖身材而燃起斗志,他發揮了業務本能,為老婆實行嚴苛的減肥計畫,再將她像件商品一樣展示出去,享受眾人讚賞的眼光。
〈夜校〉
寫一個失業、住在父母家的男人,有一天在酒吧遇見兩個搭訕的女人卻全然不覺對方明顯的意圖,甚至在最末引發兩個女人的辱罵也毫不理會,完全處於一種與社會脫節的生活狀態裡。
〈為什麼,寶貝?〉
是一個母親的告白。在與兒子的鴻溝逐日漸增之下,她束手無策,甚至懼怕起兒子,終至搬離家園、隱性埋名,即使透過報章得知兒子功成名就,也不敢再提起曾有過的母子關係。
〈沒人說一句話〉
呈現一種表面平靜、卻隨時崩離的家庭關係︰就在這一天,當小孩帶著戰利品回家,準備討家人歡心的時候,竟面對了這個家庭最冰冷、父母婚姻關係即將徹底掀牌的一刻……
卡佛以極簡的文字,將生活中最不起眼的時刻寫得趣味盎然,他的風格影響了當今許多名家︰村上春樹不但翻譯他所有的作品,並一再陳述寫作受其影響甚鉅;卡佛的筆法也成了許多創作者模仿的對象;美國文評更贊譽他是「自海明威以降,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家」。然而對我們平凡讀者而言,卡佛的作品值得一再閱讀之處,更在於它與我們的生活是如此貼近,讓我們看見︰原來,平凡的生活也能發出微光﹗
作者簡介:
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
美國短篇小說家,詩人。
被譽為自海明威以降,最具有影響力的美國短篇小說家。
《倫敦時報》推崇他是「美國的契訶夫」。
1938年,出生於俄勒崗州,19歲高中畢業後,即奉子成婚。他曾做過鋸木工人、門房、送貨員、圖書館助理維生,但生活仍難以為繼。卡佛人生的前半部分,在失業、酗酒、破產中度過,妻離子散,貧困潦倒,但始終懷抱著作家夢,堅持創作。
他的寫作功力是苦學而來,直至四十歲,即70年代後期,才逐漸在文壇嶄露峰頭,而後在1983年獲米爾德瑞─哈洛斯特勞斯生活年金獎;1985年獲《詩歌》雜誌萊文森獎;1988年被提名為美國藝術文學院院士,並獲哈特福德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同時獲布蘭德斯小說獎。然而,卡佛享受成名的滋味並無太久,只活到五十歲就過世了。他所留下的作品並不多,主要有《能不能請你安靜點?》、《大教堂》、《憤怒的季節》等短篇小說集和詩集。作品亦被改編成《銀色.性.男女》等電影。
儘管卡佛一生創作並不豐,對後世作家的影響卻相當巨大,尤以村上春樹為著。這位日本當代名家,曾譯過卡佛許多作品,為他做過很多評註,更直接透露自己在寫作上受到卡佛很大的影響,卡佛是他最景仰的美國偉大作家。學界亦常以兩者的文本做比較。村上說:「我的寫作,多數來自瑞蒙‧卡佛的啟發。」
卡佛的文字向來被歸為極簡主義,他作品中快樂的成分不多,大都是讓人想笑又笑不出來的黑色幽默;而他所描寫的,大多來自生活物品與細節,以及再平凡不過的小人物:舉凡情人、夫妻、母子、同事等,或是電話、電視、咖啡,都成為卡佛書寫的對象。他的小說沒有災難劇情的表相,卻有最波動、最無奈的人生際遇與寫照,就如他所言:「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生不是什麼冒險,而是一股莫之能禦的洪流。」
瑞蒙.卡佛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跨越世紀,三十年來持續被全球廣大的讀者拜讀,影響後世作家,或許正在於他不為任何「偉大」的目的而書寫,雖不經意,卻深刻地為我們鑿斧出最偉大動人的生命之書。
譯者簡介:
余國芳
中興大學合作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主編,目前是自由譯者,有《大魚老爸》、《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爆醒惡夢的第一聲號角》、《屠夫男孩》、《冥王星早餐》、《慾望的盛宴》、《輝丁頓傳奇》、《外出偷馬》等超過四十部文學與非文學譯作。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他們推崇卡佛,為他瘋狂︰
藝文界:
王盛弘(作家)、王聰威(小說家)、甘耀明(小說家)、向陽(詩人)、李佳穎(小說家)、李維菁(小說家)、李志薔(作家)、吳鈞堯(小說家)、何致和(小說家)、東年(小說家)、高翊峰(小說家)、凌性傑(詩人)、梁文道(評論家)、陳育虹(詩人)、賀景濱(小說家)、楊照(評論家)、劉梓潔(作家)、黎紫書(小說家)、蔡逸君(小說家)、駱以軍(小說家)、鍾文音(小說家)、顏忠賢(作家)(按筆劃順序排列)
文學教授:
李瑞騰(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邱貴芬(中興大學台文所特聘教授)
紀大偉(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郝譽翔(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
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郭強生(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梅家玲(台灣大學台文所教授)、馮品佳(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
黃錦樹(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廖炳惠(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
鍾怡雯(元智大學中語系副教授)
(按筆劃順序排列)
通路書店&報紙媒體:
宇文正(聯合副刊主任)、孫梓評(自由副刊副主編)、傅月庵(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楊澤(中時人間副刊主編)
(按筆劃順序排列)
◎他們為卡佛讚嘆:
村上春樹:「在『想要親手把這麼棒的作家介紹給日本人』的熱情推動下,我著手了卡佛作品的翻譯。這樣的熱情與想法,讓我能夠持續十年翻譯瑞蒙.卡佛的作品。對我來說,翻譯卡佛的作品是無法計量的貴重學習。若說,我現在對翻譯卡佛的作品尚有遺憾,那就是:卡佛留下來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說,我已經都譯完了。」
梁文道:「契訶夫以降,單憑短篇小說便能成名的作家恐怕數不出多少個,而瑞蒙.卡佛便是其中最受推崇也最有影響力的的一位。因為他那招牌的簡約風格總能在省略中埋下張力,於空白處填上不可以言語形容的無奈、憂鬱與孤獨。在他筆下,短篇小說成了現代生活的最佳畫像,雖然冷峻,但種種細瑣無聊的吉光片羽卻又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詩意;猶如文學中的Edward Hopper,是我們這個時代留給後人的記號。」
顏忠賢:「瑞蒙.卡佛是個悶的很有意思的傢伙。他使最日常生活的索然無味變成最著名的困境。使美國的自豪或不曾自豪的庸俗變成可怕的最具這個時代精神的災難。無法逃離。一如我們。」
李维菁:「我好愛瑞蒙.卡佛!我曾經一度把他的小說集翻到快爛掉,對我的寫作有相當影響!」
陳育虹:「被譽為『美國契訶夫』的他做過鋸木工人、門房、送貨員、圖書館助理;他說他不是『天生的』詩人或任何什麼,他只相信最好的藝術絕對根植在現實生活中,而寫作是為了溝通。精確簡約是他文字的特色,『最終,我們一切所有,只是文字;而最好這些文字是精確的,標點點在對的地方。』他說。」
劉梓潔:「寶瓶問我可否推薦卡佛,看到信我就尖叫……我才剛從美國買了卡佛這本書的原文版! 買時還一邊碎碎唸,怎麼台灣出版社都沒有眼光引進……」
王聰威:「有些小說很明顯的,你一讀就知道如此驚心動魄的事情不太可能會在你的日常生活裡出現,比方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實在太難了吧。另外當然有些小說相當平淡,可能比你的日常生活更無聊,同樣的,你絕對不會想到:「啊,我的生活跟小說一樣!」
瑞蒙.卡佛的小說卻恰如其分地讓我覺得日常生活有一種「小說感」,也就因此感到非常可怕。每日,我如同一般的狀況下平凡地生活著,沒有什麼好炫耀的人生,但是卻有什麼惡意的東西隱藏在街角等著撲殺我。這一日沒有發生,也許就在下一日發生,總之是無可避免的,無法挽救的,一定會來臨的,不在這處街角,就在另一處街角。讀瑞蒙卡佛的小說,就像人生已被透視,並無情地被提早告知了。」
蔡逸君(小說家):「他的小說這麼的好,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文字才能表達崇敬,只能在心裡喃喃:太好了太好了……」
王盛弘(作家):「以簡約的文字與結構,逼視粗礪、曖昧,複雜萬分的生活切片。」
何致和(小說家):「閱讀卡佛,讓我想起小學時代那位紮著馬尾、戴著圓框眼鏡,連續四年作文比賽都拿第一名的女生。有時候我們只能遠遠看著這些人的背影,他們巨大到讓你連想要超越的念頭都不致於產生。也幸好有這些人的存在,我們才能充份享受到自在與安全,有如在烈日底下躲進龐大石像陰影面那般舒暢。」
李志薔(作家):「以最少的文字,寫出最荒涼的人心;幾十年後,瑞蒙卡佛的小說依舊擄獲了村上春樹、蘇童和我等之心。事實上,我是在讀過卡佛的小說之後,才算窺進短篇小說的堂奧。我也建議所有想寫小說的新人,都應該先從卡佛讀起。」
甘耀明(小說家):「瑞蒙.卡佛不像記者寫些聳動的新聞來嚇人,而像日常的觀察者,挖出平日的生活樣貌。他的小說看似尋常,裡頭卻遮藏銳利的細節,每看完一篇後總會令人大喊:『他太厲害了,幫我偷窺到了鄰居的祕辛。』」
高翊峰(小說家):「我深深相信,如果海明威的短篇堆砌出美國文學的一座高峰,瑞蒙.卡佛的小說,誕生於這座峰頂;如果海明威終一生成就了「冰山理論」的文學價值,卡佛以一生削去冰山菱角,寫成他願意留落漂浮的六十五篇短篇,都是裸露水面的八分之一。」
凌性傑(詩人):「瑞蒙‧卡佛《能不能請你安靜點?》讓我看見現代生活的冰山一角,沒說出的部分永遠比說出的多更多。特別是那些故事,以一種幾乎沒有大事的悲哀,給了我深深的一擊。他筆下的一切,或許就是現代人的宿命。」
郝譽翔(中正大學台文所教授):「卡佛總是使用最簡單平凡的字句,卻能迅速切出人生中最無奈的片刻,和最荒謬的悲喜。他的小說從頭到尾沒有冷場,就像一塊透明而冷冽的水晶,讓人看過之後就一輩子難以忘記。」
傅月庵(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有一種作家,小說寫得密密麻麻,看得你透不過氣來,彷彿被掐著脖子,只得說好!瑞蒙卡佛不是這種的。他的文筆精鍊,用字準確,絕不浪費一個字。『狀難寫之情,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這種功夫,一如中國畫裡的『留白』,讓你能呼吸,能思索,能對話。所以,我們都愛卡佛,他不掐人脖子!」
名人推薦:◎他們推崇卡佛,為他瘋狂︰
藝文界:
王盛弘(作家)、王聰威(小說家)、甘耀明(小說家)、向陽(詩人)、李佳穎(小說家)、李維菁(小說家)、李志薔(作家)、吳鈞堯(小說家)、何致和(小說家)、東年(小說家)、高翊峰(小說家)、凌性傑(詩人)、梁文道(評論家)、陳育虹(詩人)、賀景濱(小說家)、楊照(評論家)、劉梓潔(作家)、黎紫書(小說家)、蔡逸君(小說家)、駱以軍(小說家)、鍾文音(小說家)、顏忠賢(作家)(按筆劃順序排列)
文學教授:
李瑞騰(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邱貴芬(中興大...
章節試閱
1 他們不是妳的丈夫
厄爾‧歐伯丟了推銷員的工作。多麗,他的太太,在城外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咖啡店裡當夜班的女服務生。有一天晚上,厄爾喝著酒,忽然決定到那家咖啡店去吃點東西。他想看看多麗上班的地方,看看是否可以點些什麼東西來吃。
他坐在櫃台上研究菜單。
「你怎麼來了?」多麗看見他坐在那裡就問。
她把一份點單交給廚子。「你想點些什麼,厄爾?」她說。「孩子們沒事吧?」
「他們很好,」厄爾說。「我要咖啡和一份二號的三明治。」
多麗把他點的東西寫下來。
「有好康的嗎,妳明白我的意思?」他對她眨眨眼說。
「沒有,」她說,「現在別跟我說話。我正忙著。」
厄爾喝著咖啡,等著三明治。有兩個穿西裝的男人,鬆著領帶,敞著領口,坐到他旁邊叫咖啡。多麗拎著咖啡壺走開的時候,其中一個男的對另外一個說,「你看那個屁股,真是厲害。」
另外那個哈哈大笑。「我看過更厲害的。」他說。
「我就這個意思,」第一個說。「可是有些傢伙就愛大屁股。」
「不是我。」另外一個說。
「我也不是,」第一個說,「我說的就這個意思。」
多麗把三明治放在厄爾的面前。三明治周圍還擺了炸薯條、涼拌包心菜和醃黃瓜。
「還要別的嗎?」她說,「牛奶?」
他沒吭聲。看她還站在那兒,他只搖了搖頭。
「我再給你們加些咖啡。」她說。
她拎著咖啡壺回來,幫他和那兩個男人倒完咖啡,再取了一個碟子,轉身去挖冰淇淋。她搆進冰桶拿杓子挖冰淇淋,白裙子貼著臀部,一路往大腿上提。露出了裡面粉紅色的束褲,腿胯的肉灰白起皺,還帶著一些汗毛,腿上佈滿了青筋。
坐在厄爾旁邊的兩個男人交換著眼色。其中一個挑起眉毛,另外一個咧著嘴,湊著咖啡杯繼續死盯著多麗,看著她把巧克力糖漿淋在冰淇淋上頭。就在她開始搖奶昔罐子的時候,厄爾站起來,餐點也不吃了,逕自往門口走。他聽見她在喊他的名字,他只管走他的。
***
看過孩子們之後,他走向另外那間臥室,脫掉衣服。他拉起被單,閉上眼胡思亂想。感覺先是從臉上開始,然後一路下到肚子和腿。他睜開眼,腦袋在枕頭上來回磨蹭,不一會兒他側轉身睡著了。
早上,多麗送走小孩去上學之後,回到臥室,拉開窗簾,發現厄爾已經醒著。
「妳去照照鏡子。」他說。
「什麼?」她說。「你說什麼?」
「去照照鏡子就是了。」他說。
「要看什麼?」她說。不過她還是去梳妝台照了照鏡子,順便刷開肩膀上的頭髮。
「怎麼樣?」他說。
「什麼怎麼樣?」她說。
「我實在不想說,」厄爾說,「可是我覺得妳最好考慮一下節食這件事。這不是開玩笑,我很認真的。我覺得妳稍微減掉幾磅就好了。千萬別生氣啊!」
「你在說什麼?」她說。
「我剛才不是說了。我覺得妳可以稍微減掉幾磅,就幾磅而已。」他說。
「你以前從來沒說過這種話。」她說。她把睡袍提到臀部上面,轉身對著鏡子看自己的肚子。
「我以前從來沒覺得那是個問題。」他說,用字遣詞盡量小心。
睡袍仍舊攏在多麗的腰上。她背轉身,越過肩膀看自己的背後。她把一邊的屁股抬起來,再讓它自動垂下。
厄爾閉上眼。「也許我錯了。」他說。
「我想減重並不是做不到,只是很辛苦。」她說。
「妳說得對,確實不容易,」他說。「我會幫妳。」
「也許你是對的,」她說。她放下睡袍看著他,然後把睡袍脫了。
他們倆聊著減肥食物,聊著全蛋白質飲食減肥、全素食減肥和葡萄柚果汁減肥。可是他們買不起全蛋白質飲食所需要的全牛排大餐,多麗又說她不喜歡吃那麼多的蔬菜,加上她也不太愛葡萄柚果汁,所以她也不會採用這種方法。
「好吧,算了。」他說。
「不,你是對的,」她說。「我來想別的辦法。」
「運動怎麼樣?」他說。
「我光在店裡運動量就足夠了。」她說。
「那就不吃吧,」厄爾說。「反正就幾天而已。」
「好,」她說。「我試試。就試個幾天,我聽你的。」
「記住,我是妳的後盾。」厄爾說。
***
他估算了一下活存帳戶的餘額,開車到折扣商店去買了一個浴室磅秤。他看著店員在收銀機結帳。
回到家他叫多麗脫掉全身的衣物,站上磅秤。看到那些青筋的時候,他忍不住皺眉,手指順著其中一條青筋往上爬。
「你在幹嘛呀?」她說。
「沒有。」他說。
他看了磅秤,把數字記在一張紙上。
「好了,」厄爾說,「好了。」
第二天的面試幾乎佔去了他一整個下午。雇主,高大威武的一個男人,帶厄爾到庫房看水管配備的時候,厄爾才發現他竟然是跛腳,他問厄爾方不方便四處出差旅行。
「很方便。」厄爾說。
那人點頭。
厄爾笑了。
***
他還沒開門就聽見屋裡電視的聲音。他走過客廳,孩子們也沒抬眼看他。廚房裡,多麗裝扮好了準備上班,正在那兒吃炒蛋和培根。
「妳在幹什麼?」厄爾說。
她繼續嚼著食物,腮幫子撐得鼓鼓的。可是一會兒,她又把嘴裡的東西全部吐到餐巾裡。
「我忍不住啊。」她說。
「笨蛋,」厄爾說。「吃吧,吃吧!盡量吃吧!」他走進臥室,關上門,躺在被單上,還是聽得見電視的聲音,他又把兩隻手枕在腦後,瞪著天花板。
她打開門。
「我會再試一次。」多麗說。
「好啊。」他說。
兩天後的早晨她在浴室裡喚他。「你看。」她說。
他看看磅秤,打開抽屜取出那張紙,再看一次磅秤,她在笑。
「快到一磅了。」她說。
「了不起。」他拍著她的屁股說。
***
他看分類廣告,去了州立職業介紹所。每隔三四天,他便開車外出參加一次面試,每天晚上數著多麗帶回來的小費。他把紙鈔放在桌上撫平,把銅板、零錢以一元為單位,把它們一堆堆的排好。每天早上他監督她上磅秤。
兩個星期的時間她掉了三磅半。
「我有偷吃,」她說。「我餓了一整天,上班的時候有偷吃一點,就只有這樣。」
一個星期之後她掉了五磅,再過一個星期,九磅半。衣服穿在身上都鬆垮垮的,她只好從房租裡挪扣一些錢買新制服。
「上班時候人家都在說閒話。」她說。
「什麼閒話?」厄爾說。
「說我臉色蒼白之類的,」她說,「說我看起來都不像我了。他們擔心我體重掉得太多了。」
「掉太多又怎樣?」他說,「別理他們,叫他們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他們不是妳的丈夫,妳不必跟他們過日子。」
「我得跟他們一起工作。」多麗說。
「沒錯,」厄爾說。「可是他們不是妳的丈夫。」
***
每天早上他跟隨她進浴室,等著她站上磅秤,他拿著紙和筆蹲在地上,紙上寫滿了日期、星期和數字。他讀著磅秤上的數字,再查看那張紙頭,查看的結果不是點頭就是噘嘴。
現在多麗賴床的時間愈來愈長。孩子們一上學她就回床上睡覺,下午上班之前她也要打個盹。厄爾幫忙打掃整理屋子,看電視,由著她去睡。採買的工作也由他包辦,偶爾才去參加一次面試。
有一天晚上他把孩子安頓好上床睡覺,關掉電視,決定出去小喝兩杯。可酒吧打烊了,他就開車到那間咖啡店。
他坐在櫃台等候服務。她看見他,說,「孩子們都好吧?」
厄爾點點頭。
他慢條斯理的點著菜。她在櫃台後面忙進忙出,他不時的看著她,最後他點了一份吉士漢堡。她把點單交給了廚子,再去招呼其他的客人。
另外一個女服務生拎著咖啡壺過來為厄爾注滿一杯咖啡。
「妳那個朋友是誰?」他朝他自己的老婆點點頭。
「她叫多麗。」女服務生說。
「她跟我上次看見她的樣子變了很多啊。」他說。
「我哪知道。」女服務生說。
他吃著吉士漢堡,喝著咖啡。客人不斷地進來擠到櫃台邊。櫃台邊的客人多半是多麗在招呼,偶爾另外那個女服務生也會過來拿點單。厄爾一面盯著自己的太太一面用心聽人說話,中間因為上廁所不得不離開座位兩次。每次他都懷疑自己是不是漏聽了什麼。等到第二次回座,他發現他的杯子不見了,有人坐在他原來的位子上。他只得挑了櫃台盡頭的一張凳子,旁邊是個穿條紋襯衫的老男人。
「你還要什麼?」多麗看見他就問。「該回家了吧?」
「再給我一杯咖啡。」他說。
厄爾旁邊的男人在看報。他抬起頭,看著多麗替厄爾倒咖啡。她走開的時候他瞥了她一眼,然後回頭繼續看報。
厄爾啜著咖啡,等著男人開口說話。他從眼角的餘光瞄著那男的。男人已經用完餐點,餐盤推到一邊,點起一支菸,摺一下面前的報紙,繼續看報。
多麗過來收走了用過的餐盤,再替那人加了些咖啡。
「你覺得如何?」厄爾對著男人說,把腦袋衝著走遠的多麗點了一下。「你不覺得有什麼異樣嗎?」
男人抬起頭。他看看多麗再看看厄爾,再繼續看他的報紙。
「怎樣,你覺得如何?」厄爾說。「我在問你。覺得好還是不好?告訴我。」
男人刷刷的抖了抖報紙。
多麗又從櫃台那頭轉過來了。厄爾頂了頂男人的肩膀說,「你聽我說,注意她的屁股。注意看好了。我想要一杯巧克力聖代!」厄爾喚住多麗。
她停在他面前大聲的嘆了口氣,然後轉身取了碟子和冰淇淋杓。她趴向冰桶,彎下腰,開始拿杓子往冰淇淋裡挖。多麗的裙子揪到了大腿上,厄爾朝著男人眨眼。可是那男人的眼睛卻被另外那個女服務生吸了過去。接著男人把報紙夾在胳臂底下,一隻手往口袋裡掏錢。
另外那個女服務生直接走向多麗。「那傢伙是誰啊?」她說。
「哪個?」多麗端著冰淇淋碟子四處看。
「他呀,」另外那個女服務生向厄爾的方向點一下頭。「那個痞子誰啊?」
厄爾擺出一副最佳的笑容,並且維持不變,直到他覺得自己的臉都快變形了。
另外那個女服務生還是盯著他不放,多麗這才慢慢的搖了搖頭。男人把一些零錢擱在咖啡杯旁邊,站了起來,只是他也在等著聽答案。大夥全都盯著厄爾。
「他是個推銷員。他是我先生。」多麗聳聳肩膀,終於說。說完了她把還沒舀好的巧克力聖代擺在他面前,開始幫他結帳。
2 你是醫生嗎?
電話響了,他穿著拖鞋、睡衣、睡袍衝進了書房。因為十點已過,這通電話一定是太太打來的。她每次出遠門的時候,晚上都會來電話──總是在這個時候,喝過幾杯之後。她做採購,這一整個星期她都在出差。
「喂,親愛的,」他說。「喂,」他再說一次。
「是哪位?」一個女人發問。
「啊,哪位啊?」他說。「妳打幾號?」
「等一等,」女人說。「273-8063。」
「這是我的電話沒錯,」他說。「妳怎麼會有這個號碼?」
「我不知道。我下班回家後,看到一張紙上寫著這個號碼。」那女人說。
「誰寫的?」
「我不知道,」女人說。「應該是是小孩的保姆吧,我猜。」
「哦,我不知道她怎麼會有這個,」他說,「這確實是我的電話號碼沒錯,只是並沒有登錄在電話簿上。我想妳最好把它扔了。喂?妳聽見我說話嗎?」
「有,我聽見了。」女人說。
「還有別的事嗎?」他說。「時間很晚了,而且我在忙。」他不想失禮,可是防人之心不可無。他就著電話旁邊的椅子坐下來說,「我不是有意唐突,只是時間真的晚了,再說我很在意妳怎麼會有我這支電話號碼。」他脫掉拖鞋,按摩著腳丫子,等待回應。
「我也不知道,」她說。「我剛才說了,我只看見紙上寫著這個號碼,其他什麼也沒有寫。我會問安妮的──就是那個保姆──等明天看到她的時候。我不是故意打擾你。我下班回來就一直在廚房。」
「沒關係,」他說,「沒事。就把它扔掉忘掉就沒事了。沒有問題,不必放在心上。」他把話筒移到另一隻耳朵上。
「你聽起來是個很好的人。」女人說。
「是嗎?謝謝誇獎。」他明知道應該掛斷了,但是在這麼安靜的房間裡聽見一個聲音的感覺真好,即使是他自己的聲音。
「是啊,」她說,「我聽得出來。」
他放開擱在腿上的那隻腳。
「你怎麼稱呼,不介意我問吧?」她說。
「我叫阿諾。」他說。
「你的大名?」她說。
「阿諾是我的名字。」他說。
「啊,抱歉,」她說,「阿諾是你的名字。那你貴姓啊,阿諾?你姓什麼?」
「我真的要掛斷了。」他說。
「阿諾,別這樣啦,我叫克萊拉.何特。那你是阿諾某某先生?」
「阿諾.布雷,」他說完立刻補上一句,「克萊拉.何特。太好了。不過我真的要掛斷了,何特小姐。我正在等一個電話。」
「對不起,阿諾。我並不是故意要占據你的時間。」她說。
「沒關係,」他說。「跟妳談話很愉快。」
「你真會說話,阿諾。」
「妳等我一下好嗎?」他說。「我得去找個東西。」他往書房裡找了一支雪茄,花一分鐘時間拿桌上的打火機點上火,摘下眼鏡對著壁爐那邊的鏡子照了照自己。再拿起電話的時候,他有些擔心她會不會已經離線了。
「喂?」
「喂,阿諾。」她說。
「我以為妳已經掛電話了。」
「喔沒有。」她說。
「關於妳有我電話號碼的事,」他說。「不必放在心上。把它扔掉就好了。」
「我會的,阿諾,」她說。
「那,我得說再見了。」
「是啊,當然,」她說。「我現在也要說晚安了。」
他聽見她呼了口氣。
「我知道我有些過分,阿諾,你覺得我們是不是該找個地方見面聊一聊?就幾分鐘?」
「這恐怕不行。」他說。
「就一會兒時間,阿諾。我發現你的電話號碼這些事情,我強烈的覺得有這必要,阿諾。」
「我是個老男人。」他說。
「喔,你不是,」她說。
「真的,我很老了。」他說。
「我們可以碰個面嗎,阿諾?我還有好多事沒跟你說,關於別的事情。」女人說。
「妳的意思是?」他說,「妳究竟在說什麼?喂?」
她掛斷了。
他準備上床睡覺的時候,太太來電話,他聽得出來有些醉意,兩人聊了好一會兒,他並沒提起另外那通電話的事。掛完過後,他正要拉開被罩,電話又響了。
他拎起話筒。「喂。我是阿諾.布雷。」
「阿諾,很抱歉剛才電話斷了。我還是那句話,我覺得我們一定要見個面。」
***
第二天下午,他才把鑰匙插入鎖孔,便聽見屋裡的電話鈴聲。他甩下公事包,帽子、大衣、手套都還穿戴著,就趕到桌旁拎起話筒。
「阿諾,抱歉又來打擾你,」女人說。「今天晚上九點到九點半左右,你務必過來我家裡一趟。你可以嗎,阿諾?」
聽見她喊他的名字,他心動了。「我不能答應。」他說。
「拜託啦,阿諾,」她說。「真的很重要,不然我不會開這個口的。今晚我走不開,因為秀莉感冒了,我得顧著那個男孩。」
「妳的先生呢?」他等答案。
「我沒結婚,」她說。「你會來吧,會嗎?」
「說不準啊。」他說。
「我懇求你來。」她迅速說完地址,便掛斷了。
「我懇求你來。」他重複說了一遍,手裡仍握著話筒。他很慢很慢的摘下手套,脫掉大衣。他覺得自己必須謹慎小心。他進浴室盥洗,照鏡子時,發現頭上還戴著帽子。就在這時間,他決定去見她,他摘下帽子和眼鏡,用肥皂洗臉,仔細檢查指甲。
***
「你確定是這條街嗎?」他問司機。
「就是這條街這棟樓。」司機說。
「繼續往前開,」他說,「到街尾再放我下來。」
他付了車資。上層窗戶的燈光照亮了陽台,他看見欄杆上的盆栽和隨地散置的一些戶外擺設。其中一面陽台上,有個穿長袖運動衫的大個子挨著欄杆,看著他走到門口。
他按下克萊拉.何特的門鈴。開門的蜂鳴聲響起,他回到門口走進去。他慢慢爬上樓梯,每到一層平台便稍微歇一下。他記起盧森堡那家旅館,他跟他太太一起爬上五樓,那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他忽然覺得身子有一邊痛了起來,想著會不會是他的心臟出問題,會不會就此兩腿發軟,會不會從樓梯往下栽,砰砰的一路摔到底。他掏出手帕擦擦前額,再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等待那顆心臟回復平靜。
他往門廳瞧,這棟公寓非常安靜。他停在她的門口,摘下帽子,輕輕的敲門。門開了一條縫,露出一個胖胖的、穿睡衣的小女孩。
「你是不是阿諾.布雷?」她說。
「是的,我就是,」他說。「妳媽媽在家嗎?」
「她說你會來。她要我告訴你說她去藥房買咳嗽藥水和阿斯匹靈。」
他帶上門。「妳叫什麼名字?妳媽媽跟我說過,可是我忘記了。」
見那女孩不說話,他再問一次。
「妳叫什麼名字?該不會叫雪莉吧?」
「秀莉,」她說。「ㄒㄧㄡ──四聲『秀』。」
「對,現在我想起來了。其實我猜得很接近了,對吧。」
她坐在面對面的一張座墊上看著他。
「是妳生病了,對吧?」他說。
她搖頭。
「沒有生病?」
「沒有。」她說。
他環看四周。整間房就靠一盞金色的落地燈照明,落地燈架上附著一個大型的菸灰缸和一個書報架。靠牆擺著一台電視,電視開著,但聲響很小。有條窄窄的通道通往公寓的後門,還有暖爐也開著,空氣裡有一股藥味。咖啡茶几上擱著一些髮夾和髮捲,一件粉紅色的浴袍垂掛在沙發上。
他又看了看孩子,然後抬眼望廚房,陽台和廚房中間隔著玻璃門。那門沒關緊,一絲寒意從細縫鑽進來,他想起了那個穿運動衫的大個子。
「媽媽出去一下下。」孩子好像忽然醒過來似的說。
他費力的傾著身子,拿著帽子,注視著她。「我要走了。」他說。
這時有鑰匙在鎖孔轉動,門開了,一個小小的、蒼白、滿臉雀斑的女人,提著一個紙袋走進來。
「阿諾!好高興看到你!」她很快的、不自在的看了他一眼,提著紙袋搖搖晃晃的走進廚房。他聽見碗櫃的門關上的聲音。那孩子坐在座墊上看著他,他只能一會兒這條腿、一會兒換那條腿的方式,支撐著全身的重量,對那頂帽子也是同樣的擺弄,一會兒戴上一會兒拿下,女人終於又現身。
「你是醫生嗎?」她問。
「不是,」他吃了一驚。「不是,我不是。」
「秀莉生病了,我出去買點東西。你怎麼沒幫人家拿外套?」她轉向那孩子說。「請你原諒啊,我們很少有客人。」
「我不能久留,」他說。「我實在不該來的。」
「請坐,」她說。「這樣不好說話。讓我先給她吃藥,我們再好好的談。」
「我真的要走了,」他說,「聽妳的口氣,我想必定有急事。可是我真的要走了。」他低頭看兩隻手,發覺自己有氣無力的比著手勢。
「我去燒水泡茶,」他聽見她說,就好像完全沒把他的話聽進去似的。「給秀莉吃完藥,我們就可以好好的說話了。」
她攬著孩子的肩膀,帶她進廚房。他看見女人拿起湯匙,先看過瓶子上的標籤再把它打開,倒了兩劑出來。
「好了,跟布雷先生說晚安,進房間去吧。」
他向孩子點了點頭,便跟隨女人進廚房。他不坐她指定的座位,而是另外選了一張面對陽台、通道和小客廳的椅子。「介意我抽支菸嗎?」他問。
「不介意,」她說。「沒關係的。阿諾,你只管抽吧。」
他決定不抽。他兩手擱在膝蓋上,一臉凝重的表情。
「對我而言這件事真的太離奇了,」他說。「太不尋常了,真的。」
「我明白,阿諾,」她說。「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怎麼會有你的電話號碼這件事吧?」
「的確,」他說。
他們面對面坐著等水開。他聽見電視的聲響,往廚房四周看了一眼,視線再回到陽台上。水開始滾了。
「妳要跟我說電話號碼的事。」他說。
「什麼?阿諾,對不起。」她說。
他清清嗓子。「告訴我妳怎麼會拿到我的電話號碼。」他說。
「我從安妮那裡。那個保姆──這你都知道了。總之,她告訴我說她在家的時候電話響了,說是有人要找我。對方留了一個號碼,她寫下來的就是你的號碼。事情就是這樣。」她轉著面前的茶杯。「對不起,我只能說這些。」
「水開了。」他說。
她擺上茶匙、牛奶、糖,把滾燙的開水沖到茶包上。
他加了糖攪動一下茶水。「妳說有急事要我來。」
「喔,那個啊,阿諾,」她別開臉。「我不知道我怎麼會這麼說,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那就是根本沒事了?」他說。
「不是。我的意思是是的。」她搖著頭。「我的意思就是你說的,沒事。」
「我懂,」他繼續攪著他的茶。「不尋常,」過一會他又說,幾乎是在自言自語。「太不尋常了。」他無奈的笑了笑,把杯子移到一邊,拿餐巾碰了碰嘴唇。
「你不會就這樣走了吧?」她說。
「我得走,」他說。「我得在家等一通電話。」
「再坐坐吧,阿諾。」
她刮著椅背站起來。她的眼睛是很淺的綠色,深深的嵌在蒼白的臉上,他原先還以為她在眼睛四周畫了黑色的眼妝。令他自己大吃一驚、甚至唾棄自己的是,他居然站起來笨拙的摟住她的腰。她被動的吻著,眼瞼顫動著閉了一下。
「時間晚了,」他說,並放開手,步履不穩的轉開。「妳非常親切,可是我非走不可了,何特小姐。謝謝妳的茶。」
「你還會來嗎,阿諾?」她說。
他搖頭。
她跟著他走到門口,他伸出手。他聽見電視的聲音,並且很肯定音量轉大了。他這才想起另外一個孩子──那個男孩,他在哪裡?
她握住他的手,飛快的把它舉到她的唇上。「你不要忘記我,阿諾。」
「不會的,」他說。「克萊拉。克萊拉.何特。」
「我們聊得很愉快。」她說。她在他西裝領口撿起什麼,一根髮絲,一根線頭。「我很高興你來,我相信你會再來的。」他仔細地看著她,她的視線卻越過了他,彷彿在想什麼事情。「那──晚安了,阿諾。」她說,說完這句話她立刻關門,快得幾乎夾住了他的大衣。
***
「怪了。」他下樓的時候自語著。步上人行道後,他做了一次深呼吸,停下腳步回頭看那棟樓,卻已經無法確定哪個陽台才是她的家了。穿運動衫的大個子靠著欄杆稍微移動了一點位置,依舊往下看著他。
他開始步行,兩手緊緊的插在大衣口袋裡。剛回到家,電話在響。他靜悄悄的站在屋子中央,鑰匙夾在手指上,等著鈴聲停止。然後,很溫柔的,他把一隻手貼在胸口感覺,透過層層的衣服,感覺著他的心跳。過了半晌他才走進臥室。
幾乎立刻,電話鈴聲又活蹦亂跳地響了起來,這次他接聽了。「阿諾。我是阿諾.布雷。」他說。
「阿諾?天哪,今天晚上我們太正式了吧!」他的太太說,她揶揄的口氣超重。「我從九點就開始打了。出去玩瘋啦,阿諾?」
他保持緘默,思量著她的口氣。
「你還在嗎,阿諾?」她說。「感覺不像你了耶。」
1 他們不是妳的丈夫
厄爾‧歐伯丟了推銷員的工作。多麗,他的太太,在城外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咖啡店裡當夜班的女服務生。有一天晚上,厄爾喝著酒,忽然決定到那家咖啡店去吃點東西。他想看看多麗上班的地方,看看是否可以點些什麼東西來吃。
他坐在櫃台上研究菜單。
「你怎麼來了?」多麗看見他坐在那裡就問。
她把一份點單交給廚子。「你想點些什麼,厄爾?」她說。「孩子們沒事吧?」
「他們很好,」厄爾說。「我要咖啡和一份二號的三明治。」
多麗把他點的東西寫下來。
「有好康的嗎,妳明白我的意思?」他對她眨眨眼說...
目錄
1. 他們不是妳的丈夫
2. 你是醫生嗎?
3. 學生的妻子
4. 為什麼,寶貝?
5. 潔兒,茉莉和山姆
6. 鄰居
7. 胖子
8. 點子
9. 沒人說一句話
10. 六十英畝
11. 阿拉斯加有什麼好?
12. 夜校
13. 腳踏車,肌肉,香菸
14. 收集者
15. 你去舊金山幹嘛?
16. 請你為我想一想
17. 鴨子
18. 這個好不好?
19. 父親
20. 真的跑了那麼多里程嗎?
21. 信號
22. 能不能請你安靜點?
1. 他們不是妳的丈夫
2. 你是醫生嗎?
3. 學生的妻子
4. 為什麼,寶貝?
5. 潔兒,茉莉和山姆
6. 鄰居
7. 胖子
8. 點子
9. 沒人說一句話
10. 六十英畝
11. 阿拉斯加有什麼好?
12. 夜校
13. 腳踏車,肌肉,香菸
14. 收集者
15. 你去舊金山幹嘛?
16. 請你為我想一想
17. 鴨子
18. 這個好不好?
19. 父親
20. 真的跑了那麼多里程嗎?
21. 信號
22. 能不能請你安靜點?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