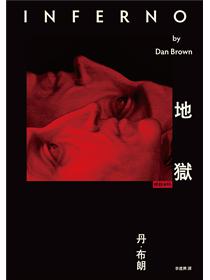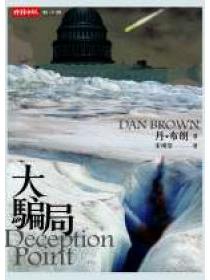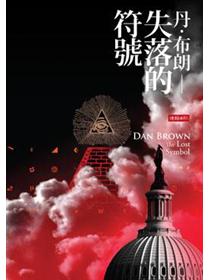連安潔莉娜裘莉也抗拒不了的角色──
女法醫史卡佩塔探案故事,電影即將開拍!
以法醫為名,以懸疑為姓;
一個熟悉屍體語言的死亡翻譯人,一本窮究事件真相的犯罪偵查日誌。
以手寫的方式記錄送進停屍間的每件個案。對凱?史卡佩塔而言,這本日誌將被賦予新的意義。
甫結束一場發生在佛羅里達州與一名精神病患的慘烈遭遇,凱.史卡佩塔決心改變步調,移居南卡羅來納州的歷史古城查爾斯頓,展開私人法醫病理學的嶄新事業與老搭檔彼德.馬里諾以及外甥女露西,共同提供專業犯罪現場鑑識調查與法理驗屍,來協助缺乏調查死亡案件能力與現代科技的地區。看似理想的新工作型態卻受種種因素影響起了變化,諸如當地政客與既得利益者的干預,然而這一切不過是開啟連串暴力謀殺的前奏而已。
十六歲的女子網球選手珠兒.馬丁與朋友同遊羅馬時走失,再次被人發現時,已是納佛那廣場上一具赤裸的屍體,一把來源可疑的沙子取代原有的一雙眼睛,眼瞼遭人用膠水緊緊封黏。
身分不詳的小男孩內出血致死,渾身滿布傷痕;海灘上一處千萬豪宅裡,一名婦人成為某種儀式的受害者。同時,在新英格蘭的哈佛大學附屬醫院,一位名流病患的問題讓幾樁恐怖的謀殺案之間有了關聯。
一具具屍體送進了史卡佩塔工作的停屍間,檢驗文字被記入進那本被稱為「死亡名簿」的停屍間日誌裡。在找出解答、揪出凶手之前,日誌上的名字仍持續增加,或許下一個被登錄的姓名將會是凱.史卡佩塔……
每一具屍體都有一個故事,每一具屍體也都說著這個故事,但它的語言我們聽不懂,我們得仰賴一個熟悉屍體語言的人,一個專業老練的翻譯者,用我們可理解的人間語言來告訴我們,這個專業的翻譯者,我們稱之為法醫──
作者簡介:
作者 派翠西亞.康薇爾 Patricia Cornwell
1956年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她的職業生涯從主跑社會新聞的記者開始,1984年在維吉尼亞州的法醫部門擔任檢驗記綠員。1984~86年間,康薇爾根據自身的法醫工作經驗寫下了三本小說,然而出書過程並不順利。
後來她聽從建議,推翻原本以男偵探為主角的構想,改以女法醫為主軸,終於在1990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結果一砲而紅,為她風光贏得1991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頒發的愛倫坡獎年度最佳首作、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約翰.克雷西獎、安東尼獎、麥卡維帝獎以及法國的Prix du Roman d’Adventure獎,是當年獲獎最多的年度矚目之作。
1993年,康薇爾再以《失落的指紋》拿下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代表年度最佳小說的金匕首獎。系列作品中的主人翁凱.史卡佩塔醫生,則在1999年獲頒夏洛克獎最佳偵探獎;2009年,好萊塢指名由知名女星安潔莉納裘莉飾演史卡佩塔,電影預計2011年上映。
派翠西亞?康薇爾目前擔任國家法醫學院,應用法醫科學部門的主任。
譯者簡介:
蘇瑩文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任職外國駐華機構及外商公司十餘年,現專職英、法文筆譯與口譯。譯有《南方之星》、《我認識你嗎?一個生命老去的美麗故事》、《再見寶貝,再見》、《蒼白冥途》、《最高權力──西塞羅執政之路》、《沉默的十月》等書。
章節試閱
楔子 羅馬
水花潑濺,紅陶地板上嵌著一座灰色馬賽克浴池。
老舊的黃銅出水口水花奔流,暮色湧進窗內,凹凸不平的老舊玻璃外,有個廣場、一座噴泉以及黑夜。
她靜靜地坐在冰塊漸融的水中,眼神黯然,不再透露太多神情。起初,她的雙眼像是向他求助,央求他出手拯救。現在,這雙眼眸呈現出幽暗的瘀青色調,眼底的一切幾乎消失殆盡。很快地,她將沉眠。
「來。」他說,遞給她一只慕拉諾手工平底玻璃酒杯,裡面斟滿了伏特加。
她身上從未在太陽下曝曬的部分,彷彿萊姆石,令他十分著迷。他將水龍頭關到極小,讓流水細細淌下,然後看著她短促地呼吸,聽到她的牙關打顫。她的乳頭受冷而硬挺,猶如粉紅色的花蕾。這時他想到了鉛筆,想到自己還在學校的時候,咬下粉紅色的橡皮擦頭,然後告訴自己的父親,有時也會告訴母親,說自己不需要橡皮擦,因為他不會犯錯。實情是,他喜歡咀嚼。他無法克制自己,這同樣也是事實。
「你會記得我的名字。」他對她說。
「我不會,」她說,「我可以忘記。」一邊含糊打顫。
他知道她為何會這麼說。如果她忘記他的名字,她的命運就會如同不入流的戰鬥計畫一樣,重新受到考量。
「是什麼?」他問道。「把我的名字說出來。」
「我不記得了。」她一邊哭泣,一邊發抖。
「說出來。」他說著,端詳她曬成棕色的雙臂,上面冒出雞皮疙瘩,金色的汗毛根根豎立。他看向她年輕的胸脯,和水中雙腿之間的一片陰影。
「威爾。」
「然後呢?」
「藍波。」
「你覺得這名字好笑。」他赤裸著身子,坐在馬桶蓋上。
她猛力搖頭。
撒謊。當他說出名字的時候,她還取笑了一番,放聲大笑,說藍波是虛構的電影人名。他說,這個姓氏來自瑞典;她則回答,他不是瑞典人。他又說,這是瑞典姓氏,否則她以為這姓氏打哪兒來的?這是個真實的姓氏。「對,」她說,「就像洛基一樣。」她一邊大笑。「去網路上查查看,」他說,「是貨真價實的姓氏。」對於自己必須為姓氏做出一番說明,他一點也不高興。這是兩天前的事了,他並沒有因此討厭她,然而卻謹記在心。他原諒她,因為不管她說了些什麼,她都得承擔難以忍受的痛苦。
「就知道我的名字會有迴響。」他說。「但這不會改變任何事,絲毫不會。只是個已經說出口的聲音罷了。」
「我絕對不會說出這個名字。」一陣驚慌。
她的嘴唇和指甲泛紫,並且無法控制地打著寒顫。她雙眼直瞪。他要她再多喝一些,而她也沒有拒絕。只要稍有不從,她知道接下來就會有什麼遭遇。即使是一聲微弱尖叫,她也知道他會如何處置她。
他沉著地坐在馬桶蓋上,雙腿打開,好讓她目睹他的亢奮,並且為之感到恐懼。她不再開口哀求,或是要他對她為所欲為,彷彿她是因為如此才成為他的俘虜似的。她不再說這些話,因為她知道,只要自己開口侮辱他,或者暗示他有法子對她下手,接著便會有事發生;這代表她不肯自發性地付出,而卻又想要。
「你明白,我可是好聲好氣地開口問過你。」他說。
「我不知道。」她的牙關打顫。
「你知道。我要你向我道謝。我的要求不過如此,而且友善地對待你。我好聲好氣地問,然而你卻這麼做。」他說。「你就是得讓我這麼做,看看,」--他起身望向光滑大理石洗手檯上方鏡子裡自己的赤身裸體--「你受到折磨,卻讓我變成這樣。」鏡子裡赤裸的他如此說。「可是我不想要這樣。所以,你這就是傷害我。你知道嗎,害我變成這樣,是嚴重地傷害我?」鏡子裡赤裸的他這麼說。
她說她了解。當他打開工具箱的時候,她渙散的眼神如同四散的玻璃碎片,直盯著美工刀、小刀和細齒鋸子。他拿出一小袋沙,放在洗手檯邊緣,接著掏出小瓶薰衣草膠水,也一併放了下來。
「我會依你,你想做什麼我都依你。」她不停地重複。
他早就命令過她不許再說,但她卻又脫口而出。
他將雙手浸入水中,冰冷的水溫讓他發凍。他抓住她的腳踝,將她往上拉。他拉住她曬成棕色的雙腿,緊握著冰冷發白的腳掌時,感受到驚慌肌肉傳來的恐懼。他拉著她的時間比上一回來得久,她猛力掙扎扭動,不停拍打,冷水高聲地潑出水花。她又喘又咳,發出窒息地哭喊,卻沒有怨言。她學會不去抱怨;花了好一段時間,但終歸學會了。她領悟到這一切都是為了她自己好,並且感激這個即將改變他生命的犧牲--不是她的生命,是他的--儘管過程並不愉快。絕不可能美好,她應該要感激他的贈與。
他拿起垃圾袋,裡面裝有稍早從吧檯製冰機裡取來的冰塊,接著將最後一些冰塊倒進浴缸裡。她看著他,淚水滑下臉龐。哀傷的陰鬱魔爪油然浮現。
「在那裡,我們都把他們吊掛在天花板上,」他說,「一次又一次猛踢他們的膝蓋側邊,就在那裡。我們每個人都進到小小的室內,踢他們的膝蓋側邊。這種痛苦極端難耐,絕對會造成重大傷害,當然,他們有幾個就這麼死了。但是比起我在那裡見過的其他事,這還算微不足道。你瞧,我可沒有在監獄工作,也沒有必要,因為這種事的分量多到足以好好分配。人們不懂,錄下這一切、拍照,這些絕對是少不了的。一定得要有的。如果沒有,事情就會像是沒發生過一樣。所以人們會拍照,給他人觀賞。只要一個;一個人看過,等於全世界都看過了。」
她瞥向灰泥牆邊,放在大理石桌面上的攝影機。
「他們自找的,不是嗎?」他說。「他們強迫我們成為與原來不同的自己。所以是誰的錯呢?不是我們的錯。」
她點頭,發著抖,牙關打顫。
「我並沒有每次參加,」他說,「但是我觀看。剛開始的確很難,我幾乎受不了,無法接受這一切,但是,他們對我們做出那些事。因為他們的作為,我們被迫反擊,所以這都是他們的錯、他們逼的,我知道你懂。」
她點頭,一邊哭喊一邊發抖。
「放在路邊的炸彈、綁票,比你聽說的還多。」他說。「你會習慣的。就像你現在適應冰水了,是吧?」
她沒有適應,只感覺到麻木,漸漸進入失溫狀態。到了這個時候,她的腦子裡已經出現轟鳴聲,心臟也好像要爆開來。他將伏特加遞給她,她喝了下去。
「我要打開窗戶,」他說,「好讓你聽到貝尼尼的噴泉聲,我聽了大半輩子了。夜色很美,你應該要看看星星。」他打開窗戶,看著夜裡的星空、四河噴泉,以及這時候空無一人的露天廣場。「你不要尖叫。」他說。
她搖頭,胸腔猛烈起伏,無法遏止地顫抖。
「你在想你的朋友,我知道。他們當然也會想到你,但是真糟糕,他們人卻不在這裡,到處都看不到人。」他再次看著無人的廣場,聳聳肩頭。「他們怎可能在這裡?離開了,早就走了。」
她涕淚縱橫,不停發抖,雙眼中的光芒與當初兩人相遇時大不相同。他感到厭惡,因為她毀了對他的意義。先前,在更早的時候,他以義大利文與她交談,因為這讓他成為一個陌生人,而這是有其必要的。現在,他對她說英文,因為這不再有差別。她瞥向他的亢奮,視線在他亢奮的肉體上跳動,猶如飛蛾撲火。他亢奮的部位也感受到她。她懼怕它,但是遠比不上她對其它東西,比方說水、工具、沙袋及膠水的恐懼。她不明白老舊地板上圈起的黑色寬皮帶是做何用途,這是她最該害怕的東西。
他拾起皮帶,告訴她,毆打無法自衛的人是一種原始的欲念。為什麼?她沒有回答。為什麼?她充滿驚恐地瞪著他,眼中的光芒遲鈍但卻狂亂,好似在他面前碎裂開來的鏡面。他要她站起身來,她照做,但是打著顫,雙膝發軟。她站在冰冷的水中,接著他關上水柱。她的身軀使他聯想到緊繃的弓,同樣地彎曲、充滿力量。水珠順著她站立的身子往下淌。
「背對著我轉過身去。」他說。「別擔心,我不會拿皮帶打你,我不做這種事。」
她轉身面對著有裂縫的老舊灰泥牆面,以及拉上的百葉窗,水在浴缸裡靜靜地波動。
「現在,我要你跪在水中,」他說,「然後看著牆,不要看我。」
她面牆跪下。他拿起皮帶,將整條皮帶穿過扣頭拉到底。
第一章
十天之後,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
虛擬實境戲院裡,坐著十二名義大利最具影響力的執法者和政治家,法醫病理學家凱•史卡佩塔無法完全記清楚這些人的名字。唯一的非義大利人,只有她自己,以及法醫心理學家班頓•衛斯禮;兩人都是國際調查組織的顧問,這個單位是歐洲法醫科學研究中心的專設部門。義大利政府的處境並不單純。
九天前,美國網球明星珠兒•馬丁在度假期間慘遭謀殺,赤裸殘缺的屍首,在羅馬舊城區的納佛那廣場上被人發現。這個案件轟動國際,電視上不停地重播這個十六歲女孩的一生和死亡的細節,螢幕下方的跑馬字幕毫無間斷,頑強地慢慢跑著,重複主播和專家述說的細節。
「那麼,史卡佩塔醫生,讓我們弄清楚,因為混淆之處似乎不少。根據你的說法,她在當天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就已經死了。」奧托林諾•波馬隊長這麼說,他是義大利國家憲兵隊的法醫,這個單位是負責調查案件的軍事警察。
「不是根據我的說法,」她說,神經緊繃了起來,「是根據你們的說法。」
他在昏暗的光線下皺起眉頭。「我很確定是你說的,就在幾分鐘之前,你提到她胃裡的殘留物和酒精含量,這些都指出她是在友人最後看到她的幾個小時之後死亡的。」
「我沒有說她是在兩點或三點的時候過世。我想,這麼說的人是你,波馬隊長。」
他年紀輕輕就已經聲名遠播,但卻是毀譽參半。兩年前,史卡佩塔在海牙的歐洲法醫科學研究中心年度會議上第一次見到他,他嘲諷地學著中心負責人說話的模樣,並且還把他模仿得自滿又好辯。波馬隊長十分英俊--老實說,帥極了--對於美女和華服極具品味,今天他身穿藍黑色的制服,披掛寬幅的紅色飾帶和耀眼的銀色飾章,加上一雙閃亮的黑色皮靴。當他一陣風般在這天早晨走進劇院時,還披著紅襯斗篷。
他坐在史卡佩塔的正前方,就在第一排的正中央,視線幾乎沒有離開過她。班頓•衛斯禮坐在他的右邊,大半的時間都保持安靜。每個人的臉上都罩上立體實境眼鏡,同步觀看犯罪現場分析系統,這個傑出的革新系統,使得義大利科學警察暴力犯罪分析小組成為全球執法單位豔羨的對象。
「我想,我們必須從頭再來一次,好讓大家完全了解我的立場。」史卡佩塔對波馬隊長說,後者雙手撐起下巴,好似正啜飲著美酒,與史卡佩塔親暱對話。「如果她在當天下午兩點或三點遇害,接著到了屍體在隔天早晨大約八點半時被人發現,應當離死亡時間至少有十七個小時之久。她身上的屍斑、死後僵硬程度,以及屍體的冷卻程度,都與這個推論互相矛盾。」
她以雷射筆引導眾人的目光,看向牆面大小的螢幕,上面投射著晦暗的立體架構影像,似乎他們就置身於犯罪現場,瞪視珠兒•馬丁慘遭凌虐的屍首,以及四周的垃圾和挖土機具。紅色的光點順著她的左肩滑向左臀、左腿,然後到了赤裸的左腳;右臀和右大腿的一部分不見蹤影,彷彿歷經鯊魚的攻擊。
「她的青色屍斑......」史卡佩塔開始說話。
「我要再次致歉。我的英文沒有你好,不確定這個字眼的意思。」波馬隊長說。
「我之前用過這個字眼。」
「我那時候也不確定。」
笑聲四起。除了翻譯人員以外,史卡佩塔是在場唯一的女性。她和翻譯一樣,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笑,但是那些男人卻不以為然。班頓除外,他當天連個微笑也沒出現過。
「你知道在義大利文裡,這字怎麼說嗎?」波馬隊長開口問史卡佩塔。
「用古羅馬的語言來說如何?」史卡佩塔說。「拉丁文。既然大多數的醫學辭彙都源自於拉丁文。」她的語氣並不粗魯,但卻十分嚴肅,因為她清楚知道,他只有在自認為恰當的時機,英文才會不甚流利。
他的立體實境眼鏡瞪著她,這讓她連想到蒙面俠蘇洛。「用義大利文,拜託,」他對她說,「我的拉丁文一向不好。」
「我用兩種語文告訴你。拉丁文的livid在義大利文是livido,意思是色斑;mortis 是morte,就是死亡。屍斑就是在死後出現在屍體上的色斑。」
「用義大利文說,的確有幫助,」他說道,「而且你解釋得真好。」
她並不打算在這裡說義大利文,儘管她對此遊刃有餘。在這些專業討論當中,她寧願說英文,因為細小的差異極其微妙,何況翻譯人員無論如何都會逐字翻譯。語言的難處、政治壓力以及波馬隊長的緊迫釘人,和令人難解的譁眾取寵,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全都加諸在這件原本就已經十分不幸的事件上。
而且在這個案件當中,凶手的手法不但前所未有,還跳脫出常見的犯罪側寫,使得一切混淆不清。即使是科學證據,也成為爭論當中令人發狂的源頭,並且似乎在挑戰他們、蒙蔽他們,這迫使史卡佩塔不得不提醒自己以及其他人:科學決不說謊、不會犯錯,不會蓄意領他們誤入歧途,或是尋他們開心。
波馬隊長無視於此。或者他只是假裝,以毫不配合的爭辯語氣談起死去的珠兒,彷彿自己與屍體有某種關係,而只是在和它爭吵,也許他並非當真。他堅稱珠兒死後屍體的變化代表著一種情況,而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和胃部的殘留物又代表著另一種情況,但是他與史卡佩塔看法相左,認為食物和飲酒的資訊絕對足以信賴。至少對於這一點,他是認真的。
「珠兒生前的飲食揭露出實情。」他重複自己在稍早慷慨激昂的開場演說中的話語。
「揭露事實,沒錯,但不是你所謂的實情。」史卡佩塔回答,語氣比所使用的字眼來得有禮。「你所謂的事實,是經過誤解的事實。」
楔子 羅馬水花潑濺,紅陶地板上嵌著一座灰色馬賽克浴池。老舊的黃銅出水口水花奔流,暮色湧進窗內,凹凸不平的老舊玻璃外,有個廣場、一座噴泉以及黑夜。她靜靜地坐在冰塊漸融的水中,眼神黯然,不再透露太多神情。起初,她的雙眼像是向他求助,央求他出手拯救。現在,這雙眼眸呈現出幽暗的瘀青色調,眼底的一切幾乎消失殆盡。很快地,她將沉眠。「來。」他說,遞給她一只慕拉諾手工平底玻璃酒杯,裡面斟滿了伏特加。她身上從未在太陽下曝曬的部分,彷彿萊姆石,令他十分著迷。他將水龍頭關到極小,讓流水細細淌下,然後看著她短促地呼吸...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7收藏
17收藏

 5二手徵求有驚喜
5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