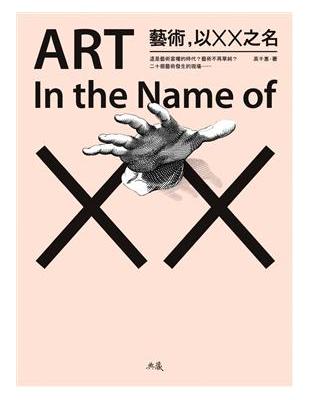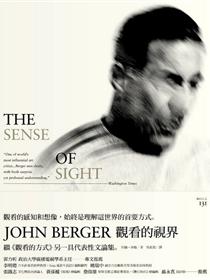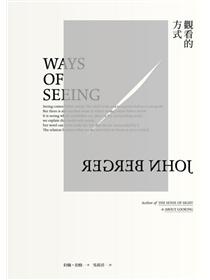以酒神之名
以酒神之名,許多節慶活動都動起來了,許多公共經費也灑了起來。
1.
廣義的文化創意產業範疇義中,有一種以酒神之名的活動,成為官民「公共性」的橋樑。因為,以酒神出巡之名,任何套上「文化」的行動和活動,都正當有力,一切都具有「奉獻」和「犧牲」的社會意涵。
屬於常民節慶式的文化活動,基本上是建立在對節慶主題的信仰,並且透過年度的變化,延伸出它的歷史意義,以便積累出新的文化資產。它有「大拜拜」的意味,乃在於「festival」或「fest」一詞,在精神上、俚俗上,都具有以祭物牲品供奉主上的意思。與「祭」相關,自然須要供奉出許多好東西,同時也要享用許多平日不易享用的好東西。季節性的「節慶」,因與四時運轉有關,往往呈現人們對自然生息的祟敬與讚美。是故,節慶化的活動有其特點,一是關乎地方上的風俗信仰,二是期能造成承傳的儀式活動,三是具有將知識傳遞給下一代的目的,四是每一次的文化內容,都能是未來的參照。因為這些虔誠的心意,推出的活動作品,應該都是好東西才對。
當代藝壇,繼「雙年展」之後,另一個新名稱「藝術節」或謂「藝術祭」( Art Festival),正以節慶化、活動化的姿態紛紛在各地出現。當代藝術原與傳統文化相對,有了這些「節」或「祭」的出現後,當代藝術也意謂著承傳的渴望。取代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不連續或斷裂性的語意,現行藝術(Live Art)以涵括當代和傳統並存的親和力,逐漸出現在當代文化活動的名稱裡。
無論是用「Festival」或「Live Art」,地域性的當代文化活動,以回顧與再生的方式,總希望能在年代風潮中,推廣出地方性或社區性的文化觀光魅力。這個構想並無過,但若沒有一個承傳性的集體信仰,對活動主題的投入支持,並使其滲入生活,所有的活動,很可能是消耗意義大於文化意義。不過,活動有沒有意義,現在已愈來愈不重要了,反觀昔日的節慶文化活動,其實有其年代生活條件。
2.
在各地城邦節慶活動裡,最早完整出現活動美學,並因此建立哲學系統的論述之地,當屬希臘雅典。希臘的酒神戴奧尼斯崇拜是在西元前13世纪左右,從小亞细亞傳到希臘,並成為希臘大城雅典的傳統活動。至西元前七、八世纪,酒神祭的活動,除了傳統遊行之外,也出現了表演競賽,使整個城市為了競賽活動的準備,上下全年都有了文化狂熱。
酒神的祭祀一年有四個。十二月是「鄉鎮上的戴奧尼斯節」,一月是「雷納亞節」,二月下旬是「安塞特亞節」,三月下旬則是「城市的戴奧尼斯節」。除了安塞特亞節之外,其它三個節慶都有戲劇演出。十二月的鄉鎮酒神祭,是屬非常地方性的部落活動,鄙俗不拘。一月的雷納亞節,因值風浪較大的時序,外地觀光客少,乃以雅典居民為主要參與對象,所以不用擔心家醜外揚,可以努力以臧否城邦人事為主題。至三月下旬的城市酒神祭,氣候宜人,海上觀光客擁進,活動自然要提昇到「國際規格」,重要表演競賽,也在這為期四、五天裡發生。這至少二千五百年前的城市文化活動,已顯示出具有宗教、經濟、藝術、娛樂和外交等多重意義。
城市酒神祭的三個表演項目,悲劇、諷刺劇和喜劇,在今日也可以視為三種地方文化精神的象徵。一是民族英雄的犧牲精神,二是民間輿論的臧否態度,三是民俗文化的誇大自嘲。「悲劇」(tragedy),原文之意是「山羊之歌」。據悉,原是一個歌隊圍繞一隻作為犧牲或獎品的山羊歌舞。酒神頌原來也是以戴奧尼斯的故事為內容,後來發展出以希臘英雄的故事為本。娛神活動變成人間頌歌,也逐漸成為娛人活動。最早的悲劇人物是以奧迪帕斯為本。奧迪帕斯因命運使然而弒父娶母,在城市將遭天譴之際,他扮演了自願犧牲救城的角色。因此,祭典始於對「犧牲者」的闡述,也是對城市精神的一種省思。
悲劇之外,還有諷刺劇( Satyr Plays)。撒特是陪伴戴奧尼斯的半人半羊,早期演出時,是以半人半羊妝扮組成歌隊,後來也形成戲劇形式。撒特劇的精神,如同丑角,以滑稽戲謯、粗俗鄙陋的語言,誇張放縱的動作出現,且往往以諷刺或嘲笑主人翁為旨。依節目排序,通常三個悲劇之後,便接演一個撒特劇,以此平衡觀眾的情緒。是故,當時悲劇作家除了要能寫正經八百淒風慘雨的故事之外,在競賽中還要有書寫輕鬆冷絕之諷刺劇的本事。
喜劇發展較晚,直至西元前487年,雅典政府才將喜劇纳入城市的戴奧尼斯神節。「喜劇」(komoidia),原意是「縱性歡飲之歌」。它源自鄉鎮酒神祭,與民間風俗中的陽具崇拜有關。原始活動可能只是一種以誇大陽具為主題的化妝遊行,產生即興演出後,也發展出劇本。喜劇的劇本,多屬鬧劇場面,人物也多以市井之徒為對象。演員以日常行為的現實為主,嘻笑辱罵,語帶譏鋒之外,也有一套語言美學。換言之,此城邦節慶活動雖有其傳統儀式,但在節目內容上,卻類似今日的當代藝術概念,既是當下(Con-temporary),也是現行(Live),既是歌頌,也可反諷。
希臘城市戲劇節,奠定了一個比當代很多文化活動還開放的態度。神話英雄的悲劇複習,提醒了人性高貴面的追求;而撒特劇的參與,乃是作為一種自由評論的註腳。喜劇則以現世社政問題為本,以便反映當下時世問題。在活動上,一年一度的城市戲劇節雖前後為期五至六日,但籌備期卻近乎一年。活動期,為鼓勵全民參與,雅典市還作了一個開放政策。在仍有奴隸制的雅典社會,20至30萬人口中,去除非公民的女性、幼童、奴隸,只有佔全民五分之一強的四萬人口是合格公民。為了活動熱絡,在酒神祭時間,所有機構放假、工商歇業、犯人假釋。劇場收費儘量低廉,甚至曾設基金,供人申請入場補助。酒神戲劇節在春秋鼎盛之時,每場觀眾高達總人口四分之一以上。而就像當代的國際性文化活動,地方高官祭司與友邦使節貴賓總會應邀列席,而他們所帶來的禮物贈品,如同視覺藝術品,也得在現場公開示眾。頒獎結束後,大會還會清理活動期間所有不當行為,加以控訴和懲誡,作為會後檢討。
3.
當代希臘文藝研究者,亞蘭.索瑪斯坦(Alan Sommerstein)編譯過不少希臘戲劇節的劇本,對西元前五世紀鼎盛中的「城市的戴奧尼斯節」和「雷納亞節」之活動過程尤有研究。他不僅曾考據當時政治與藝術的運作關係,還寫了不少當時城市文化運動的生產系統,提供不少當時的歷史資料。據載,城市酒神戲劇節的組織很像當代雙年展的前身。籌備期近十一個月,在祭典結束後,主席會選出下一屆活動行政執行者。參展劇作家將向他申請十五人為一團的歌隊,而他和他的委員們,通常是三名贊助富紳,可遴選最後三名劇作家,用抽簽方式分別支助他們去編撰、排演三個悲劇一個撤特劇。獲選的劇作家可分配到一個演員。籌備期,市府將提供編導作家微薄的個人薪水、演出服裝。至於喜劇組,每年五人競賽,一人只提一件作品。
城市酒神祭具有數百年傳統,富紳的贊助總有不足之時。雅典市府有很多折衷辦法作為應變。被指名的富紳如果能找到更富有者,可用自己的財產抵押,換人去回饋社會。在戰亂時,也允許二家富豪養一家藝術團隊。若在昇平日,富紳們超額贊助,以養面子或盡公民美意者,也大有人在。經過數百年,這些花費証明,值得。黃金時代的城市酒神戲劇節,所留下來的劇本幾乎成為後來西方音樂、詩文、藝術、表演文化的重要經典源頭。
例如,希臘悲劇之父,艾斯奇勒斯(Aeschylus)的〈七雄聯攻底比斯〉(Seven Against Thebes),曾帶給日本名導黑澤明一些靈感。1954年黑澤明拍出經典的〈七武士〉(Seven Samurai);1960年美國導演约翰.斯圖格斯(John Sturges),又根據〈七武士〉翻拍出好萊塢式的西部片〈豪勇七蛟龍〉(The Magnificent Seven)。儘管內容與〈七雄聯攻底比斯〉相逕已遠,但在戲劇淵源上,仍有可溯之處。近年,安哲帕普羅斯(Theo Angelopoulos)執導的〈希臘首部曲:悲傷草原〉,不在字面上雷同,但在故事結構上則最接近〈七雄聯攻底比斯〉,提出兄弟對峙戰場的宿命悲劇。日本動漫,最近也出現改編的〈七俠蕩寇誌〉,顯示「七雄」的故事原型至今不衰。另外,莎士比亞的悲劇,也常出現希臘經典劇的歷史資料身影。〈李爾王〉與〈哈姆雷特〉裡的一些對話,均可溯源到索發克里斯(Sophocles)的〈奧迪帕斯王〉。此外,因參與戲劇活動的觀眾增多,此活動還發展出劇場建築,也因場景須要,而發明一些舞台機關和道具設計。這些總體藝術表現概念,在21世紀初的歐陸雙年展中,可以看到「文藝復興式」的慾望,希望能將詩歌、音樂、表演,帶進原本靜態的視覺活動領域。
4.
在酒神戲劇節中,另一有別於今日的特殊作業,是評審制度。希臘古典戲劇來自競賽,優勝者可以在祭典時間獲得公演機會。當時的民眾也擁有評審權,顯示民眾的藝術品味足以參與或引導劇作者的表現。在平衡雅俗共賞的條件下,劇本不乏出現俚俗內容,但長期互動下來,仍建立了四個重要的評審方向:主要理念、矛盾張力、與現實對應、邏輯發展。也就是說,民眾透過評審機會,亦開發出一般的審美品味,並對藝術表現的好壞產生意見。
年輕的柏拉圖,早年也愛看戲。在他後來的《法律》篇裡,便製造了一個「劇場政體」(Theatrocracy)的名詞,以對應菁英的「貴族政體」(Aristocracy)。一方面表示劇場觀眾的勢力不能忽視,民間審美勢力有其政治性效應;另一方面也指出此種迎合民眾低俗趣味的品味,具有「民粹化」的危機。此觀察很有現代感。晚後,所謂高文化的發展,觀眾保持靜默直到終場,成為對藝術尊重的禮節。此後,觀眾不再被鼓勵於現場中,立即表露好惡。
當代文化以各種節慶活動為名,乃是希望藝術重新上街頭,以便喚起全民的藝術參與意識。此意無差,只是有活動,但供不出「好東西」,此舉便差矣。沒有信仰或沒有承傳性的節慶活動,如同酒神不在家,膜拜無人,一群搞活動加上看熱鬧的人,遂權充了善男信女。酒神不在家,酒鬼當家也罷,總還有人惦記著醇酒的存在。就怕酒商當家,好酒劣酒都是酒,能擺出來的,就是酒家。還有,以酒神之名,文化經費要永遠宣稱不夠。如果發現酒神已變成財神爺,那更不能明說。誰敢這麼說,那肯定是酸葡萄發酵下的一陣暈眩,我們可以確定,他家的葡萄酒再也上不了酒神的桌。
以戀物之名
以戀物之名,藝術不再僅屬於精神領域,而是社會符號學的百科庫房。
1.
以戀物之名,戀事、戀景、戀人,都有了栩栩如生的物証。在戀物行為當中,歡聚時光,便容易讓人產生收集紀念物的念頭,而名流的戀物,更往往是時尚的指標。至於藝術界的戀物、戀舊、戀當下,則可能成為未來的年代文件。
戀物非罪。一如禁慾者和被閹割者的克己態度不同,「自然樸素」與「追求樸素」也是兩回事。時尚中「侈華的樸素」或是「精緻的古拙」的流行語,便有著不簡單的物語情境。在2004年10月看到安迪.沃荷美術館推出他15箱〈時間膠囊〉與具諧音的〈Phoney〉展之後,可以肯定一件事:不認識「流行戀物家」的安迪.沃荷,便無法了解「藝術家」的安迪.沃荷。
幾乎看過展覽的人,都要讚嘆這位普普大師的日常收藏宴饗,他真是無聊而又粗俗得偉大。當代少有藝術家可以像他這麼身心一致地媚俗,而且是帶著天真又狂妄的色彩。他不僅連飛機上的刀叉、旅館的肥皂都拿、所有的小紙條都留、跟朋友聊天的電話要錄,最後,連老媽媽一動也不動的睡相,他都能拍個半天,生活一點一滴都要為留世而典藏。安迪.沃荷不僅是愛追求名星名流的追星族,他本身就是大眾文化,而且是最大化的那種媚俗法,連他的「私房日誌收藏」,都是當下的、眼前的、便宜的、地攤式的收集法。
沃荷神祕的〈時間膠囊〉,一箱箱存放了沃荷真正的日常生活,也同時典藏了藝術家那個年代的文物。2004年,在卡內基美術館推出第54屆國際當代展之際,安迪.沃荷美術館則推出了〈Really Phoney〉與〈時間膠囊〉,後者開了15箱,是美術館極大的開箱手筆。「Phoney」在美俚「Phony」是偽造的,或騙徒之意,同時也是具有「音」或「聲」的名詞尾音,例如電話「tele-phony」。沃荷在15歲那年,家裡有了電話後,他就像今日的手機族,非常喜愛「聲在熱線」上的人際溝通方式。有了錄音機之後,他也開始珍藏他與別人的線上對話。這個使用行動,在手機氾濫的今日,更顯出「擁機自重」的跨年代現象。
2.
1970年代中期,沃荷開始用同一尺寸的紙箱打包他的日常生活,包括他的仰慕者信件、請帖、克拉克.蓋柏的鞋子、飛機上的刀叉、黃色雜誌、旅館筆紙、肥皂等。〈時間膠囊〉展出15箱,三千多件物件,公開了沃荷的私人世界、社會關係、藝術與生活。沃荷自己真正的系列收藏,也就是他的「品味」,其實都是漫畫書、名星海報、唱片等。他愛美,愛活生生的美,他的收藏一點「傳統的氣質」都沒有,極像六、七十年代舊書報攤的感覺。
戀物之外,安迪.沃荷也戀聚。沃荷是個很愛開派對的人,他記錄自己宴會的方式,就像在拍「獨立小電影」,在極尋常裡的場面裡經營出他獨特的節奏。另一方面,藝術家的派對往往引人遐思,雖未必星光閃閃,但會讓人想像具有歷史檔案的可能。基於歷史癖的作祟,他們往往連一個聚會鏡頭都想當歷史事件來處理。
沃荷的聚會,當然也需要有在場者的觀點才算數。就像多數刻意要登入名冊的歷史鏡頭安排,他的聚會也很有秀場氣氛,來客要有演員的心理準備。另外,也好比南唐的〈韓熙載夜宴圖〉,沒有顧閎中的觀看,就沒有「苟全生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之縱情聲色的韓熙載。透過沃荷的聚會來觀看沃荷的記錄者不少,他們都企圖用變奏的剪接影像,來捕捉這個普普藝術家的群居關係,以便這一卷卷膠捲裡,有他也有我。
1964年,沃荷獲得〈影片文化雜誌〉獨立製片獎,他不想參加公開的頒獎活動,另一位獨立製片者,立陶宛移民的強納士.米卡斯(Jonas Mekas),便決定為沃荷拍攝一卷私房性的〈慶祝與頒獎〉記錄文件,以便在真的頒獎現場放送。米卡斯去沃荷家,帶了一籃水果,當時,現場還有沃荷幾位朋友。米卡斯只拍12分鐘,就是一群人吃水果,排好隊,像所有拍紀念照一般,面無多大表情地對著鏡頭作出定裝秀的姿勢。米卡斯最後替這12分鐘配了當時最流行的舞曲,使得這個「Party」變得很有普普年代的搖滾爵士感。這些非職業性的臨時演員--俊男美女們,刻意作出一種詭異的平凡,在幌動的鏡頭裡流動。
〈慶祝與頒獎〉的影片畫面,頗像西班牙畫家哥雅1800年的〈查理第四合家歡〉,漂亮的一群人排立著,且紛紛透露出一股疏離神采。米卡斯還整理過1965年至1982年間,他參加過沃荷的聚會影錄。片中,1966年流行的〈Velvet Underground〉曲子,幾乎貫穿他們共有的回憶世界。影片聚會地點,以沃荷紐約靠聯合廣場的工作室與蒙塔克(Montauk)海濱渡假小屋為主,出現的人物相當多,但內容平常得像任何居家的家庭記錄影片。
在同儕名流交往上,畫家、演員,兼製片者瑪瑞.曼肯(Marie Menken),她和製作家丈夫維拉德.馬士(Willard Maas),被沃荷稱為「最後的波希米亞族」。維拉德.馬士曾用隱喻的方式拍沃荷的世界,他拍沃荷那件浮在天空的銀色枕頭群,上下飄浮,似群聚,又似獨舞。瑪瑞.曼肯則用自己的詩意來描述沃荷的視野,她採用默劇兼記錄影片的方式,交叉地對比出比利時畫家馬格利特式的觀念性理念:「這是文件」、「這不是文件」。外人根本搞不清楚那些鏡頭才是真實記錄。強.卡吉(John Cage)的工作夥伴,朗尼.納米斯(Ronald Nameth),也用尼克(Nico)的〈Velvet Underground〉作沃荷記錄片的背景樂。他用聲光、潮水,交替地詮釋沃荷普普式的生活調調,聚會中的人物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個只有一號表情的男主角,讓人覺得有很多問號與驚嘆號。
3.
沃荷之前,也有不少藝術家喜歡描繪聚會現場,並且也把自己放在畫面,表示自己是現場的一份子。他們一樣記錄了生活圈的情事。17世紀西班牙畫家,維拉斯貴斯(Diego Velazquez)畫〈內廷的宮女們〉,就把自己安放在人們皇家的家庭聚會裡,但他畢竟是記錄者,未必融得進人家的活動。18世紀英國畫家霍加斯(William Hogarth),喜歡把畫面連接成連環畫或道德劇。他畫〈浪子旅程〉裡的〈縱慾狂歡的宴會〉,走中下階層民俗生活記事,也反映出那個年代所參與的宴會場景頗似妓院現場。19世紀法國畫家古爾貝(Gustavo Courbet),在他有名的〈我畫室的內景:一幅總結我藝術生涯的真實性象徵畫〉,邀請入畫的不是皇親貴冑,而是他生活裡的群眾正親近著他作品。很清楚地,他是畫面核心,是唯一在工作的創造者。
19世紀末法國畫家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的〈紅磨坊夜總會〉,描繪的紅磨坊不像娛樂場所,反倒像頹墮之鄉。藝術家也不自比清高,在畫面中心,大家都看到這個長著鬍鬚的小矮子,正穿行而過,不諱言他正是這燈紅酒綠世界裡的大常客。二十世紀初,藝術家的聚會多豔聞。奧地利的奧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1912年在文藝聚會裡碰到名作曲家葛斯多.馬勒的遺孀,艾瑪(Alma Mahler),他最有名的倆人私會証據,就是作品〈風的新娘〉。
有了攝影機與影錄機,最常見的藝術家集體留影,是在展覽現場排排站。另外,若是在酒會或餐埸所,媒體則可以拍到人物與食物。藝術界人士公開聚會的相片總是具市場效果。藝術家自認是歷史見証,媒體當公關效應,而觀眾可以看到,原來誰捧誰的場。藝術家群聚鏡頭,只有藝術家們全成為歷史人物,否則,這類公關相片雖有檔案作用,卻未必有藝術價值。比較起來,19世紀末,喜歡化裝聚會的巴黎藝術家羅特列克,曾經留下他扮演吉普賽人、日本文士、日本藝妓、小丑、穆斯林教士,甚至男扮女裝的寫真照,可以想見,其聚會之創意了。
藝術家的任何記實行為,包括了戀己、戀物、戀人。以歡聚一堂,奉有圖為証之名,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獲得正當性和歷史性。當藝術家開始有了典藏文件的計劃,若非共襄盛舉,生人最好迴避。因為「以戀物之名」加上「以藝術之名」,誰還能提出權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