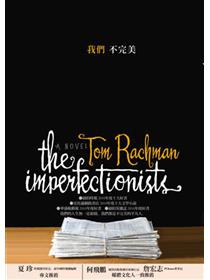友情可以很複雜、很揪心
有些感情妳永遠切不斷……
愛笛‧唐思和薇樂莉‧亞德勒會是一輩子的好朋友。愛笛九歲那年見到薇樂莉搬到她家對面之後就如此深信著。不過她們在高中撕破臉之後,薇樂莉變成校園人氣女孩,膽小怯弱的愛笛卻變成全校爭相欺負的倒楣鬼。
十五年過去了。薇樂莉開始追逐名利,成為電視臺的美女氣象主播;愛笛則獨居在她爸媽留下來的房子裡,照顧著身心障礙的哥哥,在網路上尋覓白馬王子。一個寒冷的夜裡,愛笛剛結束第六場難堪的約會回到家,卻發現失聯已久的姊妹淘站在門口,一臉驚惶,袖口還染著血漬。「大事不妙了,」薇樂莉對愛笛說,「而且我只能靠妳了。」
作者簡介:
珍妮佛‧韋納Jennifer Weiner
出生於路易斯安那州,在學期間即得過普林斯頓大學美國詩人獎,書中處處可見其詩詞寫作的才華。目前專職於寫作,與丈夫亞當、女兒露西及愛犬維多住在費城。
因處女作《慾望單人床》一躍為暢銷書作家,第二本小說《偷穿高跟鞋》被改編為同名電影。韋納以一貫幽默細膩的筆觸,不著痕跡地輕碰人心最深處的傷痛,並予以溫柔縫合。
韋納的最新作品《永遠的好朋友》,有如將電影《末路狂花》加一點風趣、哀愁、甜蜜來證明都會小說有更豐富的內涵。韋納讓小薇這個電視臺的氣象播報員和愛笛這個全世界最孤單的女孩,在劇情起伏中歷經破碎的家庭、心痛的背叛、易脆的自尊……卻在最意想不到的轉角尋得真愛,當然更真切地刻劃了姊妹淘真情相繫的友誼。
譯者簡介:
葉妍伶
英國愛丁堡大學翻譯研究所、國立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口譯組。譯作有《消失的艾思蜜》、《名牌戀人》、《愛情的抉擇》等書。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這本適合在海灘上慢慢享受的讀物將會以詼諧和智慧攫取讀者的心思。以《末路狂花》為基礎,加上一點機伶、一絲憂愁、一抹甜蜜,就成了史上最逗趣又帶原創性的改編版。」──《出版者週刊》
「愛笛‧唐思──珍妮佛‧韋納最新創作中的平凡女性──可能變身為我們今年最欣賞的女主角。一個重量級女孩以寬大的胸襟氣度讓各種體型的男女讀者都能會心一笑。」──《今日美國報》
「珍妮佛‧韋納讓兩個一起長大的小女孩,到了高中時期經歷分離,多年後再度聚首,意外地踏上讓友情彌堅的冒險旅程。」──《Elle》
「珍妮佛‧韋納創造了深刻而真實的角色,她慧黠地編織出多重支線和伏筆,讓故事情中埋藏了許多幽默。強力推薦給喜好女性文學的讀者。」──《圖書館雜誌》
媒體推薦:「這本適合在海灘上慢慢享受的讀物將會以詼諧和智慧攫取讀者的心思。以《末路狂花》為基礎,加上一點機伶、一絲憂愁、一抹甜蜜,就成了史上最逗趣又帶原創性的改編版。」──《出版者週刊》
「愛笛‧唐思──珍妮佛‧韋納最新創作中的平凡女性──可能變身為我們今年最欣賞的女主角。一個重量級女孩以寬大的胸襟氣度讓各種體型的男女讀者都能會心一笑。」──《今日美國報》
「珍妮佛‧韋納讓兩個一起長大的小女孩,到了高中時期經歷分離,多年後再度聚首,意外地踏上讓友情彌堅的冒險旅程。」──《Elle》
「珍妮佛‧韋納...
章節試閱
《永遠的好朋友》
丹.史旺西在黑暗中醒來,完全不記得自己是誰、身在何方。他舉起一隻手,撐著頭,但放開手的時候看到手上沾了濕黏的血液,不禁疼痛地哼了一聲。他慢慢地(至少他是這麼覺得)感覺到回憶浮現在腦海中。他想起了自己的名字。他在戶外停車場,仰躺在碎石地上,他冷得快凍僵了。還有,除了鞋襪之外,他全身赤裸。
他坐起身,肚子突然一陣難受,痛楚席捲全身。他又擦擦頭,在砂礫地上滴下了一串血珠。他跟著一個女孩來到這裡。那個女孩——她的名字呼之欲出,卻又偏偏想不起來。高中同學,以前同班過,一口亮白潔淨的牙齒,穿著紅色皮鞋。上我的車吧,她悄聲說,車內比較溫暖。他們親熱了一會兒,女孩的背靠在駕駛座車門上,她的雙脣熱烈地貼上他的脣,他們的呼吸在黑暗中化為蒸氣,這時她將他向前一推。把衣服脫掉,她說,我要看著你。很冷耶!他雖然嘴上抗議,但雙手已經開始解開襯衫鈕扣和皮帶,因為天氣很冷、妞兒很辣,他才不會放棄這機會。絕不。
他轉轉身體脫下衣服,踢動雙腿讓長褲滑到鞋子上,脫下來的衣服在碎石地上堆成一座小丘,他全身赤裸在寒風中打著哆嗦,單手捂著下體,一抬頭,只見她拿著一樣東西抵著他。他嚇到心跳都停了——是槍嗎?——但他還來不及細想,他就發現那不是槍,而是手機。
閃光燈一亮,她按下快門時他只感覺眼前一片黑。「喂!」他大叫著,「搞什麼鬼?」
「看你有什麼感覺?」她咆哮著,「看你覺得被大家嘲笑是什麼感覺?」
他朝她猛撲,想要奪走手機。妳有什麼問題啊?
我有什麼問題?她踩著紅底皮鞋以輕快的步伐往後跳,一邊回答他:我的問題就是你。你毀了我的人生!
她迅速衝回車內,闔上車門,他甚至還來不及抓住門把。引擎醒了過來,呼嘯而去。他跳到車子正前方,以為她會停車,但根據他身體兩側的傷口和頭痛欲裂的感覺來判斷,她應該沒停下來。
他又呻吟了一聲,用力一撐讓自己站起來,往鄉村俱樂部瞅了一眼,那裡都沒人,而且會館已經鎖起來了。他在黑暗中仍可以看到網球場在一邊,高爾夫球場在會館後面,工具棚和其他附屬建築物在一排松樹下,離會館有一點距離。先找衣服穿,他決定好下一步後就痛苦蹣跚地朝最近的建築物走去。先找衣服穿……然後再復仇。
2
現在回想起來,當初那陣敲門的聲音應該會嚇到我,至少會讓我措手不及。我家——我從小就在這棟房子裡長大——在伊利諾州悅山鎮中一條死巷的末端。這個芝加哥郊區的小鎮裡有安靜的街道、整齊的草坪、優質的公立學校和一萬四千個靈魂。新月路上鮮有行人,通常這個社區裡晚上十點後唯一的生命跡象僅限於隔壁鄰居巴斯太太舉辦莎士比亞讀書會時,那時才會有車頭燈的光線投射在我臥室的牆上。
我一個人住,而且通常十點半就睡著了,但即便如此,當我聽到敲門聲,我的心跳竟沒有變快、手掌也沒有冒汗。在我的潛意識裡,我大腦細胞的某個位置,也就是科學家說存放記憶的地方,等著這一陣敲擊已經等很久了,我一直在等著雙腳走過地板,等著手放上冰冷的黃銅門把。
我拉開門,感覺到自己的雙眼瞪大,胸口呼吸急促。那是我過去的摯友,薇樂莉.亞德勒。我從十七歲之後就沒跟她說過話,高中畢業之後也沒跟她見過面,而她這時就站在前廊的燈光下:精緻小巧的瓜子臉、立體豐盈的櫻脣、濃密如扇的睫毛。她十指交叉緊握放在腰前,好像在祈禱。她的軍裝大衣上綁了一條腰帶,袖子上有深色的汙漬。
我們在寒夜中站了約莫一分鐘,在光錐下看著彼此,我腦中的思緒和煦如陽光、甜美如花蜜。我的姊妹淘,我一邊看著小薇一邊想,我的姊妹淘回到我身邊了。
我張開口,不確定要說些什麼,但是先說話的是小薇。「愛笛。」她說。她的一口皓齒亮白而整齊,她的聲音就和我多年前所記得的一樣富有磁性、充滿自信。那股聲音不管說什麼都像是在傾吐祕密,而她這個技巧已臻成熟,在芝加哥三級電視臺的夜間新聞播報氣象。電視臺在六個月前錄用她,不但大張旗鼓歡迎她加入,還在州際公路旁立了大型看板公布她氣象播報的時段。(大型看板的標題寫著「看這陣風把誰給吹來啦!」小薇的照片就在這行字上頭,焦點全在她隨風輕揚的髮絲和笑意盈盈的嘴脣。)「聽我說,真的有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發生了,」她說,「妳可以幫我嗎?拜託?」
我始終閉著嘴。她穿著一雙高跟鞋,鞋跟比大頭釘還要細,她的上身微往後傾,一邊壓抑著自己的情緒,一邊任雙手梳過秀髮,停在腰間,然後不安地轉著皮帶。難道我要我的髮型設計師動手改造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她的新髮型長及肩膀、亮如黃菊,而且在雨中會變成微捲的層次嗎?我雖然要求自己不要看她的新聞臺,但或許我在轉臺的時候曾經瞥見她的身影,或是經過公路時注意到她的造型,否則我現在怎麼會穿著法藍絨睡衣和厚毛襪,頂著前任死黨的髮型。
「妳看看妳,」她低沉的聲音裡滿是驚喜。「瞧瞧妳,」薇樂莉說,「妳瘦了。」
「小薇,進來吧。」我說。如果時間是個維度空間,而不是一條直線,如果時間像水一樣能讓你清澈地往下看,表面也會有漣漪和波瀾,其實我已經開門了。一切早就發生了,一如過往,一如應然。
3
我帶薇樂莉走進廚房,聽著她跟在我後頭用高跟鞋在硬木地板上踩出節奏。她抖抖雙肩,脫下軍裝外套,指尖一拎就把大衣披在椅背上,然後從上到下打量我。
「妳沒去參加同學會。」她說。
「我要約會。」我回答她。
她揚起眉毛。我轉身,在水槽裡將水壺注滿水然後放到爐子上,轉開瓦斯,不願意多說。
今晚打一開始就不是很順利,在交友網站建議下,我和網站替我安排的第六位相親對象約在餐廳見面(「絕對不要邀請陌生人到妳家!」網站上有嚴格的教戰守則。「永遠約在公共場所,記得帶手機、車鑰匙和足夠搭乘大眾運輸的現金,而且一定要讓朋友知道你在哪裡!」)我確實遵守第一條準則,開自己的車去,手機也充飽電,皮夾裡也有足夠的現金可以付賬,但第二條準則我卻沒辦法落實,因為當時我沒有朋友(我就是喜歡獨來獨往,不行嗎?),所以我印了一張紙條,用十八級字加粗體,貼在冰箱上:我十一月二十三日去見麥修.夏普。如果我出事,八成是他下的手。我還在紙條上印了相親對象的電話號碼和餐廳的地址電話,加上保險卡的影本。我想了一會兒,然後加了一行字,附註:我希望葬禮依軍儀舉辦……因為,說真的,誰不想呢?軍樂號兵奏安息號時總能引人熱淚。
「愛笛?」站在帶位檯邊的男人說。「我是麥修.夏普。」他準時到了,而且身材修長,一如交友網站的保證。這樣的改變讓我精神一振:我之前見過的那五個男生,整體來說,並不符合我的期望。麥修.夏普穿著合宜,粗呢運動外套、深藍色鈕扣襯衫、筆挺的褲子、皮革便鞋。他靠過來握手的時候,呼吸帶著肉桂的香味,人中有一道短短的鬍子。好,我心想。這個我還可以接受。沒錯,鬍子是個不討喜的驚喜,而且自從他放照片到網站上之後,他的髮際線又退後了很多,但我有什麼立場嫌棄呢?
「很高興認識你。」我說完便脫下黑色羊毛外套。
「謝謝妳赴約。」他的眼神上下打量我,短暫在我的身體上流連一會兒才回來看我的臉。他看起來沒有很驚愕,也不像是打算隨時往門外奔逃。反應不錯,我身上的衣服已經快變成相親制服了:黑色裙子的下擺精準地切過膝蓋中間(不會短到讓人覺得隨便,也不會長到失去女性魅力)、深紅色的絲質上衣、黑色絲襪、黑色低跟靴。穿低跟靴的用意是怕他在網站上的身高欄灌水,低跟靴的另一個用途雖然派上用場的機會不大,但也不無可能,就是穿低跟靴方便逃跑。「我們的餐桌已經布置好了。妳要不要先到酒吧點杯飲料?」
「不用了,謝謝。」網站上建議相親過程中喝一杯酒就夠了。我要保持頭腦冷靜,隨時應變,而且我也不希望讓他誤以為我有酗酒的問題。
女服務生接過我們的外套,將寄物證遞給麥修。「妳先請。」他說話的時候我正把圍巾和帽子塞進包包裡,甩頭讓頭髮自然散落。我的小腿終於瘦到可以把及膝靴的拉鍊拉到頂。我今天早上去髮廊的時候原本只打算修修髮尾,但保羅開口閉口都是「美女!」讓我聽得暈陶陶,而且他一看到我的時候甚至還濕了眼眶,所以我就被他說服,花了六小時和美金五百元又剪、又染、又燙,最後弄了一個層次豐富的及肩短髮。保羅發誓說我從某幾個角度看起來只有十六歲,頭髮挑染成蜜糖色,再搭配法國品牌的護髮乳,他保證未來四個月裡頭髮都會充滿光澤不毛躁。
我點了一杯夏多內白酒、凱薩沙拉、烤鰈魚,醬汁放旁邊。麥修點了卡本內紅酒、一份中卷當前菜、然後一份牛排。
「妳的假日過得好嗎?」他問。
「很不錯,」我告訴他,「很寧靜。我白天都和家人在一起。」此言不假,我把全套感恩節大餐——奶油瓜濃湯、烤火雞、栗子內餡、覆蓋在烤棉花糖下的甜馬鈴薯、還有感恩節絕不能少的南瓜派——都帶到城南的照護中心和我哥哥裘恩一起吃。我們一起坐在那間又小又熱的房間地板上,背靠著他的單人床,看著他最愛的《星艦戰將》。我三點離開,四點回到家,替自己沖了一杯茶,加了一大匙威士忌,倒一盤火雞肉和醬汁在門外給經常來我家後門用餐的小黑貓。我整個傍晚都坐在客廳,一手撫著肚皮,看著天空用灰紫兩種顏料變化出各種不同的暮色,一直到月亮東升。
「那你呢?」
麥修說他和他爸媽、他姊姊、姊夫和他們的小孩一起吃飯。他負責烤火雞,在雞皮上塗奶油和鼠尾草,火雞放上鋪滿洋蔥的烤盤後便文火慢烤。他說他喜歡烹飪,我說我也喜歡。我告訴他我自己嘗試做墨西哥鱷梨沙拉醬,他則介紹他在美食頻道上看到的電視節目,還有芝加哥那間熱門的新餐廳他一直很想去一探究竟。
侍者在我們面前放下餐盤。麥修立刻夾了一隻烏賊腳放進嘴裡。「妳的沙拉好吃嗎?」他的鬍子裡卡了一點烤麵包屑,我得忍住衝動不能伸手撥掉。
「很可口。」其實醬料調味太重了,每一片葉菜都油膩膩到沙拉醬會往下滴,不過沒關係,用難吃的沙拉換來一個像樣的約會對象還不算太吃虧,真是感謝上帝終於給我一個體面的男人。沙拉給我在口中嚼成了萵苣糊,我們對著彼此微微笑。
「講講妳的工作吧。」麥修說。
「我是卡片插畫家。」
他真的看起來很感興趣,這和我之前的相親經驗截然不同。我怎麼會進這一行?(都是因為我媽媽,她是卡片文案撰稿人,很多年前她偷偷把我的水彩畫交出去。)我在家工作嗎?(對,我在餐廳設了一個工作室,畫架立在窗邊,那裡光線最充足。)他還問到我的工作時數,受過哪些訓練,我一個人工作會不會孤單,因為沒有同事。針對孤單寂寞的主題,我可以寫出一篇散文或唱成一齣歌劇,但我只輕描淡寫地說,「我覺得一個人很自在。」
他也介紹了他的工作,他經營自助倉儲連鎖店,在伊利諾州和威斯康辛州都有據點。我問到他在哪裡長大,現在住哪裡,同時盛了一塊濕軟鬆塌的烤麵包丁到嘴邊,但是又原封不動放回盤子上,等著我每次相親都要經歷的畫面,這些男人會在某個時間點開始咒罵前妻。我和五個男人見過面,其中四人都堅稱他們的前妻是瘋子(其中一人的診斷是「可證明為精神病患」)。唯一的例外則是第五個,因為他太太過世了;他太太是聖人,如果妳要當她的繼任者,那聖人聽起來比瘋子還糟糕。
他很吸引人,我心想,這時麥修以滿腔熱忱詳細地描述他上個週末和登山社一起健行。「我每個月大概會跟他們出去個幾次。」他主動邀約。「或許妳也可以一起來?」
我一聽就覺得他是在說笑——我,健行?去哪裡?從肉桂卷烘焙坊走到冰淇淋店嗎?我一直得提醒自己現在的身材比較正常,而麥修完全沒見過我之前圓滾滾的模樣。「好啊,聽起來很有趣。」在樹林裡面健行,我稍微想像了一下:紅色刷毛套頭上衣、同花色的帽子和手套、保溫瓶裡裝著熱咖啡。我們肩並肩坐在樹蔭下的野餐毯上,看著小溪潺潺流過。
我們的主餐到了。我的鰈魚外緣焦脆、中心透明,難吃得要死,感覺那條魚根本沒活過。我作勢吃了兩口,而麥修聊著他的同事,一個叫做弗瑞的中年中階主管突然心血來潮決定動眼睛的整形手術。「他那天走進辦公室的時候看起來——嗯,我們的一位祕書說他看起來好像松鼠,只是好像有東西卡在他……」他話說到一半就笑了,頰邊露出酒渦。「就好像受到驚嚇的松鼠,他的眼睛好像要從頭顱裡爆出來了,我聽說他孫女一看到就哭了。」他低聲輕笑,我揚起嘴角。愛我吧,我心想著,我啜了一口酒,然後刻意以彩繪的指頭蹭著上衣的領口,我的胸部在衣服下隆起,卡在令人發癢的蕾絲裡,靠牢固耐用的鋼圈撐起來。
麥修撐起上半身靠過來,領帶晃啊晃地差點就碰到盤上那一灘牛血。「妳真的是個很獨特的人,」他說。
我雙脣一勾,「獨特」的定義很廣泛,可好可壞,但我暫時不去想那麼多。
「我覺得跟妳在一起很自在愜意,好像什麼都能對妳說。」他繼續說下去。
他凝視著我,而我始終保持微笑。他鏡片後面的雙眼很迷人。或許我可以說服他刮掉鬍子。我可以看到我們在一起的畫面,在覆滿落葉的小山坡上,我戴著手套捧著杯子,咖啡的香氣在空氣中氤氳而上。說到這裡就夠了,我用心電感應求他。愈說愈多,碰到地雷的機率就更高,美好的生活就可能會離我們更遠一點。
很可惜,麥修沒接收到我的訊息。「六個月前,」他開始了,他的雙眼鎖著我的視線,「我的臥房窗戶突然有熾烈的燈光,讓我驚醒過來。我一抬頭就看到一個龐大的綠色飛碟盤旋在我家上空。」
「哈!」我噗哧一笑。「哈哈哈!」我一直笑到發現他臉上毫無笑容……這表示他很認真。
「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繼續說,但話只說一半,然後才張開鬍子下的雙脣,「我那天晚上被外星人綁架了。」他靠近到我可以感覺充滿牛肉味的呼吸撲在我臉上。「他們在我身上做了實驗。」
「要甜點嗎?」服務生在我們面前展開菜單。
我努力搖搖頭表示拒絕,我說不出話。我單身,沒錯。我很飢渴,也沒錯。我很不願意承認在過去這三十三年內我只和一個男人睡過。我只聽過我爸媽對我說「我愛妳」。不管怎麼說,我絕不會跟自稱被太空生物侵犯的男人回家。每個女生都有底限。
帳單送來的時候,麥修拿出信用卡放在皮質帳單夾上,恨恨地看著我。「我想我不應該在第一次見面就洩漏了外星人綁架的事。」
我拉拉衣領。「或許不要比較好。我通常會等到第三次約會才提起我的尾巴。」
「妳有尾巴?」現在換他無法判斷我到底是不是在開玩笑了。
「很小條。」
「妳真逗趣。」他說。他的聲音透出一種消沉的絕望,這種口氣我太熟悉了。救救我,他其實要說的是,扔給我一條繩子,給我一抹微笑,讓我知道沒關係。我站起身時麥修在口袋裡掏零錢給寄物處的妹妹當小費,然後我跟著他走過餐廳,讓他幫我開門。「我覺得妳應該是個好人。」麥特在停車場說這句話的時候想要牽我的手,我往旁邊靠一步讓他牽不到。你錯了,我不是。
餐廳外頭,晚餐前的薄霧已經聚成寒冷刺骨的濃霧。街燈在金色光環下漫出光芒。麥修伸手撥撥頭髮,就算在寒夜裡他還是冒著汗。我看到小汗珠在鬍子裡一閃一閃。
「我可以打電話給妳嗎?」他問。
「當然可以。」我當然不會接,不過現在不適合提這件事。「你還留著我的號碼,對嗎?」
「還在。」他微微笑,感激的表情很可憐,然後他整個人往前傾。我花了一秒才搞懂原來他要吻我,又花了一秒才曉得我願意讓他吻下去。他的鬍子刷過我的上脣和臉頰。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他可以用奶瓶刷或鋼絲球刷我的臉,我大可以親他的領子或我那部喜美轎車的引擎蓋。
等我回到家時,他已經留了一則錄音,冗長、曲折、充滿歉意。他說對不起把我嚇到了。他覺得我很棒。他希望能再見一面,星期六好嗎?有一部電影獲得《先鋒報》極高的評價,或者去熱氣球嘉年華也不錯。我們可以去兜風,去野餐……他滿懷希望,愈講愈小聲。「那,」他說,「我再找時間打給妳囉。」他又複誦了一次他的電話號碼。我按下數字鍵「三」刪除,踢掉靴子,用塑膠髮捲把新髮型固定起來,然後坐在床沿雙手捧著頭,讓自己簡短地發出一聲老處女的無淚之泣。別放棄希望。網站可沒這麼說,只是我都會這樣對自己精神喊話,就像是一劑愛情童話的預防針。我要像雜草一般充滿毅力,我要相信其中一人就是我的真命天子:我也可以墜入愛河、嫁作人婦、養兒育女,當個正常人。別放棄希望,我會在開車去星巴克或蘋果蜜蜂美式餐廳時不斷朗誦,像唸經一樣。我在和第四號相親對象見面時也不斷為自己喊話。當時在保齡球館,這傢伙不知怎樣異想天開竟然約第一次見面的相親對象參加兒子的五歲生日派對(他的前女友見到我就臭臉,他五歲的兒子也是)。別放棄希望……但每次我不放棄,我那顆單純愚蠢的心就多一道傷痕。
「喔,好吧。」我大聲說出來。逗趣。這個評論還真不錯,但這世界真不公平!女人想在網路上交朋友真是困難重重,首先一定要瘦,接下來更殘忍的是還要有吸引力,個性親切,還要善於傾聽和好相處。當然要年輕,還保有生育力,還保有女性魅力,還保有窈窕的身材,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和支持妳談感情(卻不會介入)的家人。女人的標準那麼多,可是男人甚至不需腦筋正常。
我看了看時鐘,那個粉紅色和綠色相間的古董瓷釉鐘下面有圓胖粗壯的金色腿架撐著,那是我買給自己的生日禮物。才剛過十點,同學會現在應該氣氛正熱烈。瑪麗.安姆布拉斯特還打了電話給我,想在最後一刻說服我出席。「妳現在看起來很正!而且我相信大家早就忘記……反正,妳知道,我們都大了,同學還有其他話題可以聊。」
謝了,但不用了,謝謝。我倒了一杯水,和維他命一起吞下去,再灌下一口小麥草汁(我已經喝小麥草汁兩年了,但現在這玩意兒喝起來還是像院子裡割下來的草泥)。我把約會制服掛起來,脫下蕾絲胸罩換了一件純棉的。穿上法藍絨睡衣、套上襪子後,我就在床沿坐了下來,突然覺得精疲力竭。最近我才經常在思考我以前是個什麼樣的女孩,然後又如何轉變成現在這個女人。我想像著小時候的自己站在臥室門口,我的寢室原本是我爸媽的臥室。我穿著棉衫和百褶裙,深棕色頭髮紮成馬尾,綁頭髮的緞帶和及膝長襪花色相配。房間牆上的豐富色澤先讓小女孩喜不自勝,我畫的油畫高掛在窗邊,裡面的燈塔讓水面閃耀著金色的光芒。她喜歡床頭小桌上的瓷釉花瓶、潔淨的亞麻床罩、雕工細緻的床頭板,不過她馬上就發現這原本是爸媽的房間。還要住在這裡?她不禁好奇,而我必須解釋其實我也不想留在這裡,我想要去外地念大學,我計畫到大城市去生活,交幾個男朋友,找一份有趣的工作,四處旅行,我會用旅行途中在世界各地獲得的紀念品、公仔、照片來布置我的公寓,我一切都計畫好了,不過……
我側躺下來,血液流得很快,我的思緒也狂亂地到處奔撞,從看起來很像樣的約會對象,到我認識他的交友網站,到我的前男友維杰,他已經當我「前」男友當了四個月,但在那之前他其實也不算我男友。我猜,如果我們只出去過一次大概不能說他是我的男朋友,但我愛他愛到我覺得——或至少說我希望——那種轟轟烈烈的強度應該留給第一個讓你心碎的男人。
《永遠的好朋友》
丹.史旺西在黑暗中醒來,完全不記得自己是誰、身在何方。他舉起一隻手,撐著頭,但放開手的時候看到手上沾了濕黏的血液,不禁疼痛地哼了一聲。他慢慢地(至少他是這麼覺得)感覺到回憶浮現在腦海中。他想起了自己的名字。他在戶外停車場,仰躺在碎石地上,他冷得快凍僵了。還有,除了鞋襪之外,他全身赤裸。
他坐起身,肚子突然一陣難受,痛楚席捲全身。他又擦擦頭,在砂礫地上滴下了一串血珠。他跟著一個女孩來到這裡。那個女孩——她的名字呼之欲出,卻又偏偏想不起來。高中同學,以前同班過,一口...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