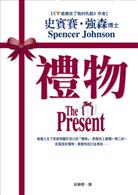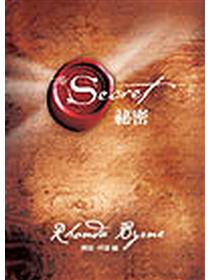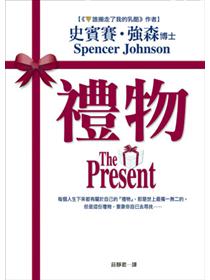導論
我的故事或許可稱為美國驅逐艦「班福特號(Benfold)的教育史」。在1997年6月我接管了班福特艦,之後的二十個月,我都在這艘導彈驅逐艦上度過。這艘美麗的戰鬥機器從1996年開始服役於美國海軍的太平洋艦隊,裝甲重達8600噸,並配有海軍最先進的自動化導彈;雷達系統可追蹤到五十英里外一隻飛鳥大小的目標;三百多位受訓精良的男女官兵;四部渦輪引擎使得船速高達三十海里,能急赴戰場痛擊敵人。
首次擔任艦長就掌管如此先進的設備,不僅令人興奮,也是極大的挑戰。既有表現機會也充滿困難。美國海軍對設備的投資總是毫不手軟,但我們知道科技應該站在輔助的角色,要能在實戰中發揮作用,操作設備的人員才是關鍵。然而,我們總是忽略人力養成的重要性。
驚人的統計數據指出,每年加入的二十萬人次美軍中,約有七萬人(近35%)提前退伍。其中雖然大部份都是非自願離開,卻也不代表他們原本喜歡留在部隊。而在完成第一階段役期的官兵中,希望繼續留在部隊的比例亦極低,甚至無法填滿高階軍官的宿舍床位。更糟的是,有軍事天份的人總是最先選擇離開部隊。這對納稅人而言是驚人的負擔,因為每名新兵單是招募成本即高達三萬五千美元,其他的軍事訓練費用亦是以數萬美元計。同時這也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開端,當退役軍人向親友做出了負面的宣傳,則後續新兵招募的難度勢必大幅增加。
美國政府每年編列高達三千二百五十億美元的國防預算,我們應該要使其發揮更大的效用。除了確保國家的安全及防衛能力,我們應該提供美國青年一種生活形態,不僅能成為傑出的公民,更能貢獻偉大的國家。
班福特艦儘管設備先進,但仍未能發揮應有的實力。這是因為官兵士氣消沈,且急於退伍,不願效力於海軍。而我畢生最大的驕傲就在於將這局面扭轉過來,使全艦官兵同心協力、士氣高昂。現在,很多人甚至認為班福特艦就是美國最佳的海軍軍艦。
會在此分享我的成功和失敗經驗,不僅因為這是個有趣的故事,同時也可提供許多企業或組織的領導者以為借鏡、指南。不管是海軍或企業,都應該協助內部人力成長。蓋洛普(Gallup)的調查指出,65%的離職員工其實是想離開自己的上司。由此可知,領導者的失職實將導致組織的鉅額損失。保守的估計,失去一名稱職員工的成本將是其薪資的1.5倍,其中包括生產力的損失以及新血的招募、訓練成本。
各式組織領導者所面對的共同問題,是如何從員工身上獲得最大的回報,這取決於三大變數:領導者的需求、組織的氛圍以及員工的潛力。我將在本書中說明海軍和一般企業是如何不適當的連結這三個變數,以及這錯誤所造成的驚人損失。當然,這些故事背後是希望能幫助各領導階層(不論是軍隊抑或企業)能更妥善處理這三個變數,使其發揮百分百的效力!
超卓的領導者總是難得一見,雖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領袖,但多數還是需要後天的學習,本書就是一個良好的他山之石。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人們意識到卓越領導人的重要性。唯有卓越的領導,才能帶領社會各階層回到生活的常軌,無論是教堂、家庭、學校、醫院、國會、法庭,乃至白宮。其中,軍事單位和企業尤其需要優秀的領導者,因為他們肩負著國家安全及經濟穩定的使命。在這次事件中,美國無論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加快了全球復甦的速度,並在反恐的作戰中獲得勝利。
危機總能孕育出優異的領導者。在面對9月所降臨的死神面前,人們蛻變成了英雄。或許我們已能不懼的面對一次次危機,但卓越的領導卻益顯重要。
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任何一位與我一般,遭遇著各式挑戰的人,並瞭解到領導是學習而來的。
總而言之,過往的經驗告訴我,要做一個成功的領導者必須先認識自己,並以此為基礎建構一個傑出的組織。身為一個領導者,必須有讓部屬將能力發揮到極致的空間。然而,在組織中限制部屬表現機會的往往就是領導者本身,這可能是源自於其自身的恐懼、自尊的需求或習慣。因此,要進行組織的變革,領導者的自我認識是必要的第一步。
透過對自我的認識,將改變領導者對組織日常互動的觀點,並提升領導層次至完全不同的境界。領導者的決策將不再受限於自身的恐懼、自尊的需求或習慣;更重要的是,領導者的改變將很快影響周遭的觀感,並得到正面的回應。如此的良性循環,會使員工與上司有更好的互動,並提升忠誠度。無論是在軍艦或公司,這樣的文化轉變都能使生活變得更有意義,而目標更明確。
要記得,組織不是一個收容所,每個組織都有存在的目標。軍艦要能作戰致勝,公司要能獲得利潤。但在達到目的的過程中,往往是採用單向命令的方式。縱使短期似乎有所獲益,但長期而言將導致不堪的後果。我的經驗顯示,唯有幫助員工探掘自己的潛力並加以發揮,才能完成在「命令與控制」體制下不可能的任務。
在經濟繁榮的時代,許多青年投身於科技產業,然而,也有青年選擇從軍。我們的工作就是使他們成為高科技專家──價值數十億美元尖端武器的操作者;再者,也要使他們有信心在國家危難或是身處異鄉時能貢獻心力。我們做到了,神奇的是我們沒有開除任何一個人,就成就了一般人認為難以達成的目標。
班福特艦雖然獲得驚人的成功,但尚未獲得全美一致的高度重視。美國海軍仍苦惱於內部眾多風格的將領,但若給我的屬下進行選擇,我有信心會受到屬下的青睞。
在接下來的章節,我將細述贏得部屬信任的概念及技巧,而這些正是達成班福特艦偉大成就的要義。本書將以我在艦上所獲得的經驗及歷程進行章節的安排,每一條寶貴經驗都將點出重點,並展開為一章來說明,章節安排如下:以身作則、積極傾聽、有效溝通、創造信任的組織文化、重視結果不論位階、合理冒險、超脫成規、攜手共進、團結一致,並盡可能改善部屬的生活品質。
在海軍學院時,我們認識到許多傳奇的海軍將領,包括亞歷山大(Alexander)和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等,但我總認為敘述得不夠全面。撰述傳記的人記錄了這些將領的輝煌戰績,但我的經驗告訴我,領導的藝術往往發生於不起眼的小事件──這些看似平常的舉動常能提振團隊士氣,並提高獲勝的機會。
領導者必須學著如何將團隊績效置於個人自尊之前,這對許多人而言是個困難的課題。「命令與控制」的領導絕對不是獲得部屬全心投入工作的最佳方式;相反的,我發現我給部屬的空間越大,他們回饋的效果越佳。剛開始時,他們還會事事徵詢我的意見,後來我告訴他們:「這是你的船,你該對它負起責任,請自己做出決定,並看看結果為何。」從此,「這是你的船」就成了班福特艦的口號。每個官兵都把班福特艦視作自己的責任。讓你的員工參與經營的過程,你就能獲得痛擊對手的力量。
艦長必須學會由官兵的角度來檢視軍艦的運作,他們應該鼓勵官兵勇於表達自我意見,並學會適時適當的分配任務。
接任艦長之後,我發現我有兩種選擇,一是不做任何變革,安穩的度過這兩年。這是種明哲保身的方式,我也曾經奉為圭臬。但這也指出美國海軍的一個大問題──即使兩年無所事事,仍會獲得升遷。
第二種選擇比較危險,就是進行革新。而我選擇了後者。在擔任班福特艦的艦長之前,我有過十六年其他職務的經驗,但直到現在才有進行革新的自信。
不論在企業或軍隊,我們很容易理解「他們」不希望規則被質疑或挑戰。「他們」可能是管理者,也可能是更高階的執行長。我花了很多的時間讓部屬知道,我希望規則能被質疑或挑戰,且應將上司與下屬視為一個整體。我自己也以身作則,對我的上司挑戰與質疑既有的規則,最後,我的上司與部屬都理解了我的想法。
在階層明顯的海軍中我是怎麼做到的?原因之一是海軍目前正有許多困境需要突破,也因此高位者願意提供更多的空間來試驗新方法;但更重要的是,我摸索出一種不需徵詢太多上司意見的方式。事實上,我試著站在上司的角度,並問:我能為班福特艦做什麼?我想,上司要的應該是在預算內能達成所有的任務、保持士氣高昂,並使官兵認同自己的任務。我想若能做到這些想法,上司應該就不會有所反對,他會把心力放在其他更需要改善的地方。
同時我也謹慎的選用採行的方法,不讓上司有被威脅的感覺。我想我的方法在公司裡應該也不會造成公司的危機,或是影響任何人的生涯規劃。總而言之,我會慎選方法,並在獲得長官認可的前提之下進行。同時任何行為都不是為了彰顯自身的功勞,目的僅在於改善組織的和諧與運作,絕無任何私心。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長官對這樣的結果也感到驚訝,並派遣其他艦長到班福特艦進行觀摩與學習。這也間接使其他艦長獲得改善,當然長官總是樂見其成。我相信這對希望進行變革的組織而言,也是值得效法的方向。
很多人都認為進行大幅度的變革將不利於生涯規劃,但這對希望永續經營的企業領導者而言是錯誤的想法。企業必須給勇於革新的領導者更多鼓勵,即使會有陣痛,也應適時施以援手,而非袖手旁觀。對我而言,保持變革就是維持組織活力、成長的不二法門。不能前進,就是敗滅──這就是生存的法則。許多規則在創立之初可能相當合時合宜,但隨著時間遷移,很有可能不再適用,這時就應該遭到淘汰。
當然,嘗試新事物總是不易。但沒有前例可循,換個角度看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我曾在《快速企業》(Fast Company)雜誌所舉辦為期兩天的會議中進行演講,與會人士高達六百多人,其中包括迪伊•霍克(Dee Hock,VISA國際創辦人)和湯姆•畢德士(Tom Peters,管理大師,著有《追求卓越》)。演講結束時的發問讓我有些不知所措,其中最難回答的問題是:建立改革目標時,衡量的標準為何?
這問題讓我有些尷尬,我只想加速完成變革的速度,並脫離傳統管理學的巢臼,僅此而已。但我從聽眾裡聽到了一些竊笑聲。
事後,我接到妹妹康妮(Connie)的電話,她擁有MBA學位,並曾任職於數家大型金融機構。她說組織中的管理委員會在進行任何變革前,總是希望能有具體的衡量尺度,否則對於變革的結果將很難評鑑。
但對我而言,我只知道班福特艦目前的狀態,以及我希望它達到的狀態。若我當初被迫定下了一些衡量的指標,官兵的創造力可能會被抑制,而最終所達成的結果或許將不復存在。
但問題在於沒有衡量標準的話,我怎麼決定變革是否需要?我無法解釋。生活本來就是充滿變化,種瓜得李的事也時常發生。因此,我進行判斷的方式相當簡單,單憑經驗直覺。若你正在進行「對的事」,就不必擔心走錯方向。
該如何定義對的事?如同美國最高法院法官波特.史都華(Port Stewart)對色情所下的定義一般:「色情很難定義,但一望即知。」若有事情你覺得是對的,沒有任何不妥,那你就是在進行對的事。
或許這樣簡單的說法還不能說服你,但在海軍、企業或生活上,很多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我希望、也相信,這本書能幫助各式企業的管理者體認到他們也有機會成為優異的領導者,就如同我剛上任的時候一般。同時,我也希望我的故事能幫你找到自信。雖然驅逐艦與寶鹼(P&G)等企業有所不同,但海軍的舊式管理概念卻和一般企業的規則相去不遠。身為一個領導者,你可以對你所屬的領域進行革新,就像我當初所做的一樣。
因為,那是你的船!
第二章 以身作則
談到海軍將領給人的印象,不外乎是穿著鑲金邊的筆挺軍服並厲聲的發號司令。但這並不足以成為一位領導者,真正的領導者,應該是以身作則而非斥責訓誡。
無論你是不是喜歡,你的所作所為都將成為下屬仿效的對象。他們會從你身上尋找可行的訊號,你的一舉一動都會有重大的影響。若是他們知道你會敷衍你不喜歡的政策,他們也會把這種作法視為可行之道。若是你曾說謊,他們也不會誠實。同樣的,若你勇於挑戰不合時宜的舊規,他們也會樂於嘗試。所有的影響都將深植於組織文化中。每次,當有軍官向我提出一個方案,我總是會問:「我們一定得這樣做嗎?有沒有更好的做法?」於是,他們在與我討論前便會試著思考更好的方案。領導者所散發出的訊號至為重要,你的決策邏輯以及你所做的一切,都會是部屬遵行的方向。
有趣的是,問題常出在自己身上
每當事情的結果不如預期,我會先耐住性子,看看自己是否為問題的癥結之一。我會問自己三個問題:我是否明確告知任務的目標?我給與的資源與時間是否足夠?我是否有予以他們足夠的訓練?經過統計,我發現有90%的比重,我必須負起全部或部分責任。
第一次體認到這個狀況,是我在菲律賓擔任韋伯斯特上將助手的時期。每個上將都有以自身名字命名的專用駁船,這是一艘可用於娛樂或巡視的遊艇。韋伯斯特上將就擁有這樣一艘美麗的駁船,負責照料它是我的職責之一,但我並沒有相關維修的人力。
某日,上將決定行駛這艘船前往蘇比克灣,我交代兩位水兵負責駕船,並與上將隨行前往灣外的一個小島。而在回程時,船拋錨了,我們在海上漂流了一個小時,而且連無線電也損壞無法使用。上將說道:「把我的旗子降下來。」當一個上將或將軍在船上時,會升起代表他的旗子,但顯然上將不想讓這種窘境被人發現。當時我真是無地自容。幸而有一艘清理垃圾的船經過,我招手請他們幫忙。他們用一條繩子將我們拖回港口,而這段期間上將都沒露面。
我不曾見過上將如此生氣,讓人明顯的感受到怒意。我或許可以用很多理由來搪塞,例如人手或工具不足等,但我最後還是負起責任,畢竟我應該準備得更充分。
當然,在剩下的期間內我使盡全力讓這艘船保持穩定和良好的狀態,也沒有再出過任何問題。
多年來的經驗發現,時時做好準備是避免失敗的不二法門。在1994年的事件讓我記憶猶新,當時我還是希洛艦的副艦長。有一名水兵在站崗時睡著了,這是非常嚴重的過失,因為在無警覺之下,全艦人員都有潛在的生命之憂。這名水兵的過失被寫成報告,也意味著他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而我必須決定是否將這名水兵移送審判。
事件顯示出是該名水兵失職,於是我將這名水兵送交艦長進行懲處,而未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令我驚訝的是,艦長竟詢問該水兵為何在站崗時睡著,而水兵回覆是因為前晚整夜都在進行打掃工作。為何要在夜間清掃呢?因為他的長官要他在早上八點以前完成這些工作。「士官長,你為何不給他更多的時間完成工作呢?」「因為部門指揮官要我們在八點以前完成。」我立即意會到問題的所在,並開始冒出冷汗。艦長回頭看著部門的指揮官,部門的指揮官把頭轉向他的上司(此時,我如坐針氈,幾乎要暈倒)看著我,然後對大家說:「副艦長要我們在八點以前完成。」
我根本沒想到他們會派遣一個隔天需站崗的水兵來清掃!但追根究柢,我應該更明瞭這個命令的適切性,也應該注意到他們沒有足夠的人力和資源來及時完成。艦長沒有對這位水兵進行懲處,而我覺得自己是個搞不清楚狀況的笨蛋。我對自己發誓絕不再犯,往後的每道命令我都仔細審視是否已清楚說明目標,是否賦與足夠的資源,以及授命者是否已有足夠的相關訓練。
當然,人非聖賢,總會有失誤的時候。不可能所有的細節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但我盡力而為。
別忽略你對部屬的影響
領導者必須了解自己對下屬的重大影響力,包括持有樂觀或悲觀的態度等,這都將影響周遭人事的步調。
有多少次你在進入上司辦公室時覺得受到了輕視?例如,他忙著檢收電子郵件而沒跟你打招呼;或雖然跟你討論,但仍不時接電話,似乎電話比你還重要。更糟的情況是,他根本不認同你或你的努力。
平庸的領導者大多不會想去了解自己的下屬。這經驗是我從下面的一個意外獲得啟發的:當時我的前任艦長巡視完班福特艦,他叫住一個來自德州的水兵布萊恩•亞歷山大(Blaine Alexaner),問他是否是一個新兵,事實上布萊恩在班福特艦服役的時間甚至還比他還久。但布萊恩沒說出這個事實,還佯稱自己是新兵,並客氣的問道:「請問長官在艦上擔任什麼職務?」我的前任指了指自己的胸針,並說道:「你不認得這胸針嗎?我是班福特艦的指揮官。」布萊恩表示很高興見到他,但見到這一幕的其他水兵則是大笑不已。
身為一個管理者,你必須傳達出一種想法:屬下們對你很重要,甚至沒有其他事物比他們還重要。你必須了解你的影響力,並聰明地用在正面的方向。站在下屬的立場,為他們著想,並試著幫他們成長。
當我離開班福特艦後,我成了一位高階文官的助理,當上司不能出席星期一的例行會議時,我就必須代為出席。這會議氣氛並不平和,因為有一個人通常都不太會控制自己情緒,尤其是對自己的下屬。若是你指出一些與他相關的問題,他會激烈的為自己辯解,就像是要與每個人吵架一般。我想他不了解其他人之所以保持沈默,是因為他傳達出一種訊息:我的作法很完美,沒有需要變動的地方。
雖然他也是一位優秀的領導者,但其面對批評的態度,對事情的解決根本於事無補,反而會令組織產生更多的問題。我試著想辦法去幫助他,最後我決定用電子郵件的方式委婉的告知,讓他知道我的想法,並請他試著控制自己的脾氣。
猜看看後續如何?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提到:「你是對的,我忽略了自己對他人的影響,在你指出後,我會在往後多加注意。」而他真的開始轉變。我想,若我是在公開場合予以指責,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
我發的這封電子郵件對我沒有任何利益關係,我想這就是能發揮效果的重要原因。我明確表明只是想讓海軍有所改善,而所有功績將歸於我的上司,不是我自己。我想,若是內容含有一點自我彰顯的色彩,可能會引起他更大的憤怒。因此,表達出自己動機的正當性,是讓長官接受想法的一個關鍵。
所有的領導者都會對組織運作設定出一個基調。熱情的領導者就會產生一個活潑的組織;相對的,若是領導者心情不好,整個組織也會跟著陰風怒雨。
但領導者在低潮時,又該如何扮演激勵而正向的角色呢?關鍵在於極小化對組織的傷害。我的部屬將壞心情稱為「陰暗面」。一艘軍艦的運作是全天候的,因此我也是隨時待命,準備處理問題的狀態。不久後,官兵會發現,若前晚我被叫醒的次數過多,導致睡眠不足,我隔天的心情就會不大好。他們計算過,不管是處理事情或巡察,假如我被叫起來的次數達四次以上,他們隔天的工作心情也會受到影響。後來,我發覺在起床號(早上6點)之後,官兵就會互相轉告我被叫醒的次數。有一次,我因通宵沒睡,隔天一早,有個年輕的水兵看我坐在駕駛艙的椅子上,就跟我說:「艦長,大家都說今天會是個『陰暗面』。」我到現在還覺得很有趣。但這件事也告訴我,每個人都有「陰暗面」,若你了解得越透徹,你就越能有效管理。於是,我決定在「陰暗面」發生時儘量減少與部屬的互動,這樣一來,至少能不對他人造成傷害。
領導者應建立起負責任的文化
在海軍多年,見過許多意外事件及錯誤的發生,例如軍事演習、設備搬運、戰術操練時。說實話,有很多情況是無法避免的,在這麼密集大量的操演運作下,有些事故發生在所難免,而這些事故常常所費不貲。
每當事件發生,我總是驚訝於每個人推諉卸責的態度。這或許是人類的本能,沒人願意成為眾矢之的。但我堅信,領導者應該知道何時該挺身而出,扛起責任。
以個人而言,我喜歡一個能使人坦白承認錯誤並負起責任的組織文化。我想,找出問題點並杜絕再發生的可能,遠比責任歸屬來得重要。身為一個艦長,我不想建立起一個推諉塞責、獨善其身的文化。
以《華盛頓郵報》的角度衡量對錯
當我接掌班福特艦時,毫無疑問的,我想讓它成為美國海軍史上最優秀的軍艦。但到達這個目標的過程也同樣重要,我總是小心的避開有違道德的捷徑。對我而言,判斷是否有違道德標準的準則很簡單,我會問我自己:若這件事被刊載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上,我會覺得驕傲還是感到羞恥?若是後者,我就不會去執行;若是前者,我會加倍努力去實踐。
達成目的很重要,達成目的的方法也同樣重要。這個非道德的標準其實相當簡單:做對的事。忘了那些太過鄉愿的職場政治,也別太擔心你的舉動會不會得罪某人;若你判斷這事是對的,就尋找一個適當的方法,拋開一些無謂的包袱,並付諸實現!
有時很難斷定將要執行的事情是否正確無誤,這時就更需要勇氣。這樣的理念,我曾將其落實到班福特艦上一名水兵所發生的事件,至今我仍深感欣慰。
由於作戰時每個人都必須堅守自己的崗位,於是當軍艦出海後,我們就不會讓官兵任意離開,除非家人患有重病,我們才會用飛機接載他們回家。而有小孩將出生這樣的理由通常不會獲准離艦,但我手下一名重要的軍官卻提出這樣的破例請求。醫生估計他的妻子將於軍艦離港後三天生產,但如此一來,該軍官將錯過在前往檀香山途中的一次關鍵演習。
這件事讓我天人交戰許久,許多人都沒能目睹自己的孩子出生,而我也不想為他破例。但最後我決定承擔潛在的風險,從海軍的角度而言,這會不會是個好決策,事實上我也不太敢確定。
在我們出發後四天,這個嬰兒在危急的情況下進行生產,由於生命跡象很不穩定,生產後一個月內都處於危險期。根據海軍的規定,這位軍官有了合理離艦的理由,因為他的嬰兒正處於生死未卜的邊緣。這位軍官離開不只一個星期,而是整整六個禮拜。現在回想,我真高興他能在危急的時候陪在妻兒的身邊,我做了一件對的事!他的孩子今年已經四歲,而且相當健康。
我想這個故事若刊登在《華盛頓郵報》上,我只會覺得驕傲,而不會感到羞愧。
事後我也更改了產假的規定:除了戰爭之際,所有軍官與水兵都有請產假的權利。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