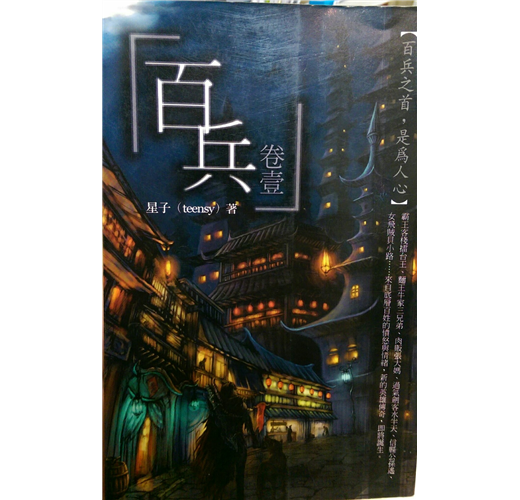第五章、地下海來
一夜過去,天終於亮了。衛靖自離飛飛客棧數條街遠的暗巷中探頭出來,偷瞧客棧外頭那對正忙著整備店面,準備做生意的梅家姊妹。
梅文柔臉色難看,對妹妹阿鳳頤指氣使,阿鳳卻笑瞇瞇地十分順從,還不時拍拍姊姊的肩,像是安慰著她一般。
衛靖領著阿喜,慢慢地靠近,想趁姊姊梅文柔離開時,趁機和阿鳳說些話。
他昨晚摸黑走了許久,總算走回飛飛客棧,當時客棧已經打烊,衛靖也不願惹來梅文柔的注意,便在不遠處的窄巷裡找著了個乾淨角落,窩上一夜。
梅文柔自顧自地埋怨了一會兒,無精打采進了客棧,阿鳳則還勤奮擦拭著客棧招牌。
「阿鳳!阿鳳!」衛靖壓低了聲音,遠遠向阿鳳招手。
「咦?又是你呀!」阿鳳見了衛靖,有些驚訝,放下水桶,碎步趕了過來。
「你昨天的錢給得多了,我不能收。」阿鳳一本正經,摸摸身上,跟著就要轉回客棧裡拿錢。
「不不!」衛靖連忙將她拉住,問:「我有急事,前晚搶了我上房的那對祖孫還在嗎?」
阿鳳搖搖頭:「他們昨天傍晚便走了,那少年回客棧時,身上受了傷,流了許多血,還向我問有沒有見到你呢,難道是你將他打受傷的嗎?」
「這……解釋起來倒挺費功夫,當然不是我打的,我和那小子成了朋友倒是真的。昨天我們在外頭碰上了土匪惡霸,搞得灰頭土臉。」衛靖聽公孫遙祖孫已經離開飛飛客棧,一時不知所措,也不願解釋太多。
阿鳳點了點頭:「我想你應當不是壞人,公孫公子向我問及你時,也是一臉關切,只是我姊姊一口咬定是你打傷了他,不停提議要報官逮你,反倒惹得那公孫公子不高興,斥了姊姊幾句,之後他們便退房走了,我姊姊為此生氣了一晚上,到剛剛氣還沒消呢。」
「妳姊姊這樣勢利,瞧人家生得俊朗漂亮,又是有錢大戶,想討好那小子,卻碰得一鼻子灰,當然生氣啦!」衛靖哈哈笑著。
阿鳳連忙對他比了個手勢,要他小聲點,衛靖也趕緊壓低聲音,生怕又惹得那兇蠻姊姊出來罵街,可難纏了。
「你對我姊姊很有成見,她有時說話不留情面,但她總也家中大姊,要擔著咱全家上下生計,和你立場不同罷了。你這樣取笑我姊姊,我不想和你說話了。」阿鳳嘆了口氣說。
「好好,是我的錯!」衛靖聳聳肩,無奈地嘆了口氣,他本想若是公孫遙平安返回飛飛客棧,或許可以來討回綠鐵劍,但此時公孫遙祖孫已經離開,不知去向。
「對了,阿鳳,你知不知道這些地方?」衛靖取出貝小路的手帕,說了上頭三個地名。
「老原客棧我倒沒聽過,黃樑巷離這兒挺遠,比昨日你去的富貴居還遠許多,鴣水街倒離這兒不遠……但那兒總有些奇怪的人聚集著,你上那兒要做什麼呢?」阿鳳邊想邊說,將鴣水街的位置說明了一遍,突然怔了怔,像是想起了什麼一般,說:「要是我沒記錯,這三個地方都是通往海來市地下街道的地方,你要去地下街道嗎?」
「地下街道?妳是說海來市有藏在地下的街道?」衛靖狐疑問著。
阿鳳歪著頭想:「我不甚清楚,但聽姊姊說,地下街道和地上街道一般,有商家,有民戶,只是貧破許多便是了,姊姊說那兒都是些流浪落魄、沒出息的傢伙,或是犯了律法的壞人,才像隻老鼠躲去地底的……」
阿鳳性格耿直,此時只是將姊姊的形容轉述,但見衛靖臉色有異,知道他或許也要前往那地下街道,姊姊的形容自然是傷人了,連忙住口。
「這樣好了,我和姊姊說一聲,我帶你去吧!」阿鳳歉然笑著。
「我只是好奇問問而已,我丟失了東西,還能再到處亂跑嗎?我準備要回家受爹爹責罰了,唉……」衛靖苦笑,和阿鳳道別,阿鳳仍然要將多收的房錢退給衛靖,衛靖嘻嘻笑著,也不願收下,領著阿喜轉身快步跑了。
□
清晨的陽光曬來舒暢,衛靖在早餐店鋪買了燒餅豆漿,提在手中吃著,沿路向路人詢問,去找尋有多馬車站的地方,準備返回小原村,向父親說明一切。
衛靖走著,一陣陣熟悉的敲打聲傳入耳中,那是打鐵的聲音,衛靖循著聲音轉入一條街,這條街裡的店家,十之八九都是鐵舖,有些販賣著兵刃,有些販賣的生鐵鋼材。
衛靖想起了此行還要替父親添購鑄劍鋼材,一想至此,又嘆了嘆氣,按照本來計畫,本來可以在富貴居玩耍休息,一住十天半個月,每日將購來的材料安置,等到返家那天,王老爺會安排馬車,將他和鋼鐵材料一併送回小原村。此時他隻身一人,根本揹負不了預定要購買的鋼材數量。
儘管如此,衛靖還是轉入了那打鐵街,心想買些較輕的工具如磨石、繩結之類的東西,也算是聊勝於無,就算是開開眼界也好。
他接連逛了幾間鐵舖,像個行家似地對著店裡的東西品頭論足,一會兒嫌這家賣的鋼鐵條偷工減料,一會兒嫌那家牆上懸掛著的幾柄長劍中看不中用。
「咦,這家鐵舖倒是真材實料。」衛靖進了一家鐵舖,四處摸摸看看,這鐵舖不大不小,幾樣兵刃價錢不算便宜,但也不貴,不論材質還是造工,皆屬一流。
門簾一掀,自舖子內房出來的男人卻是何聞,衛靖瞪大了眼睛,連忙轉身,佇在展示兵刃的小櫃前,假裝觀賞物品。
何聞並未發覺衛靖,他身後還跟著一個男人,手上拿著兩柄劍,一柄是自武裕夫手中奪來的烏鋼劍,一柄正是昨日富貴居中,衛靖借給公孫遙使用的純鋼劍。
衛靖一點也料不到會在這兒遇上何聞,本來趁著何聞與鐵舖老闆交談之際,悄悄挪動身子,想神不知鬼不覺的離開,跑得越遠越好。正慢慢接近店鋪門口之際,偷偷瞥頭一看,見著了鐵鋪老闆手中拿著的純鋼劍,不由得一怔。
只聽那何聞正色地吩咐:「你可要好好用心,這兩柄傢伙其中一柄叫作『白龍』可是滿大哥的,他本來吩咐我去請長青爺修補,但長青爺忙,你是長青爺的高徒,和我又是舊識,我才找你幫忙,這價錢……」
那鐵舖老闆拍著胸脯說:「何大哥,你放心,我在長青老師門下學藝十年,要說到打造神兵利器可不敢和恩師比擬,但修補這尋常缺口,絕對包管何大哥與滿大哥滿意,至於這個價錢,意思意思便夠了,只盼何大哥來日飛黃騰達,照料一下小弟便是了。」
鐵舖老闆邊說,邊含蓄地以手勢比了個數字,何聞也滿意地點點頭,掏摸出錢付帳。
衛靖假裝瞧著木架上展示的劍柄繩結,一面豎耳聽著,心中先是一驚,那鐵舖老闆口中的「長青老師」,便是他的大伯父衛長青。
衛靖偷聽著,很快明白,心想必定是滿全利吩咐何聞將這柄打出缺口的純鋼劍交給衛長青修補,衛長青名揚海來,是城裡著名的大鑄劍師,這工錢自然不便宜。何聞陽奉陰違地找了衛長青一個學成開業的徒弟來做這買賣,自然是貪圖這鑄工價差了。
何聞又吩咐些事情,還吹噓著自己在闖天門裡頭地位越來越高日後必定是個重要角色,那鐵舖老闆和何聞也是舊識,兩人聊了一陣,這才將何聞送出了鐵舖。
衛靖等何聞走遠,這才揀了幾串繩結拿到結帳櫃臺,和那顧店的伙計夾纏不清地問著:「老闆,你這繩結做的真漂亮,但我不知道要如何綁到劍柄上頭,你能不能教教我?」
那伙計搖搖頭,答:「我不是老闆,我是伙計,咱們開店便是賣東西,哪裡還有時間教你手藝?」
衛靖偷瞥到那鐵舖老闆將純鋼劍放入內房後,又走出外舖,正在另一邊招呼客人,便放開了嗓子,嚷得更大聲:「大哥,你行行好,大強的伯父從外地回來,帶了好多木頭寶劍分給大家,就是少了繩結,我買了繩結,卻不懂得綁,你教教我,我便再買十個!」
那伙計連連搖頭,說:「別嚷嚷了,我說不行就是不行,走吧你。」
鐵舖老闆皺皺眉頭,先是對衛靖笑笑,又將那伙計招來,在他耳邊低聲斥責:「咱們開店做生意,客人要買你難道還不賣?結個繩結又不是什麼高明技術,你隨便教他個簡單的結法,便賺他十個繩結的錢,這還要我教?」
「舖子上沒有劍可以示範給他看,我進工房裡拿柄短傢伙……」那伙計應了幾聲,心有不甘,轉身要往內房走。
鐵舖老闆還不忘吩咐:「順便瞧瞧爐子,火候足了便叫我,我進去替何聞修劍。」
那伙計應了一聲,瞪了衛靖一眼,撥開簾子進入內房,衛靖吐吐舌頭,見到此時又有幾個客人進來,鐵舖老闆正忙著招呼客人,心中一喜,抓起櫃臺上的繩結跟在那伙計後頭,也進了內房,嚷著:「大哥,你要我跟你進去嗎?你忘了帶繩結怎麼教我吶?」
「小弟,你不能進去!」鐵舖老闆瞥到了衛靖跟入內房,本要出聲阻止,但見到進來的幾個客人衣著華貴,像是行家,便也不敢怠慢,心想快快讓伙計教衛靖個簡單結法,做了這筆生意便是。
衛靖跟入了內房,裡頭是鑄劍工房,十分寬闊,一面壁上有好幾張大木窗,以供通風,內房裡頭的器具設施他都十分熟悉,伙計正在一旁桌上挑著短劍,要當作道具來教衛靖結繩,一見衛靖進來,破口便要罵:「你怎能進來……」
衛靖趕忙對他比了個小聲的手勢,低聲說:「外頭來了大買家,你老闆要我進裡面和你學,大哥,你人好,教會了我,我另外付你十銀當作學費!」
衛靖邊說,一邊傻笑,一邊打開腰間錢袋,掏摸著裡頭的錢。
那伙計走向門邊,瞧瞧外頭,果然見到老闆正和幾個客人高談闊論,他摸摸鼻子,向衛靖點點頭:「好,老闆要我交你個簡單的結法,我想你對這玩意很有興趣,和我是同好,我教你個漂亮的結法,這學費不會白收你的。」
伙計這麼說,卻已將手伸出,一副「先給我錢再說」的模樣。
衛靖連聲稱謝,從錢袋中拿出十銀,交給伙計。
伙計也隨手取了柄短劍,接過衛靖遞來的繩結,教他如何將繩結牢靠又美觀地結在劍柄上。
衛靖心中暗暗好笑,這玩意兒他六歲便會了。他仰裝認真地學,不時發問,一面四處觀察,見到一面牆壁處那爐灶火生得旺盛,旁邊一張木桌子上橫擺著兩柄常劍,便是何聞帶來的那兩柄劍。
衛靖心頭隨著那爐火炙熱跳動,一面假裝認真學著結繩,一面四處望望,見那幾扇木窗都敞得極開,要是能找著機會奪了劍便跑,那丟失了的純鋼劍便又失而復得了,屆時何聞不知會是什麼表情。
衛靖一想至此,忍不住要笑出聲,他打了個哈欠,伸伸懶腰,又掏摸出三銀錢,放入伙計手上,說:「大哥,這兒熱得很,有沒有茶,我向你買一杯來喝!」
「茶?有,你等等,我倒給你!」那伙計接過了錢,正想著眼前這傢伙呆愣得好笑,外舖老闆正和顧客解說一柄寶劍,便再和這小子夾纏一會兒,說不定他還會掏錢,連忙推開另一間房門,進去倒水。
衛靖一見那伙計進去倒水,二話不說,拔腿衝到了那木桌前,抓了兩柄劍便往木窗跑去,一翻身便跳出了木窗。
「哈哈,真想看看何聞得知劍沒了的樣子!」衛靖忍不住狂笑,也不管劍鞘還留在鐵舖裡頭,隨意自背後包袱取出一件衣服,將雙劍包起,繞道自鐵舖外頭,要叫喚在店外等著他的阿喜。
衛靖繞到鐵舖外頭,已經聽見了裡頭傳來了伙計的叫嚷聲,正要開口叫喚阿喜,突然如遭雷殛。
街道一邊佇著三、四個人,其中一個正是何聞,另幾個是他的跟班,身上大都負傷,都是在富貴居和衛靖、公孫遙一戰時傷的。
阿喜讓幾個人圍著,伏在地上不住哀嚎,一腳曲折,像是斷了骨頭一樣。
「阿喜!」衛靖大叫,衝了上去。
「大哥,那小子來了!」何聞跟班見了衛靖衝來,連聲大喝,原來何聞一行來這兒找鐵舖修劍,何聞踏出鐵舖,正要離去,幾個跟班買了小菜好酒前來迎接,其中一個認出了富貴居一戰時,跟在衛靖左右的阿喜,便窩在鐵舖外頭一角。
當衛靖在店裡頭糾纏之時,何聞一夥人便將阿喜抓到了一旁,打斷了腿,等著衛靖來尋。
「啊呀,小子!你總算來了,讓咱們等得這麼久,你說,該當何罪?」何聞打了個哈欠,哈哈笑著,一旁的跟班也跟著起鬨,叫嚷:「哈哈,你要留下一手還是一腿?」、「另一個傢伙呢?上哪兒去了?」
其中一個跟班叫嚷著,還用腳踏了踏阿喜的斷腿,阿喜發出了痛苦的哀嚎聲。
此時鐵舖裡頭也起了騷動,那伙計倒茶出來,遍尋不著衛靖,桌上雙劍竟都沒了,只得告訴老闆,老闆和伙計嚇得魂都沒了,聽了外頭衛靖叫嚷聲,這才出來,見著了衛靖,雙雙大叫:「他在那兒,劍在他手上!」、「何大哥,他偷了你的劍!」
何聞一驚,果然見到衛靖手上抓著兩柄劍,劍身用衣服裹著。
「別過來!」衛靖大叫一聲,扯去裹著劍身的衣服,抓著兩柄劍跑到路邊一處水井旁,大喊:「何聞,你放了阿喜,我將劍還你!」
「好小子……好小子!」何聞怒極,但見衛靖舉著劍,作勢要往井裡丟,那井既深又窄,水也有五、六分滿,劍給丟了下去,可得費好幾天抽乾井水,才能取回,那時早超出了滿全利交代給他修劍的時限。
「好,我們將狗還你。」何聞恨恨說著,朝著跟班使個眼色,那跟班哼了兩聲抱起阿喜,他動作粗魯,觸動了阿喜斷腿,阿喜連連嚎著,斷腿不住發抖。
「其他人別來,一個人將阿喜抱來就行了,我把劍交給他!」衛靖大聲喊著,他見阿喜痛苦,心中甚是難過,阿喜是他家中老狗,年紀只比他小了兩三歲,衛靖有記憶以來便一直和阿喜玩耍在一起,如同家人一般。
「別刺激他,劍比臭狗重要太多。」何聞低聲向那跟班吩咐,跟班應了幾聲,抱著阿喜朝衛靖走去。
衛靖也將雙劍放在井上,一步一步遠離,跟班見了,便也又上前幾步。
「阿喜,咬他臭手!」衛靖見跟班離自己已然不遠,陡然大叫,本來痛苦發抖的阿喜聽了主人呼喚,果真發了狠勁,一口咬在那跟班手腕上。
那跟班本來凝神注意著衛靖,就怕他說話不算話,得了狗兒又將劍扔下井,但見衛靖一步步遠離水井,這才漸漸放心,正打算接近井時一得了劍,將狗拋入井裡,卻忘了手中的阿喜卻是活物,還懂得聽主人號令,惡狠狠咬了他一口,手上突地劇痛,一個放鬆,阿喜已經跳落下地,儘管斷了一腿,仍是拚足了老命用另外三隻腿狂奔向衛靖。
衛靖在大喊的同時,也向前奔出,在何聞等驚覺情勢生變的同時,抬腿一踢,將那放在井上的雙劍,一齊踢入了井中,跟著抱起奔來的阿喜,轉身就逃。
「好可惡的臭小子!」、「將他抓住,殺了他!」、「趕快將劍撈起!」一干幫眾們大罵要追,何聞儘管怒極,但仍大聲喝止,吩咐他們趕緊想法子抽水救劍。
□
衛靖六神無主地逃著,懷中的阿喜隨著衛靖的奔跑發出一陣一陣的哀嚎聲。衛靖逃了好一陣,直到抱著阿喜的雙臂痠極,連連轉頭去看,見無人追來,這才在一個老巷中將阿喜放下,在堆放在角落的雜物堆中找著了根小木片,用八手小刀割開一件衣服,替阿喜將斷了的前腿包紮緊實,不時連連安慰著:「可憐的阿喜,那些惡人實在太可惡,將你的腿弄斷了……」
衛靖又是難過,又是害怕,不時探頭出老巷,瞧見有幾個闖天門幫眾走來,儘管那些闖天門幫眾與何聞未必是同一掛的,但衛靖終究心虛害怕,抱起阿喜便逃,走了幾條街,漸漸覺得雙臂痠疼不已,只得又停下休息,只見到這小道前頭後頭不時也有兩三個闖天門幫眾走過。
他曉得闖天門是海來第一大幫派,鬧區裡四處都有闖天門幫眾。本來在原先的行程計畫中,在富貴居中住上十天半個月後,王老爺會安排馬車將他送回小原村,衛靖壓根沒有仔細考慮返家的方式,儘管他依稀記得當初下車的多馬車驛站,但東逃西竄之下,連自己所在位置都糊塗了,也不知還有哪兒有多馬車驛站,又怕走上大街便碰上闖天門幫眾,一時之間,竟不知所措。
衛靖連連抓頭,正想硬著頭皮去找路人問路,突然見著前方一條不起眼的巷口立著一塊小小的路名板子,上頭寫著「鴣水街」。
衛靖突然想起昨晚那老婦一番話,趕緊在包袱裡掏摸,摸出了貝小路的手帕,看看上頭的字樣,又看看巷口那塊板子,原來自己在市區裡亂逃亂繞,竟找著了那老婦所說,通往「地下海來」的入口之一。
事實上情勢演變至今,就算不剛好碰著,他也遲早想起那手帕,阿喜腿傷得重,就算找著了多馬車驛站,衛靖也絕不忍心讓阿喜再忍上一日一夜的顛簸車程,然後再走個大半天的路程回到小原村。
衛靖嘆了口氣,對著懷中的阿喜說:「阿喜呀阿喜,我帶你去躲藏幾天,等你腿好些,再回小原村,咱們再也不要來這可怕的地方了。」
衛靖抱著阿喜,走入了鴣水街。鴣水街離鬧區不甚遠,卻不同於其他街上那般繁華,街道兩側大都是些低矮的磚房,消沈死寂,像是廢棄許久一般。
如同阿鳳所說,鴣水街上的人看來的確有些不同,眼神較為犀利,大都揹著行囊。衛靖想找些人問那枯井在哪兒,但一靠近那些人,就聞到一股特殊的臭味,像是霉味。
衛靖遲疑著,自顧自地逛了許久,隨著那些從外頭轉入巷子的人走著,心想要是這兒是通往什麼「地下海來」的通道,必然有進有出,隨著人群找必然找得著。
果不其然,鴣水街街尾一處轉角,那兒搭了個棚,棚底下正是一口枯井,說是枯井,但井上頭蓋著木板,堆疊了滿滿的雜物。四周有些戴著笠帽的小販,在附近做著茶水小吃、雜貨物品之類的生意。
衛靖默默地靠近,見到枯井兩側也有幾間破屋,牆上的木板小門時開時關,不停有人進進出出。
衛靖口渴,向一個蒼老小販買了杯涼茶,剛喝入口就聞到重重的霉味,差點噴出口,但總算強嚥了下去。
「外地來的?第一次下去?少年人打傷了有錢人家,要避難來著?」那小販冷冷瞧著衛靖,用沙啞的聲音問。
「嗯……和人結了仇,下去玩幾天。」衛靖不願耗時間和他解釋,隨口應著。
「要不要買些實用東西,底下用得著的。」蒼老小販在那枯井木板上頭堆疊著的滿滿雜物中翻著,東西千奇百怪,有破損了的單筒望遠鏡、有漆黑的老舊扇子、有不知放了多久的零嘴乾糧,還有些看不出是什麼的古怪東西。
衛靖挑揀半晌,先是買了些乾糧包入包袱,又買了幾杯涼茶裝滿水壺,跟著挑了柄扇子,他心想這附近都瀰漫著一股霉味,要是到了「地下」,可能更不透氣,有把扇子也好搧搧風。
衛靖付足了錢,還傻怔怔地站在原地,那蒼老攤販遲疑問著:「還想買點什麼?」
衛靖怯怯問著:「鴣水街枯井,指的便是這口井嗎?可以請老先生你掀起木板,好讓我『下去』嗎?」
「當真是第一次來!」那蒼老攤販沙啞笑著,指向一旁的破屋說:「往那兒去!」
衛靖尷尬笑著,抱著阿喜推開木門,只見到小屋裡頭地板是空的,有一條大梯斜斜地深入地下。
「這可真是稀奇……」衛靖見那大梯深不見底,不禁有些害怕,猶豫了好一會兒,深吸了口氣,踏下階梯。
那階梯陰暗漫長,兩側不時有些巨柱大樑,參天木是世上最堅實的木材,作為地底街道的樑柱最是穩固。
樓梯似乎有十數層樓那麼高,衛靖走著走著,越來越是疲累,臂彎裡的阿喜也因為難受而不停亂動,衛靖只得停下,靠坐在樓梯牆邊歇息。
此時這漫長樓梯寂靜暗沈,唯一的聲音是些許漸遠、漸近的腳步聲,許久才有一兩個人和衛靖錯身而過。
衛靖心中害怕,包袱越抓越緊,忽然想到什麼,打開包袱,胡亂摸著,突然大叫一聲:「我的『小衛』不見了!」
「啊,一定是那賤丫頭!」衛靖大叫,原來是溫于雪送他的娃娃無故不見了,他想起昨夜巷弄追逐中,貝小路曾一度奪了他的包袱,還拿在手裡打量玩弄。躲藏竹簍時,聽那天龍地虎幫說起飛雪山莊當家是個大賊頭,那大賊頭指的應當便是那老婦,貝小路則是那老婦的孫女兒。
衛靖想起昨夜和貝小路初次相見時,貝小路也是偷了什麼韋爺夫人的夜明珠,才受得韋家家僕的捉拿。貝小路顯然是個厲害慣竊,定是自己在言語上得罪了她,她心中記恨,儘管聽她奶奶的話,還了包袱,但還是暗中摸去了裡頭娃娃。
「可惡,好可惡,飛雪山莊貝小路!」衛靖怒罵著,心中的害怕倒減少了些,歇息了好半晌,這才抱起阿喜重新往下。
走走停停,許久之後,樓梯出現分道,有通往兩側同樓層的,也有繼續向下的。
衛靖終於見到較為寬闊,且是平行的通道,低頭見通往下方的樓梯更顯陰暗,便不再往下,轉向往前方的岔道走去。
那是條陰森晦暗的長道,兩側牆壁盡是泥石土磚,每隔一段也有些粗壯參天木柱作為基樑。
這通道裡頭兩側牆上,不時可見到一些漆黑的破窗子,和一些老舊招牌,倒真像是埋藏地底的街道。
長道漫長,似乎永無止盡,相隔十分遠,牆上才會出現一盞油燈,勉強提供些微照明,且每隔一段距離,便會出現通往兩側的岔道,走著走著,四周的人也多了起來。
衛靖見到有些流浪漢隨地倒臥在牆角,便也有樣學樣,找了個較為乾淨的角落坐下,將阿喜放在身旁——他和阿喜,都沒力氣繼續趕路了。
他不停搧著扇子,只覺得四周霉味重得要令他窒息,但扇子本身就帶著厚重霉味,越是搧風,反而更臭。
他取出乾糧和涼茶,和阿喜分著吃。他邊吃,邊伸手摸著石牆木柱,上頭有些字跡,大都是些無意義的塗鴉字句,字跡陳舊久遠,當中也夾雜了些看得懂意思的句子,諸如「張某某、田某某,某年某月在此刻下愛的誓約……」或是「第四隊李隊長,率全隊兄弟一十六人,死守不退,殲敵六十餘人……」等。
吃完了乾糧,衛靖靠著牆發愣,撫摸著牆上斑駁痕跡,天馬行空地幻想,不知不覺打起了盹兒,輕輕拂著阿喜的背,在這地下街道度過了第一個晚上。
□
「今兒個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呢?這地底街道不見天日,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也不知道,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衛靖拉拉褲子,他剛在這地下街道一間空房中的角落解決了大小便,順手用角落的沙土埋了。
漫長的發呆之餘,他也會耐不住性子,起來活動一下,發現街道兩旁的空屋,是久未有人居住的,裡頭更為破爛、悶臭得令他將要窒息,且伸手不見五指,他這才明白為何沿著長道上見著有些流浪漢寧願窩在懸著細微燈火的牆角邊,也不願住在屋裡。那些燈火少而珍貴,底下總有較多的流浪漢盤據,誰也別想悄悄地將燈火偷去空屋獨佔。
他回到阿喜身邊,阿喜經過了這兩天還是三天的歇息,斷腿處慢慢復原,至少已經能夠以三隻腿,一跛一跛地四處嗅聞。
衛靖瞧瞧包袱,乾糧和涼茶都已經吃盡,自己和阿喜都餓得極了,此時他在這地下街道待了兩三天,已經不那樣害怕,反倒起了些好奇。便領著阿喜開始往深處走。
這一走,又走了許久,令他感到驚訝的是,漫長的通道兩旁,人潮漸漸多了,也慢慢可見到些做著生意的商家,賣著牛肉餡餅、豬肉包子之類的食物。這兒街道的兩側的房間,多半有人居住,不像前頭那區域的無主空屋。
衛靖餓得昏頭,也顧不得那些餡餅、包子,是否如上頭那蒼老小販的茶水一般臭,大步走去一間賣餡餅的店家,也不管那小店陳舊昏黃、四周骯髒油膩,掏出錢來買下幾個牛肉餡餅,大口吃了起來。
「唔?」衛靖有些訝異,這餡餅雖然稱不上美味,卻沒想像中的難以下嚥,衛靖大口嚼著,一下子吃去好幾個餡餅,還餵了阿喜兩塊,又和老闆要了兩碗水,和阿喜一人一碗,咕嚕嚕喝著。
吃飽喝足,衛靖抹抹嘴巴,覺得精神好了些,便繼續往前走去。接下來兩三條街更加熱鬧,流動的人潮更多,偶爾也可見到些小孩子四處遊玩。
衛靖好奇逛著,只見兩側的店家千奇百怪,有賣著蛇湯蛇羹的店家;有賣著奇怪玩物的店家;也有些藥鋪,瓶瓶罐罐滿是些奇異毒蟲,光是蜈蚣便有好幾櫃。
衛靖吐了吐舌,心想這些蜈蚣,可能大都是從這四通八達的地下街各個角落抓來的吧。
衛靖注意到某些靠得近的店家甚至是民居,門外會懸著同一顏色或是圖案的旗幟,表示他們歸屬於同一勢力範圍。
另一個令他覺得奇怪的現象,是家家戶戶不論勢力範圍,門裡門外大都擺放了兩三盆奇怪小草,他注意到整個地下街道的古怪味道,有一部分便是來自這一盆盆的奇怪小草, 混合著整片地下海來積年累月的陳舊霉味。
前頭一家店,裝潢得倒挺華麗,雖然比不上地上市中心裡熱鬧商家那樣富麗,但在這老舊的地下城中,卻也顯得格外亮眼,至少那酒紅漆木門外頭那幾盞夜明珠燈,便十分閃亮迷人。
店家的門口掛了面米色麻布旗子,上頭的圖案是兩柄彎刀交叉。
幾個掛著鼻涕的小孩聚在店外閒聊交談,衛靖也湊了上去,店裡頭大都是賣些人偶娃娃,店裡頭的胖老闆笑瞇瞇地坐在竹椅上,揮著扇子搧風。
令他感到好奇的是,店門口那兩座木造小箱,像是精心設計的機關一般,上頭擺著小招牌,一塊寫著「神兵」,一塊寫著「百畜」。
衛靖怔了怔,這才想起以往在小原村,曾經聽過上過大城市的孩子說,這是大城市中最新的玩物,一座大箱子中藏著許多小罐子,孩子們投下銅幣,便會掉落出小罐子,罐子裡頭裝的都是些童玩飾品。
衛靖當時聽得著迷,一心想見識這神妙的販賣器具,又想瞧瞧罐子裡頭裝著的漂亮玩物。
衛靖取出錢袋,數了數錢,這趟行程至今,父親給他的旅費和自己的零用錢已所剩無幾,剩下來幾張大面額鈔票,是要用來購買鑄劍材料用的工錢。
衛靖摸著最後幾枚銅板,捏著一枚投進那上頭寫著「神兵」的罐子機上頭的小孔中,只聽得喀啦幾聲機關轉動聲,木箱子下頭果然滾出了個罐子,衛靖趕緊蹲下拿了,罐子只有半個手掌大,打開來一看,裡頭是柄雕工精美的木製月牙鏟。
「哇!」衛靖高興得閤不攏嘴,拿在手上瞧了半晌,心想他在家裡和父親極少鑄造刀劍以外的其他兵刃,街坊們耕作用的鐵鋤鏟子倒是修理過不少,此時見了這柄月牙鏟,不免盤算著這鏟刃要如何鑄造,長柄要用什麼材質,柄尾是裝個純鋼尖頭好還是裝個黃銅鈍頭好。
衛靖又投了枚銅幣,這次落下的是雙短戟,衛靖不免又把玩了好一會兒,他跟著又將一枚銅幣投入一旁寫著「百畜」的罐子機,掉落出來的是隻木雕小狗,長得竟和阿喜有些相似。
衛靖對這兩座罐子機可真是愛不釋手,恨不得整座抱回家,好好研究把玩一番。
在這玩具店鋪對面是間米舖,裡頭聚了許多駐足購米的地下住民,米舖四周則是些小吃店、雜貨鋪等等,光顧的客人也不少,店家外頭都插了面雙刀交叉的小旗。衛靖見到米舖外頭一張凳子上,坐著一個中年大漢,捏著塊米糕吃著,睨眼打量著四周。
衛靖瞧那大漢穿著長褲捲到膝蓋上三吋,一雙肌肉精壯的腿上滿布傷痕,左腿肚上也紋著一塊青色的雙刀圖樣。
衛靖猶自猜測那大漢小腿肚上誇張突起的肌肉是否硬得過石頭的當下,小吃店起了騷動。
幾碗湯麵、菜盤子飛砸而出,跟著桌椅也給撞出了好幾張,吵鬧聲更加熱烈。幾聲哀嚎,那小吃店的店老闆、店小二一個個鼻青臉腫地跑了出來,大叫:「余大哥——余大哥!田鼠幫潘元那廝又來了,他帶了個好厲害的傢伙!」
米舖外頭那粗腿大漢吞下米糕,有些口乾,向米舖老闆要杯水喝,看了朝這兒逃來的小吃店老闆一眼。
小吃店裡一群人大步走出,帶頭的那個一雙小眼分得極開,臉上生了許多痣,腰間懸著一柄大刀和他的鼠輩模樣極不相稱。
「潘元,你又來搗亂!」、「上次你讓咱余大哥打得還不過癮?」小吃店附近幾家懸著雙刀旗幟的伙計們紛紛出來向,但見那一行被稱作「田鼠幫」的十來個漢子們趾高氣昂地往米舖走來。
帶頭的潘元拍拍腰間大刀,頭仰得極高,向小吃店老闆哈哈一笑說:「上次我便跟你說過,再來定砸你的店,你們這些『雙刀幫』的傢伙敬酒不吃吃罰酒,這次你們可有得受了,哈哈!」
「潘元,你是被打上癮了,還是腦袋給我打壞了。」凳子上的大漢懶洋洋地站起,冷冷瞧著潘元。周邊店家大都是雙刀幫,一些客人也是雙刀幫的,聽了大漢這樣說,紛紛歡呼叫嚷:「余大哥打死這些傢伙!」、「咱們老老實實地做生意,他們便只會耍流氓、欺負人。」
潘元讓姓余的大漢一瞪,身子一抖,退了幾步,卻還是狠狠地說:「余二腿,我敬你是條漢子。這些平庸傢伙和你有何干係,你護著他們幹啥?這次我帶了花剌街的擂臺王來,識相的滾遠一點,別什麼都往身上攔!你自以為是英雄好漢?別裝模作樣了,李闖天都死了幾十年了!現在哪裡還有好漢?」
「鼠輩!」那叫作「余二腿」的漢子怒眼一瞪,猛一抬腳,將凳子朝著潘元直直踢去。
「哇嗚——」潘元尖叫一聲,抱頭閉眼,像隻讓貓嚇著了的老鼠,連閃避都不會了。
凳子卻沒砸在潘元身上,是潘元斜後側一人,伸出胳臂接住了那凳子。
「好!擂臺王就是擂臺王!」、「一出手就立了功,潘大哥定看重你了!」田鼠幫的一票漢子大聲鼓譟,替己方這人歡呼助勢,也有幾個不屑地說:「我看也沒什麼,他靠潘大哥近,這才撿了這功勞,要是換做我,一拳便將那椅子打碎。」
潘元回過神來,又叫又跳,大力拍掌喊著:「好一個擂臺王,好一個樊軍,這余二腿交給你了!你接連替咱田鼠幫立下大功,我不會虧待你的!」
潘元邊說,邊將那替他接下凳子的「擂臺王」拉到身旁,自個也挺了挺胸,扳回氣勢。
衛靖擠在眾人之中看著熱鬧,只見那擂臺王樊軍劍眉鷹眼、皮膚黝黑、虎背狼腰,兩條繩子在胸前交叉,綁著背後那棍形包袱,應當是他的隨身兵刃。
「我聽說這幾日田鼠幫挺囂張,四處拔別人的旗子,四街的大刀王義和三十六街的鐵頭王都敗了,原來便是多了你這傢伙。我余二又叫余二腿,你好好記著,以後想報仇儘管來找我。」余二腿大聲說著,壓根不將樊軍放在眼裡。
「我叫樊軍,花剌街霸王客棧,你想報仇,可以來找我。」樊軍哼了哼,同樣這麼回答,又瞧瞧余二腿的那雙精壯的腿,說:「聽說你腿上功夫不錯。」
潘元搶著說:「這傢伙又不使刀,搞了個雙刀幫,卻是自吹自擂他那雙腳有如兩柄刀子。你說說,是不是很會裝模作樣吶!」
「這雙裝模作樣的腿,上次將你踢得在地上求饒,一邊拉屎一邊打擺子,你忘了嗎?」余二腿一腳微微向前,夾腳草拖鞋晃呀晃地說。
「今天便將你打成瘸子,樊軍,上啊!」潘元大喝一聲,拔出腰間大刀,亮晃晃地好不嚇人。
余二腿瞧了瞧潘元那柄大刀,知道大刀王義向來寶愛自己配刀,刀不離身,此時大刀既在潘元身上,王義想來是遭逢巨厄,他和王義並無交情,卻也聽聞過他名號,此時豪氣勃生,拍著自己大腿喊:「潘元,你搶了大刀王義的刀,有種也搶了我這兩柄刀!」
「好,我成全你!」潘元大聲應著,樊軍已經大步邁向余二腿,身形一矮,架出馬步,隨即便是直直幾拳打去。
「好!」余二腿後躍閃開,猛一抬腳,往樊軍臉上壓去,去勢威猛,當真如同開一柄山大刀。衛靖和圍觀眾人一齊發出驚呼,都只能見著那草鞋的殘影在空中畫出弧形。
磅!樊軍卻不後退,而是握拳抬手硬格接下,余二腿但覺得樊軍的手腕像是堅石一般,後足筋竟有些發疼,心想至此,身子卻已經又接連發出三腿。
樊軍或閃或格,往前逼近數步,要往余二腿懷裡鑽。樊軍使的是結實威猛的近身拳術,只要能鑽入余二腿身懷近處,余二腿那雙腿便沒了用處。
余二腿一面出腳,一面閃身,要和樊軍保持距離,兩人鬥到了牆邊,余二腿一個迴旋重踢,踢在樊軍臉上,將樊軍頭和半邊肩膀都壓砸在土牆上,登時土石飛揚。
「嘩——」圍觀眾人見余二腿這腳重得有如劈裂大山一般,都想大勢已定,樊軍定然給踢死了。雙刀幫的伙伴正要歡呼,卻聽聞余二腿悶吭一聲,身子搖晃後退,竟是乘勝追擊的第二腿,讓樊軍抬肘正好頂著,便像是大腿踢擊在堅石上一般。
余二腿只覺得一腿痠麻無力,才退兩步,樊軍已虎竄而來,幾下踩踏在地上的腳步聲如擂戰鼓,鑽入了余二腿身前。
「好厲害的硬氣功!」余二腿猛喝一聲,身子躍起,雙腿像柄鉗子,緊緊挾住樊軍雙臂,騎坐在樊軍胸前。
「你以為靠得近了便能打著我,是吧!你以為余二腿便不會使拳了,是吧!」余二腿大聲笑,展開雙臂,或拳或掌、一記一記朝樊軍頭臉上打。
「是!」樊軍大喝,身子一沈,雙腳踏地發出巨響,將挾在身上的余二腿震得鬆了些。樊軍突地也踢一腳,踢得高極,腳尖蹬在余二腿的後腦杓上。
「你不也以為我不會踢腿?」樊軍剛這麼說,余二腿已然落下,暈眩眩地摀摸著後腦,見樊軍又已逼來,正要後退,樊軍的拳頭手肘已然紛紛頂撞在余二腿胸腹上,轟隆隆地好響。
余二腿口中鮮血飛灑,骨頭不知斷了幾根,身子飛撞在土牆上,落下時憑藉著蠻橫狠勁,盡力躍起想奮力一搏,樊軍卻躍得比余二腿更高,幾記連環踢腿全踢在余二腿身上,力道竟不輸余二腿的腿勁。
余二腿摔落在地,再也無法爬起,那些店家老闆、伙計、客人紛紛擠來,七手八腳地扶起余二腿,心痛喊著:「余大哥!」、「這幫鼠輩流氓,下手如此兇殘!」
潘元哈哈大笑,大步走來,身旁一干田鼠幫眾一擁而上,將雙刀幫的店家伙計全拉起便是一陣痛打——雙刀幫只是這地下海來普通住民,為了自保而立的名號,並不是逞兇鬥狠之徒,為首的余二腿一倒,便遠遠敵不過形如惡匪的田鼠幫了。
「跟何聞那些傢伙一般蠻橫可惡!」衛靖本來見樊軍威猛,心生欽佩,但見田鼠幫形跡兇惡,四處砸店打人,將好端端的貨物糧食亂拋亂砸,不由得心生憤怒,四周有些圍觀的人,卻都不敢作聲。
潘元猶自笑著,舉起大刀,往癱倒在地上的余二腿雙腿砍去。
「你做什麼?」樊軍手快,在潘元一刀斬下之際,捏住了大刀刀背。
「啊呀!」潘元叫喊一聲,額頭讓一枚小石子打中,淤青了一小塊。
「樊軍,你又做什麼?」、「你為何阻止潘大哥?」、「讓潘大哥斬他雙腿,斷他雙刀呀!」田鼠幫叫囂著。
「誰扔石頭打我?」潘元摀著額頭大叫,又瞪著樊軍:「你抓著我的刀幹嘛?田鼠幫要壯大聲勢,當然要幹得狠一點,讓開,讓我斬了這傢伙一雙臭腳!」
「潘哥,我早便說明,這次隨你來市區,便只是來練拳頭。你們田鼠幫要壯大聲勢,那與我無關。我練拳頭,也不是要取人性命,我將那使刀的大漢打昏,你撿去他刀,那便罷了,我打倒這余二腿,你卻要斬他腿,這可過份了些。你要斬他,便等他傷癒,自己打敗他,屆時要斬要剮,也和我無關。」樊軍說完,還打了個大大的哈欠。
潘元瞪大眼睛,氣得說不出話,一干幫眾瞎起著鬨,大聲嚷嚷:「你這傢伙,說什麼大話!別忘了你欠潘大哥多少錢?」、「潘大哥要斬誰,就斬誰!知道嗎?」
樊軍聽見了潘元手下提起自己的欠債,似乎讓針刺了一下,轉頭冷冷瞧著那兩個叫囂跟班,說:「潘大哥替我扛下的債,我會還給他。我有我的做事方法,你夠膽子,就將剛剛說的話再說一遍。」
樊軍冷笑,將兩隻手搭在方才叫囂的兩個跟班肩上,那兩個跟班登時洩了氣,一個賠笑道歉,一個神情僵硬,以眼神向潘元求救。
「樊軍……」潘元清咳兩聲,他替樊軍扛了一筆債務,這才挖來了這厲害打手,替他打敗地下海來不少強勁對手,勢力擴展地極快。他知道樊軍性格剛強,儘管有樊軍欠他人情,卻也不能逼絕,正要想些化來緩和氣氛,那些米舖店家、小吃店家的老闆伙計,也趁亂將余二腿救出,抬到不知哪兒去了。
「啊呀!」潘元話還沒講出口,又讓石子射了一記,惱怒跳腳痛罵:「到底是誰偷打我?」
四周的幫眾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紛紛走入圍觀人群搜著。
衛靖摸摸鼻子,蹲低了身子,石子當然是他射的,他瞧那潘元不順眼至極,在地上摸些碎石,以阿喜的身子作為掩護,趁亂偷襲。
「樊軍,你眼快,有沒有瞧見是誰扔石子?」
「石子從那兒飛來的。」樊軍隨手一指,便指著衛靖那兒方向。
衛靖倒吸了口冷氣,不安地挪動身子,幾個田鼠幫眾走來,拉扯著衛靖身旁的圍觀人群。
「我剛剛瞧見一個鬼鬼祟祟拿著彈弓的小鬼,跑入那邊拐道了!」衛靖摸著阿喜身上的毛,和一名田鼠幫眾大眼瞪小眼,胡亂說著。
「讓開,讓開!是誰朝我扔石子,有種出來說話?」潘元大叫大嚷,推開了人群走來,見了一旁衛靖蹲在地上摸狗,隨口問著:「小鬼,你手上那是啥玩意兒?」
「哥哥,這是梳子。」衛靖拿在手上的八手搬出來的正是柄梳子,隨手替阿喜梳著毛。
「喝!小子,你腳邊那堆是啥!」潘元大叫。
衛靖低頭一看,腳邊還有十來顆小石頭,是他剛剛在地上摸來的,卻忘了踢散,而是堆疊成一小堆。
「扔石頭的分明便是你這臭小子!」潘元一把揪起衛靖領子,舉起了手就要打他。
衛靖仍隨口瞎扯:「大哥,我又不會彈指功,哪能扔疼你?那石頭分明是彈弓射出的,射你石頭的小鬼明明逃入了那兒,你又不信?」
「你敢頂嘴!」潘元心中惱怒,根本也不理究竟是不是衛靖,舉起巴掌就打了衛靖兩個耳光。
衛靖本來還覺得有趣,但讓潘元重重打了兩巴掌,惱火至極,抓住潘元手腕一扭,使出家傳擒拿術,腳一拐,將潘元摔倒在地。
潘元本也有練過兩下子,但料想不到衛靖會使擒拿,一不留神給摔了一跤。
「我踩扁你!」衛靖既已動手,也不再多解釋什麼,順手抱起阿喜,還狠狠一腳踩在潘元臉上,拔腿就跑。
「臭小子,給我追!追!」潘元的怒吼聲遠遠發出,田鼠幫大叫大嚷地追趕。
衛靖腳快,在人潮中亂跑亂鑽,趁亂轉入了一條不甚熱鬧、暗沈沈的拐巷,回頭看看,見田鼠幫沒能追上,心中得意,呵呵笑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