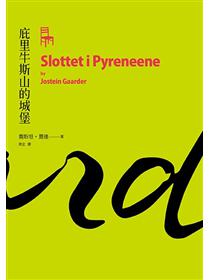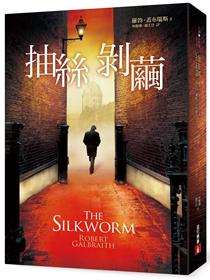他的任務───
是終結教宗的性命,
這好比直接撕裂信徒的心。
不過,殺死教宗,
卻能避免其他
沒必要的謀殺計畫……
宗教陰謀+政治詭計+金援賄賂+黑幫操弄=(為教廷奉獻)/(靠教廷得利)?!
一個教宗之死,揭開了權勢角力與貪污腐敗的黑幕,
然而,教宗之死是種種惡行的句點?
還是另一個深不可測的陰謀的起點?
幕後主使者是梵蒂岡教廷?是美國中情局?還是義大利地下組織?
P2是何方神聖?人人聞之喪膽的J.C.真實身分又究竟是誰?
眾所周知,若望․保祿一世於上任第33天離奇猝死,
官方說他是心臟病突發,但關於教宗實遭謀殺的小道傳言卻延續至今。
據說梵蒂岡教廷的人事變動及財務調查,乃至於義大利黑手黨活動,
皆與若望․保祿一世之死脫不了關係。
18,15-34,H,2,23,V,11
Dio bisogno e IO fare lo. Suo augurio Y mio comando
GCT(15)-9,30-31,15,16,2,21,6-14,11,16,16,2,20
一天,派駐倫敦的葡萄牙記者莎菈‧蒙泰羅,
先是在機場海關受到攔阻,返抵住處後竟還遭到槍擊,
並且收到一份莫名所以的郵件,內含一組密碼、一把鑰匙、一份名單,
令莎菈既驚又疑的是,她父親的大名就出現在名單上。
除了莎菈,紐約的費理斯神父、馬德里的菲力貝神父、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巴布羅神父,
皆在羅馬主教斐蘭吉遇害後收到一份他寄出的文件,
他們不知道的是,文件暗藏「法蒂瑪第三個祕密」,
更是解開若望․保祿一世之死、
瓦解教廷謊言與詭計的關鍵……
★本書真實歷史人物★
若望․保祿一世:一九七八年八月膺選為羅馬教宗,同年九月辭世,是歷任教宗在位時間最短者之一。
卡米涅‧貝可瑞里:一九二八年生於義大利,為專門披露政治、金融醜聞的《政治觀察》週刊創辦人,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遭暗殺。
亞道‧莫洛:義大利政治家,曾五度當上義大利總理,最終遭紅軍旅槍殺。
利齊歐‧蓋里:共濟會義大利第二分會的「當家老大」,曾為蓋世太保其中一員,策畫過無數恐怖攻擊,若望‧保祿一世謀殺案便是其中之一。
保羅‧馬辛庫斯:美國總主教,一九二二年生於美國。一九七一至一九九○年間擔任梵蒂岡銀行主管,直接涉及無數金融醜聞。
羅貝多‧卡維:米蘭銀行家,與梵蒂岡及保羅‧馬辛庫斯總主教往來密切,人稱「上帝的銀行家」。
若望馬利‧維勒:法國樞機主教,一九六九年受保祿六世任命為國務卿,若望․保祿一世藏想將他革職。
桑多斯耶穌路濟亞: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生於葡萄牙,為法蒂瑪預言見證者之一。
馬力歐‧莫雷第:第二代紅軍旅創立者,最後被判處六個無期徒刑,但卻於一九九四年意外獲釋。
J.C.:生卒年不詳,為無數恐怖行動之真正主使者,義大利共濟會成員,在犯罪世界舉足輕
重。
作者簡介:
路易斯‧馬吉爾‧羅沙(Luis Miguel Rocha)
一九七六年生於葡萄牙,曾於倫敦工作多年,擔任電視編劇及製作人。現居葡萄牙,持續從事電視及電影創作。著有三部宗教歷史懸疑小說,官方網站www.luismiguelrocha.com。
譯者簡介:
陳枻樵
畢業於東海大學外文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目前於英國Imperial College London進修中。有電子信箱可供意見交流:cycmaclaren@yahoo.com.tw
章節試閱
「所以他們是在教宗出手前先下手為強。」莎菈下了這樣的結論。
「正是如此。而且教宗還打算將所有祕辛公諸於世,這會讓那些人全吃上牢飯。他手中掌握的內幕多不勝數,比方說,靠著P2居中牽線,阿根廷於福克蘭群島戰爭中所用的飛魚反艦飛彈其實是受惠於梵蒂岡銀行。妳能想像這後頭牽連多廣嗎?」
「天啊。」
「他們甚至還和具有黑手黨背景的米切雷‧辛多納合作,由他負責和黑手黨聯絡,共同賺進大把鈔票。」
「他也是成員之一嗎?」
「沒錯。不過,雖然有許多人死於辛多納之手,其中還不乏達官顯要,但教宗之死與他無關。可是即使如此,他光其他問題就一個頭兩個大了。」
「沒有人負責調查其他詐騙案嗎?」
「有,歐洲各大相關單位與美國司法部門根據手中情報進行調查,但仍花了好一段時間才釐清真相,並在若望‧保祿一世當上教宗不久便登門造訪。密會中,美國司法人員向教宗說明當前情況,讓他採取適當措施,而教宗也是在那個時候才曉得梵蒂岡內部有不法分子,得整頓一番。但是他們早教宗一步動手。」
「就是他們謀殺教宗的嗎?」
「這我不清楚,但我認為他們至少該負起道德責任,而且和真正兇手一樣有罪。」
「你口中的他們是誰?」
「利齊歐‧蓋里、羅貝多‧卡維、總主教保羅‧馬辛庫斯以及樞機主教若望馬利‧維勒。此外,梵蒂岡內部另外有人幫忙為兇手開路,事後再清掉所有線索。清晨四點半時有人發現教宗去世,他的寢室在下午六點便已清理乾淨、封鎖起來了,房門鑰匙由維勒保管。十二個多小時後,使徒宮已找不到亞畢諾‧路奇安尼住過的半點痕跡。」
「真有效率。」
「他們做得很趕。當天早上五點半,相關人士宣告教宗去世也才過四十五分鐘,遺體保存處理員便抵達梵蒂岡了。仔細分析那天的情形,席諾拉吉兄弟來得這麼快實在讓人起疑,更何況義大利法律規定,人死後二十四小時才能進行遺體保存工作。」
莎菈搖搖頭。
「同一天下午六點,若望‧保祿一世的遺體便處理好了,這根本公然違法。」
「但是是什麼毒藥讓醫生也驗不出來?」
「教宗不是被毒死的。」
「不是嗎?」
「嗯,醫生也沒有被騙倒。」
「那……」
「單純的心臟病發作不足以讓教宗死對頭如此慌亂,傻瓜也看得出事有蹊蹺。保祿六世於一個月前去世時可不是這種情形。」
「那到底是誰謀殺教宗?」
「沒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想就是這個兇手在追我們。」
「那他一定和P2有關係。」
「沒錯,謀殺若望‧保祿一世的人從以前到現在都是P2會員。」
「但是你卻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只知道他名字的縮寫是J.C.」
「那我是從哪裡開始被牽扯進來的?」莎菈又問一次,希望父親能說個明白。
「妳從哪裡開始被牽扯進來?」上尉大聲地重述一次,然後嘆了口氣,想著要怎麼解釋比較好懂:「法戴瑪‧斐蘭吉和我一樣是P2舊會員,他花了好多年搜尋線索、蒐集證據,為的是想找到那份消失的文件。就在他打算放棄時,終於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
「在哪裡?」
「梵蒂岡祕密檔案庫。」
「怎麼會在那裡?」
「我也搞不清楚,這妳得去問J.C.。跟這起事件有關的人先後死去,J.C.也許因而覺得比較安全了,所以把文件留下來,但這真的是不智之舉。」勞悟回答。
「我同意,不過這不是重點,斐蘭吉發現文件,然後呢?」
「發現文件前不久,羅馬檢察官皮耶妥‧薩維歐帝重查若望‧保祿一世命案,那些文件成了非常重要的物證,所以十分有價值。此外,許多人皆想將之銷毀。於是斐蘭吉決定把文件帶出梵蒂岡,寄給大家都不認識的人,請他代為保管。然而,隔牆有耳,有人發出威脅,結果斐蘭吉怎麼處理?他寄了張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照片給菲力貝‧亞拉岡跟巴布羅‧林崗,上頭有他倆才懂的訊息。後來發生了某件事情,雖然我不知道怎麼回事,但他因為那件事才決定將名單寄給妳。」
「可是為什麼是我?」
「因為妳是他的代女。小時候,我曾向妳提過這個人,忘了嗎?他好久以前就搬到羅馬去了,所以妳不認識他。」
「斐蘭吉得找個跟組織無關的人幫忙,在名單上看到我的名字後,他推測妳收到文件必定會和我聯絡,而我也會馬上做出反應,最壞的情況是妳對他的信置之不理。只是斐蘭吉沒想到自己後來會被抓,還讓組織幾乎掌握所有情報。」
「那他現在在哪裡?」
「一定死了。」她的父親語帶哽咽地說。
想著想著,莎菈表情更為凝重。
「我不記得自己有個義大利代父。」
「別被名字給騙了,斐蘭吉是如假包換的葡萄牙人。」
「什麼人都一樣,他讓大家陷入險境。」
「別這麼說。」
「我說的是實話,他攪亂一池水,為的是什麼?」
「揭露真相。」
「真相被鎖在暗處,對大家都好。」
拉斐爾看看外套口袋,抽出一張紙和本篤十六世的照片。
「那是什麼?」莎菈問。
「菲力貝神父在馬德里收到的東西。」
拉斐爾將信遞給莎菈,雖然她不懂西班牙文,但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類似,所以理解上幾乎沒有問題。
今天是我七十四歲生日,也是我為過去所犯的錯付出代價的時候。造化弄人,祂是幕後推手。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仍無法理解當初那些決定與行動有何意義。一開始我們走在正軌上,胸懷崇高的理想,後來卻為內心的醜惡所蒙蔽,犯下卑劣的罪行。我們的所作所為,就算把剩餘的人生都拿來行善贖罪、將自己與外界隔絕也無法彌補,身上的污點永遠清洗不掉,彷彿在告訴我們:「你逃不了的,你逃不了的。」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我的生日,我終於要付出代價了。在道別之前,我寫了這封信給你,並附上敬愛的教宗的照片,柔光之下,當能祈禱。至於我,則以此告解作為道別,我太懦弱,只是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教宗死去。
「我和菲力貝是好朋友,前往西班牙籌備他的葬禮時,相關單位交給我這些東西。」
「他們不覺得信的內容有問題嗎?」
「他們沒有仔細推敲,而且幸好我比組織早一步拿到這封信。但是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邊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不但殺死巴布羅,還拿走照片。」
「那照片有什麼特別的?」
勞悟掏出一支小型紫外線手電筒。
「靠近一點。」
剛開始還有點猶豫的莎菈禁不住好奇,於是靠到父親身邊,拉斐爾稍稍瞄一眼,沒有忘記自己正在開車。紫外線之下,本篤十六世的容顏完全消失,某個老人的樣貌巧妙地浮現。
「他是誰?」莎菈問。
「我不知道。」勞悟回答。
「這張照片有雙重肖像。」拉斐爾說。
勞悟移開紫外線,本篤十六世的身影立刻重又出現。
「我一頭霧水。」
「我不知道他是誰,但組織必定很清楚,文件在這個人手上。」勞悟說。
「而莎菈手上握有的另外兩樣東西跟這有關。」拉斐爾說。
「什麼東西?」勞悟問。
「一組密碼……」
「不管怎樣都被你朋友吞下去了。」莎菈說。
「還有鑰匙。」
「沒錯,鑰匙。」莎菈完全忘記了,她從褲子口袋裡掏出來交給父親。這把鑰匙很小支,可以用來開掛鎖。
「這是從哪來的?」勞悟一邊端詳一邊問:「能開什麼東西?」
兩人沉默了幾秒,心裡都在想鑰匙的可能用途、照片的祕密還有勞悟一路上所說的話。
「妳提到有一組密碼。」
「對,可是已經不見了。」莎菈說。
「正本不見了,但是我有影印本。」拉斐爾邊說邊從口袋抽出一張紙,上頭有密碼,是瑪古利斯著手解碼前印的。
勞悟仔細研究這組密碼。
18,15-34,H,2,23,V,11
Dio bisogno e IO fare lo. Suo augurio Y mio comando
GCT(15)-9,30-31,15,16,2,21,6-14,11,16,16,2,20
「你朋友解開密碼了嗎?」上尉問。
「來不及解開,因為那幫人先一步殺死他了。」莎菈回答。
「那我們就得花幾個小時分析了。」
「等一下,」拉斐爾似乎想到什麼事情:「他死前曾朝我這邊看。」
「誰?」莎菈問。
「瑪古利斯。他死前曾朝我這邊看,要我算算字母。」
勞悟沒再聽下去,逕自將紙擱在大腿上,自動鉛筆快速移動,手指也不停數算。過沒多久,上尉挺直身子。
「解開了。」
* * * * * * * * * * * * * * * *
期盼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他等這一刻等了好多年,認真算的話,其實從牽著父親的手站在格但斯克舊街道時,等待便開始了。
他的父親為冶金專家,同時還是活躍的團結工聯成員,一心追求波蘭自由化。他厭惡當時政府獨裁專制,卻沒注意到自己對小男孩的母親同樣霸道。然而,儘管身心受盡折磨,這位女性仍舊樂觀開朗,她營造父母在莫特拉瓦河畔愉快開心的假象,想讓小男孩記住美好的一面。但事實卻不然,有暴力傾向的父親長期棄妻兒不顧,整天和專斷政府進行不對等的戰爭。他對於此一目標十分執著,至少還算有可取之處,可惜的是,得來不易的自由在他家裡也生不了根,比方說,讓小男孩的母親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其實很簡單,但他卻沒這麼做。開朗的母親想營造快樂的河畔景象,但這和現實不符,如此景象從未存在過,有的只是恐懼,每天害怕聽到魔鬼轉動鑰匙的開門聲,那代表長期離家的父親再度歸來,象徵和平又一次終結。父親又帶回裝滿美金的黑色皮箱,說:「這是美國人給的。」接著便狼吞虎嚥吃光妻子準備的晚餐,這位女性心地純良,從沒想過在食物中加點老鼠藥,要是他就會這麼做。父親繼續說:「這是梵蒂岡給的,這次我們一定會成功。」眼看夢想即將實現,他笑得像小孩一樣,還說這筆錢的來源是祕密,如果外人知道了,金援者會否認到底。此外,這是黑錢,從吸毒、人口販賣這些齷齪事上賺來的,現在這髒錢卻用來資助高尚的理想,實現平等、公理、自由。外國人、間諜和敵人都不清楚這筆錢從何而來,他的父親說,金援者是美國和梵蒂岡,對於資金怎麼輾轉到手卻沒詳加說明。永遠不會有人曉得那些錢經過多少人的手、讓多少空殼公司和貪腐銀行處理過。
年輕人記得那天回家的情形,一切彷如昨日。她睜著呆滯的雙眼,鮮血從脖子流到地上漫成一攤,純白襯衫全變了色。醉醺醺的父親靠著牆坐在地上,嘴裡不停咒罵,想解釋她是多麼輕蔑他,且在他回神之前,傷害已經造成。「孩子,現在只剩我們兩人了,」父親既醉又悲地說:「過來,讓爸爸抱抱。」那不是請求,而是命令。聽話的小男孩走向前去,身體抱著父親,心裡卻想著母親。刀身完全插進他的身體裡,小男孩緊閉雙眼,仍舊帶著豐沛的愛抱住父親。最後,他死了,兒子走向一旁,看了母親屍體最後一眼。
「現在只剩我一個人了。」
他期待許多年,這一刻終於到來,現在的他正準備和大主人會面。主人搭乘的飛機已於紐約拉瓜地機場降落,這位僕人站在飛機預定著陸的隱蔽跑道旁恭候大駕。他開了輛與主人尊貴身分相符的名車,臉上掛著笑容掩飾內心排山倒海的緊張感。他視主人如父親,儘管素未謀面,主人仍給了他身為父親所會給予兒子的一切,包括遮風避雨的棲身之地、教育、工作以及鼓勵。兩人距離遙遠,卻反而讓他對主人產生莫大的敬愛之情。
飛機在跑道上停妥,引擎止歇後機門開啟,第一個出來的是身穿亞曼尼西裝的男子,和他在格但斯克見過面。這名助理負責攙扶走在後頭的老人,老人一手拄著金獅頭柺杖,一手抓著身邊男子的手臂,最後,這三個人總算見到彼此了。聖父、聖子與聖靈,主人、僕人與助理。
長久的等待是值得的,波蘭僕人跪在主人跟前,恭敬地低下頭。
「先生,終於有機會與您見面,我備感榮幸。」他雙眼緊閉地說。
老人伸出顫抖的手摸摸僕人的頭。
「孩子,起來吧。」
僕人立刻照做,但完全不敢直視主人。老人坐進車內後,他便替他關車門。
「你把我伺候得很好,非常有效率,也很熱忱。」
「我對您絕對忠誠,請放心。」僕人語氣中帶著由衷的敬畏。
「這我知道。」
「目標在哪裡?」助理問。
「現在正在參觀博物館。」
「他真喜歡陶冶性情。」穿得一身黑的男人笑道。
「先生,您想去哪?」波蘭人怯怯地問。
「開車帶我們四處繞繞,先當一下觀光客吧。」老人回答。
他的話如同命令。
坐在後座的兩人交頭接耳,講了些僕人不該知道的話。
交談過後,主人打電話,花了幾秒鐘等對方回應。
「我們什麼時候碰面?」他跳過寒暄,直截了當地問,聽完對方回答後,簡明扼要地說:「巴恩斯先生,我的命令希望你都照做了。」
* * * * * * * * * * * * * * * *
富豪汽車以九十哩時速在里斯本附近的公路上急駛,要在這條繁忙的高速公路飆出如此速度只有這個時候才有可能。裡頭的三個人已經好一陣子沒開口了。
莎菈望著窗外出神,車子經過農田、體育場、商業區,還超越其他大小車輛,但她並沒有仔細瀏覽這些景物。此時此刻,人們正在研擬什麼計畫?好讓某些人控制其他人,強國主導弱國。在她眼裡,政治分成兩種,一種專供大眾消費,只是表象,藏在檯面下的另一種政治才真正具決定性。
「親愛的,妳還好嗎?」勞悟轉頭問。
「很好。」莎菈還在專心想事情,所以嘴巴回答的聲音聽在耳裡是如此遙遠:「我剛剛在想,除了教宗,P2還謀殺許多人,那些人有誰?」她看著拉斐爾,語氣特別強調最後一個字。拉斐爾直盯前方道路,但仍感受到她的視線。
「這方面的情報很難獲得,但遭到刺殺的瑞典總理奧洛夫‧帕爾梅就是受害者之一。」
「嗯,顯然他們能輕易踢掉任何擋在路中間的石頭。」
「的確如此。」
「他們為什麼要殺他?」
「因為他從中作梗,妨礙某些重要行動,或許跟軍售有關。」
「那中情局跟這些謀殺案有何關聯?」
「關係可大了,那些人之所以會被處理掉都是為了方便中情局做事。」
「謀殺教宗也能讓他們得利?」
「那是特例,美國司法部當時和若望‧保祿一世合作,身為P2盟友,中情局不得不出手。教宗一死,他們的調查行動便受到極大的影響。」
「真是錯綜複雜。」
勞悟轉向拉斐爾。
「從這裡開始要往哪走?」
「往南,穿越四月二十五日大橋後直直開到馬德里。」
「聽起來很簡單。」勞悟說。
「我想確認他們是否還跟在後面。」
莎菈馬上激動起來:「這我們怎麼會知道?」
「開進窄路或死巷,只要有車跟在後頭,一定是跟蹤者。」
「到時候我們也無處可逃。」莎菈反對道。
「是沒錯,但至少能確認有沒有人在跟蹤。走私毒品的人常常用這招,避免交貨時被逮。如果沒被跟蹤便會繼續往目的地前進,不過每開一段路就會確認一次,只要遭到監控,行動馬上取消。當場,他們會和警察展開槍戰,然後就地被逮,而毒販頭子則毫髮未傷地待在豪宅裡,從容計畫下一次交易。」
莎菈茫然聽著。
「我完全不想碰到槍戰,昨天那次就夠了。」
「我只是說這種情況通常會發生槍戰,不代表我們一定會碰上,路不只這一條。」
「還有其他條路?」
拉斐爾突然把車停在路中央,惹得後頭傳來抗議的喇叭聲。
「你瘋了嗎?」莎菈大叫。
「冷靜點,莎菈,」父親開口安撫:「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拉斐爾轉頭往後看,正巧和憤怒的莎菈四目交接。
「能不能請妳坐到一邊去?」他如此要求。
莎菈瞪著他。拉斐爾看見三輛車停在公路旁,距離大約六十公尺。差點衝撞上來的車還停在後頭,不斷按喇叭。
「有三輛。」拉斐爾說。
「搞不好那裡發生意外。」莎菈緊張地說。
拉斐爾轉回身子,繫上安全帶。
「請確認綁緊安全帶。」
莎菈馬上照做,內心越來越害怕。「天啊,我一點都不喜歡這種情形。」
「我也是,莎菈,但是聽好了,」拉斐爾從後照鏡看她:「不要等一下才抱怨說我沒提醒妳,我們接下來要在市區飆車,但是別擔心,坐穩就好。」
富豪汽車的輪胎壓在柏油路上,引擎發出充滿威脅的低鳴,車子猛然加速,強大拋物力將莎菈往座位擠,回頭看,三輛車就在後頭,此時富豪汽車離開高速公路,闖過紅燈,以七、八十哩的時速穿梭在車陣中。
莎菈發現拉斐爾駕駛技巧非常高明,坐在一旁的父親則十分冷靜,看來自己對他根本認識不深,這兩個人與她如此接近,卻又那麼陌生。跟蹤者緊追在後,上尉不斷指示路線,四輛車在里斯本市中心的共和大道競速狂飆。
經過薩爾達尼亞公爵廣場後,四台車沿著另一條大道往龐巴爾侯爵廣場去,闖過無數紅燈、引來許多咒罵及喇叭聲,但拉斐爾毫不在乎,只顧全速前進。
「坐穩了。」他提醒道。
話剛說完拉斐爾便突然煞車,讓跟在後頭的車子差點撞成一團。其中兩台想從兩側包抄,但還沒準備好就讓富豪汽車從左邊閃出去,衝進隔壁車陣裡。
環顧四周,莎菈緊張到快崩潰了,他們在單行道上逆向行駛,前方來車狂按喇叭還急著閃到一邊去。
「我快吐出來了。」莎菈哀聲說道。
一陣瘋狂追逐後,他們開進商業廣場,此時還有輛車尾隨在後,更在通過廣場東邊時不斷逼近。沒有其他選擇了,拉斐爾油門踩到底,以自殺般的速度開上七月二十四日大道,這條路雖然又長又寬,但太過曲折蜿蜒,拉斐爾只能不停加速、減速。
後頭的跟蹤者技術一樣高明,但和富豪汽車的距離卻越來越大。「好像有點不對勁,他們落後我們太多了。」
「搞不好他們的車子出問題了。」
「希望是這樣。」
車子開進印度大道後,有束強光從上而下籠罩富豪汽車,光源來自一架直升機。
「現在是什麼情形?」莎菈強忍高漲的恐懼感問道:「我們該怎麼辦?」
「逃不了了。」拉斐爾衡量情況後表示。
「一切都完了?」
拉斐爾嚴肅地看著她。
「一切都完了。」
「他們會殺死我們。」莎菈嚇得臉色發白。
「沒那麼快,要是想殺我們早就動手了。」拉斐爾轉向勞悟。
「上尉,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束手就擒。」
富豪汽車還在大馬路上奔馳,現正經過葡萄牙總統官邸貝倫宮。車子又走了一會兒,拉斐爾看見傑洛尼莫斯修道院附近車燈閃爍,有一整排車擋在那裡。無處可逃了,距離那排路障越來越近。
六百公尺。
「上尉,讓您失望了,對不起。」
「沒必要道歉。」
五百公尺。
四百。
「停車。」有人從直升機裡說話:「立即停車。」
「上尉,您認為該停嗎?」拉斐爾問。
民用車、警車、廂型車,各種車排成一列擋在路中間,許多人拿著槍躲在敞開的車門後頭。
兩百公尺。
不等對方再次警告,拉斐爾便主動煞車。
「上尉,一切都結束了。」
「所以他們是在教宗出手前先下手為強。」莎菈下了這樣的結論。
「正是如此。而且教宗還打算將所有祕辛公諸於世,這會讓那些人全吃上牢飯。他手中掌握的內幕多不勝數,比方說,靠著P2居中牽線,阿根廷於福克蘭群島戰爭中所用的飛魚反艦飛彈其實是受惠於梵蒂岡銀行。妳能想像這後頭牽連多廣嗎?」
「天啊。」
「他們甚至還和具有黑手黨背景的米切雷‧辛多納合作,由他負責和黑手黨聯絡,共同賺進大把鈔票。」
「他也是成員之一嗎?」
「沒錯。不過,雖然有許多人死於辛多納之手,其中還不乏達官顯要,但教宗之死與他無關。可是即使如此...
推薦序
推薦序:親臨梵蒂岡,目睹神聖的陰謀
文史工作者 謝哲青
羅馬初秋的午後,空氣中蒸騰著暑意,從台伯河的南岸眺望,拙樸厚重的聖天使堡像是個守衛看顧著天國之門,由聖天使橋越過台伯河後向右轉,協和大道(Via della Conciliazione)盡頭的巨大圓頂在陽光中閃耀著的金色光芒,嚴謹的建築式樣,清晰地表達出這裡可是非比尋常的所在,現場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參雜著華麗尊貴的氛圍。一六六七年完工的圓型廣場是大道的終點,兩道巨大弧形翼廊像是慈母張開雙臂,擁抱遲歸的兒女。弧廊頂端,一百四十位聖人石像注視著熙來攘往的紅塵男女,正信者在這裡重新與教會契合,同時也為異端開啟了通往真理之道。廣場透過戲劇性的空間規劃向旅人宣告,你正跨越分界,一方是屬世的人間民主共和政體,另一邊是屬靈而古老悠久的封建殘跡。
走進大教堂,莊嚴筆直的中廊更讓外人驚歎不已,在米開朗基羅與貝里尼的規劃下充滿力量,文藝復興的純粹形式與表情十足的巴洛克張力在此巧妙融合,既精緻又充滿動感。在中心祭壇的上方內圍,有一行距離我們二十公尺高的拉丁銘文,節選自馬太福音第十六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我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當教宗在主祭壇上主持彌撒時,新約與現世,天堂與凡世,就聯結起來了。至此,難道我們不會動容,感歎是怎樣的力量與意志構築出眼前的一切嗎?
前方巨大的廣場空間與宏偉的大教堂,再加上後方的宮殿與小花園,組成了地球上最小的國家,它是有史以來最古老的組織,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團體。它的領導人,是地球上最具權威的決策者,全球將近十二億的人口將他視為不可動搖的權威領導,他的話語被奉為至高無上的圭臬,他的意見在風雲詭譎的政治議堂與極私密的個人心靈同樣發揮作用。他的職權,象徵了上天對世俗的唯一代言;他的職責,是對廣大信眾的精神進行良知的統治。他,簡居在零點四四平方公里的深宮禁苑內,同時又是全世界最熟悉的臉孔,從兩千年前彼得從耶穌的手接下天國之鑰開始,他所奠基的天主教會歷經了古典時代的迫害與尊崇,走過紊亂混沌的中世紀,見證了世局分裂與動盪,無數王國的興起與殞落,人類文明九死一生的浩劫,乃至於在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與美蘇對峙的冷戰時期,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直到巴伐利亞的Joseph Alois Ratzinger於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正式登基,繼任為第兩百六十二任教宗,這部歷史仍在進行之中。
在時光的洪流之中,教宗不僅僅是個沉默的旁觀者,當世局走到起承轉合的關鍵時刻,他更是積極參與的意見領袖與推手。當羅馬帝國土崩瓦解之際,教會抵禦了日耳曼蠻族對西方的殘戮破壞,在文明的海角天涯苟延了微弱的知識之光,其後更填補了政治真空,成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團體,它發動清洗異端的戰爭,罷黜叛經離道的君王,甚至為帝國主義背書,制定殖民強權的勢力範圍與遊戲規則。所以一些歷史學家更大膽斷言,教會發展紀錄就是西方文明興衰史。
有光明就有黑暗,除了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之外,隱身於黑暗角落的祕密組織,不分遠古、中世、近代到今天,亦不斷地與教廷爭鬥對抗。
從國家民族的分離拮抗──都鐸王朝君王亨利八世率領英格蘭出走,到祕密結社的顛覆活動,無論是事實還是道聽塗說,都為歷史增添許多傳奇故事。如今,這些與教廷對抗的黑暗同盟──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ism)、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光明會(The Illuminati)、骷髏會(Skull and Bones) …… 藉由網際網路、通俗文化與視覺媒體的召喚,再度返回人間,重生於二十一世紀的現代舞台。
或許你知道,傳說文藝復興前期的佛羅倫斯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是聖殿騎士團第三教團聖信實團(Fede Santa)的首腦之一,史詩大作《神曲》便是古代祕儀的教義說明:地獄、煉獄、天國的三界旅程,就是由死而生的入會祕儀。而莫札特則是位復興共濟會的狂熱分子,阿瑪迪斯晚期鉅作《魔笛》,處處充滿了共濟會的暗示與象徵;簽署《獨立宣言》的五十六名美國開國元勳中就有五十三位是共濟會會員: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這些會員均發揮了絕大的影響力。歷史學家娜絲塔.韋伯斯特(Nesta H. Webster)於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世界革命》便把矛頭指向光明會,她的研究認定,自法國大革命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均源於光明會的陰謀。而納粹統治的德意志第三帝國,更是現代神祕主義集大成者,希特勒信奉的亞利安主義,脫胎於十九世紀末諸多祕密組織:新聖殿騎士團、日耳曼騎士團、神智協會(Theosophical Society)、圖利協會(Thule-Gesellschaft)、維利協會(Vril),企圖透過不可知的力量掌握世界,進入新秩序。
時至今日,教廷似乎已純化為奉獻主上的宗教機構,而祕密結社也只是娛樂文化中的傳奇題材,茶餘飯後助談的馬路八卦,我們的世界,真的攤在陽光下無所隱藏了嗎?
《教宗之死》為讀者重啟一椿塵封的歷史懸案,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黎明之際,「有人」發現端坐在床上的若望.保祿一世已經去世了。此時,距他擔任教宗僅僅三十三天的時間。梵蒂岡發布聲明說他們六十五歲的教宗「可能」因前一天晚上心臟病突發而逝世。
然而,為了證實這個「不確定的診斷」所該做的行政驗屍解剖卻沒有進行。這個不確定的診斷,以及隨後官方發表的前後矛盾的聲明,讓這椿離奇的死亡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非議,教宗可能死於謀殺的說法不脛而走。當時的疑點探討:是誰發現了教宗的屍體,何時發現教宗已經去世的,以及教宗去世時手上拿的文件的內容。
某些傳聞聲稱,來訪的都主教Metropolitan Nikodim of Leningrad的去世是因為喝了原本為教宗準備的含有毒藥的茶。實際上,都主教Nikodim去世與教宗死亡時序相隔過久,而且,沒有證據證明牧首是被毒害致死的。可是,這一次行政解剖仍然未能進行,因為都主教甫逝世就被進行了防腐處理。另有傳聞指出,教廷正籌劃梵蒂岡徹底的人事變動,將一些梵蒂岡高級官員解職,因為他們有貪污行為。教宗遺體立即做了防腐處理被懷疑是為了迴避驗屍程序。梵蒂岡堅持聲稱,根據梵蒂岡法律,對教宗遺體的解剖是被禁止的,然而,有人從Agostino Chigi的日記中找到證據,一八三○年,梵蒂岡對教宗庇護八世的遺體進行了解剖。更有媒體掌握獨家,報導黑手黨的暗中活動以及隨後教廷將對梵蒂岡銀行及其附屬公司進行財務調查,因而發生謀殺事件。今天,原因與動機仍籠罩在五里迷霧之中。
小說家或許天馬行空,卻也提供了事實另一種想像馳騁的象限。透過路易斯.馬吉爾.羅沙的筆端,由陰謀與權術所形塑的惡魔,仍虎視眈眈窺伺著我們自以為安全的虛假日常。
【本文作者】
謝哲青,生於北方首善之都,成長後山,求學於南方港市。對自由與世界有著無限嚮往與追求,周遊八十餘國。千禧年後負笈歐洲,於倫敦亞洲與非洲學院取得藝術史及考古學位。現為傳媒人、旅行作家、特約領隊、歷史文化工作者。
推薦序:親臨梵蒂岡,目睹神聖的陰謀
文史工作者 謝哲青
羅馬初秋的午後,空氣中蒸騰著暑意,從台伯河的南岸眺望,拙樸厚重的聖天使堡像是個守衛看顧著天國之門,由聖天使橋越過台伯河後向右轉,協和大道(Via della Conciliazione)盡頭的巨大圓頂在陽光中閃耀著的金色光芒,嚴謹的建築式樣,清晰地表達出這裡可是非比尋常的所在,現場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參雜著華麗尊貴的氛圍。一六六七年完工的圓型廣場是大道的終點,兩道巨大弧形翼廊像是慈母張開雙臂,擁抱遲歸的兒女。弧廊頂端,一百四十位聖人石像注視著熙來攘往的紅塵...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7收藏
7收藏

 3二手徵求有驚喜
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