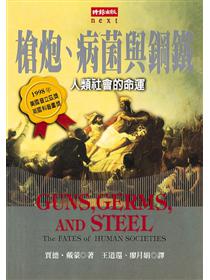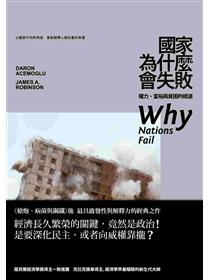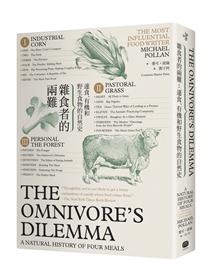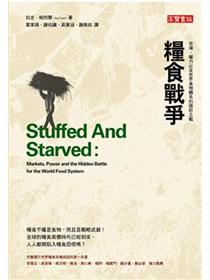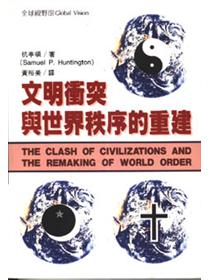二○○三年三月,美國以絕對優勢的戰力橫掃伊拉克,八年後戰火卻依然繼續燃燒;一九八○年代,中國經濟飛躍成長,至今引發無數或喜或憂的「中國崛起」論戰;二○一一年一月,一樁突尼西亞小販自焚事件,透過臉書和推特的流傳,演變為「茉莉花革命」,還一路從北非延燒到中東。
這一個又一個事件告訴我們,在全球競爭的世界舞台上,經濟力、網路力成為與軍事力等量齊觀的權力來源,權力已經從硬實力演化到軟實力到巧實力。未來決勝的關鍵比的可能不是誰的拳頭大,而是誰說的故事最動聽。
以提出「軟實力」聞名於世的約瑟夫.奈伊,用了一個絕妙的比喻描述全球主導權的競賽:你必須同時下軍事、經濟、網路三盤棋,對手可能是國家聯盟、單一國,或「非國家行為者」。時空對手皆不同,當然需要全新的策略,關鍵心態是「隨境應變」,關鍵詞則是「聰巧」:Smart。
關鍵武器呢?正是巧實力,Smart Power:一種結合軍事力、經濟力、網路力,依情境的不同,聰巧的運用硬實力,和軟實力的能力。除了豐富的實務經驗、紮實的知識素養,最難能可貴的是奈伊舉重若輕的能力。清晰的思考理路,搭配鮮活的實例,從容的引領閱讀者由淺入深,盡得此一權力議題之真髓。難怪美國前國務卿歐布萊特如此讚譽:「想瞭解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事務,《權力大未來》是最好的指南。」
別以為國際權力的議題太偉大,與你無關;這是個牽一髮動全球的時代,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作者簡介:
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
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目前為該校傑出教授。
1977~1979年間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主掌安全援助、科學與技術業務,並主持國家安全會議核子武器非擴散小組。1993~1994年,出任國家情報會議主席,1994~1995年任國防部助理部長,負責國際安全事務。於1989~1993年間擔任美國駐聯合國秘書長裁武諮詢委員會代表。
著作有《柔性權力》(Soft Power)、《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領導力》(The power to lead)等書。
譯者簡介:
李靜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外交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職出版社與外交部。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何謂全球事務之權力?
就一個運用得如此廣泛的概念而言,「權力」的難以、無以衡量,著實令人意外。但是,概念並不會因為有這樣的問題就變得毫無意義。很少人會否定愛的重要性,雖然我們沒辦法說:「我愛你比愛其他人多三點六倍。」就像愛一樣,儘管我們無法精確衡量,但是日常生活中卻時時體驗到權力的存在,而且權力也真正發揮了具體的效果。有時候,分析家會因為某個概念太過模糊與不精確而傾向棄之不用,但是,「權力」這個概念已證明難以取代。
偉大的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經將「權力」在社會科學中的角色與「能量」在物理學上的角色相比較,但是這樣的比較反而產生誤導。物理學家可以相當精確地測量無生命物體之間的能量與力的關係,但是權力指涉的人類關係轉瞬即逝,隨時會因情況改變而產生不同的樣態。也有人說,權力之於政治,等同於金錢之於經濟;但這樣的譬喻還是會產生誤導。金錢是流動或可替代的資源,可用以購買各式各樣的貨品。而在某種關係或某種情境中產生權力的資源卻未必能在其他關係或情境中產生權力。你在房地產市場、蔬果市場或拍賣網站都可以使用金錢;但是,做為最重要國際權力資源之一的軍事力量,或許可以在裝甲戰場上產生你所希望的結果,但在網路上則不然。
多年來,許多分析家都嘗試提供方程式,量化國際事務上的權力。例如,中央情報局高階官員雷.克萊恩(Ray Clime),他的工作是在冷戰時期負責為美國政治領袖提供美蘇權力平衡的分析,他的觀點足以影響涉及高度風險與數以億計經費的政策決定。一九七七年,他發表了用以計算權力的公式:
認知的權力=
(人口+領土+經濟+軍事)×(策略+意志)
把數字帶進公式之後,他得出結論:蘇聯的國力是美國的兩倍。當然,我們今天已經知道,這道公式對結果的預測並不準確。僅僅十幾年之後,蘇聯解體,甚至有學者宣稱美國已成為單極世界的唯一超級強權。
更晚近所創造的權力指標包括一個國家的資源(科技、企業、人、資本、天然資源)、國家的表現(外在限制、基礎建設、理念)以及這些要素對軍事能力與戰鬥力的影響。這道公式能讓我們瞭解相對的軍事力量,但無法讓我們掌握權力的所有相關類型。儘管在國際事務上,有效的軍力仍然是關鍵性權力資源之一,但如同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的,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像十九世紀的歐洲那般不受拘束了,當時的史學家可以用「贏得戰爭優勢」的能力做為衡量「強權」的標準,但今天這個標準已不再適用。
例如,面對金融或氣候變遷,軍力和戰鬥力並不能讓我們掌握事態的結果,也不能讓我們瞭解非國家行為者的權力。從軍事的角度看,比起美國這個巨人,蓋達組織形同侏儒。但是恐怖份子的衝擊並非來自其武力的大小,而是來自他們的行為與論述的戲劇性效果,以及因之產生的過度反應。就此角度觀之,恐怖主義就像柔道,較弱的選手利用較強的對手自身的力量,借力使力加以對抗。這種動能是軍事力的傳統指標所無法涵蓋的。
在某些談判的情勢之中,就像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的,談判一方可能崩潰的脆弱與威脅是談判力的來源之一。欠債一千美元的破產人權力是小的,但如果欠的是十億,反而擁有相當大的談判力—二○○八金融危機中那些被認為「大得不容倒閉」的機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北韓的金正日很可能是今時今日唯一能讓北京看起來很無力的領導人……外交人士說,金正日厚顏無恥地玩弄中國的恐懼,他揚言,如果中國不挹注北韓搖搖欲墜的經濟,就等著面對大量湧過邊界的難民與隨之而來的動盪不安。
發展單一權力指標的努力註定失敗,因為權力建立在隨不同情境而變化的人類關係之上。金錢可以在各種不同的市場中用來衡量購買力,卻沒有一套價值標準可以統整所有的關係與情境,產生普遍接受的全面性綜合權力。
權力的定義
一如許多基本概念,權力是一個迄今仍爭辯不休的概念。沒有任何一個定義可以為所有使用這個名詞的人所接受,而人們對這個名詞定義的選擇,恰可反映出他們各自的利益與價值。有人認為,權力是造成或抗拒改變發生的能力。另外有些人認為,權力是獲得我們所想要的事物的能力;這個廣泛的定義包括制服大自然與制服其他人的力量。基於對行動與政策的興趣,我認為尋找定義最合理的出發點應該是字典。據字典定義,權力是去做事情的能力,以及在社會環境中影響其他人以獲致我們所希望之結果的能力。有些人稱之為「影響力」,同時又認為權力與影響力並不相同,這很讓人疑惑,因為字典裡說這兩個名詞是可以相互替換的。
獲致我們所希望之結果的能力受到許多因素影響。我們生活在既存的社會力網絡中,有些是具體可見的社會力,有些則是間接、有時稱之為「結構性」的社會力。我們傾向於依據自己的利益,特別辨明並聚焦在其中的某些限制與力量之上。例如,政治學家彼德.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他探討文明的著作中指出,文明的權力(power of civilizations)與文明之內的權力(power in civilizations)是不同的。文明之內的行為者掌握了硬實力與軟實力。社會力在行為層次之下運作,型塑了基礎社會結構、知識體系與一般環境。儘管這種結構性的社會力非常重要,但是為了政策的需要,我們仍然必須瞭解行為者或能動者(agent)在特定情勢下能做什麼。文明和社會並非恆久不變,歷來有效能的領導人物都可以努力型塑更大的社會力,並獲致程度不一的成功。誠如德國知名理論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言,我們想要瞭解行為者在社會關係中遂行自身意志的可能性。
即使將主要的焦點集中在特定的行為者或能動者身上,如果沒有特別指出某一行為者「做什麼」的權力,也不能指稱他「擁有權力」。我們必須明確指出涉入該權力關係的是誰(亦即權力的範圍),涉及的議題是什麼(即權力的領域)。例如,教宗對天主教徒擁有權力,但對其他人(如新教徒)則無。而即使在天主教徒之間,教宗或許希望能對教徒的一切道德決定擁有權力,但是有些教徒可能會在某些議題(如節育或不在天主教堂舉行婚禮)上反抗他的權力。因此,要說教宗擁有權力,我們就必須先清楚辨明教宗與每一個個人權力關係的情境(亦即範圍與領域)。
精神病患或許有力量可以隨機殺死或毀滅陌生人,卻沒有說服那些被害人的力量。有些影響其他人並獲致所欲結果的行動可以純粹是破壞性的,完全不顧受害者怎麼想。例如,波布(Pol Pot)殺害幾百萬名柬埔寨人民。有人認為,這種力量的運用並非權力,因為不涉及兩方的關係,但這須視情境與動機而定。如果行為者的動機純粹是殘暴或恐怖,那麼這種力量的運用就符合權力的定義:影響其他人,獲致行為者想獲致的結果。然而,大部分的權力關係都與受害者的想法息息相關。想懲罰異議份子的獨裁者或許會誤以為自己是在運用權力,卻忽視異議份子其實是希望透過殉道行動來推動目標。但如果獨裁者只是想要毀滅異議份子,那麼異議份子的意圖對他的權力而言就無關緊要。
行動常會造成威力強大又超乎原本意圖的結果,但是從政策的觀點看,我們關注的是產生所希望之結果的能力。如果有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士兵在阿富汗以流彈殺死一名孩童,那麼他的確擁有摧毀生命的力量,卻未達成他所希望達成的結果。消滅叛軍並殺害眾多平民的空襲行動展現廣泛的摧毀力量,卻可能對戡亂政策造成不良後果。經濟強國的行動或許會產生預期之外的效果,為小國帶來意外的傷害(或財富)。如果這些效應並不是原先預期的,那麼這只是造成傷害(或帶來財富)的力量,而非達成其希望獲致之結果的權力。加拿大人常抱怨,與美國為鄰彷彿和大象同眠。從加拿大的觀點看來,意圖一點都不重要,只要巨獸翻身,他們就會倒楣。但從政策導向的角度而言,要獲致所希望的結果,意圖就非常重要。政策導向的權力概念必須以明確的情境為基礎,讓我們知道誰得了什麼,如何、何處與何時得到。
務實的政治人物和平民大眾常覺得這些行為與動機的問題太過複雜,難以預測。行為定義以行動的後果來判斷權力,所以只能在行動之後(經濟學家所謂的「事後」),而非在行動之前(「事前」)進行。但是決策者都希望能預測未來,以做為行動的指引。因此,他們經常只用可以產生結果的資源來界定權力。將權力界定為資源的這第二種定義認為,一國如果擁有相對較多的人口、領土、自然資源、經濟實力、軍力和社會穩定性,則擁有較大的權力。第二種定義的優點是讓權力顯得具體,可衡量且可預測—可以成為行動的指南。在這層意義上,權力就像在牌局中拿到一手好牌。但是這個定義有很大的問題:當我們將權力視同(或許)可以產生結果的資源時,常會碰上無解的難題,也就是那些擁有最佳權力的國家,卻未必永遠能得到所期待的結果。
我們並非否定權力資源的重要性。權力必須透過資源傳達,無論是有形的或無形的。如果你在撲克牌局中拿到一手好牌,其他人很可能會乾脆蓋牌,而非挑戰你。但是可以在某個牌局中獲勝的權力資源,卻不見得對所有的牌局都有利。如果玩的是橋牌,拿到一手好牌未必會贏;即使玩的是撲克,如果你把一手好牌打爛,或因為對手虛張聲勢或耍詐而上當,那還是照輸不誤。權力的轉化—從資源轉化成行為的結果—是最關鍵的中介變項(intervening variable),擁有權力的資源,並不保證你可以永遠獲致你想要的結果。例如,若以資源為標準,美國遠比越南有權力,但還是輸掉了戰爭。把資源轉化成權力以取得想要的結果,需要設計良好的戰略與技巧圓熟的領導能力—也就是我所謂的「巧實力」。然而,戰略經常設計不良,而領導人也常做錯誤判斷。
儘管如此,以資源來界定權力是決策者認為很有用的一條捷徑。一般而言,擁有較多權力資源的國家比較可能影響較弱的國家,而比起弱國,強國也較少仰賴優異的策略。較小國有時或許可以獲致希望的結果,因為他們挑選規模較小的戰鬥,或選擇性地聚焦在少數幾個議題上。一般而言,若是正面衝突,誰都沒預期到芬蘭能戰勝俄國。
在任何牌局裡,第一步都是先搞清楚誰握有王牌,以及那個玩家手上有多少籌碼。然而同樣重要的是,決策者要有情境因應智能以瞭解自己玩的是哪一種牌局。在特定情境中有哪些資源可以做為權力行為的最有利基礎?在工業時代以前,石油算不上什麼重要的權力資源;核子時代之前,鈾也沒有特別的重要性。依據傳統現實主義者對國際關係的觀點,戰爭是國際政治牌的終極牌局。所有牌全攤在桌上時,相對權力的評估有些可以獲得證實,有些則未符實情。但隨著時代發展,科技不斷進化,戰力的來源也常有變化。甚至,隨著二十一世紀議題的增多,戰爭也不再是終極的定奪。
因此,許多分析家認為「國力要素」的分析途徑易產生誤導,顯然不如在二十世紀後半開始主導社會科學研究的行為或關係分析途徑。嚴格來說,這種懷疑論是正確的。權力資源只是隱藏在權力關係下的有形與無形原料或載具,某組特定的資源能否產生所希望的結果,取決於情境之中的行為。載具並非權力關係,瞭解某部車子的馬力或里程數,並無法讓我們知道這部車能否到達想去的目的地。
實務上,討論全球事務中的權力時,這兩種定義其實都包含其中。我們每天使用的大部分名詞,譬如「軍事力」和「經濟力」都是結合資源與行為的綜合體。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釐清我們討論的是以行為為基礎或是以資源為基礎的權力定義,同時必須意識到這兩種定義之間存在的不完美關係。例如,有人談及中國或印度權力的崛起,他們所指的通常是這兩國眾多的人口,以及增長的經濟或軍事資源。但是這些資源隱含的能力可否真正轉化為所希望的結果,則取決於情境,以及該國是否有足夠的技巧將資源轉化為策略,以獲致希望的結果。權力的這兩種定義可以濃縮為圖一.一。這張圖也從關係的角度對權力提出更縝密的定義:權力是改變其他人行為以獲致所希望之結果的能力。
正因如此,才有人會說:「權力並不必然產生影響力。」(儘管基於上文已闡明的理由,會將權力與影響力混為一談也頗令人不解。)
最後,因為關注的是結果而非資源,所以我們必須更注意情境與策略。權力轉化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變數,卻未得到足夠關注。方法與目的必須透過策略才能連結在一起,而能在不同情境中將硬實力與軟實力成功結合的策略,就是巧實力的重要關鍵。
關係權力的三個面向
除了區分權力的資源與關係定義,區分關係權力的三個不同面向也頗有助益。這三個面向包括:主導改變(commanding change)、控制議程(controlling agendas)以及建立偏好(establishing preferences)。這些不同的面向常被混為一談。例如,最近的一本外交政策教科書就把權力定義為:「讓某些人或某些團體去做其不願做的事」。這種狹隘的看法易導致誤謬。
要求其他人違背原本的偏好去改變自身的行為,是關係權力的一個重要部分,但並非全部。另一部分是影響其他人偏好的能力,讓他們去做你想做的,而你不必要求他們改變。美國前總統(也是前將軍)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曾指出,這就是讓其他人「不只因為你告訴他們要這樣做,而是他們本能地要為你這樣做」。這種同化的權力與指揮的權力恰恰相反,卻也彼此互補。認為權力只涉及命令其他人改變行為的能力是錯誤的看法,你可以用型塑其他人偏好的方式影響他們的行為,產生你想要的結果,而不只是在「沒有轉圜餘地時」仰賴軟硬兼施的方法去改變他們的行為。有時候,你不需要施加任何壓力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結果。執著於太過狹隘的權力定義而忽略此一層面,就可能導致拙劣的外交政策。
權力的第一個面向,或面貌,是耶魯政治學家羅伯.達爾(Robert Dahl)一九五○年代研究美國城市紐哈芬(New Heaven)時界定的,儘管只涵蓋部分的權力行為,但迄至今日仍廣受運用。這個權力的面向聚焦在讓其他人違反自身原本的偏好或策略去採取行動的能力。要衡量或判斷權力,你必須知道另一個人或國家原本的偏好有多強,以及因為你的努力而產生的改變有多大。在擁有某種程度選擇的情況下,強制脅迫也可以是很明顯的。比方說有人拿槍指著你說:「要錢還是要命?」你是有某些選擇沒錯,但選擇的彈性不大,而且和你原本的偏好並不一致(除非你原本的偏好包括自殺或殉道)。捷克屈服於德國與蘇聯,讓兩國軍隊分別在一九三八年和六八年開進布拉格,並不是因為捷克本就希望如此。
然而,經濟手段的衡量卻更為複雜。負面制裁(剝奪經濟利益)顯然會被認為是脅迫。而以金錢收買或經濟利誘讓你去做原本不想做的事,或許對當事人來說更具誘惑力,但是任何金錢利誘在以明示或暗示方式威脅要取消時,卻可以輕易轉化成負面制裁。年終獎金是一種獎勵,取消年終獎金感覺上卻是一種懲罰。尤有甚之,在不對等的談判關係裡,比方說在身價百萬的地主和挨餓受凍的貧農之間,「要拿就拿,不拿拉倒」的微薄金錢可能讓貧農有別無選擇的感覺。重點是某人有能力讓其他人做出違反自己原本偏好與策略的行動,而且讓雙方都感受到權力的存在。
一九六○年代,就在達爾發展出他廣為世人接受的定義之後未久,政治學家彼德.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莫頓.巴拉茲(Morton Baratz)指出,達爾的定義少了他們所謂的「權力的第二種面貌」—達爾忽略了議題的型塑與設定。如果理念和機制可以用來型塑行動的議題,讓其他人的偏好顯得無關緊要或超乎限度,那麼或許並不需要對他們施加任何壓力。換言之,我們或許可以透過影響他人對何謂正當與可行性的看法,去塑造他們的偏好。議程型塑著重在讓議題上不了桌的能力,或者就像福爾摩斯說的,讓狗不吠的能力。
有權力的行為者可以確保較弱勢的行動者不會獲邀上桌,或者即使上了桌,遊戲規則也早已由先到的人制定好了。國際金融政策就具有這個特色,至少在二○○八年金融危機發生,八國集團(G8)擴增為二十國集團(G20)之前是如此。權力第二種面貌行使的對象或許有、或許沒有意識到權力的存在。如果他們接受型塑議題之機制或社會論述的正當性,或許不會覺得自己受到權力第二種面貌的過度限制;但如果行動的議程受限於脅迫的威嚇或金錢的允諾,這就只是權力第一種面貌的行使。目標方對議程正當性的默認讓這個權力的面貌具有同化性,同時也是構成軟實力的部分要素—透過型塑議題、勸服、誘導出正面吸引力等同化手段,獲致你想要的結果的能力。
更晚近,一九七○年代,社會學家史蒂芬.路克斯(Steven Lukes)指出,理想與信念也有助於塑造其他人的初始偏好。依據達爾的分析途徑,我可以透過讓你做原本不會做的事情來對你行使權力;換言之,就是透過改變你的立場,讓你改變你所偏好的策略。但是我也可以透過決定你的需要,來對你行使權力。我可以塑造你基本或初始的偏好,而不只是透過改變你追求偏好的策略以改變情勢。
達爾的定義遺漏了這個面向的權力。十幾歲的小男生可能會慎重其事挑選一件流行襯衫穿到學校去吸引女生,但他或許沒意識到,這件襯衫之所以這麼流行,是因為某家全國性零售商大打廣告戰的結果。他的偏好和其他青少年的偏好,都由某個塑造偏好結構的隱形行為者所建構。如果你也能讓其他人自己想達成你希望的結果,或許就不需要讓他們改變自身的初始偏好。路克斯稱此為「權力的第三種面貌」。
人們在選擇偏好時到底擁有多少的自由,就涉及唯意志論(voluntarism)的重要問題。在外界批評者的眼中,不是所有的軟實力看起來都如此柔軟。在部分極端的例子裡,甚至很難斷定影響偏好自願形成的因素是什麼。譬如,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中,被綁架並遭受凌虐的受害者開始認同綁匪。綁匪有時試圖給綁架對象「洗腦」,有時甚至試圖以親切的態度贏得他們的好感。但是在某些情況中,更難的是確定其他人的利益。阿富汗婦女選擇穿罩袍是一種壓迫嗎?在民主的法國選擇戴頭巾的婦女呢?有時候單從外在的表現很難判斷自由意志的限度,比如希特勒或史達林這樣的獨裁者,會努力塑造所向無敵的形象以吸引追隨者,而東南歐部分國家的領袖也折服於此一效應。如果威力創造出足以吸引其他人的敬畏之情,那麼發揮到極限,就是同化性權力的一種間接來源;如果威力是直接的脅迫,那麼就只是權力第一種面貌的展現而已。
部分理論家稱這三個面向分別是權力公開、隱藏與不可見的面貌,反映出目標方察覺權力來源的困難程度。第二種和第三種面貌是結構性權力的具體展現,結構其實就是某一整體之各個部分的組合排列,人類置身在文化、社會關係與權力的複雜結構中,深受影響與限制。一個人的行動範圍是「受限於和他沒有互動與溝通的行為者,時空距離遙遠的行動,以及他並未清楚意識到自己就是目標的行動」。某些權力的運作反映出特定行為者有計畫的決定,但也有其他的權力運作只是無心的結果與更大社會力的產物。
舉例來說,為什麼我們的街道充斥著大型汽車?部分原因是個別消費者的選擇,但是,這些消費偏好本身卻是由廣告、製造廠商的決定、稅賦誘因、公共運輸政策、連絡道路的興建以及都市計畫的社會史塑造的。過去許多可見與不可見的行為者在這些議題上所做的種種不同選擇,賦予今天的都市居民受限的選項。
一九九三年,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的政治顧問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據說曾開玩笑希望下輩子可以變成債券市場,那麼就可以擁有真正的權力。我們提到市場力時,指的就是一種結構力的形式。種麥的農夫想多賺點錢付女兒的大學學費,可能會決定種更多小麥。但如果其他農夫也種更多(而需求並未改變的情況下),市場力或許反而會使他的收入減少,影響他女兒未來的教育。在完全市場中,個人並沒有訂價的權力,而是由其他數以百萬計、看不見、各自作出獨立決定的個人,創造出決定價格的需求與供給。也就因為這樣,生產貨物的貧窮國家在貿易條件上常受制於許多的變數。但如果某個個人可找出改變市場結構的方法,引進某種賣方壟斷(monopoly,單一的賣家)或買方壟斷(monopsony,單一的買家)的要素,就可以擁有制定價格的權力。她可以透過廣告、專利商標、選擇特殊地點等等使她的產品不同於其他產品,以達成目的。或者,以產油國為例,行為者也可以成立像「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Exporting Countries, OPEC)這樣的卡特爾(Cartel)。
不同的分析家從不同的角度剖析複雜的因果關係型態,釐清個人選擇與更大結構之間的界線。例如,社會學家一般不像政治學家那麼重視特定的行動與結果。只著重個別行為者的分析家,就像關注權力第一面貌的人,顯然無法全面瞭解並描述關係權力。但是,只著重廣泛社會力與更大歷史觀點的人,就如同關注權力第二與第三面貌的人,很少注意到對決策有重大影響力的個人選擇與意圖。部分批評者認為我的分析途徑太過「行為者取向」,但是我的分析研究就算未涵蓋結構的所有面向,卻也還是將結構力納入考量。
有些分析家認為,這些區分其實都是無用的抽象之物,可以全部納入權力的第一面貌中。然而,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論點,那麼很可能將所見的一切局限於以行為做分析,從而限縮了決策者設計來達成其目標的策略。命令權力(第一面貌)具體可見,易於掌握,硬實力—透過脅迫與收買獲致所希望之結果的能力—即以此為基礎。第二與第三面貌的同化權力則更微妙,更不可見,而這可構成軟實力—亦即透過議題設定、勸服、吸引等同化方式獲致所希望之結果的能力。決策者通常只著重於命令權力,以迫使其他人採取違反自身偏好的行動,卻忽略透過型塑偏好而來的軟權力。但如果同化的手段可行,決策者就可以不必威脅利誘了。
在全球政治上,國家追求的目標,有部分受權力第二與第三面貌的影響,大過於權力的第一面貌。阿諾德.沃爾弗斯(Arnold Wolfers)曾經區分他所謂的「佔有目標」(possession goals)—特定且通常有形的目標,與「周邊環境目標」(milieu goals)—通常為結構性且無形的目標。例如,取得資源、駐軍權或貿易協定是一種「佔有目標」,而推動開放貿易體系、自由市場、民主制度或人權則是一種「周邊環境目標」。以前面用過的術語來說,我們可以認為國家有特定的目標與一般性或結構性的目標。只強調命令權力與權力的第一種面貌可能會產生誤導,讓我們對如何推動這些目標抱持錯誤的看法。例如,在推動民主制度方面,結合軟實力的軍事手段比單純的軍事手段來得成功—這是美國在伊拉克已經發現的結論。而吸引與勸服的軟實力可以同時兼顧個人與結構的層面。例如,一國可以透過諸如公共外交的行動吸引其他國家,也可以透過其所示範的結構性效果—亦即所謂的「山崗上的光輝城市」效應—吸引其他國家。
不能將權力的三個面貌全納入第一個面貌的另一原因是,這樣做會讓我們忽略網絡的重要性,而網絡又是二十一世紀結構性權力的重要類型。網絡在資訊時代越來越重要,在社會網絡中的地位可以是重要的權力資源。例如,在樞紐—輪輻網絡(hub–and–spokes network)裡,溝通樞紐的角色可以產生權力。如果你透過我來和其他朋友溝通,那麼就賦我以權力。如果輪輻邊緣的各個點無法直接彼此溝通,那麼它們在溝通上對樞紐的依賴,就會塑造其議程。例如,許多非洲的法國殖民地在獨立之後,彼此之間的溝通仍然透過巴黎,這也使法國得以強化其塑造議題的權力。
分析家也指出,在更為複雜的網絡構造中,讓網絡的某些個部分無法直接彼此溝通的結構性洞隙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能跨越或利用結構性洞隙的成員,就可以控制其他成員的溝通,因此能利用自己的地位獲取權力。網絡另一個與權力相關的面向是其延伸範圍的廣闊:即使是薄弱的延伸連結關係,也能有效取得或散播新穎與創新的資訊。薄弱的連結關係可以讓各種群體用合作的方式成功連結,這可以提升國家的能力,透過與其他國家合作而非制服其他國家的方式取得權力。創造信任網絡,讓不同群體可以合力朝向共同目標邁進的能力,就是經濟學家肯尼斯.鮑丁(Kenneth Boulding)所謂的「整合力」(integrative power)。心理學家指出:「多年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取得與行使權力上,同理心與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要比強迫、欺騙與恐怖手段重要得多。」
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人們合力行動時,權力就大量湧現。」同樣的,國家可以透過與其他國家的交往和共同行動,而不只是對抗,來行使全球性權力。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者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y)論稱,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權力植基於多種制度所形成的網絡,這些制度雖對美國有所約束,但因為對其他國家開放,因此也使得美國與其他國家合作的權力得以提升。這是評估當前國際體系中各國權力的重要觀點,也是評估二十一世紀美國與中國權力發展的重要面向。例如,美國如果參與更多的溝通網絡,就擁有更大的機會可以藉由權力的第三種面貌去塑造偏好。
將社會科學家創造的權力三面向順序顛倒過來思考,或許有助於政策的擬訂。決策者應該先考慮偏好的型塑與議題的設定,將之視為塑造環境的手段,再來考慮權力的第一個面貌:命令的權力。簡而言之,若有人將權力的第二與第三面向納入第一面向,將會錯失在本世紀益形重要的權力層面。
第一章 何謂全球事務之權力? 就一個運用得如此廣泛的概念而言,「權力」的難以、無以衡量,著實令人意外。但是,概念並不會因為有這樣的問題就變得毫無意義。很少人會否定愛的重要性,雖然我們沒辦法說:「我愛你比愛其他人多三點六倍。」就像愛一樣,儘管我們無法精確衡量,但是日常生活中卻時時體驗到權力的存在,而且權力也真正發揮了具體的效果。有時候,分析家會因為某個概念太過模糊與不精確而傾向棄之不用,但是,「權力」這個概念已證明難以取代。 偉大的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經將「權力」在社會科學中的...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5收藏
15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



 15收藏
15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