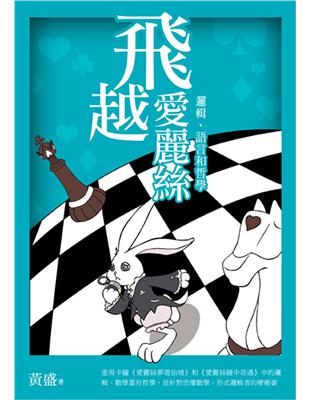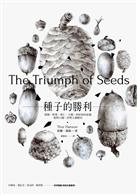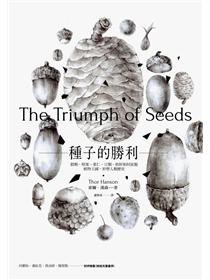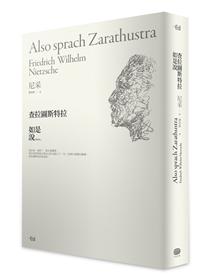1
愛麗絲與姐姐並排坐在池塘邊,由於無事可做,她開始感到膩煩。她不時朝姐姐正在讀的那本書瞧上一兩眼,可書上既沒有圖畫,也沒有對話。愛麗絲尋思:「要是一本書裡沒有圖畫或對話的話,那還有什麼用呢?」
她在心裡暗自盤算(她盡可能地集中精力想,因為悶熱的天氣弄得她頭腦遲鈍,昏昏欲睡),做一隻雛菊環的樂趣到底有多少,自己值不值得費勁地起身去摘雛菊呢?
真的是左右為難。做點什麼或什麼也不做──怎麼辦呢?雖然,做點什麼也不會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什麼不做便活不去,而且,要串一圈雛菊環還是需要先採摘幾朵雛菊吧,那便要把身子生拉硬拽地拖起來,可是炎炎夏日,草長地軟,偶爾一陣微風,令人懨懨欲睡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摘幾朵菊花,說得輕鬆,實在不是那麼地容易。可是嘛,坐在無趣的姐姐身旁,什麼也不做,枯燥無味,不悶壞才怪哩!你看她,竟然還一本正經地看書咧,可書上既沒有圖畫,也沒有對話。那還算是書嗎?
這就是無聊的愛麗絲遭遇到的兩難 ,而她的兩難,固然不是琢磨其自身的「困境」的一個邏輯後承,但卻為愛麗絲冒險進入一個超越常理的世界揭開序幕。當然,這個超越常理的世界並不一定便缺乏常理。這是一個卡羅式序幕,典型的狡猾和惡作劇。在即將發生在愛麗絲身上的歷險和讀者的期待之間,這個卡羅式序幕設下貫通全書的思維風格和調子。
「要是一本書裡沒有插圖或對話的話,那還有什麼用呢?」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問題?讓我們做個馬虎的假設:圖書館內的書大概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沒有圖畫和對話的書,另一類是有圖畫和/或有對話的書。讓我們頭腦再簡單一點,於是,我們聲稱,有圖畫和/或有對話的書都是給兒童看的,沒有圖畫和對話的書都是給成年人讀的。可以想像,小小的愛麗絲只對有圖畫和/或有對話的書感興趣,甚至覺得有用,譬如打發一個懶洋洋的下午。的確,如果愛麗絲「能夠」讀到自己身為主角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她必然會興高采烈,因為該書的每一頁,稀奇古怪的對話碰巧多得是,滑稽有趣的人物也不少,卡羅甚至為該書親自繪畫了很多插圖哩。《愛麗絲夢遊仙境》就是那樣的一本書,一本兒童書,而根據不成文規則,兒童書的內容大概都是些有點蠢的故事,荒奇怪誕,都是些人們從尷尬的青春期中長大過來之後便丟棄的無用的書。
等一等!真的嗎?兒童書真的那麼頭腦簡單、低智,所以不值得在兒童書上花時間嗎?這正是卡羅式轉折上場的地方。這是一本只有對話、圖畫和虛幻的書。可是,在這些之外好像還多了一點什麼,超乎大眾的期待。《愛麗絲夢遊仙境》無疑是本兒童書,但說句真心話,見多識廣的成年人呀,你真的看懂了嗎?
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吧,卡羅彷彿在敦促讀者,不要讓愛麗絲離開你的視野,跟著她,飛身躍入深沉黑暗的兔穴,看你能否比愛麗絲聰明,疏通理路,全身而退?
2
在緊跟愛麗絲跳進兔穴之前,我們要先與白兔見個面。這時出現了愛麗絲邂逅白兔的插曲。當愛麗絲還在盤算接下來幹什麼的時候,或者那只不過是她的神志恍惚,在無聊中開始走神,一隻粉紅眼睛的白兔突然貼著她身邊跑過:
這也沒啥讓人感到特別奇怪的,甚至在愛麗絲聽到兔子自言自語地說:「噢,天啊!哦,我的老天!我太遲了!」的時候,也沒有感到太多異乎尋常的地方(過後仔細回想這事兒,她覺得自己應該對此感到奇怪,但在當時看來,這一切似乎相當自然)……
關於這一段插曲,詮釋之一認為這時的愛麗絲已經進入了夢境之中。當她見到白兔在身旁跑過,還沒有跳入兔穴,她的世界早已顛倒過來:一隻會講話的白兔就像隨後發生的一切一般的普通、正常。但是,一隻會說英語/會說話的兔子真的「沒有……太多異乎尋常的地方」嗎?在我們的世界裡,的確異乎尋常!任何人,只要稍微有點好奇心,多少總會覺得異乎尋常的吧,雖然背後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因素?但也要看你是誰。如果是生物學者或人類學者,碰到一隻擁有熟練的語言技能的兔子,應該是饒有趣味的一件事情吧。生物學者可能會想檢查一下兔子的聲帶結構;人類學者可能要反思語言界定人類這個命題。一個飢餓的尼安德塔人想的極可能是與好奇心無關的另一樁事情。除此以外,難保沒有知識份子熱中於界定何為「常態」。畢竟,常態和異乎尋常的分界線在哪裡?但說到底,可能只是態度問題。一隻會說人話(英語)的兔子跑出來,那又怎麼樣?耶穌誕之夜,當教堂敲響午夜鐘聲,所有動物都會說人話(波蘭語) 。閣下可能感到異乎尋常,我可不覺得。愛麗絲也不覺得,起碼當其時不覺得。
最無所謂也少不免在某方面仍然懷有好奇的心情吧。
這隻兔子竟然從西裝馬甲的口袋裡掏出一塊懷錶,看了一眼,然後又匆匆忙忙地趕路了。這時,愛麗絲跳起身來,因為一個念頭突然閃過:她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馬甲上有口袋的兔子,更別說還能從口袋裡掏出懷錶了。
穿馬甲的白兔,還從口袋裡掏出懷錶?講英語有什麼了不起,能夠從口袋裡掏出懷錶才稀奇哩。什麼時候見過這樣的事情?
白兔看一眼懷錶後立刻匆忙趕路。不知從哪裡來的衝動,愛麗絲跳起來便隨著白兔跑。剛好看見白兔跳進了樹籬下邊的一個大兔子窩。愛麗絲想也不想便跟著跳下去。
兔子窩下是一條向前伸展的長長的隧道,不知通往何處?不過,愛麗絲也沒有時間推敲,因為隧道突然向下,形成一個大洞,她就這樣墜落,長時間,但輕飄飄地墜落!地洞變成深井的模樣,壁上滿布書架和櫃櫥,到處釘上地圖和圖畫。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地圖卻沒有一本書?「地圖」可能是一個暗示:要辨別方向,找尋出路,可能要靠一張地圖,這是一個卡羅式轉折;但有地圖沒有用,因為如果沒有圖例,空有一張地圖也是枉然,看不懂便是白紙一張,這是第二個狡猾的卡羅式轉折;可是,井壁之上掛著的不是一張地圖,而是數之不盡的地圖,哪一張有用,哪一張沒用,這是第三個卡羅式轉折。最令人為之氣結的是愛麗絲最後選擇的是一瓶橘子醬!這是第四個卡羅式轉折。愛麗絲笨嗎?唔,你說呢?
很難說愛麗絲的墜落是否針對基督教舊約創世紀中關於人類的墮落而營造的,但兩者的比較似乎相當有趣,即使冒著不恰當的聯想的忌諱。如果卡羅將愛麗絲拋進兔子窩時的確以創世記的寓言為目標,這個不可思議的旅程的起點便完全符合一個卡羅式轉折,顛倒了猶太基督教的創世記寓言!在舊約創世記的基督教神話中,亞當和夏娃在偽裝成蛇的撒旦的誘惑之下,吃了知識之樹的果子,違背了全知全能的上帝的意旨,在中世紀歐洲神學家的評釋中成為所謂原罪的由來。人類的墮落/墜落,始於亞當、夏娃對上帝的意旨的違背。這是歐洲文化中最早出現的出生論,比中國文革時期搞的出生論早一千多年。但在《愛麗絲夢遊仙境》的開頭,「誘惑」愛麗絲的竟然是一隻可愛的白兔,而驅策愛麗絲跳入兔穴的是天真幼稚的好奇心。還有比這更人性化嗎?彷彿是初生嬰兒,總是要盯住近距離的移動物體,伸出細小紅潤的手掌,緊抓住物體不放。天真的欲望,知的意志!愛麗絲的墜落是人類冒險精神的源頭、開創新世界的純真好奇之心。沒有不必要的罪疚心理,佛洛伊德口中的「無用情緒」。
隨著故事的開展,我們將發覺到愛麗絲的墜落是好的、充滿樂趣,更像一個嘉年華式的歡慶活動!
此時此地,筆者不禁想起了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當真理要由不容質疑的權威口授,「真理」便只不過是「教條」的同義詞。猶太基督教的聖經、梵蒂岡、美國等都是當代的真理部,他們說他們的上帝才是唯一的上帝、他們的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信奉真理部的真理之時即理性被殘酷放逐的一刻。真理來自對知識的探索、對未知的敢於求知及那掀起紗幕的意志。強加別人身上的偏執不是真理!
3
愛麗絲掉呀掉,似乎掉個沒完沒了,因為掉得太慢啦!不斷重複著一個動作實在太無聊沉悶了。愛麗絲的腦袋開始浪蕩,反覆思考應該是貓吃蝙蝠還是蝙蝠吃貓,嘗試計算下墜了多少里路程,推測如果這樣繼續掉下去會否穿越地心,會否從紐西蘭或澳大利亞那邊出來,等等。雖然處於劇烈的智力活動之中,愛麗絲還有閒暇從井壁的架上取下寫著「橘子醬」的一個罐子。但罐子是空的,於是愛麗絲將罐子放回剛巧經過的一個櫃櫥中。
迷迷糊糊地,她繼續思考了一大堆嚴肅的問題;不知什麼時候,她竟睡著了。就在此時,突然「撲通」一聲,她掉在一堆枯葉上,總算掉到底了,連小指指甲也分毫無損!抬起頭來,見到白兔走在一條長廊之內,正在趕路。愛麗絲匆忙站起來,朝著白兔追過去。拐了一個彎,兔子不見了。愛麗絲發覺自己走進了一個又長又低的大廳裡,四周有好多門,可都打不開。門和地圖的意義差不多,就算打得開,但那麼多門(就好像井壁上眾多的地圖一樣),哪個門才是出路呢?回過頭來,愛麗絲這時才發現大廳中央有一張三腳桌子,桌子上有一把小金鑰匙,碰巧可以用來開一扇約十五英寸高的小門。愛麗絲跪下來,往門的另外一邊望過去,竟然有一個漂亮得難以言喻的花園。花園裡還有一個清涼的噴泉啊!有生以來,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麗的花園。但十五英寸高的門就像個老鼠洞,如何爬得過去呢?愛麗絲開始思考。從最近的異乎尋常的經歷來推斷,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的不可能的吧。如果有本教人怎樣像望遠鏡那樣合攏的手冊(book of rules:寫有規則的書)便好了。愛麗絲在大廳內再走了一圈,這一次,她瞧見桌上放了一個小瓶。瓶上有張標貼,寫著兩個漂亮的大字「喝我」。
大家要留意,「規則」一詞首次在《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故事中被提及,到了《愛麗絲鏡中奇遇》時,「規則」一詞被引用得更多。在《愛麗絲》兩書和二十世紀英美哲學之中,「規則」一詞的重要性是難以被高估的。本書稍後會論述「規則」的概念與日常語言哲學 的關係,特別在詮釋《愛麗絲鏡中奇遇》的故事的時候。再強調一點,在鑑賞《愛麗絲》時,不要忘記日常語言哲學大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冒起,而《愛麗絲》的寫作時間是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相差約七十年。卡羅在日常語言哲學史中的先驅位置,少有受到承認,本書稍後會提供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