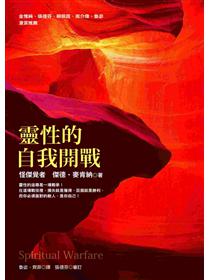名人推薦:
佛光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系副教授 藍吉富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闞正宗
專業推薦



大師教你有系統研讀經論
呂澂大師和印順法師並稱
「當代佛學雙璧」
藍吉富老師讚譽:「呂澂大師實為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界的第一人。」
呂澂大師在民國動盪時期興辦佛學院,為了有系統地培育佛子,他將自身融會貫通的學識,編列出一套學程,教導學生次第研讀經、律、論三藏。
更了不起的是呂澂大師在帶領研讀時,簡潔扼要點出該經該論之重點,又可比對其他經論,最後還能指出某些不合理之處。講解經論這些精華,皆收錄到這套書籍裡面。
本書特色
呂澂大師獨到深入的見解,讓你暢遊三藏智慧之海。
呂澂大師的卓越成就:
(一)對於十九世紀以來,歐美所盛行的新穎的佛學研究法(亦即以文獻學、歷史學、哲學等等各類學術方法及學術態度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呂澂有完整而深入的理解。他是將這種研究態度與方法介紹給中國佛學界,並且本身的成就也最大的中國學人。我們也可以說,呂澂是這種新式佛教研究在中國的主要奠基者。
(二)呂澂的佛學研究,不唯功力深厚,而且所涉及的領域也至為廣博。從他的著作來分類,他在佛書版本及辨偽、印度原典的研究與迻譯、因明與聲明、戒律、西藏佛教、印度佛教、中國佛教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績。在所有佛教研究領域裡,如果綜合起來衡量,在廣度與深度上,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界的第一人。
(三)在學術創見方面,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學術發現之外,呂澂的大部份論文,其實或多或少都有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之處。而綜合性的創見與對中印佛學融貫疏解,則表現在他那兩部講稿(《印度佛學源流略講》與《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之中。尤其《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一書,更大體可以展示其一生主要佛學功力之所繫。
作者簡介:
呂澂
江蘇省丹陽縣人。字秋逸(又字秋一、鷲子)。出生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四歲時開始自修內典。十八歲時,到南京金陵刻經處的佛學研究部隨歐陽漸學佛學。這是他一生生命的重要轉捩點。從此,唯識學大師歐陽漸得到一位「超敏縝密」(歐陽漸語)的傳人,而呂澂一生中的後面七十五年,也從此奉獻在佛學研究領域裡。
呂澂二十二歲開始協助歐陽漸籌辦支那內學院。到歐陽逝世後,曾先後出任該院的教務長及院長等職。中共政權成立後,他續掌院務,到 1952年該院停辦為止。此外,在世俗職務方面,他也曾擔任中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委員,及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等職。
呂澂(時七十歲)從「文革」開始以後,就不曾有過新著問世。他的身體還算健康,到九十一歲時還曾向訪者自謂「耳聰目明」,且能研討佛學問題,可見他在七十歲時是肯定有著述能力的。可惜從那時開始即告封筆。從1971年起,呂澂即卜居於清華大學的清華園,直到去世為止。
他的著述,在文革過後,先後曾由他的學生加以整理出版。其中,較早的有談壯飛整理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與《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張春波整理的《因明入正理論講解》。
名人推薦:
佛光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宗教系副教授 藍吉富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闞正宗
專業推薦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闞正宗藍吉富謹識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影片僅供參考,實物可能因再版或再刷而有差異
作者:呂澂
 3收藏
3收藏

 3二手徵求有驚喜
3二手徵求有驚喜
優惠價: 9 折, NT$ 899 NT$ 999
限量商品已售完
大師教你有系統研讀經論
呂澂大師和印順法師並稱
「當代佛學雙璧」
藍吉富老師讚譽:「呂澂大師實為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界的第一人。」
呂澂大師在民國動盪時期興辦佛學院,為了有系統地培育佛子,他將自身融會貫通的學識,編列出一套學程,教導學生次第研讀經、律、論三藏。
更了不起的是呂澂大師在帶領研讀時,簡潔扼要點出該經該論之重點,又可比對其他經論,最後還能指出某些不合理之處。講解經論這些精華,皆收錄到這套書籍裡面。
本書特色
呂澂大師獨到深入的見解,讓你暢遊三藏智慧之海。
呂澂大師的卓越成就:
(一)對於十九世紀以來,歐美所盛行的新穎的佛學研究法(亦即以文獻學、歷史學、哲學等等各類學術方法及學術態度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呂澂有完整而深入的理解。他是將這種研究態度與方法介紹給中國佛學界,並且本身的成就也最大的中國學人。我們也可以說,呂澂是這種新式佛教研究在中國的主要奠基者。
(二)呂澂的佛學研究,不唯功力深厚,而且所涉及的領域也至為廣博。從他的著作來分類,他在佛書版本及辨偽、印度原典的研究與迻譯、因明與聲明、戒律、西藏佛教、印度佛教、中國佛教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績。在所有佛教研究領域裡,如果綜合起來衡量,在廣度與深度上,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界的第一人。
(三)在學術創見方面,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學術發現之外,呂澂的大部份論文,其實或多或少都有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之處。而綜合性的創見與對中印佛學融貫疏解,則表現在他那兩部講稿(《印度佛學源流略講》與《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之中。尤其《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一書,更大體可以展示其一生主要佛學功力之所繫。
作者簡介:
呂澂
江蘇省丹陽縣人。字秋逸(又字秋一、鷲子)。出生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四歲時開始自修內典。十八歲時,到南京金陵刻經處的佛學研究部隨歐陽漸學佛學。這是他一生生命的重要轉捩點。從此,唯識學大師歐陽漸得到一位「超敏縝密」(歐陽漸語)的傳人,而呂澂一生中的後面七十五年,也從此奉獻在佛學研究領域裡。
呂澂二十二歲開始協助歐陽漸籌辦支那內學院。到歐陽逝世後,曾先後出任該院的教務長及院長等職。中共政權成立後,他續掌院務,到 1952年該院停辦為止。此外,在世俗職務方面,他也曾擔任中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委員,及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等職。
呂澂(時七十歲)從「文革」開始以後,就不曾有過新著問世。他的身體還算健康,到九十一歲時還曾向訪者自謂「耳聰目明」,且能研討佛學問題,可見他在七十歲時是肯定有著述能力的。可惜從那時開始即告封筆。從1971年起,呂澂即卜居於清華大學的清華園,直到去世為止。
他的著述,在文革過後,先後曾由他的學生加以整理出版。其中,較早的有談壯飛整理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與《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張春波整理的《因明入正理論講解》。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闞正宗藍吉富謹識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 二手徵求後,有綁定line通知的讀者,
該二手書結帳減2元。(減2元可累加)
請在手機上開啟Line應用程式,點選搜尋欄位旁的掃描圖示
即可掃描此ORcode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