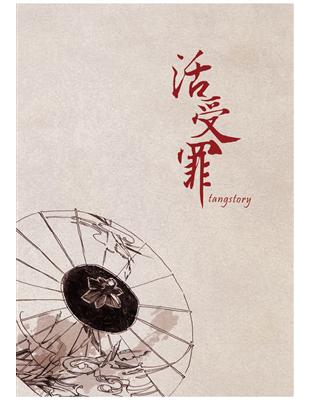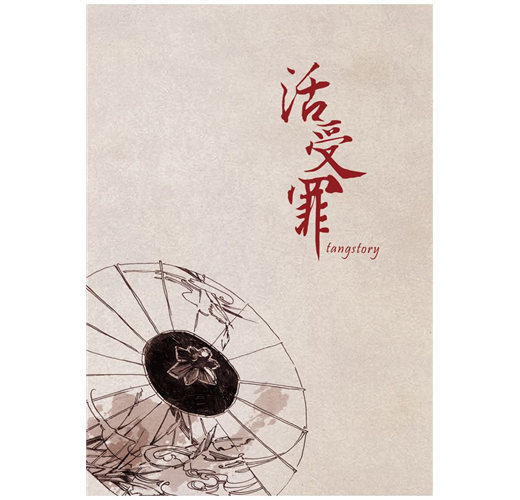《活受罪》
一
迷濛間沈涼生聽到雨打紙傘的聲音。夏時陣雨稠密急促,砰砰地打在傘面上,似夢中戰鼓,敲得氣海翻騰,終於痛醒過來。
沈涼生睜開眼,便見一把油紙傘罩著他的頭臉,傘上繪著漠漠黃蘆,筆意靈活,一派不勝雨打風吹之態。
他聽到身畔有人聲道:「這雨下不久,再過片刻也該停了。」便欲伸手去摸佩劍。秦敬立在他身側,執傘望著他,看他手指動了動,便又躬身湊近了些。
荒涼山間,除了他們再無人跡。沈涼生傷重之時尋到這間破廟,本欲入內避雨裹傷,卻終是體力不濟,倒在了廟門口。
這土地廟早已荒廢多時,破得門都塌了,沈涼生被斜躺在泥地上的木門絆了一絆,倒在門板上,暈過去半柱香光景。
血流得太多、太快,雨澆不去,滲進門板裡,又隨著雨水自木紋裡泛上來,濕潤鮮妍,像棺材底新鋪的一層硃砂。
這半死不活的光景令秦敬有些為難,猶豫了一下,還是直截了當道:「你叫什麼名字?若你死了,有個名字也好立碑。」
沈涼生暗提真氣,覺得渾身經脈無一不痛,似千萬把刀在身體中細細銼磨,全然不能出聲。
秦敬見他不答話,只以為他不甘心就此嚥氣,便點點頭,隨口道:「也是,若是能活,還是活著好。」
雖說痛到極處,沈涼生也不願再暈過去,強撐著意識清明,對上秦敬的眼。
秦敬與他互望,見那目光中並無懇求搭救之意,亦無倔強不甘之色,只如千尺寒潭,既冷且靜,映出自己的影子——半躬著身,一手執傘,一手撓頭,認認真真地瞅著對方,一副犯傻的德性。
秦敬咳了一聲,直起身,想撿回些世外高人的氣派,又連自己都覺得好笑,只好再咳一聲,正色道:「方才探過你的脈象,內傷外傷加在一塊兒,也就剩了這一口氣。我也不願見死不救,但若貿然挪動……我怕這路上你就撐不過去。你意下如何?」
沈涼生身為密教護法,經脈行氣之道本不同尋常。他自知這身傷勢並沒此人想得那樣重,便是一直躺在這兒淋雨,淋上一天一夜怕都死不了,何況一段路。
沈護法心中權衡一番,若放出教中通信煙花,引來的是敵是友尚未可知,不到萬不得已之時還是罷了。現下既然有人願救,便暫由他去,至於這人是什麼來路,是真心相救還是另有玄機,且走一步看一步。
秦敬見他沉默片刻,微微頷首,便當他是願意試試這一線生機,遂收了手中紙傘,挾在腋下,彎腰使力,想將人打橫抱起。可惜秦敬的武功本就平常,又走的是借力打力的輕巧路數,要論實打實的力氣,和不會武的普通人也差不多,要挾著傘抱起一個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男人,實在有些力不從心,只得嘆了口氣,將傘棄到一邊,雙臂運勁將人橫抱在胸前,再嘆道:「可真是重。」
沈涼生閉目養神,覺出那人使出輕功趕路,心忖一句,這功夫可真是糟糕,如若醫術也是這個水準,大抵還是得靠自救。索性不再管他,任由他抱著自己顛顛簸簸,暗自運起獨門心法平復受損經脈。
沈涼生這門心法名喚「五蘊皆空」,名出佛門心經,卻也只是借個名而已,與佛家內功不沾半點干係。不過此門心法的奧義確是一個「空」字,運功之時心跳脈搏漸趨於無,教內典載若功至頂層,可假死百年,只餘一縷內息流轉不滅,復生之日功力亦以百倍計,當世無敵。
沈涼生這名字聽上去有些姑娘氣,倒是人如其名,性冷心寒,定力了得,是修煉此門心法的好材料。雖說練至第七層後再無進境,但功至此步,運功之時氣息脈像已頗微弱,幾近假死之貌。
秦敬不知他心法奇詭,只覺得懷抱之人漸漸沒了氣,腳下更急,心頭卻不免湧起一絲哀意。雖說素昧平生,但既已說了要救他,若還是只能眼睜睜看他死在自己懷裡,這滋味當真不好受。
夏時陣雨果不持久,雨勢漸緩漸歇,天邊出了日頭,林間點點金斑,鳥聲蛙鳴,更襯得懷中一片死氣沉沉。秦敬低頭看了眼懷中人,面白如紙,唇色寡淡,神色倒平靜寧和,不見苦楚。
不痛便好,秦敬默默心道,反正人活一遭,多多少少都得受些罪,若能無知無覺死了,最後少受點罪,也是造化。
抬頭遙望,自己的藥廬還得再翻一個山頭,這人恐怕真是撐不到了。自己雙臂痠痛,抱他也抱得不甚安穩,若是顛醒了他還要活受罪,這麼一想乾脆暫停了停,小心地將懷中人挪了挪,欲再抱穩一些。
沈涼生雖在運功,卻也不是對外物無知無覺,見他停了步子便以為是到了,睜眼打量,正見秦敬皺眉望著他,看他睜眼又忙展眉擠出個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輕聲道:「離得不遠了,你若累了便繼續睡。」
沈護法活了二十六年,頭一次有人拿這哄小孩兒的口氣與他說話,略一思忖,便猜到這人恐怕以為自己是迴光返照,又見他面上神色似是當真不好過,影影綽綽的日光下,自眼角至頰邊竟像有道淚痕,便也低聲回了句:「有勞。」
要說沈護法平生雖與「好人」二字全不沾邊,卻也是壞人裡的正經人,便連殺人也殺得禮數週到——毫不留情地將人捅個對穿,再客客氣氣地補聲「得罪」,一本正經得讓教內同仁看著他就牙疼。
秦敬聽得這句「有勞」,咧嘴笑了笑,暗道等我給你掘坑挖墳時再謝不遲。心裡難過,面上笑意反更深了些。
沈涼生並未繼續運功療傷,一來銳痛漸緩,二來欲速則不達,左右不急於這一時。他平心靜氣地端詳這個抱著自己趕路的人,心中並無絲毫感激之情。世上有諸般善良美好,亦有諸多奸邪苦厄,萬象自然。無論是善是惡,與己無關有關,沈涼生觀之皆如日月草木,不知動心為何。
「咦?」盞茶過後,秦敬也覺出懷中人氣息平穩綿長,不似一般迴光返照之態,心中稱奇,低頭看他,笑道:「看來你命不該絕。」
沈涼生端詳他半晌,想的卻是原來這人並未當真掉淚。只是自眼角向下有道纖長傷疤,淺而細,晃眼間頗似淚痕,非要細看方能看出端倪。
這樣一道疤,算不上破相,卻為這張平淡臉孔平添一絲趣味。尤其是嘴角噙笑時,便是一張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的臉。
二
秦敬,表字恆肅,為人卻一點也不端方嚴肅。與沈涼生裹傷時互通姓名,他便笑著調侃,一碗涼水,生不逢時,真是個好名字。
沈涼生不答話,任他在自己身上摸摸索索敷藥,心知外傷並無大礙,只是內傷少說要休養月餘,功體全復更不知要等到何時,而天時已近,教中正值用人之際,真是麻煩。
「你經脈受損頗重,培本固元乃當務之急。」秦敬把七七八八擺了一床的藥瓶拉進藥箱收好,「若專心調養四、五十日,大約能拾回八成功力,最後兩成還需你自己……」
秦敬話說了一半,便見沈涼生抬眼直直望向自己,以為他嫌太慢,搖頭勸道:「此事急不來。我跟你說實話,助你更快回復功力的法子不是沒有,但此法三五年後必有後患,我不想用。你還年輕,往後日子長得很,不值得。」
「你是個好大夫。」雖無感激之情,沈護法這句評語給得倒是真心實意——但他臨陣對敵之時,偶爾遇上難纏的對手,也通常是在收劍入鞘後,真心實意地用一句「多謝指教」將人送入輪迴道——所以便是真心讚賞可也不大吉利。
「不敢當。」秦敬起身走去藥架旁,揀出個青瓷藥瓶。
「方才話未說完,那剩下兩成……」復又走去桌邊,倒了杯白水,頓了頓,還是打算把話攤開來說明,「剛剛細探過你的脈象,先頭倒是我走眼。你修習的心法太古怪,那剩下兩成我的確無能為力,得靠你自己慢慢補足。」帶著藥瓶白水回到床邊,倒出兩粒朱紅藥丸遞至沈涼生眼前。
「內服。」
沈涼生並未接藥,仍是直直望向秦敬,毫不掩飾眼中查考神色。「五蘊皆空」這門心法雖為教中密寶,只有歷代大護法方能修行,但江湖上對此也並非一無所知。若是這位秦大夫已看明此中關節,卻仍肯出手相救,便定不是「善心」二字那麼簡單。
沈涼生不接藥,秦敬也未著惱,自顧自拿過他的手,將藥丸茶杯塞過去,收手續道:「此間現下除了你我,再無旁人。方才進來時,你想必也看到了,此處除卻地勢隱蔽,更有陣法加持,不是什麼人想進就進得來的。我既已答應救你,便沒打算害你。我是大夫,你是病人,別無其他。天色已晚,要走還是要留,你自便吧。」
秦敬說完便走回桌邊,也為自己斟了杯涼水,一氣喝完,心口隱痛似是好了一些。
實則秦敬自己也知道,那痛其實是不存在的,只是思及之後的棋局命數,錯覺心痛罷了。
沈涼生沉默片刻,淡聲問道:「你要什麼?」
秦敬回身看他,挑眉一笑:「救命之恩,自然是要以身相許了。」
要說秦敬平生雖與「壞人」二字全不沾邊,卻也是好人裡頂不正經的那一種。不但嗜賭,而且好色。尤其後者,見到樣貌好的,不拘男女,總愛口頭上佔點便宜。雖然真讓他做點什麼他也沒那個膽子,眼前這人他更是萬分惹不起,但有便宜不佔,到底不符合秦大夫一貫嘴賤的做派。
「你是大夫,我是病人,別無其他?」同一句話,沈涼生以問句道來,雖是平淡語氣,秦敬卻生生從裡面聽出一絲揶揄意味,想必是諷刺自己上一句還說得好聽,下一句便出言無狀,沒有醫德。
唉。秦敬默嘆口氣,愁眉苦臉地望著坐在床上的沈護法,心道這位仁兄明明看上去冷漠寡言,怎麼耍起嘴皮子來也那麼厲害。好好的冷美人不做,真是浪費了那張面皮。
沈涼生不再多言,就水吞下藥丸,和衣而眠。他直覺這人早晚有求於己,現下不直說,便留了交換條件的餘地。以利換利,最為讓人放心。
再醒來已是三日後,秦敬所予之藥果然無錯,培本固元,平經理氣,便連外傷藥也著實管用,短短三日,傷口皆已癒合結疤,想來再過幾日便能好全。
「如何?能走了吧?」秦敬自己配的藥,自然心中有數,掐好了點兒過來探了一眼,正見沈涼生披衣下床。
「多謝,外傷已無大礙。」
「往後一月,每隔一日進藥泉泡兩個時辰,隨我來吧。」
出了藥廬,兜兜轉轉,便見一方暖池,籠著薄薄水霧,撲面一股清苦藥香。沈涼生並不避諱——兩個大男人,按說也沒什麼可避諱的——直接除盡衣物,走入池中坐定。
秦敬的心思也不在他身上,只看著地上血衣,好言商量道:「不值錢就扔了吧?捨不得你就自己洗。」
「隨意。」
秦敬揀起衣服,轉身走了幾步,又想起他這幾日也未得空洗漱,遂回身道:「我去拿皂角,你順便洗洗頭髮。」
待到秦敬拿著洗漱之物回轉,卻見沈涼生似又睡了過去,閉目靠在池邊,一副無知無覺的模樣。
「天氣熱,泡這藥泉的確有些難受,下次你可晚上再來。」
「……」
沈涼生不出聲,秦敬繼續自說自話:「莫要真睡過去,雖說水不深,萬一淹死了也是作孽。」
「……」
「東西我放在這邊,洗頭髮你總會吧?」
「……」
「沈涼生沈護法,我是秦大夫,不是秦老媽子……唉,我算見識到什麼叫不聲不響地支使人了。」
其實沈涼生倒也沒什麼使喚他的意思,不過是在運功行氣而已。
心經道,五蘊皆空,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心法卻全違佛家本意,偏要自無中生有,內息生生不滅,對外物知覺反更加敏銳。
他覺得有手輕輕取下他的髮冠,一絲一縷打散頭髮。
秦敬取下沈涼生的髮冠,打散髮絲,拿過木瓢,舀一勺熱水,當頭淋下。
黑髮如墨,逶迤蜿蜒。
——覺得有手細細梳過髮間,不厭其煩地,解開一個又一個髮結。
沈涼生當日血流得多,頭髮飽浸了鮮血,乾涸後黏連不清,遇到熱水後又再化開,水中平添幾縷薄紅。
秦敬的眼追逐著融開的血色,微波蕩漾中似一抹水紅縐紗,紗後是長年習武之人赤裸的身體,身上幾道深長傷口,血痂猙獰有如活物、有如暗紅長蛇,彎轉攀附在這樣一具軀體上,蛇頭臥於胸前,正是乳頭的位置,絲絲毒信一吐一收,自乳頭上反覆滑過。
——覺得那雙手不疾不徐地按揉髮絲頭頸,時而重,時而輕。何時重何時輕卻是……不可捉摸。
日光朗朗,池水清澄直若無物。目光再向下,就著對方閒適坐姿,腿間蟄伏的陽物亦纖毫畢現。因為太坦蕩,反無什麼情慾遐思。
秦敬收回目光,只盯著沈涼生的臉,專心手下活計。
修眉鳳目,直鼻薄唇,冷漠如雪後荒原,銳利若掛松冰凌。並非妖邪之相,只是煞氣太重。
還有……秦敬微錯開眼,連臉也不敢再看,心道怎麼偏偏就有人明明未著一物,卻仍是一派禁慾之意。
須知愈是禁忌……愈會讓人多想。
——覺得身周熱水沁入四肢百骸,輕飄不著力的酥麻。藥香漸漸濃郁,卻是兩股不同的味道。誰人身上草藥香氣,似濃霧中一個淡淡的影子,越步越近,終自霧中現出身形。
眼觀鼻,鼻觀心,秦敬打定主意不再瞎瞧。
可惜不看歸不看,指間滑膩髮絲卻像張躲不開的網,網中活魚左掙右突……秦敬猛地鬆開手,站起身退後一步,胯下半硬的陽物蹭著褻褲,恰似魚在網中,緊也難受,鬆也難受。
只因早晚死路一條,便在水中多活片刻,也只是活受罪。
——覺得那雙手突地離開,像霧中人影就要明了之時,又兀地隱去不見。
「換洗衣物就在池邊,你泡夠了時辰就自己上來吧。」
秦敬清了清嗓子,講完話便轉身離去。餘下沈涼生獨自泡在池中,內息走完一個周天,慢慢睜開眼。
頭髮這東西……他捋過一縷髮絲,難得有心想到一些閒事。
頭髮這東西本是無用之物。割之不痛,棄之復長,卻偏偏又有時靈活得像懸絲診脈的那一根細絲。
諸般雜念,灼灼情慾,瞞不可瞞,欲蓋彌彰。
《長相守》
就期待三十年後交匯十指可越來越緊
願七十年後綺夢浮生比青春還狠
——《任白》 林夕
一
三月初天仍冷著,天時卻長了。六點電影散場後,外頭也不過將將擦黑。天宮戲院票價低廉,便是平日上座也有七、八成。加之最近正逢上海阮姓女星香消玉殞一週年,雖說津城遠在北地,各大戲院也紛紛趕趟,翻出幾部佳人舊作重映,一時場場爆滿。
今日天宮放的是部《野草閒花》,當年公映時沈涼生尚在英國唸書,只在當地華人報紙上見過兩張劇照。如今再看來,螢幕上聲賽黃鸝的賣花女早化作一抔塵灰,好好的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戲碼,終成了一個笑話。
散場後人潮洶湧,摩肩接踵地往外擠。自去年孫傳芳於居士林遇刺後,各路蟄居在津的政要軍閥人人自危,沈涼生亦被沈父強制要求帶著保鏢方能出門,是以場面再擠也同他沒什麼關係,兩個保鏢一左一右當先開路,沈涼生走在中間好似摩西渡紅海。
眼見快到了門口,卻聞身後一陣騷動,有人操著方言喝罵:「擠嘛擠嘛,趕著投胎吶!」
沈涼生微回了下頭,原來是有人不知掉了什麼東西,正彎著腰四下找,被人潮擠得來回踉蹌,萬一摔趴了,多半要被踩出個好歹。
沈涼生看那人著實狼狽,頓了頓,難得發了回善心,帶著保鏢退回幾步,為他隔出一小方清靜天地。
「勞駕讓一讓……誒這位,您高抬貴腳……」那人只顧彎腰埋頭,嘴裡咕咕叨叨,倒是一口字正腔圓的國語,不帶本地土音。待終於找到東西直起身,也是一副斯文讀書人的模樣,看面相挺年輕,穿著身藍布夾袍,高高瘦瘦,未語先笑。
「多謝。」那人先禮貌道了聲謝,又順嘴開了句玩笑,「這人多得跟下餃子似的,再擠可就成片兒湯了。」
「不客氣。」沈涼生淡淡點了下頭,瞥見他手裡攥的物事,原來是副黑框眼鏡,鏡片兒已被踩破了一邊,鏡腿兒也掉了一根,便是找回來也戴不成了。
「我說秦兄,怎麼一眨眼你就不見影兒啦?」
過了這麼會兒,人已漸漸稀疏,不遠處有個圓臉年輕人招呼著擠過來,待看清幾個人對面立著的陣勢,又疑惑地停了步子。
「小劉,我沒事兒,」那人先轉頭對友人交待了一句,方同沈涼生告辭道:「這位……」想必不知如何稱呼,卻也沒有問稱呼,只笑著點點頭,「回見。」
「再會。」
沈涼生答過一句,兩人便繼續各走各路。只是出了戲院大門,走出去十幾步,沈涼生又鬼使神差地駐足回頭望去。
二十一號路兩側商家林立,正是華燈初上的光景,人群熙熙攘攘,他卻一眼便自其中捕捉到方才那人的背影。瘦長的身形套著件薄夾袍,足比身邊敦實的同伴高出兩個頭,正微傴著身聽友人講話,邊聽邊走,暮色中灰撲撲的一條背影,搖搖晃晃地沒入人流,慢慢找不見了。
「秦兄,剛才那人你認識?」
「不認識。」
這廂閒話的主角卻正是身後駐足回頭之人,小劉好奇地追問了句:「那你有沒有問他叫什麼名字?」
「你看他那身打扮,就知道跟我們不是一路人。瞎套近乎這碼事兒,秦某可從來不做。」
「秦敬,你少跟我貧嘴。」小劉笑罵了一句,眉飛色舞道:「我倒覺得那人我在《商報畫報》上見過,看著挺像沈克辰的二公子。」
自北洋政府倒台後,隱居於津的下野軍閥多如過江之鯽。其中有野心不死的,想著天津與北平相距不遠,那頭有個風吹草動這頭便可伺機再起;也有棄政從商的,沈克辰便算其中翹楚。
「那你定是認錯了,若真是沈家的公子,看戲也要去小白樓那頭才是,怎麼會來勸業場湊熱鬧。」
「誰讓平安自恃身價,極少上國片。說不準人家沈公子也是阮小姐的影迷,特來觀影以悼佳人唄。」
秦敬沒再接他的話茬,專心垂頭擺弄著破片兒掉腿兒的眼鏡,一臉「心肝兒我對不住你」的喪氣相。
「祖宗,您眼神兒不好就多看著路!」小劉沒奈何地扯住他的袖子,生怕一不留神又弄丟了人。
秦敬確是眼神兒不大好,為了看清東西一直瞇縫著眼。少了鏡框遮掩,眼角邊生來便帶著的一顆硃砂痣愈發鮮明。
說起眼角這顆痣,秦敬在北平師範大學唸書時,還曾被同窗好友取笑道:「你這痣紅得實在邪性,又長在這麼個地方,可見你上輩子準定是個姑娘,被相好沾著胭脂點了記號,方便轉世投胎再續前緣吶。」
秦敬這人眼神兒不好,脾氣可是一等一的好,而且特別愛開玩笑。聞言也不著惱,只板著臉道:「怪力亂神之事,秦某是從來不信的。」跟著湊去友人眼前,痛心疾首道,「但自打見了你,真是容不得我不信。官人,你可知奴家苦等了你多少年?」唬得友人跳開三尺,連連笑著擺手:「最難消受美人恩,冤家你還是趕緊忘了我吧!」
「二少?」
沈涼生突然駐足回頭站了半晌,隨行保鏢不由有些緊張,以為周圍有什麼動靜,手已伸進懷裡,暗暗握住槍柄。
「無事,走吧。」
走到泊車的地方,一人鑽進前座,一人立在車旁,待沈涼生上了車,方陪他一起坐到後座。
沈涼生原本的車是輛雪佛蘭,可自打孫傳芳出了事,沈父便逼著他換了輛加裝了防彈鋼板的道濟,可見對這個小兒子有多著緊。
但這著緊的緣由,卻關係著一段不光彩的秘辛。
沈涼生的母親有一半葡國血統,從事的行當不怎麼正經,說白了就是個高級妓女。沈克辰認下了她生的兒子,卻礙於得罪不起正房太太的娘家,未敢將人娶進門,只養在外面,先頭還給些花銷,後來見她染了大菸癮,怕是個填不滿的無底洞,索性不管不顧了。
當年那個被菸癮折磨得形銷骨立的女人曾三番五次跑到沈家鬧事,來來回回只叫著沈家大太太的名字,聲聲嚎著:「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阿涼,你要還認我這個娘就別放過她!」
沈克辰多少顧念點以前的情分,每次都是將人趕走了事。次數多了,沈涼生在沈家愈發難以立足,十四歲便被送去英國,說是留洋,與流放也差不多。家裡只給付了頭兩年的學費,後幾年全靠自己半工半讀,待到學成歸國,並非為了認祖歸宗,也並非想著為母報仇——說句實話,他對生母、對沈父、對故國都沒什麼感情,只是權衡了一下形勢,比起孤身在異國打拚,吃盡苦頭也不一定能出頭,還是回國有更多機會。
尤其是北洋政府倒台後,沈太太那個得罪不起的娘家也是雨打風吹去,沈太太在沈克辰面前再說不上話,未等到沈涼生回國便鬱鬱而終。沈克辰於花甲之年鰥居在津,身邊大兒子不太爭氣,午夜夢迴時憶起當年愛過的女人,對小兒子實有幾分歉疚,見沈涼生願意回來,自是欣然應允。
沈涼生一個人在異國磨煉多年,歸國做了少爺,外表是嚴謹而一絲不苟的,骨子裡卻是不擇手段的秉性。此番回國,抱的就是撈一筆算一筆的念頭,只待撈夠了本便遠走高飛,反正世界之大,哪裡對他都一樣。
從未覺得哪裡是家鄉,便處處皆是異鄉,反而了無牽掛。
沈家大少原本只是「不太爭氣」,待沈涼生歸國後,多少也有了些危機感。兄弟倆表面上還算過得去,暗地裡幾番較量,做大哥的卻一敗塗地,好不容易燃起的一點志氣被狠狠打壓下去,人便愈發頹唐,整日泡在馬場,後來又迷上了賭回力球賽,回家就是伸手要錢,「不太爭氣」終變成了「太不爭氣」,沈克辰的精力又一年不如一年,待到沈涼生歸國的第四個年頭,已將沈家泰半生意投資掌握在手,走與不走,什麼時候走,端看時局如何發展。
這段過往雖不光彩,卻也難免有知道幾分內情的熟人。背地閒談起來,對沈家二少的評價總離不開一句「會咬人的狗不叫」。沈涼生不是不曉得這些風言風語,可壓根不往心裡去,又或者連有沒有心都要兩說。有時候連沈涼生自己都覺得,他這名字可真沒取錯。
確實活得涼薄。
車開出二十五號路,道上稍微清靜了些。沈涼生八點在起士林還有個飯局,趕著回家換衣服,便叫司機提了速,卻沒開兩個路口,又突道了句:「慢點。」
駕車的保鏢槍法不錯,開車的技術卻不怎麼樣,聞言竟踩了腳剎車,沈涼生身子傾了傾,倒也沒發火,只淡淡吩咐了聲:「沒事了,繼續開吧。」
車子繼續往前駛去,沈涼生斜倚在皮座裡,一手支頭闔目養神,面上波瀾不興,心裡頭卻有些不平靜。
方才有那麼一瞬,他透過車窗,瞥見路邊一個高瘦的人影,脫口而出叫了聲慢,下一瞬又看清了,並不是自己腦中想的那個人。
明明素昧平生,不過是偶然的一段小插曲,如此念念不忘,沈涼生自己也覺得十分訝異。
他閉著眼,在腦子裡重勾勒了遍那個人的面目,竟是鮮明得像幅版畫,一筆筆都是用刀子刻出來的。
那人似仍立在身前,高瘦斯文,嘴角含笑。大約因為戴慣了近視鏡,一直微覷著眼,眼角一小粒色若桃花的硃砂痣,竟似有股脈脈含情的神氣。
便在那刻,彷彿疾馳中猛踩了一腳剎車,沈涼生心中突地一沉,又再一輕,只覺一瞬恍惚。像有隻看不見的手,在自己心上猛地推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