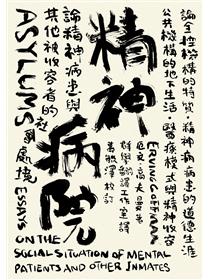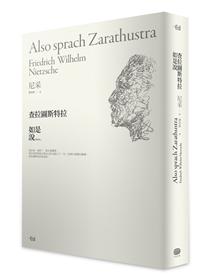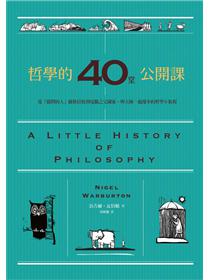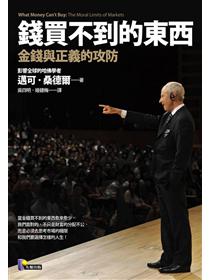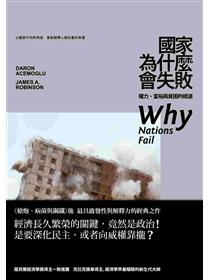西田幾多郎
日本近現代哲學的推手
琵琶湖畔的哲學之道──日本京都學派創始者的思想精粹
西田幾多郎是日本近現代哲學中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西田哲學作為東方傳統思想現代化的代表,「京都學派哲學」即是以他為首建立的。西田以後的日本哲學若非深受西田的影響,就是以哲學為出發點。他的出現將日本哲學推上世界哲學的舞台。
《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第一篇選文〈作者序〉收錄西田幾多郎為數本書所撰寫的序言,為初次接觸西田哲學的人提供思想脈絡的分期概觀。西田於1936年《善的研究》的「新版序」中,將自身思索的發展區分為五個立場:「純粹經驗」、「自覺」、「場所」、「辯證法的全般者」與「行為的直觀」。相對前三期從「自我來看世界」的立場,第四、五期則是「從世界來看世界」的立場。前者類似中國哲學中「心學」的道路,後者則類似「史學」的道路。但是這種「轉向」嚴格說來並不是立場的「轉變」,而是立場的「深化」。
在〈絕對自由意志〉一文中,西田認為不論是「思維的體系」或「經驗的體系」都來自於同一體系,由自覺出發的自我發展,而絕對自由意志則是各體系可能性的根源,屬於「體驗的世界」,是「超越我們的言語思慮的世界」。與新康德學派先驗哲學的對決來突顯自己的思想的〈種種世界〉一文,則討論「物」自身必須是「在概念的知識之前就既予的直接經驗」,西田將其理解為「絕對自由意志」,它是「活動的活動」、「先天性的先天性」。以上兩篇選文都充分顯示了西田初期思想中「主意主義」的思想。西田將意識的根本理解為「意志」。但是這樣的意志,最終的意義並不是主客對立下的意志,而是超越主客對立且致使主客對立成為可能的「絕對自由意志」。另外,西田一方面肯定作為終極實存的絕對自由意志是一種「創造的無」,是無限的創造活動,一方面又認為它擁有思想所無法到達的神秘性。
〈場所〉一文作為西田的場所邏輯之代表,其核心想法在於:「有必須內存於某處,否則有將無法與無區別」。沿著這個想法,西田在這裏區別出了三個場所,分別是:「有的場所」、「相對無的場所」和「絕對無的場所」。其中,「絕對無」必須是將有無都包攝在內,並且讓有無得以成立的場所。由於知識主要是以判斷的形式表達,因此,將這個想法轉譯成判斷的主述詞形式,就形成了場所邏輯。場所邏輯的提出原本是一種認識論的想法,所針對的概念是新康德學派的認識論,但是它隨即擴張為一個形上學的體系。在〈場所〉論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西田用「靜態的」或「映照的鏡子」等概念來說明絕對無,但這只是因著認識的可能性基礎而提出的,真正的絕對無必須是「絕對的無而有」,是具創造性的無。
西田的絕對無除了「知識成立的可能性基礎」與「絕對無的創造問題」之外,還擁有宗教的意義,而這其實是西田的終極關懷。〈場所邏輯與宗教的世界觀〉一文即指出宗教經驗是一切經驗的根本。西田藉由場所邏輯來解釋「改宗」與「悟道」的經驗,說明宗教領域中的人與眾生、神與人、相對與絕對、有限與無限的關係。西田認為宗教的根本經驗在於「死的自覺」,唯有體會到自我的根本是矛盾性的存在的時候,我們才能超越現行的自我,逆對應地體驗到真正的神。
作者簡介:
西田幾多郎
西田幾多郎(1870-1945)為京都大學教授,是日本京都學派哲學的創始人。其學說融合歐洲哲學的精神、日本傳統思維及佛教思想,被稱為「西田哲學」。其著作《善的研究》涵蓋純粹經驗、形上的實在、倫理的善、與宗教的神,並通過西田獨特的哲學思想將其回歸到純粹經驗之本然的狀態。高橋里美譽之為「恐怕是日本人最初,且唯一的哲學書」。西田重視主體性的思維,曾經提出「純粹經驗」、「場所的邏輯」、「絕對無」等哲學理論。另外,西田透過對西洋的思想與哲學的討論來尋求一個更根本的東西方哲學之共同基礎,從這個基礎來重新定位東西方的思想,試圖建立一個對東西方都具說服力的哲學。他也因此將「日本哲學」提升到「世界哲學」。
譯者簡介:
黃文宏
1998年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現為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專長領域為現象學、詮釋學與京都學派哲學。近年來關於日本哲學的著作為〈論早期西田哲學中「自覺」的基本構造――以〈邏輯的理解與數理的理解〉為線索〉(2012)、〈論日本現代哲學中的「感性論」傾向──以中村雄二郎的「共通感覺」為例〉(2011)、〈西田幾多郎宗教世界的邏輯──兼與新儒家宗教觀之比較──〉(2011)、〈西田幾多郎的「直觀」論〉(2010)、〈西田幾多郎場所邏輯的內在轉向〉(2010)。
章節試閱
〈場所〉(1926)
在當今的認識論當中,人們區別開對象、內容、活動這三個項目,並且討論這三者間的關係,但是,我認為在這種區別的根柢上,人們所思想到的只有隨著時間推移的“認識活動”,以及超越認識活動的“對象”間的對立而已。然而,要主張對象與對象間相互關聯著、形成一個體系,並且自我維持自身 的話,那麼就必須有維持這種體系自身的東西,也必須有讓這個體系在其中產生,並且這個體系可以說是“內存於其中”(に於いてある)的東西。有必須內存於某處,否則有與無將無法區別。邏輯地來看,我們可以區別開“關係項”與“關係本身”,也應該可以區別開“關係的統一者”與“關係所內存於其中者”。試著從活動 這一面來看的話,那麼除了作為純然活動之統一的“我”,以及相對於“非我”的“我”之外,也必須存在著將“我與非我的對立”內在地包含的東西,也就是說,必須存在著讓所謂“意識現象”得以內在地產生的東西。像這種可以說是“理型的容受者”這樣的東西,我倣傚柏拉圖〈蒂邁歐斯〉篇 的話,稱它為“場所”。當然,柏拉圖的“空間”或者所謂“容受的場所”(受け取る場所),與我所名之為“場所”的東西是不能視為等同的。
認為物體存在於空間中,在空間中相互作用,這是極為素樸的思考方式,迄今的物理學也都是這樣來思考的。有些人認為,沒有物體,就沒有空間,空間不外是物體與物體間的關係而已;再者,我們也可以像洛徹一樣,主張空間內存於物體當中。但是,如果這樣來想的話,形成關係者(関係するもの)與關係必須是一個東西,例如,物理的空間就是如此。但是,能讓物理的空間與物理的空間得以關係在一起的,並不是物理的空間,而且物理的空間還必須有“內存在的場所”(於てある場所)。或許有人會認為,處於關係中的存在,當它被還原到關係的體系的時候,只要思想一個由其自身所產生的全體就可以,不需要再去思想一個讓它得以產生的場所。但是,嚴格來說的話,不論是什麼關係,只要它作為關係而成立,那麼就必須有作為關係項的既予物,例如,相對於知識的形式,必須有〔知識的〕內容。就算兩者合一而為一個全體,也必須有映照這種全體的場所。有人或許會說,場所不外是單純主觀的概念而已。但是,只要對象是超越主觀活動並且自立存在的話,那麼,讓客觀的對象得以產生的場所,就不能是主觀的,場所本身必須是超越性的。當我們將所謂的“活動”對象化來看的時候,我們也是將它映照到思惟對象的場所來看。如果連所謂的“意義本身”也被認為是客觀的話,那麼讓意義本身得以成立的場所也必須是客觀的。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樣的東西不過只是單純的無而已。但是在思惟的世界當中,即使“無”也擁有客觀的意義。
當我們思考事物的時候,必須有類似映照事物的場所。首先,我們會認為“意識場域”(意識の野)就是這種場所。要意識到某物,某物就必須被映照在意識的場域當中。因而,我們必須區別開被映照的“意識現象”與能映照的“意識場域”。我們或許可以說,除了意識現象的連續本身之外,並沒有像意識的場域這樣的東西。但是,相對時時刻刻流變(時々刻々移り行く)的意識現象,必須有不變動的意識場域。透過意識場域,意識現象得以相互關聯、相互連結。有人或許會將意識的場域思想為像“自我”(jp. 我)那樣的一個點。但是,當我們區別開意識的內外的時候,我的意識現象必須是在我的意識範圍之內的。在這個意義下的“我”(jp. 私)必須將我的意識現象內在地包含。從上述的意識立場出發,我們就會認可意識的場域這樣的想法。思惟活動也是我們的意識活動。思惟的內容首先就是映照在我們的意識場域中的東西。透過內容指涉對象。當今的認識論者區別開內容與對象,認為內容是內在的,而對象是超越的。對象被視為是超越了所有的活動,並且是在其自身而存在的東西。在這裏,我們走出了意識的場域。對象並不屬於意識的場域。但是,要將意識與對象關係起來,必須存在著將兩者內在地包含東西。讓兩者得以關係的場所必須存在,這樣的話,讓兩者得以關係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如果說對象超越意識的活動,並且是全然在意識之外的話,那麼從在意識之內的我們出發,是沒有辨法思想我們的意識內容指涉著對象這件事,甚至連對象是超越意識活動這件事也不能說。相對於認識對象的世界,康德學派在主觀的方向上思想了“先驗的主體”(jp. 超越的主観)或“意識全般”那樣的東西。但是,我們難道可以說,我們在認識的主觀中超越了意識並且走出了意識場域之外嗎?這〔意識場域之外〕或許是意識場域的極限也說不定,意識場域並不消失。以心理學的方式所思想出來的意識場域,已然是被設想出來的東西(考えられたもの),它不過只是一種對象而已。意識到這種意識場域的意識場域,就算在其極限當中,它也不能被超越。再者,即使是被我們視為具有現實性的意識場域,在其背後也總是有著超越現實的東西。以所謂實驗心理學的方式所限定的意識場域,不過只是屬於可以單純地進行計算的感覺領域而已。但是,意識必須包含意義,回想起昨日的意識,在意義上就必須包含著昨日。因而,意識也可以說是全般者的自我限定。就算是感覺的意識,就其包含著之後接受反省的可能性而言,它也可以說是一種意識現象。如果我們認為“全般者”作為極限是無法達到的話,那麼我們也必須主張“個物”是無法達到的極限。
在康德學派裏面,認為認識是透過形式來統一質料,但是在這種思想的背後,必須已然假定了主觀的構成活動,認為形式是主觀所具備的東西。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認識的意義就無法形成。單純地透過形式所構成的東西,不過只是“超對立的對象”而已。再者,如果主張“客觀的形式”構成“客觀的質料”的話,那麼這是客觀的活動,它並不能夠產生認識的意義。“形式與質料的對立”與“主觀與客觀的對立”不能直接視為等同。要形成判斷活動的對象,除了形式與質料的對立之外,還必須再加上一種不同意義的對立。形成判斷之直接內容的東西,必須是真或偽這樣的東西。讓形式與質料的對立得以產生的場所,必須不同於讓真偽的對立得以產生的場所。在產生認識的場所當中,不僅要區別開形式與質料,兩者的分離與結合還必須是自由的。在這個情況下,相對於超對立的對象,我們可能會認為,主觀性是外在所附加的。就像拉斯克一樣,相對於根本的邏輯形式,他將全然非邏輯的體驗對象,思想為“根本的質料”。但是,就如同拉斯克本人所承認的,認知(知る)也必須是體驗的一種。就算主張“體驗的內容”是“非邏輯性的質料”,它仍然不等同於“感覺的質料”。與其說體驗的內容是非邏輯性的,不如說它是“超邏輯性的”;與其說它是超邏輯性的,不如說它是“包邏輯性的”。藝術與道德的體驗,也可以這樣來主張。認識的立場也必須是“體驗”在自身之中映照自身的一種表現。認識不外是體驗在自身之中的自我形成。形式與質料的對立關係在體驗的場所當中產生。如此在自身之中無限地自我映照的東西,自身是無而包含無限的有的東西,它是真正的自我,所謂主客的對立就是在其中產生的。這樣的東西既不能說是“同”,也不能說是“異”,既不能說是“有”,也不能說是“無”,它不能為所謂邏輯的形式所限定,反而是讓邏輯的形式得以產生的場所。不論我們將形式推進到多遠,都沒有辨法超越所謂的形式之外。真正的形式的形式,必須是“形式的場所”。亞里斯多德在〈靈魂論〉中,傚法柏拉圖學院,將「精神」思想為「形相的場所」。這種可以說是自我反照自身的鏡子的東西,並不只是知識產生的場所而已,情感與意志也在其中產生。當我們談到體驗的內容的時候,大多數的情況下多已經把它給知識化了,因而它也被思想為“非邏輯性的質料”。真正的體驗必須是完全的無的立場,必須是離開知識的自由的立場,在這個場所當中,情意的內容也被映照出來。知情意都被認為是意識現象,就是基於此。
如果我們如上述來思考場所的話,那麼我認為“活動”是在被映照的對象與能映照的場所之間所出現的“關係”。當我們只考慮到被映照者的時候,那麼它不過是某個沒有任何作動的單純對象而已。但是,即使是在這種對象的背後,也必須存在著映照這種對象的鏡子,必須有對象的存在場所(対象の存立する場所)。當然,如果這個場所只是純然能映照的鏡子,並且對象只是內存於其中的話,那麼我們就無法看到作動的對象。在可以說是全然自我淘空(己を空しう),並且映照一切事物的意識全般的場域當中,所有的一切作為純然認識的對象,之所以被思想為是完全超越活動的存在,就是基於此。但是,如果意識與對象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話,我們就不能說,意識映照對象這個事情,要主張對象內存於意識更不可能。因而人們將兩者之間的連繫思想為“判斷活動”。一方面不僅必須有超越活動的“對象”,另一方面也必須有超越活動並且將活動包含在內的“意識場域”。而當我們認為意識全般的場域容受對象並且是無限廣大的時候,那麼對象在意識全般的場域當中,就可以取得種種不同的位置,並且能夠映照在種種不同的形式當中。在這裏,對象以種種不同的方式接受分析、受到抽象,而所謂“意義的世界”就產生了,而這種在種種不同的位置、種種不同的關係中來映照〔對象〕這件事,在某個側面下,可以思想為“判斷活動”。因而,當超越的對象與意識全般的場域相互分離,並且活動不能夠屬於其中一端的時候,人們就設想出了作為“活動的統一者”的所謂“認識主觀”。從常識的角度來看,如果物內在於空間,既然物與空間是不同的,那麼物在空間中就能夠內在於種種不同的關係中,並且可以以種種不同的方式來改變它的形狀與位置。在這裏,我們一定會在物與空間之外,再思想“力”那樣的東西。而如果我們可以將擁有力的物思想為力的本體的話,那麼也可以將力歸屬於空間來思想物理空間。我就想要試著將“認知”歸屬於意識的空間來思考。
迄今的認識論,都是從主客對立的思想出發,並且將“認知”思想為“透過形式來構成質料”,取而代之地,我想要試著從“在自我之中映照自我”這種“自覺”的思想出發來看。我認為在自我之中映照自我是“認知”的根本意義。從對自身之內的認知,可以達到對自身之外的物的認知。對自我而言是既予的東西,首先必須是在自我之中既予的。也許有人會將“自我”思想為某種“統一點”,並且將內存於自我意識的“認知者與被認知者”、或者說“主與客”、“形式與質料”思想為相互對立。但是,這樣的統一點不能夠稱為“認知者”,它已然是某種對象化了的東西,只能是“被認知者”。就算設想無限的統一方向來取代這種統一點的想法,情況也是一樣的。“認知”首先必須意謂著“內在地包含”(内に包む)。但是,當“被包含者”相對於“能包含者”是外在的時候,就如同物體內在於空間一樣,被包含者就只是存在而已(単にあるといふこと)。當能包含者與被包含者是一的時候,無限的系列才能產生。而當這個“一”,在其自身當中,無限地包含質料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思想到無限的作動者、純然的活動。然而,這樣的“一”還不能夠說是“認知者”。唯有將這種自我內存於自身的東西再內在地包含的時候,才能夠說是認知。就形式與質料的關係來說,單單只是形式的構成,並不能說是認知,認知必須將形式與質料的對立內在地包含。如果我們將質料也視為低階的形式的話,那麼“認知者”也可以說是“形式的形式”,它必須是連純粹形式與純粹活動也超越,並且讓純粹形式與純粹活動得以在其內在產生的場所。像拉斯克之所以認為主觀是客觀對象的破壞者,也是基於此。就如同物體在空間中具有可分性一樣,思惟的對象在思惟的場所中也可以具有可分性。就像物體在空間中,在種種不同的意義下具有無限可分性一樣,思惟的對象在思惟的場所中也是可分的。或許有人會認為,如果我們以上述的方式來思考“認知者”的話,那麼主客對立的意義將會消失,在主觀中會失去“統一”與“活動”的意義,“主觀”的意義也可以說會跟著消失。現在,我們沒有辨法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單純地就物內在於空間這種情況來說,物與空間是互為外在的,空間中並沒有主觀的意義。可是,當物的本體性(jp. 本体性)推移到物所內存於其中的場所關係的時候,物就被還原為力。但是,“力”就必須思想到力的本體,關係必須思想到關係項。這個所謂的本體到底要到哪裏去尋找呢?如果我們在本源的物(元の物)當中來尋找的話,這樣就會殘留著完全無法還原為力的物。如果我們將它〔力的本體〕歸因於空間本身的話,那麼它就只能是作為空間的關係項的“點”而已。然而,如果關係的本體只是“點”的話,“力”就必須消失。真正將力的關係內在地包含的東西必須是像“力場”那樣的東西。而在力場當中,所有的線都必須擁有方向性。在將純粹活動內在地包含的認識的場所當中,一切的現象也都必須擁有方向性。透過將認知者思想為包含者,主客對立的意義就會消失,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人們將場所思想為外在於被包含者的場所的緣故。純然空虛的空間是無法真正地將物理現象內在地包含的。真正能夠將種種對象內在地包含的東西,就像種種的形式(jp. 形)在空間中產生一樣,它必須在自身之中映照出自身的形式。這麼一來,所謂「內存在」(「於てある」)的意義或許可以說就消失了,包含對象且無限展延的“場所”的意義也消失了。唯有內在於將一切認識對象內在地包含並且又與一切認識對象分離的意識場域當中,這兩個意義〔內存在與場所〕才能夠結合。
如果認知是在自身之中的映照自身,並且活動可以在被映照者與能映照的場所的關係當中來觀看的話,那麼拉斯克所說的全然超越了活動的“無對立的對象” 究竟是什麼呢?就算這樣的對象也必須是內存於哪裏的。我們要認識“有”,就要對“無”有所認識。但是,相對於“有”所認識到的“無”,仍然是“對立的有”。真正的無必須是包含這種有無,並且是讓這種有無得以產生的場所。否定“有”並且與“有”相對立的“無”,並不是真正的無,真正的無必須是“有”的背景。例如,相對於紅色的非紅色也是一種顏色。擁有顏色的東西、顏色所內存於其中的東西,必須是沒有顏色的東西,它必須是紅色也內存於其中,非紅色也內存於其中的東西。我認為可以將同樣的思想,超越作為認識對象的限定,也推進到有無的關係上。這種「內存在的場所」(「於てある場所」),在顏色這個情況中,它被思想為一種物,就像亞里斯多德一樣,我們也可以說性質內存於物。但是這麼做的話,場所的意義就失去了,而物就成為擁有屬性的東西。反之,如果將物完全地解消於關係之中,那麼我們就會將包含有無的東西思想為一種活動。然而,在活動的背後仍然必須有“潛在的有”。雖然我們可以相對於“本體的有”而主張“無本體的作動”、“純粹的活動”,但是,如果將活動除去潛在性,那麼活動將會消失。讓這種潛在的有得以產生的背後,還是必須要思想“場所”那樣的東西。如果物擁有某種性質,那麼這個物就不可能包含著與這某一性質相反的性質。然而,作動必須在其中包含著反對,變動是往其反對面變動而去。因此,包含有無的場所本身,也可以直接地思想為活動。但是,要觀看到一個活動,在其根柢當中必須限定一個類概念,唯有內在於一個類概念當中,我們才能觀看到相反的東西。在活動背後的場所並不是真正的無,也就是說,並不是純然的場所,而是擁有某種內容的場所或者受限定的場所。在活動中,“有”與“無”雖然結合在一起,但是我們不能說“無”包含“有”。在真正的場所當中,某物不僅往其反對面推移而去,而且這個往其矛盾面的推移還必須是可能的,也就是說,走出類概念之外是可能的。真正的場所不單單是變化的場所,它是生滅的場所。當我們越過類概念,進入生滅的場所的時候,作動的意義就已然失去,留下的唯有觀看而己。當類概念被視為場所的時候,潛在的有就無法去除,我們只能觀看到作動者,但是,在連類概念也映照的場所當中,我們所觀看到的並不是作動者,而是將作動也內在地包含的東西。真正的純粹活動並不是作動者,而必須是將作動也內在地包含的東西。潛在的有並不是先在的,現實的有才必須是先在的。在這裏,我們可以觀看到讓形質得以融合的“無對立的對象”。
〈場所〉(1926)
在當今的認識論當中,人們區別開對象、內容、活動這三個項目,並且討論這三者間的關係,但是,我認為在這種區別的根柢上,人們所思想到的只有隨著時間推移的“認識活動”,以及超越認識活動的“對象”間的對立而已。然而,要主張對象與對象間相互關聯著、形成一個體系,並且自我維持自身 的話,那麼就必須有維持這種體系自身的東西,也必須有讓這個體系在其中產生,並且這個體系可以說是“內存於其中”(に於いてある)的東西。有必須內存於某處,否則有與無將無法區別。邏輯地來看,我們可以區別開“關係項”與“關係本...
作者序
第一篇選文〈作者序〉收錄西田幾多郎自己撰寫的「序」言。選擇「作者序」的主要考慮是「西田思想的分期問題」,也是給予初次接觸西田哲學的人一個概觀。西田哲學雖然統稱為「場所哲學」,但是西田思想仍然重點的轉移與深入,這關係到西田哲學的分期。表面上來看,日本學界對西田思想階段的分期是相當分歧的,從一期說到六期說的主張都有。但是,筆者個人認為哲學思想本身很難有嚴格意義下的「轉折」或「分期」發生,思想的分期其實只有幫助理解的好處,因而任何的分期總是帶著研究者的興趣與目的,不能執著於分期。真正的問題只在於,哪一個分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西田的思想發展及各個重要的詮釋者的觀點。就這一點來看,學者的解釋雖然各各不同,但西田如何理解、劃分自己的哲學,就客觀地介紹西田的思想而言,仍然是最重要的,或至少一定會牽涉的部分。而西田的自我理解、自我解釋最明白地表現在其「作者序」當中。西田在這裏陳述出了自己思想的發展、計畫、不足與所遭遇到的困難等等。這是哲學家對自身哲學思想的分期,也是筆者最感興趣的地方,因為在這裏,我們的思考才可以介入。至於一些文獻資料的說明,則以「題解」的方式置於各個「序」的最後。
談到西田思想的分期,最常會提到的就是西田1936年《善的研究》的「新版序」,在這裏,西田將自身思索的發展區分為五個立場:「純粹經驗」、「自覺」、「場所」、「辯證法的全般者」與「行為的直觀」。
純粹經驗的立場到《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我藉由費希特的事行的立場,而推進到絕對意志立場,更進一步地,在《從作動者到觀看者》的後半部當中,透過希臘哲學一轉而到達「場所」的思想。在這裏,我找到了將我的思想予以邏輯化的端緒。「場所」的思想具體化為「辯證法的全般者」,「辯證法的全般者」的立場則直接化為「行為的直觀」的立場。
這五個「立場」的說法嚴格說來是五個「基本概念」。「純粹經驗」時期,主要以《善的研究》(1911)為中心,在《善的研究》當中可以看到西田哲學的基本型態。自《善的研究》以後,西田就比較少談「純粹經驗」,而轉向體驗與邏輯、直觀與反省、價值與存在、事實與意義的結合問題,這形成了「自覺」的時期。這一期的著作主要以《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1913-1917)為主,包括《思索與體驗》(1914)、《意識的問題》(1920)、《藝術與道德》(1923)。誠如西田在《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的改版序(1941)中所說:「雖然種種不同的方向與角度皆暗示著最後的立場,但是,這最後的立場並沒有被真正地把握,因而沒有辨法從這裏積極地來解決問題。」對於這「最後的立場」西田在思想上經歷了一個摸索的過程,終於在《從作動者到觀看者》後半部的1926年的〈場所〉論文中確立為「場所」,這形成左右田喜一郎所說的「西田哲學」。往後西田的哲學思考,即指向將「場所」的立場予以具體化的階段。然而,「場所」概念並不是一成永成的,它也在發展之中。西田一方面依據「場所邏輯」建立「場所哲學」的體系,一方面也在實際的思考中探索著「場所」更深一層的意義,這時期的論文主要包含《從作動者到觀看者》後半部、《全般者的自覺體系》(1930)、《無的自覺的限定》(1933)與《哲學的根本問題――行為的世界》(1933)。從《全般者的自覺體系》的原始構想是「一個哲學體系的企圖」可以看出西田系統化自身思想的強烈意圖。標示西田另一個階段的「辯證法的全般者」概念,則主要是從收於《哲學的根本問題續編――辯證法的世界》中的〈辯證法的全般者的世界〉(1934)一文開始。在這裏西田思想經歷的一個「轉向」,隨著這個轉向的發生,我們可以從西田在1935年的《哲學論文集第一》的副標題「邁向哲學體系的企圖」,知道西田的思想再進入了第二次系統化。最後的第五個概念則是從1935年以後一直到1945年一系列以「哲學論文集」為總標題所收的論文,它包含了《哲學論文集第一――邁向哲學體系企圖》到《哲學論文集第七》。在這裏「行為的直觀」是重點,它標示著西田歷史哲學的展開,也是純粹經驗徹底化的結果。「行為的直觀的世界、製作的世界就是真正的純粹經驗的世界。」
就思想的發展來看,西田哲學開始於「純粹經驗」的提出,「我的思想的傾向自《善的研究》以來就已然確定了。」。但是,這個時候的西田仍然還沒有完全擺脫心理主義,邏輯的自覺也不十分充分。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形成了「自覺」的時期,然而這個時候的「自覺」,即使前進到「絕對自由意志」,也還沒有到達西田最終所指向的立場,西田的最終立場出現在1926年的「場所」論文。然而「場所」的意義是在具體的思惟中發展出來的。西田經歷兩次「系統化」的想法,分別相應於轉向前與轉向後。相對於第一、二、三期都是從「自我來看世界」的立場,第四、五期則是「從世界來看世界」的立場。這樣來看的話,西田哲學的形成是在自我批判之下所形成的哲學,它並不是一直線地往一個方向而去,而是「從自我來看世界」先徹入自我的內部,從這裏再「從世界來看世界」。誠如西田於1930年《全般者的自覺體系》的「序」中所說,「由於我的思想是一步步發展出來的,所以前面的論文全部都應該透過後面的論文來加以補充與修正。」(NKZ 4:3)這一點應該適用於西田哲學全部。如果我們以「心學」的路為徹入「自我之內部」,「史學」的路為指向「歷史現實世界」的路的話,那麼在西田身上,這兩條路並不是衝突的,也不是直線的,而是圓環的,心學的發展必然走向史學,也必須透過史學來取得其最終的意義。
這樣的話,筆者個人認為「兩段三期」的說法,在理解西田思想的發展上是有幫助的。「兩段」的說法是根據西田所指出的自身「思惟方向的改變」,一反於「第一階段」的深入自我的內部,「第二階段」的西田轉向歷史的現實世界。前者類似中國哲學中「心學」的道路,後者則類似「史學」的道路。但是這種「轉向」嚴格說並不是立場的「轉變」,而是立場的「深化」。此外,我們也可以根據西田個人獨特「場所邏輯」的提出為中點,區別開「三期」,以場所邏輯提出之前,探討西田如何轉化希臘哲學、新康德學派等人的哲學(初期);場所邏輯提出、形成與西田的第一次系統化場所邏輯的嘗試,探討其所遭遇到的困難(中期);之後場所邏輯轉向「從世界來看世界」的歷史實在的邏輯,場所邏輯在這裏取得其最終的形式(後期),而西田在這裏也再次地肯定「行為的直觀的世界、製作的世界就是真正的純粹經驗的世界。」三期的想法主要是在第一階段中,再區分開場所邏輯的成立之前(初期)與場所邏輯的內部發展(中期與後期)。「兩段三期」的說法就像九流十家一樣,並不是真有五個不同的階段,也不是有兩種不同的分法,而只是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期。原則上來看,第三期則與第二階段是一致的。第一階段(或可稱為「前期」)包含「初期」與「中期」,第二階段(或可稱為「後期」)則與三期分法中的「後期」大致上一致。
西田第一階段(前期)的思想主要是從類似心理學的想法開始,經過先驗哲學的反省,進行知識論的奠基工作。對西田來說,前期(純粹經驗、自覺、場所)的重點,表現在對康德先驗哲學的超克,特別是李克特所代表的新康德學派。相對於「李克特的康德」,回歸「康德的康德」,乃至「超越康德」,是西田思想的一個主軸。場所邏輯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來的,並逐步建立為一種「全般者的自覺體系」。就思惟的方式而言,它是一種內向的思路,也就是說,沿著意識的方向深入,問向最根源的意識,這在西田思想的初期是「絕對自由意志」,在中期則是「絕對無」,絕對無是西田中期內向之路所達到的最終境界,其思惟的考慮主要開始於知識的奠基工作,而終於形成一個形上學的體系。從〈場所〉論文來看,中期的西田場所傾向於靜態的表達,但絕對無並不是單純的觀想。西田在〈全般者的自覺體系──總說〉中也稱其為「心之本體」,是「絕對的無,也是絕對的有」。但是,「絕對無」與「歷史世界」的關係是什麼?與新康德學派哲學所遭遇到的問題一樣,西田也同樣遭遇到先驗哲學與歷史哲學的連結問題。西田的綜合表現在第二階段,場所邏輯在這裏擴張為一種「歷史實在的邏輯」。這開始於〈我與汝〉論文中的對「原歷史」(Urgeschichte)的討論。但據西田自述,〈我與汝〉的轉折是不充分的,在我與汝之間,還必須思考一個第三者「彼」。這形成了西田「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與「辯證法的世界」。這樣來看的話,心學的發展必然走向史學,這無關於西田個人的意志,而是實事本身的客觀要求。無論如何,西田的場所邏輯經歷兩次系統化的努力,這兩次的系統化工作,分別區隔開了中期西田與後期西田的差異。同一的邏輯之所以能有造成兩次的系統化,是因為場所邏輯內部有一個轉折。中期的西田以意識為述詞,從深入自我的內部,發現存在於超越的述詞面的絕對無,場所在這裏主要的意義是「述詞」,構成所謂的「述詞邏輯」。後期的西田轉而從包攝自我與環境的全體或「辯證法的全般者」來思想,突顯了場所的「媒介作用」,自覺的主體由述詞往「繫詞」或「媒介者」推移,形成所謂的「繫詞邏輯」,這是西田場所哲學內部的轉折。
這樣來看的話,筆者兩段三期的說法,其實是根據不同的判準將第一階段(或也可稱為「前期」)再細分為初期與中期;第二階段(亦可稱為「後期」)大致上與後期一致。就西田的著作來看,「初期」由《善的研究》中類似心理主義的想法開始,還未完全區別開心理程序與邏輯程序的差別。隨後西田透過與古希臘哲學、新康德學派思想的對決,最終在《從作動者到觀看者》中的〈場所〉,形成場所邏輯的想法,中期的西田開始於這裏。據西田自述,他在〈場所〉這篇論文當中,找到了系統化自身思想的「端緒」,在中期的階段「場所」概念慢慢地由述詞轉移到繫詞,由此端緒而形成場所邏輯的第一次系統化,這屬於場所邏輯內部的形成與發展。後期西田的思想則開始於《哲學的根本問題續編》中「從世界來看世界」的立場。場所邏輯在這裏取得其最終的形式──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思惟方式的轉變是比較根本性改變。西田的許多哲學內容,相應地也可以區別開前期(第一階段)與後期(第二階段),例如:「前期的藝術哲學」與「後期的藝術哲學」、「前期的歷史哲學」與「後期的歷史哲學」,甚至「前期的自覺」與「後期的自覺」等等。細分出兩段三期的好處在於可以釐清其中的轉折,了解西田哲學的建立與轉折的必要性。
從「作者序」中,我們也可以知道,西田文章的樣式往往先是一篇篇獨立的論文,然後再集結成書。所以各篇文章自成一體,而歸屬於一個更大的思想體。原則上,本選輯可以視為是西田哲學的導論,也希望慢慢補足其他的論文。
第一篇選文〈作者序〉收錄西田幾多郎自己撰寫的「序」言。選擇「作者序」的主要考慮是「西田思想的分期問題」,也是給予初次接觸西田哲學的人一個概觀。西田哲學雖然統稱為「場所哲學」,但是西田思想仍然重點的轉移與深入,這關係到西田哲學的分期。表面上來看,日本學界對西田思想階段的分期是相當分歧的,從一期說到六期說的主張都有。但是,筆者個人認為哲學思想本身很難有嚴格意義下的「轉折」或「分期」發生,思想的分期其實只有幫助理解的好處,因而任何的分期總是帶著研究者的興趣與目的,不能執著於分期。真正的問題只在於,哪一...
目錄
凡例
譯注者導讀
生平與著作
選文解說
選文
作者序
《善的研究》序
《思索與體驗》序
《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序
《意識的問題》序
《藝術與道德》序
《從作動者到觀看者》序
《全般者的自覺體系》序
《無的自覺的限定》序
《哲學的根本問題──行為的世界》序
《哲學的根本問題續篇──辯證法的世界》序
《哲學論文集第一──邁向哲學體系的企圖》序
《續思索與體驗》序
《哲學論文集第二》序
《哲學論文集第三》序
《哲學論文集第四》序
《哲學論文集第五》序
《哲學論文集第六》序
《哲學論文集第七》序
二、絕對自由意志
三、種種世界
四、場所
五、場所邏輯與宗教的世界觀
西田幾多郎年譜
譯注者後記
凡例
譯注者導讀
生平與著作
選文解說
選文
作者序
《善的研究》序
《思索與體驗》序
《自覺中的直觀與反省》序
《意識的問題》序
《藝術與道德》序
《從作動者到觀看者》序
《全般者的自覺體系》序
《無的自覺的限定》序
《哲學的根本問題──行為的世界》序
《哲學的根本問題續篇──辯證法的世界》序
《哲學論文集第一──邁向哲學體系的企圖》序
《續思索與體驗》序
《哲學論文集第二》序
《哲學論文集第三》序
《哲學論文集第四》序
《哲學論文集第五》序
《哲學論文集第六》序
《哲學論文集第七》序
...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9收藏
9收藏

 21二手徵求有驚喜
21二手徵求有驚喜




 9收藏
9收藏

 21二手徵求有驚喜
2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