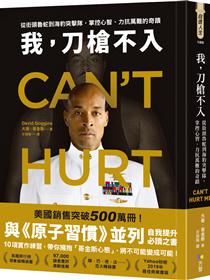伙夫張七(二)
過後幾天,張七得了一個新的綽號,很快地傳遍後指部。原來是那天和素梅一起騎機車跑街,被阿兵哥瞧到,大家議論封的。
「是什麼……丈來的?」張七苦苦地思索。
這時夏天的蟬兒們默契十足,突然齊聲合唱,吵到了他。張七定定神,尋找素梅騎機車的蹤影,早已不知去向,只見晴空萬里,點綴著一二片殘破的白雲,像被烈日烤得七零八落。
張七感到有點暈眩,走到樹蔭下,找一塊平坦的岩面,坐下來休息。
「什麼……丈?」他繼續想。
「丈人? 不對,國丈? 不,表丈……對嗎? 不︙︙應該是『婊丈』!」這些王八羔子! 事隔許久,張七仍舊憤恨不平。
「人家素梅可是孝女哪,哪像這些沒心肝的小夥子,得了便宜還賣乖!」
最令人生氣的是那阿土,也隨著大家起鬨。就在二個月前左右他退伍的前夕,張七找他結算欠款,還差四百元,阿土雖然發誓回家後立刻寄過來,最後卻嬉皮笑臉地加上一句:
「士官,你都可以對那婊子那麼慷慨,但對我這個打炮的忠實夥伴,卻一
分一毛的計較……」
張七氣那粗鄙的字眼,作勢要揍他,阿土一溜煙就跑了,結果退伍至今,
音訊全無,更不用說寄錢來還債了。
「唉!」張七嘆口氣,世事作不準的,人心也測不準的,什麼承諾,什麼
感恩,不可當真,隨時起變化的。就像月亮,有圓有缺,氣候有熱有冷,日子一久,張七感覺到素梅對他的態度也變得冷淡下來,他想成家的話更加說不出口。
「如灶中的火燄,由熾轉淡,最後熄了。」張七自我解釋著。可是他清清
楚楚記得,就在這股火燄灰滅之後,另一股大火又熊熊燃起。
是愛或欲望作祟? 張七也搞不懂。白天他忙著煮大夥的三餐,雖然顯得魂不守舍,大致也還過得去,但一到夜晚,腦海裡的素梅立刻變得鮮明活潑起來。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笑著、躺著、呻吟著,或辦完事攏著頭髮,整理衣服的樣子,也可以聽到她哼著山地小調,訴說著老家的種種……一會兒又聽到素梅翹著腿、嗑瓜子,和別的女郎聊天,甚至跟阿兵哥打情罵俏……都栩栩如生,而許多景象是張七前所未見的。這把他嚇壞了,他以為自己著了魔,嘗試去阻止自己的頭腦,但幻想就好像下坡無人拉住的板車,顛簸著衝下去,力大無比。
於是,中了邪似的,每天匆匆用完中餐,他便趕往八三么。他沒有買票,
只是站在一旁,無神地望著素梅房間外排隊的人群,每進出一個,胸中便點燃一個火苗,七八個火苗總匯一起,火勢覆天蓋地,延燒他的毛髮、肌膚、血液、骨骼……最終剩下一片灰燼。直到傍晚時分,他再拖著疲憊的身子返回廚房作菜。這樣日復一日。約莫經過一個星期,張七做一個怪夢,夢中爹爹拉著板車,七、八歲左右的他坐在上頭,後面一堆人拿刀、拿棍追趕著。爹好緊張飛奔著,還不時轉頭看他的寶貝兒子有無坐穩。跑呀跑,爹不見了,換成張七自己拉著車,上面側坐著素梅,一群共匪扛著槍追著。他跑得上氣接不了下氣,聽著追兵的腳步近了,猛一回頭,意外瞧見素梅正低頭把玩著手帕,嘴角微笑著……那天早上醒來,在床上反覆思量,終於思念素梅的心戰勝一切,張七敲定,是該見她一面的時候了,順便把事情弄個明白。
灰色地帶
「心理學、經濟政策、貨幣理論、總體分析……」阿學一一細數,全都溫習得差不多了,哦,當然還有法文,他心裡升起了幾分期待,說不定彭的造訪對他的法文大考也能有所助益呢。彭在電話裡說,他會晚上十點卅分左右抵達。阿學看看手錶,尚差十分鐘,現在應該在爬坡的路段了,這個老外,哪有人這麼晚才來初認識的朋友家?
「有禮無體!」如果被老爸知道,他一定這麼說。不過這樣講也不見得公平,阿學記起來,上回在火車上,彭說他白天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晚上還在五星級的飯店兼差彈奏鋼琴,說起來可是一個勤奮又有才藝的好青年呀!
這時阿學腳邊的雜草急驟地動一下,接著,唰的一聲,一小團黑烏烏的東西跳過他穿拖鞋的腳ㄚ子,把阿學嚇了一大跳。過幾秒鐘,他心情平緩下來,定神看那小塊黑影,居然就在左腳邊一呎之遙靜靜地趴著。他心裡有點譜了,彎下腰來近距離辨認,沒錯!是隻青蛙,也是和他一樣出來透透氣、乘乘涼。夏日啊! 夏仙子的魔杖把他這便宜租來的民房四周弄得神氣活現,一會兒這邊蟲鳴,一會兒那邊蛙叫,好不熱鬧。最值得一提的是院子裡的夾竹桃像皇后般傲然豔麗的綻放,還有那七里香就是香香公主的化身,渾身上下散發出濃郁的體香,引人無限遐思。阿學陶醉地聞著,琢磨那味道……
「嗯,真叫人痴狂……」他搖頭晃腦地想著。隨後他聽到快走的腳步開始爬著階梯,上等的皮鞋跟碰撞著老舊的混凝土,發出輕脆聲響。估量著差不多時,阿學抬起頭來,一張溫和的笑臉恰好伸出最後一道台階,香水味也迎面飄至。
「Pardonnez-moi, j'ai du vous faire attendre pendant longtemps!」(中文:對
不起,讓你久等了!)彭對他說。
阿學趕緊起身迎接他:「Ce n'est pas grave, Je suis seulement ravi que vous puissiez venir.」(中文:沒關係,我很高興你能來到。)
引彭進了斗室,藉著燈光,阿學才看清楚彭穿著正式黑色的西服,結著領花,一副演奏家的架勢,頗為氣派。大概是趕路的緣故吧,髮際的汗水清晰可見。彭拿出一條絲手帕,一邊擦拭,一邊脫掉外套,那外套他拿在手裡好一會,雙眼四處張望,不知如何處置才好。
阿學看了,笑了出來,這斗室四公尺見方,擺一張雙人床,一張桌子,二隻椅子和一個置物架,已沒有多餘的空間,他自己的衣服都收拾在床下的行李箱中。
「Permettez-moi de vous aider!」(中文:讓我來!)
阿學對彭說,接過外套,隨手掛在椅背上。
「Oh, merci, j'aurai du y-penser plus tôt.」(哦! 謝謝,我早該想到。)彭帶著歉意。
「Faites comme chez vous et asseyez-vous.」(中文:請別拘束,坐吧!)阿學順手倒一大杯冷開水給他。
彭咕嚕咕嚕一下子喝光它。
「Êtes-vous fatigué?」(中文:累嗎?)阿學關心地問。
「Je suis ok.」(中文:還好。)
「Vous venez directement du bureau ?」(中文:剛下班?)
「Oui!」(是的!)
「Qu'avez-vous joué aujourd'hui?」(中文:今天彈了哪些曲子?)「Du
Chopin principalement.」(中文:大部份是蕭邦的曲子。)
蕭邦,這古典樂阿學也是有點涉獵的,於是他倆從蕭邦、舒伯特,聊到莫札特和柴可夫斯基,這柴氏和他的女性贊助者,到底誰對誰有愛意,還引起他們兩人一小段的辯論。
花開
現在少了老伴,沒人和他對談,空間奇怪的變大了,到處都可見寂寞的影子。他也練就了自言自語的本領,彷彿這樣可以增添一些人氣。不過今天不會太無聊,因為他的小學同學阿基和阿平會過來抬槓。
謝伯心有旁騖地翻起報紙。每隔三、五分鐘便抬頭看一下時鐘,分針像老烏龜似的,舉步維艱。等到九點四十五分,他起來準備老人茶具。十點正,他在屋內踱起方步,不時引頸眺望屋前來路。超過十分鐘,他隨即破口大罵:
「三小咧! 這兩ㄟ猴三,死去叨位? 這麼不準時!」
到十五分,兩人邊說邊笑走了進來。
「三八耶! 林北等了一個上午!」謝伯有些惱怒。
「哎喲! 外邊是大晴天,怎麼謝家卻有一個颱風。」阿基頑皮地向阿平使個眼色。
「真是人在禍中不知福!」阿平坐下來搖頭笑著說。
「共襄小!一來就胡說八道!」
「謝耶! 你沒聽過嗎? 中年喪偶比得樂透還難得!」
「是啊! 可以名正言順討第二個老婆!」
兩人像唱雙簧,有來有往。
「幹恁姥母! 阮某才死二個月,你們不怕她上來找你?」
「驚小! 我是為了殷尪好!」阿平挺起胸膛,理直氣壯。
「是啊! 伊要去前,都還擔憂沒人照顧你。什麼阿綢,這才是最好的辦法。恁某地下有知,一定贊成!」阿基說得振振有詞。
謝伯沉默下來。
「謝耶! 換作是我,絕對忍受不了一個禮拜冰冷的被窩。」阿平接著說。
「是啊! 你兒子媳婦都不在身邊,一個人孤孤單單,未免太可憐了!」阿基誠懇地望著他,一副真心為他好。
謝伯有些感動:
「可是這把年紀,都已超過六十了。」
「有什麼關係,有人七十、八十都還續弦,你也不過六十三。」
「是啊! 我們不要找二、三十歲的,四十歲總可以吧?」
謝伯心意有些動搖了。
「就這麼說定,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隔壁住著一位媒人婆,這種事她最內行。隔壁村的老陳,一個月前死某,她立刻成功地介紹了一位。」阿平打鐵趁熱,做了結論。
他們三人繼續天南地北,從小時糗事一直聊到最近的政治醜聞。謝伯今天心情特別好,難得一掃多日來臉上的陰鬱,笑得十分開朗。
等到他們兩人離開後,空氣又結凍起來。謝伯開始想,這也許是不錯的主意。他有點愧疚地看著老伴的遺像,心裡琢磨要不要在她牌位前擲筊,問問她的意見? 嘀咕好久,舉棋不定,後來就算了。當天晚上懷著幾分的興奮,竟然怎樣都睡不著。
苦等了兩個禮拜,毫無訊息。謝伯猛叩阿平,問他進行得怎麼樣?
阿平耐心地和他說:「等等,等等,總要給媒人婆一些時間!」
千熬萬熬又過了兩個禮拜,終於阿平帶媒人婆來了。
媒人婆一坐下,笑著恭喜謝伯:
「謝桑,你運氣真好。現在有三個資料供你選擇。」
「才三個?」謝伯一臉失望的表情。
「三個咧! 不錯啦! 你以為是皇帝選妃,一堆人排隊哦?」媒人婆白他
一眼。
「謝耶,多少人不重要,我們只要選一個對的人。」阿平趕緊安慰他。
看到謝伯無奈地點頭稱是,媒人婆拿出第一張照片。年輕漂亮的外表,讓謝伯眼睛為之一亮。
「林小姐,三十五歲,是大陸姑娘,老芋仔的遺孀。她要求的條件是:千萬家產,百萬聘金,明媒正娶。」
謝伯的眼神立刻黯淡下來。阿平也說:
「搶錢嗎? 這種唯利是圖的女人再漂亮也不能娶。」
「那麼第二個是張小姐,五十二歲……」照片中的女人是一般歐巴桑,笑得憨憨的。
「五十二歲? 不要! 不要! 娶來做阿祖嗎?」謝伯憤怒至極,大聲吼起來,把其他兩人嚇一大跳。
「那就剩最後一個,王小姐,四十一歲。」照片中的她長得清清秀秀,皮膚白皙。
「有什麼條件?」謝伯看來還算滿意。
「禮金二十萬。家裡要有洗衣機、烘乾機和洗碗機。」
「洗衣機是有的,不過烘乾機和……」
「謝耶,買了就有了,不是問題。」阿平搶著說。
「那麼我來約對方見面,看看有沒有緣份。」媒人婆初步任務已經達成。
今天是個重要的日子
佳姿被健雄上浴廁的聲音吵醒,心中隱隱約約有一絲滄桑的感覺。她的雙腿重拾大抱枕夾著,側身蜷曲,試圖回想夢中情景。努力好久,只有灰濛濛的一片,中間點綴著幾片亮點。
賴了廿分鐘的床,懶洋洋地起身,走到廚房打開冰箱,把昨夜的剩菜剩飯一一整齊排放在便當裡。
「再煎個荷包蛋吧!」她想。
正在熱鍋,走道上飄來健雄的話語:
「我上班去了!」隨著關門,空氣中送來一縷男人的香水味,是春天嫩草的氣息。
「今天下班後肯定去見富美那個妖精了!」她惴度。
說來好氣又好笑,大約五年前吧? 她拿著家裡的帳單去公司找會計,想請她辦理轉帳手續。湊巧健雄站在富美的辦公桌旁,他們兩人看到她走進來時,彼此互望的一個神情被她瞧在眼裡,她的心突然莫名地揪緊,當下明白了幾分。強忍了半天等健雄回家,原來計畫用旁敲側擊的方式把實情套出。沒想到一看到他,情緒便如排山倒海地洶湧過來,她忘記了原先準備的策略,開始怒沖沖地質問。健雄的臉色由慌張、惶恐,漸漸轉成不耐,她更發變得歇斯底里,尖叫、砸桌,完全失控。
「事到如今,妳就看著辦吧!」他淡淡說,轉身離去。留下她在客廳內,搥胸頓足,哭得驚天動地。
佳姿把鍋裡的荷包蛋翻個身,不到一分鐘就起鍋,放在白飯上面。宥哲,她的寶貝兒子喜歡蛋黃滑嫩嫩的口感。
健雄消失了一個星期,連公司都不去,富美也藏身不見蹤影,之後他回來了,當作從未發生過。不解釋、不辯駁,問到這段關係的過去和未來,則充耳未聞,只是從此以後他把家裡當成旅館,兩三天回來一次。
「媽! 我要上學了!」宥哲在門口喊著。
她趕緊用手測一下荷包蛋的溫度。嗯,已經降溫,她把便當蓋壓緊,遞給他。
「一路小心!」她習慣性叮嚀。這個寶貝兒子是她在踩中婚姻地雷時最大的安慰。發現健雄出軌後兩個月,她常在家裡酗酒,以淚洗面。宥哲做完功課會靜靜地陪她坐著,遞面紙給她。後來佳姿覺得老讓孩子看到這樣的場景,可能對成長產生不良的影響,她決定走到外面,命運居然像唱盤跳針般,改奏出不同的旋律。富美事件如颱風過後,天色漸霽。不,應該說,如交響樂的序曲,揭開了另一幕。
佳姿透過窗戶往下瞧,宥哲高瘦的身影站在公車站牌旁。五年來她的寶貝從可愛的小學生變成青澀的高中生。相同的五年,她的人生波濤起伏……
看到宥哲順利搭上公車,她在廚房烤了二片土司,泡一杯咖啡,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慢慢品嚐。
「好久沒有看到承富了!」她想。思念、歡樂和哀傷的情緒,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其實佳姿第一次走出來也懷著報復的心態。經過輾轉的探聽,她選擇了一家鴨店。抱著不安的心,趁四顧無人,她幾乎用百米衝刺的速度連跨五步,低頭走入。開門的人,引導的人,長什麼樣子,她都無暇辨識。
「小姐,想點誰?」有人問。
她迷迷糊糊,不知所云。
問的人很有耐心,過一會兒禮貌地再發聲:
「那我幫妳介紹好嗎?」
她胡亂地點頭。
來的人有一雙修長的腿,她抬頭偷瞄一下,長得油油的帥氣,他問喜歡什麼酒?
「JOHNNIE WALKER。」她小聲說。
他轉身,回來時托一個盤子,上面有兩杯酒,一盤水果、乳酪、餅乾。
他緊捱她坐著,一股淡淡的汗漬香水迎面襲來。
「為我們的認識乾杯!」他舉杯邀請,她隨意迎合。順著燈光看到這個牛郎前額兩側都有一排青春痘,像極了差她十五歲的小弟,心裡一陣掙扎。
接著他溫柔地問佳姿,如何稱呼? 從事什麼行業? 有何嗜好? 她都恍恍惚惚。弄了半天,佳姿沙啞著問一句:
「你今年幾歲?」
「廿一歲,大姐。」說著他伸過來輕摩著佳姿的手。佳姿恍如觸電般,毛髮聳立。終於下定決心,她甩開他的手,站起來顫聲說:
「結帳吧!」搞得牛郎不知所措。
經過那次的冒險,她改去Pub,孤獨自飲,澆愁自憐。喝到半茫,前桌一對男女不知何故發生爭執,女的撇開男的手,掉頭就走。佳姿聯想到自己在鴨店的舉止,不禁微笑起來。
這時一個男子走到身旁,問她可否同坐? 昏暗的燈光中她迅速看一下,結實的身材,一副誠懇的臉。她沒吭聲,男人逕自坐下,衝著她笑,大姆指往後仰,比著前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