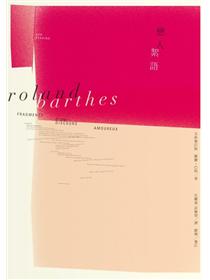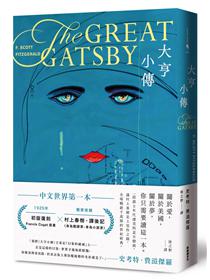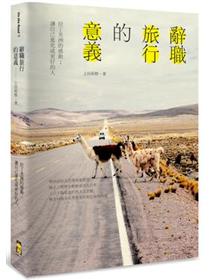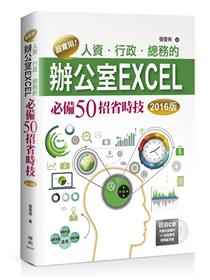在論敵梁實秋眼中,他是脾氣火爆的老頭子;
在後輩蕭紅眼中,他是最慈祥的祖父;
在同仁林語堂眼中,他是心思敏銳的鬥士;
在同窗陳寅恪眼中,他是諄諄勉勵的學長……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壇耀眼的星斗,魯迅一生交遊極廣,既有章太炎、陳寅恪、許壽裳這樣相談甚得的師長或摯友,亦有蕭紅、蕭軍、丁玲這樣受其關懷、提攜的後輩,更有梁實秋、陳西瀅、林語堂這樣觀點相左、論戰不休的“敵人”。本書將帶您走進一個由魯迅的摯交、師長、後輩、論敵等人組成的朋友圈,看魯迅與他們的往來事跡與命運糾葛,從中不但可以見出一個生活化、有血有肉的魯迅先生,更可以窺見一代民國文人的人生悲歡與命運浮沉。
1、呈現魯迅的平凡生活和交友之道,講述一代民國文人學者的人生浮沉;
2、本書以魯迅為中心,以魯迅5次搬遷的住址為線索,以獨立小傳的形式,記述了他和眾多民國文人往來、論戰、分歧等諸事跡,向您360°呈現立體的魯迅,不止是戰士、批判者,更是脾氣火爆的小老頭、熱心幫助青年的文壇前輩;
3、作者文風時髦,適合年輕人閱讀。
作者簡介:
陶方宣
安徽蕪湖人,編劇、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國內近千家報刊雜誌上發表作品約數百萬字,並在《東方文化週刊》等多家報刊開設個人專欄,出版《霓裳‧張愛玲》《今生今世張愛玲》《西裝與小腳》等各類著作三十餘種。劇作有長篇電視劇《江郎山下》。
桂嚴
1970年生於安徽繁昌,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出版《暗香》《金盞花》《花開塵埃‧鉛華畢落》等多部著作。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紹興會館 1912 – 1919
許壽裳
拖在身後的“老虎尾巴”
許壽裳搖著芭蕉扇從北邊的嘉蔭堂出來的時候,魯迅已經在槐樹下的石桌旁坐了好一會兒了。他不停地抽著煙,淡淡的煙草味道正好驅除了樹蔭下多得成把抓的蚊子。他面前的桌子上放著兩盞茶,一盞是他自己的,一盞是許壽裳的 ── 這樣的飯後茶聚對魯迅來說是每日的老習慣。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與許壽裳的弟弟許壽昌都不會露面打擾,這也是他們的老習慣。兩個弟弟都知道兩個哥哥關係很鐵。哥們兒關係鐵到這種程度,對於脾氣不好的魯迅來說非常難得。這綿延一生的友誼的形成事出有因:首先他們都是紹興老鄉,在少年時代又同赴日本留學。坐過一樣的烏篷船,吃過一樣的梅乾菜,也許還戴過同樣的烏氈帽,家門前也許還都有一棵烏桕樹吧?髮小加同鄉,鄉黨加同窗,這樣的鄉誼在兩個紹興男人之間竟然維持了漫漫三十五年,這就是命中注定。用許壽裳的話來說:“這三十五年間,有二十年(我們)是朝夕相處的。”“同舍同窗、同行同遊、同桌辦公、聯床夜話、彼此關懷、無異昆弟” ── 人生難得一知己,這樣的友誼雖說不是“鮮血凝成”,起碼也是“肝膽相照”,照到最後就剩下兄弟間的默契,如同這樣一個平淡的清涼的夏夜,一個守著清茶在等候著另一個。也沒甚麼可談,那就聽聽蟲鳴、看看星空吧,這樣也是好的。這是每天必須要經歷的一道程序、一個過程,不這樣坐一會兒,晚上肯定睡不好覺。
許壽裳在魯迅對面坐下來,談話照例都是他先開口:“明天休假,是去廣和居吃飯還是到琉璃廠淘書?”魯迅說:“你說呢?”許壽裳不置可否地笑笑:“北平胡同裡有一種老房子叫‘老虎尾巴’,莫非你也是我的‘老虎尾巴’,老頭子?”魯迅不到四十歲,但是官場失意、婚姻失望讓他內心頹廢、心如止水,一直自稱“老頭子”。聽著許壽裳的話,他不置可否地苦笑了一下。許壽裳說:“老頭子枯坐終日,極其無聊。”魯迅答道:“是啊,四十歲上頭,一事無成,做了十幾年僉事,眼看著走馬燈似的換了三四十任教育總長,都是些官僚遊士,誰肯靜下心來做幾件實事?”許壽裳也長歎一聲,然後問:“這幾日又在抄哪位聖賢的書?”魯迅答:“《沉下賢集》、《唐宋傳奇》,還有《異夢錄》。”許壽裳點點頭,呷著殘茶,任月光隨同樹影斑駁地照在青布衫上。
這樣會客的地方實在有點簡陋,但是在生性散淡的文人看來,可能別有一番幽情與詩意,尤其在這樣一個夏夜。蚊子很多,時不時會在屁股上咬出一片紅包,老鼠與尺蠖應該也不會少。對於從小在百草園長大的迅哥兒來說,這些都不算甚麼,或者將來都成為他的回憶。原來在院子一角長著棵開淡紫色花的苦楝,一場風雨後它被攔腰折斷,補種了這棵槐樹,也留下一個詩意盎然的名字 ── 補樹書屋,它是紹興會館的一部分,還有藤花館與嘉蔭堂。魯迅後來寫道:
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裡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甚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許廣平在魯迅去世後回憶,許壽裳與魯迅的談話範圍很廣泛,從新書介紹到古籍探討、從歐美文學到東洋近作,無所不包。而兩人間的人事交往、喜怒哀樂在對方面前從不隱瞞,直接坦露,這樣的友誼在魯迅、在許壽裳都是終生的唯一。不可以設想,如果沒有許壽裳,魯迅的一生該是甚麼樣子?許壽裳說魯迅是他的“老虎尾巴”,確實是很準確的比喻。只是魯迅這根“老虎尾巴”並不是高高翹起來,而是像個大掃帚似的一直拖在他身後。當初還在日本同讀弘文學院時,兩個人班級相鄰卻從不來往。後來因為一場剪辮子風波讓兩個身處異鄉的少年一下子變得志同道合,男人腦袋上盤著個蛇一樣的大辮子,許壽裳和魯迅都煩得不得了,剪去煩惱絲痛快一下吧!他們一拍即合。不久,許壽裳接編刊物《浙江潮》,第一個便向魯迅約稿,因為他早在魯迅抽屜裡發現他讀過的大量書籍。魯迅不客氣、不推辭,第二天就交來一稿《斯巴達之魂》,藉斯巴達的故事來激勵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隔了一天,魯迅又交來一文《說鐳》,此時居里夫人剛剛發現金屬元素“鐳”,魯迅藉此事說明科學研究的偉大與重要。
同鄉之誼演變成編輯與作者的關係,兩個人漸漸變得形影不離,常常在一起討論三件人生大事: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甚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魯迅徹夜思考著這三大問題,開始有了棄醫從文的念頭,因為他認定醫治一個人的心靈比治療他的身體更緊迫、更重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而沒有一個健全的心靈,這個人同樣也是廢物。他的看法深得許壽裳的認同。那時候,許壽裳雖然與魯迅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但是他已從弘文學院畢業,正在補習德文,計劃前往歐洲留學。那是1908年春天,他在東京西片町租到一個紳士的住宅,紳士搬到大阪去了,將那片華美的豪宅租給了他。他帶著魯迅去看房,兩個人都驚呆了,那片漂亮得不得了的房子還擁有一個遍種奇花異草的庭院,僅僅是籬笆上的牽牛花就有幾十種顏色。更何況那個漂亮的宅子就在東京帝國大學的隔壁,那一片老街區家家鴻儒、戶戶博士。可是僅憑許壽裳和魯迅兩人的財力根本租不起,他們又邀請了三個同學一起租下。在大門楣上掛上一盞紅燈籠,上書“伍舍”。
那一段美好的日子後來成為許壽裳與魯迅最美好的回憶,魯迅這根“老虎尾巴”從此就纏上了許壽裳。一起去上野看櫻花、嚐清茶與櫻餅,一起去神田淘舊書。因為學費無著落,許壽裳的歐洲行中止了,回國後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當教務長。魯迅對他說:“你要回去,我也要跟你回去。作人尚未畢業,我不能不先出來工作。”結果許壽裳四月份回國,魯迅六月份就到兩級師範學堂當老師。兩年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請許壽裳幫忙,草擬各種規章制度,每日不分晝夜地忙碌著,許壽裳心裡始終惦記著在杭州的魯迅。終於有一天他實在忍不住,對蔡總長說:“我向先生推薦我的同學周樹人。”蔡元培一聽,馬上點點頭,說:“其實我早就慕其大名,正打算馳函延請。現在你正好提起此事,那麼就請你代為邀請,請他早日來京。”許壽裳喜出望外,當天連著發了兩封信給魯迅,說明蔡元培先生的攬才之意。教育部隨北洋政府北遷北平,魯迅與許壽裳重新聚首,他們的命運便又捆綁在一起 ── 是一對螞蚱,也是一對苦瓜。由兩肋插刀的好友成為生死之交的莫逆,這其中的一個主要事件就是震驚全國的“女師大風潮”。
“女師大”全稱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許壽裳當過校長,凡他的好事絕對少不了魯迅的份兒,魯迅也在這裡做客座教授,與許廣平的師生戀就在這裡萌發。楊蔭榆做校長後,他不顧一切解散學生自治會,動用軍警進行鎮壓。魯迅同情這些女生們,成立了以他為首的“女師大校務維持會”,與教育部對著幹。教育總長章士釗一怒之下開除了這個吃裡爬外的傢伙。許壽裳不開心了,在教育部,誰都知道許壽裳與魯迅好得換褲子穿,哥們兒魯迅被開除,許壽裳不幹了。日日在走廊裡抬頭不見低頭見,但他就是不開口說出,而是將事情捅到了媒體上,根本不給章士釗留面子。在幾天後的《京報》上,許壽裳發表了《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的宣言》:“署教育總長章士釗,本一輕薄小才,江湖遊士,偶會機緣,得躋上位。於是頓忘本來,恣為誇言,自詡不羈,盛稱飽學,第以患得患失之心,遂輒現狐狸狐滑之態。近復加厲,本月十三日突將僉事周樹人免職,事前既未使次長司長聞知,後又不將呈文正式宣佈,秘密行事,如縱橫家,群情駭然。壽裳自民元到部,迄於今至,分外之事,未嘗論及。今則道揆淪喪,政令倒行,雖在部中,義難合作,自此章士釗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這樣的宣言也可以看作是決裂書與辭職書,為了魯迅,許壽裳斷掉自己的後路。後來經過打官司,他與魯迅的職務得到恢復,但如此是非之地爺們顯然不可久留。魯迅當時正與許廣平搞婚外戀,像一座上百年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忽然又失了火,燒得劈哩啪啦的,救也沒得救。他們先是去了廈門大學,接著又轉赴廣州的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魯迅還兼教務主任,手中有一點實力,投桃報李,把許壽裳也請了來,鐵哥們兒又開始了同吃同住的生活:“那時候,他(魯迅)住在中山大學的最中央、最高最大的一間屋 ── 通稱‘大鐘樓’,相見忻然。書桌和床鋪,我的和他的佔了屋內對角綫的兩端。這晚上,他邀我到東堤去晚酌,餚饌很上等甘潔。次日又到另一處去小酌。我要付賬,他堅持不可,說先由他付過十次再說。從此,每日吃館子、看電影,星期日則遠足旅行,如是者十餘日,豪興才稍疲。”後來許廣平來了,魯迅搬出了中山大學,租住在白雲樓,他依然帶著許壽裳,兩男一女在一起合居。這樣的時間並不長,辭職後他去了上海。魯迅一走,許壽裳在中山大學待著相當無趣,很快也追隨他來到上海。
在上海的魯迅已成為萬眾矚目的文化英雄,但在經濟上仍然不寬裕,此時的他說白了就是一介自由撰稿人,收入極不穩定。幾年前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買下阜成門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房子,向許壽裳借了四百元一直未還。許壽裳為他心急,當時蔡元培創辦大學院,對外邀請有一定聲望的教授做特約著作員,相當於美國的駐校作家。許壽裳馬上向蔡元培推薦了魯迅,事實上魯迅既不駐校也沒有為大學院寫過甚麼著作,每個月卻能領到三百元的補助費,並且一領就是好幾年,這能讓他心無旁騖地寫著他想寫的東西,讓他攀著天梯,一步步上升到最後的如日中天。
不管魯迅的名氣有多大,他和許壽裳的友誼顯然不受雙方地位的影響,他們的相交始終是家常的和平常的,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發蒙讀書,魯迅做了他的“啟蒙先生”。許壽裳的長女要結婚,魯迅放下手頭一應事務幫他操辦。魯迅在外面是匕首、是投槍,但在許壽裳這裡,他始終是一條甩不掉的“老虎尾巴”。外人說起魯迅的“罵人”,許壽裳替他護短:“有人以為魯迅好罵,其實不然,我從不見其謾罵,而只見其慎重謹嚴。他所攻擊的,雖間或係對個人,但因其人代表著某一種世態,實為公仇,決非私怨。而且用語極有分寸,不肯溢量,彷彿等於過秤似的。要知道,倘說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罵。說婊子是婊子,哪能算是罵呢?”魯迅逝世後,許壽裳回憶說:“那時候我在北平,當天上午便聽到了噩音,不覺失聲慟哭,這是我生平為朋友的第一副眼淚。”
失去了“老虎尾巴”的許壽裳去了台灣編譯館做館長,後來在台北寓所意外慘遭歹徒殺害。
第一章
紹興會館 1912 – 1919
許壽裳
拖在身後的“老虎尾巴”
許壽裳搖著芭蕉扇從北邊的嘉蔭堂出來的時候,魯迅已經在槐樹下的石桌旁坐了好一會兒了。他不停地抽著煙,淡淡的煙草味道正好驅除了樹蔭下多得成把抓的蚊子。他面前的桌子上放著兩盞茶,一盞是他自己的,一盞是許壽裳的 ── 這樣的飯後茶聚對魯迅來說是每日的老習慣。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與許壽裳的弟弟許壽昌都不會露面打擾,這也是他們的老習慣。兩個弟弟都知道兩個哥哥關係很鐵。哥們兒關係鐵到這種程度,對於脾氣不好的魯迅來說非常難得。這綿延一生的友誼的形成事出...
作者序
隨著時代的消失而消失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魯迅從教科書上悄然消失了。一代大師的身影隨著時代的起伏而消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總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這讓我想起魯迅曾經說過的話:“希望我的文章隨著時代的消失而消失。”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對他的手稿一直不珍惜,發表過的原稿都拿來當手紙。許廣平看不下去,暗地裡替他收藏,他知道後也就笑笑,不以為然。他希望死後人們不要紀念他,臨終前一再叮囑許廣平:“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他知道“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大時,他已經變成傀儡了”。即便面對死亡,魯迅也最後一次顯示了他作為大師的超乎尋常的警醒與智慧。可能他早已明白,他的一生注定要成為一個標牌。
魯迅猶如一根蒼老的古藤,一路彎彎曲曲、疙疙瘩瘩,還傷痕纍纍;他又像一條蟄伏的巨蟒:紋絲不動,幽幽的目光洞若觀火,時不時還吐出毒辣的信子。所以魯迅能寫出《狂人日記》、《阿Q 正傳》、《藥》這樣直搗中國人病灶的驚世之作。在民國那樣摩登又開放的年代,除了魯迅,誰能寫得出這樣的傑作?沒有,不可能有 ── 邵洵美、徐志摩、胡適之之流,太西化、太洋派,年輕的他們還號不準中國的病脈;王國維、章太炎、辜鴻銘之流,太過於傳統與保守,只知道發出九斤老太似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咒罵。只有魯迅火眼金睛、見解深刻,把中國腐敗之軀上寄生的癌細胞解剖得一清二楚。生命永遠不能承受之輕,一定要經過烈火的焚燒,你才有可能鳳凰涅槃。魯迅的超人清醒得益於命運熔爐對其兩次淬火:一次是祖父因為科舉舞弊案導致破家,讓他一個跟頭從天堂摔進十八層地獄,各色人等的醜態百出讓他頭一次嚐到世態炎涼與命運的多變;另一次是與朱安的婚姻,這個名存實亡的婚姻讓他生不如死。一個要做聖人的人,結果活得像塊石頭,不打麻將,不逛戲園,當然更不逛窯子,甚至也不交朋結友。這時候他已經四十歲出頭了,自嘲為“老頭子”,成天就是關著門抄抄古碑、翻翻舊書,打算了此殘生。為了壓制性慾,甚至大冬天只穿一條單褲,不蓋新被子。能量從來都是守恆的,這自然鐵律也適用於個體生命:這裡有強烈的壓抑,那裡必定要強烈的噴發。在魯迅來說,他的表現就是痛罵,他說過這樣的話,“到死也一個都不寬恕”,“活著就是要讓他人不舒服” ── 因為人生首先讓他不舒服。
魯迅自己也不知道,這其實全都是命運在佈施障眼法,讓他生不如死、痛不欲生之後,寫出了一系列振聾發聵之作,成為了文壇旗手。當他擁有了主動權之後,他在日本結識的那幫革命者左右了他的人生之路,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沒有人吃人、人壓迫人的公平社會,於是,中共毛澤東成了他的心靈夥伴 ── 一切都從這裡開始,包括他後來被奉為左派旗手。
歷史的無情與公正在於,它有它的價值觀與坐標系,它不受任何人為的力量所操縱。現在,真的應了魯迅自己的話:“希望我的文章隨著時代的消失而消失。”曾經紅得像太陽一樣的魯迅,如今終於到了日落西山的時候。這太正常了。再紅的太陽,其實都是要落山的。朝陽噴薄而出的那一刻,注定了它將會日落西山,世間的規律就是自然的秩序,沒有力量可以改變。魯迅終於隨著那個時代的離去而漸行漸遠。離去就離去吧,世間畢竟存在過一顆偉大的、思想者的頭顱,還有他塑造的一個不朽的人物:阿Q。魯迅可以死,但是阿Q 這個人物不會死,他將一直活在我們中間。他就是你,就是他,就是我。
隨著時代的消失而消失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魯迅從教科書上悄然消失了。一代大師的身影隨著時代的起伏而消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總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這讓我想起魯迅曾經說過的話:“希望我的文章隨著時代的消失而消失。”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對他的手稿一直不珍惜,發表過的原稿都拿來當手紙。許廣平看不下去,暗地裡替他收藏,他知道後也就笑笑,不以為然。他希望死後人們不要紀念他,臨終前一再叮囑許廣平:“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他知道“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大時,他已經變成傀儡了”。即便面...
目錄
第一章 紹興會館 1912-1919
許壽裳:拖在身後的“老虎尾巴”
錢玄同:爬來爬去的“爬翁”
孫伏園:催生阿Q的茶童
蔡元培:氣味不相投的“此公”
胡適:不打不成交的冤家
陳獨秀:吃馬屎的焦大
劉半農:演雙簧戲的范瑞奴
章太炎:裝瘋賣傻的狂徒
章士釗:穿長衫的士大夫
陳寅恪:豪門裡走出的書呆子
第二章 八道灣 1919-1923
林語堂:糊裡糊塗的愣小子
許羨蘇:留短髮的“令弟”
許廣平:住三樓的乖姑
第三章 阜成門內西三條 1924-1926
郁達夫:飄來飄去的風箏
韋素園:瘦小的守寨者
廢名:把月光閂在門外的王老大
高長虹:黑夜裡的太陽
梁實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台靜農:人緣極好的未名社員
第四章 景雲里 1927-1930
瞿秋白:會耕田的犬
馮雪峰:“長得很醜”的鄉巴佬
內山完造:討厭蚊子的書商
曹聚仁:赤臂打仗的烏鴉先生
茅盾:沉默寡言的編者
柔石:講寧波話的旁聽生
潘漢年:瓦窯堡來的小潘
史沫特萊:並不漂亮的舞伴
胡風:一隻耿介的牛虻
白薇:生肺病的仙女
蘇雪林:脾氣不好的徽州姑娘
陳西瀅:外冷內熱的正人君子
第五章 大陸新村 1931-1936
蕭紅:狼狽不堪的小母親
蕭軍:東北來的“土匪”
丁玲:被嘲弄的“休芸芸”
邵洵美:富翁家的贅婿
周揚:令人討厭的漢子
巴金:獨得三昧的浙江老鄉
成仿吾:掄板斧亂砍的黑旋風
聶紺弩:寫小說的“金元爹”
宋慶齡:同一陣營的同志
第一章 紹興會館 1912-1919
許壽裳:拖在身後的“老虎尾巴”
錢玄同:爬來爬去的“爬翁”
孫伏園:催生阿Q的茶童
蔡元培:氣味不相投的“此公”
胡適:不打不成交的冤家
陳獨秀:吃馬屎的焦大
劉半農:演雙簧戲的范瑞奴
章太炎:裝瘋賣傻的狂徒
章士釗:穿長衫的士大夫
陳寅恪:豪門裡走出的書呆子
第二章 八道灣 1919-1923
林語堂:糊裡糊塗的愣小子
許羨蘇:留短髮的“令弟”
許廣平:住三樓的乖姑
第三章 阜成門內西三條 1924-1926
郁達夫:飄來飄去的風箏
韋素園:瘦小的守寨者
廢名:把月光閂在門外的王老大...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收藏
2收藏

 2二手徵求有驚喜
2二手徵求有驚喜



 2收藏
2收藏

 2二手徵求有驚喜
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