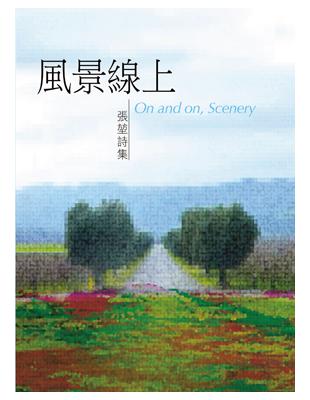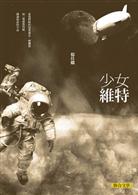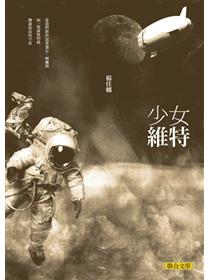名人推薦:
【序一】
風景線上的傾斜之歌 ⊙鴻鴻
半生在台灣,半生在美國,詩人張堃從事的是國際貿易,卻從沒放棄筆耕。距離上一本詩集《影子的重量》出版不過兩年,他又完成了一本新詩集《風景線上》,創作力堪稱步入顛峰狀態。
張堃有如一位吟遊詩人,所到之處,屢屢在詩中留下痕跡。而由於詩人的閱歷,這些景致在讀者眼前重現時,便都充滿了歷史感。例如他在涵江行過,眼中白塘的月亮是宋代的月亮,老街是民初的老街,而寧海橋頭又是元明的落日。除了一如古典詩人般的詠懷,當下的詩人也感官全開──走在澳門,他從苦澀的咖啡中喝到溫柔,聽見巷弄的鞋聲和公園的鴿子咕嚕聲,在砲台感受到砲管在落日下的冰冷。
然而最富詩意的,其實是現代和古代的衝突,透過一些精心挑選的細節,在詩中呈現出來。他在江南吃蟹,吟不出半句詩來唱和,「只吃出了/滿嘴滿手的腥」;在蘇州夜半聽到斷斷續續的古箏獨奏,卻「被抽水馬桶/一陣嘩啦啦的沖序一風景線上的傾斜之歌/鴻鴻水聲沖走」。冷靜地描寫這些氣味與聲響,讓我們忽然置身真實的當下,感受到夢醒的巨大悵惘。
在熟年的心境中,張堃傾訴的,已不是年輕詩人慣見的渴求、戀慕,而每多生命的領悟。但靈光一閃所照見的,往往不是得到什麼,反而是發現失去什麼。猶如留白反襯的手法,以無證有,以毀壞來證明存在,以忘卻、放空,來迎接未知的一切。例如詩人寫他往訪花蓮的和南寺,好不容易攀登至觀世音菩薩的腳前,「卻把上山的因緣/還有要說的話/全都忘得一乾二淨」。此時,鐘鳴不知由何處陣陣響起,從四面八方傳來「蟬聲如交響樂的演奏」!放眼望見靜止的太平洋上「千朵萬朵蓮花/悠悠在海上綻放開來」,這種柳暗花明的發現過程,雖若有所失,卻格外驚喜。如無所失,何來所得?一趟旅程,恰是生命境界意味深長的譬喻。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原來計較太多,只是自尋煩惱。面對老化、退化,張堃用一首〈失物招領〉來排解:「雨傘掉了/天氣終將放晴/老花眼鏡丟了/報紙上的新聞/看看大標題就好」。他還如此調侃失憶症:發生過的不記得,想起的卻是「那段似有若無的往事/原來從未發生過」!人生無從執著,一切都會像「軟片曝光、錄音帶洗掉、記憶晶片刪除」一樣,「瞬間歸零」。然而即使回憶已經消失,還有舊相簿、老唱片、老電影可以喚起某種情感。詩人從33又1/3轉黑膠唱片中聽見的不僅是老歌,而是「沙沙作響的低泣」;從黑白電影中看到的不僅是老故事,而是「回到童年夢境」;還從博物館「怒目睖瞪著」的動物標本中,聽見荒野的風聲、獵人的吆喝聲、以及槍響的回音。一生的恐懼或思戀,在暮年或者斷續、殘缺、傾斜,卻正可讓深藏角落的記憶傾倒出來,斜也斜出了美妙的意外:
身體歪一邊
輪椅也跟著歪成
下坡的坡度
回憶傾倒了
印象歪到模糊不清
終至一片空白
心事的斜角
又正好切入夜夢的邊緣
想念的那人
卻久未在夢中出現
只偶爾感覺
踽踽行走的背影
斜斜閃過
豁達的視野,產生幽默的達觀,足以寬慰自己,鼓舞他人。這種心境,〈螢火蟲〉表達得最為懇切──
夜間從草叢裡飛出
林木中只有光
在飛行
不見自己
每一個自己
都在微弱的光裡
就算弱到快要看不清了
也不用電池
更不靠別人來發電
光只照別人,不照自己;不靠別人,只靠自己──這是多麼認份、又多麼自得的生命態度。是詩路的自況,也是生命的自覺。張堃證明了,無須尋幽訪奇,最奇最險的,就是尋常事物;而經歷千山萬水,最可貴的,還是誠實地面對自己、述說自己。
【序二】
他的風景遍佈時間─張堃及其詩集《風景線上》 ⊙楊宗翰
在創作時想像力沒有疆界的華文作家,遇到文學史卻常被強制限定待在某一區塊,譬如中國作家、台灣作家、香港作家、北美作家……。除了一向自居中心的中國大陸,其他區域的華文作家早早便被劃入「海外華文文學」—後面這個標籤彷彿廉價速乾膠,迅速黏上後便難以擺脫,不時發出怪異難聞的氣味。標籤的創造者,當然自認是「海內」一員;被劃入「海外」的作家,則不幸得接受「台港澳文學」這類內與外、中心與邊緣的分類方式。我認為「海外華文文學」、「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乃至近年流行的「世界華文文學」,骨子裡一樣都是以中國為圓心的同心圓架構,始終未曾擺脫事大主義、屬地主義幽靈的糾纏。推崇「世界華文文學」觀念者,嗜談它包括了中國大陸在內的所有用華文(漢語)寫作的文學,以統一的語言來形成精神共同體,是源於中國文學傳統的有機整體。殊不知「有機整體」不過是同心圓架構的「二刷」,「有機整體」也未曾取消「中心」的權威及大欺小、強凌弱的「秩序」。在中心牢固、秩序未改、整體大夢正酣的狀況下,多中心主義、跨越國家界限、以文學想像為疆域……這些恐怕都只是美麗的修辭,後面潛藏著「世界華文文學」這個概念「何新之有?」的尷尬事實。
「世界華文文學」概念既不足恃,可依傍者唯有作家之書寫軌跡。以今日遷移之便利迅捷,漂泊觀光遊學旅居甚至移民皆非難事,要創作者困守一地、穴居終生恐怕才無比困難。強制把作家作品歸類為「北美」、「台灣」、「東南亞」等,只是便宜了研究者,也是對文學閱讀的最大簡化—或者應該說:當文學研究者不再能考究作家生平、探詢詩人行止時,才是閱讀作品的真正開始吧?每當談到這些問題,我都會想到張堃(一九四八—),和他值得慢品細讀的近期詩創作。我說「近期」,是因為他的處女作《醒‧陽光流著》(臺北:創世紀詩社,一九八○)並沒有給我太大的驚喜。這本收錄了他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三年的創作,之後二十五歲的張堃便歇筆忙於謀生,久不詩矣。一直要到二十七年後,收錄他一九八○到二○○六年間一百一十一首作品的第二部詩集《調色盤》(臺北:唐山,二○○七)問世,其間還經歷了國際貿易事業的經營擴展及高低起伏,與一九八九年舉家移民美國的環境變遷。張堃詩作數量雖少,但因為持續在台灣媒體發表(這比參加詩社聚會、出席活動、常飛回台灣……都重要太多),我倒不覺得他是什麼「天涯詩人」—這個《調色盤》書封折口的文案,很容易誘使讀者混淆了「到世界各地旅行」(生命經驗)與「化各國風景為心境」(書寫軌跡)。我認為後者才是詩人張堃的當行本色,譬如這首〈黃昏登倫敦塔〉:
秋已深
而暮色再濃就入夜了
僅只日落的俄頃
守塔人的背影
竟也長滿了青苔
我是否來得太遲?
此詩最末附了一則「後記」說明倫敦塔故事及登塔之感受,我以為不妨刪去,相信亦無礙理解。「巍峨的城堡不語/一如緘默的時間/冷冷的在牆垛上/留下苔癬」,苔癬成了歷史遺留在牆垛上的鞭痕,安安靜靜卻比任何話語更為有力。〈黃昏登倫敦塔〉貌似以詩記遊,實為遙指時間及歷史襲向詩人的重量,手法堪稱上乘。張堃在《調色盤》中,似乎還不能完全擺脫前輩詩人的影響,譬如一九八一年發表於《藍星詩刊》新十二期的〈登樓〉:
樓梯
是灰塵的路
一階一階的鋪了上去
鞋印
跟著我一路追趕
對照洛夫一九七○年的現代禪詩〈金龍禪寺〉:
晚鐘
是遊客下山的小路
羊齒植物
沿著白色的石階
一路嚼了下去
兩者句型頗為相近,或許張堃是刻意向前輩致敬?倒是同書中另有〈贈魚〉一詩,標明附題為「寄洛夫」,原來是從一尾贈魚啟發聯想,可惜失之於過度落入言詮。《調色盤》一書也收錄了〈遙遠的彩虹〉,一九八五年由樓文中譜曲、當紅歌手王芷蕾演唱並收入由飛碟發行的唱片中。原詩跟因應錄音所修改的歌詞,詩味皆偏清趨淡,不無遺憾。
真的讓張堃在詩壇有紮實重量的,畢竟還是從二○○七至二○一一、五年累積下的第三部詩集《影子的重量》(臺北:釀出版,二○一○)。此時期張堃發表詩作密度遠甚以往,無論書寫母親、懷念父親、思及故舊、描摹今友,都能做到句淡味濃,不時閃現哲思及人生體悟,讓我自二○○七年後對他開始投以關注,最後索性主動邀稿成書。詩人在《影子的重量》裡或懷人、或記友,對紀弦、周鼎、大荒、沙穗、秀陶、秦松、商禽、碧果、張默等人的摹寫,成為張堃近期相當重要的書寫方向。類似題材的探索,還應該包含詩人無緣實際親近、唯靠想像致之的翁山蘇姬、帕華洛帝、達賴喇嘛十四世等。我認為張堃在《影子的重量》裡,其人其詩早已跨越任何「國家」或「區域」疆界,當然「世界華文文學」這個框架對他也無甚意義。這位走過世界多處、流轉各地的詩人,〈散步小集〉彷彿是一則聲明:
曾經奔走於大江南北的腳
現在漫無目的地走在
行人道上
鞋聲輕了許多
拖在身後的影子卻重了
鞋聲與影子的輕重之間,真是何等妙筆/妙比!詩人此時期更為嫻熟如何尋找歷史罅隙、影中之影:「在拱門的陰影裡/我取出相機/隨意拍下風景明信片上/沒有的斑駁」(〈布萊爾拱門〉)。我以為應該把「漫無目的」及「隨意拍下」,都當作張堃的「態度」—既是對生活的態度,也是面對詩題材的態度。
但漫無目的不代表散漫停滯,隨意拍下也不是從此失焦,收錄二○一二到二○一四年詩作的新書《風景線上》就是最為雄辯的證明。從《影子的重量》以降,懷人、記友的書寫方向在《風景線上》更顯發揮:譬如前者有〈人物素描六幅〉,寫蓉子朵思等六位女詩人;後者亦收錄〈人物素描五幅〉,對象改為陳育虹、利玉芳等五位女詩人。唯靠想像方能致之的,在《風景線上》有〈我擁抱過辛波斯卡〉、〈咖啡館偶遇巴哈〉,以及寫狄瑾蓀的〈在預感中相遇〉:「聽她輕聲朗讀/我為美死去」,我認為三者成績更勝過〈人物素描〉。若再加上書中懷紀弦的〈落幕之後〉、懷周夢蝶的〈瘦至無形〉、悼鄧育昆的〈最後一行詩句〉,此類創作在《風景線上》所佔篇幅不可謂之不大,顯現了張堃近年來對此一書寫方向的鍾情。
除了延續前一部詩集的長於寫「人」,我以為《風景線上》的另一特色,乃是示範了如何以風景書寫「時間」。張堃早在一九七三年就發表過一首〈時間〉,是處女詩集《醒‧陽光流著》裡的佳作:
假如時間是靈魂的生命
短暫的停留又匆匆的走開
我們決定跟著離去還是
駐足?
推開門
我在出入之間
許多燈亮起後又相繼熄滅
陌生的鬼魅一閃而逝
不知在門裡還是
門外?
寫這首詩時,詩人才二十五歲。《風景線上》的張堃已經六十五歲了,四十年收穫的不只有閱歷的增長,更是詩藝的精進。諸如:「夢漸漸老去/再老一點/就會返老還童了」(〈兒童節〉)、敘述者看到自己「竟從一幅/黑白電影的海報裡/隱隱地/走了出來」(〈街景〉)、「那人緩緩走入/陳舊的夜景/去和自己重逢」(〈在逝去的鐘點裡〉)等小詩,都是顯例。這部新詩集裡的「風景」,其意涵往往超越旅遊景點或名勝古蹟層級,而是指向更為抽象、非具體之景。譬如〈風景四題〉中有一篇〈雨景〉:「傘下的人撐起/一段灰濛的往事/匆忙走過街頭又回頭/濕淋淋的記憶/斜斜落下」,讀後便知此詩中的「景」已非重點,「事」才是關鍵。往事固然灰濛、記憶可能潮濕,但還是必須面對過去,儘管那裡遍佈時間的皺褶。
張堃這些近期詩創作看似無一處提及時間,其實時間總已(always already)在詩行中潛行,譬如顯然不屬於賞心悅目「風景」的〈無題小詩三首〉:「老人坐在角落/漸漸坐成一尊雕像/他不懂裝置藝術/只在沉思中把出神的自己/化作孤單的風景」。當老人「被藝術」為一尊雕像時,「風景」兩字顯得何等諷刺!跨越六十五歲(在台灣,這恰是退休年齡門檻)的張堃,自編詩集《風景線上》時選擇以〈老人院二帖〉作為全書首篇,理應別具深意。甚至在以記遊為主的第四卷「古鎮同里」,像〈涵江水鄉初晤〉這篇歌詠風景之作,貌似書寫宋朝湖泊、民初巷弄、元代石橋,最終實在寄託詩人的「驚悟」:「為了載負時間的重量/落日還是元代的落日/石橋卻老了」。福建涵江這座橫跨木蘭溪兩岸的寧海橋,在張堃筆下不只是一片風景,而是被詩人之眼視作時間重量的載具。其實讀畢《風景線上》全書便可發現,詩人的風景遍佈時間,直到象徵生命終結的〈墓園一角〉亦復如是:「所有的墓碑/都不說話/沉默如青苔/綠著/碑石上/說不清的斑駁」。一切旅跡遊蹤、感懷寄託、懷人記友,張堃皆力求存詩為證,以「證明我們曾經來過/在短暫/與永恆之間,在寂靜的/回憶裡」(〈北回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