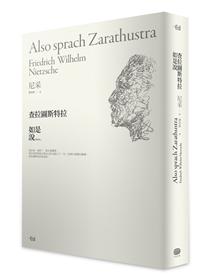兩種相互交戰的本質──人性與狼性
(更準確一點說,其實是不下千百之多的本質)
一層一層剝開在世俗與教養下,
對工業文明、對義務、對愛、對自我、對內在心靈最深層也最根本的詰問……★赫曼.赫塞最魔幻、最精湛,既獲至高肯定亦備受誤解的──人性與狼性、真實與幻覺交戰之作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托馬斯.曼(Thomas Mann)譽為德語世界的《尤利西斯》,想要一讀再讀的作品
★看清自己的多元心靈,告別單面向,認可自己的每一重社會角色──這是赫塞一層一層袒露自身最深層的脆弱而給我們當代讀者的禮物!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花亦芬、本書譯者 柯晏邾 專文導讀
作家 陳雨航、律師 呂秋遠 推薦
當他是狼的時候,裡面的人就一直盯著他,評判他,挑剔地關注著──在他是人的時候,那匹狼也做著同樣的事。好比說,當人的哈利有個美好的想法,感覺到一種細緻珍貴的感受,或是過了所謂美好的一天,他之中的那匹狼就齜牙咧嘴,嘲笑他,血淋淋地嘲諷他……一匹狼,內心知道得很清楚,他所謂的舒適就是獨自走過荒原,有時狂飲鮮血,或是追逐母狼──就狼的眼光來看,人類所有的行為是極端怪誕與困窘,愚蠢而虛榮的。
《荒野之狼》,1927年出版,赫塞五十歲即將進入「知天命」之年的作品,透過主角哈利.哈勒爾的故事,反省中產階級的生活,批判知識中產分子的價值觀,並藉著主角身上兩種相互交戰的本質──人性與狼性(更準確一點說,其實是不下千百之多的本質),尖銳而機巧、諷刺而謙遜地反覆辯證。在人與狼,哈利與歌德、莫札特的「穿越」對話中,主角最終進入「神奇劇場」,於一扇又一扇門背後,一個又一個似夢、似幻又似真的房間中,一層一層剝開在世俗與教養下,對工業文明、對義務、對愛、對自我、對內在心靈最深層也最根本的詰問……
作者簡介:
赫曼.赫塞 Hermann Hesse
1877年7月2日生於德國南方小鎮卡爾夫(Calw)。年少時迫於父命曾就讀神學院,後因精神疾病而休學,但始終立志成為詩人,更在21歲時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浪漫詩歌》。27歲《鄉愁》一出,佳評如潮,繼而是《車輪下》、《生命之歌》、《徬徨少年時》、《流浪者之歌》、《荒野之狼》、《玻璃珠遊戲》等一部部不朽之作,讓他於194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位20世紀德國文學浪漫主義的最後英雄,於1962年病逝,享年85歲。
譯者簡介:
柯晏邾
畢業於輔仁大學德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後背叛文學,轉投社會學懷抱,於德國哥廷根大學取得社會學/德國文學碩士,專研歷史社會學,卻又舊情難忘地改編舞台劇本、翻譯文學著作。譯有《流浪者之歌》《荒野之狼》《玻璃珠遊戲》(遠流即將出版),另與林倩葦合譯《車輪下》。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湯瑪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有必要多說《荒野之狼》是本大膽實驗性質不亞於《尤利西斯》(Ulysses)或是《偽幣製造者》(Les Faux-Monnayeurs)的長篇小說嗎?《荒野之狼》是長久以來第一本再度教會我何謂閱讀的書。
阿佛列德.沃芬史坦(Alfred Wolfenstein,1888-1945,表現主義詩人)
這是關於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帶著滿懷高漲的怒氣,想要擊潰百貨公司和教堂的虛偽存在,扭轉中產階級世界秩序;這是關於一個自我的革命份子的故事……《荒野之狼》是反中產階級勇氣的文學創作……
名人推薦:湯瑪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有必要多說《荒野之狼》是本大膽實驗性質不亞於《尤利西斯》(Ulysses)或是《偽幣製造者》(Les Faux-Monnayeurs)的長篇小說嗎?《荒野之狼》是長久以來第一本再度教會我何謂閱讀的書。
阿佛列德.沃芬史坦(Alfred Wolfenstein,1888-1945,表現主義詩人)
這是關於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帶著滿懷高漲的怒氣,想要擊潰百貨公司和教堂的虛偽存在,扭轉中產階級世界秩序;這是關於一個自我的革命份子的故事……《荒野之狼》是反中產階級勇氣的文學創作……
...
章節試閱
當我走過圖書館,我遇到一個年輕的教授,我曾經和他談過一兩次話,那是我上次在這個城市停留的時候,幾年前甚至好幾次到他的住處拜訪,好和他討論東方的神話,那是我當時相當專注研究的領域。那個學者走向我,僵硬而有些近視,我已經打算走過他身邊,那時他才認出我,十分誠意地撲向我,而我,以我可悲的想法,對他的感激並不由衷。他高興得開朗起來,因為我們過去的談話記起我來,擔保他非常感謝我的看法,而且常常想到我,從那以後他就不常和同事們進行這麼刺激而收穫豐富的討論了。他問我何時到城裡來的(我謊稱只有幾天),以及我為何沒有去找他。我看著這規矩的男人有教養的美好臉龐,覺得這一幕其實可笑,卻仍然像一隻飢餓的狗享受這許多溫暖,吞一口愛,咬下他的認可。荒狼哈利感動地作著鬼臉,乾燥的咽喉裡聚集起唾液,感傷不顧他的意願讓他駝了背。是唷,我於是熱情地撒著謊,說我只是臨時到這裡來,半做些研究,而我又覺得身體不是那麼舒服,否則當然會去拜訪他。這時他誠心地邀請我今天傍晚和他一起消磨,我感激地接受了,向他太太表達我的問候。熱情的說話和微笑讓我的雙頰發痛,我這兩頰已經不再習慣這麼費力。當我,哈利.哈勒爾,站在街上,喜出望外、受盡奉承,禮貌而熱切,對著這個友善的男人近視的美好臉龐微笑著,另一個哈利這時正站在一旁,同樣作著鬼臉,站著歪著臉,想著我其實是怎樣奇特、扭曲而不老實的兄弟,兩分鐘以前還詛咒著世界,激動地咬牙切齒,而現在不過遇到一聲呼喚,一個值得尊敬的正直人士無害的問候就讓我感動,過度熱情地稱是說阿門;享受一絲善意、尊重和友善的時候,就像隻嫩仔豬一般翻滾。於是這兩個哈利就這麼站著,兩個彼此極度不友善的人物,面對著有教養的教授,彼此嘲諷,彼此觀察,互相唾沫,然後就像每次發生這種情形,又再一次提到那個問題:這單純是人類的愚蠢和弱點,普遍的沒人性,還是這樣敏感的利己主義,缺乏個性,感覺的混沌和分裂只是一種個人的、荒狼的特點;如果這種卑劣的個性是普遍人性的,那麼我對世界的蔑視又重新衝了上來;如果那只是我個人的弱點,那麼就有理由來一場自我輕視的狂歡。
在兩個哈利的爭執下,教授幾乎完全被遺忘;突然間我又覺得他煩人,急忙擺脫他。我從背後看著他良久,看他如何在光禿禿的林蔭大道上走遠,像個理想主義者,有種信徒般善心又有些怪誕的走路方式。我內在的殺戮激烈吵嚷著,機械式地把僵硬的手指彎起又伸直,和暗自升起的痛風戰鬥著,我必須承認我當時愚弄了自己,結果攬了個七點半的晚餐邀約,連帶承擔禮貌、科學閒聊、觀察陌生家庭幸福的責任。我生氣地走回家,把白蘭地和著水,吞下我的痛風藥丸,躺在長椅上,試著看書。當我終於成功地讀了一會兒《蘇菲從梅莫爾到薩克森的旅行》,一本源自十八世紀令人愉快的閒書,我忽然又想起那個邀約,而我還沒有刮鬍子,也還要換衣服。天知道我為什麼要這般對待自己!所以,哈利,站起來,把你的書放到一邊,塗上肥皂,把你的下巴刮到流血,穿好衣服,喜愛大家吧!正當我塗肥皂的時候,我想到墓園裡骯髒的黏土坑,今天那個陌生人被放下的地方,還想到無聊的基督教友們板著的臉,一點都笑不出來。在我看來,在那裡結束的,在那個髒汙的黏土坑洞旁邊,隨著傳教士困窘的語句,隨著送葬者愚笨而尷尬的表情,看到所有鉛製和大理石製的十字架與牌匾時無望的目光,所有那些假的鐵絲花和玻璃花,在那裡結束的不只是那個陌生人,不僅明天或後天我也會在那裡走到終點,被眾人圍繞,在參與者的困窘和虛偽下聚集在汙穢裡;不,一切都會如此終結,我們所有的努力,整個文化,整個信仰,我們全部的生命歡愉和樂趣是那樣的病態,也即將在那裡被掩埋起來。墓園是我們的文化世界,裡面有耶穌基督和蘇格拉底,有莫札特和海頓,但丁和歌德,都只是生鏽的鉛墓碑,周圍站著尷尬虛假的送葬者,他們可能會多付出一點,如果他們還能夠相信那些鉛板,那些對他們而言曾經是神聖的東西;他們可能會多付出一點,就算只能說些正直嚴肅的追悼話語,以及說出對這個沉淪世界的絕望,而不是除了困窘、作鬼臉地團團站在墳邊以外什麼都沒留下。我憤怒地一再刮著下巴的同一個地方,傷口刺痛了一會兒,還是將要把換上的乾淨領子再換一次,完全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做這些,因為我一點都不想赴約。然而一小塊哈利又在作戲,說教授是個令人喜歡的傢伙,希望聞一些人味,閒聊一下,有人作伴,想起教授美麗的妻子,覺得在一個友善的主人家度過一個晚上,這基本上還是滿讓人高興的,而且幫我在下巴貼了塊創絆貼布,幫我穿好衣服,打上一條體面的領帶,和氣地讓我打消主意,不再如我原先期望的待在家裡。我同時又想:就像我現在穿著整齊要出門,拜訪教授,和他交換一些或多或少虛假的客套,全都不是原來設想的,大部分的人每天就這樣生活這樣進行著,一個又一個小時被迫的,不是原來就想做的,拜訪別人,聊天,在辦公室裡坐著等下班,所有的都是強迫的,機械式的,不帶希冀的,所有這些事盡可用機器做得一樣好,或是根本不做;正是這永遠運作下去的機械式阻攔這些人,以及我,對自己的生活進行批判,認清以及感覺生活的愚蠢和膚淺,它可憎扭曲的疑惑,無望的悲傷和荒蕪。啊,他們是對的,非常對,人類這樣活著,玩著自己的小把戲,追逐自己的重要性,而不是對抗抑鬱的制式生活,絕望地盯著空洞,就像我這脫軌的人所做的。就算我在這幾頁文字當中藐視人類,加以嘲諷,畢竟不會有人因此以為我想把罪過推到他們身上,控訴他們,想把我個人的悲慘歸咎於他人!然而我,這個我現在已經走得那麼遠,已經站在生命的邊緣,即將落入無底的黑暗,如果我試著欺騙自己和他人,就好像我還跟隨那種機械形式,好似我還屬於那個永恆作戲的軟弱幼稚世界,那麼我就是做了不義之事撒了謊!
那個夜晚結果相當奇妙。在朋友的房子前面我站定了一會兒,向窗戶張望。那裡住著這個男人,我想著,他年復一年地做著自己的工作,閱讀評論文章,找出小亞細亞和印度神話之間的關連,從中得到樂趣,因為他相信自己作為的價值,他相信科學,相信他服務的這個對象。他相信單純知識的價值,儲存知識的價值,因為他相信進步,相信發展。他沒有經歷過那場戰役,沒有經歷過直至目前的思想基礎因為愛因斯坦而發生的顛覆(他以為那只和數學家相關),他看不到四周即將展開的下一場戰爭,他認為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者是可恨的,他是個乖巧、沒思想、愉快而自恃重要的孩子,他著實讓人羨慕。我推了自己一把走進去,穿著白圍裙的女傭接待我,出於某種預感我仔細注意她把我的帽子和大衣帶去哪兒。我被帶到一個溫暖明亮的房間,她請我在那裡等著。不想念些禱文或者小睡片刻,我順著嬉戲的慾望,把旁邊引我注意的東西拿在手裡。那是一幅小小的加了框的畫,放在圓桌上,用一片硬挺的厚紙板讓它斜立著。那是一幅銅版蝕刻,呈現的是詩人歌德,一個充滿個性、髮型出眾的老人帶著一張美麗修飾過的臉龐,臉上既不缺那著名的灼熱雙眼,也不乏些微宮廷任職沾染上的寂寞和悲壯,那是這個創作者特別著力的。他成功地賦予這個惡魔般的老者一些教授的,或許也是演員的自制和正直的特性,卻無損其深度,而且總體來說,將他呈現為一個十分美麗的老先生,足以裝飾任何中產階級房舍。也許這幅畫不比勤勞藝匠所製造的那些溫和救世主、使徒、神人、精神英雄和政治家的畫像愚蠢,也許這幅畫只是因為某些精湛的技巧讓我感到激動;不管創作者本意何在,無論如何──我已經相當受到刺激而憤怒──這幅老年歌德空洞而自滿的畫像,立刻就讓我感到一種糟糕的不和諧,讓我知道這裡不是我該待的地方,這裡是優雅塑造的高齡大師和國家偉人的居所,不是荒野之狼的。
如果這時走進來的是房子的主人,那麼也許我能成功地用可接受的藉口告退。然而進來的卻是他的妻子,於是我從善如流,雖然我覺察到不祥。我們彼此問候,初步分歧接著更大的一個:女主人讚美我良好的外貌,而我卻太清楚自己從上次見面以來蒼老了多少,光是和她握手,有痛風的疼痛手指就不舒服地提醒了我。呃,然後她問我,我親愛的妻子可好,我只得告訴她,我的妻子離開了我,而且我們已經離婚。教授走了進來,我們兩個都很高興。教授也誠摯問候我,情況的走調和怪異可想而知被十足巧妙地表達。他手裡拿著報紙,他訂閱的那份報紙是一份鼓吹軍事和戰爭的派系報紙,他和我握手以後指著那份報紙對我說,裡面提到一個同姓的人,有個時事評論家哈勒爾,報載他一定是個討厭的傢伙和不識祖國的人,這個人取笑德皇,公開表示他的祖國對戰爭爆發所負的責任不少於敵對國。會是怎麼樣的一個傢伙!好啦,這小子聽說,報紙編輯部已經把這隻害蟲徹底解決掉,並且加以譴責。當他發現我對這個話題不感興趣,我們就換到另一個話題,而他們倆真沒想到會有個這麼粗魯的人坐在他們面前,但事實如此,我就是那個粗魯的傢伙。哎,何必吵吵嚷嚷令人不安!我暗自嘲笑,卻失去最後一絲希望,今晚再也不可能遇到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我清楚記得這個時刻,就在教授提到那個叛國哈勒爾那一刻,我內心最惡劣的憂鬱和絕望情緒加深,那是從葬禮那一幕以來在我內心不斷積壓而越來越強,變成一種可憎的壓力,變成一種身體(下半身)可感的緊急狀況,一種令人窒息而充滿憂慮的宿命感,它衝著我窺伺著,覺得危險從背脊湧上。幸好這時傳來通報,餐點已經準備好了。我們走進用餐室,當我盡力地不斷提起或是問些無關痛癢的事,我就吃得比平常更多,隨著時間覺得自己越來越可悲。我不斷想著,我的天啊,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費勁兒?我清楚感覺到,我的東道主根本也不覺得舒坦,保持興致耗費他們的精力,可能是因為我讓人感覺沉鬱,也可能在這屋子裡還有什麼不對勁的。他們老是問一些我無法懇切回答的問題,我一度完全撒謊,抗拒伴隨著每個字的噁心感。最後,為了轉移話題,我開始敘述我旁觀的那場葬禮。可是我沒有搭對腔,我想表現幽默的嘗試顯得敗興,我們離彼此越來越遠,荒野之狼在我之中露出猙獰的牙齒笑著,吃點心的時候我們三個都相當沉默。
我們回到最初的那個房間喝咖啡和酒,也許對我們會有些幫助。然而這時我又注意到那個詩人諸侯,雖然他被放在一邊的家具上。我沒辦法擺脫他,即使我不是沒聽到內在的警告聲音,我還是又把它拿在手上,開始和它爭執。我就像被那種覺得這個情況難以忍受的感覺所占據,而我現在必須成功地讓我的東道主又熱切起來,吸引他們,讓他們應和我,或是將情況完全引爆。
「希望歌德的長相不是真的像這樣!」我說:「這種虛誇而高尚的架式,這種逢迎周遭人的體面,在男性的膚淺之下這極度溫情感傷的世界!當然他有許多不受贊同的地方,我也常對這個擺架子的老先生有意見,然而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他,不,這太離譜了!」
女主人把咖啡完全灌下去,臉色非常難堪,然後急忙走出房間。她的丈夫解開我的疑惑,半尷尬半責備地告訴我,那幅歌德像是她太太的,而且她特別喜歡,「即使客觀而言您是對的,而我其實並不贊同您的看法,您也不應該如此直接說出來。」
「您說得對,」我承認:「可惜這是我的習慣,一種惡習,總是選擇最直接的說法,歌德在他風光的時候也這麼做。甜美市儈的沙龍歌德當然不會用直接、真誠、不拐彎抹角的表達方式。我請求您和您的妻子原諒──請您告訴她我有精神分裂症,同時也請允許我向您道別。」
有些不好意思的主人雖然略有微詞,還是重提到我們過去的談話是多麼美好而有啟發性,我對米特拉絲和黑天的推論當時讓他印象深刻,他原本希望今天的談話也會是如此……諸如此類。我向他道謝,這些話非常友善,可惜我對黑天的興趣,還有對科學談話的興致已經徹底消失,我今天還對他說了好幾次謊,比如我不是幾天前才來到這個城市,而是已經住在這裡好幾個月,過著自己的生活,已經不再適合和比較高尚的人士往來,因為第一我總是脾氣很壞而且痛風纏身,第二我經常喝醉。更有甚者,為了讓彼此關係明朗,至少不要像騙子一樣離開,我必須對尊貴的先生解釋,他今天其實相當冒犯了我。他認同那個愚蠢、頑固、無所事事的軍官的說詞,而未就一份反動報紙針對哈勒爾的意見提出合乎學者身分的看法。這位「老兄」、沒有祖國的傢伙哈勒爾其實就是我自己,而這對我們的國家和這個世界比較有益,如果至少有一些有想法的人擁戴理性,表態熱愛和平,而不是盲目狂熱地追求新一場戰爭。就這樣,願上帝保佑您,再見。
當我走過圖書館,我遇到一個年輕的教授,我曾經和他談過一兩次話,那是我上次在這個城市停留的時候,幾年前甚至好幾次到他的住處拜訪,好和他討論東方的神話,那是我當時相當專注研究的領域。那個學者走向我,僵硬而有些近視,我已經打算走過他身邊,那時他才認出我,十分誠意地撲向我,而我,以我可悲的想法,對他的感激並不由衷。他高興得開朗起來,因為我們過去的談話記起我來,擔保他非常感謝我的看法,而且常常想到我,從那以後他就不常和同事們進行這麼刺激而收穫豐富的討論了。他問我何時到城裡來的(我謊稱只有幾天),以及我為何...
推薦序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
二○一二年是赫曼.赫塞(一八七七~一九六二)逝世五十週年紀念,德國學術界出版了兩本赫塞新的傳記重新探討赫塞的一生與文學成就。兩本傳記都一致強調,赫塞因為雙親管教過於嚴格,天性纖細敏感的他,從小就深深感到不被父母瞭解與接納;也沒有機會享受孩童與青少年時期該有的童稚與天真。這種被高度壓抑、甚至於不被允許可以好好發展自我意識的成長經驗,不僅讓赫塞一生飽受精神官能症之苦;而且在他後來的寫作生涯裡,他也經常刻意透過描寫不受拘束、任意而行的小孩與狂飆少年,來捕捉自己不曾享受過的青春爛漫滋味。
嚴厲管教子女的雙親,在赫塞時代的德國社會並不少見(雖然他的雙親長年在印度傳教),因為當時正是「鐵血宰相」俾斯麥以軍國主義快速帶領德國成為強權國家的時代。整齊劃一、唯上命是從,成為赫塞成長過程中,社會上隨處可見的行為基調。年輕人不知道自己是誰,即便努力尋找,但不一定能找到,因為外在環境對具有叛逆意識的年輕人極不友善。有些人屢屢受挫後只能退回舊日窠臼。比較具備戰鬥意志的年輕人,卻又不一定能找到一條可以在日後讓自己沉穩徐行的路。誠如著名的近現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對二十世紀所做的定義「極端的年代」,被極端化╱兩極化的思潮與意識形態不斷在這個世紀互相對抗、企圖尋找自己可以生根茁壯的土壤。有些人不是徹底避世禁慾、不然就是在塵俗裡盡情放縱。就連尼采對悲劇哲學的詮釋也都是從理性的太陽神阿波羅與縱慾狂歡的酒神戴奧尼索斯兩個對立的文化創造力量談起。
兩極化的論述大興,有時其實是意味著看不到出路。看不到自己的想法與世界有進行對談、謀求讓世界往更良善方向發展的可能。尤其麻煩的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互相爭戰的,不僅是不同立場的個人或群體,有時也會是同一個人自己內心深處撕裂矛盾的自我。
看不清,放不下,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擺盪,看不到前路的困獸之鬥,但又自以為是地想乾脆用戰爭來解決所有無法解決的問題。
奮力想掙脫父權的宰制,卻終究讓自己落入以威權對待他人的網羅,想用以暴制暴來清除自己心中感到不舒坦的障礙。
焦慮、厭倦、沮喪、不時緊抓著在黑色旋渦裡載浮載沉的脆弱理性覺知。這一切構成患有精神官能症的赫塞對「自我」的認知。他無法與人靠得太近,包括自己的妻子;他也不太能與自己好好相處,內心常常陷入嚴重的自我矛盾。
對赫塞而言,面對內心世界與外在環境的混亂、失衡,唯一能讓他證明自己存在價值、打造個我生命意義的,就是文學的美,就是書。然而,連這個部分,他都有痛。傳教士的父母親看重的是道德、倫理、品格、培養謹小慎微讓自己不要犯錯的堅韌意志。音樂文學的美固然不錯,但卻「只是」次要的附屬品。眼見自己雙親將藝文之美視為可有可無,這讓對追求美感經驗無比嚮往的赫塞自小就深感不被瞭解。他曾在一九二六年寫給妹妹的信上提到,這個創傷讓他感到與父母親疏遠。相較於雙親孜孜矻矻在亞洲傳教,真正能讓飽受精神病症糾纏的赫塞看見自己與永恆連結的,卻是自己筆下營造出來的美感世界。
然而,參雜著病態美感的暴力也算是美的一部分嗎?
這是赫塞在《荒野之狼》想討論的問題之一,也是這本書經常受爭議之處。出版這本書後,赫塞一直深感自己在這本小說裡對問題的闡述受到很多誤解。但是,作為讀者,當然我們也可以問,寫這本書時的赫塞真的有掌握到足夠的文學技巧來把這個複雜異常的問題妥善處理好嗎?
赫塞將他個人心中經常感受到的黑暗爭戰,透過年近五十歲的故事主人翁哈勒爾的自我放逐生活展現了出來。哈勒爾睥睨地望著人間,小說裡女房東姪子在〈出版者前言〉裡將他刻畫為深具靈性與天賦的個體,但不時會將週遭令他感到難耐之人視為「庸庸碌碌之輩」(「庸庸碌碌之輩」這個譯法為筆者所譯,與本書中譯為「脆弱沒價值的個體」不同)。哈勒爾既沉湎於無關世俗價值的美感世界,卻又有著殘害別人的意念。赫塞在《荒野之狼》的〈出版者前言〉裡假託發現哈勒爾手稿的女房東姪子之口說:「在這份手稿中看到的是時代的紀錄,因為哈勒爾的精神疾病──我如今瞭解到──並非個人的怪念頭,而是時代本身的病態」。
赫塞企圖將文學書寫轉化為時代精神病學的剖析,把長年糾纏自己的精神官能症看成是時代巨輪給過度壓抑自我的年輕人留下的無情印跡。他在書中描述太過壓抑的人生傷痕如何透過重拾青春期少男的無所顧忌、為叛逆而叛逆來尋找自我療癒之路。這樣的說法讓這本書成為歐洲六八學運與美國七○年代嬉皮文化拿來反抗世故、反抗社會傳統制約的寶典。然而,隨著當時西方年輕人嗑藥、吸毒、濫交、自製炸彈、綁架名人……種種傷人傷己的高爆發力行為越來越層出不窮,這本書即便當時相當暢銷,但也掀起比剛出版時更多的爭議,只是赫塞在此之前幾年就已經過世了。……
(以上摘自〈找不到出路的時代焦慮與心靈困境〉,全文請見《荒野之狼》一書)
柯晏邾(本書譯者,社會學/德國文學碩士)
《荒野之狼》出版後不久,赫塞在寫給友人的書信當中曾表示:「我的生平如果有任何意義,那麼必然是我個人無藥可救卻勉強控制住的,重視精神生活的人的精神官能症,同時也是時代精神的病徵。」(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三日致雨果.巴爾)「過去三年來因為我人性及精神的孤立和疾病,除了把我的狀態變成寫作客體,我找不到其他出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歐托.哈爾特曼)誠然,赫塞之所以寫下這個故事,部份固然是為了逃脫自身困境,卻也在於他自認所遭遇的困境不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精神的病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不惜把個人最不堪的一面呈現在讀者面前,好讓大眾認識到這個「時代病徵」。為了使這樣的「材料」具備一定的客觀性,必然要經過相當的處理才能讓故事昇華,其中之一就是增加作者和角色之間的距離。這個距離也是作者敘述故事所必需的。對個人而言,命運打擊總是毫不容情,要把這樣的苦難訴諸文字談何容易!有如把自己推上祭壇,赫塞築起了華麗的舞台,層層疊疊,然後親手執刀,一筆一刀劃開自己的生命,鮮血淋漓,一層一層逐步展露,直到內心最深處,直到故事的核心。
於是我們最先讀到的不是以哈利的觀點所進行的描述,而是〈出版者前言〉,一個曾和哈利的生命有短暫交集的人,以他「中產階級」人士的立場,觀察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哈利,描述哈利其人及其看似荒誕、病態的生活,探索「疏離感」、「精神官能症」的根源,藉著「出版者」轉述哈利最初的論點:
「(…)人類生命之所以變成地獄,只發生在兩個時代、兩個文明或宗教相交錯的時候。(…)而現在有些時候,整個世代處於兩個時代,兩種生活形態之間,因而失去其正當性,喪失所有道德,失去任何安全感和無辜。」
〈出版者前言〉之後眼見就要進入小說的情節敘述,卻被〈論荒野之狼〉的反覆論證篇幅打斷,論文之後才又繼續敘述哈利的生命故事。這種安排和後來布雷希特(Bertoldt Brecht)為敘事劇所發展的手法「疏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一九四八年左右發展成完整戲劇理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了創造距離,除了拉開作者和主角之間的距離,也有牽制讀者太快進入角色,轉而針對特定主旨思考或反思自身的作用。此一手法在小說技法當中非常罕見(若非前所未見),根本違反文學作品讓讀者代入、認同角色的常見期望及設定,結果是讀者在這個階段不會沈入角色,而是和作者一樣維持客觀的高度。
在一般的情節敘述之間插入論文,就結構上看似形式、情節分離,就整部小說主旨而言卻是相續相乘的,不斷圍繞著主題以不同觀點來闡述,產生另一種效果,亦即出現哈利的第一個鏡像,似乎是哈利/荒野之狼卻又不完全等同,是哈利自行營造多重哈利的第一步。這樣的安排自有深意,容後文再敘。此外這篇論文點出整部小說的核心觀點,首先描述哈利/荒野之狼的生命特徵,他的性靈生活、藝術家氣質,和中產階級的依存、排斥關係,是夜行族群,也是自殺一族;接著指出這類人解脫的途徑在於「幽默」,唯有幽默才能讓他們認識自我,讓衝突的心性和解。論文總結處卻提出「最後一個假定,以解開根本的偽裝」,顛覆前面所提出的人/狼、精神/本能二元觀點--這種分裂只是哈利/荒野之狼解釋命運的托辭,「是種非常粗糙的簡化」,其實卻是苦難的根源,因為「哈利不是由兩種本質組成的,而是有著成千上百種本質」。作者提出之所以想像只有一個所謂的「自我」乃是種文化虛妄,因為古老亞洲人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人類是無數層膜組成的洋蔥,是許多絲束合成的組織」,但這卻是哈利畏懼的,因為他相信「兩個靈魂裝在單一個心裡已經太多」,再多幾個必然完全撕裂;其實完全相反,是兩個太少,找出自己的其他面向才能讓他變成完整的人:
「你即將踏上更遙遠的、更辛苦也更艱難的成人之道,你要將自己的一分為二更加倍分裂,你的複雜性還必須要更加複雜。不是窄化自己的世界,不是簡化自己的靈魂,你必定要將更大部分的世界,最終將整個世界納入你痛苦擴張的靈魂,才得以也許在某一天走到終點,能夠平靜下來。」
至此作者的論點已經完整闡述,接下來的情節大致朝這個方向鋪陳。赫塞一向擅長將他的想法落實在小說結構上面(所謂「內容與形式統一」),既然藉著〈論荒野之狼〉提出「人是無數層膜組成的洋蔥」,這個主旨也就充分反映在小說行進間對「人」的探討。除了適才已經剝開的兩層(甚至再加上赫塞/作者這一層)和一個鏡像之外,還安排了其他鏡像,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赫爾敏娜。赫爾敏娜這個角色在小說當中具有多重意義,其中一層意義在於使作者的論點更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她或許不像哈利那般受過高等教育,未曾享受過一定的社會尊崇,但是她卻同樣受到社會的壓縮,使她無法完全開展自己的能力。另一層不是那麼直接以文字表達的,是她充當鏡像的功能──是哈利的也是赫塞的:她的名字是赫塞名字的女性變形(Hermann轉成Hermine),在小說中代表哈利年少時的同學赫爾曼;是哈利認定的「心靈手足」,她就是女性的哈利,和哈利有著相同的困境,能把哈利模糊感受清楚地表達出來;她以女性的角色卻讓哈利表現出被動、順從、依賴、被導引,簡言之即傳統女性特質,呈現哈利陰柔的一面。赫爾敏娜是女性也是男性,哈利面對這個鏡像也隨之呈現為男性或女性。藉助角色多面化,作者就是要打破角色的一致性,進一步呈現「人」的多重面向,強調沒有一個同一的「自我」,追求這樣的「自我」就是哈利這類人痛苦的來源。
但是這還不是作者闡述的最後手段。如果只說出經歷的痛苦和困境,點出問題所在卻沒有提出解決之道,那麼這部小說也就只不過是發了一頓牢騷而已。即使藉由小說結構及角色安排已經隱約指向答案所在,真正的「實踐」卻在壓軸的〈神奇劇場〉,讓哈利確實看清自己,知道人生的目的,以及他想要成為的是什麼樣的「人」。雖然小說出現框架情節不是新的手法,但是最後的這一部份,神奇劇場,卻是文學分析上無法歸類的,因為它很難被視為框架情節的一部份,卻也不完全獨立於故事架構之外;此外它的內容可說是顛倒現實與虛幻,時間、空間一再交叉錯置,這種種安排在文學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以上摘自〈華麗舞台上的一與多〉,全文請見《荒野之狼》一書)
花亦芬(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
二○一二年是赫曼.赫塞(一八七七~一九六二)逝世五十週年紀念,德國學術界出版了兩本赫塞新的傳記重新探討赫塞的一生與文學成就。兩本傳記都一致強調,赫塞因為雙親管教過於嚴格,天性纖細敏感的他,從小就深深感到不被父母瞭解與接納;也沒有機會享受孩童與青少年時期該有的童稚與天真。這種被高度壓抑、甚至於不被允許可以好好發展自我意識的成長經驗,不僅讓赫塞一生飽受精神官能症之苦;而且在他後來的寫作生涯裡,他也經常刻意透過描寫不受拘束、任意而行的小孩與狂飆少年,來捕捉自己不曾享...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