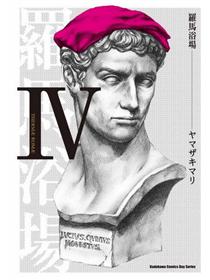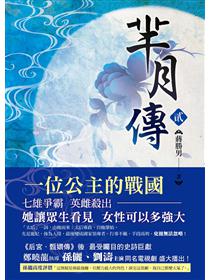贅婿 壹之玖 自掛東南枝
從中秋夜《水調歌頭》震驚了江寧的一干才子之後,寧毅一直窩在家裡看書裝病,無聊時與小嬋下下五子棋。今天他終於有興致出門,上午去學堂上課,下午去拿了之前讓人幫忙刷白的木板,隨後買些炭條,一路過來河邊,正好秦老與康老兩人都在。
蘇軾的《水調歌頭》,吟便吟了,寧毅對此是沒什麼心理障礙的。畢竟身為穿越者,自己知道的那些著名詩詞,是一種很不錯的戰略資源,如果日後閒不住了想要做點什麼事情,拿出來烘托炒作一番,加點名氣什麼的,用處很大。
前日,蘇老太公與蘇伯庸等人叫了他與蘇檀兒過去詢問一番,他隨意胡謅幾句,表示詞句不是自己寫的,誰知陰差陽錯云云……蘇老太公看了他好久,隨後笑道:「事已至此,對外可得保密才是。」
老人家很精明,信與不信那就兩說了,不過自己若真是什麼大才子,蘇家的立場其實也尷尬,於是大家也只能猜來猜去。
才子?呵呵,當才子哪有當個贅婿舒服?不用做事,不用負責,人家對你也沒有太多期待,毫無壓力,要離開這種生活,那才是白癡呢。好不容易休閒了幾個月,在沒有什麼大事之前,入贅的這個身分是堅決要賴定不走的。他心中如此想,自己倒也覺得有趣,只是若說給別人聽,怕是連小嬋都不肯信。
外面的流言肯定有,寧毅也大概能猜到是什麼樣子,倒是小嬋說起止水詩會時,他才被康賢這個名字嚇了一跳,最後不免啞然失笑。以前便知道康老不簡單,只是沒想到這麼大名頭。
康賢笑著說道,「你那《水調歌頭》,寫得實是太好,此詞一出,怕是此後幾年秦淮中秋,都無人敢再做詠月詞了……實是想不到,你這不學無術的小子竟有如此詩才。」
「都說了我不懂詩詞。」寧毅喝一口茶,「小時候有個衣著破爛的游方道士從家門前經過,吟了這首詞,我記下了,就是這樣。」他跟蘇老太公也是這樣說的。
秦老大笑起來,康賢也笑罵道:「這說法連三歲小童也不會信!你這人就是太過憊懶,需得敲打才是!」
此時兩老已經下完一盤棋,三人坐在一邊閒聊。秦老拿起茶杯,倒是對另外的事情感興趣了:「寫字?這麼說來,立恒想以炭條在白板上寫字,用之於學堂之上?」
寧毅點了點頭:「沙盤一次能寫的字太少,用起來也麻煩,終究不如這樣寫下來方便。」
就教學來說,此時上課是以沙盤寫字,寫上一個字沙盤便要推平一次,先生僅僅是演示字體寫法而已,大部分知識都是口授。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在先生說話時必須聚精會神,說完之後還得馬上理解,努力記下,若不是特別聰明的學生,想要跟上教學進度,其實是相當有難度的。
當然,對於秦老康老這些人來說,這樣的教學方法延續了上千年,自然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學問是上等人的東西,想要成上等人,不想吃苦怎麼行?這本身便是一種考驗。
秦老拿起一根炭條在白板上劃了劃,隨後皺起眉頭:「沙盤柔軟,以樹枝在其上書寫,與毛筆技法相同;木炭卻很難書寫,這等改法,怕有不妥。」他見事的角度比較不同,一下便提出了異議,畢竟寧毅作為先生,在課堂上不以毛筆的技法寫字,這事情說起來可大可小。
隨後康老也試了試,皺眉道:「此事需得謹慎才行。」若寧毅是他的弟子,說不定他已然罵上一頓,以當頭棒喝的嚴厲指出事情的嚴重性。
他們的擔心,寧毅自然理解,此時笑了笑,蹲下去也拿了一支炭條:「寫字本為陶冶性情,何況這些字體與毛筆字體其實有些共通之處,若僅為記錄而用,倒不妨放寬一點,也算是……多一個角度。」
他如此說完,伸手在白板上面寫起來,「紅酥手 黃藤酒 兩個黃鸝鳴翠柳」,這一句是楷書的模式,隨後變為隸書,「長亭外 古道邊 一行白鷺上青天」。
這兩行寫完,字體變為宋體:「三山半落青天外」。
宋體字在武朝還沒有出現,秦老與康老對望了一眼。
寧毅一向喜歡以富有衝擊力的方式說明問題,以前他與人談生意也都是這樣作,下一行轉為漂亮飄逸一點的瘦金體:「二水中分白鷺洲」。
接下來轉草書:「西北有佳人 自掛東南枝」。
然後斜黑體:「欲窮千里目 自掛東南枝」。
白板不大,寧毅寫完,收起炭條:「如何?」
秦老與康老早已笑罵出來。
「字倒是能入眼,詩詞真是瞎搞……」
「有辱斯文!可惱!」
「你這性子真是太過憊懶,呵呵,這些詩算是什麼東西……」
口中這樣說著,但兩人的目光卻沒有離開過那塊白板,偶爾唸出來,順口點評一番。
「西北有佳人……真是不學無術,分明是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此歌出自《漢書》,再接自掛東南枝……你莫非覺得西北對東南押韻嗎?」
「康老英明。」
「你若是我的弟子,少不得要叫人拿棍棒抽你!隨手塗鴉也要波及先賢名作,欲窮千里目,自掛東南枝?你不怕王之渙化為厲鬼找你算帳!句句都自掛東南枝,這首《孔雀東南飛》倒也倒楣,那東南枝可是招你惹你了?」
「只是覺得將詩詞如此拼湊一番,別有一番風味……」寧毅忍不住大笑:「西北有佳人,自掛東南枝;舉頭望明月,自掛東南枝;空山不見人,自掛東南枝;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自掛東南枝;人生自古誰無死,不如自掛東南枝……」
康老搖著頭:「事涉先賢,務必嚴謹!」話語中有幾分好笑,倒也有幾分警醒意味。
另一邊的秦老則繼續盯著白板,突然說了一句:「明月幾時有……」
「自掛東南枝!」康老笑起來。
秦老拿了炭條,指了指前幾句:「同樣也是拼湊,不知出處,想來是立恒舊作了?紅酥手,黃藤酒……後面的接得不好,這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倒該是一句……而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好意境,當是另一首詩了……」
他以炭條將這幾句圈起來,把「紅酥手 黃藤酒」與「長亭外 古道邊」分開,看了看,又在中間畫了一條,大抵覺得這兩句應該也不是一首。
康賢也點了點頭:「該是兩首。」隨後看看寧毅。
寧毅有些佩服,如果是他在這種情況下看了這十二個字,或許會認為它們是一首詩詞才對,畢竟對仗工整,詞意也算完整,但眼前兩人卻是僅憑直覺,便將詞句劃開。
「該是四首詩詞……不知是已有全詩,還是偶得殘句?」秦老朝寧毅望來。
一旁,康賢嘆了口氣:「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只是殘句,卻也已是登堂入室的大家氣度了。」
寧毅看著兩個老頭,隨後笑起來:「呵,殘句。」他攤攤手,「說了我不懂詩詞。」
「這小子不實誠,否則今日可得幾首好詩……」
話是這樣說,但如今寫詩寫詞,作者偶得殘句是尋常事,兩人倒也不再多說,隨後談論起寧毅的書法。這是相當專業的領域,詩詞寫出來可以說是別人寫的,字卻是自己的,況且白板上好幾種字體自成一氣,已然形成系統,兩人都是此道大家,自然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門道。
對他們這種書法大家來說,一筆筆的漢字自有其魂魄筋骨,這些炭條寫出來的字跡或許還到不了大家程度,但也已經顯露出足夠的功力。這年月,誰也不可能專門練習這種筆法,能以炭條寫出這等字跡的人,書法功力自然得更往上好幾成,特別是那幾種之前沒見過的字體,對他們來說,更是有著難以言喻的價值,比如那「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鷺洲」的宋體與瘦金體,只讓兩人覺得賞心悅目,大有門道。
瘦金體與宋體,本來就是宋朝時出現的,武朝軌跡與宋朝類似,文人眾多,儒學高度發達,求新求變的過程中各種創新出現,而這兩種字體,無疑是既具創新又最符合當代人審美的成果||這兩種字體,站在了時代的基礎上,彷彿是由量變達成了質變,做出了完美突破的成果。
寧毅寫的時候沒有想太多,頂多是嚇嚇人而已,只是以他的思維方式來說,各種複雜的權衡早已在潛意識中完成,過濾出一個最簡單的結果而已,而他頑童般的斜黑體,也恰好證明了他平日裡就愛瞎搗鼓這些東西,既能保持宋體與瘦金體的衝擊力,又能將這種驚豔與衝擊變得自然,不至於只是一味的尖銳。
隨後兩老探討書法時,寧毅則保持沉默,只偶爾說幾句自己知道的關鍵點。兩老是真正的書法大家,基本功比寧毅扎實得多,他自是少說多聽藏拙為上,他這些日子正在練書法,偶爾聽得一兩句,也覺得大有裨益。
若是普通才子學人之流,怕是不可能得到兩老這樣子的教導,當然,兩人若以教學的態度,大抵是以針對性的講解說給弟子聽,普通學子聽得太多反倒無益,只是寧毅本身的歸納、辨別、整理能力強,對兩人的淵博也只是佩服,不至於崇拜或盲從,聽聽倒是無所謂的。
對於書法的議論持續了大約半個時辰,幾人偶爾拿炭條在白板之上寫寫畫畫,手上已然黑成一片,隨後到河邊洗了手。秦老與康老這時候倒不說炭筆與毛筆筆法的事情,以寧毅展現出來的水準,只是在小小書院中做些革新,想來無需他們多加提點。
寧毅拍了拍手,隨後甩著手上的水滴,隨口說道:「其實木炭寫起來確實差了,過些日子我打算弄些石膏,做幾支粉筆出來用,到時候把木板刷黑,上面的字跡是白色的,比炭筆字要清晰,擦洗也簡單。」
「石膏?」康老疑惑道,「那粉筆又是何物?」
「將石膏以火煆燒之後,加水攪拌,然後在模具中凝結成條狀,可以用來書寫,比起炭筆不容易模糊,手上也不至於髒成這樣。」
武朝這時早已有了石膏石灰,康老想了想,隨後點頭:「倒是沒錯,石膏煆燒後,確實可用於書寫……呵,此事倒不用另找他人了,你若想要,老夫吩咐人製造一批給你便是,倒不知具體有何要求?」
康賢家大業大,寧毅是知道的,自然也不推辭,當下比劃一番粉筆的樣子。製作粉筆的工序本就簡單,即便沒有刻意去做,一些石灰窯中結出的硬塊也可勉強用來寫字,要說的地方倒也不多:「可以叫匠人多試幾次,或者摻點粘土之類的雜質,能儘量找個最適合書寫的配比出來就最好了。」
「此事老夫省得……阿貴!」康老每日出門,兩男兩女的跟班總是在附近,此時叫來旁邊一人,「寧公子的說話你也聽到了,回去之後將此事吩咐下去……」
先前三人手中拿著炭條,泡了的茶自然不好去喝,這時候時間稍晚,也沒了多少下棋的心思,幾人在茶攤坐了一下,康賢的丫鬟又泡了新茶來。白色木板還放在旁邊,話題自然仍在字上打轉,不一下子,秦老點評起如今一些書法大家,一路信手拈來,順便將康賢的字也調侃一番。
康賢笑罵出來:「隸書、狂草,老夫或不如你,若論正楷,你不如老夫遠甚!」
秦老笑道:「這便是術業有專攻了,明公整日以君子之道訓人,楷書若差,未免失了信服力。只是單為訓人方便便將楷書練至如此境界的,明公可為史上第一人……」
玩笑片刻,秦老想想,轉開話鋒。
「不過見立恒字跡,倒是令老夫想起一人,此人也為我秦氏本家,頗有才華,早年在東京曾以行卷投於老夫,才氣談吐都極為出眾,並且寫得一手好字,其風格章法,與立恒這句﹃三山半落青天外﹄的風格類似,得顏筋柳骨之妙……只是他當年字跡未脫窠臼,如今倒是不知如何了。」
康賢笑了起來:「秦公所言,莫非是今任御史中丞的秦檜秦會之?」
秦老點了點頭:「便是此人,早幾年遼人南下,曾將他一家擒去,不過此人也是有勇有謀,深陷虎狼之地,仍能與遼人虛與委蛇,最終在前年遼人攻山陽時趁機攜家人南歸……他如今已是御史中丞了?」
「月前邸報之中已傳來此事。因有南歸之事蹟,秦檜如今頗受重用……據說當時遼人本欲扣留其妻,兩人煞費苦心演出一場好戲,方得以雙雙南歸,逃亡途中幾名忠僕拼死殿後,方得逃脫,可見其御下有方……唉,比起前線戰事不利,他此等事蹟,更是顯得珍貴。不過,如今朝堂之上,倒也並非一味讚賞,此人南歸之事,可疑之處頗多,怕是另有蹊蹺……」
秦老想想,搖了搖頭:「此事難說,不過毫無根據隨意揣測,並非君子所為。據老夫當日所見,此人品性端方,為人中正大氣,憂國憂民,絕非是裝出來的,今後如何,且觀其行便是……呵,說起來,會之老家也在江寧,他今後若來,立恒倒可與之一見,說不定可有共同語言。」
寧毅眼角微微抽搐,隨後表情複雜地摸了摸鼻子,過得片刻,終是笑了出來,敷衍的點了點頭。
秦老與康老倒是看不出什麼不妥,康賢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望向寧毅:「不過,立恒如此才華,莫非真無半點功名之念?」
純以時間說來,寧毅與兩人的來往並不算久,如同康賢所說,不過是下下棋聊聊天的如水之交。不過文人大抵都有憂國憂民的念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或是習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都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如今看來秦老每日悠閒下棋,康賢富貴閒人做派,其中必然有複雜的緣由。
從這些時日的接觸,到中秋的《水調歌頭》再到這時的文字粉筆,種種種種,對二老來說,寧毅的才學已經無需討論了,接下來的疑問也就明確起來。如同往日秦老偶爾嘆息寧毅當個贅婿未免可惜,其實更多的是嘆息而並非疑問,但這次的提問,意義卻並不相同。
一下午的對話,字裡行間,寧毅想要否認掉才子之名的意圖很明顯,看來並非是開玩笑或隨口敷衍。世間哪有人真的沒有半點功名之念?總該有點什麼隱情才是。二老的身分都不簡單,康賢既然問出這句話,實際上是真正動了惜才之念,打算動手幫忙了。
秋風蕭蕭瑟瑟地自河畔吹過,撫動了柳枝,秦老舉起茶杯,緩緩地吹動著杯中的茶葉,顯然也是好奇寧毅的回答。
「我知道這樣說出來或許沒人信,不過……」寧毅淡淡地搖了搖頭:「有些事情,的確不想去做。才子也好,名聲也好,功名也罷,不願去碰。這個是真的。」
語氣淡然,但寧毅是認認真真地在回答這個問題,沒有勉強,沒有苦衷,真誠而坦蕩。雖然他看來不過二十出頭,然而此時此刻,一身的氣質卻絕不能讓人忽視,看起來超然灑脫,不拘於物,若他是一名四五十歲的中年人,那便是成熟穩重,淵渟嶽峙,語擲千金,不容置疑。
也正是這樣,才更讓兩老疑惑。
對康老這樣的人來說,問寧毅功名之事,意義絕不簡單,況且以幾人的來往方式,康老也並非是與他做交易,需要他報答什麼,若是一般人,或許會腦袋一熱為了傲氣而推辭,但寧毅絕非這樣的愣頭青。
「我也明白此事讓人疑惑。」寧毅有些無奈地苦笑起來:「兩位或許不知道,幾個月前我頭上挨了一下,昏迷數日,醒來之後,前事忘得七七八八,功名之事,眼下確實很難上心,與一幫才子流連青樓畫舫,吟詩作賦得女子青睞,更提不起太多興趣。如今偶爾給孩子說個故事,或來河邊下棋喝茶,倒也自在……如今這生活,我是滿意的,至於些許白眼,又何必去管?只是明公好意,在下也確能理會。」他拱手一禮:「此事,立恒銘記在心。」
這段話自然有真有假,只不過也不可能把實情說給他們聽,將心情與失憶的事情掛上鉤,推的一乾二淨反倒是最好的辦法。
果然,這話說完,二人都有些恍然,康賢搖頭笑了笑:「想不到竟有此事。」只當寧毅失憶之後,想法有些古怪。
隨後康老也不再提,喝了一杯茶,寧毅拿起白板和木炭,告辭轉去豫山書院。待到他的身影消失在遠處,康老才嘆了口氣:「沒想到被那樣一打,倒打出個淡泊心性,年輕人之中有此等心性者,卻是難得,只是可惜了那一身才華。」
秦老笑著喝口茶:「他如今不過二十出頭,日後變成怎樣,現在怎說得準?以他的才氣,該遇上的事情,避也避不過的。只是今日,有些事情,倒是令人擔憂……明公,立恒此人,太過務實了。」
康賢皺起眉頭:「你這一說,事情倒也的確是如此。看他的詩詞隨手皆是佳句,偏對詩詞之道毫不在意,書法信手拈來,多種變化,竟也都能達到如此高度,看來平日不過是當成消遣而已,這些事情,在他眼中竟還不如粉筆來的有趣。」
秦老點點頭:「務實本為好事,可若太過務實,直來直往,日後怕有麻煩……雖然立恒此人頗懂趨利避害之道,但畢竟年輕氣盛,有些事情上,還是頗為高傲的。他不願去敷衍那些學子,推了邀請,在你我面前,卻並不多做掩飾,大抵也是為此。」他想了想,隨後笑了起來:「此事無須多想,我等以棋會友,操心太多,未免過分,既知其想法也就是了。今後事情會如何,且看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