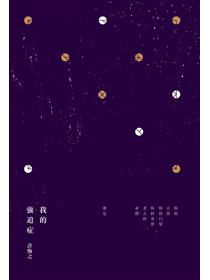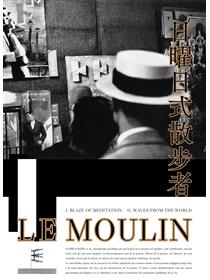瑪麗安,你知道嗎?我已不想站在對的一邊
我祇想站在愛的一邊……
──〈一九七六年記事之四〉
在詩與愛的巨幕中,展開從未見識過的抒情光影。
一開始,當我在樹洞中學會歌唱,愛的失落及獲得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題,「瑪麗安」這帶有濃濃異國風的名字,既是性靈的代號,也是一種類似綠度母般的母親幻想,聲音幻想。
瑪麗安是假,也是真,是內,也是外,既是歌聲的樹洞,也是詩的傳奇本身,大至集體的國族命運,小至個體的悲歡離合,我都可以時時在詩中向瑪麗安持咒祝禱。──楊澤
四十年後,薔薇學派誕生了又一次。經典大碟重發,像班雅明筆下的歷史天使,背對著名之為進步的風暴--究竟薔薇仍會被推捲到風暴深處,亦或就此浮盪到遠涯--木心寫過的,童年時代好不容易找回又瞬間脫手遺失的,那只青瓷小盌。──楊佳嫻
《薔薇學派的誕生》是詩人楊澤第一本詩集,最能夠代表楊澤詩作風貌。《薔薇學派的誕生》一出世,纏綿呼喚愛神精靈「瑪麗安」,便成為別名般絕響。在七○年代末期,楊澤詩歌語言的美學新調,開啟了現代派詩歌巨幕,以及未有人見識過的抒情光影。
詩人,除了詠懷,也是新時代的掌門人;「學派」的誕生,是他對自己的知識和藝術的期許,肯定世界,並開始去規劃,去認同。
四十年後,楊澤一字一句重新修訂詩作。特聘金蝶獎美術設計師黃子欽封面設計、內文美術編排,藝術家杲中孚為《薔薇學派的誕生》繪製專屬版畫畫作。封面採取進口高級美術羊毛紙五色印刷,裸背穿線裝幀,賦與詩集新一代樣貌。
作者簡介:
楊澤
上世紀五○年代生,成長於嘉南平原,七三年北上唸書,其後留美十載,直到九○年返國,定居台北。已從長年文學編輯工作退役,平生愛在筆記本上塗抹,以市井訪友泡茶,擁書成眠為樂事。
章節試閱
第一輯: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
1.我在1977年的春天在地下鐵的小站看到空中花園的花季海報時大多數人已然去過而且回來了。
2.以後我迅速的發覺在我居住的城市委實祇有兩種人:一種是去過空中花園的,一種沒有去過;而沒有去過的人委實是並不存在的。
3.我迅速的發覺:空中花園是我們可能去過的最遠的地方;空中花園是我們生存的邊界,是同歲月,季節,黃昏,夜晚一樣獨立堅固的事物;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空中花園遍植無神論的花樹的原因。
4.我迅速的發覺:空中花園已成為我們的詩,我們唯一的宗教。
在畢加島
在畢加島,瑪麗安,我看見他們
用新建的機場、市政大廈掩去
殖民地暴政的記憶。我看見他們
用鴿子與藍縷者裝飾
昔日血戰的方塊吸引外國來的觀光客……
在畢加島,瑪麗安,我在酒店的陽臺邂逅了
安塞斯卡來的一位政治流亡者,溫和的種族主義
激烈的愛國者。「為了
祖國與和平,…」他向我舉杯
「為了愛,…」我囁嚅的
回答,感覺自己有如一位昏庸懦弱的越戰逃兵
(瑪麗安,我仍然依戀
依戀月亮以及你美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肉體…)
在畢加島,我感傷的旅行的終,瑪麗安
我坐下來思想人類歷史的鬼雨:
半夜推窗發現的苦難年代
我坐下來思想,在我們之前,之後
即將到來的苦難年代,千萬人頭
遽爾落地,一個豐收的意象……
瑪麗安,在旋轉旋轉的童年木馬
在旋轉旋轉的唱槽上,我的詩
我的詩如何將無意義的苦難化為有意義的犧牲?
我的詩是否祇能預言苦難的陰影
並且說,愛……
斷片
在那個遙遠的城市,我猶記得,某次當我鼓起勇氣公開表示我對一位朋友大量製作鹼濕電影的不滿,我的朋友忽然轉過臉來大聲的對我說他的電影並不比「死亡」低級或者暴露:
「──沒有什麼,是的沒有什麼比死亡更暴露更obscene了。我的影片」他竭力對我呼喊,眼神裡閃動著我不了解的一種奇異的熱情「我的影片假如你了解的話,是用來對抗死亡──是以肉體來反叛它的…」
我的朋友,他的意思或許大部份是指血腥動作片而言。衡之當時,我聯想到的卻是圍繞在生活周圍的車禍的現象,兇殺的現象,裸屍的現場……
啊,請不要圍觀他人的死吧!冷漠的羣眾請莫要議論紛紛,因為我們同是一樹枯枝上的顫危危的敗葉。
B花蟲鳥獸
薔薇學派的誕生
黃昏的一半。
陰鬱的注視在空氣中燃著
彷彿有人(彷彿沒有)
走進來,說「昨日……」
溫柔的聲音迅速凋落。而
手上的薔薇,飄散
一地。
黃昏的一半。
一朵朵薔薇的幻影在空氣中漂著
「為了向人們肯定一朵薔薇幻影的存在,
我們必要援引古代、援引象徵
甚至辯論一朵薔薇的存在?」
黃昏無限延長。
一朵朵薔薇的幻影在空氣中燃著
很多人走進來,說:「薔薇
開了,薔薇……」
黃昏無限延長。
一朵朵薔薇的幻影在空氣中亮著
「昨日以及今日
以及今日的幻影,以及
明日的幻影必然是
屬於薔薇學派的。」
水荷
十一點五○(無人看見的一剎)
一水池的夏晨風荷開始偷偷的垂下了她們
展示許久的美麗手勢,且漸漸
漸漸抱緊自己一身止不住的興奮和睏意
抱緊自己一顆小小的脆弱的心睡去
在夢中
她們夢見自己的倒影
被種植在更廣大完美的一座水池裡
她們夢見,有一夢樣
溫柔的女子
飄然走來,專注
深情的眼神裡
他們發現了
自己及自己的來源
鴿子
挺純白胸腹在教堂屋頂上散步的
鴿子啊
請像鐘聲一樣的走下來,三兩隻
在我流動的肩上飛駐
像秋後的陽光輕輕…
送信者
坐在他人的窗下,憂愁想家
從遠方來的送信者
終於疲倦的睡著了。像他懷裡的信。
室內的燈火照在他多愁的臉上,露宿
異地的肢體,或者更像一紙沒有
信封保護的家書。而這樣
感覺寒意與燈火
在夢中,他夢見了
涉河的暗夜,他焦慮的遺失了
所有的信…
睡在他人的窗下,憂愁想家
或者他夢見的是:
一隻青色的鳥,天空小徑
銜著用絲帶繫住的信件飛越
前方半山…
C 儀式之餘
閣樓上的情歌
閣樓上
我冷冷堆疊起來的自抑
已堆疊成一座──與那些經年冊籍等高的
小小的浮屠九層
我小小的慾望
小小的美德
小小的情怯
及小小的鼠類便同居其中
閣樓上
四壁總默默的
面壁著對方:
我高坐其間
在一盞冷燭的羣書中埋藏自己。
時日曠持,
每當我廢然舉額──小小的
鼠類便狂肆成羣的奔竄過
我耳中寂寞的甬道
我的幻覺彷彿親見:
啊,那些掙扎的鼠屍
在那修練不成的三味真火中……
閣樓上
當我舉眼欲曙的今晨
壁上竟款步走了下來
一名如花似玉的美女:
我笑了笑,延請伊一旁
為我焚香、濡墨
便獨自坐抄起佛書來
一九七四‧十二
D 瑪麗安‧瑪麗安
薔薇騎士的插圖
a.
在古堡花園的廢墟,錯失了自己的年代的
光與暗影紛紛向我們描繪
那位遠方來的,被時間擊傷
被愛擊傷的薔薇騎士
我們彷彿看見,他靠坐在石像下沉思的憂愁
聽見他,像追問昨夜夢境一樣,苦苦追問
薔薇的來源和永生:
「萬物駐足,靜止
在遙遙不可及處
在我們雙手的
擁垉外。
我已然進入了
用薔薇,盛放的薔薇
凋敗的薔薇建築的歲月
我已然進入了──
啊,深淵一樣廣大的花園中心」
b.
坐在花園的中心,死滅永生的
薔薇地帶,瑪麗安,我們祇漠然的翻閱:
一本薄薄的附有插圖的書
(我們的混亂與憂鬱多麼像
那些錯失自己時代的光與暗影)
騎士就是這樣被畫好的,瑪麗安
憂愁,微笑,而且在手上提著劍
而薔薇,擊傷我們世界的薔薇啊
多麼雷同於
我們心中的一種
宿命的悲傷
給格弟非
a.
親愛的格弟非:我花了長長的一個冬天無所事事
與瑪麗安在一起讀書以及作愛。
親愛的格弟非,我們在鏡子上
簽我們的,以及你的,名字
這一切你知道,全為了你
在海潮的起落
在日月的升沉
在年輪向內急速,而暈眩的旋轉旋轉
啊,格弟非
在金黃的花系上
你是花冠、你是花萼、你是花粉
(幾次牆外孩童的稚笑裡,格弟非
啊,我兀然坐起,以為聽到了你)
親愛的格弟非:我願意再花一個春天等待你。
親愛的格弟非,我們要你
光一樣,從鏡子裡向我們奔來
坐在我們的眼裡歌頌
歌頌你自己
b.
親愛的格弟非 我願意花一千個春天等待你 擁有你
親愛的格弟非 我們在千面鏡子上簽我們的
以及你的 名字
這一切啊,你知道全為了我
c.
發光的河流是什麼,格弟非
燦爛的花色是什麼,格弟非
敗落的城市像什麼,格弟非
陰鬱的街道像什麼,格弟非
坐在金黃金黃的花系上
格弟非,啊,請不要訕笑
敗落的城市像我們像我們
陰鬱的街道像我們像我們
d.
在夜與黎明的邊界
格弟非,我記起了──
我們的名字也一度是格弟非……
在夜與黎明的邊界
格弟非,我們一直是你一直是我們
我驕傲的僭用你的名字沒命的奔跑
格弟非,祇要我們越過
那道愛與死的虛線
祇要我們一起追隨太陽
從鏡子裡奔湧而出──
則我們終於擁有了你
則我們也終於擁有了我們自己
第一輯: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
1.我在1977年的春天在地下鐵的小站看到空中花園的花季海報時大多數人已然去過而且回來了。
2.以後我迅速的發覺在我居住的城市委實祇有兩種人:一種是去過空中花園的,一種沒有去過;而沒有去過的人委實是並不存在的。
3.我迅速的發覺:空中花園是我們可能去過的最遠的地方;空中花園是我們生存的邊界,是同歲月,季節,黃昏,夜晚一樣獨立堅固的事物;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空中花園遍植無神論的花樹的原因。
4.我迅速的發覺:空中花園已成為我們的詩,我們唯一的宗教。
在畢加島
在畢加島,瑪麗安,...
作者序
瑪麗安,我的樹洞傳奇
──二○一六年新版序
/楊澤
a
想像,如果你不反對,一個來自南方小鎮的年輕人,剛過了懂得慕青春少艾的年齡不久,初抵外地的大都會求學,大街小巷,目光所及,一切對他都顯得如此新鮮立體,甚至突兀神奇。
想像,如果你不反對想像,上蒼給這年輕人天生一副多愁善感的性情,還有難得富磁性的低音嗓子。想像他初來乍到,五光十色的大城,加上以大城為背景的少艾之戀,固然令他欣喜萬分,遇事好鑽牛角尖的個性,一種無以名之,屬於一般志氣薄弱的年輕人才有的「心魔」,偏讓他吃盡苦頭,他在校園裡,在公車上,很快認了三四個乾妹妹,接連談了好幾場戀愛,到後來,竟因暗戀一個連手都沒碰過的學妹,丟掉了最先愛上,也最愛他的舊情人。
這不甘寂寞的年輕人,對愛情絕望,又自認沒愛活不了,活不下去的年輕人,同時對生命感到困惑不已,他處處模仿之前囫圇吞下,一知半解的西方存在主義讀物過日子,在內心凹洞為孤獨蓋迷宮,為憂悒起城堡,就差那麼一點便因他的天生好嗓子,被人強拉進教會聖詠隊唱詩歌,所幸他還有自知之明,在那之前,已先加入校內的現代詩歌社。
想像,如果你不反對想像,而且如果你多少知道青春,任何時代的青春,是怎麼回事,而青春時代的愛情又是怎麼回事,想像這年輕人平常愛跑到河邊玩,對著河水唱歌,半是兒戲,半是一個人落單了沒事幹,然而,就像古代詩家早說過的,「雛鳳清於老鳳聲」,幾回初試啼音,當河邊傍晚吹起涼風,天地為之變色,一時間,他竟深深愛上了自己的聲音——深深被自己嗓子所能模擬出各種情感光譜的憂愁及悲傷,被自己低沉厚重的嗓音,更準確的說,被那人聲本身給撼動了⋯⋯
b
李漁當初是這樣說的: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也就是,就各種能發出自己聲音的樂器而言,人聲不折不扣是最美好的一種。
可我得很快補上一句,人聲和絲竹之音層次有別,人聲並非任何樂器,它不止最美好,也最是獨特。
認真說來,人聲是何等素樸鮮活,複雜奇妙,而又不可思議的東西呀!人聲的背後有許許多多無意識,或人直接意識不到的美妙東西,因為它就來自人身這神奇的生命樹,知識樹,愛情樹本身。
人聲和絲竹之音層次有別,磁場有別,頻率有別,因為你我體內有太多奇妙的腺體,奇妙的「性靈的滋液」,掌握著人聲最富神韻的部分。人聲來自生命的源頭,而那正是吾人性靈,或「情之所鍾」的各種竅穴,孔洞之所在。
從伊甸園以降,戀愛中人於萬千場景的呢喃低語,既像是重演在愛情樹上偷偷刻下戀人名字的儀式,更宛如頻頻對著樹洞呼喚吶喊。古往今來,對「鍾情正在我輩」的詩人歌人而言,戀愛中人的忽忽若狂,戀愛中人的歌哭無端,乃是無上啟示,性靈的秘密與奧義,人聲的秘密與奧義,盡在於斯矣。
也因此,我們可以充分想像與理解,當傍晚涼風吹起,那外地來的,一臉迷茫的小伙子,那情場失意,只好對著河水唱歌的年輕人,反而得以誤入自己歌聲的樹洞,在一遍遍的自我聆聽底下,進一步偷覷到靈魂與肉體的雙重命題,以及自己未來的人生任務。退一萬步而言,即使人心再孤寂,世界再一無所戀,那個在向晚河邊徬徨的年輕人,他無意間發現的,可是一筆何等獨特的生命財富,何其大的性靈寶藏啊!
c
詩集《薔薇學派的誕生》(一九七七)及《彷彿在君父的城邦》(一九七八;一九八○)是我最早發表的兩本舊作,初面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今天回首已整整四十年。
兩本詩集斷版多年,而我也早過中年多時,黃仲則名句「結束鉛華歸少作,摒除絲竹入中年」,因此對我不適用。反而是,龔定庵同樣有這麼兩句:「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常會不自覺想起。有一點要說明,在我理解中,上句寫「少年哀樂過人」,恐怕並非龔定庵,或哪位詩人獨有的經驗,而下句說的「歌泣無端」,更是每個多情善感的年輕人皆如此的。
這些舊作約略皆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之間,也就是從大二大三到其後唸外文所,在台大文學院當一名小助教,執編《中外文學》階段,到八○年匆匆出國前,快筆揮就而成。當年我幾乎無日不詩,隨身帶著小筆記本,隨時隨地在其上塗塗抹抹,在校園裡,在公車上,甚至在大馬路邊,都會有靈感生起。出國打開了視野與創作的眼界,最早的那份詩的情懷證明越不了大洋,二十五歲,我後來才懂,乃是少年詩人最敏感,刻意,把自我的氣球一昧撐到最大,復從中瞬間爆裂的分水嶺。
去年初夏,我出了詩集《新詩十九首》,算是對回國後這麼些年來的人生感慨做了點總結。從《薔薇學派的誕生》到《新詩十九首》,一個人的大半輩子就這般過去了!回頭想到重印舊作,固然是重演一齣「青春悲喜劇」,但也堪稱喜事一樁,顯示個人有幸在時間的恩寵下,義無返顧,正堅定朝向某種人生的下半場,甚至是延長賽的那番深一層領悟邁進。
夢中我仍見得到,那條流過校門外的河,還有,就我一人知道的,隱現在河面,在天空上的樹洞,那座歌聲的樹洞。樹洞中有我當年遊蕩其間,整座大城的倒影,就只是倒影罷,因為樹洞中的一切其實都是我夢中的發明。
d
在某一層次上,我並未真正活在一九七○年代,那座叫台北的大城(台北日常);也因這樣,遂得以詩歌見證另一座看不見的城市(台北非常),寫出「在台北」這樣的散文詩。那是白色恐怖時代,一個讀了太多魯迅,太多芥川陳映真的苦悶文青,他常常在白晝亮晃晃的馬路上找女神,同時又將自己放逐荒野,天天擺張慘綠兮兮的臉,在內心喃喃,只有自己聽得到的獨白: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一九七七年中,我曾拿到一張盜版黑膠當禮物,那是當年英國最酷的中古搖滾樂團 Jethro Tull的新專輯,來自那位我始終手都沒碰過的女孩。但在那之前,我已對中古世紀,歐洲騎士文學十四行詩著迷,為了回報女孩的餽贈,我寫了「暴力與音樂的賦格」一詩。現在回頭看來,那是一首從 《薔薇學派的誕生》到《彷彿在君父的城邦》的跨越之作,宣告我已從稍早偏甜的綠騎士風走向苦澀萬分的藍騎士時代。
年輕詩人的 hubris (或所謂「悲劇缺陷」),常就在他過度旺盛,強大的心魔,可說成也它,敗也是它。一開始,當我在樹洞中學會歌唱,愛的失落及獲得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題,「瑪麗安」這帶有濃濃異國風的名字,既是性靈的代號,也是一種類似綠度母般的母親幻想,聲音幻想。
瑪麗安是假,也是真,是內,也是外,既是歌聲的樹洞,也是詩的傳奇本身,大至集體的國族命運,小至個體的悲歡離合,我都可以時時在詩中向瑪麗安持咒祝禱。但當青春的夢想變得愈來愈激進,孤獨,且充滿了焦慮──從藍騎士往國族的鐵甲武士不斷傾斜──瑪麗安再也救不了我。若干年後,我也不得不因此,告別瑪麗安,我那永不再的樹洞傳奇。
青春,哦青春!像那滿天蟬鳴,我一度聽見它的歌唱,至今也仍迴響在心底。
木馬.唱盤.瑪麗安/楊佳嫻
四十年後,薔薇學派誕生了又一次。經典大碟重發,像班雅明筆下的歷史天使,背對著名之為進步的風暴──究竟薔薇仍會被推捲到風暴深處,亦或就此浮盪到遠涯──木心寫過的,童年時代好不容易找回又瞬間脫手遺失的,那只青瓷小盌。
我讀楊澤是倒帶式的,曲折的。九十年代後半葉,剛剛離家生活的死大學生,不上課但是專上圖書館與書店,栽進書沼的文學良民,老師也不能說我是壞學生罷(雖然戀愛到昏天黑地以致忘了赴考試)。侷促於校園一角,與理髮部毗鄰擁擠的政大書城,背向門口左邊第一櫃,黑背《人生不值得活的》厭世氣息書名瘦瘦立在架上(縮影八百億倍的一個小寫的瘦瘦的i);接著找到了洪範專區,《薔薇學派的誕生》正常販售,尚未成為絕版逸品,學詩小子如我,於詩句一知半解外,是挺羨慕「楊牧寫序,羅智成插畫」這等黃金組合;至於較《薔薇》稍晚的《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那是又好幾年後,一位朋友預備拿別人的複印本去複印,順口來問,我也搭上一份,到手時發現影印行自行打字製作的封面「彷彿」變成了「彿彷」,直接坐擁一部倒錯的(偽)「珍」本。
今日詩迷們頗能引用一二的,一半來自《薔薇學派的誕生》,一半來自《人生不值得活的》,前者似更浪漫,風格也紛紜,後者似更踟躕,憊懶,風格其實也未必統一。現實是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何況詩集。主題與風格太整全明確的詩集,除了方便怠惰的評論家,我不以為對讀者全是好事。我們總願意看到心愛的詩人能持常,又能新變,新變處有些顛躓也無所謂,總之你知道他還在活動著,而非安於標本。既然是倒讀回去的,從中年楊澤到青年楊澤,從不值得活到誕生,班傑明的奇幻旅程,《薔薇》透露的青春志願就更為鮮明。我以為〈在畢加島〉可為全集之鎮魂詩:
瑪麗安,在旋轉旋轉的童年木馬
在旋轉旋轉的唱槽上,我的詩
我的詩如何將無意義的苦難轉化為有意義的犧牲?
我的詩是否只能預言苦難的陰影
並且說,愛……
「瑪麗安」,年輕的小母親,執著而憂愁,綠地盡頭垂著頭的雕像;「唱槽」是年輪,漩渦,時間的儀軌,可聯繫至楊澤詩作裡一再出現的唱片意象與歌手清單;「木馬」則永遠懷舊,童年式的昂揚,油彩注定剝落,可是那歡樂常在心中。比起以河流比喻生命,一去不返,顯然楊澤更同意的是,「唱槽」和「木馬」般重複旋轉,傷害與時間一點一點滲入,漸次磨損,可是磨損裡也有它的價值;前者壯烈,後者悲涼。雖然悲涼,只要「瑪麗安」不滅,「空中花園」恆存,那就能蓄養著舊精魂。
然後,詩人問:「我的詩」是什麼?有何作用?「如何將無意義的苦難轉化為有意義的犧牲」,這並非天真的自信,也非知識分子盲目為內疚感牽引;不管之後能煥發何等意義,苦難都不應該發生,假使發生了,文學去書寫不是為了攫取苦難來作為書寫者的良知標章,而是為了銘刻那震動與不忍,喚起同情與思索,幾乎像是一種愛的教育--「愛」被過度使用而俗濫,可是詩人仍全心信賴。
與〈致w.k.l.〉(w.k.l.即溫健騮)並置來讀,「由於是雨雪方停的異國清晨╱所以我並不知道死亡就埋伏在下一條街的暗角╱將你撲殺成午夜最寒的那陣風╱所以我並不知道你的名字╱即使那極可能是我的…」,異國清晨寒冷街角的死亡,無論是什麼事件,理由為何,此樁「無意義的苦難」的意義正在於「你」也可能是「我」,故「我」並非單單旁觀;或〈手記之二〉裡寫「昨夜夢見被黑鷹追殺╱在滿佈敵意的街道上狂奔╱我開槍打死了一個人╱啊,無意打死了一個人」,即使「我」分明是「有一顆善良的心」,極端恐懼下,被追殺者與追殺者可能將殊途同歸。如果詩不僅僅「預言苦難的陰影」,還要「站在愛的那一邊」,正需要這一層認識。
楊澤曾以「恨世者」來詮釋魯迅,魯迅以恨為愛,在恨尚未被傾盡之前,還不能輕易談到愛。楊澤顯然溫柔得多,空中花園裡有瑪麗安擔任警幻仙子。不過,在〈斷片〉這樣的作品裡,還是可以瞥見:
請不要圍觀他人的死吧!冷漠的羣眾請莫要議論紛紛,因為我們同是一樹枯枝上的顫危危的敗葉
犧牲者與看客,自覺者與庸眾,皆為縱貫魯迅文學的命題。然而,不僅批判圍觀者何等麻木,重點在「我們同是」,對於他人危敗處境的更深層理解,亦呼應了〈致w.k.l.〉與〈手記之二〉。還有〈獨臂人之歌〉,它具備一種迴旋的結構:左手刑斫了用槍的右手,落地了的右手反過來刑斫了寫詩的左手,再來則是是瘦長孤獨的左手自斫了的寫詩的左手;而當遠方無言的空白與零落雁行彼此見證,遠方──
將被一隻瘦長
孤獨的左手翻過來
成為我戰後詩集的
最後一頁
寫著一頁黑色的無言
沉重的手,受傷的手,變形的手,讓人想起魯迅〈頹敗線的顫動〉結尾「我夢魘了,自己卻知道是因為將手擱在胸脯上了的緣故;我夢中還用盡平生之力,要將這十分沉重的手移開」,更讓人想起商禽〈鴿子〉:「你這工作過而仍要工作的,殺戮過終也要被殺戮的,無辜的手,現在,你是多麼像一隻受傷了的雀鳥,而在暈眩的天空中,有一群鴿子飛過:是成單的還是成雙的呢?」魯迅散文詩裡的手將自我壓入夢魘,商禽散文詩裡的手像威權底下的兵,這「黑色的無言」,是面對黑夜,仍要睜了眼看。
而《薔薇學派的誕生》出版於尋找自我、不滿現實的七十年代,不免也出現革命狂想,如〈車行僻野山區〉所見:
站在雨後樹梢的
純白純白的鷺鷥:
被放逐的叛軍頭子圍在野地秘商
指向工廠的、城市的,我的一首詩的叛變
雨後樹梢上圍聚著的鷺鷥們本是田園詩的常客,這裡卻成了叛軍頭子們的會晤。除了承擔愛的教育,詩也具備叛變的潛能。楊牧曾費力詮釋「一首詩的完成」,楊澤卻想問,一首詩如何叛變它自己的年代?於是,〈在臺北〉指出「在臺北,在八億國人的重圍裡」這現實的虛構,〈拜月〉說「我們的年代純屬虛構」,連「我們的愛情」也是「無上的虛構」,我們也許分不清是薔薇還是「一朵朵薔薇的幻影在空氣中燃著」(〈薔薇學派的誕生〉)。
末了,還想再說說《新詩十九首》中十分凸顯的浪蕩子情懷,更早之前,或已顯露蹤跡。讀〈拜月〉,「雖然我沒有一個戀人,不曾愛過╱我對月的渴慕,我對生命,啊,卻有些激烈的╱不負責任的華而不實的想法╱──我對死亡的恐懼與暝想,彷彿╱彷彿我曾擁有一個死去的戀人──一個╱死去的愛太過完美以致真實╱彷彿,啊,我是一個歷經變遷,歷經死╱美文華服,耽樂頹廢的末世詩人」,現在看來有些不著邊際的幻想與氣質,卻顯示了因為青春才可能的浪擲。青春之人渴望「歷經變遷」,衰老及風塵,似乎更具魅力,且率爾將詩與死╱美縫在一起,美必有衰亡,而衰亡襯托出美的稀有,二者正如風月寶鑒正反面;曹雪芹早就藉由賈瑞縱慾死去的情節開示讀者,瞥見死亡之恐怖,不見得就醒悟生無須戀,反而會讓那份癡執黏附得更緊,因此耽樂頹廢。詩句沉溺裡,有躁動,也有陰翳,那陰翳就是歷史天使瞥向無窮廢墟的眼神。
瑪麗安,我的樹洞傳奇
──二○一六年新版序
/楊澤
a
想像,如果你不反對,一個來自南方小鎮的年輕人,剛過了懂得慕青春少艾的年齡不久,初抵外地的大都會求學,大街小巷,目光所及,一切對他都顯得如此新鮮立體,甚至突兀神奇。
想像,如果你不反對想像,上蒼給這年輕人天生一副多愁善感的性情,還有難得富磁性的低音嗓子。想像他初來乍到,五光十色的大城,加上以大城為背景的少艾之戀,固然令他欣喜萬分,遇事好鑽牛角尖的個性,一種無以名之,屬於一般志氣薄弱的年輕人才有的「心魔」,偏讓他吃盡苦頭,他在校園裡,在公車上,...
目錄
瑪麗安,我的樹洞傳奇(二○一六年新版序)/楊澤
我們祗擁有一個地球──楊澤著「薔薇學派的誕生」序/楊牧
A: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
在畢加島
斷片
荒煙
致w. k. l.
印象一題
意外二則
一九七六夜想
手記
草原記事
一九七六斷想
拜月
B:花蟲鳥獸
薔薇學派的誕生
水荷
鴿子
送信者
事件
蟑螂的速度
今天早晨在花間
荷花是水神的禁臠
車行僻野山區
戰後所見
C:儀式之餘
閣樓上的情歌
煙
獨臂人之歌
秋之電話亭
九月
亞當之歌
儀式
水月
眷村
D:瑪麗安‧瑪麗安
家族篇第一
家族篇第二
家族篇第三
浪子回家篇
光年之外
致c. l.
給h. t.
在床鏡
一九七六年的腳註
給瑪麗安
一九七六記事之一
一九七六記事之二
一九七六記事之三
一九七六記事之四
青鳥
薔薇騎士的插圖
給格弟非
E:漁父‧一九七七
漁父‧一九七七
左翻
序 木馬‧唱盤‧瑪麗安/楊佳嫻
瑪麗安,我的樹洞傳奇(二○一六年新版序)/楊澤
我們祗擁有一個地球──楊澤著「薔薇學派的誕生」序/楊牧
A: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
在畢加島
斷片
荒煙
致w. k. l.
印象一題
意外二則
一九七六夜想
手記
草原記事
一九七六斷想
拜月
B:花蟲鳥獸
薔薇學派的誕生
水荷
鴿子
送信者
事件
蟑螂的速度
今天早晨在花間
荷花是水神的禁臠
車行僻野山區
戰後所見
C:儀式之餘
閣樓上的情歌
煙
獨臂人之歌
秋之電話亭
九月
亞當之歌
儀式
水月
眷村
D:瑪麗安‧瑪麗安
家族篇第一
家族篇第二
家族篇第...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2收藏
12收藏

 18二手徵求有驚喜
18二手徵求有驚喜



 12收藏
12收藏

 18二手徵求有驚喜
1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