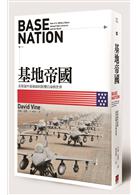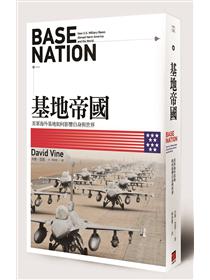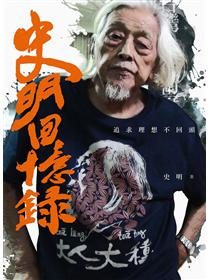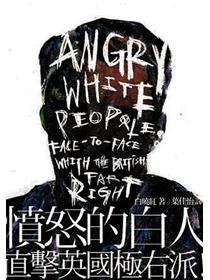香港回歸20周年,杜葉錫恩的書有助瞭解香港發展歷程。
從當年的不公正,對比後來的法治,珍惜今天社會來之不易。
「讀者可能聽說過20世紀後半葉香港的經濟奇跡,但是他們可能不瞭解當時由貪婪和腐敗引起的苦難和不公正。」 ── 杜葉錫恩
杜葉錫恩女士是香港人熟悉及尊敬的一位社運家和教育工作者。她一生熱衷於社會服務及教育工作,對推動民生的改善不遺餘力,在市民的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備受尊敬。
本書為杜葉錫恩女士生前所撰。分析了她所經歷的五六十年代至回歸的香港社會概貌,表達了她對殖民制度下社會不公正的看法,有助於讀者認識和理解香港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讀者也能看到她對現今經濟殖民主義更廣義及深入的憂慮。此外,杜葉錫恩女士當年多份重要信件、報告、演講稿也收入本書中。
作者簡介:
杜葉錫恩(Elsie Hume Elliot Tu, 1913-2015)
1913年出生於英國紐卡素,1948年到中國江西南昌傳教三年,1951年到香港。1954年創辦慕光英文書院。1963年至1995年任市政局議員,1988年至1995年任立法局議員及擔任各諮詢委員會委員。1997年至1998年任臨時立法會議員。她同時為國際司法組織香港分會會員、香港婦女協會名譽會長及國際婦女會會員。1988年獲香港大學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1994年獲理工大學頒榮譽法學博士學位。1997年獲頒大紫荊勳章(GBM)。
杜葉錫恩女士於2015年12月8日在香港辭世,享年102歲。因為她一生為香港所作的傑出貢獻,去世後得到香港各界的共同悼念,舉殯時三位在任及前任特首為其扶靈。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初版說明
杜葉錫恩女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便來到香港,在香港居住超過半個世紀,見證了香港從殖民時代走向回歸的歷程。杜葉錫恩女士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審視發生在香港的一事一物,分析和透視了香港在殖民時代及回歸後的種種變化,讓讀者從中瞭解到香港社會五、六十年代,回歸過程中,以及回歸後一系列備受關注的事件,要瞭解長達半個世紀的香港社會,杜葉錫恩女士書中所敘述的事情,所展現的香港社會概貌,給我們提供了一批香港長達半個世紀以來的珍貴資料,幫助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對香港近半個世紀的認識和理解。
《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2003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推出市場之後,反應甚好。不少讀者認為,應該為此書出版中文版。為此,香港文匯出版社接受杜葉錫恩女士的要求,為本書的英文版作了翻譯,並且推出市場,以饗廣大讀者。
為本書作翻譯的隋麗君教授,以一絲不苟的態度,領會杜葉錫恩女士原著的精神,精心翻譯出行文流水、文理順暢的中文版本,令讀者可以更深入地領略杜葉錫恩女士的著書立意。
香港文匯出版社
2004年5月
再版說明
杜葉錫恩女士在香港生活了六十多年,一直為匡扶社會公義、推動社會進步而熱心工作。她創辦教育,為民請命,與貪腐抗爭,參加社會運動,活躍於政壇,可謂六十年如一日。在香港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中,杜葉錫恩女士留下了一串深刻的足跡。
2015年12月8日,為香港服務超過六十年的杜葉錫恩女士辭世。本港各界及市民為之感到惋惜和難過,並致以敬意。舉殯時,時任特首梁振英,前任特首董建華、曾蔭權共同為其扶靈。哀榮之盛,也可見杜葉錫恩女士因其貢獻而獲得的尊敬。
杜葉錫恩女士不僅是香港半個多世紀歷史的參與者,也是觀察者、記錄者、思考者。她把親歷的殖民時代的事件記錄下來,同時也寫下自己的思考。2003年,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書: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2004年,應她要求,香港文匯出版社翻譯和編輯出版了中文版《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這本書既有助於讀者回溯和瞭解香港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也涵蓋了許多珍貴史料,受到讀者歡迎。可惜的是,目前此書已絕版。
恰逢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與香港文匯出版社攜手合作,再版杜葉錫恩女士這本重要的著作,以饗讀者。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出版社
2017年4月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初版說明
杜葉錫恩女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便來到香港,在香港居住超過半個世紀,見證了香港從殖民時代走向回歸的歷程。杜葉錫恩女士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審視發生在香港的一事一物,分析和透視了香港在殖民時代及回歸後的種種變化,讓讀者從中瞭解到香港社會五、六十年代,回歸過程中,以及回歸後一系列備受關注的事件,要瞭解長達半個世紀的香港社會,杜葉錫恩女士書中所敘述的事情,所展現的香港社會概貌,給我們提供了一批香港長達半個世紀以來的珍貴資料,幫助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對香港近半個世紀的認識和理解。...
章節試閱
第1章
20世紀50年代初次感受香港
我們最後一批傳教士是在1951年2月離開江西省省會南昌來香港的。一些年長的傳教士早在1949年初中國內戰的戰火逼近該省的時候就離開了。然而,新的共產黨政府沒有強迫我們中的任何人離開。這個新政府於1949年年中到達南昌,同年10月宣佈戰勝國民黨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事實是,共產黨接管之後,社會狀況的確有了改善,原先有人對我們說會發生各種暴行,但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通貨膨脹減輕了,經濟有了起色,法律與秩序恢復了,電力、道路、通訊和運輸也都大大改善了。我們無從瞭解是否中國所有地區都是這樣,但江西是一個特別的省份。南昌曾是民望很高的周恩來的指揮部所在地。我們傳教士很幸運,因為負責處理我們的事務的那個人在上海的一所教會學校受過教育,知道該如何同外國人打交道,而且向我們提出了許多有關該如何同新政府打交道的有益忠告。表面看來,一切都好,所有中國人,連軍隊在內,似乎都不介意外國人存在於他們之中,儘管從理論上說 ── 即使事實上並非如此 ── 英國人和其他歐洲人都是屬於敵對營壘的外國人,尤其是在北朝鮮同得到聯合國支持的南朝鮮之間爆發戰爭之後。那場戰爭中,我們在中國的一位教會長老的兒子在為北朝鮮作戰時陣亡了,當時為他舉行了英雄式的葬禮。然而,快到1950年年底時,我們聽到這樣的傳聞:所有傳教士都將離開中國,而且,英國政府大概也已告誡所有英國國民離開中國。我們的中國朋友也勸我們為自己的安全著想離開那裏,儘管政府從未把我們當作敵人來對待。不過,由於朝鮮開戰的關係,局勢是高度緊張的。於是,我們決定先去香港,到那裏再制定前往婆羅洲與我們的教會成員會合的計劃。結果,我們一直沒有離開香港,我本人竟在這裏呆了50多年。
乘火車到羅湖邊界再前往香港,一路很順利,從中國這一側的村莊深圳越過窄窄的小橋到達河的另一側、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也沒發生任何事情。橋的這一端飄揚著中國國旗,另一端則是英國國旗。懷著理想主義的我當時相信,英國國旗代表著英國的正義。但我很快便發現我想錯了。
到香港後不久,我們拜訪了我們在香港的講英語的教會的成員。其中有一位在港府工務局工作。他對我們談及無視一切法律和政策的貪污受賄現象。這令我非常訝異,因為我原以為香港是由一個民主政府治理的,這個政府以保障英國的正義而著稱。貪污和正義是不相容的。我認為這位工務局的朋友一定是在誇大其詞。但他沒有。
我們最初見到的人中還有一位為香港政府工作的醫生,是一位歐籍人士。他證實了工務局的那位外國僱員對我們講述的事情。他建議我買一部照相機,把我所見到的這類現象拍下來交給報章去發表。他說,對付貪污受賄現象的唯一辦法是把高官們「惹火」。「惹火」是他的原話。我一直沒有忘記他的忠告,但可惜我當時無法把這一忠告付諸實施,一方面我買不起照相機,另一方面我的教會嚴格限制婦女站出來講話。我的前夫甚至不許我給除了親屬和私人朋友以外的任何人寫信。至於批評政府,我們基督徒理應把注意力集中於天國中的事務而不是塵世間的事務,因此,不許我就我所見到的不公正現象投書報章。
我們到香港沒幾天,一群中國人就到我們下榻的「士兵與海員之家」看我們。他們要求我們留在香港,在他們的寮屋區教堂工作。這個寮屋區位於黃大仙區的一個叫做啟德新邨的地方。我們解釋說,香港的房租太貴,我們住不起。他們便在他們的租金便宜的寮屋區內為我們找到了一套非法住房。在那裏,我們很快就瞭解到一些貪污受賄現象,因為寮屋區的每個人都不得不交錢給黑社會幫派,而索要錢財的名目是各種各樣的。在我們拒絕交納「保護費」之後,有人不止一次企圖對我們在該區內的住處行搶。當時的強盜通常都是搶一些小東西,連襪子和其他衣物都是目標,儘管我們放在三樓陽台上的自行車也被偷過。這些被偷的自行車後來被找了回來,我猜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是外國人的緣故,而不是因為警察的破案本領高強。外國人可以避過不公正現象,而中國人就時時生活在對不公正現象的恐懼之中。寮屋區中的人經常受到黑社會分子的騷擾,這些黑社會分子的行為就好像是腐敗的政府官員的稅收大員,他們搶奪來的錢財與這些官員分贓。對歐洲人行搶是有很大風險的。政府不希望外界知道在那個腐敗的時期假英國正義之名所發生的事情。
我對我們的教會感到幻滅並最終於1955年永遠離開那個教會,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就這些不公正現象仗義執言只是其中之一。退出教會導致我的婚姻破裂。面對不公正,我覺得我無法在緘默中生活,同時我也不能繼續接受教會的保羅教義,它與基督的教義似乎不搭界。它的偏狹胸襟令人無法容忍。
一旦擺脫了教會的束縛,我就可以對殖民政府所縱容的貪污受賄和不公正現象進行較為深入的調查了。說到這裏,我必須指出,在有些居住在這個殖民地的殖民者的想像中,我的目的是製造麻煩或者「推翻」政府,但我根本無意這樣做。在我看來,政治變革是中國人自己的責任。如果他們對政府感到滿意,我將只致力於消除最嚴重的不公正現象。在本書的這一部分,我將講述我所記得的某些這類事例的來龍去脈。
作者小傳
我一歲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我的父親被派往歐洲去打仗。作戰期間,他在戰壕內中過毒氣,落下了終生後遺症。我姐姐差不多長我三歲,這使我受益匪淺,因為她的學習成績相當出色。我向她學了不少東西,所以,當我五歲開始上學時我已經先行了一步,老師們都對我稱讚不已。
我們家屬於勞工階層。我父親在11歲時就成了孤兒。儘管他在學校內成績優異,但卻無法繼續讀書,小小年紀便不得不幹起為食品店老闆送信的差事,幫助養活弟弟妹妹。他的姐姐照料著這個六口之家,而且我們這個四口之家也一直同父親的這位姐姐生活在一起,直到我八歲那年。她是一位頗有風度的女士,對我疼愛有加,直至她以97歲高齡去世。當然我從未見過我的祖父和祖母,只記得見過一次我的外公,我想那時他的妻子已經去世了。不過,從我母親的講述中,我得知我的外公曾為一個貴格會教徒的家庭工作,因此接受了當時貴格教徒所實行的那一套嚴格的禮儀規則。
我母親本人就很嚴厲,在家中是說一不二的。在朋友和鄰居面前,她顯得非常文靜優雅,但在家中,我們全都怕她。我們小時候得到很好的照料,這要歸功於母親,而且,是她教會我編織和縫製衣服。有一個時期買衣服是很貴的,我便成了家裏的裁縫師,不僅給自己做衣服,還為我的兩個妹妹做。戰後,我們家添了丁,變成四個孩子了:三個女孩、一個男孩。
毫無疑問,對我的一生有影響的人中包括我的主日學老師和在我五歲那年從戰場上歸來的父親。在主日學內,我們受到的教導是:上帝對我們的良知講話;每當我們受到誘惑要做某種值得懷疑的事情時,我們應當聆聽上帝的聲音。我認為這對我的良知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至於就連最無害的假話我也難以講出口。即便是我因犯了一個小錯受到母親或老師的責備(受到老師責備的事我記憶中只有一次),我也只有強忍住淚水,心裏想:為了一件我決不會有意去做的事情而責備我,那是不公平的。
我的父親對我的良知也是有影響的,因為他對我講述過他在戰爭中的經歷。如果說他失去了在學校中受教育的機會,那他肯定透過在軍隊中所受的教育彌補上了。他是帶著對戰爭的仇恨和對所有人 ── 不論是朋友還是敵人 ── 的同情離開戰場回家的。他在宗教方面成了一個不可知論者,反而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家中,我們在餐桌上的談話總是圍繞著宗教的虛偽性、圍繞著馬克思主義和工人的權利以及圍繞著體育而進行的。在中學時,我曾是一個田徑選手,而且,儘管我很靦腆,我當上了我們這個隊的隊長以及學校運動隊的隊長,此外還當上了年級和學校的紀律隊長。我認為,正是由於我父親的教導鼓勵了我,我才能在遇到挑戰時勇敢地迎上去,決心克服任何障礙。我聽到有人說,一個在體育方面很出色的學生通常在學業方面就不會那麼好,於是我就立志在這兩個方面都做到出類拔萃,以證明這個理論是不成立的。有一次我在歷史課上得了一個不好的分數,我就下決心以後永遠成為歷史科的尖子,而且最終由於歷史成績優異而獲得了一個特別獎項。後來,當我在1948年到中國傳教並聽一位年長的傳教士說結了婚的女人永遠學不好語言時,我就決心證明她這話是錯的,而且先於我們那個小組內的所有單身女士完成了語言課程。
當我於1951年從中國到了香港並看到腐敗阻塞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實際渠道時,上述經歷使我受益匪淺。人們常對我說,站出來講話是於事無補的,但這只會使我更加堅定仗義執言的決心。有許多次,由於人家不肯為使寮屋區的窮困兒童受到教育而施以援手,我曾失望地流著眼淚離開教育署大樓(即現在的終審法院大樓),但這種失望總是化作找到辦法的決心。雖然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這種辦法,但最後終於找到辦法為失學兒童建立了一所學校,直至在1972年和1978年實行免費普及教育,而且,在政府的補貼下,我們還提高了我們的教育水準。
但是,最嚴峻的挑戰是在我當傳教士的時候到來的。我在大學一年級時開始信奉基督教,此前我和父親一樣是一個宗教不可知論者。自信教以後,我一直憧憬著基督教的教義能拯救全世界。年輕人總是會抱有這樣的理想,但以後卻發現世界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在中國,我認識到,各國人民都有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有的則沒有宗教信仰。我發現,中國的文化是西方所無法比擬的,然而,我們傳教士中有些人卻把中國人當作劣等民族對待。正如一位誠實的英國人所說:「他們是抱有基督教的偏執意識的帝國主義者。」在我們這個奉行基要主義的基督教團體中呆了三年之後,我對這種局面已經忍無可忍。但當時我已嫁給一名傳教士為妻,而這位傳教士自幼就受到基要主義的教育,對此篤信不移。那個時期是我一生中的最低點。當時看來,唯有自殺才能獲得解脫。但願我的這段經歷能成為對那些與基要主義信仰或其他邪教發生瓜葛而又難以脫身的年輕人的一個警示。有些邪教領袖懂得如何操縱他們的信徒乃至控制他們的思想。我的教會長老們說我喪生了理智,需要休息一段時間,恢復正常。而我知道擺脫他們才是我避免喪失理智的唯一途徑。終於,在1955年 ── 那時我已經在香港了 ── 我在教友大會上公開宣佈我要離開他們了。我原以為自己會忍不住哭出來,但出乎意外的是,我卻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
那時,我和一些教友已經建立起一所窮人子弟學校,不過,我們請假回英國呆了一段時間。六個月後我隻身返回香港繼續辦學。這所學校是以我的名字註冊的,因為我們這些人中只有我是合格的教師。在開始創辦學校時,我遇到了困難,因為我們的教會希望只教授《聖經》,但由於我已不再是教會的成員了,他們最終就讓我一個人承擔辦學的工作。我的丈夫沒有返回香港,最後我同他離了婚。作出這個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這個人原則上是不贊成離婚的,只要能避免最好不走到這一步。還好我們沒有孩子,無須為子女操心。
多年之後我的生活才完全擺脫了基要主義體系的干擾。在這方面,我在學校內的同事杜學魁給了我很大的幫助。30年之後,他成了我的丈夫。儘管我們在文化和語言上存在差異,但我發現,他的理念使我感覺好像回到了我可以同父親交談的歲月,而我的父親已經在我來中國期間去世了。杜學魁和我在許多方面看法都是一致的,而在有分歧的事情上,我們總能互相開導。開始辦學校時,杜學魁教授中文,所有其他一年級的課程都由我自己來教。學校開辦後不久,另一位同事—戴宗(Tai Chong)先生加入進來,並且與我們親密共事將近50年。這兩位同事都在2000年退休,而且無論是彼此之間還是同學校之間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一種夥伴關係能保持這麼久,而且從未發生過任何嚴重的爭執、彼此深懷敬重、相互絕對信任,這真是太難得了。
多年來,我對歷史的興趣持續不減,但只是到了最近我才有時間對我在大量閱讀有關當代事件的記載的過程中摘錄下來的內容加以整理。我越來越驚恐地看到,新的經濟帝國主義所征服的領域是當年的希特拉連想也沒想到的。這是一種新型的帝國主義,它以民主的形式出現,向接受它的那套有關民主和人權的陳詞濫調的那些國家提供財政援助,但它自己卻根本不去實行這些原則。同樣,我丈夫杜學魁驚恐地注意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更加危險的是,這一次,美國成了日本的盟友,而不是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樣是它的敵人。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以簡短又簡單的形式把我從大量書籍中所收集到的歷史展現出來。這些書籍一方面很難獲得,另一方面年輕人、尤其是屬於另一種文化的年輕人讀起來有困難。應當讓年輕人瞭解這種為了一己的私利而力圖把全世界置於自己控制之下的悄然擴張的帝國主義。也應當讓年輕人瞭解到有些人利用宗教和名目繁多的邪教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許多年輕人一開始也抱著我年輕時所憧憬的那種理想,但那些理想最終成了纏繞在我脖子上的鎖鏈,制約著我的每一個行動。我的教會不許我直抒胸臆。我的前夫不許我給除了私人朋友或親屬以外的人寫信。當我發現香港存在的不公正現象時,我的教會不許我站出來反對這些現象,理由是我們所尋求的是死後的財富,而對人世間的一切事情全都不屑於關注。於是,人們希望我即便看到窮苦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也要默不做聲,因為這些東西與我無關。一旦去除了這些鎖鏈,我便決心努力把我在教會中失去的大約10年的時間補回來。我是在43歲那年開始我的新生活的。我的新生活以在人世間爭取人類的幸福為使命,而不是為自己在天堂中構築豪宅。現在,我意識到,我早年的那種在任何挑戰面前都不服輸的決心正在結出果實。我最殷切的願望是,讀過這本書的年輕人能按照事實的本來面貌去看待生活,而且要正視這些事實,而不被有人藉以矇騙甚至控制他們的那些理想所欺騙。
第1章
20世紀50年代初次感受香港
我們最後一批傳教士是在1951年2月離開江西省省會南昌來香港的。一些年長的傳教士早在1949年初中國內戰的戰火逼近該省的時候就離開了。然而,新的共產黨政府沒有強迫我們中的任何人離開。這個新政府於1949年年中到達南昌,同年10月宣佈戰勝國民黨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事實是,共產黨接管之後,社會狀況的確有了改善,原先有人對我們說會發生各種暴行,但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通貨膨脹減輕了,經濟有了起色,法律與秩序恢復了,電力、道路、通訊和運輸也都大大改善了。我們無從瞭解是否中國所有地區都...
作者序
前言
1997年6月30日午夜,是殖民主義完結、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刻。在這一時刻臨近之際,外國記者特別是歐洲和美國的記者蜂擁而至。他們全都指望在這裏撈足發生騷亂乃至暴亂的新聞題材,為他們的宣傳機器提供原料。其中有一位竟對我說,他奉命來此只報道示威和反對活動,而不報道歡慶活動。許多人聽信了香港少數世界末日派政客的鼓噪,以為這裏一定籠罩在恐懼的氣氛之中。
這些前來捕捉聳動新聞的媒體代表中有一些人曾到我的辦公室來見我。看來,他們在來見我之前是聽人介紹過情況的,因為他們全都問到一個類似的問題:「你為什麼背棄了民主?」他們一再問我這個問題使我感到惱火,因為我為尋求一個更加民主的制度,也就是說為了使民眾得到更多的公正,奮鬥了50年,而且至今還在這樣做。事實上,我相信自己生來就是一個民主派,而不僅僅是某個政黨的黨員。「一人一票」的主張本來應當保護大多數人所真正希望的東西:一種體面的生活和一個摒除了不公正及貪污現象的社會。我所主張的民主(democracy)中的「d」是小寫的,它不附屬於任何一個用大寫的D拼寫的政黨,也與透過反對中國和反對所有不是俯首貼耳地接受美國式資本主義制度的其他國家而獲得的民主稱號沒有任何瓜葛。
我就自己的民主派資格作出的回答是決不會使那些外國記者滿意的,因為他們只為找尋異見而來,而對那些為建立一個穩定平衡的香港而努力的人士毫無興趣。從1997年起,英文報章上就幾乎沒有我的聲音了,而在殖民時代,他們是經常找我表達意見的。當然,這些報章的老闆變了,看來他們的政策也隨之改變了。事實上,我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不再能透過媒體發表自己的觀點了。遇到這種問題的也不只我一個人。負責協調伊拉克人道主義事務的前聯合國代表丹尼斯.哈利戴(Denis J.Holliday)為抗議以制裁和轟炸來殺戮伊拉克平民的做法而於1998年憤然辭職。他曾這樣問道:「請問哪裏可以找到誠實的新聞報道?」「媒體都被他們的老闆或者華盛頓的當權者扼殺了嗎?或者被武器製造商扼殺了嗎?」
報章不給我陳述意見的渠道,但這本書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得以表達我對以往殖民制度下的不公正現象的看法(第一部分)以及我對現今經濟殖民主義的憂慮(第二部分)。
我不能指望我所寫的東西會產生任何震撼世界的效果,但希望它能對年輕一代中那些意識到我們這個星球的未來所隱含的危險和所蘊藏的潛力的人提供一點微薄的支持。
── 杜葉錫恩
前言
1997年6月30日午夜,是殖民主義完結、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刻。在這一時刻臨近之際,外國記者特別是歐洲和美國的記者蜂擁而至。他們全都指望在這裏撈足發生騷亂乃至暴亂的新聞題材,為他們的宣傳機器提供原料。其中有一位竟對我說,他奉命來此只報道示威和反對活動,而不報道歡慶活動。許多人聽信了香港少數世界末日派政客的鼓噪,以為這裏一定籠罩在恐懼的氣氛之中。
這些前來捕捉聳動新聞的媒體代表中有一些人曾到我的辦公室來見我。看來,他們在來見我之前是聽人介紹過情況的,因為他們全都問到一個類似的問題:「你為什麼背棄了民...
目錄
前言
第一部分 在香港尋求正義
第 1 章 20世紀50年代初次感受香港
第 2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香港 ── 剛來時的最初印象
第 3 章 香港的兩個市政局
第 4 章 小販成為貪污受賄者的獵物
第 5 章 長期存在的住屋問題
第 6 章 房屋政策刺激了貪污受賄
第 7 章 為註冊學校所經歷的考驗與磨難
第 8 章 關於官員、承包商和三合會
第 9 章 20世紀60年代的香港 ── 罪惡的天堂
第 10 章 甚至連司法系統都……
第 11 章 貪污受賄之風蔓延到交通部門
第 12 章 兩個不滿的夏天:1966年和1967年
第 13 章 葛柏的案子使事情敗露了
第 14 章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在成功地履行其使命嗎?
第 15 章 香港的民主
第 16 章 循序漸進的民主
第 17 章 1992-1997:香港的過渡時期
第 18 章 2007年以後香港的前途
第 19 章 殖民者的無知
第二部分 民主遭遇了甚麼?
第 20 章 為甚麼要寫書談民主問題?
第 21 章 民主為何物?
第 22 章 民主的發展
第 23 章 馬基雅弗利時代
第 24 章 帝國主義思維
第 25 章 一個偷來的國家有多麼民主?
第 26 章 經濟殖民主義
第 27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法西斯主義
第 28 章 門羅主義的遺產
第 29 章 民主遭到曲解
第 30 章 民主的新概念
第 31 章 投票制度
第 32 章 關於民主和假民主的言論摘錄
後記
附件A 關於1966 年香港政局的報告
附件B 在國際婦女聯盟會議上的演講
附件C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香港的生活
附件D 信件及其他
附件E 日本的頭號戰犯和美國戰後與日本戰犯的勾結
作者小傳
前言
第一部分 在香港尋求正義
第 1 章 20世紀50年代初次感受香港
第 2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香港 ── 剛來時的最初印象
第 3 章 香港的兩個市政局
第 4 章 小販成為貪污受賄者的獵物
第 5 章 長期存在的住屋問題
第 6 章 房屋政策刺激了貪污受賄
第 7 章 為註冊學校所經歷的考驗與磨難
第 8 章 關於官員、承包商和三合會
第 9 章 20世紀60年代的香港 ── 罪惡的天堂
第 10 章 甚至連司法系統都……
第 11 章 貪污受賄之風蔓延到交通部門
第 12 章 兩個不滿的夏天:1966年和1967年
第 13 章 葛柏的案...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