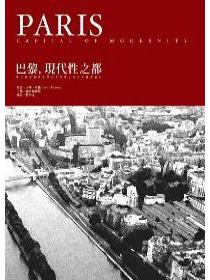史塔西:我們無處不在!
告密無所不在,祕密無所不知
一段被出賣的人生,與告密者最直接的面對
★諜報小說家約翰‧勒卡雷 盛讚!
「叛逆及妥協的描繪,教人不寒而慄」
★一揭人類史上最嚴密最恐怖的情報機構「史塔西」。
★譯成二十餘國文字、電影《竊聽風暴》真實版
記憶是救贖的祕密。而原諒與遺忘,是彼此共同的說辭。
這是一部報導與回憶兼而有之活的歷史,官方資料比對個人回憶,成熟極權主義的靜默表現對抗知識份子的良知與勇氣。
在極權時代,為什麼選擇妥協或出賣?背後的監視者又是怎麼想?
爾後,人們憑什麼譴責?同樣的,又憑什麼原諒?
為了研究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一九八○年起,作者分別在東西柏林搜集資料數年,沒想到,他在東德的行蹤被認為是間諜活動,遭到祕密員警和線民盯梢,留下了厚達三百多頁的祕密檔案。
兩德統一後,東德開放檔案,作者重訪舊地,根據國安部為他建立的「檔案」與自己的日記,一一尋訪當年那些監視他的人。他驚訝的發現,立場不同的人,往往對相同的經驗卻有截然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回憶。於是,穿越各種回憶的迷霧,探尋自身作為其中一部分的歷史之真相,成為其寫作動力。
被出賣的痛苦,被背叛後的不信任,被揭發後的沮喪、自責與否認。
在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祕密報告筆錄之間,穿梭來回……
我可以理解我檔案中的每個線人,也可以理解那些官員,甚至是克拉奇,因為他們在說起自己的故事時,你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們是怎樣在不同的時間點、不同的場所以及不同的世界中一路走來,做起那些他們所曾做過的事。…在這裡,在檔案裡,你發現到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如何深深的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提摩西‧賈頓艾許
★媒體好評不斷!
「叛逆及妥協的描繪,教人不寒而慄;勇敢又美妙的呈現出我們的時代,堪稱是難得可貴的歷史文獻。」──約翰‧勒卡雷
本書回憶賈頓艾許本人與恐怖的東德祕密警察機構史塔西交手的親身經歷。從來沒有一個族群受到如此嚴密的監控,即使是在胡佛麾下的美國聯邦調查局時期也望塵莫及。《檔案》生動地還原許多惡質的人形怪獸,他們的目光總是緊緊地盯著每一隻小麻雀折翅墜地的時候。——亞瑟‧米勒
絕妙之作,一段有關歷史與人生的探索,不僅扣人心弦、警醒世人,同時發人省思、不時觸動人心。──約翰‧勞頓,《愛爾蘭時報》(Irish Times)
觀察入微、筆鋒敏銳,宛若在『斯塔西』的監控下首當其衝……令人陶醉,讀來興味盎然。──斯泰爾‧霍恩,《英國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出色卓越、令人陶醉……賈頓艾許不僅向歷史讓步──應說是向東德無窮無盡卻又如曇花一現的惡行讓步──並展開了一段回憶之旅。其攫抓住久被遺忘的過去,發現那些過去依然具備撼動、悲痛與激怒人心的力量……發人深省。──菲利浦‧漢舍,《英國週日郵報》(Mail on Sunday)
賈頓艾許的筆風總不失簡潔明晰……足見其博學多聞且才智過人。──喬治‧史坦納,《英國觀察家雜誌》(Observer)
約翰‧勒卡雷再世──傑瑞米・帕克斯曼,《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夏季閱讀推薦專刊
嘆為觀止……《檔案》中最精采的,莫過於賈頓艾許描繪他試圖找尋長期跟蹤他的那些人的橋段,這將本書變成精采的驚悚小說,而且令人開心的是,這些還是真人真事。──理查‧肯特,《蘇格蘭週日報》(Scotland on Sunday)
在作者一貫精準的筆風及擅於詮釋的天賦下,本書內容引人入勝……《檔案》提醒我們無論如何頌揚回憶,療癒的力量仍是來自遺忘。──安‧麥可羅伊,《英國週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
本書內容描述著一個頹暗帝國的分崩離析,逼真寫實、教人入迷,這名才華洋溢的歷史學家就身處該國,逐年記錄著它的殞落。──布萊恩‧戴維斯,《超時週刊》(Time Out)
曠世鉅作,一段帶有普世意義的個人故事……本書原可能淪為忿忿不平的愛情故事,如今卻成了家中倘遭祝融時,我最想要極力搶救的好書之一。──保羅‧奧斯特賴克,英國天主教週報《小報》(Tablet)
本書探討在充滿不安的獨裁社會中,「掌控」與「合作」之間的目的、意義及特質,發人省思且引人入勝……(賈頓艾許)向來不挾恨報復或以勝者自居,而是透過豐富多元且極具啟發性的筆觸,來檢視冷戰的那段過去。──白禮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專制獨裁究竟為何得以運作,我們依舊不甚了解……在此一面向的探討,索忍尼辛、普利摩‧李維等編年史家已頗有成果,而提摩西‧賈頓艾許堪稱與上述兩者齊名。── 克里斯汀‧卡里爾,《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作者簡介:
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
英國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聖安東尼學院以賽亞‧柏林教授研究員,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為《衛報》、《泰晤士報》、《紐約書評》等報刊撰文,並出版多本著作。代表作品有:《事實即顛覆》、《吾民》以及本書。
譯者簡介:
侯嘉珏
1980年生於台北。天主教輔仁大學經濟系、英國新堡大學筆譯所畢。
曾任中央政府聘用翻譯、富邦投顧全職編輯、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助理研究員、英國文化協會雅思(IELTS)閱卷人員等。
譯作甚豐,歡迎賜教。jadehou1980@gmail.com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封面的「OPK」表示「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亦即「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onal Person Control)。根據國家安全部司法高級中學(Juridical Higher School)一九八五年版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Dictionary of Political-Operational Work),「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旨在辨認出可能觸犯過刑法、夾帶「敵對─負面態度」或者「遭敵方利用、以達到敵對目的」的人。據字典解釋,「OPK」的核心目的,在於找出「誰是誰」,每份檔案一開始都有「開場報告」和「行動計畫」。
我的開場報告始於一九八一年三月,係由溫特少尉執筆,內容除了提供我的個人資料,還註記我從一九七八年以來就在西柏林求學,然後從一九八○年一月到六月─實際上是到十月才對─才一直都住在「東德『首都』」(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相關當局總是堅持以此慣稱東柏林)。我時常往來西柏林與東德、波蘭之間,且一再「與軍事行動相關人物聯繫」,因此,「很合理懷疑G(即賈頓艾許,不然就是「目標」或「羅密歐」)刻意利用身為研究生和/或記者之工作職責,以從事情報工作。」
接著,溫特少尉把九之二反情報處為了確認這一點,而從該部所有其他處室所蒐集起來的資料全部檢視一遍。檔案後方即附有原始資料:觀察報告、來自英國大使館以及我的新教牧師朋友華納檔案的情報內容摘要、我為西德新聞週刊《明鏡》(Der Spiegel)所寫有關波蘭專文的影本,以及我從舍訥費爾德飛往華沙時,他們祕密搜索我的行李而針對我個人的波蘭文筆記和報紙所拍下的照片影本,甚至還有我牛津的家教老師所寫給英國領事館的推薦信影本等,共達三百二十五頁。
史塔西所屬的線人德文為「Inoffizielle Mitarbeiter」,即「非正式合作人」(unofficial collaborators),或簡稱「IM」。溫特的報告特別著重在這些線人所提供的資料。線人們可分為以下幾類:安全的、特別的、作戰性的、策謀的,甚至還有監視線人的線人。自一九八九年起,德文中便有了這個縮寫的「IM」。在所有歐語中,「SS」(即Schutzstaffel,表示「納粹親衛隊」)皆代表著納粹主義響亮、暴戾、全然獸性的同義詞。在德文中,「IM」則成了另一個同義詞,代表著德國共產主義獨裁專政下所特有的官僚常態,而這種常態,多以滲透、脅迫及合作的形式存在;也代表著成熟的極權主義下更罕為人知的貪汙現象。一九九○年代初期,享譽盛名的東德政治家、學者、記者或牧師經史塔西檔案確認為IM並因此而銷聲匿跡,算得上是十分常見的事。IM堪稱是個汙點。
但首先他們得經過身分確認,因為祕密警察會為自己的線人和跟蹤的人取好別名。實際上,多數線人都會先幫自己取好別名,因為作為一名常規IM的入門儀式,就是選定自己的匿名。而就在東、西德統一之後,問題來了,有一位東德的知名盲人DJ魯茲.貝特倫過去曾以「IM羅密歐」的身分為史塔西提供密報。他過去倘若曾經和我碰面,那麼我想就很有可能演變成羅密歐自己密告自己。
我的「開場報告」簡要摘述IM「史密斯」、「舒爾特」和「米赫拉」及其夫,也就是聯絡人(Contact Person, KP)「吉爾」所提供的資料,並以「米赫拉」與「吉爾」所提供的資料內容摘述最多。其中「吉爾」的前妻名叫愛麗絲,人稱「紅麗姿」(Red Lizzy),溫特少尉註記她更早之前曾嫁給英國最知名的蘇聯間諜金.菲爾比(Kim Philby)。
他發現「G一心堅定並一如學者那般仔細的工作著」,但卻儼然「一副資產自由的姿態,並不支持勞工階級」。「G的外表給人感覺很隨性,整體看來猶如『典型的英國知識份子』。」(這種怪異的恭維是來自IM「史密斯」。)然而,我已經試圖向可能有興趣從事情報工作、同時還能說明我的行為恰恰與上述說法相反的人聯繫。我前往波蘭的那幾次,幾乎可以肯定是「與反社會主義團體保持聯繫」。所以他們必須找出更多訊息,才可能依《刑法》第九十七條將我起訴。《刑法》第九十七條明文規定,凡蒐集、傳送「應當保密的訊息或物件」至他國政權、祕密情報單位或者其他不明「外國組織」之人士,將被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重大者,將可處以無期徒刑或死刑」。
接下來的「行動計畫」則包含四部分。首先是配置IM,從「史密斯」開始:「將IM主觀及客觀的可能性納入考量,須創造出與賈頓艾許恢復聯繫的條件」,並於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五日前完成書面提案。「負責人:溫特少尉」。「舒爾特」、「米赫拉」亦須重新啟動:溫特少尉將於五月一日前完成這方面的書面提案。再者,「HVA I的IM,即G在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university] B[erlin])的指導教授」則須進入「作戰模式」(the operational treatment)。
HVA係東德對外情報局,全名為「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Aufklärung」最常見的意思為「教化、啟蒙」(Enlightenment),所以亦可譯為「啟蒙局」,該局局長即為代號「米夏」(Mischa)的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Wolf)。英國著名諜報小說作家約翰.勒卡雷筆下《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中的部門「the Abteilung」,就是以「啟蒙局」為藍本所寫成的。HVA I,即啟蒙局第一處(first de-partment),主要負責監視位於波昂的西德政府。
接下來的計畫則轉為「作戰性監視與調查」(operational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施行措施包括對克雷索夫婦進行深度調查,在洪堡大學出租落地窗房間給我的,正是他們夫妻倆。第三類別「進階措施」則是下令由負責跨境交管的第六總處(Main Department VI)進行「搜索」,並由M處啟動「郵件管制」。檔案寫著「G在西柏林的地址」,但這指的想必是從我西柏林公寓所寄出的信件,因為史塔西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能拆閱他人在西德的信件。接著,溫特少尉的任務又來了,也就是整理出一份報告,評估是否將這份OPK調查轉為全面性的「作戰個案」,簡稱「OV」。「OV」是最高層次的作戰類別,含括已知的反對人士與政權評論家,如我的朋友華納在這似乎就是OV「山毛櫸」。
最後則是「與其他服務單位合作」。在此,由四之二十處(department XX/4,負責滲透教會)就我和德高望重的「山毛櫸」聯繫這點居中協調,並打聽「蘇聯國安組織目前對於英國祕密情報局(British Secret Service)正在追查菲爾比案的消息感不感興趣」。AG4從事「具體協調」,以評估是否可能在我前往波蘭時指派線人進行「貼身監視」。AG4正是史塔西所成立的工作小組,旨在追蹤波蘭團結工聯革命的可疑發展。負責人為里塞少校(Major Risse)。
文件最後不但有溫特少尉簽名,還有負責西歐所有情報單位的九之二處(department II/9)處長考爾佛斯中校(Lieutenant-Colonel Kaulfuss)批簽。
所以,那就是他們的「行動計畫」,而我現在的行動計畫,就是去調查他們對我的調查。我得循著檔案中他們從頭到尾對我的調查,試圖去追蹤本案的線人和官員、查閱其他檔案,再把史塔西的紀錄和我個人的回憶、當時所寫的日記與筆記,還有我從那時起所撰寫有關這段期間的政治史做比較,那麼我就會找出什麼。
在強而有力、辯才無礙的東德牧師約雅敬.高克(Joachim Gauck)出任「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聯邦管理機構」首長一職後,其冗長的機構名稱便常簡稱為「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我的檔案便是來自高克機構位於柏林的主要檔案庫,實際上也就是國家安全部先前的中央檔案庫。該部所處的綜合辦公大樓位在東柏林最右端的諾曼街,占地約一點五個街區。部長的辦公室和私人公寓與他離職時相差無幾:擺滿一堆電話的辦公桌(話機分為「機密」、「極機密」、「最高機密」)、整齊的小臥室,還有一盤由「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幼稚園學童所致贈的黏土模型,其中有黏土做的香蕉、小精靈、標示為「珍寧」的小狗,以及一粒由「克麗斯汀」所做的檸檬。
多數其他建物則是賦予了新的功能。所有過去曾經特別加封,以防機密文件遭雙面特務暗中帶走,或是僅被一陣不經意的風給吹走的對外窗戶,如今皆已不再密閉。以往那些考爾佛斯、溫特不斷進行著沉悶交易的場所,如今也已成了一般的辦公室、超級市場、「里特斯」運動兼桑拿館與職業介紹所。但,檔案庫的功能還在。
分類室中,身穿亮粉紅工作服和尼龍長褲的中年婦女在一台台大型的卡片索引機器間啪嗒啪嗒的踩著塑膠涼鞋。我之所以稱為「機器」,是因為它們需要啟動。一如遊戲場裡大轉輪末端的車子,真正的卡片索引盒懸於滾輪軸末,按下「K」鍵,大滾輪便嘎嘎作響,直到「K」字卡置於頂端。「F16」索引系統─此即卡片種類的縮寫─涵蓋的全是真名,只不過是按照史塔西本身的音標字母進行排序,是以,舉例來說,「Mueller」、「Muller」、「Möller」和「 Müller」全都歸在同一檔案裡。(假如你是藉由安裝竊聽器或監聽電話來選取名字,那麼你就不會知道名字確切的拼法。)粉紅色的女士就是從這裡啪嗒啪嗒的走去查看依照案例號碼編排的「F22」索引系統,或者偶爾找一找官員的個案名冊,這才會在某棟建物七層特殊加固樓板中某一層上方的特製庫房裡找到實際的檔案。塑膠涼鞋踩過來、踏過去,拍嗒拍嗒的聲響不絕於耳,伴隨著檔案庫每日定量的攪出一塊塊有毒的瑪德蓮蛋糕。
她們帶你沿著走道走到「傳統室」,在那有獎章、列寧的半身像、表現優異的證書、表揚「契卡」(Checkist,即蘇聯對祕密警察的稱呼)功蹟的橫幅,寫著:「唯有他,才是冷靜、熱心和清廉的契卡(菲利克斯.捷爾任斯基,F. Dzerzhinsky)」。桌上放著看似果醬罐的東西,每個罐子都被仔細的貼上標籤,裡頭還裝有一小片骯髒的黃色棉絨。這些都是採集好的體味樣本,倘有必要,他們會給警犬嗅一嗅味道。根據史塔西的字典,它們的正確說法應該叫「氣味保存」。我杵在那裡,頓時大膽的臆測起我自己過去的氣味,或許正如果醬那般仍被保存在這偌大建物的某一處?
附近則是他們所謂的「大銅鍋」,一個既大且深、四周都是銅牆鐵壁的房間。檔案局曾經計畫在那架設龐大、全新且涵蓋人人所有個資的電腦系統,而那些金屬,正是用來隔絕來自外部的電子干擾。但這個大銅鍋如今裝的卻是數以百計塞滿紙類的麻布袋,袋裡全是從一九八九年秋天爆發大型抗議活動,直到一九九○年初民眾強占檔案局這數週之間所絞碎的文件。假定史塔西真的煞有其事的摧毀最重要且最敏感的文件,那麼高克機構如今則是試圖一片又一片的重建起那些文件。
這個高克機構真是詭異之地:一個盤據在過往「恐懼之部」的「真相之部」。回到柏林市中心的行政總部,那裡的長廊裝有西德的新式燈光、鋪有塑膠地板,同時回音繚繞不絕,卻仍隱隱殘留著再清楚也不過的東德氣味。鬱鬱寡歡並帶有啤酒肚的門房警衛、製作精巧的訪客證、法律規定、附屬細則、三聯式的表格、隨處收費……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在顯示出德國官僚體制的龐大組織,還有傲慢的福利國家所遺留下來的習性。一如眾多的德國機構裡,職員們似乎每分每秒都在外出用餐、休假,或者「就醫」。自古以來用以辨認德國上班族的訊號,就是迴盪在走廊間的「用餐愉快!」(Mahlzeit!)或是聽聞一位祕書詢問另一位祕書「我能借用你的碎紙機嗎?」。有那一瞬間,你想像著一個繼承的部,現正想盡辦法逆轉時光,將撕碎的檔案一拼湊回來。
同時,你所看到的每一份文件,裡頭每一頁都已經過機構檔管人員重新編碼,並在史塔西親手仔細標示的頁碼上整齊的蓋上橡皮章。這就有如針對德國進行一場徹頭徹尾的拙劣模仿,由一個極端追隨起另一個極端。也許近代史中未曾有過任何一個獨裁政權,一如東德那樣擁有廣泛、嚴密又滴水不漏的祕密警察組織,除了新德國,也沒有任何一個民主政權會把先前獨裁政權所遺留下來的產物赤裸裸的坦露在世人面前。
統一後的德國議會在一九九一年通過一項特別法,詳盡規範這些檔案必須如何運用。舒茲女士曾早我一步讀過我的檔案,因在審慎的實施該法並忠於其職責下,她應把檔案上出現史塔西受害人或無辜第三方的頁面影印,在影本上把那些名字塗黑,然後再次影印,以確保名字不致在強光照射之下遭到破解而曝光。若有他人和本次調檔無直接關連,她便得遮蓋有關這些人士個資的所有段落。但所謂祕密警察正是透過蒐集、利用私生活中最不為人所知的細節才能確切運作,那麼又有什麼會跟了解這樣的祕密警察無關呢?
閱讀檔案可能會帶來恐怖的影響。我想起知名的維拉.沃倫伯格(Vera Wollenberger)案。維拉.沃倫伯格是華納牧師在潘科教區的一名政治活躍份子,她曾藉由閱讀檔案發掘出她先生克努德從和她認識以來,就一直密告她的消息。週日,他倆會帶孩子外出散步,週一,她先生便一古腦兒向負責本案的史塔西官員密報所有訊息。她以為自己嫁給克努德,後來才發現自己其實是嫁給「IM唐納」。(維拉在其個人回憶錄中稱之為「克努德—唐納」或「唐納—克努德」,如今兩人當然已經勞燕分飛。)或者一如作家漢斯.約欽.謝德禮(Hans Joachim Schädlich)發現他的親哥哥一直都在密告他。他們僅能透過檔案才能發掘出這些。倘若檔案並未公開,他們或許都還維持著兄弟、夫妻的關係,並處在一座以謊言為基石的堡壘,持續著對彼此的愛。
當然也有輕微一點的副作用。在該法施行後,東柏林洪堡大學的學生便四處向女友們吹噓:「我當然準備好看我的檔案。我很害怕去想會在裡面發現什麼,但我就是得知道。」這麼說著實會讓性感的古義大利薩賓族(Sabine)印象深刻。接著你收到來自該機構的恐怖信件,信上寫道:截至目前,您並未建檔。真是奇恥大辱,薩賓族遂轉而投入有檔案之人的懷抱。
當我告訴人們有關我的檔案,他們的回答很怪,不是「多幸運啊!」就是「何其榮幸!」倘若他們自己跟東歐有關,就會說「對,我得來申請調檔」,或者「我的檔案似乎銷毀了」,又或者「高克說我的檔案可能在莫斯科」,卻從來都沒人說過「我確定他們沒有我的任何檔案」。我們幾乎可以用佛洛伊德的說法來描述這個症狀,那就是「檔案妒忌」(file-envy)。
事實上,相較於許多檔案,我的檔案根本算不上什麼。比起作家尤根.傅克斯(Jürgen Fuchs)洋洋灑灑共三十個檔案夾,我只有區區一個檔案夾算什麼呢?比起他們專心致力於用整整四萬頁記載著歌手兼異議份子沃爾夫.比爾曼的內容,我的三百二十五頁又算什麼?但小鑰匙得以打開大門,這也正是通往更大間房的方法。不僅止於德國,無論哪裡有過祕密警察,人們都常常堅稱這類檔案毫不可靠,盡是扭曲及虛構。如今我著手檢視檔案內容是否屬實,不是要比一睹他們都寫了些什麼好得多嘛?畢竟,也只有我,才知道自己當時到底在忙些什麼。而那些監視我的官員和線人又以為自己在幹麼?難道那些檔案,還有檔案背後的男男女女,就能告訴我們更多關於共產主義、冷戰,還有暗中跟監這檔事究竟合不合理嗎?對於每位被列入祕密警察的紀錄並仍想一探究竟的公民來說,這樣有系統的公開這些紀錄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創舉。世界各地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檔案。它是否正確?它又曾對那些涉入檔案的人造成什麼影響?這樣的經驗或許可以教導我們關於歷史及回憶,關於自我,關於人性。因此,倘若本書的形式看似任性,那麼其目的並非如此。我只不過是一扇窗、一個樣本、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以及一場實驗的對象。
為此,我所需探索的不僅是一份檔案,還有一段人生,也就是我當時的那段人生。你若存疑,那我要說,「一段人生」和「我的人生」有所不同。所謂「我的人生」,只不過是持續的改寫自己的過去;「我的人生」,是我們與之共存、賴以為生的心路歷程。而實際上所發生的,根本就是另一回事。
藉著尋找一個遺失的自我,我也同時尋找一段遺落的時光,還有一個問題的答案,也就是:遺失的自我是如何塑造出遺落的時光,反之亦然?史實上的時間點及個人的時間點,公開及隱私,重大事件及我們自己的人生。史學家凱斯.湯瑪士(Keith Thomas)在撰寫多數被傳統政治史所忽略的人類經驗時,引用了知名文人塞謬爾.詹森的話:
律法或王權所能造就或療癒的部分
相較於人類心智所能容忍的
是何等渺小
但是,在我回顧過往的同時,我才發現到,我有多少個人內心的經驗都是由我們當代的「律法和王權」─也就是東、西德不同政權,還有這二者之間的衝突─所促成的。也許,強森所表達的不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而是一種僅適用於某個地區的道理,而且,要是有哪個國家真如強森所說的那樣,那麼人民可就幸福了。
第一章
封面的「OPK」表示「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亦即「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onal Person Control)。根據國家安全部司法高級中學(Juridical Higher School)一九八五年版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Dictionary of Political-Operational Work),「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旨在辨認出可能觸犯過刑法、夾帶「敵對─負面態度」或者「遭敵方利用、以達到敵對目的」的人。據字典解釋,「OPK」的核心目的,在於找出「誰是誰」,每份檔案一開始都有「開場報告」和「行動計畫」。
我的開場報告始於一九八一年三月,係由溫特少...
推薦序
出賣作為一種美德
梁文道
一九八○那一年,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還是一個在東柏林當交換生的英國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當時的女友安德莉亞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來,把衣服脫光,走到面對街道的窗戶旁邊拉開窗簾,接著又開了足以點亮整個房間的大燈,然後才回到床上。這個舉動似乎沒有什麼太深的含義,頂多是年輕人那種沒來由的浪漫罷了。可是近二十年後,已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同時替英國各式報刊撰寫評論及報導的賈頓艾許,卻對這件小小的往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懷疑安德莉亞其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插在他身邊的線人;她那天晚上脫衣服開窗簾,為的是要方便外頭的同夥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這種疑慮,是因為他看到了當年東德國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簡稱MfS,更常為人所知的是其俗稱「史塔西」,Stasi)的一份檔案。這份檔案的封面蓋著「OPK」三個字母,意思是「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戰性個人管制」,根據東德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它的意思是「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於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國人似乎對任何事物都能給出精確定義,就連情報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會有這麼古怪的辭典)。此類管制的目的,最簡單的講法,就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而關於賈頓艾許的「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就是當局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類似賈頓艾許手上這樣的檔案還有很多,將資料夾豎排起來,可以長達十八公里。這也難怪,史塔西大概是人類史上網絡發展得最龐大也最嚴密的國安機構,其正式雇員就有97000人,非在職的線民更有173000人。若以東德人口估算,平均每五十個成年人當中,就有一個和史塔西相關,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間接為它服務。在這樣的一張大網底下,當年東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謂無可逃於天地間。「史塔西」如此規模,不只蘇聯的「克格勃」(KGB)遠比不上,就連納粹時代的「蓋世太保」也要自嘆不如。東德的這一系統實在堪稱完善,至少理論上它應該很清楚每一個國民「誰是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想什麼。饒是如此,最後它也還是逃避不了傾覆的命運,這是不是一個教訓呢?這個教訓的第一個意義是,再鉅細無遺的維穩體系原來也無法挽救一個腐敗的體制(掌握一切的「史塔西」當然知道東德的腐敗,它的頭目梅爾克(Erich Mielke)便曾親口對下屬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腐敗的國家」)。它的第二個意義是,原來東德幹得還不夠出色,它們的工作應該再聰明一些細緻一些才對。至於哪一個教訓更加重要,這就得看要領會這份教訓的人是誰了。說來奇怪,雖然「史塔西」清楚東德的腐敗,但它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造成腐敗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敗可能還是比普通的權錢交易更加深層的腐敗。那種腐敗就是人際關係與社會道德的腐敗。
東德垮台之際,柏林有一大群市民衝向國安部大樓,想要占領這座掌握一切國民資訊因而也叫一切國民恐懼的建築。建築裡頭則是一群手忙腳亂的特工,他們正趕著銷毀最機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絕大部分檔案都被留了下來,現歸「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管理。這個機構負責保存「史塔西」留下來的檔案並將之分類,允許所有前東德國民調閱有關自己的檔案。
後果顯然易見,一百多萬人提出申請,想要看看「史塔西」有沒有關於自己的檔案,其中又有近五十萬人確實看到了這種材料。在這些材料當中,他們就像看老日記似的重新發現了自己,並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謂「人家」,指的是他們的同事、同學、鄰居、朋友、親人,乃至於最親密的伴侶。於是有學者失去教職,因為他曾在過去向當局舉報同行,害得後者失業;有人被迫遷居,因為他曾偷窺狂似的監視鄰家的一舉一動;有些人離婚,因為他的另一半正是當年害他坐牢的「史塔西」線人;更有些人自殺,因為他們的子女發現自己竟然被父母出賣,自此斷絕關係。
在這種情形底下,賈頓艾許懷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實在是情有可原。那時他正在牛津攻讀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第三帝國時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了搜集資料前赴東柏林留學。等他到了之後,便發現歷史即在眼前,遂把關注範圍移向當代。後來他以研究和評論德國及中歐事務聞名,得知「史塔西」密檔公開,自然想要回來查看自己是否屬於「作戰性個人管制」的範疇,同時加深了解他所喜愛的德國,以及看看當局對於「他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取得檔案之後,他以熟練記者的技巧逐一回訪監視過他的線人(也就是他當年的朋友)和負責聯絡那些線人的「史塔西」官員;又以歷史學家的素養細心檢索相關文獻,解釋其中的出入與歧義。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就是《檔案》這本書的主線。它是本奇怪的自傳,在自己的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祕密報告筆錄之間穿梭來回。它又是本微觀史述,恰如賈頓艾許自言,為那個前所未見的系統和在它管轄下的社會「開了一道窗口」,令讀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國家」這四個字的實際分量。
不難想像這本書以及其他一切近似體驗當中的情緒:發現事實之後的震驚,被出賣之後的痛苦,被背叛之後的不信任,被揭發之後的沮喪、自責與否認。所以很多德國人都說「夠了」,應該停止「高克機構」的檔案公開工作,它已經毀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關係,過去的且讓它過去,歷史的傷口就留待遺忘來修復好了。不過,這並不是今日德國人做事的風格,何況這是個在短短幾十年內經歷過兩次極權統治的國家。包括賈頓艾許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東德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如此驚人的祕密警察系統,是因為它有一個在納粹時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礎,所以德國不認真清算自己的歷史是不行的。中國人總是喜歡比較德國和日本,誇獎前者坦白對待納粹的罪行,卻又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近二十年來在處理東德歷史上的細緻(儘管很多德國人還是認為做得不夠徹底)。
與其抱怨「高克機構」的做法過火,不如想想這一切問題的源頭。難道沒有它,前東德的百姓,就會繼續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嗎?不,他們很可能只會繼續猜疑下去。就像書裡頭一個老頭的告白:「至少我能立遺囑了。過去我覺得我女婿一直都在密告我,然後我對自己說:媽的我會把房子留給你才怪。但是現在我就能放心了。」除了這個老人,當年到底還有多少人懷疑過自己身邊的人呢?這種事情並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會不存在的。「史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對付自己國民的祕密警察,既祕密又顯眼,它以祕密的行動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種下恐懼的種子。恐懼,乃是這種體制的基石。它的雙重性質要求國民也要以雙重態度來對待它,在表面上愛它愛得要死,在心裡則怕它怕得要死。結果是一群表裡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個體;這就是它的深層腐敗,東德政權大廈的散砂地基。
對「史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賈頓艾許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於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史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分很好利用,於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麼一來,他就得藉著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並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裡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赫拉」,面對賈頓艾許二十年後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私下大家都對他們怕得要死,所以有人藉著閒聊、提供各種無害的細節,以試圖洗刷自己的嫌疑,表現出自己有多麼合作。」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於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並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史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制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赫拉」,身為畫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史塔西」合作,「米赫拉」可以換取這種在很多外國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麼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著把「史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跟自己接頭的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麼地點說過什麼話,某某人又在什麼時間見過什麼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史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資訊?「米赫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常常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閒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鬆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麼樣了?」她則輕鬆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閒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後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史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於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賈頓艾許去「米赫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浩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著迷,由是不免奇怪這麼好的展覽為什麼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赫拉」她們怎麼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賈頓艾許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赫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係,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賈頓艾許是英國人,這個身分在「史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只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於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史塔西」人員會用慧眼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賈頓艾許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採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到留學生的身分;在「史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分(誰沒有好幾個身分?誰不會用不同的身分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賈頓艾許「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紀錄裡頭,他們還會把賈頓艾許替之撰稿的英國雜誌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賈頓艾許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後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後都別有深意。這就是「史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賈頓艾許在這本書裡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後,我居然感到當年「史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有些道理的。因為他就像當年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他們在東歐認識的異見份子,在能力範圍內會儘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嚮往過有著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的英式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軍情六處」,英國對外情報單位),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史塔西」監控他又有什麼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於「史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好萊塢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直譯為《他人的生活》)所顯示的,這本書裡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於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夥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賈頓艾許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就是否認,要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賣看作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視棄天下猶棄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可見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繫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後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於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麼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整套價值必須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於是每一個告密者都能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義然的理由,讓自己安心;每一個出賣過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後多年把往事推給那個時代的道德錯亂。
出賣作為一種美德
梁文道
一九八○那一年,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還是一個在東柏林當交換生的英國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當時的女友安德莉亞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來,把衣服脫光,走到面對街道的窗戶旁邊拉開窗簾,接著又開了足以點亮整個房間的大燈,然後才回到床上。這個舉動似乎沒有什麼太深的含義,頂多是年輕人那種沒來由的浪漫罷了。可是近二十年後,已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同時替英國各式報刊撰寫評論及報導的賈頓艾許,卻對這件小小的往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懷疑安德莉亞其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收藏
3收藏

 16二手徵求有驚喜
16二手徵求有驚喜



 3收藏
3收藏

 16二手徵求有驚喜
1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