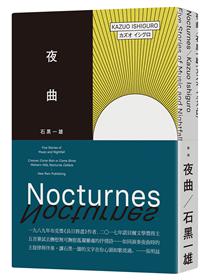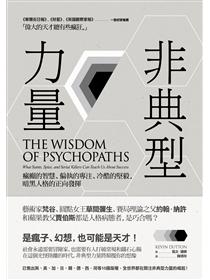一個沒用女人的一生,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歷史
一部平凡小人物的生活史,構築出大時代的跌宕興衰未知死,焉知生。
一個人怎麼信仰,便決定他怎麼活。
2017年「茅盾文學新人獎」獲獎作品
2017年「新浪文學獎」總榜第一名
最受矚目中國七○後實力派作家任曉雯最佳好評新作
★中國長篇小說年度金榜入圍作品
★2017年《南方周刊》十大好書
★榮登騰訊華文好書榜、百道好書榜年榜
「其實人都是一個一個的。單個的人構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構成了時代。一個個時代,就構成了歷史。人是歷史的目的。人是起點,也是終點。宋沒用是被歷史遺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時代篩漏了的小人物。而我想寫的,正是這麼個『沒用』的人,如何隨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難,穿過死蔭的幽谷,如何在波瀾不驚的外表下,經歷最壯闊的內心風景。」──任曉雯
宋梅用,本名「宋沒用」,在上海度過一生的蘇北女人,生於一九二一年,家中么女,因被母親嫌棄而取名為「沒用」,父母稱她「沒用」,子女也認定她「沒用」。一個「沒用」的女子,走過二○年代到九○年代的中國,戰亂、飢餓、瘟疫侵襲生命的當口,宋沒用餵養父母,拉拔子女,接濟兄長,扶持弱者。這樣一個飽受父權欺凌,歷盡人世滄桑的「沒用」女子,為何能懷抱著為人「有用」的信仰,最後成為父兄、母親與子女們所能倚賴的唯一?
宋沒用折射出大時代裡普遍的中國人身影──一個不曾被歷史惦記過的名字、一道在苦難困頓中奔波的身影,即使被紛沓而至的時代巨輪滾碾而過,面對歷史席捲而來的風浪,卻仍堅毅懷抱著為人「有用」的信仰。
相對於「未知生,焉知死」,任曉雯極力塑造的宋沒用,更體現了「未知死,焉知生」──一個溫柔且堅毅的靈魂,在一幕幕城市風景中上演一部屬於平民的史詩;任曉雯筆下的宋没用,在灰濛濛的歷史中如同一葉堅實的扁舟,隨著如流水般的時代,起伏跌宕,時起時落,未曾想過何時可靠岸,卻始終在驚濤之時守護著乘載在自身之上的家人。
嬰兒宋沒用,瘦得肚皮一褶褶。……「死了最好,省得費糧食。」母親將稀湯樣的奶,滴在她人中上。宋沒用聞著味,雙唇一嚅,活了起來。
各界讚譽
《好人宋沒用》講述的是一位蘇北女性在上海立足生根的故事,以一個普通女性的一生經歷與心路歷程貫穿起上個世紀的歷史。任曉雯的文字乾淨有力、輕靈細膩,以豐富細節和生動情節構建出活色生香、極具上海特色的市井生活。作者在考據歷史背景方面做足了功夫,通過描摹小人物的命運反映了時代變遷,頗具張力的敘述語言能貫穿始終,體現出作者的文學抱負及對文字、文學的敬重。
──新浪好書榜2017年度「十大好書」頒獎詞
無疑,任曉雯寫了一部今年乃至新世紀以來最好的漢語長篇小說,一部增色「上海學」的敘事文本。……《好人宋沒用》敞露了蘇北人的「出埃及記」……而死亡才是這部說大寫特寫的主題。《好人宋沒用》從頭至尾貫穿著死亡。任曉雯以喜襯悲,以輕快載沉重,饒是死相累累,卻也掩蓋不住一部少數族的紮根史。裸命的存在,隱忍的生受,血氣淋漓的苟且掙扎,堅韌決絕的苦熬折騰,於任曉雯筆下,莫不栩栩如生呈現出來,並剝離出蘇北人的苦難和堅強的意志,乃至原初流民的信仰系統,從而與今人形成鮮明參照。卑微而不自輕自賤,或許這是他們的精神雕像。
──文藝評論家 肖濤
在「好人」與「沒用」這對極具張力的修辭中,任曉雯為我們做出了專屬文學的釋義。她用一部長篇小說,為我們解釋了何為「好人」,何為「沒用」,解釋了「好人」如何在「壞人」的世界裡艱難地活出自己的樣式,以及「沒用」者是如何成全自己「有用」的一生。一切就是這般的纏繞,可纏繞也許就是塵世的本相。所以,當任曉雯在後記中寫道,這部小說的寫作,是「從『她們』到『她』的寫作」,我卻依舊有理由認為,這部小說同樣實現了「從『她』到『她們』」的書寫。從個體到人類,沒有一端是文學可以偏廢的,否則,閱讀這部小說時,我就不會被那個獨特的、不可折射普遍人性的宋沒用所深深地打動。我想,打動著我的,依然是那個人類共通的命運之感。
──小說家 戈舟
任曉雯又一次突破了自己,完全揚棄了早年華麗銳利的技巧,不露聲色中就讓人目不暇接,跟隨著宋沒用命運的起起伏伏,向老上海的歷史遠眺。而那看似普通的一生,投射的卻是一座城乃至一個國家的背影。
──廣州日報
近幾年的寫作中,除了陸續見諸報章,收穫讚譽的《浮生》以外,任曉雯一直在寫一部橫跨上世紀二○年代到九○年代、窮盡一個女人畢生悲喜榮辱的小說。2015年,在改了三稿以後,小說中部分片段以《藥水弄往事》為名發表在《花城》雜誌,隨即入選《2015年中篇小說選萃》等選集,並獲得當年《中篇小說選刊》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但她並不滿足,因為「文字沒能讓我自己滿意」,於是再改。前後總共寫了五稿之後,這部名為《好人宋沒用》的長篇小說終於塵埃落定。
──《文學報》
一個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發展,看似平行,在書寫中卻又是一個互相滾動的過程。其行雲流水的敘事,在帶给讀者以審美享受之餘,亦借一個普通人的歷史,於字裡行間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歷史,甚至一個國家的歷史。
──中國評論家 項靜
名家推薦
作家 路內
作家 李欣倫
作家 郝譽翔
作家 鍾文音
演員 簡嫚書
───────感人推薦
作者簡介:
任曉雯
1978年生於上海,小說家。1999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浮生》系列,出版長篇小說《好人宋沒用》《生活,如此而已》《她們》《島上》,短篇集《陽臺上》《飛毯》等。長篇小說《她們》榮獲2009年華語傳媒大獎提名獎。曾獲百花文學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南方周末》外稿獎、華文好書獎等。
《好人宋沒用》首發於《十月》雜誌,被《當代》長篇小說選刊等轉載,引起關注與好評。
小說見於《人民文學》、《花城》、《上海文學》、《大家》、《天涯》等;隨筆、評論等見於《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南方人物周刊》。作品被翻譯成瑞典文、英文、義大利文、法文、俄文等語言。
章節試閱
1.
宋梅用,本名「沒用」。當她兩歲,逢了大荒年。全家被饑餓趕逐,從阜寧搖著艒艒船,經由運河,停在蘇州河畔。起先住在船裡,船身開裂,就上岸來。撿幾根毛竹,烤成弓形,搭起「滾地龍」。
帆篷為頂,草苫作門,地上鋪一層稻草棉絮。外頭落雨,裡頭跟著泥濘。母親讓孩子們撿拾蘆葦、麻袋、碎磚、木板、鐵皮,和了泥巴,反覆修葺棚頂。
懷宋沒用時,母親逾四十,生過六女三子,夭了五個。她渾身關節痛,手指發黑變形,走起路來,拖著兩隻扁腳,洗衣服都蹲不住了。男人揍她。一邊揍,一邊從後面肏她。他在外頭姘了個女人,並不隱瞞。「你的屄都鬆了。」他當著孩子們說。
她曾掿著洗衣槌,追打那野女人。野女人奈她不得,轉拿男人出氣,抓破他的面皮,哭訴一場。
男人步子帶風地回家,見婆娘在河邊洗頭,一腳踢落下去。她自己撲騰上來,從此染了大喘氣的毛病。
說話怏怏的,時或狂咳,咳得頰頤浮腫。
她把對丈夫的怨怒,轉嫁給兒女。打得找不到好皮肉下手了,擔心小白眼狼們記恨。便撮一碟蔗糖,烹幾隻紅薯,筷頭篤篤叩擊碗沿,「媽媽自己不吃,省給你們吃。以後要待媽媽好。」孩子們抓搶著,燙著,噎著,咬著舌頭,顧不得理她。她即刻心疼起口糧。
活得太膩,等死的日子又太長。風裡長刺的季節,她以為終於絕經,卻是再次懷上了。她罵丈夫像條野狗,只知下種。她趴著睡覺,用洗衣槌碾壓肚皮,站在窪地上單腳跳。聽聞吃瀉藥管用,便也一試。拉得腸子快流下來,那團肉依舊牢牢吸在腹中。
一日,往地頭走,忽有便意,腰裡一酸一酸的。探一把褲襠,果然濕了。她裂開嗓子,喊「大丫頭,大丫頭」。大丫頭正拾柴,一聽,懂了,扔了柴火,往接生婆家跑。
生產幾乎要了她的命。每次宮縮洶湧,她都厲聲詛咒這個孩子。男人踱進踱出,罵罵咧咧,「有力氣叫,沒力氣生」。幾個親戚在褥邊圍觀半日,閒閒散去。大丫頭幫忙換盆水,洗毛巾。兩個小的顧自玩耍。
她都意識不到。人家拖她,就坐起,人家摁她,就臥倒。使力使得眼珠快爆了。熬到第八個時辰,接生婆在她腿間依稀看見腦袋。一拽不出,便捏斷孩子鎖骨,縮小了,摳出來。
嬰兒宋沒用,瘦得肚皮一褶褶。母親將她扔在旁邊。少時,不忍,揪起自己的乳頭,戳在她嘴上。父親盯一眼乳房,它們像兩掛漏得差不多了的水袋。扭頭道:「她咋不吃,是不是快死了。」「死了最好,省得費糧食。」母親將稀湯樣的奶,滴在她人中上。宋沒用聞著味,雙唇一嚅,活了起來。
2.
夏杪,起洪水,作物殆盡。仲冬時節,族人聚會。各家口糧歸作一處,反覆籌算,只夠吃百來天。離下次收成尚有半年。宋沒用的父親排行老大,性格最硬,被喚作「榔頭」。由他出門討生計。攜妻子、兒女和老太太。帶了生鐵鍋、燃火的玉米稈子、夜間蔽身的大蘆葦蓆。推著獨輪車,挨村要飯,往鎮江去。
途經一處田地,老太太不肯挪步了,「這裡風水好,讓我死在這裡吧。」她已活得不知歲數,卻牙齒一顆不落,嚼起東西來,嚓嚓響。「人老了,沒用了,讓我去罷。」他們隨意勸幾句,留下她。一起留下的,還有宋沒用。老太太將曾孫女夾在腰上,彷彿是一卷物什。
走出一二里,大丫頭說,聽見嬰兒哭。母親搧她一掌。又過半里,榔頭甩了車把,跺腳道:「我一大男人,難道養不活個小把戲。」返回田間。稻茬染了霜色,縞白縞白的。稗草、牛毛氈、野慈菇、眼子菜,被踩扁了,便往扁裡長。榔頭呼尋一晌,正欲離開,見畛邊一角熟悉的土布顏色。宋沒用在雜草中,睡得正死。他揸開五指,一提溜,摟緊么女。
他們繼續往前,至清江浦,稍稍安頓。榔頭找不到工作。全家擠上難民船,沿長江流離。在糞便穢物中吃睡了半月,被一紙官令驅趕回鄉。族人不樂,有個弟媳說:「大哥不是最能的嗎,怎就回來了,搞得大家沒法活。」榔頭耳輪赬紅,不語。
冬天過去了,全村餓死二十幾人。榔頭的大兒子,到隔壁村子偷食,被打殘。不肯說是誰打的。苦捱數日而亡。母親將蠟燭包扔到床尾,踢一腳道:「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倒死了。」土布散開,宋沒用滾出來。皮肉乾縮,頜骨凸棱,跟個小老太似的。母親哭嚎片刻,見她不動,便抓回懷裡,使力拍晃。終於,宋沒用嘴唇稍稍一咧。「小討債鬼,還沒死啊。」母親掏出乳房。
歲餘,又發洪水,榔頭起念離開。聽聞上海遍地鈔票,很多老鄉都去了。有個遠房表姐,已在那裡安家。他向父母索了一條艒艒船,用麥稈加固頂篷。將自己那份鹽鹼地托給小弟。
清晨,空氣疏冷,宋沒用一家出發了。族人木木然,杵在岸邊,漸成幾條細影子。有條影子不停揮動手臂。是榔頭的母親,佝著背,縮著脖頸,彷彿腦袋直接支在了肩膀上。榔頭眼睛熱了,朝明昧不定的地面線,吼起一嗓子。
水聲冗乏,晨昏交接,一船人忽盹忽醒。二丫頭吐得滿嘴苦膽汁,下巴都脫臼了。母親一開口罵她,小兒子就笑。他現在是唯一的男孩。父母開始稀罕他,將他養得臉圓了,還把他的名字,從「狗蛋」改為「大福」。宋大福玩水、翻弄包裹、扯姐姐們的頭髮。實在無事可做,便趴在舷邊,浸一隻手,滑小槳似的。河面順著掌側破開。那手倏然一勾,一指,「爸,媽!」
艒艒船猛烈搖晃。宋沒用驚醒了,見家人往前擠。金利源碼頭漸駛漸近。檣桅如林,沙船密匝匝挨擠。嘩響的西洋汽輪船,讓她的哥哥姐姐驚作一團。英國軍艦正在入港。煙囪、炮管、彩旗、白制服水手。母親斂了斂衣衽,鼻子齆得透不過氣。父親喊道:「大上海到啦,賺錢吃飯去!」
全家換起體面衣服,繫住船,踏上陸地。身體裡仍然一漾一漾,宛如趟著看不見的水。這是個油棧碼頭,填高之後,砌成混凝土駁岸。一桶桶洋油,等著被卸下,分運,送往各地。跳板、板車、運垃圾的馬車。碼頭工人穿梭其間。父親留意到,他們衫褲上沒有補丁,「這活我也能幹。」他的婆娘張張嘴巴,出不了聲。
父親領頭,哥哥姐姐排成一列,母親背起宋沒用押後。他們彷彿一隊盲人,在這光色濃釅的世界裡,摸著,探著,互相牽引著。走了一段,漸漸覺出,這輩子踩過的最平坦的路,就在自己腳底下。
西行,街市如織。篾竹街、豆市街、花衣街、洋行街、鹹瓜街。街街交通,鋪鋪相連。口音錯綜,人頭如麻。山東的雜糧,徽州的紙墨,杭州的綢緞,紹興的黃酒,寧波的藥品,福建的漆器,江西的陶瓷,無錫的絲棉,廣東的煙草。
一切能想的,不能想的。顏色、聲響、氣味,令人應接不暇。孩子們停在「西洋百貨」。牙粉盒、三五香煙盒、倫敦洋蠟燭、英國機制棉紗線團,樣樣新奇。店主的綢領子上,潽出一張肉臉。面皮不動,低垂的眼瞼間,露一線黑眼烏珠,緊隨他們移轉。
櫃檯邊,貼有老刀牌香煙看板,印了長衫禮帽的中國人,指著一盒煙。煙盒上是個大鬍子洋人,披掛頭巾,手拄彎刀,做海盜裝束。宋大福舔舔嘴唇,伸手去摸。店主驀地動起來,拍掉他的手,巴掌一翻,作勢要打。榔頭奔過來,兜頭一掌,替店主打了。店主甩出一句上海話,他聽懂了,是罵「江北豬玀」。榔頭捏緊拳頭,哈了哈腰,引家人出店。
3.
找到遠房表姐時,天色已然玄青,樓頂鑲了一絲粉。表姐穿窄袖短身襖子,不說話時,像個上海人了。她是「繅絲阿姐」,表姐夫在電燈廠,大兒當紗廠清潔工,二兒做掃地工。其餘三子尚小,撿撿木柴。打算把四兒送去讀書,其餘都進紗廠。
榔頭聽著,默想自家前景。婆娘不停調整姿勢,彷彿那把桐木椅子,硌得她骨頭痛。孩子們縮頭縮腦,失了魂似的。惟有宋沒用不怯,在大人腳邊蠕爬。
表姐夫高瘦,一大管鷹鉤鼻,使得面相涼薄,「我是爽快人,有話直說,」他抽抽鼻子,「工廠招人蠻挑剔的,喜歡年輕的,識字的,你夫妻倆條件差些。再講了,上海這地方,其他都好,一樣不好,就是屁股挪一挪,都要花鈔票。學手藝啦,給工頭送禮啦,對了,還得和老鄉花費結交吧,否則誰來介紹你。夯不啷噹加起來,少說三四十塊銀元。」
榔頭不語。
表姐道:「你們有條船,要不先住藥水弄。那裡老鄉多,找工作容易。實在不行,鄉下土地還在,回頭也有個退路。」
榔頭仍不接話。一時安靜。宋沒用鑽到床底,推開痰盂蓋子,探頭嘬飲。表姐拍她一下,拖將出來。榔頭突然站起,稀裡嘩啦的,抓起幾件自家的物什,顧自往外走。他婆娘「喂喂」兩聲,只得也站起,「姐啊,我們走了,別送別送。大福,糖拿好,謝謝表姑姑。」抱起宋沒用。大丫頭二丫頭拿了餘下行李。宋大福揣起兩塊梨膏糖,怕姐姐們搶,一徑跑到前面去。糖放久了,糖紙黏連。他剝幾剝,剝不開,便連糖帶紙頭,塞進嘴裡。
榔頭已衝出老遠,嘴裡亂罵,「肏他媽,狗日的,臭婊子養的」。忽聽表姐喊他名字,便立住,傲然挺起身板。
表姐喘吁吁追來,「你肯定心裡怪我,我也沒辦法。很多親戚找上門,有能力就幫了。你看這城裡房子,租金貴得要死。我家十平米不到,花掉一大半工資……」
他擺擺手,示意別再說。
「你走得太急,我剛想送點東西,表表心意的,」表姐把一隻煤油爐放在地上,又將兩小包交給表弟媳,「三五件舊衣服,我家小囡穿過沒幾天。」
榔頭道:「還給她,咱們啥都有。」
婆娘嘿嘿笑。
「知道你們有,再拿幾件,也不吃虧呀。」
榔頭冷著臉,不吱聲。婆娘讓大丫頭收好衣服。
表姐道:「你們今天吃過飯嗎,本想留你們吃飯的,」不待回答,又道,「上海流氓多,你們多當心。尤其十六鋪陸家石橋那裡,警察也管不了。」
「怕什麼,要錢沒有,要命一條,」榔頭扭頭呵斥婆娘,「怎麼還不滾,杵在這兒討人嫌。」
妻兒們快步跟住他。出了弄堂,扭頭回顧,表姐已不在。婆娘頓時慌了,迷路似的,兜兜轉。幾個孩子跟著轉。榔頭吼道:「亂個屌,都給我往前走,別朝後頭看。」
他們過南京路,沿外灘,幾次搞錯方向。霓虹漸次明亮,閃爍流轉。榔頭感覺不真實,繼而自卑了。他往暗地裡溜。一刻怕家人失散,下令跟緊些。一刻擔心過於矚目,又命分散開。時或呵一聲:「東西都拿好,別丟了。」漸走得疲乏。滿面油塵,腳步錯亂。婆娘又喘又咳的。宋大福更是眼皮一搭一搭,幾次撞到電線木頭。
回十六鋪,找到自家艒艒船,已是後夜。榔頭舉棹,向著西北,越划越荒闊。臭味濃稠起來,彷彿船底流的不是河水,是隔夜屎溺。婆娘忍耐不住,問去哪裡,回不回老家。他說:「回去?除非我死了。」
蘇州河折了一彎,浮顯大片艒艒船。岸邊幾個襤褸的女人,就著月光洗東西。腦袋此起彼伏,像一顆顆沒有刨淨的土豆。
榔頭問:「藥水弄嗎?」
有蘇北口音「嗯」一聲。
「你們別動,我去瞧瞧。」他收起纜繩,蹬離船舷,一腳踩進泥漿。
4.
月亮扎進雲團,天地暗下來。上頭的星星,底下的豆油燈,跟針刺似的,刺出一點一點的亮。榔頭腳高腳低,走幾步,定住。耳廓一顫,聽見人、貓、狗、雞、豬玀。還有嗡嗡不明的響動,猶如水在煤球爐上,持續作聲。
少時,月亮又出來。密麻麻的棚戶,小丘似的垃圾堆,一窪窪的臭水坑,皆覆上一層藍灰色。
榔頭瞪視良久。連日吊著的氣力,瀉空下來。面頰隱約作癢,一摸一手淚。他胸膛憋悶,必須張口震聲,「娘為兒歷經辛酸容顏改,娘為兒早生白髮人已衰,娘為兒節衣縮食挑野菜,娘為兒望穿秋水盼成才,看今朝兒凱旋歸來把烏紗戴,歸心似箭回雙槐,重見慈顏將娘拜,樂敘天倫笑顏開……」
這段淮劇《席棚會》,是跟唱香火戲的二伯學的。二伯跟他最親,誇他聰明,說他會有出息。二伯五十五歲上,鐃鈸一扔,光著腳,滿村跑,「閻王討命來嘍,做虧心事的別鎖門哦。」兩個堂哥說他撞了邪,將他綁在豬圈裡。榔頭的母親不忍,時常偷偷送吃的。
榔頭一念至此,唱聲哽咽。一條狗聽得不耐煩,扯起嗓門,粗暴回應他。他腦勺一悶,栽在地裡,糊了滿臉泥穢。突襲他的人,乘勢往他背上踩兩腳。一時數人齊上,拳砸,掌摑,腳踢。榔頭蜷了身子,雙臂夾護腦袋。有人掏他衣兜。「我日死你個婊生的,只只口袋空的。」轉手剝他衣褲。
遠處起了呼嘯。流氓們扔下他。榔頭等一晌,確定他們跑遠了,這才偏過臉,讓鼻孔裸在空氣裡。呼吸之間,嗆了髒水,咳幾聲。喉嚨痛,氣管痛,繼而渾身痛起來。有那麼一刻,他巴望永遠躺倒。
夜風裡裹了歌聲,「吃水不清,點燈不明,走路不平,出門不太平。」他想起大女兒,也有這麼清的嗓子。二女兒眉眼長得好,嘴巴靈巧。兒子十二歲,被全家慣著,霸得像個小混蛋。男孩就該混蛋一些,好在混蛋的世上討生活。還有宋沒用,尚不會說話走路,似一塊小肉疙瘩,但他已經不討厭她。
他把兒女想了個遍,慢慢支起赤膊身子,一步一陷,往回走。光影混沌處,暗綽綽有人。是他的妻兒,早已下了船,站成一排等他。大丫頭遲疑道:「爸?爸!」二丫頭和宋大福跟喊起來。其間一絲細嫩之聲,「爸」。那是宋沒用,生平第一次呼喚他。
5.
榔頭的戲唱得好,還會敲鹽阜花鼓鑼。從香火戲《魏徵斬龍》、《劉全進瓜》、《秦始皇趕山塞海》,到淮劇小戲《對舌》、《趕腳》、《巧奶奶罵貓》。一口高亮的淮調,唱得人鄉愁百轉,很快在蘇北老鄉中混熟。
有個姓楊的老鄉,介紹他做碼頭搬運。他興奮了一夜,早起喝半碗稀粥。婆娘拿了雙新草鞋。老楊送一塊搭肩布。晨風清爽,萬物撲簌簌閃光。他挽起袖管出門了。
搬運是苦生活。筐子沉上肩,榔頭啊呀一聲,尿都出來。「哎嚇咿、哎嘿嚇,哎嚇咿、哎嘿嚇……」扛棒號子猶如鐵鞭,抽打他的腳步。碼頭、駁船、過山跳。碼頭、駁船、過山跳。幾個來回後,胃中痙攣不止。老楊摸摸他的肚皮:「沒吃飽吧,讓你吃飽的。」榔頭提前幹掉當午飯的紅薯,仍覺饑餒。重新搭好扛棒。起肩的剎那,脊梁咔啦響,一雙膝蓋顫巍巍互磕。老楊在後肩領號,他沒有接應和唱。步律一錯亂,筐子就晃。老楊罵道:「日你個媽媽,回江北種田去!」
榔頭是想回去種田,這念頭跟浮水葫蘆似的摁不住。他用搭肩布抽自己,抽得面皮紅腫。他想起死去的二伯,捏著自己鼻頭說:「小屄樣子,做人就是做面子。」
老楊說,最初兩月難熬,熬過了,就不那麼苦。「兩月」,老楊戳起二指,像要捅進他眼睛,「心肝骨頭,統統煉一遍,你就是鐵打的了。」
榔頭每次收工回家,都用指頭蘸了黑泥,在艒艒船板上劃一道。一骨碌癱倒,瞬即睡死過去。婆娘幫他擦身。肩上的血,腳底的泡。他蹙起眉頭,在夢中哼哼。她便停下手,就著月光諦視他。他身子扁瘦了,面色像個死人。他已好久沒力氣揍她。
「只知道挺屍,怎麼不去死,」婆娘罵道,「跟你那瘋伯伯,長舌頭弟媳,爛手爛腳的娘,一起死到十八層陰間去。我好好一個大小姐,這輩子跟了你,變成討飯的了。老家再怎麼著,也有幾畝地,一棟房。偏要來上海。什麼藥水弄河水弄,是人待的嗎,畜牲都不願待。」
孩子們不吱聲。榔頭小腿抽搐,呀呀醒來,「死婆娘,我抽筋啦。」宋沒用哭了,二丫頭搧她一掌。婆娘給榔頭揉腿肚,掰腳板。他緩過來,想吃東西,「怎麼還有紅薯?這麼多天了。」「盤纏沒用完呢。」
他信了,捏捏她手,「到底自家婆娘貼心。」
6.
月底計件結薪,算來算去,每擔少五十文。老楊說:「每回都這樣,只能忍著唄。先前有幾個拎不清的,到管理所遞狀子,說工頭扣他們厘頭,結果呢,被反咬一口,丟了飯碗。」
榔頭想一想,說:「總得講個天理呀。掙這錢容易嘛,我都尿出血來了。」「天理?」老楊乜斜著眼,「懶得跟你講。」
榔頭找工頭理論,不停哈腰,倒似虧欠他似的。工頭道:「啊呀,還有這事。你先回去,我核一核。放心,你們賺鈔票辛苦,我不會短你們的。」榔頭千恩萬謝了回去。
翌日上工,老楊道:「怎麼還來呀,姓張的讓我跟你講,以後別來了。他還罵我胡亂介紹人。都怪你,連累我。」
榔頭道:「你瞎講。昨天我們談得好好的,姓張的挺客氣的。」
老楊哼道:「意思是我害你嘍,我早就提醒你。」
「不是那意思,我要見見他。」
「反正我把話帶到了,你再惹什麼事,跟我沒關係。」
「或者見見那個姓方的也行。」
老楊不理他,走去一邊,夥了新搭檔,扛起棒子來。榔頭在碼頭附近轉悠,又蹲到辦公室門前。
等了半日,無果。忽見遠遠站了個巡警,榔頭莫名惶遽,跳起便逃。回到艒艒船上,見船板二十八道黑泥,蚯蚓似的。他探出腳底,一道一道抹去。
逾數日,受另一老鄉推薦,榔頭當上更夫。組裡除卻他,都是老年人。敲了月餘夜梆,皮膚白了,腿不抽筋了,肩膀結痂出新肉。每月只得五元工資。他不敢輕易辭職。婆娘做點草鞋,貼補家用。
還幫人洗衣、撿煤渣、分撿羽毛。兜著針線籃子,給黃包車夫和碼頭工人補衣服。分派兒女們拾荒,替人看車,撿橡皮球出售。
一日,遠房表姐討債。榔頭方知婆娘為了借錢,曾跑去人家門口,墊了蘆草,跪一整天。他用木柝敲她,「人家肯定以為是我借的呢,面子都給你落光了。知道他們勢利,還給他們看笑話。」婆娘哭喊道:「你是個當家的,就賺這麼一點點碎錢。家裡五六張嘴,牙縫都塞不滿,你讓我去偷去搶嗎。」
榔頭羞愧了,愈發揍她。少時,覓了份新工作。每日丑時下更後,接著拉糞車。拉過一晌,應聘掃馬路。他嫌市裡統發的紅布衫工作服丟人。不久結識個小揚州,受薦去澡堂當臨時工。修腳、捶背、端茶送水。活計輕鬆,錢也多,還能趁隙盹覺。
兩年後,榔頭還清表姐債務,又摳省零餘,打點工頭。有煙廠老鄉牽線。廠裡多浙江人,蘇北人只能進煙葉車間。工作重,薪水低,僅招年輕女孩。他盤算幾晚,交了錢,把十七歲的大丫頭送去。
他們開始有大米吃。吃大米的頓數,漸多過吃紅薯。大腿浮腫消褪了,荒蕪的腦門上,重新生長頭髮。榔頭氣力一飽,便往別處溢。他找了相好,不小心弄出孩子。是個男的,頭頂有兩個旋。「雙旋滾雞蛋,長大做大官」。他疼愛么兒,每天都去探望。漸漸徹夜不回家。
1.
宋梅用,本名「沒用」。當她兩歲,逢了大荒年。全家被饑餓趕逐,從阜寧搖著艒艒船,經由運河,停在蘇州河畔。起先住在船裡,船身開裂,就上岸來。撿幾根毛竹,烤成弓形,搭起「滾地龍」。
帆篷為頂,草苫作門,地上鋪一層稻草棉絮。外頭落雨,裡頭跟著泥濘。母親讓孩子們撿拾蘆葦、麻袋、碎磚、木板、鐵皮,和了泥巴,反覆修葺棚頂。
懷宋沒用時,母親逾四十,生過六女三子,夭了五個。她渾身關節痛,手指發黑變形,走起路來,拖著兩隻扁腳,洗衣服都蹲不住了。男人揍她。一邊揍,一邊從後面肏她。他在外頭姘了個女人,並不隱瞞。「...
目錄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後記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後記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收藏
3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3收藏
3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