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疊的記憶作者:湘夫人
許久以來整理父親的文章,一直放在我的心頭上,卻任由歲月蹉跎,任由心緒醞釀,就是不肯一次面對好好整理,或許也是一種近鄉情怯,也許延續著是因為陪伴著我生活,不願那麼明明白白結束。細讀文章好像在跟父親對話,那麼的貼近父親,彷彿在做一份研究資料戰戰兢兢,必需要非常的專注,甚至還要寫重點筆記,才能夠拼拼湊湊出父親的形象,即使如此仍然是不完整的父親,十六年的歲月我居然一點都不認識父親,那些年我到底在做甚麼,難道是父親的嚴厲教育讓我們總想躲著他嗎?整理的過程中我撥開層層紗,勇敢的面對我自以為是的人生,飄飄忽忽,風雨天晴,我的人生已經過了大半,而我究竟明白了些什麼,又失去了些什麼,為什麼父親的影像是那麼的模模糊糊,在我心中的父親以及現實生活中的父親,居然要這麼努力的去回想才能夠喚回幾個熟悉的影像片段,我無法原諒自己,應該說我後悔莫及,偶爾在父親的文章中有寫到些童年生活,都如穫至寶,貪婪的希望可以再多擁有一些,好想跟父親對話、好想抱抱他、說ㄧ聲:爸爸您辛苦了,沒有關係我們會慢慢長大您不要發愁,其實如果您能夠活到九十歲,那我們就能夠更成熟懂事了不是嗎,就可以ㄧ起寫文章,可以很開心聊聊過往了,不是嗎?可是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想罷了,一切無法重來。
父親在鼓浪嶼出生,民國十五年遷居金門,我去戶政事務所查戶謄,期望能夠多一些資料,可惜以前的戶政登記簡要,甚至祖父都查不到他的戶謄資料,就無法知道曾祖父名字,本來想可以知道名字由族譜去找,而祖母是鼓嶼女兒在金門生活過而且長壽到一百多歲,只可惜戶謄也查不到她老人家的父母名字,而登記在父親名下的只有寫楊氏,本來期待可以往上延伸查到一些鼓嶼的生活資料,也無線索可查,鼓嶼我曾去過多次,感覺是另一個家鄉,但毫無資料可連接,只能在父親的文章「五縣婚姻儀式」中知道:遠在民十四年間,筆者童期址於鼓浪嶼鹿耳礁(即旌旗山腳),入讀旭瀛書院(註:旭瀛書院在民國路(今廈門市新華路),另在釋仔街和鼓浪嶼和記崎(今三丘田)兩處設有分院),時達十才。在鼓嶼婚娶,必僱一稚童挑灯,稱曰舅爺,屬龍生肖者(指父親童稚時曾多次當舅爺),曰吉,…坐轎置有紅綢布灯一對赴娘家,按舅爺者務宜父母雙全,兄弟姊妹多人,家境清白為宜…故在童期這匹生意,亦作得有聲有色,可是服式亦要高貴,就是長衫,馬掛,碗帽,胸掛天官鎖銀質,脚穿德國皮鞋,布料絲綢閃目…。寫到了父親童年時期在鼓嶼的生活點滴。
另外在「龍舟渡競」中也提到:謙(註:父親本名顏添源,後改名顏謙),幼時生於鷺江,在民十五年,攻讀鼓之旭瀛書院,時逢十歲,居址鹿耳礁,鼓嶼雖丹丸之島,學校林立,…轉眼雲烟憶童年,令人不堪回首,遷金五十年矣,幼時繼續金門縣立學校…。父親的戶謄上寫著國小畢業,想來求學經過一番顛波從鼓嶼唸到金門,父親排行第三,只聽說二伯很早逝世,在「清明時節」文章中提到:筆者二哥顏金源,卒於鼓嶼,距今五十年矣,葬址「五葉碑」塚地,現可能被匪徒挖掘無遺,至是恨填心胸…。父親文章中常見對兩岸冷戰無法互通的無奈與悲憤。聽母親說,父親長大成人後即負責家中經濟跑船做生意,祖父來金門開設振揚商行,看到骨灰罈上的祖父名字是顏振揚,但在戶謄上卻寫著顏伯良,卻無法查到祖父的戶謄,很是可惜。
在「淚憶大哥」文章中,這是一篇手稿沒有刊登,手稿上父親寫著隱藏,是否擔心當時的立場之故所以不敢刊登,文中提及:民國二十五年間,日寇侵華南下金門之際,浯島訓練保長,址於金門公學,現址「金城小學校址」,吾大哥顏水源入訓期滿,理應可任金城南門保長,然謂名正言順,堂皇耀譽,而大哥秉性剛直為國抗日心懷矢志,即金陷入日奴,退守同安,加入八十師行伍,身當連長之職,…及勝利後,大嫂及侄兒頤頔,姪女頑頒,赴廈攻讀廈門大學,而大哥及嫂侄兒們等,迄爾生死未卜…戰亂時期四分五離,日寇毛匪,擾亂中原數十載,祖父骸葬南安赤崎鄉,姑母泉城南門經商,鼓嶼外祖母歿,生時六十餘間,時以習武不間,外祖母年幼武藝確實不凡,早期長輩均有習武,以防不測,童期與諸表兄弟妹數十,集練拳劍國術…。由文章中父親描述了早期鼓嶼的生活習武,以及大伯的情形,我與大哥在幾年前去廈門找到了堂哥,也是藉由文章中確認以及金門耆老告知線索而得,幫我們連上了這一條線,可惜沒能寫更多了。
在「七賢次與蛇洞」中仍可見父親提及小時候:筆者祖籍泉州,南安赤崎鄉,家父遷居鷺江鼓浪嶼,出生時遇民國四年,及至民國十三年移居金門,迄五十餘載,一度攻讀於鼓嶼旭瀛書院及私塾數年,返金繼而就讀金門縣立學校,班級秋六,同窗五十餘人…。在縣立學校環境真是優美清秀,現之浯江書院講堂即早期之禮堂,兩廊皆為書堂六班…。這是父親寫國小時期生活的回顧,也寫到了延伸到金門的求學,在那個年代求學實屬不易。
父親的文章大多集中在民國64年到67年,是我的國中時期,印象中父親已經較少接油漆工程,想來也是比較有時間寫文章,很慶幸父親留下了這些文章,讓我慢慢解開塵封的記憶,在嚴厲的父親外表下我慢慢發現溫柔的部分,曾經年少的父親,擁著家裡的一艘船,橫越金門廈門海運,年少的他多麼的意氣風發,母親說父親從廈門回到金門都是請人用布袋扛著銀子回來的,而1949年的一場戰爭,兩岸不相往來,滯留金門島上的父親是否曾經有過驚慌失措?是否曾經後悔不該離開出生的鼓浪嶼?在那一年島上的居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是否曾經試著想像如果今天我們被禁止只能在島上生活那我們又應該如何存活下來?
當我看到父親的剪貼簿放著66年4月8日星期五金門日報三版四女的「離情」這篇文章,內心感到非常的驚喜與難過,瞬間明白了父親的期許,父親雖然嚴厲的教育我們,例如吃飯時只能夠夾自己面前的菜餚,不可以交談,要正襟危坐,吃飽飯的時候要將一雙筷子對齊擺在碗的正中央,雙手合十跟大家說我吃飽了你們慢慢吃,才能夠離座而去,在成長期我們確實非常的害怕父親,而跟父親有了距離,一直到我2005年回鄉經營民宿,大哥交給我父親的剪貼簿及手稿,透過文稿我開始第二次遇見父親,每次的書寫其實都是與父親的心靈對話,說著來不及說的故事,跨越了距離,一直到有一個心願出現,讓父親知道我繼續書寫他一定很高興,便開始了我認真的書寫,一個舒爽的午后我帶著一瓶高粱酒到父親墳前告知父親我得獎了,彷彿我的書寫進入了另一個層次,感受到生命的延續與意義,好像對於父親也有了一些連結,每當我在書寫或整理文稿時,總是感覺父親便在身旁,就像以往年少我幫忙謄稿寄報社時,我們是如此的接近,書寫的力量讓我度過許多的不捨,讓我的生命多了一些意義,從此書寫成為我記錄生活的一部分。
寫作也許看似喃喃自語,卻是生命裡ㄧ直斷斷續續存在的力量,每當我茫然失去目標時,總在文字裡找到力量,而這文字的背後是父親的ㄧ篇篇文章,是小時候記憶中的古厝,或是ㄧ段夢境,也許是ㄧ間靠近孩提夢境的公寓,引領我走向下ㄧ步,我在巷弄間散步慢慢接上我生命的地氣,慢慢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立於天地之間的著相,那真實引領著我書寫,持續,直到我恢復呼吸與靈氣方歇,愈往內心寫下去父親於古厝書寫的身影便愈清晰,就連結上了父女來不及的對話,在書寫裡圓滿,離開這ㄧ切我竟感覺ㄧ個字也寫不出來。
或許書寫對我來說是堆疊縫補記憶,也許是內心的救贖,慢慢幫我完成父愛的情感,讓我的生命更透徹,這絲絲縷縷的憶遊文字,讓我重生一般的補足遺憾。

圖:全家福(前排中坐者是祖母、右後二站立者為父親、母親抱著二弟、中間是開照相館的五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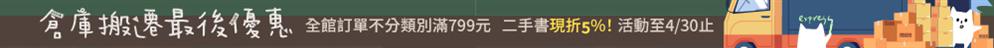





 收藏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