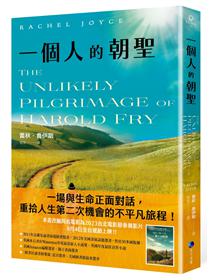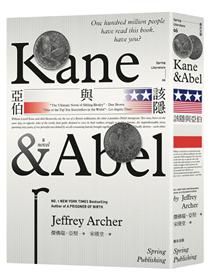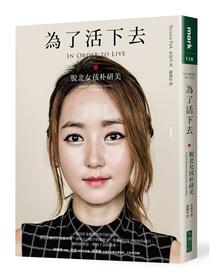「看到最後,不能不為他們的故事流下激動熱淚!」
改編自美國史上令人心痛的真實事件,Goodreads 網站 2017 讀者票選年度冠軍
全美銷售突破 110 萬冊,賣出全球 36 國版權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出版人周刊、亞馬遜網站熱銷之作
吳曉樂、陳又津、番紅花、楊富閔 同聲推薦 原本幸福美滿的七口之家,一夕之間遭硬生生拆散,
該為孤兒找到歸宿的育幼院,背後隱藏了什麼陰暗祕密?一九三九年,十二歲的瑞兒和她的四個弟妹,與年輕的父母一同住在密西西比河的船屋上。那晚風雨交加,父親必須將難產的母親送往醫院,臨行前叮囑瑞兒要照顧好自己的手足,怎料這一離就是永別。隔天,五個孩子遭警察強行帶走,送往「田納西兒童之家」,雖然大人們保證他們很快就能與父母團聚,但未知的黑暗仍逐漸朝他們襲來,瑞兒拚了命要保住所有弟妹,不讓一家人再次被拆散。
二○一七年,在南卡羅來納州艾肯市,即將舉行豪華婚禮、很可能會接下父親參議員棒子的聯邦檢察官艾芙芮,在老人安養院的一次意外遭遇,驅使她好奇地探索那段模糊隱匿的家族史,沒想到竟就此踏上一條最終走向崩壞或救贖的道路──端看她如何抉擇。
這部令人動容的小說,靈感源自美國史上一樁真實事件。兩個家庭、相隔數個世代,因為叫人心碎的不公不義而發生永難癒合的改變。
作者簡介:
麗莎・溫格特Lisa Wingate
麗莎.溫格特當過記者,是一位勵志演說家,也是暢銷書作家,著有超過二十本小說。她的作品獲得許多獎項肯定,包括派特.康洛伊南方圖書獎(Pat Conroy Southern Book Prize)、奧克拉荷馬圖書獎(Oklahoma Book Award)、卡洛獎(Carol Award)、天主教文學奬(Christy Award)與《浪漫時潮》書評票選獎(RT Reviewer’s Choice Award)。溫格特目前居住在阿肯色州西南部的沃希托山脈。
作者網站:lisawingate.com
臉書:Facebook.com/LisaWingateAuthorPage
譯者簡介:
沈曉鈺
美國西蒙斯大學兒童文學碩士。小說譯作有《北歐眾神》、《五星豪門》、《波西傑克森:終極天神》、「埃及守護神」系列、《女王,請聽我說》。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得獎、書店選書資訊
2017 年 Goodreads 網站讀者票選年度冠軍
2018 年美國南方圖書獎年度最佳小說
2018 年 Ezvid Wiki 網站年度十大歷史小說
2018 年 10 月誠品選書、城邦讀書花園選書
名人推薦:
吳曉樂、陳又津、番紅花、楊富閔──同聲推薦
★ 麗莎.溫格特選取了一章幾乎沒人想起的美國歷史,編織出一個具有延續力的故事。喬琪亞.譚恩與她成立的孟菲斯田納西兒童之家協會確實存在,拆散了無數孩子的情感連結,偷走他們的過去、改變他們的未來,讓人不寒而慄。然而,這本震撼人心小說的真正精湛之處,是溫格特帶我們深入十二歲的河上吉普賽女孩瑞兒.佛斯的心和想法。瑞兒全然單一的個人聲音,在你翻至最後一頁,將依然迴盪在耳邊。溫格特追隨她而去的勇氣也是⋯⋯鮮明動人。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 寶拉.麥克蓮(Paula McLain)
★ 這是個勁道十足的故事,關於手足、隱藏的祕密與分享的祕密。我非常喜愛這本書,到現在依然沉浸在愉悅的閱讀體驗裡,為真實犯罪的來龍去脈而震驚,為這些似乎擁有不朽靈魂的角色的旅程而讚嘆。 ——《紐約時報》暢銷書《悲喜邊緣的旅館》作者 傑米.福特
★ 難忘的閱讀經驗⋯⋯這本扣人心弦的小說很可能靜靜地令你心碎──不過,因為掌控大局的可是麗莎.溫格特,在你讀完這本書時,你的心不會破碎一地而沒被補綴。她是個說故事高手,一定能直抵核心,讓我們抱持希望、堅定地走下去。 ——《迷人生活的祕密》(Secrets of a Charmed Life)作者 蘇珊.麥斯納(Susan Meissner)
★ 麗莎.溫格特述說一個家庭因田納西兒童之家協會的惡行而分崩離析。這個令人心跳加速的故事聽起來如此逼真,使我無法成眠,直到我知道這家人後來的命運。偷竊最無助脆弱的孩子、將他們賣給出價最高的投標人,得到視若無睹的高階官員許可,這個殘酷的陰謀仍舊縈繞在我心頭,難以忘懷。 ——《喚我回家》(Calling Me Home)作者 茱莉.奇普勒(Julie Kibler)
★ 年度最佳小說之一。……在這部近乎完美的作品裡,你很難從中抽離。 ──《赫芬頓郵報》
★ 關於失去與尋回一個家庭的故事……手足之情、晦暗的祕密,交織出這部引人入勝的小說。 ──《時人》雜誌
得獎紀錄:▍得獎、書店選書資訊
2017 年 Goodreads 網站讀者票選年度冠軍
2018 年美國南方圖書獎年度最佳小說
2018 年 Ezvid Wiki 網站年度十大歷史小說
2018 年 10 月誠品選書、城邦讀書花園選書
名人推薦:吳曉樂、陳又津、番紅花、楊富閔──同聲推薦
★ 麗莎.溫格特選取了一章幾乎沒人想起的美國歷史,編織出一個具有延續力的故事。喬琪亞.譚恩與她成立的孟菲斯田納西兒童之家協會確實存在,拆散了無數孩子的情感連結,偷走他們的過去、改變他們的未來,讓人不寒而慄。然而,這本震撼人心小說的真正精湛之處,是溫格特帶...
章節試閱
序曲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
我的故事得從一個悶熱的八月夜晚、永遠不想再看一眼的地方說起。那個房間只活在我的想像裡──大多數時候,它很大,牆壁白淨,床單漿得硬挺,所有最高級的東西在這私人套房裡應有盡有。外頭空氣悶窒,知了棲息在高高樹上,窗框下方就是牠們翠綠的藏身處。風扇在閣樓天花板上嘎吱吹著,紗窗朝屋裡搖晃,使勁地將凝滯不動的悶溼空氣往屋裡送。
飄來了松樹的味道。女人尖叫出聲,護士很快將她壓制在床。她汗流涔涔,急急往下淌至臉龐、手臂和小腿上。如果知道自己成了這副模樣,她肯定會嚇壞。
她很漂亮,有副溫和脆弱的靈魂,不是故意造成此時此刻災難性破壞的那類人。活了這麼多年,我學到大多數人只是盡其所能地活下去,無意傷害他人,若是造成了傷害,那不過是依附著活存而生的產物罷了。
傷害就這麼發生了,這不是她的錯,卻伴隨著最後一道殘忍用力的使勁而來。結果絕非她所望,產下了一團靜悄悄的血肉──一個長著滿頭細髮、跟洋娃娃一樣漂亮的小女嬰,卻全身發青,一動也不動。
女人對自己孩子的命運一無所悉,就算知道,藥效也會讓這段記憶到了天明就變得一片模糊,什麼都不記得。止痛的嗎啡與鎮靜劑讓她平靜了下來,不再亂踢亂動,她在午夜時分沉沉睡去。
開藥是為了讓她放鬆,而且的確有效。
醫師進行縫合,護士清理剩餘,兩人語帶同情地談著。
「發生這樣的事真令人難過。怎麼會這樣,這生命一來到人世就沒了氣。」
「有時你不禁會想……為什麼……一個這麼受到期待的小生命……」
放下一張面罩。小小的眼睛被遮蓋起來。永遠沒法睜開。
女人的耳朵聽見聲音,無法理解聽到了什麼。話語一耳進一耳出。彷彿試圖抓住浪頭,海水卻從緊握的拳頭流失,最後只能隨著海水載浮載沉。
有個男人在附近等待,或許等在門外的走廊上。他一向高貴又有威嚴,不習慣如此無助──他原本今天要當外公。
滿懷期待化為揪心之痛。
「先生,我很遺憾,」醫師悄悄從房間走出,說道:「請放心,我們已盡了一切人道的努力,減輕令千金分娩時的不適以及搶救嬰兒。我了解這很艱難,但您聯絡上人在海外的孩子父親時,懇請轉達我們的致意。先前失望了那麼多次,我知道,您們全家一定懷抱很大的期望。」
「她還能再生育嗎?」
「建議不要。」
「這對她會是個嚴重打擊。她的母親一旦知道,也會深受打擊。你知道的,克莉絲汀是我們的獨生女……就盼小腳丫啪噠啪噠地走……新的一代延續下去……」
「先生,我明白。」
「假如她想要生育的話,會有什麼風險……」
「會賠上她的性命。而且,令千金很可能無法再次承受整個孕期。如果她想嘗試,後果可能……」
「我了解了。」
醫師安慰地拍了拍這個心碎的男人(或許在我的想像是這樣),兩人目光交會。
醫師回頭望了一眼,確保沒有任何護士聽得見自己說話。「先生,我能向您提個建議嗎?」他輕聲正色道:「我知道有個在曼非斯的女人……」
1
艾芙芮.史塔弗
現在/南卡羅來納州,艾肯市
當禮車在發燙的柏油路上停下,我深吸一口氣,快速挪動到座椅前沿,整了整身上的短外套。路邊停了不只一輛新聞轉播車,為今早這場看似無害的行程增添了幾分重要性。
但是這一天,沒有任何一刻純屬意外。待在南卡羅來納州這兩個月以來,我每天都在確認所有的細微差異能夠到位──為了僅只於此的「暗示」,沙盤推演著一切。
不會做出確切聲明。
反正還不到時候。
不會拖太久的,如果照我的方式去做。
我真希望忘了自己回家鄉的原因(儘管父親沒在讀他的筆記,似乎也沒在查看效率驚人的新聞祕書萊絲麗為他製作的簡報,已是那麼明顯且不容否認的提醒)──實在很難不注意到敵人正默默坐在車裡,與我們同行。敵人此時就在後座,藏匿在身穿灰色手工西裝的父親那顯得鬆垮的寬闊肩膀底下。
爸爸凝視窗外,頭倚向一側。稍早他吩咐了其他助理和萊絲麗去搭另一輛車。
「您還好嗎?」我伸手將自己的一根金色長髮從對面的座椅上掃開,這樣待會下車時,他的褲子才不會沾到。如果母親人在車上,她會拿出一把迷你小麻刷,但她現在在家中準備我們今天的第二場活動──提前幾個月拍攝家族聖誕合照,以防爸爸的預後惡化。
他稍稍坐挺了些,抬起頭來。端坐的坐姿使他的一叢灰髮直翹出頭來。我想為他撫平,但我沒有。我若動手就會壞了規矩。
如果說母親與我們生活中的各種小事密不可分(像是為了毛球和棉絮而煩惱,以及張羅著在七月份拍攝家族聖誕節合照),那麼父親則是對這一切敬而遠之。他是疏離的──在一幢滿是女人的屋裡,他像座堅毅的男性孤島般存在。我知道他很在乎母親、兩個姊姊和我,只是很少大聲表達自己的情感。我知道自己是最受他疼愛的孩子,同時也是最令他摸不透的一個。在他那個年代,女人去上大學,只為了拿個能覓得好丈夫的新娘學位,而他這個三十歲大的女兒,卻以名列前茅的優秀成績從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還待在檢察官這麼艱辛的崗位上忙得不亦樂乎,他真不知該拿她怎麼辦。
不管基於什麼原因(或許只是因為在我們家,已有人扮演樣樣完美的女兒和甜美貼心的女兒這兩個角色),我一直都是資質聰穎的女兒。我熱愛上學,眾人心照不宣的是,我將會成為家族的接班人,扮演兒子的角色接續父親的事業。不知為何,我總想像當那一刻來臨時,我的年紀會更長些,也已經做好了準備。
現在我看著爸爸,心想:「艾芙芮,你怎能不想要這份事業呢?這是他奮鬥了一輩子的事業。天哪,打從獨立戰爭以來,史塔弗家族已經有多少代人投入了。」一直以來,我們家族總是緊緊抓著公職之路往上爬。爸爸也不例外。他畢業於西點軍校,我出生之前他擔任陸軍航空兵,一路走來始終以尊嚴和決心維護著家族聲名。
「你當然想要這一切,」我告訴自己,「一直都想要。你只是沒想到會那麼快,而且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說穿了就是這樣。」
我暗自十指緊扣,祈禱最好的情況能發生──政治上和醫學上的兩個敵人都在戰場上被擊垮。祈禱讓他從國會夏天會期提早離開的那場手術、外加每三個星期必須穿戴在腿上的攜帶式化療幫浦能治癒他。那麼,我搬回艾肯老家就只會是暫時的事。
癌症再也不會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癌症可以擊敗。其他人也曾擊敗過。如果要說有誰做得到,參議員威爾斯.史塔弗就做得到。
再沒有哪個男人比我父親更強壯、更棒。
「準備好了嗎?」他一邊問,一邊拉整自己的西裝。當他壓平頭上那叢公雞尾巴時,真令人鬆了口氣──要我跨越從女兒變成照顧者的那條界線,我還沒準備好。
「我會跟在你後面。」我會為他做任何事,只希望被迫交換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將會是許多年後的事。看到父親掙扎著替他母親做出了決定,我明白這件事有多麼難。
過去曾那麼機智靈敏、詼諧風趣的茱蒂奶奶,現在卻成了一縷自己原本模樣的遊魂。儘管痛苦萬分,爸爸還是沒法跟任何人談這件事。如果媒體得知我們將奶奶送到安養院,尤其還是個離這裡不到十哩、有著美麗園區的高級所在──以政治語言來說,這會是個雙輸的局面。有鑑於近來一連串意外死亡和虐待案的醜聞越演越烈(其中包括我們這個州境內私人經營的老人安養照護機構),爸爸的政敵會指出,只有有錢人才負擔得起頂級照護,或指控他是個冷血的惡人,根本不在乎老人家,才會將自己的母親安置在安養院;他們會說,只要能讓他的朋友和資助他競選政治獻金的人從中獲利,他很樂意無視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實情是,他為茱蒂奶奶做的決定與政治全然無關。我們跟其他家庭沒什麼兩樣。每條可行之道上頭都鋪滿了罪惡感,一路上淨是痛苦,羞愧讓路面變得坑坑窪窪。她讓我們困窘,也讓我們擔心,讓我們為這折騰人的退化失智終將導致的結果悲痛不已。送她去安養院之前,她曾經從看護和幫傭的眼皮底下跑掉,叫了輛計程車,失蹤一整天,最後被人發現在商場裡遊蕩,而那是她以前最喜歡的一間購物商場。她不記得我們的名字,卻有辦法做到這件事,真是個不解之謎。
今早這個場合,我佩戴了一件她很喜歡的珠寶飾品,昂然步出禮車時,隱隱感覺得到它就在我手腕上。我假意是為了向她致意而選戴這條蜻蜓手鍊,但說真的,這手鍊毋寧更像個靜默的存在,提醒著史塔弗家的女人,再怎麼不情願也得去做該做的事。今天早上的活動地點讓我不舒服。我向來不喜歡安養院。
我告訴自己,這只是一場簡單的見面會,媒體是來報導活動,不會問問題的。我們會握握手、參觀安養院,和院友一塊為一名百歲女士慶生。她丈夫今年九十九歲。真是不容易。
安養院走廊的氣味,活像有人鬆開我姊姊的三胞胎任他們拿芳香噴霧大玩特玩似地。人工茉莉花香充斥空氣中。萊絲麗聞了聞,點點頭示意,然後她自己、攝影師、幾位見習生與助理圍住了我們。這場活動我們沒帶隨扈同行,他們想必正在為今天下午的市政廳論壇做準備。多年來,我父親收到許多來自邊緣團體、民兵,以及自稱狙擊手、生化恐怖分子、綁匪等瘋子的死亡威脅。他很少認真以待,但他的維安人員可不敢掉以輕心。
走到轉角處,迎接我們的是安養院院長和兩組出動了攝影機的新聞團隊。我們參觀,他們拍照錄影。我父親施展無比魅力。他握手、擺好姿勢拍照、花時間與人說話,彎下身子湊近輪椅,並感謝護士每天為困難又吃重的工作付出心力。
我跟在他身後照做。一名頭戴硬挺花呢圓頂禮帽的溫雅老紳士說了些恭維的話。他操持一口悅耳的英國口音,說我有對美麗的藍眼睛,還開玩笑道:「如果在五十年前,我會迷倒你,讓你願意跟我約會。」
「我想你已經迷住我了。」我回答。我們一起哈哈大笑。
有位護士要我小心麥墨利斯先生,說他是銀髮大情聖唐璜。他朝護士眨了眨眼,證明她所言不假。
在走廊走走停停前往百歲生日派對會場的同時,我發現自己確實樂在其中。這裡的院友似乎感到滿意,儘管不像茱蒂奶奶住的安養院那麼豪華,卻也不是最近遭點名捲入了一連串訴訟的那種不人道照護機構。然而,無論法院判賠多少損害補償金,那些官司裡沒有一個原告看得到一毛錢。那些私人連鎖安養院背後的金主以控股公司和空殼公司手法玩弄著權術,很輕易就能藉由宣告破產規避支付賠償。這也正是為何揭開其中某個機構的運作,極可能對我父親的某個政治獻金大戶老友造成重傷害,而以父親的高知名度來看,他也勢將成為憤怒輿情與政治浪頭千夫所指的對象。
憤怒和責難是強而有力的武器。政敵清楚得很。
交誼廳裡已搭好一座小舞臺。我跟其他人一塊站在一旁,那裡有道玻璃門可眺望外頭蔭涼的花園──儘管時值溽暑,園子裡仍盛放著各式各樣繽紛燦爛的花朵。
有個女人獨自站在一條覆有遮棚的花園小徑上。她面朝另一個方向,凝視著遠方,似乎全然不知正在進行派對。雙手擱在一根拐杖上。儘管天候如此暖和,她仍在一身素樸的奶白色棉質洋裝外頭套了件白色毛衣。滿頭白髮編成髮辮盤了上去,在蒼白無華的洋裝襯托下,儼如一縷早被人遺忘的過往殘魂。一陣微風吹來,吹得紫藤花棚上的花朵直搖,她卻絲毫不為所動,給人一種她其實並不真的在那兒的錯覺。
我將注意力轉移到安養院院長身上。她歡迎在場的每個人,褒揚相聚此刻的原因──畢竟,活了百年的成就可不是天天見得到。尤其和深愛的另一半共結連理大半輩子且長相廝守至今,更是難能可貴。這樣的活動確實值得參議員到此一訪。
更別說這對夫妻一直都支持我父親,打從他還在南卡羅來納州政府工作時,便開始擁護他。嚴格說來,他們認識他的時間比我還久,而且近乎死忠。當父親的名字被唸出來時,我們的壽星和她丈夫都高高舉起瘦骨嶙峋的手,熱烈地鼓掌。
院長說了個有關這對就坐在會場正中央餐桌的恩愛夫妻故事。露西出生於法國,那是個還見得到馬車在街道奔馳的年代(光要想像就很難)。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她加入了反納粹德國占領的法國抵抗運動,丈夫法蘭克則是戰鬥機駕駛,在一場戰役中被擊落。他倆的故事有如電影情節,浪漫得夠徹底──露西是協助他逃亡的一員,幫他假扮偽裝,將受傷的他偷偷送出境外。戰後,他回去找她。她仍和家人住在同一座農場,躲藏在那房子僅存唯一能住人的地方──地窖。
這對夫妻經歷過的事著實叫人驚嘆,唯有愛情情真意堅、矢志不改,不惜犧牲一切只為了在一起才可能發生。這也是我想要的,卻又不禁要想,對我們現在這一代來說,這種事可能嗎?我們那麼三心二意,又那麼地……忙碌。
低頭瞥了眼自己的訂婚戒指,心想:「我和艾略特沒道理不能幸福。我們那麼了解彼此,而且一直相互扶持……」
我們的俏女郎壽星挽著情人的手臂,慢慢從椅子上起身。兩個彎著腰駝著背的老人一塊往前走,畫面是這麼動人且揪心。我希望自己的父母能活到如此高壽──直到某天……幾年後,等到父親決定享清福時,希望他們能擁有既長且足的退休時光。這個病不可以在五十七歲時就將他帶走,他還太年輕,大家都很需要他,不管是家裡還是這個世界。他還有事要做,在那之後,他和我母親理當平平靜靜地一塊安養天年。
胸臆充盈著一片柔情,可是我隨即推開了這些念頭。「不可以在大庭廣眾下流露情感──」萊絲麗經常如此提醒道,「在政壇,女人沒本錢這麼做,這會被視為軟弱無能的表現。」
這一點我清楚明白。法庭上也差不了多少。就許多方面而言,做女律師的其實一直在受審,我們得按不同的遊戲規則行事。
當老夫婦走近舞臺時,父親向法蘭克送上致意。法蘭克停下腳步,挺直身子,有模有樣地回以軍事敬禮。他倆目光交會,多麼無瑕的一刻;這一刻或許在鏡頭前看起來很完美,卻絕非為了上鏡而做。父親緊抿嘴脣。他在試著不掉淚。
如此近乎真情流露,很不像他的作風。
一股飽漲的情緒又湧了上來,我趕緊嚥下,脣間稍顫。挺直肩膀,移開目光,我將注意力放在窗上,研究起花園的女人。她仍舊站在那兒,凝視著遠方。她是誰?她在尋找什麼?
喧囂非常的《生日快樂》歌穿透玻璃,引得她慢慢轉身看向屋子。儘管受到歌聲的牽引,也知道攝影機可能會拍到我,我看起來卻那麼心不在焉,沒法不讓自己盯著外面的花園小徑看。至少,我想看看那女人的面孔。那張臉會跟夏日天空一樣白嗎?她是因為糊塗了而遊晃,還是故意避開慶祝活動不參加?
萊絲麗猛地從後頭拉了一下我的外套,我立刻回神,像個被抓到在列隊隊伍中交談的學生妹。
「生日快──專心一點。」她附在我耳邊唱道,我點點頭;她隨即離開,去找個比較好的角度用手機拍張快照,再上傳到父親的Instagram。這位參議員會在所有最新的社群媒體現身,即便他根本不知道該怎麼使用。只要負責管理他社群媒體的人深諳此道就行。
儀式持續著。相機的閃光燈閃個不停。當父親致贈裝裱上框的祝賀信時,老夫婦的家人抹了抹歡欣的淚水,錄影記下這一刻。
蛋糕推了出來,上頭插了一百根蠟燭,火光閃閃。
萊絲麗很開心。歡樂與感動充滿全場,像極了一顆不斷漲大的氫氣球──歡樂不嫌多,大夥全都飄飄然。
忽然間,有人觸碰到我的手,攫住我的手腕。我始料未及,把手抽走,力求鎮定以免引起騷動。沒想到這冰冷、乾癟、顫巍巍地一握,竟意外強勁有力。轉過身一看,是花園裡那個女人。她挺起佝僂的背,睜著一雙生了淺白眼翳、卻依舊溫柔澄澈的淡藍眼眸注視著我(讓人想起德雷登丘家中繡球花的顏色),而她滿布脣紋的嘴脣則發著抖。
還來不及弄清狀況,有個護士過來握住了她的手,準備將她帶離。「梅伊,」護士一邊說,一邊對我露出抱歉的神情,「走吧。你不該打擾我們的客人。」
老婦人不想鬆開我的手腕,反倒緊緊抓住。她看起來很絕望,好像需要些什麼,可是我一點頭緒也沒有。
她伸長了脖子,揚起頭,直盯著我的臉瞧。
她喃喃地說著:「芬恩?」
2
梅伊.克蘭朵
現在/南卡羅來納州,艾肯市
有時候,我這副心思的門閂好像生鏽磨損了,門老按它自己意思開開關關的。往裡頭偷看一眼,空蕩蕩的。我可不敢細瞧那黑漆漆的地方。
誰知道會發現什麼。
圍欄什麼時候打開,又為什麼打開,這事沒個準。
一波又一波的觸動。電視節目上的心理醫師給了這個說法。觸動一波又一波……好比彈藥被觸發引燃,子彈咚咚咚地從來福槍槍管擊發出去。這是個很恰當的比喻。
她的臉觸動了某件事。
打開一扇通往遙遠過去的門。起初,我笨手笨腳、毫無心理準備地走進去,好奇這個上鎖的房間裡究竟藏了些什麼。可是當我一開口喊她「芬恩」,就知道她並不是我所想的那個芬恩,甚至回到了更久遠的過去──我看到的是昆妮。
昆妮是我們堅毅的媽媽,我們所有人都遺傳了她美麗的金色捲髮,可憐的卡蜜拉除外。
我的心輕飄飄穿過樹頂,沿谷底前行,風塵僕僕地去到密西西比河一處低矮岸邊,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昆妮。曼非斯夏夜暖和的空氣在我身邊流動,可那卻是個叫人上當的夏夜。
沒有溫潤柔軟可言。一點同理心也沒有。
打從這個夜晚,一切都變了樣。
我十二歲,瘦巴巴的,連骨頭都突了出來,活像根前廊柱子。這會,我正坐在我家船屋的欄杆底下,搖晃著雙腿,就著提燈發出的昏黃閃光,留意短吻鱷的眼睛。短吻鱷怎能遠遠地走偏,來到這密西西比河的上游處?但最近一直傳言這附近有短吻鱷。於是找尋短吻鱷變成一種遊戲,船屋的孩子們以找到鱷魚為樂。
尤其是現在,我們比平常更需要分散注意力。
我身旁的芬恩爬上欄杆,往木材堆裡找尋螢火蟲。她快四歲了,正學著數螢火蟲。她身體往前傾,伸出一截短胖手指,根本沒留意鱷魚。「瑞兒,我看到一隻了!我看見了!」她大喊。
我抓住她的洋裝,拉她回來。「你快掉下去了,這次我可不會跳進水裡救你。」
說實話,如果她真掉下去,可能也沒事,倒是會受點教訓。我們的船停靠在泥島對面一個很棒的小小回水處,「阿卡迪亞號」船尾的水深只到我的屁股,芬恩可能也摸得到自己的腳趾。不過,我們五個人跟蝌蚪一樣,全都會游泳,就算連一句完整句子都還不會說的小蓋比翁也會。當你出生在河上,游泳就跟呼吸一樣,再自然不過。你很清楚河流的聲響、河流的脾性,以及河流裡都住了些什麼樣的傢伙。對我們這種河上賤民來說,水就是家──一個安全的棲地。
可是眼下的空氣瀰漫著一種……不對勁。我兩條手臂起了一陣雞皮疙瘩,刺痛了臉頰。我的預感向來很準,這種事我絕不會告訴任何人,但它一直都在。在悶窒無風的夏夜裡,我竟渾身感到一陣涼意。頭頂上的天空很厚重,雲層像顆爛熟得快要裂開的西瓜。暴風雨快來了,然而我感覺到的不只是這樣。
「好了,佛斯太太,不能再用力了,你得停下來。這孩子出來的方向搞錯邊,就算來到這世上也活不了多久,就連你都會挺不住。就是這樣。你現在安靜下來。放輕鬆。」顧不得口音濃重的產婆一片苦心,船屋裡的昆妮開始急促低吟起來。
昆妮發出痛苦呻吟,活像陷在河口淤泥急於抽出的靴子。過去她生下我們五個不過就在吹呼一口氣間,這次卻生了那麼久。我揩去手臂上的冷汗,總覺得有什麼東西藏在樹林裡。某種邪惡的東西正盯著我們看。它為什麼在那裡?它是為了昆妮而來嗎?
我想從梯板跑下船去,沿著河岸一邊跑一邊喊:「馬上離開!快點走!你不能帶走我媽媽!」
我真的會這麼做,才不怕那裡是不是有鱷魚。不過我沒去,只是呆若木雞地靜靜坐著,仔細聽產婆都說了些什麼。她的嗓門有夠大,就像待在船屋裡聽一樣。
「噢,老天,我的老天爺呀!她肚子裡還有一個。她還有一個!」
爸爸在喃喃自語,我聽不見他說什麼。只聽得到他遲疑地腳踩靴子走到地板那一頭,又走回這一頭。
產婆說:「佛斯先生,這我沒辦法了。你如果不快點把這女人送到大夫那裡,不只兩個嬰兒見不到這世界,就連他們的媽媽今天也會死。」
布萊尼沒有馬上回話,只是雙拳重重捶打牆壁,震得昆妮裱了框的那些畫咯咯作響。某個東西鬆脫滑落,發出金屬敲擊木頭的聲音,從它掉落的位置和聲響聽來,我知道那是什麼。我心想,是上方站了個表情悲傷男子的那只錫製十字架;我想跑進屋裡,拿起十字架,跪在床邊,低聲唸著那些神祕的波蘭字眼,就像布萊尼人不在,雨下得淹過船頂、河浪反覆敲打船身的那些暴風雨夜晚,昆妮會做的那樣。
不過,跟布萊尼私奔住到河上之前,我並不懂昆妮在家學會的這種音調偏高的怪異語言,只聽得出幾個波蘭字,如果把它們串起來唸,也只是滿嘴胡言亂語罷了。就算是這樣,如果現在能拿到昆妮的十字架,我還是會對上頭的錫人唸出這些波蘭字眼;對了,每次暴風雨來的時候,昆妮都會親吻那個錫人。
為了幫助昆妮生產順利,好能再次看見她的微笑,要我做任何事都願意。
布萊尼腳上的靴子仍然在門的那一頭刮著地板,我聽見十字架哐噹掉到地上的聲音。布萊尼從灰撲撲的窗戶往外看;那扇窗來自他的農舍。早在我出生之前,他為了蓋這艘船屋,拆了自家農舍──當時,布萊尼的媽媽快死了,那年農作物又再次歉收,而房子終究要歸銀行所有。布萊尼盤算著可以住到河上去。這件事也被他說對了。經濟大恐慌那個時期,他跟昆妮住在水上的日子還算過得去。他每次講古的時候都會說:「就算是經濟大恐慌也餓不著河流,河流自有魔法。她總是照顧自己人,一向如此。」
但是今晚,魔法不靈了。
「先生!你有沒有聽見我在跟你說話?」產婆的態度變得很凶,「我的手不要沾染她們的血。你得把你的女人送到醫院去。現在就送。」
玻璃窗後的布萊尼臉繃得很緊,兩隻眼睛緊緊閉上。他握緊拳頭捶打自己的前額,最後又打了牆壁。「這暴風雨……」
「佛斯先生,不管是不是有惡魔在旁邊跳舞,我對這女人無能為力,一點辦法也沒有。我的雙手才不要沾血。」
「她生其他孩子時……從來沒有……出過問題。她……」
昆妮尖叫,叫得好大聲,聲音像野貓嚎叫那樣在深夜裡迴盪。
「聽著,你沒跟我說她從來沒有同時生兩個寶寶。」
我勉強移動腳步,帶開芬恩,讓她跟兩歲的蓋比翁、六歲的小雀一塊待在船屋前廊。卡蜜拉坐在瞧得見窗戶的地方,朝我這兒看來。我關上梯板另一頭的大門,準備把他們留在門廊上,還交代卡蜜拉別讓小傢伙爬過來。卡蜜拉以皺眉代替回答。十歲大的她遺傳了布萊尼的倔騾子脾氣,還有他深色的頭髮和眼珠。她不喜歡被人使喚,固執得要命。如果小傢伙們開始吵鬧作怪可就麻煩了,而現在處境已經夠糟的了。
「一切都會沒事的。」我一邊保證,一邊像安撫小狗那樣拍拍他們柔軟的金髮。「昆妮現在很不舒服,不可以去吵她。你們全都乖乖待著。老獸人今晚跑出來活動了,幾分鐘前我聽見他的呼吸聲。現在出去不安全。」十二歲的我可不相信什麼獸人、惡靈和河上強盜「瘋船長傑克」──反正不是很怕了。我懷疑卡蜜拉有沒有相信過布萊尼說的那些荒唐故事。
她伸手去開門閂。
「不可以,」我嘶了她一聲,「我來。」
布萊尼交代我們不可以進去,他是認真的,因為平常不會這麼說。可是他現在的口氣聽起來像是不知道該怎麼辦,再加上我擔心昆妮,還有我的男寶寶弟弟或女寶寶妹妹。我們大家一直在期待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可是寶寶不該現在出來,太早了,甚至比蓋比翁更早──蓋比翁出生時好小,在布萊尼還來不及把船靠岸、找女人來幫忙接生前,他就已經滑進這個世界了。
這個新寶寶好像很難纏。也許寶寶出生後會長得跟卡蜜拉一個樣,而且一樣固執。
是寶寶們才對,我提醒自己。我現在知道了,就跟生小狗狗一樣,昆妮的寶寶不只一個,這個情況不正常。在昆妮用金心牌漂亮麵粉袋縫製的睡簾裡頭,有三條性命生死未定地躺在那兒。三副身體試著拉扯、分開彼此,卻怎麼也做不到。
我開了門,在決定要不要進去之前,產婆已經高高站在我面前。她抓住我的手臂,抓得好緊。我低下頭,看見黑皮膚環扣著蒼白皮膚。如果她想,她絕對可以把我整個人折成兩半。她怎麼會救不了我的男寶寶弟弟或女寶寶妹妹呢?她怎麼會沒辦法把寶寶從媽媽的身體裡拉出來,帶他們到這個世上呢?
昆妮緊抓睡簾,又尖叫又拉扯的,連身子都用力過頭地拱離了床面。固定睡簾的鉤子有一半都被扯掉。我看見了媽媽的臉,玉米鬚一樣的纖細金色長髮黏在她臉上,一雙藍眼睛瞪得好大(我們所有人都遺傳了她那雙美麗溫柔的藍眼睛,除了卡蜜拉),臉頰皮膚繃得好緊,布滿像蜻蜓翅膀那樣細細的血管。
「爸爸?」在昆妮的尖叫聲之後,我輕輕喊著,卻似乎讓房間氣氛變得更糟。只在出了嚴重事情的時候,我才會喊布萊尼「爸爸」或叫昆妮「媽媽」。他們生我的時候年紀都還很輕,我想他們甚至從沒想過要教我「媽媽」和「爸爸」這兩個詞。我們一直都像同年齡的朋友那樣相處。可是我偶爾會需要他們當爸爸或媽媽──上一回是在兩個星期前,我們看到一個男的吊在樹上死掉了,全身都發脹。
昆妮要是死了,也會是那副模樣嗎?她先死,接著是寶寶們?還是寶寶們先死,她隨後跟上?
我的胃絞得好緊,甚至感覺不到抓住自己手臂的那隻大手。也許我該感謝有那隻手撐住我,讓我像船錨一樣能定定站著。我不敢靠近昆妮。
「你跟他說!」產婆當我是布娃娃那樣用力搖晃,好痛。她一口雪白的牙齒,在提燈的光線下,顯得那麼咬牙切齒。
不遠處打雷了,一陣強風甩上右舷牆,產婆一個重心不穩帶著我往前傾。昆妮的眼睛對到我的眼睛。她像個小孩一樣看著我,向我求救,覺得我可以幫她。
我艱難地吞了口口水,試著喊出聲來:「爸──爸爸?」之後又結結巴巴喊了一次,他仍只是瞪著眼看向前方,活像隻感覺到附近有危險而顯得全身僵硬的兔子。
我從窗戶看見卡蜜拉的臉壓在窗玻璃上,小傢伙們爬上長椅往裡頭看。小雀的胖臉落下了斗大淚珠,她討厭看到任何活物受到傷害。如果能僥倖不受處罰,她會把所有餌魚扔回河裡。只要布萊尼開槍射殺了負鼠、鴨子、松鼠或鹿,她就會表現出一副眼睜睜看著最要好朋友在自己面前被殺死的樣子。
她看著我,要我救昆妮。他們全都在看我。
遠處在閃電。閃電讓黃色的煤油燈閃遲了一下,然後變暗。我試著計算幾秒鐘後會聽見雷聲,這樣就能知道暴風雨離我們還有多遠,可是我好慌亂,算不出來。
如果布萊尼不快點送昆妮去看醫師,一切就太遲了──暴風雨來的時候,我們總在野外的岸邊紮營,而曼非斯就在那又寬又沉的密西西比河另一邊。
我喉嚨發緊,說不出話來,只好直起脖子說:「布萊尼,你得帶她過河。」
他慢慢轉向我,神情仍然呆滯,看起來卻像是一直在等待這一刻──他在等待產婆以外的人告訴他該怎麼做。
「布萊尼,你一定要在暴風雨來臨前用小船帶她走。」因為我知道移動船屋得花很久時間。如果布萊尼頭腦夠清楚,也會想到這一點。
「你得告訴他!」產婆繼續鼓動著我,接下來朝布萊尼走去,把我推到她自己面前,對布萊尼說:「你如果不把那女人弄下船,這孩子的媽會活不過今晚。」
序曲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
我的故事得從一個悶熱的八月夜晚、永遠不想再看一眼的地方說起。那個房間只活在我的想像裡──大多數時候,它很大,牆壁白淨,床單漿得硬挺,所有最高級的東西在這私人套房裡應有盡有。外頭空氣悶窒,知了棲息在高高樹上,窗框下方就是牠們翠綠的藏身處。風扇在閣樓天花板上嘎吱吹著,紗窗朝屋裡搖晃,使勁地將凝滯不動的悶溼空氣往屋裡送。
飄來了松樹的味道。女人尖叫出聲,護士很快將她壓制在床。她汗流涔涔,急急往下淌至臉龐、手臂和小腿上。如果知道自己成了這副模樣,她肯定會...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