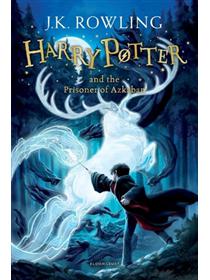她是專替妖精繪製肖像的畫師,用好手藝交換珍貴的幻咒,
卻也在無意間替自己引來禁忌的愛戀與致命的危險。
今.年.盛.夏.必.讀.的.浪.漫.奇.幻.小.品★《紐約時報》暢銷書
★ 2017美國獨立書商協會Indie Next List十大選書
★ 2017美國獨立書商協會Indies Introduce秋季選書
★ 父母選書銀牌
「一隻烏鴉代表不確定的威脅,六隻代表危機一定會到來,十二隻代表躲不過就會喪命。」
他留下這道幻咒保護我,然而在我眼前的卻是漫天飛舞的烏鴉,那代表的又是怎麼樣的危險?金黃麥田中的幻息鎮終年盛夏,居民從來不知季節更替為何物,麥田彼端,是妖精居住的森林,那裡是凡人絕不能踏入的禁忌之地,但妖精卻時常拜訪小鎮,為的是用幻咒來交換各種工藝品:精緻瓷器、手工禮服、故事書、畫作與雕刻。雖然妖精擁有魔力且永生不死,卻不如他們蔑視為蜉蝣的人類那樣具有創造力,因此這些作品對他們來說是炙手可熱的收藏物,不僅能凸顯身分地位,還能妝點他們單調而漫長的妖生。
伊索貝年紀輕輕,卻已是幻息鎮數百年來最優秀的肖像畫家。時常有妖精來委託她繪製肖像,她不僅擅長繪畫,也深諳如何與生性狡詐的妖精打交道,時刻戒慎恐懼,免得像鎮上的甜點師傅,為了一雙更湛藍的眼珠,卻不小心賠上三十年的生命。她想要的很簡單:讓一手拉拔她長大的阿姨,以及兩個雙胞胎妹妹過上衣食無缺、安全無虞的好生活。
伊索貝的好手藝,甚至連三百年都沒涉足人界的妖精王子風鴉也慕名而來,他傲慢自大,而且和大部分妖精一樣愛慕虛榮,不過這似乎只是他的其中一面。在為他作畫的那幾個陽光燦爛的午後,伊索貝漸漸對他感到好奇,甚至有些好感。畫像完成,風鴉依約給她一道可以在她或家人有危險時示警的幻咒,就此離開。伊索貝原以為再也見不到他,豈知幾日後,風鴉再次出現在她家門口,憤怒質問:「妳做了什麼好事?」
因為一幅肖像,伊索貝就此捲入妖境的權力鬥爭中。人類既嚮往又害怕的妖精森林中,藏著什麼樣的誘惑與邪惡?這一切,又跟幻息鎮困在永恆夏日中的祕密有何關聯?她又該怎麼利用身為肖像師的力量,保護所愛之人,甚至勝過妖精的幻咒與詭計?
▍各界好評羅傑森將禁忌之戀轉化為清新的冒險故事,重新詮釋妖精傳說與鄉野故事,並在故事中安排各種幽默橋段,都將令讀者印象深刻。如果你是荷莉・布萊克、梅姬.史蒂芙薇特或萊妮・泰勒的書迷,那麼一定也會愛死這本書。
──《出版人週刊》星級書評
甫出版便躍升新的奇幻經典之作。
──邦諾書店青少年部落格
羅傑森的第一本小說是本層次豐富的浪漫之作,女主角勇敢堅強。羅傑森對於文字的掌握以及世界觀的堆砌功力,將故事張力及誘人程度提升至最高點。如果你是荷莉・布萊克或尼爾・蓋曼的書迷,那這本書也會是你的首選。
──《書單雜誌》
作者簡介:
瑪格莉特.羅傑森Margaret Rogerson
當瑪格莉特不是在寫作時,就是在作畫、閱讀、玩遊戲或者是窩在廚房裡做布丁,也可能趴在樹林裡的地上找蟾蜍和香菇。目前住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北部,希望有天能夠搬到夜晚會發出奇怪聲響的森林旁邊。熱愛一切看起來很奇怪的東西。《烏鴉幻咒》是作者的第一本小說,為單本完結獨立作。
相關著作:《烏鴉幻咒(限量作者親簽版)》
譯者簡介:
林欣璇
台大外文所畢。曾任職出版社,現旅居比利時,專職筆譯。目前最喜歡的譯作是《盤根之森》。
章節試閱
1
我的客廳聞起來滿是亞麻仁油和穗花薰衣草的味道,畫布上有一抹鉛錫黃,賈弗萊絲綢外套的顏色在我筆下已經快臻至完美了。
畫賈弗萊困難的地方在於說服他每次讓我作畫時都穿同樣的衣服。要等每層油彩乾燥必須花上好幾天的時間,我無法依照他的喜好隨意變換他肖像的整套服裝,這點他老是不懂。雖然妖精愛慕虛榮,就如同「池塘通常是濕的」或者「熊很毛茸茸」一樣顯而易見,但就算是以妖精的標準來說,賈弗萊愛慕虛榮的程度仍然令人吃驚。說到底,這個特質讓我很容易就放低戒心,忘了他可是一個可以邊喝茶邊把我殺了的狠角色。
「我可能會在手腕上加點銀色刺繡。」他說,「妳覺得如何?妳應該可以加上去對吧?」
「當然沒問題。」
「然後如果我選另一條領巾的話……」
我在內心大翻白眼。臉上卻堆出彬彬有禮的假笑,過去兩個半小時以來都維持同樣的表情,裝得臉都痛了。無禮的代價我付不起。「我可以改您的領巾,只要大小差不多就好了,不過還得麻煩您再來一次才能完成。」
「妳真的太棒了。比我上一個肖像畫師好多了——前陣子那個傢伙。他叫什麼來著?賽巴斯欽.曼尼瓦茲?噢,我不喜歡他,他聞起來總有個怪味。」
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恍然大悟賈弗萊指的是工藝大賽拉斯.曼里瓦特,他早已死了三百年有餘了,「謝謝您。」我說,「真是貼心的讚美。」
「看到這門工藝隨著時間改變真是迷人。」他把我的話當耳邊風,從長沙發旁擺的托盤上挑了一塊蛋糕。他沒馬上吃下去,而是坐在那邊盯著它看,活像名昆蟲學家找到了一隻頭長在屁股上的甲蟲。「有時候我會以為已經見識過人類最傑出的才華了,但忽然又出現了那麼一只釉瓷,或是這種裡面有檸檬蛋黃醬的美味小蛋糕。」
我現在已經習慣了妖精的阿諛奉承,依然目不轉睛盯著他左邊的袖子,繼續在畫布上點按出絲綢的黃色光澤。但是我記得自己從前曾經因為妖精的儀態而感到很不自在。他們移動的方式和人類不一樣:動作流暢精準,姿態僵硬得古怪,永遠都那麼端莊,哪怕只是一根手指也不會亂擺。他們可以連著好幾個小時動也不動,眼也不眨一下,更可以用快到讓人害怕的速度撲上來,你連詫異的驚呼一聲也來不及。
我往後坐,手裡拿著畫筆,掃視整幅肖像。就快完成了,畫布上有如石化般的賈弗萊和他本人一模一樣,容貌從未改變過。妖精為何對收藏人類工藝品這麼執著,我始終毫無頭緒。他們從未反思過自己永駐的青春,因為青春是他們唯一了解的概念,而等到妖精死的時候,他們的肖像早就腐朽殆盡了,如果他們真有死去的那一天。
賈弗萊看起來年約三十五,和他所有的族人一樣身材高䠷修長,而且俊美無比。他的雙眼如水晶般清澈,和雨水洗去暑熱的天空一樣湛藍,膚色宛如蒼白無瑕的陶瓷,頭髮是陽光照亮晨露時金銀交織的燦爛色彩。我知道聽起來很荒謬,但是妖精需要這些比擬,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形容他們。曾經,幻息鎮上有名詩人絕望而死,因為他發現自己無法用明喻來捕捉妖精的美貌。我是覺得他比較可能死於砒霜中毒,但反正故事是這麼說的。
當然,必須記得這一切都是表象,全都是幻術,只是他們的皮相。
妖精是技巧高超的偽裝者,卻無法明目張膽地撒謊。他們的幻術永遠都有破綻。賈弗萊的破綻是他的手指:跟人類比起來太長了,而且關節有時候看起來很奇怪。如果有人盯著他的手指看得太久,他就會將雙手交扣併攏,或是匆匆藏在餐巾下,彷彿那是一對見不得人的蜘蛛。他是我遇過的妖精中最容易親近的,繁文縟節比起他的其他族人少很多,不過盯著他們看仍舊不是個好主意——除非像我一樣,有個充分正當的理由。
最後,賈弗萊終於開口吃了蛋糕,吞下去前我沒看到他咀嚼。
「我們今天差不多了。」我告訴他,拿一條破布擦筆刷,放進畫架旁的一罐亞麻仁油中,「您想看看嗎?」
「這還用得著問嗎?伊索貝,妳明明知道我絕對不會錯過欣賞妳匠藝的機會。」
接著賈弗萊便神不知鬼不覺忽然站在我肩膀後方,他保持一段禮貌的距離,不過那股非人的氣味仍然包圍住我:春天的葉子散發青翠的蕨類芬芳,還有野花的香甜。除此之外,更隱隱有一絲原始狂野的氣味——屬於某個已經在森林裡遊蕩千年的東西,擁有蜘蛛腳般的修長手指,可以輕易捏碎人類的喉嚨,而它的主人臉上自始自終都掛著溫暖友善的微笑。
我的心臟漏跳了一拍。我在這間屋子裡很安全,我提醒自己。
「我想我還是最喜歡這條領巾,」他說,「精巧的好手藝,一如往常。話說,再提醒我一次,我該怎麼酬謝妳?」
我偷瞧了一眼他優雅的表情,一綹頭髮從他後頸的藍色緞帶中溜了出來,看似不經意,其實不然,我好奇他為什麼刻意這樣打扮,「我們之前談好了,要在我們家的母雞上施個幻咒,」我提醒他,「牠們這輩子,每隻每個星期都要能下六顆品質良好的蛋,而且不能因為任何原因猝逝。」
「好實際喔。」他嘆口氣惋惜這個悲劇,「妳是這個世代最受讚譽的工匠,想想我能給妳的那些東西!我可以讓妳的雙眼落下珍珠而不是淚滴,還可以給妳征服天下男人心的笑容,又或者一件令人過目不忘的裙子。妳偏偏卻跟我要雞蛋。」
「我還滿喜歡雞蛋的。」我堅定地回答,非常清楚他剛剛提到的那些幻咒都會變質變調,最後甚至致人於死。而且,我要男人的心有什麼用?又不能拿來做蛋餅。
「噢,好吧,如果妳堅持的話。明天早上魔咒就會生效了。好了,我恐怕得走了,我還得去請人幫我做那個銀色刺繡呢。」
隨著椅子嘎吱一響,我站起來朝他行了個屈膝禮,他也優雅地鞠躬來回應。和大多數的妖精一樣,他很會假裝自已是出於自由意志才向我回禮,而不是因為一股無法對抗的強制力,那對他來說有如呼吸一樣非做不可。
「啊哈,」他補了一句,直起背脊,「我差點忘了,我們春季宮廷有閒言閒語說秋王子會來拜訪妳。真是難以想像!真想知道他能不能安分坐好,捱過一整節的作畫時間,還是會一抵達就立刻跳起來參加大狩獵。」
聽到這個消息,我沒辦法管好自己的表情,我目瞪口呆看著賈弗萊,久到他脣上掠過一個困惑的微笑,朝我的方向伸出一隻蒼白的手,或許是想確定我是否就這樣站在原地嚇死了,也不算毫無來由的擔心,對他來說,人類無疑連最輕微的刺激都承受不了,而且會當場身亡。
「秋王國的——」我的嗓音沙啞,只好閉上嘴輕輕喉嚨,「你真的確定嗎?我以為秋王子從來不拜訪幻息鎮。已經好幾百年沒有人……」然後我就啞口無言了。
「我向妳保證,他好得很。而且我昨天才在一個舞會上看見他。又或者那是上個月的事呢?無論如何,他明天一定會來的。記得代我向他問好。」
「我……我榮幸之至。」我結結巴巴說,因為自己反常的失態而暗自感到害怕。我忽然很需要新鮮空氣,於是大步跨過房間去開門。我送賈弗萊出門,站在那兒望著夏天的麥田,目送他的身影沿著小徑慢慢遠去。
一朵雲飄移過太陽,投下的陰影籠罩住我家。幻息鎮從來沒有季節更迭,但是小路邊的樹木掉落了一片葉子,然後又一片,我不禁感覺到有什麼改變正在醞釀,至於是好是壞,還有待觀察。
2
明天!賈弗萊說明天。妖精一向搞不清楚人類的時間觀念,如果他在午夜十二點半忽然現身,要求我穿著睡袍工作怎麼辦?而且我最好的裙子剛好破了,我不可能即時縫補好——只能穿藍色那件了。我一邊說,一邊用亞麻仁油按摩雙手,再拿一條抹布搓得手指都快脫皮了。通常我不會特別花時間清理身上的顏料,但通常我也不會替妖精皇室工作,我不太懂這些枝微末節會不會無意間冒犯到他們。「我的鉛錫黃顏料也快用完了,所以我今晚得進城一趟了——狗屎。狗屎!抱歉,艾瑪。」
我提起裙擺,免得沾到地板上擴散的積水,然後低頭躲過砸落水桶的把手。
「老天,伊索貝。沒事的,三月。」——我的阿姨壓低視線,瞇起眼細看,「不對,是五月。可以幫妳姊姊收拾一下嗎?她今天辛苦了。」
「『狗屎』是什麼意思?」五月狡詐地問,拿著一塊破布往我的腳一撲。
「就是妳不小心打翻一桶水時會說的話。」我說,知道她會發現真相可以給人諸多靈感,「三月呢?」
五月對我露出一個缺牙的笑容,「在櫃子上。」
「三月!從櫃子上給我爬下來!」
「她在那裡玩得很開心,伊索貝。」五月說,水花往我鞋子上噴得到處都是。
「等她摔死了就不開心了。」我回答。
三月高興地咩叫了一聲,然後從櫃子上一躍而下,撞翻了一張椅子,然後蹦蹦跳跳穿過房間。她朝我們直奔過來,我舉起手想擋住她,不過她的目標是五月,不是我,五月站起身,即時與她來個頭撞頭,她們在一陣頭暈目眩中搖搖晃晃了好一會兒,給我一點喘息時間。我嘆了口氣,我和艾瑪一直想改掉她們這個壞習慣。
我的雙胞胎妹妹其實不太算人類。她們出生時是兩隻羊寶寶,但後來有個妖精酒喝太多,出於好玩就對她們下咒,她們變成人類的進展有點緩慢,但我提醒自己至少還算有些進步。去年的這個時候,她們還無法好好待在房子裡,而且變形魔法其實對她們很有利,讓她們幾乎百毒不侵:我見過三月吃了一個破掉的鍋子、有毒的橡木、致命的顛茄,還有好幾隻不幸的火蜥蜴,卻一點異狀也沒有。對我來說,三月從櫃子上跳下來,有危險的其實是廚房用具,而不是她本人。
「伊索貝,過來一下。」我阿姨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她從眼鏡上緣望著我,直到我照做為止,她拉起我的手,擦掉一塊我沒注意到的污漬。
「妳明天會表現得很好。」她堅定地說,「我很確定秋王國的王子和其他妖精沒兩樣,就算不一樣,妳只要記得自己在這間房屋裡很安全就好。」她把我的手裹在她兩掌間捏了捏,「記得這是妳替我們掙來的。」
我也捏捏她的手,也許那一刻,我可以放縱自己當個小女孩。我試著不要用哀嚎的哭腔說話:「我只是不喜歡完全無法預期的事情。」
「或許吧,但是以這件事情來說,妳比幻息鎮的人任何人都準備得更妥當了。我們都知道,妖精也知道。昨天在市集,我還聽見有人說,照妳這個速度,很有可能可以去綠意之井——」
我詫異地猛然抽回手。
「妳當然不想去。我知道妳不會做那種選擇。我想強調的重點是,如果妖精覺得哪個人類不可或缺,那絕對就是妳了,這是很大的肯定。明天一定很順利的。」
我呼出一大口氣,順順裙子,「我想妳說得有道理。」我說,內心卻還是有所懷疑,「如果我想在天黑前趕回來,現在就得出發了,三月、五月,我不在的時候,別把艾瑪阿姨逼瘋了。我回家時要看到這間廚房完好如初。」
離開房間時,我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打翻的椅子。
「至少我們沒在地板上到處狗屎!」五月對我大喊。
我還是個小女孩時,進城一趟堪比一場華麗冒險。現在我只想趕快離開,只要有人經過店家窗外,我胃部那個死結就打得更緊一點。
「只要鉛錫黃就好嗎?」櫃檯後的男孩問,將粉彩條用肉販包肉用的紙張細心綑好。菲尼亞斯只在這裡工作了幾週而已,不過已經把我的習慣掌握得很清楚。
「等一下,再來一條泥綠色,和兩條朱紅。噢!還有全部的炭筆我都要了。謝謝。」我看著他準備我要的東西,一想到今晚有多少工作要做就感到絕望。我必須研磨混合那些顏料、挑選色盤,還要把新畫布拉開鋪好。很有可能明天的時段只能將王子肖像的草稿素描完畢,但是我忍不住要為所有可能作打算。
菲尼亞斯彎下腰不見人影時,我瞥了眼窗外,一層灰塵覆蓋著窗面玻璃,這家店位在兩棟較大的建築中間,看起來有點陰暗簡陋而隱密,沒有讓油燈燒得亮一點,或者讓角落不累積灰塵的簡單符咒。任誰都看得出妖精從不會多看這個地方兩眼,製造工藝品的原料對他們來說一點用都沒有,他們只想要成品。
對街的那間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名女子的裙襬消失在「芙絲與梅斯特」裁縫店門邊,雖然只有驚鴻一瞥,但我看得出那是名妖精。沒有凡人負擔得起這裡販賣的蕾絲長裙,也不會有人去隔壁的甜食店消費,甜食店的招牌推銷著杏仁糖霜花朵,杏仁做的甜點都是用高價而且冒著危險從彼岸世界進口來的。也只有幻咒才付得起這種等級的奢侈品了。
菲尼亞斯直起腰時,他的眼睛以我再熟悉不過的方式閃閃發光。不——不能說是「熟悉」,而是害怕透頂才對。他害羞地撥開前額的一抹頭髮,我的心臟往下沉、往下沉、往下沉,拜託,我心想,別又來了。
「伊索貝小姐,能麻煩妳看看我的工藝品嗎?我知道我比不上妳。」他急匆匆補上一句,想平撫自己的緊張情緒,「可是哈特佛師傅一直在鼓勵我——這是他僱用我的原因——而且我練習了好多年。」他將一幅畫作緊貼在胸前,不自在地把畫作正面隱藏起來,彷彿他害怕展示的不是畫布,而是他的靈魂。那種感覺我感同身受,但這並未讓接下來的差事變輕鬆。
他把作品遞給我,我翻過畫框,在商店昏暗的燈光中看見一幅風景畫。感謝上蒼,幸好不是肖像畫。這麼說聽起來一定自大狂妄的不得了,但是我的工藝獲得非常高的評價,除非我死了、灰飛煙滅了——而且還要等他們真的意識到我已經死了、灰飛煙滅的那天,妖精才會再委託其他人作畫,這可能得多花上好幾十年。我替那些在我成名之後才入行的肖像畫家感到絕望,也許菲尼亞斯還有一線希望。
「畫得很好。」我誠實地告訴他,把畫作還給他,「你對色彩的掌握與調配非常出色,繼續練習吧,不過與此同時,」我猶豫了一下,「你也許可以出售你的工藝品。」
他脹紅了臉,在我面前似乎長高了一吋,但我才放鬆沒多久,就又全身發冷。通常接下來的部分才是最棘手的,我準備好迎接最害怕的那個問題。「小姐,妳可以……可以介紹妳其中一個客戶給我嗎?」
我的目光又飄移回窗戶外,看見芙絲夫人正在芙絲與梅斯特裁縫店的櫥窗裡擺一件新裙子。我小時候,曾將她誤認為妖精的一員,她擁有無瑕肌膚,嗓音比百靈鳥還甜美,那一頭栗棕色的鬈髮光澤閃亮到不自然的地步。她實際年齡一定將近五十歲了,但看起來絕對不超過二十。直到我比較擅長辨別幻術之後,才發現自己錯了。隨著年歲增長,我對妖精幻術的美好想像也漸漸幻滅,那只是謊言罷了。不管措辭如何巧妙,就連最平庸、最實際的咒語都會隨著時間而變質。而措辭不當的那些則會毀了一生。芙絲夫人為了交換那二十二吋的纖腰,無法說出任何以母音開頭的字。去年十月,甜點店的首席烘焙師不小心為了一雙更湛藍的眼珠賠上了三十年的生命,害他太太成為了寡婦。然而財富與美貌的誘惑席捲過幻息鎮,而對綠意之井的想望宛如對天堂的追求,是眾人的終極目標。
菲尼亞斯察覺到我的心不甘情不願,快速的補上一句:「真的不用是什麼大人物喔!那個叫燕尾的傢伙看起來應該是可以打交道的妖精。我在鎮上看過幾次他在街上買工藝品。而且大家都說春王國的妖精在買賣時比較友善。」
事實上,沒有任何妖精是友善的,無論他們屬於哪個王國。全都是裝出來的。想到燕尾接近菲尼亞斯不到十碼,我就嚐到滿口膽汁的苦味。他遠遠不是我遇過最糟糕的妖精,但是他一定會玩弄各種文字遊戲,直到說服那可憐的男孩送出將來第一個出世的孩子,只為了消去臉上的幾顆痘痘。
「菲尼亞斯……你可能注意到我因為我的工藝,與妖精相處的時間比幻息鎮其他人更久。」我隔著櫃檯與他視線交會,他的臉垮下來,無疑是認為我打算拒絕他,但是我不理會他的悶悶不樂,繼續單刀直入,「所以,請相信我,如果你想跟他們做生意,務必小心謹慎。他們說不了謊沒錯,但不代表他們是誠實的。他們逮到機會就會企圖欺騙你。如果他們提出了什麼美好到不可能是真實的條件,那就代表的確不是真的。幻咒的措辭必須毫無破綻,不留任何可以搞鬼的空間。」
他的臉色亮了起來,我不禁害怕所有的口舌都白費了,「意思是妳會推薦我嗎?」
「可能吧,但不會推薦給燕尾。在你摸熟他們的習性前,別跟他交易。」我嚼著嘴脣內側,眼角餘光瞥見有人從芙絲與梅斯特店裡走出來。賈弗萊。可想而知,他一定會去那家店找人刺繡。雖然我站在對街這間昏暗小店裡,一定幾乎看不到,不過他卻直勾勾盯著我,燦爛地微笑,舉起一隻手打招呼。街上的眾人——包括在外頭等他的一群年輕女子——全焦急地拉長了頸項,看看是誰配得上他的注目禮。
「他可以。」我宣布,把金幣放在櫃檯上,背起包包,忽略菲尼亞斯臉上露出前所未有興高采烈的表情。「賈弗萊是我最尊貴的客人,而且他很喜歡當新工匠的貴人,你跟他來往最有機會。」
我這麼說其實有好幾層意思,菲尼亞斯和賈弗萊相處不會有危險。如果我小時候遇見的不是他,就算有艾瑪的幫助,我可能也活不過十七歲生日。儘管如此,我仍然擺脫不了我幫菲尼亞斯的忙是雙面刃的念頭,我幫他實現了心心念念的願望,到頭來卻很有可能毀滅他或令他大失所望。罪惡感糾纏著我走出門,讓我一句道別也沒說。不過我的手按在門把上時,僵在原地。
門口旁的牆壁上掛著一幅畫,因為年代久遠而褪色,畫中的男子站在一個小丘上,周圍環繞著顏色怪異的樹木。他的臉孔模糊,但他手中握的那把劍在灰濛濛的光線裡仍然晶光閃爍。一群蒼白的獵犬湧上小丘,在畫面中凍結在半空。我雙臂上寒毛直豎,我知道這位是誰。他在三百年前的畫作中時常出現,卻忽然再也不造訪幻息鎮,而且沒留下任何解釋。在後來的畫作中,他總是一個遙遠的人影,總是在與大狩獵的魔物搏鬥。
明天,他就會坐在我的客廳裡。
我推開門,對賈弗萊屈膝行禮,低著頭快速通過好奇的圍觀者,他們在我身後大呼小叫。有人喊我的名字,可能想和菲尼亞斯一樣拜託我幫忙。他們正在觀望,等待我接受一個我寧願死也不願花半秒鐘考慮的邀請。我永遠無法向他們任何人解釋清楚:對我來說,綠意之井的獎賞不是天堂。而是煉獄。
回家途中夕陽西下,我的鞋子沿著麥田中的小徑敲擊,和著蚱蜢爭鳴的節奏,光線傾斜的角度讓暑熱更灼炙,我的後頸開始因為流汗而黏答答,只有在微風吹開髮絲時才會稍微涼爽些。城裡歪斜、漆成明亮色彩的屋頂在我身後消失,在起伏的丘陵後方隱沒,而我腳底的那條羊腸小徑像是女人的髮線般劃開丘陵。如果我走得夠快,就能在三十二分鐘內到家。
幻息鎮永遠都是夏天,這裡的季節並不會像彼岸世界那裡有更迭交替,我實在無法理解那樣的概念。當我繼續一成不變的路程時,畫作中那些顏色詭譎的樹木在我腦海中縈繞不去,彷彿是近日剛作的夢。書裡都將秋天描繪成一個可怕的時節,那是個枯萎凋零的世界,飛鳥消失,樹葉變色,好像死去一般從枝椏飄落。我們這樣一定更好、更安全吧。無窮無盡的藍天,永恆金黃的麥穗或許無聊,但我不止一次告訴自己:渴望別的事物很蠢。人還有比無聊更悲慘的下場,在彼岸世界,的確是這樣。
一股腐爛的味道讓我從這些令人沮喪的念頭中回過神來。小徑在這裡蜿蜒過森林邊緣,我警戒地望了陰影一眼。濃密的忍冬和荊棘在樹枝下繁茂地生長,就像一堵障礙物。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時律法尚未明文禁止使用鐵器,農夫會冒著生命危險,將鐵釘敲入最外圍的樹木,用來抵擋不懷好意的妖精。每次看見那些老舊彎曲的鐵釘已生鏽變形到幾乎無法辨認,總讓我感到一陣不安。
我的視線再次掃過叢生灌木,沒看見什麼動靜,我肯定是因為附近某處腐爛的松鼠而疑神疑鬼。我不情願地放心下來,大概第四或第五次檢查包包,確定沒把什麼東西留在店裡沒帶——老習慣了,我從不犯這種錯。抬頭的時候,有事情不太對勁。一隻生物站在下一座丘陵的頂端,就在那棵標記著還有一半路途就到家的橡樹旁邊。
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那是隻雄鹿,體型異常巨大,不過確實有著雄鹿的外型:四條腿、兩根鹿角。然後牠轉頭望向我,我立刻察覺牠根本不是什麼雄鹿。
就這樣,不對勁的感覺開始蔓延。微風瞬間凝住,空氣靜止,熱得令人窒息。鳥兒不唱歌了,蚱蜢也不再嗡嗡叫,就連麥穗都在悶滯的空氣中垂下頭。腐爛的臭味中人欲嘔,我立刻雙手雙膝著地趴在地上,不過已經太遲了。
那隻不是雄鹿的生物緊盯著我。
就算四周炎熱,一陣寒意仍竄過我的皮膚,在我胃部凍成冰晶。我知道那隻不是雄鹿的生物是什麼東西。我也知道自己死定了。沒人能跑得過或者躲得過妖獸。這生物是從墳塚裡冒出的,妖精魔法與古老人類遺骸的詭譎組合。這種東西有些是其主人的奴僕與守衛,也有些是從土裡不請自來。一隻這種怪物在我小時候殺了我的父母,他們死狀淒慘,艾瑪不讓我看他們的屍體,而我就要用同樣的方式死去。我的大腦一定無法好好理解這個念頭,因為我下一個想到的竟然是不該亂花錢買顏料的,因為再也用不到了。
妖獸頭一低,咆哮聲穿過田野傳來,低沉、響亮又刺耳的聲音,好像有人在吹一把曾經精緻、現在卻塞滿腐爛青苔的古老狩獵號角。牠轉過沉重的身軀,犄角朝前從丘陵頂端直奔而下。
我用蹲姿往前一衝,拔腿就跑,不是朝向半哩之外家中那個安全的避風港,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往麥田裡狂奔。如果我活著的最後幾刻能有什麼貢獻,那就是把這東西引開,盡量距離家裡越遠越好。
麥穗在我拉起的裙擺邊一一分開,莖稈在我靴底碎裂,刺刺的種子甩過我裸露的手臂,割出一道道鞭痕。我的包包在大腿外側撞來撞去,很礙手礙腳,拖慢了我的速度。蚱蜢倏地蹦跳過我面前,彷彿有隻隱形的手將牠們從麥田中彈出來。起初我什麼也沒聽見,這一切都好不真實。我很有可能只是為了好玩而在原野上狂奔,在一片湛藍無瑕的蒼穹下,這天如此美好。
然後一道冰涼的陰影碰到我汗涔涔的後背,緊接而至的黑暗吞噬我。麥子像暴風雨中海浪般洶湧翻騰。一隻巨蹄在我身側重重踩下,深埋進泥土中,我踉踉蹌蹌往後跌,在一莖莖麥穗間連滾帶爬。妖獸俯視著我。
1
我的客廳聞起來滿是亞麻仁油和穗花薰衣草的味道,畫布上有一抹鉛錫黃,賈弗萊絲綢外套的顏色在我筆下已經快臻至完美了。
畫賈弗萊困難的地方在於說服他每次讓我作畫時都穿同樣的衣服。要等每層油彩乾燥必須花上好幾天的時間,我無法依照他的喜好隨意變換他肖像的整套服裝,這點他老是不懂。雖然妖精愛慕虛榮,就如同「池塘通常是濕的」或者「熊很毛茸茸」一樣顯而易見,但就算是以妖精的標準來說,賈弗萊愛慕虛榮的程度仍然令人吃驚。說到底,這個特質讓我很容易就放低戒心,忘了他可是一個可以邊喝茶邊把我殺了的狠角色。
「我可能...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7收藏
7收藏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7收藏
7收藏

 13二手徵求有驚喜
13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