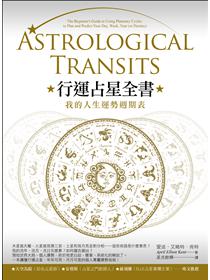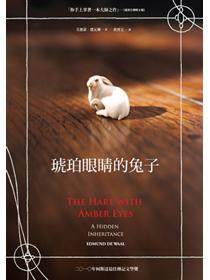獲選《衛報》「二十一世紀百大好書」
橫掃全球各大媒體年度選書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書總榜第一名
亞馬遜書店藝術類排行榜第一名
售出26種語言及電影版權,暢銷逾1,500,000冊!
透過264件根付的追索,看盡歐洲十九世紀豪門興衰史。
在跨越一百五十年、全球三大洲陸的傳奇旅程中,什麼會被記得,什麼會被遺忘?「根付」是日本江戶時代以象牙或木頭為媒材的微雕藝術。傳統和服沒有口袋,便以根付穿線連接小盒固定在腰帶,演變為今日的手機吊飾。
伊弗魯西家族是十九世紀顯赫的猶太家族,事業遍佈歐洲各大首都,交遊廣闊,富可敵國。家族成員查爾斯是藝術鑑賞家,資助印象派畫家雷諾瓦、竇加、莫內,更啟發了普魯斯特的偉大著作《追憶似水年華》。及至納粹勢力興起,在猶太人宿命般的浩劫中,家族財產聲望一夕化為烏有,唯獨264件根付藏品奇蹟般完好無損地被保留了下來。
這部橫跨五個世代的家族史,重現了十九、二十世紀歐洲舊時代的軼聞趣事與藝術成就,以及納粹大屠殺與反猶主義的政治戰爭。從快速崛起的帝國城市奧德薩到世紀末的巴黎;從被占領的維也納到東京,德瓦爾手握著細緻的根付,埋首浩瀚的文件記錄,走訪各地先祖奮鬥的宅邸,在這場溯源之旅中重新檢視那個躁動不安的年代、盛極而衰的失落家族,並看見曾經視如珍寶的收藏,如何歷經浩劫、浮於人事,對抗記憶的流失,最終成為歷史的見證。
各界推薦
張惠菁(作家)——專文推薦
吉田敦(大葉大學造形藝術系助理教授)、何致和(作家)、房慧真(作家)、茂呂美耶(作家)、劉鎮洲(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教授、陶藝家)、蔡康永(作家、主持人)——驚艷讚賞
2010年柯斯達最佳傳記文學獎、2010年英國銀河圖書獎年度新銳作家
2011年英國皇家文學學會翁達傑文學獎、2011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傑出書籍獎
2010年《經濟學人》年度最佳圖書、2010年《衛報》年度最佳圖書
2010年《每日電訊報》年度選書、2010年《愛爾蘭時報》年度選書
2010年《旁觀者》年度選書、2010年《標準晚報》年度選書
2010年《VOGUE時尚》年度之星、2011年《大西洋月刊》年度最佳圖書
2011年摩根大通私人銀行「富豪今夏必讀書單」
「這幾年來讀過最精采的一本書……豐富的故事告訴你,身為人的歡愉與痛苦。」――《每日電訊報》
「這本書一次要買兩本,一本留著,一本送給你最親密的愛書之友。」――《經濟學人》
「作者以陶藝家對造形物件細膩的感受力,清楚道盡人與物品之間彼此依存的私密關係;又以文學家對人情事理敏銳的觀察力,細緻描寫人物更迭與世事變幻的感人篇章。」――劉鎮洲,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教授/陶藝家
「我很少為了娛樂而讀書,不過,我正在看艾德蒙.德瓦爾的《琥珀眼睛的兔子》。愛不釋手的感覺真的很棒。」――詹姆斯.索特,美國藝術文學學會會員,福克納獎得主
「睿智、奇異與吸引人。」――A.S.拜雅特,布克獎得主
「出乎意料地結合了微觀的物品形式與宏觀的歷史,而且極為成功。」――朱利安.拔恩斯,布克獎得主
「你手上拿著一本大師之作。……如此優雅而令人回味的故事,讀來樂趣無窮……就像根付一樣,這本書令人愛不釋手。」――法蘭西絲.威爾森,《星期日泰晤士報》
「我這幾年來讀過最精采的一本書……豐富的故事告訴你,身為人的歡愉與痛苦。」――貝特妮.休斯,《每日電訊報》,年度選書
「這本書不只可以當成年度選書,當成十年一度的選書也行……一部引人入勝的作品,內容橫跨好幾個世代,值得數代的人珍藏與反覆閱讀。」――麥可.霍華德,《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德瓦爾令人驚歎的故事是對於變遷與時光流逝所做的探索與沉思……幾乎沒有作家像艾德蒙.德瓦爾一樣,為一部家族的故事添入這麼多的見識、驚歎與尊嚴,這是一部從第一句話就令人著迷的敘事作品。」――艾琳.貝特斯比,《愛爾蘭時報》
「一開始閱讀就停不下來,往後幾個星期,我沒辦法談別的事……完全陶醉其中。」――克蕾希達.康納立,《旁觀者》,年度選書
「一部非凡作品……德瓦爾靈巧地將一個迷人家族的各種生活主線編織起來……他也橫跨了城市、大陸與世代,時刻感受著地方與物品的力量──從國家的紀念性建築到根付──進而鋪陳出人類的歷史。」――傑拉德.賈可布斯,《星期日電訊報》
「細緻地描述對失落的家族與失落的時代的追尋。從打開這本書的那一刻起,你便走進了重建起來的古老歐洲。」――柯姆.托賓,《愛爾蘭時報》,年度選書
「德瓦爾是個陶藝家,他出色地喚起對這些日本小雕刻的觸覺,並且將它們放進口袋,帶它們前往巴黎、維也納、奧德薩,然後回到日本。他追溯這些根付的漫遊旅程,發現這些寶物閃避了主人的掌握,但又記得主人的撫觸,他們的手在象牙、木頭與石頭上留下了痕跡。」――艾德.霍利斯,《蘇格蘭人報》
「本年度最佳作品……充滿回憶的描述,文字清晰簡潔。」――安妮塔.布魯克納,《旁觀者》,年度選書
「優美、簡潔、悲劇色彩、荷馬史詩。」――史蒂芬.弗瑞爾斯,《衛報》,年度選書
作者簡介:
艾德蒙.德瓦爾 Edmund de Waal
生於 1964 年,世界知名陶藝家。大學時就讀劍橋大學,主修英國文學,並在英國與日本學習陶藝。他最著名的是大型裝置瓷器,曾在世界各地許多博物館展出,包括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泰特美術館、紐約高古軒畫廊和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等。《琥珀眼睛的兔子》是他第一本陶藝專業以外的作品,榮獲 2010 年柯斯達傳記文學獎、英國國家圖書獎、翁達傑文學獎,以及其他眾多文學獎項,並登上《星期日泰晤士報》暢銷書總榜第一名。他與家人現住在倫敦。作者網站:www.edmunddewaal.com/
譯者簡介:
黃煜文
資深譯者,譯有《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為什麼是凱因斯?》、《歷史的歷史:史學家和他們的歷史時代》、《如何寫歷史?》、《王者之聲:宣戰時刻》、《氣候變遷政治學》、《世紀末的維也納》、《耶路撒冷三千年》、《大轉向:文藝復興的開展與世界走向現代的關鍵時刻》、《文明 : 西方與非西方》等作品。
作者序
序文
一九九一年,我申請到一筆由日本基金會所提供的兩年獎學金。這筆獎學金是讓七名來自不同領域(工程、新聞、產業、陶藝)的英國年輕人,先在英國大學接受基礎日語訓練,並於接下來的一年前往東京見習。流利的日語協助我們建立與日本交流的新紀元,我們是第一批參與計畫的成員,可想而知肩負著極高的期待。
第二年到日本見習期間,我們每天上午都在澀谷的語言學校度過,從櫛比鱗次的快餐店和電器用品促銷賣場走一段上坡路,便可抵達學校。東京此時正逐漸從一九八○年代泡沫經濟的破滅中復甦,這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路口,通勤族站在十字路口看著螢幕上的日經指數屢創新高。為了避免尖峰時段洶湧的地下鐵人潮,我刻意提早一個小時出門,與另一名年紀稍長的學者——考古學家——見面,我們會先享用肉桂麵包和咖啡,然後去上課。
我有家庭作業,貨真價實的家庭作業,而且這是我脫離中小學以來再度面對學校的習題:每週要學會一百五十個漢字;一篇小報新聞專欄的語法分析;每天複述數十個日常用語。日文是最讓我頭痛的。反觀另一名年輕學者,他已經可以用日文跟老師一起揶揄電視節目或政治醜聞。語言學校有一道綠色大門,我記得某天早上我踹了鐵門一腳,想著二十八歲的人踹學校大門是什麼樣子。
下午完全是我自己的時間。我每週有兩天下午會到陶藝工作室,和其他人一起共享這個空間,包括製作茶碗的退休商人,或以粗糙的紅色黏土及網狀物傳達前衛思想的學生。你支付會費,隨手抓過一張板凳或旋轉盤,找個角落做自己的事。工作室並不吵鬧,隱約聽到有人低聲說話,但氣氛相當愉快。這是我首度嘗試製作瓷器,當我把作品從旋轉盤上取下,我會從側邊輕推一下我的瓶子與茶壺。
我從小就開始學製陶,還纏著父親,非要他帶我去上晚間的陶藝課。我的第一件陶器作品是用旋轉輪拉坏完成的陶碗,我為它上了一層乳白色的釉,噴上鈷藍色來點綴。就讀中小學的午後,絕大多數時間我都待在陶器工坊。我十七歲便離開校園向一名作風嚴厲的人拜師學藝,他是英國陶藝家貝納德.里奇(Bernard Leech)的崇拜者。他教我尊重材料並適得其所:我丟棄過數百件以灰色石黏土拉坏而成的湯碗和蜂蜜瓶,並負責清掃地板。我會協助上釉,仔細反覆校準東方的色彩。他從未去過日本,書架上卻擺滿討論日本陶瓷的作品。我們會討論某個茶碗跟早上用來盛裝牛奶咖啡的馬克杯相比,具備哪些優點。他說,避免不必要的動作——越簡潔越豐富。我們總是靜悄悄地或在古典音樂聲中工作。
十幾歲時,我曾到日本當過一整個夏天的學徒。我拜訪各地的陶藝村,包括益子、備前、丹波,向幾名同樣嚴厲的師傅學習。紙門每次開闔的聲響,以及茶屋庭園中水流經過石縫的聲音,都是神靈般的顯現,正如Dunkin’Donuts 店前霓虹燈帶給我的異樣感。我有證據足以證明當時我對陶藝的投入有多深。回國後,我在雜誌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日本與陶藝家倫理:培養對材料及時代印記的敬意〉。
學徒生涯結束後,我進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此後有七年的時間,我在威爾斯和英格蘭邊境一處規畫周詳的工作室獨自工作,然後繼續待在沒有人味的內城。我非常專注,我的作品也一樣。如今我又來到日本,待在一間凌亂的工作室,坐在一旁的男人正大談棒球經,而我則製作著一只側面內推的瓷瓶。我樂在其中——看來我已經抓到要領。
一週裡有兩天下午,我會到日本民藝館的檔案室閱讀關於里奇的書。位於郊區的博物館是由農舍改建,收藏了柳宗悅製作的日本及韓國民藝作品。柳宗悅具備哲學家、藝術史家和詩人身分,他發展出一套理論解釋何以有些物品會如此美觀,例如一些不知名工匠所製作的器皿、簍筐和織物。柳宗悅認為,這些物品表現出一種無意識之美,因為工匠是在完全超脫自我的情況下手作而成。二十世紀早期,年輕的柳宗悅和里奇在東京結為密友,兩人頻繁地書信往來,分享彼此閱讀布雷克、惠特曼及拉斯金的想法。他們甚至在近東京市郊一處小村落建立了藝術家聚落,里奇從事陶藝創作,並找來當地的男孩擔任助手;柳宗悅則對他那群波西米亞風格的朋友講述羅丹與美。
穿過一扇門,石地板變成辦公室專屬的油氈地,然後沿著後廊道來到柳宗悅的檔案室。這裡格局不大,空間約十二呎乘以八呎,延伸到天花板的書架上放滿書籍及堆疊的麻編盒,盒裡是柳宗悅的筆記本和書信。還有一張書桌和一盞燈。我喜歡檔案室,這裡極其安靜而陰鬱。我在這裡閱讀、寫筆記,我計畫書寫一部具有顛覆觀點的里奇傳記,這會是以隱微方式討論日本主義的作品,指出西方過去一個多世紀來熱情且充滿創意地誤解了日本。我想知道日本為什麼能讓藝術家的創作如此強烈又充滿熱忱,並讓學界執拗地指出一個又一個對日本的誤解。我希望藉由撰寫此書,解開我心中那股深刻難解、對日本的愛戀與沉迷。
每週,我會撥出一天下午陪伴我的舅公伊吉。
出地鐵站之後走上斜坡,經過五顏六色的啤酒販賣機,經過埋葬四十七名武士的泉岳寺,
經過一棟奇特的神道教會議廳,經過直爽的X先生經營的壽司店,在高松宮宣仁親王松園的高牆旁右轉。我走進大樓電梯上到七樓,伊吉會坐在窗邊的扶手椅上閱讀。大部分是雷納德(Elmore Leonard)或勒卡雷(John Le Carr)的作品,或者是法文回憶錄。伊吉說,真奇怪,有些語言就是比其他語言來得溫暖。我彎下腰,他親了親我的臉頰。
他的書桌放著吸墨紙、一疊印有他名字的紙張,以及筆;不過他已不再寫作。從他後方的窗戶望出去可以看到一台台起重機,東京灣已消失在四十層的公寓大樓之後。
我們會共進午餐。伊吉的午餐如果不是管家中野太太準備的,就是住在連通公寓的朋友次郎帶來的。歐姆蛋和沙拉,以及從銀座百貨公司一家精緻的法式麵包店買來的烤麵包、一杯松塞爾或普宜富美冰鎮白酒、一顆桃子、一些乳酪和極品咖啡,而且是黑咖啡。
八十四歲的伊吉有點駝背,他的穿著向來無可挑剔:西裝外套,胸前口袋襯著手帕,淡色襯衫和領帶,看來相當體面。他仍蓄著灰白的八字鬍。午餐後,伊吉會推開幾乎占滿客廳整面牆的玻璃櫥櫃拉門,把裡頭的根付*一個個拿出來。琥珀眼睛的兔子、佩戴武士刀及頭盔的男孩、扭著肩膀與四肢轉身咆哮的老虎。他會遞給我一枚根付,我們一起賞玩,然後我會小心翼翼將根付放回玻璃櫥櫃,安置在數十種動物和人物造型的根付之間。
我把櫥櫃裡的小水杯斟滿水,確保象牙不會在乾燥的空氣裡龜裂。
伊吉會說,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們小時候多麼喜歡這些玩意兒?某個巴黎的表親是怎麼把這些送給我的父母?我有沒有告訴你安娜口袋的故事?對話內容往往峰迴路轉,這一刻伊吉還在描述他們在維也納的廚子特製了皇帝鬆餅做為父親的生日早餐:層層堆疊的鬆餅撒上糖粉,管家約瑟夫大張旗鼓地把鬆餅端到餐廳,以長刀切開。父親直喊著就算皇帝過生日,也不會有這麼精采的開場!下一刻話鋒一轉,伊吉倏地談起莉莉的第二段婚姻。
但誰是莉莉?
感謝上帝,我心想,即使我不認識莉莉,至少故事地點我很清楚:巴德伊舍、科維徹什、維也納。當夜幕籠罩東京灣,起重機上的建築燈光也隨之亮起,我想像自己變成一名抄寫員,我或許應該帶著筆記本坐在他身旁,記錄在他話語中第一次大戰前的維也納。但我從未這麼做,那似乎太正式也不恰當,而且很貪婪:那是個精采豐富的故事,而我竟想要擁有它。無論
如何,我喜歡事物重複打磨之後的平滑,而在伊吉的故事裡,便有著河中圓石的觸感。
歷經一整年的下午時光,我得知伊吉的父親對伊吉的姊姊伊莉莎白的聰明
感到驕傲,以及他母親對於女兒過於贅述的談吐不以為然。說話要條理分明!
伊吉經常語帶焦慮地提到他和姊姊吉瑟拉玩的一個遊戲:他們必須從客廳拿一件小東西,下樓穿過庭院,避免引起馬夫注意,然後來到地下室,把東西藏在地窖裡。然後再慫恿對方去拿回來;而伊吉又是怎麼在黑暗中弄丟了東西。這似乎是一段無止盡且永不磨滅的回憶。
在科維徹什發生了許多事,他們的別墅往後將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伊吉的母親艾咪在破曉前將他喚醒,這是他第一次跟著獵場看守人外出狩獵,他必須親手射殺躲在農作物收割後殘梗後頭的兔子。當他看見寒冷天氣裡耳朵瑟縮顫抖的兔子時,遲遲無法扣下扳機。
吉瑟拉和伊吉偶然看見吉普賽人帶著一頭戴著鎖鏈、會跳舞的熊,這群人在莊園邊際的河邊紮
營,兩人都嚇壞了,一路奔回家。伊吉提到東方快車在一處小站停下,他祖母身穿白色連身裙,在站長的攙扶下下車。他和姐姐急奔上前迎接,祖母給了他們一盒用綠紙包裝的蛋糕,那是從維也納的德梅爾蛋糕店買來的。
艾咪早餐時會把伊吉拉到窗邊,指著窗外的秋樹,上面棲息著為數眾多的金翅雀。伊吉敲打窗戶,把金翅雀都嚇飛了,但樹仍然是鮮明的金黃色。
午餐後我清洗餐具,伊吉去睡午覺,我則開始寫我的漢字作業,一張張方格紙上爬滿扭曲的字跡。我會待在這裡直到次郎下班回來,他會帶來日文和英文晚報,以及隔天早餐的可頌。次郎會放一點舒伯特或爵士樂,我們會喝一點酒,然後我便離開留他們獨處。
我在目白租了一間舒適的單人房,窗外是一處種滿杜鵑的小花園。我有一臺電子爐和一只熱水壺,我盡可能利用這些工具。但是向晚時分,我大多以麵裹腹,顯得相當孤獨。每個月有兩天,次郎和伊吉會帶我出門用餐或者聽音樂會,他們請我到帝國飯店喝一杯,然後吃頓上好的壽司或韃靼牛排。有時為了向我們從事銀行業的先祖致意,我會來份銀行家牛肉餐。我婉謝了鵝肝——那可是伊吉的主食。那年夏天,英國大使館舉辦了一場學者接待會,我必須以日文致詞,說明這一年來的收穫,以及文化如何聯繫英日兩個島國。事前我不斷練習,直到筋疲力盡。伊吉和次郎也到場了,我可以看到他們舉起香檳為我打氣。之後,次郎輕揉著我的肩膀,伊吉親了我一下,他們不住微笑,異口同聲說我的日文「上手ですね」——專業、流利、無懈可擊。
他們一切都已安排妥當,他們兩人。次郎公寓裡有一間和室,裡面有座小神龕擺著他母親和伊吉母親艾咪的相片,他們在此祭拜、敲磬。走過連通的門直達伊吉公寓,他的書桌上擺著兩人在內海一艘船上的照片,後方是滿山遍野的松樹,水面映照斑駁的陽光。那是一九六○年一月,次郎的頭髮完美的往後梳,手臂搭在伊吉肩膀上。而另一張照片是一九八○年代,在夏威夷外海一艘客輪上,他們身著晚禮服,臂挽著臂。
活得久是一件艱難的事,伊吉低聲說。
在日本度過晚年是美好的,他的音量稍微大了些。我的人生有超過一半的時間在這裡度過。你想念維也納的一切嗎?(為什麼不直接問他:你想念什麼,當你年事已高,而且沒有住在你的出生地?)
不,我從一九七三年起就沒有再回去過,那裡沉悶而令人窒息,每個人都知道你的名字。你在克恩特納大街買一本小說,他們會問你,你母親的感冒好些了嗎?你動彈不得。屋內淨是金箔和大理石。如此陰暗。你看過我們在環城大道的老房子嗎?
你知道嗎,伊吉突然說,日本的李子餃比維也納的美味。
事實上,他停頓了一會兒繼續說,我父親總說等我年紀夠大了,要帶我參加他的俱樂部。每週四父親會在歌劇院附近和他的朋友、他的猶太朋友們聚會,因此那天回到家他總是開開心心的。維也納俱樂部,我一直想跟他一起去,但他從未帶我去過。我離家前往巴黎,之後到紐約,你知道,然後戰爭就爆發了。
我想念的是這件事,從以前就想著。
一九九四年,在我回英國不久之後,伊吉過世了。次郎打電話通知我,他在醫院裡只待了三天。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解脫,我回東京參加他的喪禮,二十幾個人為他送行,包括他們的老友、次郎家人、中野太太和她女兒,每個人無不悲傷流淚。火化時我們聚在一起,骨灰送出來,我們兩兩一組輪流向前用細長的黑箸將未燒盡的遺骨挾進骨灰罈。
我們前往一座神社,伊吉和次郎在此安置了墓地。二十年前他們便在這塊墓地做好規畫。墓園位於神社後方的山丘上,每塊墓地都以矮石牆隔開。灰色的墓碑上已經刻上兩人的名字,還有一處供人獻花的地方。水桶和刷子,以及以梵文書寫經文的木片。你拍掌三次向已逝的親人問安,然後為自己這麼晚才來致歉,之後打掃墓地,移除枯萎的菊花,插上新鮮菊花。
神社裡,骨灰罈放在一座小高臺,伊吉的照片——在客輪上身穿晚禮服那張——置於罈前。僧侶誦念佛經,我們上香祝禱,並為伊吉取了戒名,佑祝他的來生。
然後我們談到伊吉。我想以日文表達我舅公對我的意義重大,但我說不出口,不僅因為泣不成聲,也因為我的日文在我需要時並不是那麼管用,儘管我以兩年的高額獎學金學習日文。於是,在這處佛教神社的空間,在東京市郊,我誦念神聖祈禱,為了離故鄉維也納如此遙遠的伊格納斯.馮.伊弗魯西,也為了他的父親、母親及他的兄弟姊妹,那些離散的猶太人們。
喪禮過後,次郎要我幫忙整理伊吉的衣物。我打開更衣間櫥櫃,裡面的襯衫依顏色井然有序地依次排列。打包領帶的時候,我看到地圖上標記著他和次郎假期出遊去過的地方:倫敦、巴黎、檀香山和紐約。整理告一段落,我們喝了紅酒,次郎拿出毛筆和墨水寫了一份文件,並且蓋上印章。他對我說,萬一他也離開了,我可以保管這些根付。
所以,我是下一個。
伊吉收藏了兩百六十四枚根付。這些小東西的數量實在驚人。
我拿起一枚根付在指間反覆端詳,用掌心琢磨重量。如果材質是木頭,不管是栗木或榆木,都比象牙要輕得多。木雕作品更容易顯現古色古香:帶著斑紋的狼背,或者環抱身軀翻滾中的雜技演員,微弱地透出光澤。象牙根付呈現多層次的奶油色調,事實上,每一種奶油色系都有,就是沒有純白色。有些鑲有琥珀眼睛或獸角。有些年代久遠的可見輕微的磨損:半人半羊的牧農之神在葉子上休息,可惜臀部的斑紋幾近消失了。在蟬的表面有一道細微裂痕,幾乎看不見的裂縫,是誰把它掉在地上?在哪裡?什麼時候?
多數根付上都有簽名——當物品完成交付後,主人會在上面署名。有一枚木雕根付是一個人坐著,兩腿間夾著葫蘆。他彎身朝向葫蘆,兩手握著一把刀,刀刃已剖進葫蘆中。從他的手臂、肩膀和脖子可以看出這動作有多麼費力:全身肌肉專注在刀刃上。另一枚根付則是一名木桶匠正用手斧製作一個已完成一半的桶子。他屈身在木桶內,蹙著眉專注工作,這是一件表現木作的象牙雕刻。而這兩枚根付都是以完成某件半成品為主題的作品。看,它們說,我已經完成到這個程度,而他幾乎才正要開始。
當你在手中把玩這些根付,尋找簽名的所在是件很有趣的事——鞋底、樹枝末端、大黃蜂胸部——而簽名的筆觸同樣也會看出不少樂趣。我想像用毛筆寫下日文姓名的一連串動作,毛筆蘸上墨汁,筆鋒接觸紙張的那一瞬,以及再回到硯台上蘸墨。我不禁納悶雕刻根付的人要怎麼使用精細的金屬工具,才能銘刻出如此獨特的簽名。
有些根付沒有署名。有些貼了小紙張,仔細寫上極小的數字。為數不少的根付以老鼠為主題,或許是因為老鼠讓雕刻師有創作的空間,將牠長而彎曲的尾巴迂迴纏繞,也許纏繞著一桶水、死魚、乞丐的破衣,然後再將老鼠的腳爪收在根付底部。捕鼠者的根付數量也不少,這個我可以理解。
有些根付想要表現一種動態,所以你的手指可以順著解開的繩子或濺溢的水花撫摸。有些根付細微的動作太多,以致你的手指顯得忙亂:浴桶裡的女孩、蚌殼上的渦紋。你意想不到的是,有些根付甚至能夠同時表現兩者:糾結盤繞的龍倚在一顆尋常的石頭上,你透過手指感受象牙的光滑和石面的觸感,猛地卻遭遇繁密纏繞的龍身。
根付大多呈現出不對稱,我認為這是樂趣所在,就像我最喜愛的日本茶碗,你不可能從局部了解整體。
回到倫敦後,我把一枚根付放進口袋,一整天帶著到處走。「攜帶」似乎不能適切地形容把根付放在口袋的感覺,那聽起來太過目的性。根付是如此輕巧而迷你,很容易在你的鑰匙和零錢之間來回,感覺上似乎就消失了,你一下子就會忘記它。這是一枚熟透的枇杷根付,它以栗木雕成,是十八世紀末江戶時期的作品。日本的秋天,你有時可以看到枇杷樹將枝椏垂掛在神社外牆,或從私宅庭院伸展到街上的自動販賣機,那景象著實愜意。我的枇杷幾乎快要爛熟,果蒂上的三片葉子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彷彿稍加搓揉便會掉落。果實色澤有些不均,有一面看起來較為成熟。你可以感覺到底部有一大一小兩個洞,由此將絲線穿入,根付就可以充當小袋子的栓扣。我試著想像過去誰曾擁有這枚枇杷根付。它的製作時期早於一八五○年代日本開放之前,充分反映出日本人的藝術品味。這枚根付很可能是為商人或學者而雕刻的,它平靜而含蓄,卻讓我會心一笑。以異常堅硬的材質製作出觸感柔軟的掌中物,可說是個緩慢且需要實際領會的雙關語。枇杷在我的外套口袋裡,我到博物館開會討論我預計進行的研究,之後前往工作室,再到倫敦圖書館。我時不時在指縫間滾動這枚根付。
我知道自己有多麼在乎這件軟硬兼具且容易遺失的古物是如何流傳至今的。我必須想辦法挖掘背後的故事。擁有這枚根付——繼承所有根付——意味著我從此對它們負有責任,也對曾經擁有它們的人負有責任。但這份責任有多沈重,我不清楚,坐立難安。
我從伊吉口中得知這段旅程的梗概。我知道這些根付是一八七○年代,我外曾祖父的堂哥查爾斯.伊弗魯西在巴黎買下的。我知道他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將根付送給我外曾祖父維克多.馮.伊弗魯西,做為結婚賀禮。我很清楚安娜的故事,她是我外曾祖母的侍女。我還知道這些根付跟著伊吉一起來到東京,成為他和次郎生活的一部分。
巴黎、維也納、東京和倫敦。
枇杷的故事必須從製造地說起,即江戶,舊時的東京,一八五九年,美國海軍准將培理率領黑船打破日本鎖國政策並和世界展開貿易之前。只是這枚根付第一個歇腳處是查爾斯在巴黎的工作室,這是一間位於伊弗魯西宅邸、可以俯望蒙梭街的房間。
對我來說這是個好的開始,因為我和查爾斯有著直接口述的聯繫。我祖母伊莉莎白五歲時曾在琉森湖畔梅根的伊弗魯西山中別墅見過查爾斯。這幢「山中別墅」為六層樓高的粗砌石造建築,頂層是矮小華麗的塔樓,整體構造超乎想像的不雅觀。這處宅邸是查爾斯的兄長朱爾斯及他妻子芳妮在一八八○年代初期建造的,是「巴黎緊張壓迫的日子」的喘息地,這個居住空間足以容納來自巴黎和維也納的所有「伊弗魯西家族」,甚至是來自柏林的遠親。
這棟別墅有數不清的小徑在腳下嘎扎作響,小徑兩旁英國風格的黃楊修剪得分外齊整,花圃裡遍布著小花壇,兇悍的園丁會叫孩子們到別處去玩。在這座井然有序的瑞士花園裡,每一粒碎石都經過精心的鋪撒,花園往下延伸到湖邊,那裡有一座小碼頭和船塢,孩子因此有了更多挨罵的機會。朱爾斯、查爾斯和排行老二的伊格納斯是俄國公民,船庫屋頂上飄揚著俄國皇室旗幟,他們在這座別墅度過無數個漫長夏日。我的祖母是擁有驚人財富卻無子嗣的朱爾斯夫妻的法定繼承人,她記得餐廳裡有一幅很大的畫作,描繪溪邊的柳樹,她也記得別墅裡只有男僕,就連廚子也是男的,跟她在維也納的家相比,這裡顯然令她感到格外有趣。在維也納,家裡只有一名叫約瑟夫的老管家,當他開門讓她外出到環城大道時總會對她眨眼,馬夫穿梭在一群女僕和廚子之間。顯然,男僕比較少打破瓷器。而她也記得,在這個沒有孩子的別墅裡,舉目所及盡是瓷器。
查爾斯年屆中年,但是和他兩名充滿魅力的兄長比起來似乎顯得老成許多。伊莉莎白只記得他迷人的鬍子,以及他總是從背心口袋掏出一只極為精巧的懷表。此外和其他長輩一樣,查爾斯給了伊莉莎白一枚金幣。
彷彿就發生在眼前似的,伊莉莎白清楚記得查爾斯彎下腰來撥弄她妹妹的頭髮。妹妹吉瑟拉年紀雖小卻是十足的美人胚子,分外引人注意。查爾斯稱她為「我的小吉普賽」、「我的波希米亞女孩」。
這是我和查爾斯之間直接口述的連結,這是一段過往。只是當我動筆之際,我覺得一切栩栩如生。
這些故事都有後續——男僕的人數以及略顯陳腐的金幣禮物——但似乎覆蓋著朦朧的憂鬱,而我倒是很想知道關於俄國旗幟的細節。當然,我知道我的家族是猶太人,也知道我的家族曾經極為富有,但我實在不想掉進家族史詩的窠臼,寫出輓歌般充滿失落的中歐敘事作品。我不想把伊吉描述成待在書房研究的老舅父,如同查特文(Bruce Chatwin)筆下的烏茲,傳承了家族故事給我,並不忘叮囑:去吧,凡事小心。
我想,這些事情本身就可以成為小說的情節,幾則引人入勝的奇聞軼事拼湊起來,補充一點和東方快車有關的內容,當然,再加上一點漫遊布拉格或其他同樣上相的城市描寫,以及從Google搜尋來的美好年代舞廳剪報……如此產生的作品將是懷舊而傷感的,但卻淺薄。
對於一個世紀前家族喪失的財富及風華,我沒有資格懷舊,而且我也對淺薄毫無興趣。我想知道我指間把玩的這件堅硬、微妙且充滿日式風格的木製玩意兒,和它曾經流落的地方有著什麼樣的因緣。我想碰觸那道門把,轉開並感受門的開啟。我想走進這件物品待過的房間,感受那個空間,知道牆上掛著的畫作、光線如何透過窗戶灑進屋內。我想知道它曾經被誰握在手裡,這些人感覺如何,有什麼想法——如果他們思考過的話。我想知道,它看見了些什麼。
我認為,憂傷是一種無所事事的茫然,一種免責條款,一種令人窒息的失焦。反觀這枚根付是
精巧的,強硬表現出它的精確度,值得我們以同樣的精確回報。
我之所以在乎,是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製作物品。對我來說,物品如何被對待、使用和傳遞,不只是稍微有趣一點的問題。它是我的問題。我製作過數千只陶器。我不擅長記住名字,我說話總是含糊不清、不夠直接,但製陶我很專業。我能記住陶器的重量和平衡,以及陶器表面和容量如何協調。我可以解讀陶器的口緣如何產生張力或失去張力,我可以感覺那是匆促完成或歷經一番功夫——如果成品被灌注了溫情的話。
我可以看出陶器如何與周圍的物品互動,或是如何與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
我也可以記得某些作品是否希望你以雙手撫摸,或只是用指尖去碰觸,或者希望你離它遠遠的——並不是拿在手上就比較好。世上有些物品只適合遠觀,而非隨手任意擺弄。此外,身為一名陶藝家,當擁有我作品的人將它視為有生命的事物來談論,我總會油然生起一股異樣感:我不確定我能否賦予作品生命。但有些作品確實保留了製作過程中的脈動。這種脈動激起我的好奇。決定碰觸或不碰觸之前,我往往有著片刻猶疑,這是個詭異的時刻。
如果我選擇拿起把手附近有個缺口的白色小杯,這個杯子是否會在我生命中占據某種地位?一件簡單的物品,這個杯子更偏象牙色而非白色,容量太小不適合早上拿來喝咖啡,外表看起來也不均衡,卻可能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可能隱退到個人講述故事的領域,以感性而迂迴的方式和記憶交纏。一件受到喜愛、令人愛不釋手的物品,我可以收藏,也可以交給別人。物品轉手的過程背後都有故事。我給你這件東西,因為我愛你;或是因為某人交給我了;因為我在某個特別的地方買到;因為你會好好照顧它;因為它能豐富你的生活;因為它能讓別人對你心生嫉妒。
傳承絕不是簡單的故事。什麼被記住了,什麼被遺忘了?也許會有一連串遺忘的過程,前
任物主的一切完全被抹除,隨伴著故事平添枝節。傳遞到我手中的除了這些日本小物件,還有什麼呢?
我很清楚自己和根付相處太久了,我大可將根付視為往後人生的一樁軼事——至愛的長輩傳給我的新奇玩意——或是起而尋找這些根付的意義。有天晚上,我在晚餐時向幾名學界朋友講述我所知道的根付故事,我開始對自己講述時的四平八穩感到作嘔。我發現自己其實在娛樂聽眾,而他們的反應也說明了故事的內容。這已經不只是說得流暢順口而已,而是故事本身變得越來越淺薄。我必須趁現在好好整理這些故事,否則總有一天它們會消失無蹤。
忙碌不是藉口。我才剛結束一場博物館的瓷器個展,若安排得當,我可以把一名收藏家的委託延期。我和妻子達成協議,重新擬定行程。三到四個月應該可以讓我完成不少事,我有足夠時間回東京探望次郎,並且前往巴黎和維也納。
由於我的祖母和舅公伊吉都已去世,因此一開始我必須尋求父親的協助。年屆八十的他樂意為我翻找家族資料,他說,那是背景資料。他似乎很高興,因為他的四個兒子裡終於有人對家族史感興趣。留下的記錄不多,他提醒我。他帶了四十幾幀照片到我的工作室,此外還有兩份薄薄的藍色文件夾,裡面放了信件,貼有黃色便利貼,這些書信絕大多數可以辨讀;我的祖母在一九七○年代註解的家譜、一九三五年維也納俱樂部的會員名冊,以及放在超市購物袋裡一堆托瑪斯.曼的小說,上面附有題詞。我們將這些物品擺在樓上辦公室的長桌上,正好是我燒製陶器的房間上方。父親對我說,從現在起,你就是家族檔案的管理者。我看著這些資料,全然不清楚我能從中找出什麼有趣的資訊。
我有點失望地問,還有其他的嗎?當晚父親又在他退休教士庭院的小公寓裡繼續翻找。他打電話給我,說找到另一本托瑪斯.曼的作品。看來這趟旅程將比原先設想的更為艱困。
然而我不能一開始就抱怨,我對根付的第一位收藏者查爾斯所知不多,但我已經找到他當初在
巴黎的住處。我把一枚根付放進口袋,動身出發。
序文
一九九一年,我申請到一筆由日本基金會所提供的兩年獎學金。這筆獎學金是讓七名來自不同領域(工程、新聞、產業、陶藝)的英國年輕人,先在英國大學接受基礎日語訓練,並於接下來的一年前往東京見習。流利的日語協助我們建立與日本交流的新紀元,我們是第一批參與計畫的成員,可想而知肩負著極高的期待。
第二年到日本見習期間,我們每天上午都在澀谷的語言學校度過,從櫛比鱗次的快餐店和電器用品促銷賣場走一段上坡路,便可抵達學校。東京此時正逐漸從一九八○年代泡沫經濟的破滅中復甦,這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路口,通勤...
目錄
序
第一部 巴黎,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九九年
第二部 維也納,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八年
第三部 維也納、科維徹什、頓布里吉威爾斯、維也納,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
第四部 東京,一九四七年到二○○一年
尾聲 東京、敖德薩、倫敦,二○○一年到二○○九年
致謝
序
第一部 巴黎,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九九年
第二部 維也納,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八年
第三部 維也納、科維徹什、頓布里吉威爾斯、維也納,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
第四部 東京,一九四七年到二○○一年
尾聲 東京、敖德薩、倫敦,二○○一年到二○○九年
致謝
 11收藏
11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1收藏
11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