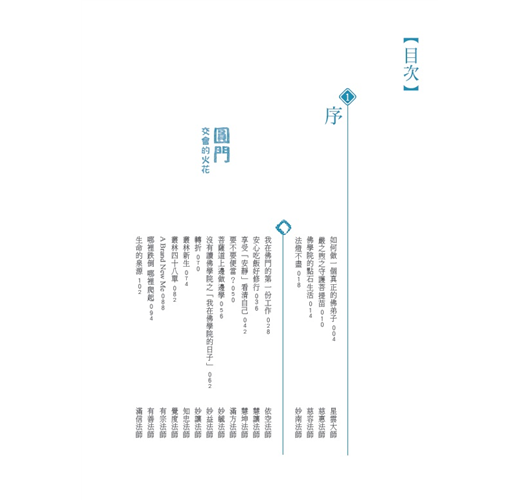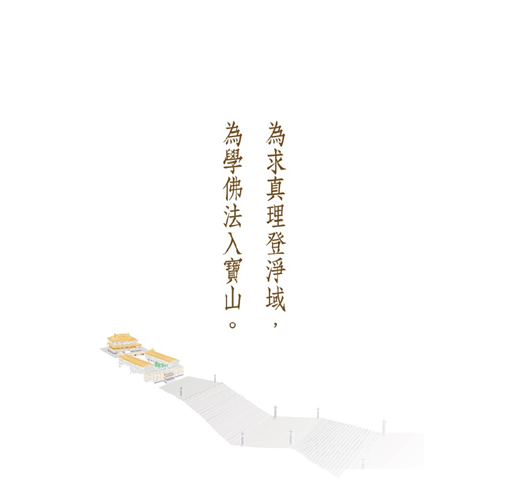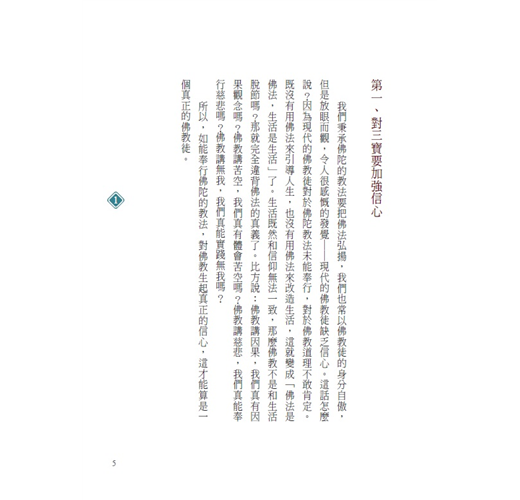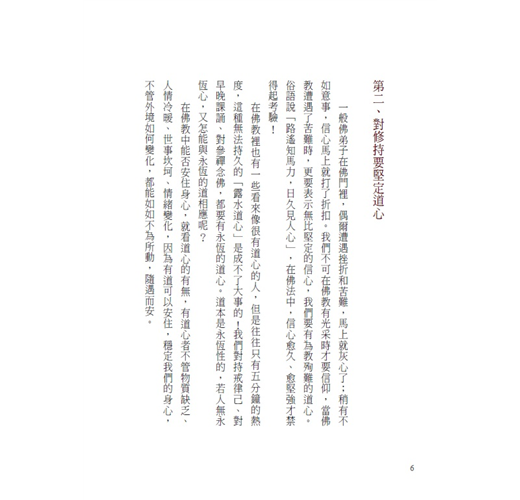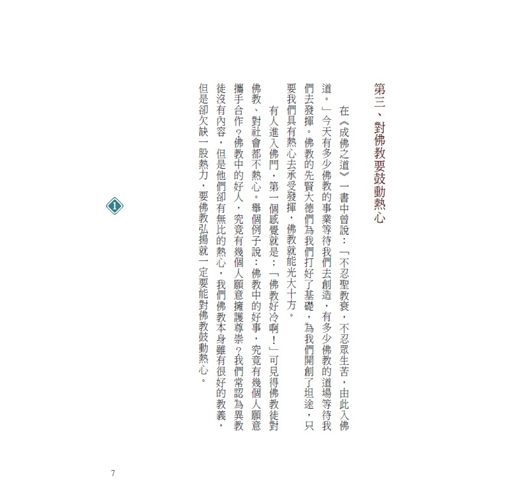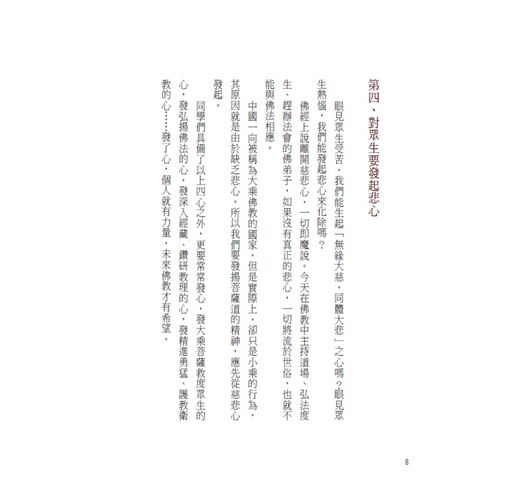我在佛門的第一份工作/依空法師
當年辭掉彰商教職,上佛光山承擔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佛學院的教務工作,師父時任叢林大學院長,慈莊法師則擔任東方佛教學院院長。為了讓學生有堅強的師資陣容,慈莊法師帶著我,拿著聘書,披著袈裟,去頂禮聘請教界的耆宿法師,上山教授因明、唯識等佛學課程。為了請成功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唐亦男教授來教「魏晉玄學」,我們造訪成大教師宿舍,最後因為我大學曾選修唐教授的先生王淮老師的「老莊」課程,以此因緣而成就一樁美事。
當時適逢佛光山開山的第一個十年,開山機不曾停歇,職事們最期待的是,每天早上七時至九時,聆聽師父的「成佛之道」等課程,然後跟隨他去巡視工程,看他拿著瓦片在地上描畫,一棟棟輝煌的殿宇就從地涌出矗立於佛光山。下午四點半是全院師生最快樂的時刻,
早期到老育幼院前的廣場,後來移至東山籃球場,全山總動員,天龍地虎打成一片,每天進行一場不計輸贏、只在參與的籃球賽,球員可以隨時上下場,甲乙隊隨興加入。我們球技不好的人,則圍坐在場邊四周,稱職的當個啦啦隊員。
因為在開山,常住經濟非常拮据,全山大眾都沒有水果吃,只有初一、十五供奉大悲殿觀世音菩薩時有供果,這些水果則要留著以招待遠來、外請的教授專家們。我因為辦教務,有時須陪貴賓用齋,偶爾可能吃到一、二片水果,日子過得既清貧簡淡又滋潤飽滿。直到現
在,我都沒有養成吃水果的「好」習慣。現在的學生物質豐裕,過堂時輕易推出水果、菜餚,可惜無法體會物力維艱、來處不易的稀有難得精神。
師父常說:「佛光山以文教起家。」念茲在茲,傾全力要把教育辦好。他禮賢下士、尊師重道,把教界僧信二眾的大德幾乎都網羅上佛光山教書,在寶藏堂召開無數次的佛教人才培育會議。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會議正如火如荼的熱烈進行,師父突然叫人趕快準備午齋,因為座中有一位外道場的出家人修「過午不食」,大家只好臨時中止會議,吃飯要緊。多年後,他倡導的佛光會主題「尊重與包容」,其實他早已身體力行。
佛學院有些教授從台北搭飛機來山上課,以當時台灣的經濟條件,搭飛機算是高等消費。為了辦學,作育英才,佛光山不惜一切資源投入教育工作,其中有一位教授,經常半夜三更才到達佛光山。辦教務的我,不好驚動別人,只好獨自枯坐在頭山門的大樹下,在幽微的星
光中守候教授的到來,並且還要張羅他的掛單、點心,讓貴客賓至如歸,沒有絲毫的不便。這是師父一向教導我們「給人方便」的待客之道,某位教授有感而發說:「三代禮節,盡在於斯。」意思是說「禮失求諸野」,夏商周三代的禮樂精神,保藏在佛門展現無遺。
從日本完成學業回山,一頭栽進一連串的行政工作。前後接管過普門中學、大慈庵、雙林寺住持、佛光山文教基金會、文教處(佛光山文化院的前身),每週並且要舟車輾轉的到文化大學哲學系上課,這其間始終未曾更換的單位,就是佛學院的工作。歲月悠悠,一晃十幾寒暑。其中舉凡招生、設計課程、聘請師資、為學生覓設獎學金等等,都是我們的職務。
有一年,師父更是破釜沉舟,把我們幾位負責佛光山僧伽教育行政工作的人,集合在美國西來寺,整整一個月,每天不眠不休的討論佛學院的辦學方向與策略,最終定下佛光山僧伽教育三級制度:等同高中程度的「東方佛教學院」、大學學歷的「佛光山叢林學院」、相當於研究所的「中國佛教研究院」。「叢林大學」正式轉型為「佛光山叢林學院」,下設「經論教理」、「文教弘法」、「法務行政」、「社會應用」等四系,先行試辦「經論教理」和「法務行政」兩系,成效斐然,延續至今不輟。「中國佛教研究院」則因南華與佛光兩所大學設有宗教研究所而併入。自此佛光山的僧伽專才教育體系,脈胳分明,人才輩出。
佛學院最鼎盛的時候,全院學生曾多達七百多人,分部林立。佛光山叢林學院分為專修部和國際學部,專修學部下設本山的男眾學部和女眾學部,以及台北女子佛學院、基隆學部、彰化的福山學部;東方佛教學院則分有本山的沙彌學園、東方佛教學院女眾部、嘉義的圓福學園。國際學部有英文佛學班與日文佛學班。大學級別的專修學部學生,一年級初入學時不分科系及區域,都在佛光山接受扎實的通識教育,等到二年級時,再依學生的志願分發到各個區域,或台北,或基隆,或福山,或留在本山就讀,務期達到快樂學習。雖然如此,大悲殿內總本部的教室、寮房、齋堂、圖書館等硬體設備,仍然不敷使用,責成永昭法師監督工程,因此在原來東西兩廂的寮房上加蓋第三層樓,綜合圖書館、研究圖書館、青齋堂、禪堂、大會堂等建築,像雨後春笋般林立在佛光山最早期開山的一座山頭,一片朝氣蓬勃的氣象。
佛學院的教育分兩大領域,一為生活教育,特別注重五堂功課的訓練,平日課誦禮佛、過堂跑香、搬柴運水,屬於行門的實踐;一為思想教育,學習基礎佛法,八宗兼備,乃至專經專論的深入研讀,建立正知正見,是為解門的積學。除此之外,佛光山系統的僧伽教育對
於實務經驗的培訓特別加強,叢林四十八單的工作樣樣都能一肩挑起。時逢佛光山開山二十週年慶,我們帶著學生從台北行腳到佛光山,三十天走了六百多公里,不管烈日曝晒、大雨傾盆,走出佛子正信的道路。每天雖然要照顧長了水泡的「足下」,但是每個人精神抖擻,
晒出一身健康的古銅色。
師父以托缽行腳的淨財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會,辦公室就設在佛學院之內,我後來接掌執行長。為了接引更多的青年學佛,學院師生集體合作,舉辦了連續三期的「短期出家修道會」,每期十天,男眾要剃去鬚髮,規矩嚴格比照出家眾的三壇大戒,結界、禁語、不捉金
錢珠寶等等,引起台灣媒體的熱烈報導,培育了一批法門龍象,慧寬法師三姐弟、佛光山日本總住持滿潤法師等人,都是第一期的發心菩薩,短期出家後來遂成為佛學院每年必定舉辦的重要活動。在佛學院的香雲堂,我們以「堂」為「廠」,租來機器,自行印刷第一屆「佛
學會考」的試題,仿照大學聯考,嚴禁閒雜人等入闈。
一九八八年冬起,由佛學院承辦了「國際禪學會議」,有台、日、韓、美、義等多國佛學專家學者來發表論文,轟動一時,接著又舉辦一場「佛教學術會議」。尤其後來舉辦的兩場「佛教青年學術會議」,場地就設在佛學院內,並且由佛學院的學生自己策劃、執行所有的議程工作,舉凡會議順暢進行的議事組、接送機的交通組、掛單的住宿組、飲食的典座組等等繁瑣的事項,學生們都一手包辦,從容不迫,完全可以勝任任何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老師們只要站立一旁,悠閒的欣賞自己苦心陶鑄出來的藝術品。
要深入經藏,如何解讀古文是無法避免的關卡。都說文史哲不分家,自己大學讀的恰巧是「中國文學系」,為了加強學生的中文能力,有一段時間,每天傍晚藥石過後三十分鐘,我就搬了一張矮凳,拿著大聲公擴音器,面對大悲殿,坐在四十坡的平台,每日一成語,為學
生講解每個成語的典故及用法,完全自由參加,氣氛輕鬆,是個快樂的師生互動時間。
佛學院保有許多優良的文化,譬如尊師重道的傳統精神,學生自動為老師擦黑板、茶水供養、更換擦手毛巾等等禮節。長幼有序,敬重學長的佛門倫理,學弟看到學長要合掌,行進時要側立讓路,這些良好的教養要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不能斷層。往日每年有三百多位
學生畢業,各個單位的職事們摩拳擦掌,極盡遊說之能事,就像社會企業團體的招攬人才舉動。「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人生一樂也」,多年來佛學院的畢業生們,無論在文化、教育、寺務、國際交流等佛教事業,均能住持一方,弘法五大洲。佛學院是作育佛教英才的搖籃,期盼江山代有人出,文化薪傳,綿延不絕。
佛光山栽培了我/如常法師
我記得師父星雲大師的《往事百語》裡面有一篇文章,叫做〈破銅爛鐵也能成鋼〉,那篇文章是大師講他對人才的運用。事實上我在佛光山的僧團裡面,並不是優秀的,也不是口才好的,學識上也不是頂尖的,可是大師會看到一個人的潛能。我在完成《佛光教科書》的時候,師父對我說:「你有美術的天分,應該再去讀書。讀個研究所。」我說:「師父,我來跟您出家,就是想要跟您學習佛法,並不是想要再去社會上讀書。」師父當時講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你不要學歷,但是信徒要看學歷,所以你還是再去讀個研究所。」我就跟師父說:「我不見得能夠考得上,因為您要叫我跨領域的學習。」
師父想了想,就叫我去找文化政策以及博物館學這個領域的科系。有一天,又是把我帶在旁邊,從口袋抓了一把錢放在我手上,他說:「你現在就剩下半年要考試了,這些錢拿去買考試要讀的書。」我說:「師父,我如果考不上怎麼辦呢?我覺得很對不起您,這個錢也還不了您。」那時候是在二十年前吧,五千塊也不少啊!師父又跟我講一句話:「你也不要太有壓力,你要去考試,只有你知我知,如果沒考上,也沒有人知道,如果考上了,再跟大家宣布好了。」突然間我就覺得輕鬆了,因為沒人知道我要考試。結果我因緣很好,一放榜,我考了那個系所的第六名,大師就很高興,但是他又告訴我:「我不是叫你去讀書的,我是叫你去認識老師跟同學,因為研究所裡面有很多在職進修的,你必須有一些社會的朋友,你才能夠弘法。還有你必須有老師的資源,你才能夠弘法,那個時候我心裡想。師父你怎麼想得這麼遠,我的同學跟我的老師這麼了不起嗎?果不出其然,馬英九時代的文化部長洪孟就是我的老師,台北市立美術館黃光男館長是我的老師,歷史博物館張譽騰館長也是我的老師,等到我做佛陀紀念館館長的時候,這些前輩都是我的老師,所以很快的就把佛陀紀念館跟所有的博物館,跟文化界接上了線。我想二十年前,沒有人會想到星雲大師的遠見,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現在佛館跟台灣文化界的接軌非常順利,也是因為這一段善因緣。師父培養了我,我現在也希望能夠提拔佛光山年輕的一代,不管是出家眾、在家眾。我很感恩師父這樣栽培弟子,事實上我並不具備很好的資質,但是,就像他講的,「破銅爛鐵也能成鋼」。
鍛鍊身心的大叢林/滿謙法師
時間真快,回顧進入佛學院的時間,才一眨眼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當年上山時,剛好欣逢佛光山慶祝開山二十週年紀念,舉行全省行腳托缽圓滿的日子,我從朝山會館雲水寮通過不二門經過五百羅漢,沿著放生池,邁步踏入叢林學院的大門,一路直上六十坡,通往學院的路上滿地落葉繽紛,好孰悉的情景,霎時我的淚眼泉湧,感覺我回
到家了,從此心靈不再迷茫,皈投此生心靈的故鄉。
在佛學院的日子,記憶中最深刻的是,一開學,老師要我們六位同學去大寮典座整學期,原因是過去每週同學輪流典座,同學們煮不出叢林菜,每每讓職事嫌棄連菜都煮不好,因此讓我們這一組要爭氣,一雪前恥,改變職事法師們的印象。
我們這一組真是絕配,因為都是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下廚過,唯一的我會起柴火,每天負責起火,然而同學們挑菜很慢,我的鍋子都要燒焦了,菜還沒挑好更遑論洗菜切菜,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只好放一瓢水入鍋,回頭去幫忙挑菜洗菜切菜,一陣混亂後終於下鍋炒菜完成典座,趕在最後一刻讓行堂完成分發菜色,喝!終於不用整組被罰跪香,因為老師說讓大眾每人延遲一分鐘,一千個人就是殺生一千分鐘,事情嚴重。
每天三餐典座彷彿都在與時間賽跑,也在磨練我的耐心,學習與不同個性的同學相處,如何以最快速度完成色香味俱全的飲食供養大眾,這廚房的典座就是一面「照妖鏡」,照出我的貪瞋癡慢疑,讓我看到自己的問題,進而學習鍛鍊身心,降伏八萬魔軍。
第二學期開學,心中暗暗歡喜終於可以從典座解脫,孰料老師說你去學習「庫頭」工作,庫頭是管理廚房大寮,包括開菜單、叫菜、清點送來的菜,還要管理人事,確定每餐能準時完成,這個工作比起單單典座更加複雜,於是又開始與時間賽跑,在人事時地物中淬鍊,
每天開大靜敲鐘鼓靜坐時,我已經閉眼昏沉,頻頻點頭,與被尊為「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相會。
仔細回想,在佛學院我服務的時間多過上課時間,同學自修我要去典座,晚上藥石後趕著洗衣晾衣,在晚自習之前要回到教室自修,這樣讀書非但沒有比別人少讀,最奇特的是老師交代的功課,我只要到了圖書館,很快就找到書籍,彷彿韋馱菩薩協助提點,讓我很快能完成作業,而因為沒有時間重做筆記,訓練出上課就要專注聆聽,下課前要完成筆記;利用零碎時間背書更是每天分秒必爭的功課,奇怪的是很多原本不孰悉的經文竟然都自然熟悉。
在佛光山是解行並重,師父上人經常教導我們「做中學」,在佛學院的日子,本山經常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或是國際性活動,每天跟隨在師父、長老們身邊看聽,慢慢的也熟悉如何策劃國際會議,對於日後主辦南半球最大寺院||南天寺的落成開光和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四屆第三次理事會會議在雪梨舉行,不感覺吃力,之後在西來寺參加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會議,在桃園講堂擔任住持時承擔第十八屆會議的交通接送,乃至千禧年在南天寺承辦第二十屆的世佛會,一次比一次輕鬆,這都是「在佛學院的日子」的鍛鍊學習。
而在南天寺落成後,有鑑於教育的重要,開始辦南天佛學院,二○○四年師父上人到大洋洲弘法,調弟子回叢林學院擔任院長職務,我從學生角色轉為教育工作者,三年的時光晨鐘暮鼓陪著學生讀書研習,任滿後受調到歐洲,籌建歐洲本山法華禪寺完成後,開始在法華
禪寺開辦法華書院希望能培植更多僧伽人才。從叢林學院到海外辦佛學院,目的是希望把在本山佛學院的學習經驗能夠移植到大洋洲、歐洲。法華書院第三期完成,即將邁入第四期辦學。一路走來,佛學院點點滴滴的美好歲月,竟然是最美的記憶。
有許多人常說:「想當年,我在佛學院的日子……。」對我來說,這一生,生生世世都是在佛學院,只要還沒成佛之前都是在「佛學院」學習,只是佛學院從本山的佛學院擴大到世界的每一角落,佛光的佛學院,是無止盡的學習與淬鍊。
佛學院是此生修道鍛鍊身心的大叢林,感謝「在佛學院的日子」,感謝母校「叢林學院」,讓我成長茁壯。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