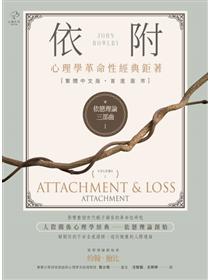我愛她,真的愛。
但若要說我心中沒有一丁點對她的恨,那我就是在說謊。
★橫掃全球9項大獎,諾貝爾文學獎熱議人選
★《華爾街日報》年度最佳選書
★《紐約時報》暢銷榜、《獨立報》外國小說獎決選吳明益/專文推薦
江佩津、朱嘉漢、吳曉樂、李桐豪、言叔夏、郝譽翔、高翊峰、
張亦絢、陳栢青、盛浩偉、湖南蟲、盧郁佳、廖偉棠、顏擇雅
──齊聲讚譽
繼以文學埋葬父親,克瑙斯高揭露自己戀情最深處的情感。
有純潔無瑕的愛情嗎?在與琳達經歷過半年的瘋狂熱戀的日子後,爭執開始浮現。種種日常生活的摩擦,對獨處的渴望、對行動受宰制的不滿,內疚與忿懑揪扯,那累積起來的情緒啃噬著他的心。
「在斯德哥爾摩,僅僅過了半年多一點,一切都不同了。我的心裡充滿了怨恨。戀愛引起的恐懼如此強烈,讓我想要離開,卻又做不到。......我太軟弱了,我愛她。」
「這是無情的美麗。」──挪威《Aftenposten》報
寫作前,當克瑙斯高詢問妻子琳達是否可以將她寫入書中,她只回答了:「別讓我感到無聊。」而當一次長途旅行時,他將完成的手稿交給了妻子,她讀完後喊了他三次。第一次她說,她覺得還行,但她不怎麼喜歡。第二次她告訴他,他們之間恐怕不會再有任何的浪漫可言。第三次,她喊了他一聲後隨即哭了出來。
「有時我認為,自己像是與魔鬼做了一次交易。」
──
《我的奮鬥》為2009-2011間所創作的半自傳小說,共六冊,主題分別為:死亡、愛情、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克瑙斯高在第一部《父親的葬禮》以死亡作為開篇,談論了父親於他的意義及父親悲慘的晚年,他大膽地揭露了自己的生活,直白且露骨的創作風格吸引了無數讀者,光是在挪威的銷量就突破了五十萬冊。
在接續的第二部《戀愛中的男人》裡,他描寫的是如何與第二任妻子墜入愛河的故事。 從追求、戀愛、結婚到生子,克瑙斯高完整地記錄了一段愛情中最熱烈與最黑暗的時刻。
推薦人
江佩津、朱嘉漢、吳曉樂、李桐豪、言叔夏、郝譽翔、高翊峰、張亦絢、陳栢青、盛浩偉、湖南蟲、盧郁佳、廖偉棠、顏擇雅
得獎紀錄與重要事件
2009年 獲得挪威文學界最高榮譽──布拉哥文學獎
2009年 挪威文學評論獎
2009年 挪威NRK P2聽眾獎第一名
2010年 榮獲具有小諾貝爾獎之稱的「北歐理事會文學獎」
2010年 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長名單
2012年 美國《Believer》年度最佳圖書獎
2013年 英國《獨立報》外國小說獎長名單
2013年 《衛報》十大最佳長篇小說
2013年 《紐約客》年度好書
2014年 都柏林文學獎短名單
2014年 美國最佳翻譯圖書獎(由唐‧巴特利特從挪威語譯為英語)
2014年 英國《獨立報》外國小說獎短名單
2015年 榮獲德國《世界報》文學獎
2015年 英國《獨立報》外國小說獎長名單
2015年 《我的奮鬥》改編為瑞典語劇本,並首次於斯德哥爾摩進行公演。
2017年 榮獲以色列耶路撒冷獎
2019年 榮獲瑞典科學院北歐獎
「這呈現出了一種令人痛苦的親密感,這種親密感超越了個人,使得克瑙斯高能夠追尋他更宏遠的藝術理想,他的日常喜悅以及疑慮,竟異常地熟悉。」
──《Time Out New York》
「這是無情的美麗。」──挪威《Aftenposten》
「這史詩般的探索只是前一部分,疲憊不堪的讀者能夠在這裡找回生活。」──《獨立報》
「我不能停下來,我想停下來。我停不下來,只要再一頁就好……我就會去煮晚餐,只要再一頁……」 ──瑞典西博滕報
「有些書在美學上過於強勁,以至於具有革命性,克瑙斯高寫的書就是其中之一。」
──《巴黎評論》
「這本書探討了那些積累於生活中的無盡謎團......克瑙斯高的敘事樸實而謹慎,有時可能漫不經心,但那些他從來不寫。他的核心是美與恐怖皆在真實的生活下共存。他是一位英雄,偉大來自於拋棄了既有的文學典範,他是一位皇帝,赤裸卻輝煌無度,比不過穿上了任何一種華麗的服飾。」
──強納森‧列瑟,《衛報》、《布魯克林孤兒》作者
「我的奮鬥是一部驚人的創作,克瑙斯高發明了一個怪異、善感、殘忍、溫和、虛假、謙遜、自私、聰明與平庸的男人,名為卡爾‧奧韋‧克瑙斯高,他的生活每分每秒地被記錄著。」
──理查.費納根,澳洲《世紀報》、《行過地獄之路》作者
「克瑙斯高擺脫了那些文學花招,突破了語言,引爆了技巧。他的誠實與睿智在當代絕屬稀少。第二部之所以成功捉住了讀者的心,是因為克瑙斯高對理想充滿熱情,而非是只位狡猾的抱怨者。他想要創作偉大的藝術,想要與當代布爾喬亞的協調與同質性相抗衡。」
──詹姆斯·伍德
「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學事業。」──《衛報》
「……形式自由,充滿恐懼,描述密集……自易卜生以來,挪威最偉大的文學巨星。」
──《新政治家》
「《我的奮鬥》已經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文學成就。」──《每日快報》
「《我的奮鬥》出乎意料地引人入勝,細節與親密感交織,製造了住進了另一個人腦中的錯覺......《我的奮鬥》是值得的奮鬥的。」
──GQ
「隨著他每一本書被翻譯成英文,克瑙斯高也鞏固著他在當代不可撼動的重要地位。」
──英國《觀察者日報》
「就像《追憶似水年華》一樣,克瑙斯高的文字有著普魯斯特風格,且他的作品是延展成一系列,這應象徵著是一次文學大事件,在我們的一生中可能不會再出現。 與二十一世紀幾乎所有其他的藝術品都不一樣,克瑙斯高的那本巨著是一項持續不斷的文化活動,我們有幸得以品嚐。」
──傑森·戴蒙德,紐約文化雜誌《絕版》
「在普魯斯特和樹林之間。像花崗岩精確而有力。比真實更真實。」
──義大利《共和國報》
「就像脖上的繩子,刀子刺在心裡。這本書充滿了魔法。整個世界是敞開的……克瑙斯高的地位將來堪比亨里克·易卜生,以及克努特·漢森。
──丹麥《Kristeligt日報》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卡爾‧奧韋能夠充分展現自己並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如今這一能力是很少見的。書寫每個細節的時候,他並不顯虛榮及華麗,彷彿寫作與生活是同時發生的。這裡不會有讓你太過震驚的事件,然而,你會完全沉浸於其中。你是和他一起生活。」
──查蒂‧史密斯,《紐約時報》評論
「我很確信這部作品的成功不僅反應在銷售上──光是挪威就占了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還成為了老年人會在地鐵上讀的,每個新生們都必須預訂、擺在架子上的那種書,走到洗衣房裡,你甚至可以聽見還有房客在那裡討論。」
──《The New Inquiry》
「日常生活變得令人著迷……納斯加德和他的翻譯巴特利特(Bartlett)創造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從不迴避人類的細節。」
──《哈佛評論》
作者簡介: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
挪威最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被譽為「挪威的普魯斯特」。1968年生於奧斯陸。1998年,以首部小說《出離世界》(Ute av verden)獲得挪威文學評論獎。2004年,以第二部小說《萬物皆有時》(En tid for alt)獲得北歐文學獎提名,及國際都柏林文學獎提名。2009年至2011年間,克瑙斯高出版了六部半自傳體小說《我的奮鬥》(Min Kamp),主題分別為死亡、愛情、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此系列完成後,隨即獲得挪威文學界最高榮譽──布拉哥文學獎。2015年9月,更獲得了德國《世界報》文學獎。如今《我的奮鬥》系列已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近年著有《四季四重奏》(暫譯,Årstid encyklopedien)四部曲。
譯者簡介:
康慨
1970年於內蒙古,現居北京,作家和翻譯家。
自1999年起,他為《中華讀書報》工作,任編輯和記者,並為中國和歐洲多家著名的報刊撰寫書評及文化評論。
作為譯者,他已出版的書包括大衛‧薩克斯的《偉大的字母:從A-Z,字母表的輝煌歷史》、卡勒德‧胡賽尼的小說《遠山的回音》和湯姆‧拉赫曼的《我們不完美》。
章節試閱
二○○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夏天已經很長,此時仍然沒有結束。六月二十六日,我完成了這部小說的第一部,此後一個多月,
幼稚園放假了,我們將萬妮婭和海蒂接回家,日子變得更加忙碌。我從來不明白假日有什麼意義,從來感覺不到對假日的需要,總是一心想做更多的工作。可如果我非得如此,那就如此吧。我們本來計畫頭一個星期到木屋裡過,那是去年秋天琳達讓我們買下的,一方面是為了有個寫作的地方,另一方面用於週末隱居,但是三天過後我們就待不下去,回了城裡。把三個小孩和兩個大人放進一個很小的空間,前後左右都是人,除了收拾收拾花園,修剪一下草坪,也就沒什麼事情好幹了,這未必是個好主意,尤其是出發之前氣氛就已經彆彆扭扭。我們在屋外狠狠吵過幾架,想必讓鄰居們頗為受用,而置身於幾百個精心打理的花園和那麼多半裸的老人中間,更讓我感到幽閉恐懼和焦躁易怒。孩子們很快會察覺出這種情緒並加以利用,特別是萬妮婭,她對聲音在高度和力度上的變化幾乎馬上就能做出反應,而如果變化明顯,她就開始做她知道我們最不喜歡的事,沒完沒了,最後必定導致我們大發脾氣。我們本來就憋著一肚子火,此時簡直沒有自衛的可能,只好任由大難臨頭:尖叫,咆哮,一塌糊塗。第二個星期我們租了輛車,向哥德堡外的雪恩島開去,琳達的朋友米凱拉,也是萬妮婭的教母,邀請我們去她伴侶的夏屋同住。我們問她知不知道和三個小孩住在一起是怎麼回事,問她是不是當真想讓我們過去,但她說她是當真的,她已經計畫好了,要跟孩子們一起做燒烤,帶他們去游泳,捉螃蟹,好讓我倆有時間獨處。我們接受了這番好意。我們驅車駛向雪恩島,夏屋位於南挪威般曼妙的鄉間地帶,我們停車入內,用孩子和大包小包把房子填滿。我們原本打算在那裡待上一整個星期,但三天後就把全部家當塞進車裡再度南下,米凱拉和艾瑞克明顯因此得到了解脫。
沒有孩子的人很難明白要應對什麼,不管他們在其他方面表現得多麼成熟與睿智,起碼我自己有小孩之前就是這個樣子。米凱拉和艾瑞克都是事業型的人:我認識米凱拉這麼多年,她所擁有的無一不是文化行業的優越職位,艾瑞克則是某家跨國基金的主管,總部位於瑞典。雪恩島之後他在巴拿馬有個會議,此前他倆還要去普羅旺斯度假,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那些我只是聽說過的地方卻是他們常來常往的居所。我們一家子就這樣殺進去了,帶著嬰兒的溼巾和尿布,約翰到處亂爬,海蒂和萬妮婭連打帶叫,又哭又笑,孩子們從來不在桌上吃飯,從來不聽大人的話,至少我們到別人家串門,真心想讓他們聽話時他們不聽,因為他們知道當時的情形。我們的處境越危險,他們就越不守規矩,夏屋高大而寬敞,但也沒大到或寬到足以對他們視而不見。艾瑞克假裝不在意,他想表現出慷慨和喜歡小孩的樣子,可這和他的身體語言不斷地產生抵觸:他兩條緊貼著肋骨的手臂,他走來走去把各種東西放回原位的動作,還有他眼睛裡那恍惚的神情。他對如數家珍的物事和場地感覺親近,卻與那些剛剛佔據這裡的人相隔甚遠,對待他們時便或多或少地拿出了與對待鼴鼠或刺蝟同樣的方式。我知道他的感受,我也喜歡他。但這一切都是我帶來的,情意相投也就無從談起。他在牛津和劍橋讀過書,還在倫敦金融城做過幾年經紀人,但有一天到海邊散步的時候他和萬妮婭爬了山,竟讓她一個人在前面多走了好幾公尺遠,而他動也不動,只是站著看風景,完全沒考慮到她只有四歲而且沒有預估風險的能力,弄得我不得不抱著海蒂一路跑過去救援。半小時過後我們在一間餐廳落座,我的雙腿因突然運動的刺激而完全僵直,我把一盤小圓麵包遞到他手邊,請他幫約翰拿一點,因為我在給他們找東西吃的時候還得照看海蒂和萬妮婭,他點了點頭,說好,可就是不放下手裡正在讀的報紙,甚至頭都沒抬,根本沒注意到離他只有半米遠的約翰正變得越來越煩躁,最後無望地漲紅了臉,終於放聲尖叫,因為他想要的麵包就在眼前,卻怎麼也夠不著。此情此景激怒了坐在桌子另一端的琳達,我能從她的眼裡看得出來,可她咬緊牙關,不作評論,一直等到大家離開,只有我們自己的時候才說我們應該回家了。現在,我已經習慣了她的喜怒無常,於是當她說要回家時我要她住口,保持克制,別在一肚子氣的時候做那樣的決定。這當然讓她更加憤怒,於是就這麼耗到第二天早上,我們才爬進車裡,動身離去。
藍色無雲的天空,拼布般暴露在風中但仍然美妙的鄉村風景,連同孩子們的快樂,全家老小擠在一輛車裡,不是火車車廂,或者飛機的機艙,那一直是過去幾年的旅行常態,此時這一切舒緩了氣氛,但沒過多久便故態復萌,因為我們得吃飯,而我們找到一家餐館,停車登門,卻發現是一家遊艇俱樂部的內部餐廳。服務員告訴我,我們只要過橋,步行到鎮裡,大約五百公尺,便還有另一家餐館,於是二十分鐘之後,我們上了一座又高又窄、交通繁忙的橋,費勁地推著兩輛童車,饑腸轆轆,出現在眼前的卻只是一片工業區。琳達大發雷霆,兩眼凶惡,我們總是把事情搞成這個樣子,她咬牙切齒地說:別人都不會這樣,我們真沒用,現在早該吃飯了,全家人本來能好好吃頓飯的,現在卻要晾在這頂著大風。一輛輛車嗖嗖駛過,廢氣簡直要把人憋死在這破橋上。我從來有沒有看過別人帶三個小孩出門卻搞成這樣子的。我們沿路走到底,最後是一道鐵門,上面刻著某家保安公司的標誌。鎮裡看上去破敗淒涼,要想到那裡,我們就得繞路,花至少十五分鐘穿過這片工業區。我應該把她丟下,因為她總是抱怨不停,總是想要好的結果,卻從來不做任何事得以轉變局勢,只是抱怨、抱怨、抱怨,從不正視困難的局面,如果現實無法與她的期望相符,不管事情大小,她通通會怪罪到我頭上。唉,正常情況下我們早已分道揚鑣,但是和往常一樣,出於實際的考慮又把我們拉回到同一條船上:我們有一輛汽車和兩輛童車,所以你只好假裝那些說過的話根本沒有說過,推起弄髒的要散架的童車過橋,回到光鮮亮麗的遊艇俱樂部,把它們塞進汽車,給孩子們繫好安全帶,開車駛向最近的麥當勞,結果它就位於哥德堡市中心外的一個加油站,我坐在店裡的長凳上吃香腸,萬妮婭和琳達則在車裡吃自己的那一份。約翰和海蒂睡著了。我們拋開原定的行程,駛向利瑟貝里遊樂園,考慮到目前我們之間的氣氛,這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然而幾個小時過後,我們心血來潮,止步於一個假冒的所謂「童話世界」。每樣東西的品質都差到了極點,我們先帶孩子到了一個小「馬戲團」,裡面有隻狗能跳過膝蓋那麼高的呼拉圈,一位長得像男人的壯碩女士,大概來自東歐的什麼地方,身穿比基尼,把狗剛剛跳的一模一樣的呼拉圈拋到空中,再繞到腰臀上大力搖擺,這招把戲我剛上學時隨便哪個女孩子都會。還有一位和我年齡差不多的金髮男子,穿平底鞋,戴著女式頭巾,腰上成圈的肥肉擠在燈籠褲外,他往嘴裡灌滿汽油,朝著低矮的頂棚噴火四次。約翰和海蒂看得目不轉睛,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萬妮婭的心思都在我們剛才經過的抽獎攤上,在那裡可以抽到玩具,她用力地捏我,不斷問說表演什麼時候結束。我偶爾看一下琳達,她抱著海蒂坐在那邊,眼裡含著淚。出來後,我們走路去小型遊樂場,一人推一輛童車,經過一個游泳池,那裡配有很大的溜滑梯,在最上面的後方,還聳立著一個巨大的轉輪,也許有三十公尺高吧,這時我才問了她為什麼在哭。
「我不知道。」她說,「可是看馬戲團總是讓我覺得很感動。」
「怎麼說?」
「嗯,那麼悲傷,那麼微小,那麼便宜。可是又那麼美。」
「這一場也是?」
「是啊。你沒看到海蒂和約翰嗎?他們完全被迷住了。」
「萬妮婭可沒有。」我說著笑了笑。琳達回以微笑。
「什麼?」萬妮婭問,「你在說什麼,爸爸?」
「我說你看馬戲團時腦袋裡想的全是玩具。」
萬妮婭笑了,跟她和我們分享她做過什麼事時一樣,開心,但也很機警,想知道得更多。
「我怎麼了?」她問。
「你還偷偷捏我。」我說,「還說你想去抽獎的地方。」
「為什麼?」她問。
「我怎麼知道?」我說,「我猜你想要玩具。」
「那我們現在就去嗎?」她問。
「好,」我說,「我們走吧。」
我指了指通往遊樂場的柏油小道,我們可以從小樹林穿過去。
「海蒂也有嗎?」她問。
「她想要就有。」琳達說。
「她想要。」萬妮婭說著,朝童車裡的海蒂俯下身。「你想要嗎,海蒂?」
「想。」海蒂說。
我們不得不花了九十克朗買票,這才讓她們每人手裡拿上一個小布老鼠。烈日灼人,樹下的空氣靜止不動,遊樂場傳來各種喧鬧不休的聲音,混合著貨攤上八○年代的迪斯可音樂,一起包圍著我們。萬妮婭想吃棉花糖,於是十分鐘後,我們便坐到小賣部外的一張桌子旁,黃蜂憤怒且固執地圍著我們嗡嗡不停,陽光滾燙讓糖黏到了所有能碰到的東西上,桌面、童車背面、手臂和手,孩子們氣得大喊大叫,這跟他們剛看見小賣部大瓶子裡裝的螺旋形糖果時想的可不一樣。我的咖啡太苦,難以下嚥。一個髒兮兮的小男孩蹬著三輪車朝我們過來,一頭撞上海蒂的童車,然後滿臉期待地看了看我們。他一頭黑髮,黑眼睛,大概是羅馬尼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要不就是希臘人。他又以腳踏車擠了幾下童車,橫過來擋住我們的去路,然後就站在那,眼睛看著地面。
「我們走嗎?」我問。
「海蒂想騎馬。」琳達說,「騎了再走不行嗎?」
一個長著招風耳,也是黑臉龐的壯漢走過來,提起男孩和他的腳踏車,把他帶到小賣部前的空地,
朝他腦袋上拍了幾下,然後便往他負責操控的機器章魚那邊去了。章魚的腕足上裝有可以讓人坐進去的小筐子,慢慢轉起來便一起一落。男孩騎上腳踏車從入口前橫行而過,但見穿著夏裝的遊客絡繹而來,絡繹而去。
「當然可以。」我說,然後起身,拿過萬妮婭和海蒂的棉花糖,丟進垃圾筒,再推起約翰,他腦袋左搖右甩,正在捕捉各種有趣的東西,我們穿過廣場,走向通往「牛仔鎮」的小路。可這牛仔鎮只是一堆沙子和三個新搭的棚子,掛著牌,分別寫著「礦山」、「警局」和「監獄」,後兩處還貼有「懸賞捉拿,不論死活」的告示。一邊圍有樺樹,還有條坡道,有些青少年在那裡玩滑板,另一邊便是騎馬區,已經關門了。正對著礦山的圍欄內,那東歐女人坐在一塊石頭上,正在抽菸。
「騎馬!」海蒂說,左顧右盼。
「我們要去入口那邊騎驢了。」琳達說。
約翰把自己的水瓶扔到地上。萬妮婭從圍欄底下爬過去,跑向礦山。海蒂看見,也爬出童車跟在後面。我發現警局後有個紅白相間的可樂機,便摸出短褲口袋裡的東西,仔細一看:兩個髮夾,一個是瓢蟲的,一個打火機,三塊石頭,還有萬妮婭在雪恩島撿到的兩個白色貝殼,一張二十克朗紙幣,兩枚五克朗的和九枚一克朗的硬幣。
「我先在這裡抽支菸。」我說,「去那邊。」
我指了指這區最遠處的一棵樹。約翰舉起了雙臂。
「去吧。」琳達說著把他抱起來。「你餓嗎,約翰?」她問道,「天氣好熱,就沒個陰涼處讓我帶他坐下來嗎?」
「那邊。」我指著山頭的餐廳說。它形同火車,櫃檯在機車裡,車廂內擺著餐桌。那裡連個人影也看不見。椅子緊挨著餐桌。
「我這就過去。」琳達說,「然後餵餵他。你能看一下女兒嗎?」
我點點頭,走向可樂機,買了一瓶,坐到樹幹上,點了支香菸,抬頭看著倉促搭建的棚屋,萬妮婭和海蒂正在門口跑進跑出。
「這裡面都黑漆漆的!」萬妮婭叫道,「快來看!」
我抬手搖了搖,似乎很僥倖地滿足了她。她還在用一隻手把老鼠捂在胸前。
對了,海蒂的老鼠哪裡去了?
我抬眼向山上瞭望。它在那裡,就在警局外面,頭朝下紮在沙子裡。琳達在餐廳拉過一把椅子,靠著牆坐下,開始給約翰哺乳,他剛開始還在蹬腿,後來便安靜下來了。馬戲團的女士正在上山。一隻馬蠅在我腿肚子上蟄了一下。我把它拍死了,力道之足,打了它一個稀巴爛。香菸在高溫下味道很差,但我毅然將其吸入肺中,抬眼盯住雲杉的樹冠,陽光捕捉到的綠色何其強烈。又一隻馬蠅在我腿上降落。我不耐煩地趕跑它,站起身,把香菸扔到地上,手裡拿著仍然冰涼的半瓶可樂,走向兩個女兒。
「爸爸,我們在裡面,你繞到後面去,看看能不能透過裂縫看見我們,行嗎?」萬妮婭抬頭瞇著眼睛對我說。
「可以。」我說,然後繞到棚子後面。只聽她們在裡面乒乓作響,咯咯亂笑。我低下頭,靠近一條裂縫,往裡瞧。但是外面的陽光與裡面的黑暗反差過於強烈,我什麼也沒看見。
「爸爸,你在外面嗎?」萬妮婭喊道。
「在。」我說。
「你看得見我們嗎?」
「看不見。你們隱形了嗎?」
「對!」
等她們出來,我假裝看不見她們。直愣愣地盯住萬妮婭的方向,叫她的名字。
「我在這裡。」她揮著手臂說。
「萬妮婭?」我喊道,「你在哪裡啊?快點出來!別再開玩笑了!」
「我在這裡!這裡!」
「萬妮婭?」
「你真的看不見我嗎?我隱形了?」
她聽上去帶著無窮的喜悅,可我也從她聲音裡聽出了一絲不安。就在這時約翰開始尖叫。我抬頭看去,琳達在懷裡緊抱著他站起來了。約翰哭起來不應該是這樣的。
「咦,你在這裡啊!」我說,「你一直都在這裡?」
「是︙︙是啊。」她說。
「你能聽到約翰哭嗎?」
她點點頭,往上看去。
「我們得走了。」我說,「走吧。」
我伸手去牽海蒂的手。
「不要。」她說,「不要牽手。」
「好吧。」我說,「那你進童車裡。」
「不要童車。」她說。
「那我抱你?」
「不要抱。」
我下去取童車。回來時她已經爬到圍欄上面去了。萬妮婭坐在地上。山頭上,琳達已經離開餐廳,正站在路上往下看,一隻手朝我們揮舞著。約翰還在尖叫。
「我不想走路。」萬妮婭說,「我腿疼。」
「你一整天也沒走一步路。」我說,「腿怎麼會疼?」
「我腿麻了,抱我。」
「不,萬妮婭,你說謊。我不能抱你。」
「你能。」
「進童車,海蒂。」我說,「然後我們去騎馬。」
「不要童車。」她說。
「我腿麻—!」萬妮婭說。她最後一個字是尖聲叫出來的。
我感到憤怒,真想一把把她們抓走,一條手臂底下夾一個。那也不會是我第一次拉著又踢又叫的她們走開,無視行人的目光,其他人對於我們上演這小小的一幕總是很感興趣,好像我們戴著猴子面具。
但是這一次,我努力壓住了脾氣。
「你能進童車嗎,萬妮婭?」我問。
「除非你抱我起來。」她說。
「不,你得自己來。」
「不要,」她說,「我腿麻了。」
如果我不讓步的話,我們會在這裡站到第二天早上。別看萬妮婭好像缺乏耐心,一遇抵抗就會放棄,如果她真要對什麼事認真起來的話,就會變得極其固執。
「好吧,」我說完便抱起她放進童車。「你又贏了。」
「又贏了什麼?」她問。
「沒什麼。」我說,「來,海蒂,我們走吧。」
我把她抱下圍欄,幾聲不那麼堅決的「不,不要」之後,我們便邁步上山了,海蒂讓我抱著,萬妮婭在童車裡。我在半路上撿起海蒂的布老鼠,拍掉上面的土,把它塞進網兜。
「我不知道他怎麼了。」琳達在我們走到山上後說,「他突然開始哭。應該是被黃蜂什麼的蟄了。看這裡︙︙」
她拉起約翰的衣服,給我看一個小紅點。他在她懷裡扭動,不停地哭鬧,臉紅紅的,頭髮也溼了。
「可憐的小傢伙,」琳達說。
「我也被馬蠅咬了。」我說,「也許這就是原因。先把他放童車裡吧,這樣比較好走。反正我們現在什麼也做不了。」
我們幫他繫好安全帶,他左右扭動,厭倦地低下頭,還在叫喊。
「我們上車吧。」我說。
「好。」琳達說,「但是我得先幫他換尿布。那邊有個換尿布的兒童屋。」
我點點頭,然後我們開始下山。我們到這裡已經好幾個小時了,天上的斜陽,林間灑落的陽光,不由讓我想起家鄉的夏日午後,我們要嘛開車去島的另一邊,爸爸媽媽下海游泳,要嘛走上居民區下方海灣的山坡。這些記憶在幾秒鐘內便注滿我的腦海,沒有確切哪個事件的外形,而更多只是氣氛、味道、感覺。中午更清亮陽光也更透徹,到了下午就深鬱起來了,一切都有如濃墨重彩。啊,七○年代的一個夏日,在小路上奔跑,穿過濃蔭裡的森林!一頭紮進鹹鹹的海水,游向對岸的耶爾斯塔島!陽光照耀著海邊光滑的岩石,幾乎把它們變得通體金黃。岩石之間中空的地方,生出了挺直的枯草。感受到海面以下的深沉,一旦進入山影,竟是如此黑暗。魚兒一掠而過。然後是我們上方的樹冠,細長的枝條微微顫抖,迎著海面的輕風!薄薄的樹皮,下面是腿一樣光滑的樹,綠色的植物︙︙
「就在那裡。」琳達說著,朝一幢八角形的木制建築噘了噘嘴。「你能等一下嗎?」
「我們慢慢走。」我說。
圍欄裡的雜樹叢中,有兩個木雕的地精,這就是此地可以名正言順地叫做「童話世界」的原因了。
「快看,通彭!」海蒂叫了起來。「通彭」︵Tompen︶正確的發音是「通滕」︵Tomten︶,也就是地精。
她對地精念念不忘已經很長時間。直到春天,她還在指著聖誕前夜地精出現的門廊說「通彭要來了」,玩地精給她的禮物時,她總要提前對禮物來自何處做一番說明。不過,通彭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還很難講,因為聖誕節過了以後,她在我的衣櫥裡發現地精的裝扮時,並沒有表現出絲毫的驚訝或難過。當時我們什麼也沒說,她只是對著衣櫥喊「通彭」,好像那是他的更衣間似的,我們遇見白鬍子老流浪漢在屋外廣場上閒盪的時候,她也會從童車裡站起來,撕心裂肺地喊「通彭」。
我俯身向前,親了親她胖嘟嘟的小臉蛋。
「不親!」她說。
我大笑起來。
「那我親你行不行,萬妮婭?」
「不!」萬妮婭說。
一道稀疏但前後相連的人流經過我們身邊,大部分人身穿夏裝—短褲、汗衫和涼鞋—有些人穿著運動褲和運動鞋,胖子的數量驚人,衣著光鮮的幾乎一個也沒有。
「我爸進監獄了!」海蒂歡快地大叫。
萬妮婭在童車裡轉過頭。
「沒有,爸爸沒有進監獄!」她說。
我再次大笑,然後停住了腳步。
「我們得在這裡等等媽媽了。」我說。
你爸進監獄了,幼稚園的孩子相互之間經常這麼說。海蒂把它理解為巨大的恭維,於是想拿我吹牛的時候便常常這樣講。據琳達說,上一次我們從木屋回來時,海蒂就是這樣對公車上一位坐在她們身後的老太太說的。我爸進監獄了。因為我不在場,而是帶著約翰站在公車站等,所以這句評論便久久地回盪在空中,無人加以爭辯。
我低下頭,用袖子擦去頭上的汗。
「我能再買張票嗎,爸爸?」萬妮婭問。
「不行。」我說,「你已經贏到玩具了。」
「好嘛,再一個嘛。」她說。
我轉過頭,看見琳達走過來,約翰端端正正地坐在童車裡,戴著遮陽帽,看上去滿開心的。
「沒事吧?」我問。
「嗯,我拿涼水洗了蟄過的地方。不過他累了。」
「待會上車他就會睡覺的。」我說。
「幾點了?」
「三點半吧。」
「八點到家?」
「差不多。」
我們再次穿過小型遊樂場,經過海盜船,其外觀慘不忍睹,後面的梯子,有幾個獨腿或是獨臂漢子的擺設,裹著頭巾,揮舞刀劍的模樣;然後另一區設有美洲駝和鴕鳥的裝飾,一小塊鋪過的地面,有些孩子在上面開四輪車。終於到了入口區,這裡簡直像障礙訓練場,其實只是幾根木頭,三三兩兩的木擋板,中間掛了網,還有一個帶彈跳床的高空彈跳架和騎驢用的跑道。我們在跑道邊停下,琳達抱起海蒂,帶她去排隊,讓她戴上頭盔,而萬妮婭和我則帶著約翰站在圍欄邊觀看。
跑道上一次有四頭驢,分別由家長牽著。跑到不過三十公尺,但大部分動物卻走得很慢,因為它們是驢,不是小馬,驢子一想休息便停下不動。絕望的家長使盡全身力氣拉扯韁繩,但這些動物就是不肯妥協。他們徒勞地拍弄驢子的側腹,這些蠢驢照舊紋絲不動。有個孩子在哭。收票的女人不停喊叫,向家長提供建議。使勁拉啊!使勁點!快拉,它們不怕痛!用力!就是這樣,對!
「看見了嗎,萬妮婭?」我說,「驢都不想動。」
她哈哈大笑。她高興,我就高興。與此同時,我也有點擔心琳達會怎麼樣面對這種僵局;她的耐心不比萬妮婭多多少。但輪到她時,她卻沉著應對。只要驢子一停下,她就站過去,背對著驢肚子,嘴裡發出一連串歡快的聲音。她是騎馬長大的,馬在她的生活中曾經非常重要,肯定是這一點讓她知道現在該做什麼。
海蒂跨騎在驢背上,喜氣洋洋。當驢子對琳達的把戲不再買帳的時候,她就特別用力地拉著韁繩,彷彿絕不允許它有半點固執。
「你真是個好騎手!」我對海蒂大聲說道,又低頭看看萬妮婭,「你想試試嗎?」
萬妮婭堅定地搖搖頭,扶正眼鏡。一歲半的時候她騎過小馬,我們搬到馬爾默的那個秋天,她兩歲半就開始上騎術學校。地點在人民公園的中心地帶,一座淒慘而潦倒的訓練廳,地面鋪著木屑,這對她而言堪稱絕佳的經歷,她全神貫注,下課後還要繼續談論。她在掉隊的小馬身上坐得筆直,讓琳達牽著一圈又一圈地轉,有時我自己陪她上課,便由那些好像在馬校長大的十一二歲的女孩子牽馬,一位指導老師在場中央來回走動,做著講解。老師講的萬妮婭不一定全能聽懂,不過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馬和馬所處的環境帶來的經驗。馬廄,在草垛上養育小貓的母貓,當天下午誰要騎哪匹馬的名單,她挑選的頭盔,馬被牽進訓練廳的那一刻,騎行本身,此後她在咖啡廳要的肉桂小麵包和蘋果汁。那是一週當中最重要的事。但第二年秋天再上課時出現了變化。他們換了一位新老師,四歲的萬妮婭看上去年齡要大一些,於是開始面對一些她完成不了的要求。雖然琳達跟老師談過,情況卻沒有好轉,得去上課了,萬妮婭卻開始抗議,她不想去,一點也不想,最後我們罷手了。現在看見海蒂在公園裡騎小驢子,就算沒有任何要求,她也不想騎。
我們還替她報名參加過一個遊戲小組,孩子們有時在一起唱歌、畫畫,或隨意消磨時間。她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們要畫房子,萬妮婭把草地塗成了藍色。遊戲小組的負責人走到萬妮婭身邊說,草地不是藍色而是綠色,她能再畫一遍嗎?萬妮婭撕碎了自己的畫,還表現出生氣的樣子,讓家長們紛紛側目,並為自家孩子很有教養而大感慶倖。萬妮婭有很多特點,但首先她很敏感,而這種態度正在形成並且固化的事實讓我擔心。看到她成長也改變了我對自己童年的看法,原因不在於質而在於量,在於你單獨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大量的時間。那麼多個小時,那麼多天,那麼多突然出現又安然度過的狀況。對我自己的童年,我只記得很少的一些事件,我認為它們都很重大,但現在我懂了,它們只是一小部分,還有大量的事情,它們的意義已被沖刷殆盡,因為我怎麼能知道那些存放在我腦海裡的特殊事件,而不是那些我什麼也記不起來的事情才是決定性的呢?
二○○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夏天已經很長,此時仍然沒有結束。六月二十六日,我完成了這部小說的第一部,此後一個多月,
幼稚園放假了,我們將萬妮婭和海蒂接回家,日子變得更加忙碌。我從來不明白假日有什麼意義,從來感覺不到對假日的需要,總是一心想做更多的工作。可如果我非得如此,那就如此吧。我們本來計畫頭一個星期到木屋裡過,那是去年秋天琳達讓我們買下的,一方面是為了有個寫作的地方,另一方面用於週末隱居,但是三天過後我們就待不下去,回了城裡。把三個小孩和兩個大人放進一個很小的空間,前後左右都是人,除了收拾收...
 6收藏
6收藏

 15二手徵求有驚喜
15二手徵求有驚喜



 6收藏
6收藏

 15二手徵求有驚喜
15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