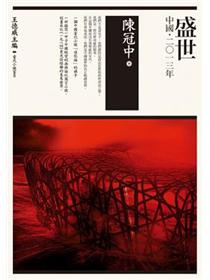自傳的改寫、神話的變形、創傷的揭露、疾病的隱喻、離散的困境……文學扣連生命的永恆命題,從張愛玲溯回《紅樓夢》,俱是愛情
張愛玲上追紅樓,下開後現代,她一個人走了好幾代,並以愛情將小說推向最前衛之處。
周芬伶三十年張學與紅學研究集成
追溯情典文本的生成
張愛玲如何在抒情傳統中別開生面成為聖手
以張愛玲為核心,上溯兩百年前《紅樓夢》的情癡幻愛,下推現代文學中創傷、疾病、流亡離散的女性書寫脈絡,深度分析張愛玲一生不斷變體轉譯的自傳書寫與古典小說的互文交織,她彌合古典與現代的分裂,追溯傳統,將之現代化,而愛情這亙古不衰的主題,正是她把握的關鍵,愛情是她最大的訴說,也是她自身的代名詞。
張愛玲曾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是她一切的來源。
她詮釋經典,經典塑造她,她提出愛情,愛情也籠罩她,因此成為愛情小說「教主」。追溯張愛玲的一生,很複雜也很單純,不斷遷移與流動,造成寫作題材與文風轉變︰國籍與身分轉變,讓她越走越在主流之外;家族陰影與才子佳人傳奇,成為她書寫不盡的泉源。
她的才子佳人只是表面,骨子底是虛無的,非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說,創造出新的情典。穿過世情,洞視愛情的荒謬本質。
我的永不不是永不,我的永遠是永遠,我的愛是自然死亡,但自然死亡也可以很磨人和漫長。──張愛玲
◎邪惡母親與純真/世故的女兒一向是張作品中重要的主題,因此《雷峰塔》是少女成長故事,她逃離父親奔向母親,也是從傳統逃走向現代,《易經》則是切斷母子臍帶回返家園/樂園的旅程。小女孩成為救難英雄,她解救自己與同學,逃出戰場,回返上海。
◎文學的傳承道路如此不可思議地發生在宅世代、厭世代身上。所謂七年級說「張愛玲已不是問題」,是說已經可以越過去,我們卻在林奕含身上發現新的可能。誘姦與性侵的問題層出不窮,也許異女的問題一直沒解決,女權提升也是假象,訴說女性被父權與語言的作品並未終止。
◎文學的更替,不會是一刀切,或走極端,或許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就是一刀切與走極端的例子,張愛玲不是國故派或復古主義者,她跟李維史陀或榮格一樣,是古老的象徵學者,認為人類的進步只是幻覺,只是原地踏步,或是變化而已。
作者簡介:
周芬伶
屏東人,政大中文系畢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以散文集《花房之歌》榮獲中山文藝獎,《蘭花辭》榮獲首屆台灣文學獎散文金典獎。《花東婦好》獲2018金鼎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作品有散文、小說、文論多種。近著《張愛玲課》、《雨客與花客》、《花東婦好》、《濕地》、《北印度書簡》、《紅咖哩黃咖哩》、《龍瑛宗傳》、《散文課》、《創作課》、《美學課》等。
章節試閱
張愛玲自傳改寫與雜種神話
二十一世紀初,離張愛玲過世十年之後,由宋以朗經手出版了張愛玲從一九五○年末期到七○年末期的重要著作,依年代順序是英文版《易經》在前而中文版《小團圓》之改寫在後,說明張在美國文學創作努力並未交白卷,論者謂之「張愛玲自傳小說三部曲」。一九五七年張將滿四十歲,母親過世,她想以自己家族的故事進攻美國市場,就像當年她以〈金鎖記〉奠定文學地位,這在她離開大陸前仍在進行電影改編的作品,可能是她最滿意的作品,之後一再改寫為英文小說《Pink Tears》與中文小說《怨女》;另一方面進行自傳小說的大部頭書寫,拋棄了前期小說的戲劇性、香港時期的政治性,轉而朝向自我審視的夾縫書寫,這些小說難讀且評價兩極,大多具有影射意義,有優有劣,有人拿它與《孽海花》相比,令人想到薩伊德所指的「晚期風格」;另外,書中人物與母親關係為小說的主軸,其中重大的轉折點發生在香港,她在香港大學因成績優異得到自信,她的上進與母親的墮落為重要對比與衝突點,從此母女切斷臍帶,並以雷峰塔倒塌作為父權倒塌的象徵,以及改裝白蛇神話與女仙故事,具有移民的變種神話意涵,從自傳散文到女英雄神話,在這場親情災難中她完成她自己,卻給讀者帶來許多疑惑,果真如朱天文所說煉金成了灰嗎?本文從她的後期的自傳書寫討論其晚期風格,說明在上海—香港—美國之間往復帶來的風格變異。
前言
彷彿很舊,其實也有些新意,細看真的是舊了,畢竟那都是上世紀中葉的事了。本篇討論的自傳焦點在其生命史與家族史上,其他的自傳性散篇僅能省略,自傳為AUTO-BIO-GRAPHY,指的是「自我生命書寫」,然亦非依「自傳契約」嚴格定義的自傳,僅集中討論張愛玲具有生命史意義的作品上,尤其是一九五七年之後的自傳書寫。
這些作品引起的討論甚多,然肯定中文書寫的《小團圓》居多,對《雷峰塔》、《易經》,持失望與懷疑態度的不少,雖也有極力為她辯護的,然也難說服大部分讀者,我自九○年代初期發表張愛玲的論文開始,一直肯定她在女性文學上的開拓,為華文作家少有的奇才,然讀《雷峰塔》、《易經》時卻有強烈的幻滅感,覺得這是她畢生最大的敗筆,其刻薄病態令人反感,曾有結束討論這作家的念頭。
時經兩年,再細讀她晚期的作品,覺得一部敗筆不能全面否定作家畢生的努力,也不能獨立拿出來評斷,或許這是作家移民後企圖改變風格的艱辛努力過程所碰到的挫折,自傳書寫為她在美國創作的最大工程,費時三十餘年,而其中經過退稿與擱置,她也自知作品有問題,這些自傳書寫在傳記上的意義多過文學上的意義,在雜種文化認同上的意義多過美學上的意義,不瞭解晚期的張愛玲,對她的理解只會是片面的。這種風格的改變是否如薩伊德所言「在他們的晚年作品中並非表現得成熟與圓融,反而表現得更孤僻,更不守常規,展現了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一種刻意不具建設性的、逆行的創造。」1,以逆行的創造或者移民作家的困境視之,或許能解開多重心結。
鏡與影—自傳書寫與現代性
有關張愛玲的自傳書寫,是一個重覆經驗不斷增刪改寫的過程,最早是在散文中明白表露自己的成長,主要是與父親的衝突並逃家,對於母親則多所保留,那是一九三八年的英文散文〈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與一九四四年的《流言》中的諸多篇章,那時與母親的關係尚未決裂,移民至美國之後,接續長達五十幾年的自傳書寫,由自傳散文、小說至一九九二年《對照記》才算終止,這讓她戀戀不捨的題材,她用了近一輩子書寫,以自傳始也以自傳終,其中經歷文體與手法的轉變,由實寫變成虛寫,再由虛寫變成實寫。討論其中的演化或可說明一個作家如何割斷臍帶走向孤獨的過程,也可說明移民作家的離心書寫,是如何崎嶇而坎坷的路程,其轉折大約如下:
〈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一九三八→〈私語〉一九四四→《雷峰塔》一九五七起筆→《小團圓》一九七五起筆→《對照記》一九九二
〈燼餘錄〉一九四四→《易經》一九五七起筆(書中描寫母女決裂在香港一九四○,母因間諜嫌疑被扣押)→《小團圓》一九七五起筆(書中描寫母女決裂在上海一九四八)→《對照記》一九九二
從上海到香港,又從香港回到上海,二度從上海到香港,直到美國,她寫母女決裂的情事由委婉到酷烈到慘不忍睹,這中間過了近四十年,寫法不同,時間也改了,書寫過程時間很長,空間都在香港、上海、美國之間往復,講的重點都是同樣一件事,女兒與母親之間複雜的情感與決裂過程,夾雜紛繁的家族史與不堪的情史。由自傳散文二度改寫為自傳小說,最後濃縮為圖文對照的自傳散文,甚少有一部作品如此被作者一再改寫轉譯,其複雜性不亞於曹雪芹《紅樓夢》,不同的是增寫與續書者都是張愛玲,這種歧異與互文性,在現代文學史上可謂少有,成不成功是一回事,探討其中的轉變心理,或可說明其現代意義。
把一九五七年作為分水嶺,之前的自傳書寫以散文為主,之後以自傳小說為主,最後以圖文並置的《對照記》為結束,文類與寫法都不同,代表不同時期的創作心理與美學。
張愛玲的自傳書寫或以散文或以小說或以電影劇本為載體,雖然小說與劇本難免虛構,不能以傳記視之,自傳小說可分為求真的自傳小說與詩化的自傳小說。求真的自傳小說接近自傳,但它並不在意事實的真實,而注重人在「現實」中的意義,因此由主角牽出時代背景與社會變遷,英文版《雷峰塔》、《易經》即屬於此類,然這時代性與社會性屬於「時代紀念碑」的作品並非張愛玲擅長,故而背景模糊不清,這類自傳小說雖明白地進行虛構,有時連作者都「無從分辨藝術的虛構與生活的真實」;詩化的自傳小說比求真的自傳小說更細膩更敏感更浪漫,《小團圓》兼有求真與詩化自傳小說的特點,也可說是自傳小說的新寫法,在七○年代台灣中文作家在西方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中交戰時,張愛玲選擇走向自己。
有人說張愛玲在美國沒有新的創作,我們只能說她沒有像《傳奇》、《半生緣》那樣的創作衝動,而具有創新意義的自傳小說的創作衝動。人們只知道她極保護隱私,卻不知她的自傳書寫從未間斷,而且更赤裸更坦白,對讀者傾訴之心從未改變。
這種走向自己的衝動,可能是流亡作家對自我身分的再認定,或對過往創傷的療癒書寫;或對他人誤解的辯護。對於一個習慣對創傷與指控無言以對的作家,書寫自我像一面鏡子,照映自己,也照映他人。至於投射出許多陰暗的影子,或讓人不忍卒睹的往事,那只有哀矜而勿喜。
從意識層寫往個人潛意識層,再觸及集體潛意識;從對父母的控訴到情感的宣洩,再觸及內心的良知與審判,對她來說是她一生最大的課題。
一切在潛意識底下進行,所以寫得影影繪繪,人性的黑暗如猜忌、復仇、背叛、淫亂與人性的微光如天真、付出、犧牲一明二暗相輝映,如果之前的自傳書寫是分散性與實驗性的,《小團圓》可說是集大成之作,《對照記》則是極度濃縮與刪減,充滿「物質感」,她選擇讓照片來說明。
她的人性觀與創作美學是採「一明二暗」的寫法,前面寫港大的學生宿舍「這些板壁隔出來的小房間『一明兩暗』」,一明二暗是房子的隔間,也可是一種空間與人性隱喻,一般公寓型三開間的房子,都是以一明二暗的形制呈現,明的是開放的公共空間,暗的是隱密的私人空間,明也是可見的事物表面,暗是看不見的心靈側影。為什麼是二暗?也就是暗大於明,倍於明,一明是一切事物帶有的希望面,一暗是人性本身的陰影面,二暗是小說家的心靈暗影,也就是創作者擅長的猜忌與推測,讓事件不清晰且布滿小陰影,如她書中所說:
回憶不管是愉快還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種悲哀,雖然淡,她怕那滋味。她從來不自找傷感,實生活裡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這麼想了想,就像站在個古建築物門口往裡張了張,在月光與黑影中斷瓦頹垣千門萬戶,一瞥間已經知道都在那裡。2
在這座回憶的古建築中,被月光與陰影充滿,連在狂喜時有強光也有陰影,在淺水灣飯店看母親回來:「對海一隻探海燈忽然照過來,正對準了門外的乳黃色小亭子,兩對瓶式細柱子。她站在那神龕裡,從頭至腳浴在藍色的光霧中,別過一張驚笑的臉,向著九龍對岸凍結住了。那道強光也一動都不動。他們以為看見了什麼了?這些笨蛋,她心裡納罕著。然後終於燈光一暗,撥開了。夜空中斜斜劃過一道銀河似的粉筆灰闊條紋,與別的條紋交叉,並行,懶洋洋劃來劃去。不過那麼幾秒鐘的工夫,修女開了門,裡面穿堂黃黯黯的,像看了迴腸蕩氣的好電影回來,彷彿回到童年的家一樣感到異樣,一切都縮小了,矮了,舊了。她快樂到極點。」那時她對母親還有愛。全篇光與影的描寫很多,像電影中的燈光技術,它能改變作品的底色,增強人性的層次,內心的寫照,還有氣氛。轉場也更為自由,其中有許多蒙太奇剪接,跟她早期重視色彩已有不同。
《小團圓》在結構上夾雜著三個家族的故事和一樁離奇的華人殺妻命案,這簡直是推理小說的故佈疑陣了。小說結構也採一明二暗的結構:明寫盛家,暗寫卞家、竺家;明寫九莉,暗寫三姑二嬸;明寫之雍,暗寫燕山、緒哥哥;明寫異性戀,暗寫同性戀、雙性戀、亂倫……考據古典小說近二十年之後的張,已是學者型作家,對於古典小說的明暗、映襯、夾縫、閃躲技巧可說十分偏愛,它讓小說難讀,但更耐讀。
在一個沒有恥感的時代,作家寫出她的恥感,或對恥感也麻木的感覺,她的良知不斷檢視過往的一切。
她逐漸明白過來了,就這樣不也好?就讓她以為是因為她浪漫。作為一個身世淒涼的風流罪人,這種悲哀也還不壞。但是這可恥的一念在意識的邊緣上蠕蠕爬行很久才溜了進來。
那次帶她到淺水灣海灘上,也許就是想讓她有點知道,免得突然發現了受不了。
她並沒想到蕊秋以為她還錢是要跟她斷絕關係,但是這樣相持下去,她漸漸也有點覺得不拿她的錢是要保留一份感情在這裡。
「不拿也就是這樣,別的沒有了。」她心裡說。
反正只要恭順的聽著,總不能說她無禮。她向大鏡子裡望了望,檢查一下自己的臉色。在這一剎那間,她對她空濛的眼睛、纖柔的鼻子、粉紅菱形的嘴、長圓的臉蛋完全滿意。九年不見,她慶幸她還是九年前那個人。
蕊秋似乎收了淚。沉默持續到一個地步,可以認為談話結束了。九莉悄悄的站起來走了出去。
到了自己房裡,已經黃昏了,忽然覺得光線灰暗異常,連忙開燈。
時間是站在她這邊的。勝之不武。
「反正你自己將來也沒有好下場,」她對自己說。3
自我省視與批判最嚴厲的是自己,就像她自己說的:「我在《小團圓》裡講到自己也很不客氣,這種地方總是自己來揭發的好」4,這樣勇敢地面對自己,令人想到她的祖父張佩綸,因中法之戰之恥,死前自擇墳地對後人說:「死即葬我于此,余以戰敗罪人辱家聲,無面目復入祖宗丘壟地。」5,張愛玲的自傳書寫,也可說譴人譴已的漫長過程。
從控訴、揭發、罪責到傾訴—文本轉換與心理轉折
每一次的改寫,都代表她心理的轉折,對於有「增刪癮」的作家,克里斯多娃利用互文性與「演進批評」研究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認為他花十多年不斷刪改修訂作品,其潛意識是為隱藏其同性戀的傾向;而張愛玲長達五十多年的自傳改寫,除了表達愛的匱乏與愛的死亡,是否有更深一層的心理因素?從開頭的開門見山式的寫法,越寫越隱晦,越是夾纏,這裡面是否也反映她對文學手法的追求,陷入某種困境?
早在一九三八年她逃出父家便在報紙上刊登〈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控訴」與「罪責」父親對她的囚禁,之後改寫成〈私語〉,「傾訴」的意味較濃,作者將原始經驗化為散文,對叛離父親的過程描寫較多,對母親尚有浪漫的愛,因其委婉冷靜的筆調,加以文字意象較講究,故能引起廣大共鳴。之後的空白與幽居,讓人誤以為她已將自己藏起來,事實上她從未停止「傾訴」自己,只是被宋淇夫婦與自己扣下來,有些作品連她自己這關也過不了,如《雷峰塔》與《易經》、《小團圓》皆為「揭發」、「罪責」之作,前者擱下,後者仍想發表,她到過世之前仍未放棄修改《小團圓》,可見她的自傳書寫也是未完,跟《紅樓夢》的命運相似,五易其稿,可能仍是殘稿的狀態,張是紅學作成書研究的引領者,如果把她的自傳書寫的成書過程作比對,將可發現天才的橫剖面與命運沉浮。
一九五七年起改寫的《雷峰塔》與《易經》,雖擴寫為家族故事,著重家族尤其是母親的變態描寫,也隱含作者的病態,可說是最失敗的版本,主要是「控訴」與「罪責」的意味過於強烈,一九五七年黃逸梵過世,她將母親寫入小說,這時她住在東岸的小城嚮往著大城市,故而書中的場景都是城市:天津、上海、香港……她在天津生活六年,從兩歲到八歲,那六年中,母親出國,她跟奶娘較親,她會對她亂發脾氣,張干很是護衛她,她卻說:「那是她的事業。」總之活在沒有愛的家庭裡,她對感情充滿懷疑。
天津的童年描寫,補充新的傳記資料頗多,讓我們更加瞭解她二歲至八歲的生活,天津這城市對她來說是在小公館與堂子,新房子與老家的世界,在姨太太未進門前,姊弟與奶媽相依為命,每天到公園散步時,有時她奔跑著,自己好像被切成兩半:「琵琶忍不住狂奔起來,吞吃下要求她將自己切成兩半,占據吞噬自己的廣原。」
在這個城市,對她而言是過於擁擠與複雜的城市,讓她自己也分裂了,如同她明明不願背叛母親,當姨太太問她喜歡媽媽還是喜歡我,她回答的是「喜歡你」,她常覺得自己是別人,「像她在公園看見的黃頭髮小女孩,只是作了個夢,夢見自己是天津的一個中國女孩」,這如夢般的感覺,以及看己像是別人的視角一直貫串她的人生與書寫,說她無情,只是疏離。
上海對她而言更是充滿戲劇性的城市,離開大陸前在上海停留最久,她需要大城市作舞台才能成名,也喜歡城市生活,時尚與櫥窗,電車與市聲,還有出版活躍作家群集,這裡有她的一舉成名,青春婚戀與尚稱優渥的生活,她當然愛上海。
上海是她的舞台,天津像後台,前台的戲好看,後台像個舊夢。
不相信家人的情感,她倒十分依賴朋友,朋友越是精采她的想像越豐沛,根本她是靠想像生活,不需跟人太多接觸,只需有個他在哪裡可以供她想像,一般的社交是完全不需要的。她曾為胡到過南京,那也是祖父母的舊居,令她把隔代愛情聯想一起,因此覺得這是種神祕的傳承,格外香豔,這又說明為什麼《十八春》的愛情場景發生在上海與南京兩座城市中,因為那時她的人與心魂都在這兩座城市,她只會寫城市。
張的成名以上海與香港兩座城市為舞台,《雷峰塔》與《易經》主要也是以這兩座城市為舞台,尤其是香港,隨著作者的遷移,她的觀點不斷轉移,由兒童的眼光對照成人世界的複雜、病態,她自己對這寫法也充滿懷疑,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給宋淇夫婦的信中說:
《易經》決定譯,至少譯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夠長,或有十萬字。看過我的散文〈私語〉的人,情節一望而知,沒看過的人是否有耐心天天看這些童年瑣事,實在是個疑問。下半部叫《易經》,港戰部分也在另一篇散文裡寫過,也同樣沒有羅曼斯。我用英文改寫不嫌膩煩,因為不比他們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說更「長氣」,變成中文卻從心底裡代讀者感到厭倦,你們可以想像這心理。6
作者也明說是舊文重寫或擴寫,寫此書時雖然覺得「有滋有味」,她自己也覺得不妙,果然始終賣不掉,讓她灰了心,此後很少提起,在賴雅的日記中她因此沮喪到臥床不起7,只靠營養針補給,作為初至美國的大企圖之作,從此湮沒半個世紀才見光。
當時她住在彼得堡,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英國有信來告知母親的死訊,並寄來一只大箱子,是隨著母親搬遷的遺物,一直到四月二十三日,張才打開箱子整理遺物,賴雅看著黃逸梵的照片說:「照片就像一部小說」,也許是這樣,讓張此時期的自傳書寫更多地集中在母親身上,但此時的寫法如新喪母親的女兒,無助且天真,連她也覺得:「裡面的母親和姑母是兒童的觀點看來,太理想化,欠真實。」
太理想化或欠真實也許並非此書的缺點,而是剛從散文改為小說,材料還是不足以撐起大部頭的小說,增添的人事物紛雜,故事卻不吸引人,母親的形象過於負面,令人不忍卒睹。看來母親的死並未弭平心中裂痕,這時的自傳書寫較傾向宣洩,並夾雜「控訴」與「罪責」;正如她所說:「藉寫作來宣洩─於是其他人就會分擔我的記憶,讓他們記住,我就可以忘卻。戀愛上的永不與永遠同樣的短促嗎?但我的永不不是永不,我的永遠是永遠,我的愛是自然死亡,但自然死亡也可以很磨人和漫長。」8
這句話表明幾個重要理念,一是藉宣洩以忘卻,一是她的永遠是永遠,一件事不管時空多遠都會永遠;而她的愛死得自然卻非常磨人與漫長,宣洩與傾訴差不多,所差的是宣洩帶著攻擊性,傾訴只是訴說本身。
這說明為何同一件事反覆說反覆寫,都不厭倦,正因對她而言是永遠,那是愛的死亡過程,如此磨人與漫長。
(未完)
張愛玲自傳改寫與雜種神話
二十一世紀初,離張愛玲過世十年之後,由宋以朗經手出版了張愛玲從一九五○年末期到七○年末期的重要著作,依年代順序是英文版《易經》在前而中文版《小團圓》之改寫在後,說明張在美國文學創作努力並未交白卷,論者謂之「張愛玲自傳小說三部曲」。一九五七年張將滿四十歲,母親過世,她想以自己家族的故事進攻美國市場,就像當年她以〈金鎖記〉奠定文學地位,這在她離開大陸前仍在進行電影改編的作品,可能是她最滿意的作品,之後一再改寫為英文小說《Pink Tears》與中文小說《怨女》;另一方面進行自傳小說...
目錄
當代大觀園
張愛玲自傳改寫與雜種神話
禁果與樂園──《小團圓》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的文學與疾病雙重隱喻
病恙與凝視──海派女性小說三大家的疾病隱喻與影像手法
生活性與空間性──張愛玲的香港書寫與晚期風格
南北合──宋淇與張愛玲喜劇電影劇作
移民女作家的困與逃——張愛玲〈浮花浪蕊〉與聶華苓《桑青與桃紅》的離散書寫與空間隱喻
穿越紅樓夢
「情典」文本的生成──張愛玲「自傳小說三部曲」與《紅樓夢》的互文與新異
「情典」文本的傳播──張學與紅學的交織中的愛情主題
「情典」文本的擴大──《紅樓夢》兩書合一後的複合角色與排行序列
擬古或續書──論《劉心武續紅樓夢》及續書問題
當代大觀園
張愛玲自傳改寫與雜種神話
禁果與樂園──《小團圓》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的文學與疾病雙重隱喻
病恙與凝視──海派女性小說三大家的疾病隱喻與影像手法
生活性與空間性──張愛玲的香港書寫與晚期風格
南北合──宋淇與張愛玲喜劇電影劇作
移民女作家的困與逃——張愛玲〈浮花浪蕊〉與聶華苓《桑青與桃紅》的離散書寫與空間隱喻
穿越紅樓夢
「情典」文本的生成──張愛玲「自傳小說三部曲」與《紅樓夢》的互文與新異
「情典」文本的傳播──張學與紅學的交織中的愛情主題
「情典」文本的擴大──《紅樓夢》兩...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收藏
2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



 2收藏
2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