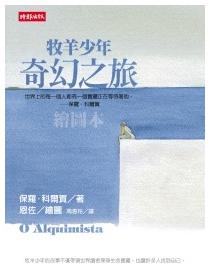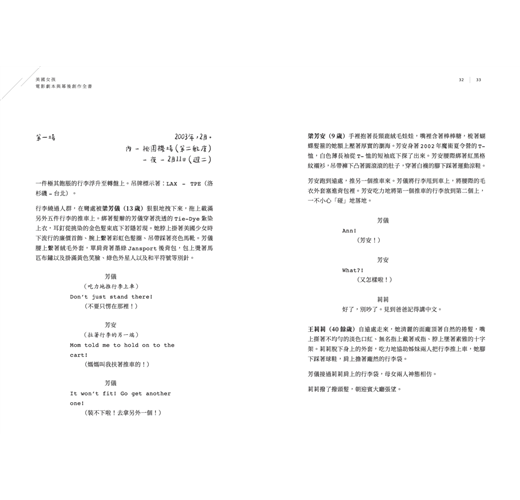給家人的情書
——導演、《美國女孩》監製.林書宇
「我真的受寵若驚。謝謝書宇,for everything。」
收到鳳儀傳來的訊息時,我正在會議中,一個故意安排在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時的會議。因為很在乎,所以我習慣選擇讓自己忙碌而不去面對,畢竟當下看了也改變不了結果。看到訊息的我趕緊回,「我沒有在看,發生了什麼事?」電話立馬響起,包括最佳劇情片,《美國女孩》入圍七項大獎!我們開心地互相表示驚訝,也恭喜彼此,匆忙掛了電話後,我繼續回到還沒結束的會議。接著,手機傳來一則則的祝賀簡訊,而除了祝賀也開始有更多人好奇問起一個讓我認真思考與回憶的問題,「你怎麼會擔任阮鳳儀導演的監製?」
因為緣份,因為命運,但最初的原因,就是你(讀者)手中的電影劇本。我無法說我第一時間就看出鳳儀的導演才華,或馬上知道我會參與其中,但我知道這個故事深深地觸動了我。有些劇本就是這樣,你看著當中的細節、看著角色的互動,就會知道這不是編造出來的。這些點點滴滴,一定都是作者最真實最赤裸的經歷。而最真實的,往往都是最動人的。
擔任監製之後,在鳳儀的劇本上我跟她來來回回不知多少次,我不停地提出疑問,她不斷地繼續修改。與其說我是監製,我更像是嚴厲的老師,一直打槍學生的作業不讓她過關。其實,鳳儀每次的修改都讓我驚艷。又寫出更棒的戲、又找到更深的連結、又取捨掉一塊(對故事來說多餘的)心頭肉。但因為一次次看到她的潛力,相信她還可以更好,我就貪心地像個無情的編輯,一再地退鳳儀的稿。
有人說,創作個人故事,就是要寫到會讓人害羞分享的內容。這劇本是鳳儀的私人日記,也是她給家人的情書。分享出來有沒有讓她害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每一位讀者都會被他們對彼此的愛療癒。如今影片已完成,從文字變成影像的過程,鳳儀完美地平衡著她的理性與感性(面對自己的故事,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啊),成就一部私密又處處顧及觀眾的動人作品。
過程中,亦師亦友的我們彼此分享許多關於創作,也關於生活。無論私下或公開,鳳儀也時常謝謝我對這部電影的幫助。但都是她在道感謝,我卻好像沒有反過來對鳳儀好好地說聲「謝謝」。我要謝謝鳳儀,讓我參與她人生如此重要的第一部長片。謝謝鳳儀,讓我首次擔任監製的作品就這麼的優秀。參與《美國女孩》,我得到的遠遠比我付出的還要多好多。
謝謝鳳儀,for everything。
《美國女孩》讓我想起,我心中那個受傷的小孩
——詩人.林婉瑜
看《美國女孩》讓我深有同感,做母親難,做女兒也好難。
看《美國女孩》讓我想起自己跌跌撞撞的成長過程。
在電影中,我們看到「境遇的變遷」:母親從健康到癌症;女兒從享受美國校園生活到面對台灣體罰教育;父親從好幾年獨居到迎回心情糟糕的返台家人;大環境從平靜無波到SARS之亂。
電影勾起了我自己的成長回憶,記得國一下,轉學到會體罰的私立國中,那幾乎是最慘澹的年歲。
那時我聽過最傷人的話是:「成績那麼爛過什麼生日!」出自我母親口中。那一年,父母只幫妹妹過了生日,沒有幫我過生日。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成績並不是在班上的後段,只是,和每次都是第一名的妹妹比較起來,不夠好。
那年代的父母,經常有一種「我們家小孩如果有什麼不對,老師儘量打沒關係」的共同態度。我曾經因為自習課發呆,被導師殺雞儆猴叫到講台上,背對同學,在小腿上又狠又重打了三大板!每天穿著夏季制服短裙,小腿上的瘀青兩三個禮拜才消退。
某天早上,上學前我猶帶著,前一晚和母親齟齬衝突的不快,她交給我一把零錢讓我帶去學校,我用力把錢擲到牆角,她憤怒地打了我一巴掌。那天中午在學校,導師說,母親來學校找她,擔心早上打得太重,我耳朵有沒有受傷。
因為母親的粗線條,她從不理解,那樣的方式,對我而言是完全沒有用的。
這些貶低和高壓的方式,母親應該只是覺得,她採用了激將法。但自尊心強烈、倔強好強的我,只想逃走、只覺得恨。
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不會說,母親不愛我。在我十五歲前,身為家庭主婦的母親每天都親力親為備好健康美味三餐,讓我擁有很好的身體底子,那何嘗不是另一種方式的愛?後來,有一個冬天,她開車到我住宿的高中,只為了送一件她買的外套給我穿。或者在我十八歲生日當天,她從台中搭車到台北我讀的大學找我,和我吃晚餐,並送我金飾慶祝我成年,這也是另一種方式的愛,不是嗎?
只是,因為國中時的許多衝突,往後,和母親的相處已是非常冷淡了。
事隔多年,我終於可以用大人的眼光,重新去回想和解釋成長過程的痛苦遺憾。
當我自己也成為母親,才發現,當母親真難。
當我面對外人或陌生人,至少可以直接地用尖銳語言把怒氣完整奉還給對方,但,當我面對的是自己的小孩,我經常在做的是收斂、隱藏,儘管不悅不爽,也把攻擊和怒氣降到最低。
其實,身為大人的我,難道不知道怎麼針砭錯處句句見血?只是,小孩若因我的話崩潰了,最後,後悔不已的仍會是我。
所以看到這個情節:芳儀對莉莉出言不遜而被宗輝痛打,最後反是莉莉哭著不捨地向芳儀道歉。
我實在是再認同不過。
家庭關係若即若離,無時無刻在「我」和「我們」之間遊走。
對立的「你我」,隨時可以成為並肩的「我們」。
並肩的「我們」也隨時可以成為,對立的「你我」。
姊姊讓妹妹被鎖在家門外,對立的你我。
不被女兒理解的莉莉,在親師座談會挺身為芳儀說話時,和芳儀成為了「我們」。
一起吃冰淇淋回憶美國時,母女三人成為「我們」。
過往,影劇中,家庭的場景常有一種讓人出戲的刻板印象代入,或者莫名的客套虛假。
有時,我邊看邊在心裡吶喊:「難道感情戲(愛情戲)才是重點!?家庭戲不應該那麼浮面啊!」
導演兼編劇阮鳳儀,用剔透的眼細膩的心、靈巧布局創造了劇中一家四口,觀影到後來,觀眾似乎成為這個家中的隱形房客,看家庭小劇場日日上演,對每個家庭成員的心情都懂、都收納。
最後,莉莉那句「很愛很愛」擊中了我的淚腺。所有衝突、反感、憤怒、攻擊、自傷、忍耐、委屈、嘗試,都是出自「很愛很愛」,都是因為「很愛很愛」。
欣喜出現了一部清新深刻動人的電影,也很期待鳳儀未來的新作。
我很久很久,沒有進電影院看戲了
——作家.廖瞇
我很久很久,沒有進電影院看戲了。一方面是因為現在住鹿野,更大的原因是,我越來越少主動去人多的地方。去人多的地方多半是因為工作需要,或什麼什麼原因必須。而看電影更是,近年來我都是在家看電影,窩在小小的房間,看電影時可以隨自己的狀況情緒起伏,不需顧慮身旁的陌生人。
所以,今年去到金馬影展看《美國女孩》是機緣,但除了機緣還要有那麼一點「想要」。在收到《美國女孩》劇本書的編輯邀約看戲時,當時我想,我人又不在台北,實在很難特地北上看電影,而且就算想看,之後有機會在家看就好了。而後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因為工作需要北上,發現電影上映時間就在工作的前兩天,「要答應嗎?要答應嗎?」這個巧合讓我思考答應的可能性。雖然覺得時間似乎可以安排,但我好像有點怕去戲院看這部電影,因為它是導演阮鳳儀的親身故事,它在講家人之間複雜的情感;一方面我怕它講得太深刻令我在戲院情緒失控,另方面又怕萬一我沒有被擊中而無法寫序,那不是很失禮?
觀影後的結果是前者。傷腦筋,那眼淚真的是再多一點鼻涕就會出來,就必須換口罩的地步。電影結束後在跑片尾字幕時,我根本沒辦法看。我把眼鏡拿下來,哭那種沒有聲音,卻一直流出來的眼淚。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眼淚,我也在想。我的問題就是會忍不住一直想,一直想要用腦袋想,但為什麼我不能好好的哭就好了呢?我突然想到我哭成那樣很有可能是,我弟過世時我沒有在第一時間大哭。我一直沒有大哭,所以現在眼淚分散從別的時候跑出來。
電影快結束時,有一幕是女兒躺在媽媽的腿上,媽媽幫女兒掏耳朵。媽媽對女兒說:「媽媽好愛妳,妳知道嗎?好愛好愛。」
我想到我弟將離開世界而我們卻不知道的那天早上,我媽說她抱著弟弟。我想著弟弟已經多久沒有讓人碰到他了,我想著媽媽已經多久沒能抱自己的小孩了。那樣相似的姿勢,孩子的頭枕在媽媽的腿上。媽說弟弟一直不願意去醫院,但最後靜靜的躺在她的腿上,讓她抱著。
我想起我跟爸爸在家裡的房間,等醫院的電話。因為新冠肺炎的緣故,就算進加護病房後家屬也不能在醫院陪病。那天凌晨四點多,我接到爸爸打來的電話說弟弟入院,原本以為只是要進院治療,而第二通電話變成進了加護病房,「可能一週,也可能這幾天,」爸在電話中這樣跟我說。我買了車票趕緊從台東回高雄,卻只能在家裡等候。晚上八點,醫院來了電話發病危通知,要我們隨時有心理準備,可能就是今晚。電話掛掉後,爸爸靜靜地說完醫院交代的話後回到房間,過了一會我聽到像是笑聲的聲音,後來才發現那是爸爸在哭。
我好像沒有聽過爸爸哭。印象中爸爸沒有在我面前哭過。爸爸可能太久沒有哭了,他哭的聲音像是在笑。
所以當我看到演爸爸的莊凱勛,在獲知小女兒只是一般肺炎而不是感染SARS後,那因為壓力放下之後在樓梯間的大哭,我的眼淚就直直地掉下來。我忍不住想到我爸。現在回想竟然那樣巧合,戲中的小女兒因為SARS疫情必須被隔離,而我的家人也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無法陪在弟弟身邊—那種處在害怕與擔心,卻又必須與家人分開的處境,這種相似讓我幾乎無法停止自己的眼淚。
我好像寫太多自己的事了。這是《美國女孩》劇本書的推薦序,我卻寫了那麼多自己的事。但之所以推薦就是因為共感,共感就是彼此經驗與感受的連結。《美國女孩》的故事很簡單,它想說的是家庭裡的「每一個人」之間那複雜微妙的感情。不只是女孩芳儀,還有媽媽,還有爸爸,還有自己的手足。我看到媽媽林嘉欣做化療時,那個必須忍受身體不適和心理不安的表情,就想起自己的媽媽在忍受暈眩時的表情。我想起弟弟與媽媽之間的爭執,弟弟生氣媽媽為什麼不能對自己再好一點?我看著媽媽林嘉欣打果汁,就想起我媽媽切水果;媽媽會把家裡的水果都切好放進小盒子裡,讓我回老家時早上起床吃早餐時就有得吃。我看著媽媽林嘉欣因為身體不舒服而鬧脾氣,「你們都不要做,我來……」就想起我媽也會鬧脾氣,而作為女兒的我和作為她伴侶的我爸卻無法體諒的說:「有什麼事不能好好講嗎?」
好多好多的細節,好多好多的連結點,包括,「我希望你好,你為什麼不能聽我的呢?」在戲的後段,我看到了馬的隱喻。但這就不說破,留待讀者與觀眾自己去看。
電影結束後,我與編輯見了面。我說我能寫序,跟她要了劇本書檔案。劇本書與電影不同在,讀者必須去揣摩對白,也能藉此感受演員從文字劇本到演出所做的努力。書中還有編劇阮鳳儀與李冰分享劇本如何成形的過程,也讓我藉此思考紀實故事改編為電影,那中間的距離與變化。而無論那中間的距離與變化如何,《美國女孩》之所以能打動我,是因為那裡面真實的情感,以及演員感受到那真實情感後,替角色所注入的靈魂。
點字成靈:美國/台灣女孩的乒乓實戰
——知名影評人.藍祖蔚
面對劇本書,總是猶疑著要先看?抑或看完電影再看?
30年前先讀了《悲情城市》劇本書,再看電影,儼然兩個世界,一度迷航在字裡行間,沒能理解劇本與電影的龐大落差:電影拍出了很多書中難盡的時空滄桑,劇本多了很多電影潛入水面的生命細節。然而,電影究導演說了算,劇本只是個過程,侯孝賢悄悄擦乾吳念真與朱天文的汗水,換上自己的體悟與再現。
《美國女孩》不然。
阮鳳儀是編劇(還有一位協力執筆的李冰),亦是導演,更是自傳故事的分享創述人,雖然劇本歷經十八稿,從最後刊印的劇本比對電影,忠實度與還原度都極高,細讀劇本宛如再一次重看了電影。當然,也因為重讀才得以發覺電影增加或消減了哪些部份。畢竟劇本只是骨架,拍攝時的場面調度或演員表演,不管來自即席創作或機動調整,創作團隊當下的靈光閃動除了為電影加肉添血之外,還多添了幾分靈氣。
例如,散居台美兩地多年的夫妻再度同床,太太先去洗澡,疲累丈夫躺在兩片枕頭上睡著了,太太的枕位是空的,顯然,他早已習慣太太不在家,習慣獨霸床位。等到丈夫起身洗澡去,太太嘆口氣,抽出下面那一枕來睡,上面那一枕有丈夫的溫度、髮油和口水氣息,或許是嫌不乾淨,或許是分隔多日後有了生份間隙了。生活中的小細節、小心思在演員詮釋下,電影生命在字裡行間中流瀉出極其纖細的活力。
例如,電影中的父女相逢,是從口哨聲音開始,結局亦在父親的口哨聲中再次團圓。劇本有團圓的欣喜,唯獨少了口哨。沒有,不影響理解;有,則是聲影魔法的傲入展示:口哨聲的首尾呼應,家的意象就更鮮活。劇本沒能兼及的細節,在拍攝或後製現場都加足了馬力。
當然,劇本書也提供足夠資訊,讓電影中驚鴻一瞥就掠過的畫面,留下更多耐人咀嚼的註解。例如,媽媽曾在芳儀的課本中發現了一匹又一匹的馬兒描圖。書頁翻動時,馬兒有如跑馬燈在書頁上跑著,然而芳儀同學思婷的國文課本上有著什麼塗鴉?坦白說,觀影時我來不及注意。但是劇本告訴你,思婷課本上的作者肖像都被塗鴉成不同世界足球賽的明星:李白成了貝克漢、杜甫成了外號「外星人」的羅納度……阮鳳儀在劇本中留下這些文字,對於表演者或讀者都是關鍵的青春素描,看了就懂,難以言宣或者放不進電影的青春心緒,都在文字見證下,有了呼吸。
這場戲同時提供從聲音中得著的想像:芳儀向出借課本的思婷說了聲「謝謝」,思婷也回了句「You’re welcome.」中文謝,英文答,兩位女孩用對方最能理解的語言來溝通。文化位差、心理預期,就在她們乒乒乓乓的言語互動中讓人會心一笑。然而,思婷的台式英語,比對芳儀姊妹的美式英語,不論是姊妹分享心事的英語交心,或是母女用英文回嘴爭吵的自然反射,不經意就脫口出口的美式英語,你更加確信「美國女孩」的聲音表演讓角色的真實度更加立體,那亦是看過電影的你,再回頭細讀劇本時,必然會唇角上揚的原因。
芳儀與馬的對話是全片畫龍點睛的關鍵戲。劇本用一行交代坐上公車要去馬場的芳儀看著大腿上的瘀青,然而電影中,你另外看見了車窗上「緊急出口」的四個紅字。這是公車上一定都有的逃生警語,然而選用這面窗做背景,不論是偶然或巧合,都強力點出和爸媽嘔氣的芳儀急尋出口的「逃生」心情?劇本畫龍,導演導睛,觀眾只要瞄一眼就通透了。
接下來,劇本描述馬兒「來回踱步,就是不讓芳儀套上韁繩」,芳儀(近乎哀求)地說著:「Take it!」,最後則是「馬兒與芳儀對視,眼神盡是溫柔」。光是「溫柔」一詞,就已標示出這場戲有多難拍。據說,阮鳳儀原初還有讓芳儀上馬墜馬的情節,基於安全考量最終刪除了,最終的處理既簡約又動人。從第一稿到第十八稿,電影終究長成了如今的模樣。即使我只能約略比對,卻也依舊可以「腦補」鳳儀沒能放進劇本的章節,但我依舊好奇,想看看她的「原稿」究竟如何處理少女從期待到失落的人生跌撞?
我慶幸自己先看了電影,才讀到劇本。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PLAY BACK之旅,慢慢讀,細細看,觀影時有過的悸動與歎息,再次回來相聚。如果,你先讀到書,相信我,你一定會想要看看導演如何點字成靈。
《美國女孩》是阮鳳儀的青春告白,而你我剛巧也走過她的那個年代,看過相似的風景,即使我們只是路人甲,即使我們只是「死台客」,她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