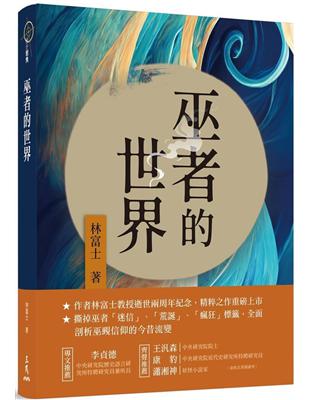章節試閱
〈臺灣童乩的儀式裝扮〉
童乩儀式裝扮的宗教與社會意涵
那麼,童乩為何要做如此裝扮呢?關於這個問題,由於童乩並不隸屬於組織性的宗教,也缺乏共同的經典,而且,他們多數不曾替自己的信仰或儀式留下隻字片語,因此,我們只能憑藉「他者」對於童乩的觀察、紀錄、批判、詮釋或想像,以及數量有限的科儀書和極少數的童乩訪談錄,[1]進行嘗試性的解釋。
首先,我們發現童乩裸露軀體的目的,似乎是為了便於以刀、劍等利器自傷或展示神異(如袒臥釘床、跣足過火、「爬刀梯」等),讓信徒相信或知道神明已經附體,因此,能夠「創而不痛」、不畏流血,也就是傳統文獻所說的「以示神靈」。而「操五寶」以流血這一類的動作,也可視為是童乩向廟中主神的獻祭或禮拜,同時,其鮮血有時也被用來替其信眾除煞、淨化、治病。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動作基本上都和所謂的「調五營」、「安五營」、「拔五營」儀式連結在一起,因此,其鮮血似乎也有淨化其「兵馬」行經之處或駐紮之地的功能。[2]此外,我們甚至可以從「科學」或「比較宗教」的角度看待這樣的動作,因為,具有節奏性的揮擊兵器的動作、規律性的跳躍(又稱「跳童」)、「自傷」所造成的疼痛,再加上以點燃的香柱灼燙胸腹,或是猛烈嗅吸爐香的濃煙,或許可以催化童乩進入精神迷離(trance)的狀態。
[3]
不過,這樣的儀式裝扮似乎還有另外一層的社會意涵。童乩「披髮」(散髮)、「裸體」(袒裼)、「露臂」、穿戴布巾或圍兜等物的裝扮,以今日的社會習尚來說,似乎並不足為奇。但是,在傳統社會中,尤其是在對於「髮式」極為敏感的清代社會,「披髮」而不辮髮,若不被視為反叛也會被當作瘋子。[4] 同樣的,以當時的標準來看,裸露身軀、穿著兒童式的肚兜或婦人式的褻衣,也不合「禮教」,至少是一種異常的行為。至於持拿兵器(再加上聚眾、遊行、神轎、儀仗等),更容易引發官方的疑慮,被視為治安的隱憂或是對統治權威的挑戰。而使用兵器自傷的行為,在清代士人的眼中,無異違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聖人教訓。從日治時期之後,這也常被政府官員及知識分子視為野蠻、瘋狂的舉動,事實上,童乩也因而被視為精神病患。
[5]
結語
上述的儀式裝扮並不是臺灣童乩獨有的特徵或創發。事實上,無論是在臺灣、福建,還是在東南亞的閩南語族群中,「童乩」這種人都不罕見。[6] 而這樣的裝扮似乎是起源於閩南一帶,例如,根據十九世紀末年荷蘭學者高延(J. J. M. de Groot, 1854-1921)所做的調查,[7]福建當地的童乩在儀式中通常是披散頭髮、赤腳、裸露上身,穿著圍兜(繡肚),手中持拿劍和刺球,並且能以粗針(或大椎)貫穿兩頰或舌頭。他所留下的童乩照片,也很清楚的表現了這樣的特徵。
[8]
而這種裝扮的起源至少還可以前推至十八世紀。例如,《福建省例》〈雜例〉中有一案名為「禁迎神賽會」,其中提到:
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一月,奉巡撫部院崔示諭:……查閩省向有迎神賽會惡習。本部院自幼親泛澎臺外海,還經八閩地方,每見誕妄之徒,或逢神誕,或遇令節,必呼朋引類,旗鼓喧鬧,或擡駕闖神,或迎賽土鬼。更有一種私巫馬子,妄降假神,用大椎貫穿口內,茨毬摔擊其背,血肉糢糊,竟立駕上,繞市號召,竟同兒戲。且若與他迎神相遇,則又彼此爭途。稍有不讓,群起互甌,反置神駕於道旁,每致滋生事端,身蹈刑法。是求福而反得禍者,總由狎褻不敬之所致也。近年法禁森嚴,此風或亦稍息。第恐法久禁弛,愚頑之輩,或有仍蹈故轍,擾害地方,亦未可定。合行明白示禁。
[9]
崔應階是在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代莊有恭為福建巡撫,[10]上任才三、四個月,便有這道禁令,可見閩(臺)一帶的「迎神賽會」的「惡習」是他上任後急欲處理的要務。[11] 他嫌惡「迎神賽會」,一是擔心民眾「滋生事端」,二是無法認同「私巫馬子」在迎神賽會中的種種舉止。他認為,這種人「妄降假神」,「用大椎貫穿口內,茨毬摔擊其背,血肉模糊」,「竟立駕上,繞市號召」,簡直是「兒戲」。這是崔應階的親自見聞,而他在「示諭」中針對「私巫馬子」儀式展演所做的描述,基本上和臺灣(及福建)童乩的儀式場景及特點幾乎沒有差異。事實上,童乩或乩童在傳統文獻中大多被稱作巫覡或巫者,兩者應該沒有不同。[12]事實上,在世界各地的「巫俗」(shamanism)之中,童乩這種「自傷」的儀式可以說相當獨特,罕見於其他社會。
[13]
總之,當代臺灣童乩的儀式裝扮,可以說相當成功的形塑了獨特的宗教形象,充分展現其「入神」狀態和神靈「代言人」身分,而其基本元素和特質則至少可以遠溯至十八世紀,而且和閩南地區的童乩(巫者)有高度的相似性,應該屬於同一宗教文化區(信仰圈),甚至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一些時代和地區的變異,尤其是近年來臺灣地區童乩在服飾穿著上的「隨意性」,以及部分童乩操持法器的「多樣性」。
____________
[1] 從1999年歲末開始,我和一群年輕的學生展開一項名為「臺灣童乩基本資料」的調查工作,截至2003年12月底為止,共計完成五百九十六個童乩的初步訪談工作。在這過程之中,不少童乩對於訪談都抱持排拒的態度,因此,工作並不是進行得很順利,但也大致完成其社會背景和主要宗教歷程的資料收集。可惜的是,除了少數例外,訪談的場合都不是在廟會,因此,較少對其儀式裝扮和演示進行詢問,即使提問,也很少獲得回應。
[2] 臺灣民俗認為廟宇、村落的五個方位(東、西、南、北、中)都有神將及其兵馬鎮守,平時擔任守衛的工作,當廟中神明及村落民眾到異地「進香」時,則會擔任隨從及護衛的工作。當村落遭逢外面的鬼怪入侵、攻擊時,也能發揮禳妖除邪的功能。因此,在某些特定的場合,法師或童乩便會舉行「調五營」(或叫「召五營」)的儀式,調動神將及其兵馬相助,進香時更會請祂們隨行,到達目的地則必須舉行「安五營」(或叫「放五營」)的儀式,讓神將及其兵馬安駐、休息。進香之後,還必須舉行「拔五營」(其實也就是「調五營」或「召五營」)的儀式,請神將及其兵馬起身,護衛神明及其信眾返回村落。關於「五營」的信仰及相關科儀,參見黃有興、甘村吉,《澎湖民間祭典儀式與應用文書》(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3),頁83-94。
[3] 根據一些神經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說法,當巫者被鬼神所「憑附」(possession)時,其精神狀態往往會進入所謂的「迷離」(trance)的境界,也就是「意識的變異狀態」(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這種精神狀態的改變主要是由腦部一種叫做安多芬(endorphin;腦啡)的化學物質所主導。至於促使腦部分泌這種物質的原因則包括:規律性的肢體動作(諸如顫抖、晃動、和舞蹈)、節奏性的聲音(尤其是鼓聲和各種反覆不斷的敲擊聲)、極端恐怖或痛苦的經驗、夢(尤其是惡夢),以及服用「精神藥物」(psychedelic drugs) 或「致幻劑」(hallucinogens)等。這也就是說,經由上述方式,即使是一個平常人也可以進入「迷離」的精神狀態。而大多的巫者則特別精擅於這些技能,並且具有比較特殊的體質,更容易變異其意識而造成所謂「鬼神附身」或「魂遊」(ecstasy)的現象。相關的研究,參見Raymond Prince, “Shamans and Endorphins: Hypotheses for a Synthesis,” Ethos, 10:4 (Winter 1982), pp. 409-423; Jeanne Achterberg, Imagery in Healing: Shamanism and Modern Medicine (Boston and London: Shambhala, 1985), pp. 11-51, 113-141.
[4] 詳見林富士,〈頭髮的象徵意義〉、〈披髮的人〉,收入氏著,《小歷史──歷史的邊陲》,頁165-170,171-179。
[5] 詳見林富士,〈醫者或病人──童乩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與形象〉,頁511-568;林富士,〈清代臺灣的巫覡與巫俗:以《臺灣文獻叢刊》為主要材料的初步探討〉,《新史學》16:3(臺北,2005),頁23-99。
[6] 詳見J. J. 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892-1910), vol. 6, pp.1269-1294; Alan J. A. Elliott, Chinese Spirit-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5); 陳潤棠,〈巫術、童乩與降頭〉,收入氏著,《東南亞華人民間宗教》(香港:基道書樓,1989),頁162-198;佐佐木宏幹,〈東南アジア華人社會のシャーマニズム〉,收入關西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編,《シャーマニズムとは何か:國際シンポジウム.南方シャーマニズム》(東京:春秋社,1983),頁18-30;佐佐木宏幹,《シャーマニズムの人類學》(東京:弘文堂,1984),第3部,〈東南.南アジアのシャーマニズム〉,頁279-367;藤崎康彥,〈童乩〉,收入植松明石編,《神神の祭祀》(東京:凱風社,1991),頁294-419。
[7] 有關 J. J. M. de Groot(1854-1921)的生平及著述,參見Leonard Blussé, “Of 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 Leiden University's Early Sinologists (1853-1911),” in Willem Otterspeer ed., Leiden Oriental Connections, 1850-1940 (Leiden: E. J. Brill, 1989), pp. 317-353; Wilt L. Idema, “Dutch Sin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Ming Wilson and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pp. 88-110 (pp. 91-92).
[8] 詳見J. J. 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vol. 6, pp.1274-1278.
[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臺灣文獻叢刊》本],卷34,〈雜例〉,頁1201-1202。
[10] 詳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卷13,〈本紀〉,頁476。
[11] 事實上,這並不是崔應階的創舉,在乾隆年間,不少地方首長曾多次針對類似的「迎神賽會」下達禁令,但卻屢禁屢復;參見木津祐子,〈赤木文庫藏《官話問答便語》校〉,《沖繩文化研究》31(東京,2004),頁543-657(550-553)。
[12] 詳見林富士,〈清代臺灣的巫覡與巫俗──以《臺灣文獻叢刊》為主要材料的初步探討〉,頁23-99。
[13] 詳見Mitsuo Suzuki, “The Shamanistic Element in Taiwanese Folk Religion,” in A. Bharati ed., The Realm of the Extra-Human: Agents and Audiences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Publishers, 1976), pp. 253-260; Ruth-Inge Heinze, Trance and Healing in Southeast Asia Today (Bangkok, Thailand: White Lotus Co., Ltd., 1988); Donald S. Sutton, “Rituals of Self- Mortification: Taiwanese Spirit-Medium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 4:1 (1990), pp. 99-125.
〈臺灣童乩的儀式裝扮〉
童乩儀式裝扮的宗教與社會意涵
那麼,童乩為何要做如此裝扮呢?關於這個問題,由於童乩並不隸屬於組織性的宗教,也缺乏共同的經典,而且,他們多數不曾替自己的信仰或儀式留下隻字片語,因此,我們只能憑藉「他者」對於童乩的觀察、紀錄、批判、詮釋或想像,以及數量有限的科儀書和極少數的童乩訪談錄,[1]進行嘗試性的解釋。
首先,我們發現童乩裸露軀體的目的,似乎是為了便於以刀、劍等利器自傷或展示神異(如袒臥釘床、跣足過火、「爬刀梯」等),讓信徒相信或知道神明已經附體,因此,能夠「創而不痛」、不...
推薦序
推薦序
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1978 年秋進入大學,歷史系班上人才濟濟,其中一位同學特別出色,不僅善詩能文,還很會說故事。他來自雲林濱海的村莊,講述兒時見聞,童乩降神附體,活靈活現,常令生長於城市的我感覺匪夷所思。他是林富士。
之後十多年,富士以自幼熟悉的巫者為題,陸續完成碩、博士論文,先談漢代、後論六朝,為當時幾乎無人涉獵的領域拓邊開新。普大畢業後,重返史語所,他持續關注巫者的世界,對帝制中國的巫覡研究,下探至宋代和清末。更重要的是,他跨出文字史料的框限,進行田野考察,跑遍臺灣大鄉小鎮,普查記錄童乩與信眾,又遠赴韓國,拍攝巫女在喪禮中牽亡的儀式影片。他的研究室和我比鄰,不論在講論會、工作坊,或走廊上、茶水間,聽他分享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經驗,總是他說得興高采烈,我聞言莫名感佩。
《巫者的世界》一書,正是富士多年來爬梳史料、尋訪考掘、反覆思辨之後,對傳統中國和近代臺灣巫覡信仰的精道剖析。2016年曾以簡體字出版,今依原稿補正更新,以正體字刊印。其中收錄八篇專論,涵蓋巫者的社會形象與地位、他們和統治政權弛張交錯的關係、巫覡作為醫療者與病人信徒的互動, 以及這些角色功能對歷代巫俗巫風的影響。篇篇皆反映史語所鋪天蓋地蒐羅史料的傳統, 也展現富士不畏艱難勤跑田野的毅力。即以 〈臺灣童乩的儀式裝扮〉一章為例,雖短小卻精悍,透過細究巫者的外貌、服飾、法器,以及在儀式中的作用與意義,綜論古今、反思學史,並且圖文並茂,充分顯示他調度各種資訊、推進論題的志氣與功力。
早期宗教史研究,多從經典教義入手,也有分析教團組織的。上世紀末,宗教經驗的考察風生水起,學者對信仰所涉及的儀式、物品、活動,乃至其中個人的身體、情感及其意涵,皆興趣大增。富士自學涯之始,便立志追尋巫者在歷史上的足跡, 藉由掌握宗教人物來認識更廣大的社會文化, 可謂慧眼獨具。巫覡信仰非組織型宗教,巫者在帝制時期屬底層人物,史料分散,載論隱曲,研究者除了廣事蒐羅的耐性,還需有觸類旁通的機敏,而富士以溝通者自期,這些正是他作為歷史學者最在乎的能力。
是的,富士研究歷史,正是以上古絕地天通,巫者溝通人神自況。他致力於穿越古今、進出知識異域、梳理紛紜眾說,再以流暢的文筆傳達轉譯。瀏覽本書,不論是宗教史、中國史或臺灣文化的專家學者,相信都能因其中豐富的資料、寬宏的論述而受益。初入門者,即使僅僅閱讀他的長篇自序,也能受到啟發。〈序:吾將上下而求索〉彷彿一篇學術自傳,始於「摸索」,終於「未央」,循循善誘,引領年輕學子一窺士林堂奧。
確實未央!雖然,富士已在2021年遠颺,但他留給學界的遺產豐厚,我們將透過他的著作,和他,以及他所探討的巫者世界繼續
推薦序
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1978 年秋進入大學,歷史系班上人才濟濟,其中一位同學特別出色,不僅善詩能文,還很會說故事。他來自雲林濱海的村莊,講述兒時見聞,童乩降神附體,活靈活現,常令生長於城市的我感覺匪夷所思。他是林富士。
之後十多年,富士以自幼熟悉的巫者為題,陸續完成碩、博士論文,先談漢代、後論六朝,為當時幾乎無人涉獵的領域拓邊開新。普大畢業後,重返史語所,他持續關注巫者的世界,對帝制中國的巫覡研究,下探至宋代和清末。更重要的是,他跨出文字史料的框限,進行田野考...
作者序
出版緣起
林富士教授為臺灣史學界的著名學者,畢生研究以身體為軸心,致力於宗教史、醫療史與文化史,以做一個現代薩蠻為自我定位,透過文獻進入異域,瞭解另一個世界的現象,不僅探究歷史發展的脈絡轉折,也關注於「邊緣」的小歷史。教授自2000年起,擔任三民書局「文明叢書」編輯委員,並出版《小歷史──歷史的邊陲》(2000年)及《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2001年)等作品,透過教授的研究,我們得以看見庶民歷史的精彩與活躍。
教授2021年辭世後,各界無比悵然,但其所遺留的豐碩研究成果,仍持續影響著相關學術主題的發展。《巫者的世界》是教授多年來針對巫者歷史的研究總結,對於臺灣常見的宗教人物「童乩」亦多所關注,曾以簡體中文出版,但始終未曾以繁體中文版呈現給臺灣讀者,甚為可惜。源此若能出版以饗讀者,將有助開拓讀者對於臺灣宗教文化的理解,為學界之福,想必也是富士教授所願。
出版本書,對與教授有多年淵源的三民書局而言,責無旁貸,幸得其家人林雅蘭女士促成,及陳藝勻博士協助審閱、校訂,特此致謝。亦希盼本書的出版,能將教授嚴謹的研究精神與學者風範永傳後世。
三民書局編輯部謹識
序:吾將上下而求索
一、摸索 (1982-1984)
1982 年夏天,我從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 立刻面臨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抉擇:繼續升學或當兵。後來,我選擇入伍擔任預備軍官,但仍保留了歷史研究所的入學資格。
當兵是無可逃避的「義務」,也是體魄與心智的鍛鍊。在文學院浸泡了四年,心靈自由而奔放,生活隨意而自在,因此,在入伍之後,格外難以忍受講求權威、服從、標準、齊一的軍人文化。而且,當時還在「戒嚴」時期,言論、思想與行動幾乎都戴上了手銬與腳鐐。役期一年十個月,苦悶慢慢煎熬。所幸我是少尉經理官,擔任補給和管理的工作,較為輕鬆,而且還有獨立的臥室,在半是禁閉的狀態下,讀書成為最好的解脫。
那時,我帶了王守仁 (1472-1529) 的《陽明全書》和葛洪(約284-363)的《抱朴子》到部隊。我特別挑沒有標點的版本,一個字一個字點讀,在斷句的過程中,彷彿吐納一般,呼吸著儒、道二家的思想。我先是讀王陽明,因為我大學時代的志業是彬彬的儒者。但是,越讀越無聊,紙面上充斥著天、人、性、命、道、理、心、良知、格物這一類的字眼,以及一篇又一篇的問答、書信、序文,反覆纏繞著仁義道德與學問事功。我非常佩服,但如墜五里霧中。後來讀《抱朴子》,一看,眼界大開,驚愕連連。葛洪所描述的道教世界實在太有趣了,有煉金、房中、辟兵、禁咒、長生、神仙、隱形、分身、變形等法術,提供了各種慾望的滿足方法。對於神仙之說,我雖然不敢置信,但仍被勾引起一絲富貴不死、法力無邊的貪念。更重要的是,童年時期在鄉村的一些經驗突然醒覺,我恍惚又聽見了道士在喪禮中的搖鈴聲、吹角聲、唱誦聲,看見了三清道祖、十殿閻王、地獄鬼怪的圖像。在閱讀、冥想的過程中,我逐漸找到當下與往昔的聯繫,也找到自己歷史研究的方向。
我選擇宗教作為主戰場。原本打算從中國道教史入手,但是,當時我所能讀到的只有許地山 (1894-1941)、傅勤家、孫克寬 (1905-1993)、李豐楙(1947-) 四人的著作,而他們在討論道教起源的時候,都提到道士與巫覡有緊密的關係,這讓我想起小時候所碰到的童乩。
1960年代,我所生長的濱海村莊(雲林縣臺西鄉五港村瓦厝)還相當「落後」,沒有象徵「現代文明」的自來水、汽車和醫生,多的是蒼蠅、流氓和砂眼。病痛的時候,通常會求助於童乩,降神、問卜、畫符、唸咒、收驚、叫魂、祭解、驅邪,無所不致。而我的表姨丈就是村裡最神氣的童乩。事實上, 我還有一位姨丈、兩位表哥、一位堂哥,也都是童乩。我對於這樣的人並不陌生,他們應該就是傳統文獻所說的巫者。
可是,根據《國語‧楚語》的記載,巫者在古代是聖、智、聰、明的才藝之士,是統治集團的一分子,而童乩在當代社會卻受人輕賤,被人打壓。官方與主流媒體不斷宣稱他們是低級、野蠻、邪惡的神棍,應該予以禁斷。在知識的殿堂中,他們更是毫無立足之地,很少人願意碰觸或討論這樣的人。因此,我很快就決定要探索巫者的古今之變。我的終極關懷,不是陌生巫者的往日光輝,而是我所熟識的童乩的當代困境。
(完整請見內文)
出版緣起
林富士教授為臺灣史學界的著名學者,畢生研究以身體為軸心,致力於宗教史、醫療史與文化史,以做一個現代薩蠻為自我定位,透過文獻進入異域,瞭解另一個世界的現象,不僅探究歷史發展的脈絡轉折,也關注於「邊緣」的小歷史。教授自2000年起,擔任三民書局「文明叢書」編輯委員,並出版《小歷史──歷史的邊陲》(2000年)及《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2001年)等作品,透過教授的研究,我們得以看見庶民歷史的精彩與活躍。
教授2021年辭世後,各界無比悵然,但其所遺留的豐碩研究成果,仍持續影響著相關學術主題的...
目錄
出版緣起
推薦序
序──吾將上下而求索
中國古代巫覡的社會形象與社會地位
一、引言
二、神話與傳說中的古代巫覡
三、先秦時期的巫官、官巫及其職事
四、先秦時期的民巫與營業之巫
五、先秦諸子對巫覡的態度
六、禁巫與抑巫
七、秦漢時期的巫覡
八、結語
中國中古時期的巫者與政治
一、引言
二、三國時期(220-265)
三、兩晉十六國時期(265-420)
四、南北朝時期(420-589)
五、隋朝(581-618)
六、帝王崇信巫者之緣由
七、結語
「舊俗」與「新風」──試論宋代巫覡信仰的特色
一、引言
二、祀神的改變
三、儀式的新貌
四、結語
附錄 陳淳,〈上趙寺丞論淫祀〉
清代臺灣的巫覡與巫俗──以《臺灣文獻叢刊》為主要材料的初步探討
一、引言
二、「童乩」與巫覡釋義
三、巫覡的信仰對象
四、童乩的儀式特質
五、童乩的社會角色
六、士人對於童乩的態度
七、結語
醫者或病人──童乩在臺灣社會中的角色與形象
一、引言
二、「童乩」釋義
三、童乩的醫療者角色
四、童乩的疾病觀與醫療法
五、精神異常與人格解離
六、巫病與成乩
七、另一種病人
八、結語──另一種醫者
臺灣童乩的儀式裝扮
一、引言
二、童乩的服飾與法器
三、傳統文獻對於「童乩」裝扮的描述
四、近代學者對於「童乩」裝扮的觀察
五、童乩儀式裝扮的特點
六、童乩儀式裝扮的宗教與社會意涵
七、結語
中國的「巫醫」傳統
一、引言──「獵巫」的醫學史?
二、巫為醫先
三、「巫醫」考釋
四、巫醫同職共事
五、病人巫醫兼致
六、信巫不信醫
七、不用巫醫與巫醫無用
八、結語──在批判與禁斷之下
附錄:略論占卜與醫療之關係──以中國漢隋之間卜者的醫療活動為主的初步探討
一、引言
二、卜者與治病者
三、漢隋之間卜者的治病事例
四、占卜的醫療功能
五、結語
出版緣起
推薦序
序──吾將上下而求索
中國古代巫覡的社會形象與社會地位
一、引言
二、神話與傳說中的古代巫覡
三、先秦時期的巫官、官巫及其職事
四、先秦時期的民巫與營業之巫
五、先秦諸子對巫覡的態度
六、禁巫與抑巫
七、秦漢時期的巫覡
八、結語
中國中古時期的巫者與政治
一、引言
二、三國時期(220-265)
三、兩晉十六國時期(265-420)
四、南北朝時期(420-589)
五、隋朝(581-618)
六、帝王崇信巫者之緣由
七、結語
「舊俗」與「新風」──試論宋代巫覡信仰的特色
一、引言
二、祀神的改變
三、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