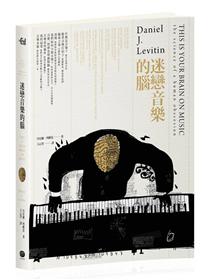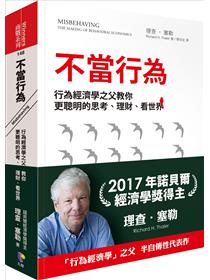一部書寫人世深情致遠的大戲!
王安憶最新重磅長篇小說,
書寫上海老城舊宅,市井歷史的頹然美學。大時代的洪波中,他們這一間老屋,好像《聖經》故事裡的方舟,既隨波逐流,又自給自足,等待彼岸臨近,終有臨近的時刻吧!
我將小說題作「考工記」,顧名思義,圍繞修葺房屋展開的故事,又以《考工記》官書的身分,反諷小說稗史的性質,同時還因為房屋裡的人——這個人的一生時間,倘若只是奔走修房,未免太托實了,也太簡單,世事往往就是簡單,小說可不是,小說應該有另一種人生,在個體中隱喻著更多數。這個人,在上世紀最為動盪的中國社會,磨礪和修煉自身,使之納入穿越時間的空間,也許算得上一部小小的營造史。
——王安憶
「半水樓」,又稱「煮書」,陳家老宅,晚清時期的貴冑大宅邸,整幢樓不用鉚釘,全是插和套,渾然一體,歷經百年不散架。陳書玉的祖父有一日帶著他遍走樓上樓下告訴他,門扉上的雕飾都有源頭,源頭都是八仙。門板上的圖案是八仙操持的法器,張果老的巾箱,藍采和的板子,何仙姑的果籃,韓湘子的牡丹花;窗櫺的鏤刻是四款花色,冬梅,秋菊,夏荷,春天的芍藥……
上海西廂四小開,朱朱、奚子、大虞和陳書玉。大虞經營木藝工坊,奚子父親是律師,朱朱家與洋人作生意;陳書玉的老祖宗乾隆年間從台灣來到上海,開船號,經營碼頭生意,世代靠遺澤蔭庇度日。
四小開在他們生命最美好的青春時期,一起品美食,泡舞廳,走冒險……然而在惶遽的世事裡,人往往身不由己,那些不期然的邂逅,打個漩,又匯入滔滔洪流,奔騰而去。他們歷經太平洋戰爭、淞滬會戰,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狂流後,好友們一個個離去,陳家宅子裡的人,也一代一代地蛻殼,蛻到後來,終於什麼都沒有,獨留下陳書玉,孑然一身,與那百年老宅,相依為命,淡看世態炎涼。
陳書玉一生與老宅相依相存,歷經戰亂及文革洗禮,老宅存活下來了,但也傾圮敗漏;面對這衰敗,他燃起修復老宅的冀望。他找來木工功夫了得的好友大虞,商研宅邸的古老修葺工法,試圖讓老宅在新時代的摩登上海,矗立如昔。然而,古蹟法和產權如此繁複,官方承諾忽明忽暗,眼看老宅日漸傾圮,他能以古老工法,如願修復這座新時代摩登上海巷弄裡的古宅大院嗎?或者他將與落拓的老宅,彷如被時代遺忘的孤舟,黯然飄蕩在新舊社會交接的渡口,何去何從!
《考工記》以陳書玉為主軸,陳家「正宗清代古建築」大宅院為基底,輻射書寫動盪戰亂時期到新時代的二十一世紀,陳書玉與他的老宅、友人,一生的浮沉故事;王安憶以其不慍的筆,細膩描繪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傷與情,她的考工除了考究建築工法,也考古眾生的浮生記憶與情感。
作者簡介:
王安憶
1954年生於南京,翌年隨母親遷至上海,文革時期曾至安徽插隊落戶。曾任演奏員、編輯,現專事寫作並在復旦大學任教。
《長恨歌》榮獲九○代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作品、1998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1999年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2000年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1年第六屆星洲日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富萍》榮獲2003年第六屆「上海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長篇小說二等獎;《天香》獲2012年第四屆紅樓夢文學獎;《紀實與虛構》獲2017年紐曼華語文學獎(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2011年入圍第四屆曼布克國際文學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2013年獲頒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Chevalier of the Order of Arts and Letters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著有《紀實與虛構》、《長恨歌》、《憂傷的年代》、《處女蛋》、《隱居的時代》、《獨語》、《妹頭》、《富萍》、《香港情與愛》、《剃度》、《我讀我看》、《現代生活》、《逐鹿中街》、《兒女英雄傳》、《叔叔的故事》、《遍地梟雄》、《上種紅菱下種藕》、《小說家的讀書密碼》、《啟蒙時代》、《月色撩人》、《茜紗窗下》、《天香》、《眾聲喧嘩》、《匿名》、《鄉關處處》等。
作品被翻譯成英、德、荷、法、捷、日、韓、希伯來文等多種文字,是一位在海內外享有廣泛聲譽的中國作家。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一
一九四四年秋末,陳書玉歷盡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這一路,足有二月之久。自重慶起程,轉道貴陽,抵柳州,搭一架軍用機越湘江,乘船漂流而下,彎入浙贛地方,換無數貨客便車,最後落腳松江,口袋裡一個子不剩,只得步行,鞋底都要磨穿。但看見路面盤桓電車軌道,力氣就又上來。抬頭望,分明是上海的天空,鱗次櫛比的天際線,一層層圍攏。暮色裡,路燈竟然亮起來,一盞、兩盞、三盞……依然是夜的眼,他就要垂淚了。
二年前,隨朋友的弟弟、弟弟的女朋友、女朋友的哥哥、哥哥的同學——據說是韓復渠司令的侄系親屬,絡絡繹繹十二人,離開上海。去時不覺得路途艱難,每一程必有接應和護送。陳書玉沒出過遠門,中國地理也學得不精,並不知道哪裡是哪裡,只覺得很開眼。天地江河都是壯闊,漫野的青紗帳——他沒見過莊稼地,原來也是壯闊的。尤其入山西地界,車走在黃土溝裡,山崖上一道城牆,箭垛如同鋸齒,插入蒼穹,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氣勢。吃苦是難免的,食宿簡陋倒不計較,他最懼的是臭蟲。夜裡一吹燈,就聽壁紙與篾席沙沙的山響。蝨子也是一懼,這兩項甚至超過日本人封鎖區的可怖。也因為日本人的事不歸他管,自有負責的人。這一路也有月餘,說是避亂,更像遊山水,從仲夏到秋初,正值西南宜人的季候。許多年過去,方才知道一行匿身特殊人物,或者說,是為這一位特殊人物,方才集起這一行同道,所以如此順遂。以致回程中,時不時想起那一句舊詞:別時容易見時難。而他萬萬想不到,就因為此一行,日後新政府納他入自己人,得以規避重重風險。
邁過電車路軌,路軌沉寂地躺在路面,眼前彷彿電車的影,那影裡明晃晃的窗格子,閃爍一下,又滅了。腳下的柏油地,漸漸換成卵石,硌著磨薄的膠鞋底,他穿一雙元寶口的膠鞋,在多雨的西南可是個寶,到上海卻變得奇怪了。就在這一刻,天陡地沉下來,路燈轉到背後很遠的地方,街邊的房屋十之七八坍塌,間或一二座立著,緊閉門窗,沒有動靜。有人在瓦礫堆裡翻扒,咻咻驅趕野貓。一隻肥碩的老鼠從腳下躥過去,他原地跳一跳,放了生。廢墟上亮起一星點火,湮染開一圈,火上的瓦罐吐吐地小沸,有食物的香甜瀰漫在空氣裡,他吸吸鼻子,辨出南瓜的氣味。映著幽微的光,面前呈現一片白,這一片白彷彿無限地擴大和升高,仰極頸項,方搆著頂上一線夜天,恍然悟到,原來是宅院的一壁防火牆,竟然還在——從前並不曾留意,此時看見,忽發覺它的肅穆的靜美。他不過走開二年半,卻像有一劫之長遠,萬事萬物都在轉移變化,偏偏它不移不變。
從防火牆下走,順時針方向到西門,抬手一推,推不動。門上掛了鎖,托在掌上,沉重得很,是原先的舊鎖,又是一個竟然,竟然完好如故。停一停,退後兩步,張開雙臂,一臂扶牆,一臂扶牆邊柳樹,再原地一躍,兩腳就分別撐在牆面與樹幹,離地三尺,蹭蹭數步,又上去三尺,就到地方了。稍歇一歇,站穩,扶樹的手,慢慢移動摸索。某年某月,雷電正中劈開,都當它要死,卻發出許多新枝,養了許多洋辣子,大人孩子都繞道走,樹身且又長合,留下一個木洞,容得下一巢鳥雀,日後作了他家兄弟的祕處。
一番摸索,脊背就迸出熱汗,腦穴處則通電般一涼,摸到什麼?鑰匙!鳥雀都換了族類,可鑰匙原封不動。拳起手,握緊了,腿腳卻軟下來,溜到地上,站不起身,就抱膝坐著。這把鑰匙是叔伯兄弟幾個為各自晚歸設的約定。家中規矩,晚十點即閉戶,關前後門,此西門平素不進出,常年掛一把鑄鐵大鎖,於是,偷出鐵鎖鑰匙,私配一件,藏在樹洞內。都會的大家,子弟們難免沾染浮華風氣,夜間的去處特別多,不是說,海上升明月嗎?一九三七年淞滬會戰硝煙未散盡,「薔薇薔薇」 就處處開了。離開上海的前一晚,陳書玉還在西區舞場流連,準確說,出行的計畫,就是在舞場裡做成的。
坐一時,喘息稍定,奮發精神,試圖站起,這才發現周身癱軟。發力幾回,立住腳,手索索地抖,鑰匙噠噠地碰擊鎖眼,就是對不準。天又墨黑,乞兒的篝火被阻在另一面,借也借不到。他懷疑是不是換過鎖或者鑰匙,正決不定,月亮跳出來,咔噠一聲,手底下一彈跳,就是它!推進門,抬頭望一眼,只見防火牆剪開夜幕,將天空分成梯形兩半,一黑一白,月亮懸掛在最高的梯階上,像一盞燈。
門裡面,月光好像一池清水,石板縫裡的雜草幾乎埋了地坪,蟋蟀瞿瞿地鳴叫,過廳兩側的太師椅間隔著几案,案上的瓶插枯瘦成金屬絲一般,腳底的青磚格外乾淨。他看見自己的影,橫斜上去,綴著落葉,很像鏤花的圖畫。走上迴廊,美人靠的闌干間隔裡伸出雜草,還有一株小樹,風吹來還是鳥銜來的種子,落地生根。迴廊仿宮制的歇山頂,三角形板壁上的紅綠粉彩隱約浮動。跨進月洞門,沿牆的花木倒伏了,卻有一株芭蕉火紅火紅地開花,映著一片白——防火牆的內壁。他佇立片刻,忽生一念,當初造宅子時候,周圍定是空曠無人跡,直面黃浦江,所以會有防禦的設置,就像歐洲貴族的城堡,那是什麼年代?他的歷史課和地理課一樣馬虎,也受實用觀的影響,目力之外,在他就是不存在。天井的地磚,覆了青苔,厚而且勻,起著絨頭,亮晶晶的。兩口大缸被浮萍封面,面上又蓋了落葉,青黃錯雜,倒像織錦。
他立在天井中央,看自己的影。這宅子走空有多時了,有在他之前走的,又有在他之後;有往南,有往西,還有往東——兩年中,他收到過父親一封信,途中不計經歷多少時間,多少不知名的地點,信中所寫都是遲到的消息。問他身在何處,境遇如何,妹妹們是否可去投奔。他沒有回覆,一來時過境遷,妹妹們早就去了該去的地方;二也是,他們本來就是疏離的家人,彼此間並不怎麼親密。自祖父與伯祖一輩向下,各有二房和三房男丁,就像大樹發杈,再發成七八家,將個宅子擠得滿騰騰。從他落地,放眼望去,都是人,耳朵裡則是齟齬。他們家的人元氣旺,秉性強,就沒聽說有早夭的,生一口,活一口。放養著,從中挑一個寵慣,滿足為人父母的天性,其餘也不為不平,因為是大多數。他雖是這房獨子,卻不是那個被選中的,選擇多是隨機,沒有什麼理由,這才能說走就走。
現在,一宅子的人都走淨了,留下無限的空廓。昆蟲啁啾,樹葉撲嗍嗍划拉,窗扉和門軸時而的支扭,野貓倏地躍下,腳爪柔軟著地,還有一種崩裂的銳叫,來自木頭的縮漲,由氣候的乾濕度引起……這是靜夜的聲音,老房子的低語。這幢木結構的宅院,追究起來,哪裡是個源頭!榫頭和榫眼,梁和椽,斗和拱,板壁和板壁,縫對縫,咬合了幾百年,還在繼續咬合。小孩子的夢魘裡,就像一具龐大的活物。諸暨籍的奶娘拍哄夜哭郎:再哭,山魈來吃你!這活物大約就叫山魈,誰見過它?奶娘夜裡說,早起忘,沒有人去向她詢問。天光大亮,院子裡四處起煙,各房的老媽子爭洗臉水;小孩子搶奪淘籮裡的茨飯團,咬著上學堂;車夫敲著門,先是無人應,然後一窩蜂上,都說自己要的洋行上班的車;電話鈴響著,不知道打給誰,所以都不接,打的人也耐心,一直等著,終於接起來,對面又掛上了;無線電裡,小熱昏唱新聞,操一口浦東本地話;自來水開足了,嘩嘩淌;好天氣,都要晒被褥棉花胎,女人們的戰爭就開始了。也不知道怎麼一來,戛然間,塵埃落定。
木的迸裂,從記憶的隧道清脆傳出來,即是熟悉,又陌生。他回家了,卻彷彿回到另一個家。挪步上台階,推門,門不動,曉得是從裡面插上。透過門窗雕飾的鏤空望進去,依然舊擺設。堂案上列了祖宗牌位,兩樽青花瓷瓶,案兩翼的太師椅,一對之間隔一具茶几。鏤刻的門窗投在石台階,花影幢幢。花影裡移過去,移過去,忽然不見了,原來進去夾牆裡。夾牆底處,一扇窄門,推開來,一團漆黑撲面。手在壁上摸索,觸到開關,扳下來,不亮,供電局早已斷電。眼睛倒有些習慣,於是漆黑裡浮起一層薄亮,顯出一道木樓梯,手腳並用爬上去,陡然豁朗。他到了樓上陽台,沿陽台走一圈。樓上的房間全下了百葉窗,依次推過去,有一扇活動,下力搖幾搖,插銷脫落下來。慢慢打開,手撐住窗台,一條腿先上去,另一條再上去,進去了。是祖父的屋子,一個統間,前面臥房,後面書房。他不記得什麼時候曾經來過,其實,連祖父的面容都是模糊的。
拉開百葉窗,透進光,已是中天的月亮,將窗櫺照得通明。撩起夏布蚊帳,坐進去,摸出口袋裡半張麵餅,乾嚥著。蚊帳裡有一股艾草的氣味,居然滲漏過戰時的歲月,存留下來。吃完餅,褪去膠鞋,合衣躺下。綠豆殼的枕頭芯子,沙啦啦地輕響。翻身側睡,手在枕後頭摸到一柄摺扇,展開,看不清字跡,但有墨的餘香,不由想,祖父在什麼地方,還有父親母親,又在哪裡?思緒變得輕而且薄,升上去,漂浮在帳頂底下,罩著他。更聲敲響,不知夢裡還是醒裡,過去還是將來,他鄉還是故鄉,再有,那打更的人,是原先的一個,或者另一個?
二
人們稱陳書玉「小開」。上海地方,「小開」的本意是老闆的兒子,泛指豪門富戶的子弟,陳書玉大約屬後者。事實上,在他可視範圍內,家中無一人有經營,相反,多是無業,也不知坐吃多少代了,至此尚可繼續。雖談不上錦衣玉食,但也不缺,所以就沒有勞動的概念。到他這一輩,有出去做事的,並非出於生計,而是現代教育的緣故。祖父和伯祖穿長衫,父親伯父則一律西服革履,讀新學堂。晚清民初的人,都嚮往西洋,他們的家,看起來彷彿舊式,實際一點不保守,甚至是開放的。祖父臥房裡,有一具自鳴鐘,上足發條,每日午時,小木屋的柵欄門打開,跳出一隻金絲雀,連著叫十二聲。據家裡人說,是宮裡的玩物,義國人朝貢來的,後經一個太監的手,送給高祖。以此來看,高祖交遊廣泛,朝野有人,所以,遺澤蔭庇百年不衰,才會有今天的日子。
陳書玉讀的是交通大學鐵道系,不知如何形成,又根據什麼緣由,這家女子不定讀書,男孫都學工科。工科是西學的概念,中國道統中屬淫技奇巧,這又見出不是上等的門閥世家,更像新起,多少帶暴發的嫌疑。可是,誰會去追究呢?尤其身在事中,反而漠視來龍去脈,只當天生成。總之,他們家人都受新鮮的物事吸引,積極向學,至於學成之後當什麼用途,暫不考慮。他是個喜歡交友的人,進大學讀書,有一半是為結識不同的人,不免讓他失望了。同學中,多是埋頭苦讀,那些勤工儉學的青年,還要任職助教、宿管、抑或圖書管理員,少有閒暇。工科生天性又呆板,缺乏生活的興味,談話不出三句半就到了機械的動力世界。他們這一班,全是男生,沒有新女性的倩影。倘若時間充裕,憑他的單純誠摯,或許能交到一二個知己,可惜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學校就計畫南遷。去與留的混亂裡,方才建立起的一點同窗之誼也渙散掉了。他是留的那部分,讀書和學位的熱情本不強烈,遷走的又只電機和機械兩個專業,再則,也捨不下上海,購買的冬季音樂會套票還沒用完呢!
學校散了,他回到原先的朋友淘裡。
他們要好的幾人,稱「至友」不太像,因沒經過什麼考驗,只是玩樂的交道。要叫「死黨」,且未見其有道和謀,還是玩樂居上。倒是世人起的諢號「西廂四小開」,比較名副其實。「西廂」指的經常出入的地方,公共租界的西區,至於「小開」,即如前面說的,富貴門戶的晚輩。上海這地方,富貴要分兩頭說,「富」沒有問題,「貴」就可疑得很了。黃浦江開埠不出百年,都是一吊錢兩腳泥上江灘,本地民謠唱的「赤腳穿皮鞋,赤膊戴領帶」,大約可視作上海的發家史。從跑街先生做成大亨的,比比皆是。「小開」這稱謂也很有意趣,「小」字當頭,「開」呢,可能來自撲克牌裡的老「K」,通常用於幫會裡的頭目,所以,「小開」就有了點黑道的氣息。
「西廂四小開」裡,那三位一姓朱,一姓奚,一姓虞,互相暱稱為:朱朱,奚子,大虞,陳書玉叫「阿陳」。也有點像幫會。朱朱與阿陳是世交,坊間傳說,兩家有夙怨,陳家的中落與朱家有關聯,可事情過去那麼久,聽起來就像古代,孩子們都玩在一起了。奚子其實是讀書人家,祖父起就留洋學法律,父親也開律所,他自己卻學油畫。即非邏輯思維一派,也無辯術之技藝,還談不上衣食保障,唯同出西洋這一項,其餘都離家道甚遠。但子女多了,總有一二個走邊路,大人並不十分干預。大虞的人生與上幾位略有二致,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可謂延續祖業,就是木器。最早時候,先人依附海格路停柩所,開棺材鋪。海格路停柩所主要面對西人,老闆就是義國人。西洋棺材重雕飾,幾近藝術品。大虞耳濡目染,或者天性裡就有,對手藝和美觀都喜好,時常去美術專科學校旁聽,畫幾課寫生,於是,和奚子結誼。這一對和那一對且是在工部局夏季音樂會邂逅,都是買套票的朋友,有固定座位。年輕人都是自來熟,不很久便同進同出,各騎一架自行車,吹著口哨,一陣風去,一陣風來,成為一道街景。
四個人中間,家境數大虞殷實。一技在身,任憑改朝換代,都有飯吃。尤其殯葬業,愈是亂世愈是興隆。從棺材鋪起頭,開出幾爿細木工作坊,承接多是上等西人的訂製。油畫框;插屏鐘殼架;首飾盒,仿法國路易王朝宮廷用物;還有鳥籠子,好比一座古希臘城池,吃食、休憩、洗浴、如廁,細木棍柵欄區隔,開閉機樞,全用套榫,不打一顆釘。都說是中國傳統工藝,事實上,西洋也有。虞家和義國人打交道,曉得文藝復興和翡冷翠,那裡也出木匠。見過幾幅木器貼面的打樣,如同絲織般繁複堆砌,堂皇瑰麗,就知道,月亮不止是中國的圓。於是,再激再勵,求深求進,事業就一逕向上。中國的鄉下人,義大利其實也是鄉下人多,對於財富還是古典的觀念,置地置產,南市的幾條弄堂,周邊四鄉八里,都有虞家的田畝房屋,東邊有雨西邊晴,交上來的租子就吃不完。
奚家在滬上有些聲譽,打響過幾樁出名的官司,身價直線上升。但在世人眼中,律師總是開口飯,多一間寫字間而已。雖然上海新世界,新人類,舊俗尚有餘韻,所以當作末技。家道呢,大約僅夠列入小康。然而,事實上,滬上小康人家才是真正的聚寶盆。西區的新里,一幢幢西式樓房,半地下的汽車間停著汽車,花園裡栽著玫瑰花,小孩子穿吊帶短褲,白線長筒襪,牛皮鞋,僕傭送去上洋學堂,鋼琴彈著奏鳴曲,不是從這窗戶就從那窗戶傳出來,還有聖誕歌,平安夜的派對上,燭光融融映著長窗簾,「金哥貝,金哥貝」的一遍遍唱。業主們就是小康,他們是新起的階級,代表著社會的中堅力量。
相對來說,阿陳和朱朱代表的是過去,有淵源不錯,可已經在末梢上了。要一逕追溯,大約追溯得到清乾隆,可不是古代了!阿陳的老祖宗從台灣來到上海,開一爿船號,經營海運,順便建一個碼頭,停泊與裝卸。朱朱的老祖宗就在船號擔任通事,就是今天的翻譯員,專司洽談洋人的生意。小刀會攻占上海城——小刀會都出來了,像不像歷史書?小刀會砍了朱通事的首級,陳家這才發現船號早被掏空,勉強撐到同治年,每一樁事都有年號,也像是真的,同治年,清廷在上海設輪船招商局,這時候,陳家的祖宗也換代了,將船號與碼頭盤給招商局,得手的銀子,一直開銷到如今,數目之鉅,可想而知。朱家後來還有經營,豆行米市之類,終也發不起來,只維持溫飽。上海的正史,隔著十萬八千里,是別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渾然不覺。
這四個人,叫是叫「小開」,其實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倘若分開來,一個一個出場,大概都是一般人,但四個人一夥,集團軍上陣,就有一股子氣勢,年輕力壯,有來頭,又摩登,不叫「小開」叫什麼?四個人所以結緣,除興趣愛好相投,更重要的一項,就是經濟。經濟是一切的基礎,他們不是極富,又絕不是寒素。大虞和奚子兩家風氣比較謹嚴,也是上升時期的生活方式,兒女就不受縱容。兩個舊家呢,有餘心無餘力,手頭多少拮据著,但生性慷慨,便抵住了。兩上兩下,基本能夠持平。四人出行,或美式AA制,或中國式輪流坐莊,倘有特殊的理由,也不妨額外做東。比如,清明時分,大虞邀那幾個去郊外踏青。虞家本是南翔鎮上人,到滬上三代有餘,鄉土疏遠了,但老墳尚在。看墳人是族親,每年上木器鋪領餉,漸漸地,置下一片地,過起莊主的日子。這四個少年騎著自行車飛行俠般來到,好比天兵天將,鄉下人哪裡見識過。不免手忙腳亂,又殺雞又宰鵝,又摸魚又捉蝦。上海人都有一條嘗鮮的舌頭,獨對野生瓜菜起反應,番薯藤南瓜藤,剝去皮,裸出嫩芯子;萵筍葉,也是撿嫩的,搓了鹽,潷去水;剛露尖的豌豆莢,生著吃;肥田的紅花草,石臼裡捶成漿,和進麵糊攤餅;過年餘下的醃臘和糟貨燉成老火湯,野薺菜滾進去,白湯上面一層碧綠,自釀的米酒,新打的年糕、舂的米,點鹵的老豆腐,柴灶裡的煙火氣——這是吃,還有看。籬笆上的茄子花都是稀罕物,河邊爬的螃蜞,以為是大閘蟹的幼子,蜂子閃亮亮飛過,趕著捕捉差點螫了手和臉。看墳人家有一隻老山羊,小馬似的身量,毛長及地,性情溫順,於是四個人輪流當坐騎,沿了田埂,顫顫巍巍地走。鄉人們的眼睛裡,是為人夫為人父的年齡,卻作小孩子的形狀,都覺好奇好笑,看戲似地看。又有一個愛熱鬧的,真牽出一匹馬來,與他們玩耍。是匹兒馬,沒吃過教訓的,見不得生人,近一步,它退一步,再近一步,就撂蹄子。輪番上陣,輪番不得,最後,那人的七歲小兒,一翻身坐上背,得得跑遠了。玩過旱地,又玩水裡,乘一條舢板,河道裡划,看漁人握一束網,迎著日頭一脫手,先是一片,然後一兜,金水四濺。岸上的桃樹生出花骨朵,柳條爆芽,灌木抽枝,糾成一團,真是個桃花源!太陽西行,四人才踏上回程,車後架各馱一簍螺螄,一罈燒酒,一袋子蔬果,大虞又多一個豬頭和一條羊腿。抖抖擻擻,搖搖晃晃,一路騎去。
奚子的款待很別緻,旁聽會審。長三堂子的一樁凶案,情節頗似《玉堂春》,大報小報爭搶著第一手新聞,事主當年的接生婆都讓挖出來做文章。奚子的父親擔任辯護律師,所以才有這路子。門口幾重警衛,還是人疊人,翻幾座人牆,經幾道盤查,日前的通行證此時都不作數了,又打電話到裡頭找人,足有半個時辰,只見衛兵垂下槍口,雙扇大門間露一線縫,縫裡是奚家爸爸的臉,面有慍色,生氣兒子多事,當了眾人且不好發難,遞出一串掛牌,一人頸上一個,算作庭堂職員,進去了。裡面固然清靜些,卻也座無虛席。奚子到底熟悉,領他們從後樓梯上到二層,主要是記者和連載小說的寫家們,花插著坐下來,再等少許時間,鈴聲響起,開庭了。與場外的熱烈氣氛相比,庭訊卻顯得平淡多了,在一些瑣細上來回糾纏,出生原籍姓名年齡,這幾項就占去有一個時辰還多。煙花業裡,都是假作真時真亦假,外行人聽不出與案情有何關聯,奚子隔著人告訴同伴,必須驗明案中人的正身,才可向下進行。左右座又都噓他,攪擾了聽話。早先的激動此時已經平息,只覺得熱和渴。樓座離得遠,越過無數人頭,望見被告的頸背,後腦上梳一個髻,不知有意還是無心,顯得老而且醜,彷彿前一個世代的人,毫無青樓風月的意蘊。於是,四下交換眼色,取得一致,起身退出了。
異性交遊是朱朱的特供。四個人裡面,朱朱相貌最好,當然,決定於哪個角度看。他屬潘安型的美男子,唇紅齒白,嘴角有兩個笑靨,即讓女子生性愛,也讓女子生母愛。到舞廳裡,總能結下朋友。職場有職場的規矩,跳舞不能白跳,出了舞廳,就是自己的時間和自由。「四小開」一行,少不了要有紅顏相伴,多是朱朱的「姊姊」們。姊姊未必年長,可朱朱卻是永遠的弟弟。姊姊們,教育程度多在中等,甚至以上。上海的娛樂圈,幾句英文是必須的,客人們要說些時事時政,科學哲學,即便情話,不定也是襯著詩詞底子的,如今的風尚,又趨向書香型。所以,就是現代女性的裝扮,梳學生頭,戴大黑框平光眼鏡,夾幾冊書本。既然不談婚姻,戀愛就須謹慎,行為舉止矜持。他們表現出來的一種新式關係,到左翼文化人筆下,是「五四」的精神,坊間世俗,則就是「小開」的形狀。
阿陳家幾代賦閒,與社會斷了聯繫,沒什麼人脈,且囊中羞澀,沒有剩餘資源作長例外的奉獻,要說也有,那就是秉性了。在他紈絝的風流外表下,其實是一顆赤子的心,為人相當實在。他們之間,平日裡的聚合,都是由他召集;大小事務商議,也由他串聯與互通,用餐的定位,餐後拆帳的計算,姊姊來到,又是他接應得多,就好像是姊姊們的大哥,真有幾個認他兄長自稱妹妹的。所以,看上去他是個可有可無的人,實際上,沒有他,四小開就成了散沙,姊姊們會變得沒著落——弟弟將她們帶進來,就沒他的事了,那兩個呢?新鮮過去也淡下來。遇到聰明有趣的,尚多幾個回合,只是「姊姊」這樣風月場上的人,善言懂解多半在敷衍上,往深裡就沒大可言的了。他們又不是一般的舞客,是大學生,愛好藝術,有情懷,不止紅顏,還須知己。上海歡場最不缺的就是紅顏,走馬燈似地轉,然而,女人的世界總歸是狹小的,他們則五湖四海,家雀安知鴻鵠之志!很快就覺無聊,枯坐著,人家再有涵養也露出窘來。阿陳心中不忍,暗中埋怨朱朱多事,還有點薄倖,可是人性都是天生成,活潑的「弟弟」,讓「姊姊」拴死,也是不忍的。其餘更是無辜的人,沒義務擔責任。最後,只好攬過來,漸漸的,就有屬意他的人。他不木訥,相反,算得上敏感,只是樣樣不落忍,一逕被推著走。其時,聽到去西南的計畫,立即報名,拔起腿跑路。實在是事態發展,耽誤不得了。
第一章
一
一九四四年秋末,陳書玉歷盡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這一路,足有二月之久。自重慶起程,轉道貴陽,抵柳州,搭一架軍用機越湘江,乘船漂流而下,彎入浙贛地方,換無數貨客便車,最後落腳松江,口袋裡一個子不剩,只得步行,鞋底都要磨穿。但看見路面盤桓電車軌道,力氣就又上來。抬頭望,分明是上海的天空,鱗次櫛比的天際線,一層層圍攏。暮色裡,路燈竟然亮起來,一盞、兩盞、三盞……依然是夜的眼,他就要垂淚了。
二年前,隨朋友的弟弟、弟弟的女朋友、女朋友的哥哥、哥哥的同學——據說是韓復渠司令的侄系親屬,絡絡...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弟五章
第六章
《考工记》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弟五章
第六章
《考工记》跋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
 10收藏
10收藏

 19二手徵求有驚喜
19二手徵求有驚喜





 10收藏
10收藏

 19二手徵求有驚喜
1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