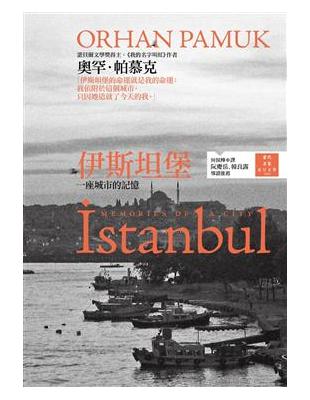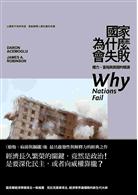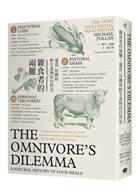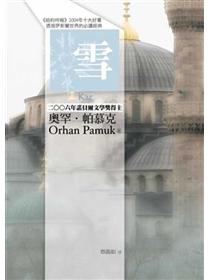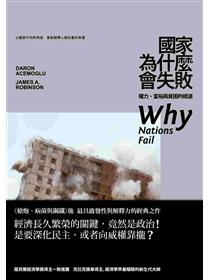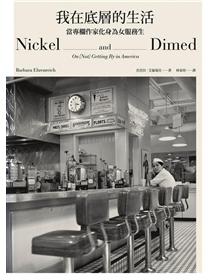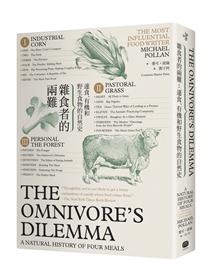得獎紀錄:
1、1979年第一部作品《傑夫代特先生與他的兒子們》(Cevdet Bey ve Oğullari)得到Milliyet小說首獎,並在1982年出版,1983年再度贏得Orhan Kemal小說獎。
2、1983年出版第二本小說《寂靜之屋》(Sessiz Ev),並於1984年得到Madarali小說獎;1991年這本小說再度得到歐洲發現獎(la Decouverte Europeenne),同年出版法文版。
3、1985年出版第一本歷史小說《白色城堡》(The White Castle)這本小說讓他享譽全球,紐約時報書評稱他:「一位新星正在東方誕生--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這本書得到1990的美國外國小說獨立獎。
4、1990年出版《黑色之書》(The Black Book)是一個里程碑,這本小說讓他在土耳其文學圈備受爭議的同時也廣受一般讀者喜愛。1992年他以這本小說為藍本,完成電影劇本《神秘面容》(Gizli Yüz);並受到土耳其導演Ömer Kavur的青睞。
5、1997年《新人生》(The New Life)一書的出版在土耳其造成轟動,成為土耳其歷史上銷售速度最快的書籍。
6、1998年他的第六本小說《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出版,這本書確定了他在國際文壇上的的文學地位;獲得2003年都柏林文學獎,這個獎獎金高達十萬歐元,是全世界獎金最高的文學獎。
7、2006年,奧罕‧帕慕克榮獲文壇最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
名人推薦:
伊斯坦堡就是我的命運
──帕慕克的呼愁
台北‧韓良露‧文
一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之中,創造出文明的地方一定是城市;偉大的文明誕生在偉大的城市之中,但偉大的城市並不一定能創造出大的文明。
有的城市文明在歷史的長河中湮沒,成為文明記憶的悲歌,如中國《清明上河圖》中的繁華汴京(開封);有的城市文明經歷一次又一次死而復生,成為永恆的火鳳凰城市,如義大利的羅馬。
城市是文明的化身,乘載著無數或死或活的人類的集體意識,對城市或古或今的總合靈魂最敏感的往往是作家,他們有如通靈人,飄蕩在歷史的黃泉路上,傾聽著無數幽靈的文明低語,再以寫作為媒介,為世人訴說城市的前世今生與命運曲折,城市的歷史因此在作家的話語中暫時還魂。
不是所有的作者都剛好可以成為某座城市的靈媒,這需要歷史命運的因緣與個人身世的際遇相連,但當作者有幸成為某城市的靈魂代言人時,往往意味著作者將成為城市的分身,成為文明的重量與能量將作品推升至較高的視角,俯覽城市命運的起伏變異,作品的意義成為城市的隱喻。
張愛玲書寫上海,其作品中角色的悲涼與傾覆,成為上海性格的象徵。白先勇的台北人的離散與追憶,成為台北身世的記錄。普魯斯特的巴黎人的時間囈語,成為「美好年代」的記憶史詩。喬哀斯的尤里西斯,恍如一場都柏林的神話夢遊。
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當然了解以上種種論述。他曾說過,伊斯坦堡就是我的命運。他曾想寫作一部伊斯坦堡的尤里西斯,記錄伊斯坦堡一日的時間神話與街道史詩。雖然這部作品並未以這樣的方式寫出,但他選擇了用不同的方式述說伊斯坦堡的命運,不管是《白色城堡》或《我的名字叫紅》,或是自傳體的《伊斯坦堡》等,這些書中千篇一律的核心角色都不是那一個人,而是一座城,伊斯坦堡是帕慕克的終極主題。
二
帕慕克在《伊斯坦堡》一書中說:我們一生當中至少都有一次反省,帶領我們檢視自己出生的地方,問起自己我們何以在特定的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這一角。
這樣的問題是研究占星學如我,每天都會反思好幾次的事,當帕慕克在二○○○年的十一月底來到台北,在麥田出版社的晚宴中我遇到帕慕克,帶著占星學好奇的我立即問他是在那一個特定的年月日時誕生在伊斯坦堡,因為我想為他繪製一張命運星圖。帕慕克以並不驚訝的方式回答我的問題,來自古老的伊斯坦堡的人是不該對古老的占星學陌生的,不管是希臘或阿拉伯的占星學,伊斯坦堡都曾是重要的奧祕之城。
帕慕克何嘗不是在為他自己或伊斯坦堡做同樣的事呢?只不過他的視角來自文學靈魂的敏感,他靠記憶與想像去爬梳個人及伊斯坦堡命運的肌理,尋找記憶迷宮中的符號,再透過想像解謎,如同占星學辨識星象密碼的隱藏訊息一般。
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七日(時間保留)誕生在伊斯坦堡的帕慕克,以無比巧合的方式在這個特定的日子來到了人間。他的太陽、水星、金星都落入希臘神話中的信息使者雙子星座之中,這個在神話中代表天使米加勒的雙子星,負責的工作是與世人講道,將宇宙或神的訊息用人類聽得懂的方式傳說出去。雙子星的雙重性,既是尋求對稱,亦是不斷衝突的正反能量,在永恆的拉扯與衝突中追求和解與統一。但任何一次能量的暫時匪合,勢必開展新的對立。這是無止盡的輪迴。
三
人類歷史中曾經存在過不少是有雙重意義的城市,如印度與伊斯蘭雙靈魂的德里,這些雙重意義的城市,或因為宗教、種族、語言或地理環境(一條河,一座山的分隔)的差異,而形成雙重或多重的隱喻。但在今世界中,要選出一座最強大,最具有雙重意義的城市,我以為非伊斯坦堡莫屬。
伊斯坦堡,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建立的新都,位於亞洲大陸和歐洲大陸的交會點,代表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面對場。古名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堡,又名東羅馬,和西羅馬是雙重屬性的宗教概念:東羅馬是東方的,語言是希臘語,信奉的是希臘正教;西羅馬是西方的,語言是拉丁語,信奉羅馬天主教。但在西羅馬帝國淪亡後的千年歲月之中,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卻成為西方文明的守護者,將希臘的、羅馬的文明殘火像聖火般傳遞下去,義大利在中世紀後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的潮流即來自君士坦丁堡的推波助勢。
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文化,本質上是亦東與亦西的文化混血,但在一四五三年之前,這種雙重對立,仍在西方基督教大文明的體系下對稱,但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或君士坦丁堡陷落,怎麼稱呼,端看你站在歷史的那一邊,亦有如中國或台灣的不同歷史觀點),從拉丁語源的君士坦丁堡之名,變成突厥語源的伊斯坦堡,東西方文明的對立擴大成游牧文化與城邦文化的對立,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對立,亞洲人種、語言與歐洲人種、語言的對立。
一直到今天,界定伊斯坦堡的身分,仍是困難的工作。贊成土耳其加入歐盟的人說,伊斯坦堡有一部分屬於歐洲大陸,何況歐洲人欠伊斯坦堡一個大恩惠,即伊斯坦堡保護了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血脈。但不贊成土耳其加入者也會說,伊斯坦堡更多的部分屬於亞洲大陸,五百年來土耳其的歷史發展早已使伊斯坦堡成為伊斯蘭文化的養子,根本不可能認祖歸宗,土耳其若加入歐盟,只會造成文明的遺產糾紛。
四
太陽、水星、金星都在雙子座的帕慕克,恐怕挑遍全世界也找不到一個比伊斯坦堡更適合他去面對文化、歷史、地理雙重性的地方。有趣的是,帕慕克的家族三代居住在分占亞洲和歐洲地景的伊斯坦堡歐洲區之中,祖父是以代表西方強勢工業文明的鐵路投資者致富,父親是西化得不成功的商人,卻能以翻譯法國詩人梵柴希的詩自娛。
帕慕克初高中唸的是外僑學校,原本極有可能像他哥哥一般高中畢業後就赴美留學,作一個西化的現代土耳其人。但帕慕克身處的時代,遠比他祖父的時代,在東西文化認同上有更大的衝突。在他祖父及父執輩那一代,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剛毀,新的土耳其共和國一心西化及現代化(這多麼像中國民初的命運啊!),土耳其共和訂定新憲法,還訂定新的語文、衣著,當時的選擇是單一的,朝向西方是主流,反之是歷史的倒退。但到了帕慕克這一代,主流變成分歧之道,伊斯坦堡從歐化的五十萬人口之城變為本土化的一千萬人口之城,從亞洲大陸湧入的移民帶來了伊斯蘭式的東方價值及生活態度,伊斯坦堡再度陷入東西方文明的強大衝突之中。
奇異的是,帕慕克所經驗的文化衝突,亦反映在他個人星圖中。他的太陽、水星、金星都在雙子座,代表他的顯意識認同伊斯坦堡或土耳其的本土性,因此除了去紐約三年求學外,他一直是伊斯坦堡居民。但帕慕克的月亮卻在代表遠方的射手星座,剛好和雙子星座呈一百八十度,意味著他的家庭根源及祖先血脈(月亮的意指),有強烈的外國與異族認同。帕慕克這一姓氏,即意涵皮膚較白的人,在亞歐人種中,即為較接近歐種的一方。
星圖中太陽和月亮呈一百八十度的人,也意謂著父母長期的對立;帕慕克從小便活在父母親衝突、分裂及分居的狀態中。父親是個浪漫不實際的人,卻教會他人生很短,要做自己愛做的事。母親是保護和約束他的人,要他把人生之夢落實在現實中。為了母親,帕慕克放棄繪畫,但找出了父母親勸告的折衷之道,太陽和月亮的對立形成互補之途,他選擇成為作家來安頓夢想與現實的身分。
五
帕慕克在《伊斯坦堡》書中,好幾次提到隱藏的對稱性,他的小說藝術與人生態度的核心價值即在於此。在《我的名字叫紅》中,他藉著東西方不同的看待世界與神的觀點,表達全知的主觀藝術與肉眼的客觀藝術之間的不同美學,沒有誰是對的或好的,只是宇宙本身的對稱性與不同顯相而已。
帕慕克是好的藝術家,絕不會讓他的雙重性或對稱性用簡單的二元性表現,他編織的是敘事的迷宮,對稱性隱藏於繁多的對比之中。
帕慕克尋找個人和伊斯坦堡這個城或土耳其這個國家或伊斯坦堡/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不同的歷史分身的認同時,用的不是簡易的和解之道,反而像他形容自己和他爭奪母愛的哥哥之間從童年期無止盡的爭吵、鬥毆、衝突的方式一般,幾乎把對方當成敵人,但最終卻發現他最親密、最容易思念的人,就是一直和他兄弟鬩牆的人。帕慕克對待他的城市、國家、歷史、文明不也是,一直在翻歷史的舊帳、找時代的麻煩、挖東西文明的爭論。這個帕慕克寫出了在土耳其極暢銷的書,也被土耳其伊斯蘭正統教派視為敵人。
這一切的對立,帕慕克恐怕是身不由己。他恐怕會說自己就是有一個容易惹起爭端的靈魂。但在現實人生的角色扮演上,有時帕慕克也努力當一個隨眾從俗的人。就是在《伊斯坦堡》書中,帕慕克不斷地提到他每次參加過家族宴會後,都會發誓下一次不再去,但之後卻仍忍不住參加,而且當場也不見得不快樂。
帕慕克來台北時,我和他一起參加了兩場晚宴,以藝術家的標準而言,帕慕克實在演出了「好客人」的角色;他有著東方式的有禮,會稱讚主人的飯菜,也有著西方式的周到,跟一大群陌生人在一起還會努力融入大家的話題。尤其在土耳其大使舉辦的官方晚宴中,帕慕克讓我想到了喬哀斯《都柏林人》中〈逝者〉那篇小說的男主角,合乎禮儀地與官樣文章互動,但其實又心有別思地觀察這一切。
帕慕克關心現實中的人,他絕不是那種想遠離人群的作者,他要寫出真的人,因此他的小說中會有常人的逼真靈活。在帕慕克的世界中,家人或他人都是他凝視人間與宇宙全像的材料,材料要真實,但他表達的絕不是這些人表達的,他不是自然主義的作家,他要創造的是他個人的現實神話,即無數人間碎片所組成的宇宙對稱性,文學中的統一力場。
六
羅馬門神的頭有兩張臉,一張朝向過去、身後,一張朝向未來、遠方:當帕慕克來者不拒的和要求與他一起拍紀念照的人合照時,別以為他擺出燦爛笑臉的同時,心中不會存有「我為什麼要和這些陌生人親密合照呢?」的荒謬感;當他在東區世貿中心頂層的國際聯誼會參加晚宴時,在愉快的社交閒話中,別以為他不正在觀察台北西化、殖民化的一面。帕慕克對待土耳其也是如此。他特別關心土耳其在現代與歷史之間徘徊的鬼魂。
《伊斯坦堡》書中,帕慕克用「廢墟」、「呼愁」兩個詞作為伊斯坦堡的隱喻。
伊斯坦堡是歷史的廢墟也是文明的廢墟,有如文藝復興之前的古羅馬,一座衰老實用的城市,湮沒在鄂圖曼帝國遺跡的餘燼之中。當伊斯坦堡人習以為常地在廢墟間生活,歷史將成為沒有意義的辭彙,反而將現存的一切廢墟化,才能自在地活在歷史的廢墟中。但帕慕克不想讓他的城市及個人生命廢墟化,他檢視著廢墟中的遺蹟,尋找文明有意義的印記,藉以在小說中重建偉大的伊斯坦堡的魂靈。
伊斯坦堡人面對歷史的虛無,有一種導體的情緒,帕慕克稱之為「呼愁」,呼愁一詞的根源來自阿拉伯語,代表心靈深處的失落感。呼愁可以是陰暗的情緒,讓人陷落在憂傷之中,卻也可以是創造性的情緒,帶領人進入詩意的人生氛圍。
對伊斯坦堡,帕慕克有著強烈的呼愁,在《伊斯坦堡》書中,他比較像是詩人而非小說家,詩意的追尋與體會是《伊斯坦堡》的基調。許多篇章都寫很美,充滿隱喻,像描寫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霧;作為歐亞大陸分隔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也成為帕慕克的心靈地標,這是分隔亦是融合的象徵,文明會改變,城市會改變,但博斯普魯斯不會變,同時擁抱歐亞大陸。
在占星學中,海王星是海的象徵,亦是藝術的象徵,帕慕克之所以成為優秀的作者,靠的就是他的太陽、水星、金星在雙子星座,和位於天秤座的海王星形成十分有力的吉星。海王星位於天秤座代表平衡與融合的理想,這是帕慕克的夢想根源;在現實的對立、對稱之中,完全藝術的融合。
而博斯普魯斯海峽成為他的命運之海,「生活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帕慕克在中寫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隨時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魯斯沿岸。」
韓良露
寫過影評、電視和電影劇本,製作過紀錄片、新聞節目,喜歡研究天上星象、收集地上的城鎮,去過六十幾個國家,足跡踏遍三百多個大小鄉鎮,目前定居台北。韓良露對美食的啟蒙甚早,好聽飲食掌故,愛讀食譜食經和下廚。最喜歡藉由飲食和旅行,與各種不同的文化做密切的心靈交流,體會煮食者的美好用心,是全方位的生活家。著有:《雙唇的旅行》、《食在有意思:韓良露與朱利安的美味情境》《美味之戀》、《微醺之戀》等飲食文學書;《大不列顛小旅行》、《狗日子 貓時間》、《舊金山私密記憶》等旅行文學書;《12原型星座》、《生命歷程全占星》、《寶瓶世紀全占星》、《人際緣份全占星》、《愛情全占星》等星座書;以及《有心,就可以幸福》、《生活捕夢網》、《浮生閒情》等生活札記。
這城市令我憂傷 /阮慶岳
這是小說、自傳、還是某種城市史?
閱讀著奧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堡》時,我問著自己。
讀完,依然不能清楚回答自己。我告訴自己,文類與企圖的多向交織,大概就是這書的意想與特質吧!
我知道在主架構上,帕慕克應該是以沙特自傳體書籍《The Words》,來作為這本書文學創作的出發點。那是一種人正立在生命峰坡處,回顧兼前眺的自我凝看,因此除了對自身生命作攬照外,常可同時引出對其他面向的觀視;但也因為這畢竟並非是與生命最終告別時的迴光絮語,因此自然容易見到陳述多於懺悔、掏揀甚過返照、織錦忙過袒露的書寫風格,而且對他人與自我的某種宣告,往往明顯大過對自己的省思低語。
但這或就是帕慕克原本的意圖。像他讓伊斯坦堡的近代城市生命史,強力在書中與個人生命交織難分,彼此眺看、鄙夷、緬懷的相互糾纏。城市扮演著既像祝福、也像詛咒的雙面天使角色,讓人愛恨交夾。在書中他寫著:
所謂不快樂,就是討厭自己,討厭自己的城市。
「我真的需要這個總是掛著面具、不肯現出真貌的天使嗎?」我好像聽見聰明也頑皮的帕慕克,不斷審慎的衡量質問著自己。
是的,伊斯坦堡真的值過自己的生命嗎?但是,好奇心與某種未明的誘惑,使帕慕克似乎不願也不能捨棄這個對決般的面具天使。城市像其他一切難於割捨生命瑣碎一切,習習伴隨著晚風的陣陣吹來,帕慕克望著遠邊的西天,猶豫著不知當開窗迎迓,或閉起來視而不見。
伊斯坦堡作為輝煌歷史的鄂圖曼帝國殘餘廢墟遺址,作為東西文明近世代相交傾軋的戰場,作為自身與他者間曖昧難自明的身分,都讓帕慕克有著難於確立自己觀看伊斯坦堡位置點的惚恍模糊特質;而尤其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強勢介入,更加添了這樣彼與此間恩怨情愁的複雜性。
這本書底層款款流淌的,自然還有帕慕克以及伊斯坦堡,究竟當如何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焦慮與矛盾。這裡的西方文化,可能是另一個讓帕慕克的位置點,更形顯得撲朔迷離的巨大幽靈。
他在書中寫著:「就像一隻眼睛始終盯著西方的每一個伊斯坦堡作家,我有時因不知所措而感到痛苦。」
無法移開自己書寫時不斷遠眺他者的目光,有可能終究會混淆了自己與他者的位置關係,譬如:我是他者或我能成為他者嗎?還有:我書寫時期待的讀者究竟是誰?本來這可以不必是書寫時思考的問題,但當自我位置讓作者「有時因不知所措而感到痛苦」時,這就是亟待被認真檢驗與釐清的事情了。
也許我們可以以這樣一個軸線,來簡單閱讀這本書:鄂圖曼帝國瓦解─—伊斯坦堡的凋零—─家庭意義的空洞虛化─—自我位置與身分的難明。
若回到文學來看,全書會讓我嗅聞到普魯斯特與喬哀斯的氣味。或這麼說吧,體味與溫度接近普魯斯特,肌理容貌則是喬氏基因。因為,當帕慕克真正迷人時,是十分難於抗拒的,他像是個人人憐惜的純美哀傷男孩,可以唇齒間喃喃不斷吐露出無花果般的芳香語句,意象則閃爍跳躍如同眼中盈盈欲出的淚珠;可是他又時而小心翼翼如世故的說書人,不斷他者般置身事外的望著自己,並聰明機智想著再下來故事的合理性,詩意中暗藏著某種惶惶的焦慮與不安。
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可能是他真正想召喚,並與之對語的那個隱身神明,然而有趣的是,喬哀斯先生卻總是會不邀而至(關於這個,晚些再說)。《伊斯坦堡》前段的書寫,有著濃濃《追憶似水年華》裡,因時間的流動與凝止,所萌生的哀傷詩意性,這也證明帕慕克捕蝶追虹的能力,都絕對優質難敵;而對這個天真完美世界終將碎化逝去,對童年記憶必是不可挽回的緬懷追念,也都能成功編織出某種帕慕克宣稱為「呼愁」的動人情緒,讓人沉陷難拔。
對微小細節不遺餘力的屢屢作觀照,是帕慕克和普魯斯特可以同樣身為哀傷男孩,並帶引我們墜入另一個迷人世界的原因之一。兩人都有著某種或因長時疏離與寂寞而生的內向自我獨特視點,與因過度受寵而微微傾向自毀的個性,這些質地自然地編織出一種濃烈的華麗與豐饒。但這同樣的編織,普魯斯特卻顯得層理更交織細密,雖然他所觸及的外在廣大現實與知識典故,都遠遠不及帕慕克來得有企圖與扎實嚴謹;也就是說,普魯斯特一直堅持著男孩的視角,拒絕成人們以知識與歷史觀,所建構出來社交般的優雅交語法則,作為被接納參加成人禮的誘引。
普魯斯特堅持著他對世界微觀的哀傷低視角,拒絕以被建構的知識(或任何成人價值觀)來對這底層情感作掩飾。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堅持,他得以透過微小,視見真正珠寶般的生命內裡底層。因為本來微觀的目的,不是為了見到細小物,也不是要顯得更楚楚動人,而是要見到那總是隱身的某種不可見物,而這樣的不可見物,常是偏愛藏身於細小物間的。
我覺得這是普魯斯特與帕慕克間,既細小卻也重大的差異處。
當然帕慕克畢竟不是普魯斯特,他們各有自己的世界要面對與建構。帕慕克的確並沒有如普魯斯特那樣,堅持讓自己全然停留在一個單一完整的世界觀裡,而不斷的躍入躍出於宏觀與微觀、自我世界與外在現實、此刻與歷史間,也就是在讓自己內在自由流淌的同時,會不時顯得理智的拉遠眺看全局走向,讓外在的鋪譜與內在的竄流,同時雙向並走。
這樣的寫法其實是更接近喬哀斯的了,我們或可以簡單並世俗的就暫時叫這個作「文以載道」吧!
文學必有其意在言外的功效,只是作者要不要讓這暗藏的話語,由自己親身安排的包裹入書寫裡,還是讓話語自己決定現身與萌芽的方式,絲毫不做過強的主導與安排。這其實也是普魯斯特與喬哀斯寫作上的態度差異,喬哀斯是長於控制書寫背後的聲音與聲張的,普魯斯特則是少見能讓聲音可以不受干預,而依舊自己自然流露的。
我覺得帕慕克的文風隱隱有普魯斯特的氣味,但是他其實在技巧與信仰上,是接近喬哀斯的。
這無關好壞,而只是作者的本質為何的問題。帕慕克作為一個作者,讓我們尤其容易注意到他身形轉換的漂亮與優雅,也就是說,他可以同時穿梭自己在許多全然相異的風格與形貌裡,讓讀者因炫目而難於辨出他的真實身影。但是,雜貨店式的攤列,與百科全書式的列舉,若不能真正刻畫出作者的思索與關懷何在,就尤其更要小心的自我檢驗,看是否有著賣弄技巧與知識的嫌疑,以及對讀者有無輕忽與失卻誠懇性的態度出現。
聰明絕對是作家要小心收放的那頭獵鷹,因為獵鷹不但可以獵回肥美野兔,也能回頭啄瞎獵人雙目。
就如同文章開頭講的,我覺得這本書技巧與文風多層交織,有些章節可以讓人迷醉得幾乎心疼,例如他寫他的母親:
「是電梯嗎?」母親問道。
我們兩人都停下來聽,卻聽不見任何讓人覺得是電梯的聲音。我父親並未在上樓途中。母親再次專心於紙牌上,精力充沛地翻開它們,我驚異地望著她。她的舉止動作小時候讓我覺得舒緩鎮靜,儘管在她收回她的愛時,見她這般舉止使我痛苦。現在我已經不曉得如何解讀她。我感覺自己陷入困境,在無限的愛與憤怒之間左右為難。
帕慕克絕對是個華麗、優美與充滿才氣的作家。但他的寫作有著某種奇怪的自我困惑,像望著鏡中映照出來自己的影像,忽然驚慌起來的男孩。或許帕慕克真正的迷團還是他自己,也就是他在書中所宣稱的「另一個奧罕」,他是這樣作著描述的:
在我整個童年以及大半的青春期,他(另一個奧罕)始終纏繞在我心間。冬夜走過城裡的街道時,我總會透過淺橙色的燈火凝望別戶人家,幻想和樂的家庭過著和樂的生活。而後我想到另一個奧罕可能住在其中一戶人家,便不寒而慄。隨著我逐漸長大,幽魂成為幻想,而幻想成為反覆出現的惡夢。在某些夢裡,我問候這位奧罕─—總是在另一棟房子裡─—的方式總是驚恐的尖叫;在別的夢裡,我倆在可怕無情的沉寂中逼視彼此。
因為文學是這樣難,既不可織網捕捉,也無法積累成富;而書寫更不是犁田,可以一畝一畝犁耕過去的,以為必然一株不漏;它跳躍、自在隱身現身、並善於讓守候者失望。
因此,我們還是該向帕慕克致上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