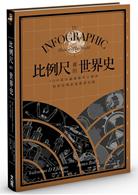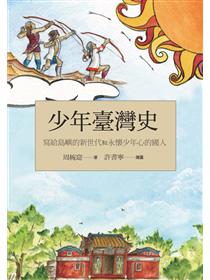圖伯特、Tibet與命名的力量
唐曰烏斯國、明曰烏斯藏
今曰圖伯特、又曰唐古忒
-《西藏誌》
上述文字是清初一個關於地名沿革的有趣評語,徵引自一部十八世紀佚名作者的Tibet方志,也許會讓讀者感覺是瑣碎而玄秘的藏學知識,雖然令人感到好奇,卻似乎與今日理解Tibet議題沒有什麼相干。而它也確實相當奇怪:作者說在他的時代,這個地方稱為「唐古忒」(“Tangut”),又稱為「圖伯特」(Tibet)。這一點真的與現代讀者無關嗎?正好相反,作者藉由告訴我們「圖伯特」這個名字在清朝就是Tibet的名字之一,碰觸到一個二十一世紀初嘗試以中文寫作Tibet的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若要以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文化與民族整體來稱呼那一塊廣袤的土地,而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數個行政區之堆砌時,究竟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的急迫性之所以未引起重視,很大的程度正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指稱Tibet與Tibetans的名詞已經非常僵化。然而那樣的拘泥與束縛早該讓我們質疑建構在這些名詞之上的人為結構。即使我們不談意識形態或後現代的術語(以及囈語),然而在這個例子裡,語言就是力量。因為中國能夠安排、限定關於Tibet詞彙的意義與範疇,因此有了界定Tibet、定義Tibetans的本事。它允許中國在討論Tibet議題時,可以單方面決定其最基本的條件。這些議題將在本文之後的章節陸續提到。
現在我們看到有愈來愈多以中文寫作的文章、部落格的貼文──有些來自圖伯特的作家、許多來自台灣的網友、甚至還有想辦法突破中國網路防火牆的人──正在接續上述這位十八世紀的不知名中文作者所未完成的,就是使用「圖伯特」,或者它的一個變化形式,「圖博」,來稱呼Tibet,是一件令人欣喜和期待的事。而就是為了本文即將闡明的理由,本書將使用「圖伯特」來指稱Tibet文明所在的世界和博巴(譯按:亦即中文習稱的「藏族」)所生活的地方,一個疆界遠比今日西藏自治區更加悠遠遼闊的國度。
大部份使用中文的人所習用的Tibet 正式名稱,是西藏。這個名詞的來源廣為人知,從官方修訂的歷代正史與其他常見的文獻所紀錄的用法,亦一目瞭然,容易理解。西方的圖伯特支持者有一種普遍的錯誤觀念,那就是西藏意謂著「西方的藏寶屋」,而會如此命名是因為中國視此區為一礦藏極為豐富、有待開採開發的寶地,這當然是大錯特錯。西藏一詞的「藏」字,雖然可以意謂「儲存」,但在這裡只是因為它音譯了Gtsang,指的是組成此區的一部份,一般稱為圖伯特中部地區,也就是博伊(譯按:即中文習稱的「藏文」)裡的Dbus-Gtsang。在明代,Dbus-Gtsang被翻譯成「烏斯藏」。 清朝時,這個名詞則變成了「衛藏」(也是Dbus-Gtsang之音譯),最後再演變為「西藏」,以表示其方位在西邊,而其兩個音節的聲音,又與之後中華民國政府為圖伯特東南部的康區(Khams)創建之行省「西康」相類似。
這一切所造成的結果是,「西藏」至今指稱的,依舊只有圖伯特中部以及一小部份的康區,而這個名詞所傳達的,就是上述的定義,也唯有那層意義而已。然而藏學研究的更廣闊世界,也是博巴所思維感知的世界,係將Tibet看成是三個主要地區所組成的地方:圖伯特中部(衛藏)、康與安多。目前有許多來自圖伯特、台灣、中國的作者與部落格作家,愈來愈體會到這一點,因此,也愈來愈多人使用圖伯特(或圖博)來指稱博巴所理解的Tibet。這當然具有顛覆的意義:博巴在中文的書寫裡,使用一個他們自己選擇的名字,是為了重新掌握他們被剝奪的,並且採取行動來定義他們自己。
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整套少數民族和各種與民族相關的語系,充滿了藉由定義以遂控制目的的政治操作。「少數民族」這個名稱本身,就已將所有如此被稱呼的民族貶降為同一層次,不論他們是人口數百萬、曾是一個政治強權、不但有自己的政府、還有嫻熟自己語言的官僚系統、擁有一部充滿自覺的歷史;或者人口不過數萬、沒有國族史的族群。
我們如果聰明的話,就應該記取「西藏」的意義先天即由政治所定義的事實: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其定義的範圍甚至比現今更小得多,因為康區的絕大部份(甚至一部份的「衛」,Dbus),都被畫進國民政府的西康省地圖裡,雖然國民政府對此區鞭長莫及,只有在名義上統治而已。更不要說,今日位於青海、雲南、甘肅境內的圖伯特區域,都不包括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所定義的「西藏」之內,一如它們今天也都不被涵括在其中。因此,傳統與歷史的Tibet,至今都沒有一個單一的、中國官方所承認的中文名詞來指稱。當然,我們可以使用說明性的文字來描寫它,如「藏族居住地區」。然而,那是個描述,而不是個稱呼。這麼多作者漸漸偏好使用圖伯特一詞,顯然其來有自。
描述圖伯特地區的詞彙,以其特殊的拘泥和僵化,拖累了描述博巴作為一個民族的詞彙,使之蹇滯難通。如果Tibet只能等同於西藏,而西藏∕Tibet僅只能指西藏自治區,描述博巴整體的名稱也被附加人為的僵硬規矩。他們可以被描述為「藏族」,然而「西藏人」只能單指西藏自治區內的居民。中國官方甚至指定,博伊也必須依樣畫葫蘆,分別使用Bod-rigs(藏族) 與Bod-pa(西藏人)來顯示這兩者之間的區別。這是一個相當晚近才創造出來的區分,而這一點,由紅軍回憶長征時經過康區的一些地方所做的紀錄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這些作品裡,我們發現中國人是有意識到,至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博伊的名詞Bod-pa(亦即中國官方指定翻譯中的「西藏人」)並不限定於達賴喇嘛政府轄下(也就是現今的西藏自治區)的居民而已。因此我們讀到了紅軍建立一個壽命很短、只在康區一些地方運作的「圖伯特人民的政府」,他們稱為「波巴人民政府」,「波巴」就是音譯博伊的Bod-pa。
除了博伊以外,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現代語言之中,在談到博巴所屬的整體文化與歷史世界時,都使用Tibet一字的各種變化形式來表示。在那些語言裡,現代中文所產生的束縛限制、種種用來支持中國對Tibet與Tibetans作政治定義的設限與規矩,都不適用。愈來愈多圖伯特、台灣與中國的作者與網路作家選擇使用「圖伯特」一詞,顯示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瞭解,不但深刻,而且是嚴肅懇切的。除了圖伯特以外,許多人在他們的作品中紀錄了Tibetans 作為一個民族的名稱(「博彌」、「博巴」,亦即博伊中的Bod-mi、Bod-pa),Tibetan作為一種語言(「博伊」、「博蓋」,Bod-yig、Bod-skad)等等,都是為了避免使用中文名詞「藏」,特別是它與「西藏」有關時,所影射的限制。
諷刺的是,中文裡唯一一個 “Bod” (譯按:博伊中的Tibet)被正式規定為可以名正言順地指稱Tibet的地方,是唐朝稱呼Tibet的名字吐蕃(音:Tufan),這個名詞的發音受到官方的指定,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處,都已經被讀作Tubo、也依此音譯為羅馬化的漢語拼音字母。然而,這個唸法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法國語言學家也是漢學家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徹底地剖析、清楚地顯示為謬誤了。我回想起許多年前參加一個研討會,會中一位中國同行不斷地提起 “the Tubo Kingdom”(吐蕃王朝)。一位藏學界的泰斗傾身對我低語:「難道沒有人要同情一下這個可憐的人,告訴他伯希和早在一九一五年即已說明了那個字不能念成bo?」當然,我們的中國同行有可能早就知道伯希和對此問題的評析;然而,政治無疑在這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中國學者而言,去想像Bod這個名字,唐代人早有所悉,並揉和於當時指稱圖伯特國家的中文名字裡,顯然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目的論裡一個不容造次的成分:它似乎在表面上顯示,即使是在那麼古老的時代裡,博巴與漢族已經愈來愈接近,勢不可擋了。
有趣的是,如同伯希和所顯示的,希望把吐蕃唸成Tubo,想見到Bod這個名字出現於中文書寫之中,其濫觴並不來自於中國官修正史的傳統,而是來自西方十九世紀的東方學專家(Orientalists)的作品,從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emusat, 1788年-1832年)到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年-1914年)與其他人等等,此一傾向殊為明顯。我們可能會注意到,就算我們接受了蕃(fan)應該念成bo,我們還是得解釋第一個字,吐(Tu)的問題,而關於這個問題,他們的想像簡直到了天馬行空的地步。伯希和文中所提到的一些東方學者,幻想著古代的圖伯特使用 “Mtho-Bod” 或者 “Stod-Bod” 這樣的名字。這兩個名字皆翻譯成類似於「高博」(High Tibet)或「上博」(Upper Tibet)的說法。然而,這樣的名字,在古代的博伊文獻裡並沒有證據可以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們也不曾出現於圖伯特帝國時期的雙語史料中,其中Tufan只是翻譯成Bod而已。未得到這些史料的佐證, “Stod-Bod”與 “Mtho-Bod”看起來只不過是十九世紀為了炮製一個並不存在的名字,而在字典裡、辭表裡搜求尋覓,所牽強附會的結果而已。
事實上,圖伯特高原對於唐代以前的此地居民而言,並非統一的畛域。我們所知的圖伯特帝國早期、或帝國尚未建立時期的每一件事,皆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四分五裂、沒有明顯齊一現象的地方──族群、語言、與宗教上皆如此──也一直沒有任何 “Bod” 作為一個大地理區域之意識的文獻證據,一直到圖伯特皇帝與他們的軍隊遠征吐谷渾(’A-zha)、蘇毗(Sum-pa)、象雄(Zhang-zhung)、瓊波(Khyung-po)及其他族群的地區,並且創造出Bod的意識為止。雖然如此,我們確實擁有Bod這個名字在更早期就被使用的證據,然而其來源僅囿限於高原的中南部地區,而我們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成書年代大約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九百年之間的印度文學《吠陀經》裡曾談到 “Bhoja”(波札) ,然而它並不是一個在帝國之前遍及圖伯特高原的名詞。而確實,鑑於帝國建立之前與帝國建立初期,高原上的居民所處的分裂狀態,它又豈能不是如此?去假設那個時期住在圖伯特高原上的人都視自己統一在一個旗號之下,或者他們全都瞭解高原以外地方的地形,因此普遍地認為他們所住的地方是「上」、「高」圖伯特,這是完全經不起檢驗的看法。
事實是,如同伯希和在一九一五年時所解釋的,在唐朝的正史中,對吐蕃這個名字之起源有一個合理而令人滿意的解釋。我們在《舊唐書》〈吐蕃傳〉的開頭找到一段文字描述它起源,據說它是來自一個鮮卑的族名「□髮」(Tufa),並由後來建立南涼國(397年-414年)的後人繼承此名:「以□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換言之,吐蕃之所以變成Tibet的名字,就是因為其正確的名字「□髮」在發音時以訛傳訛所導致的結果。而一開始用來指稱Tibet這個地方的,就是□髮(Tufa)的族名;直到後來它才音訛地變成吐蕃(Tufan)。「□髮」的古代發音實際上更加接近 “Tupat”,並早在公元八世紀,即由中亞的突厥人所紀錄,寫為突厥語的Tupet從這裡,它再輾轉西傳,進入阿拉伯語及波斯語,寫成Tubbat與其他類似的拼法。稍後,在中世紀末期的歐洲,馬可波羅(1254年-1324年)的遊記將它拼寫為Tebet,另外類似的寫法也出現在中古時期不同歐洲旅行者的紀錄中。 “Tibet”與其他類似的稱呼就此陸續進入歐洲各國的語言之中。
一個部族的名字歷經長途的旅程,最後轉變成為一個地理的名字,也許看起來十分迂迴曲折,然而這並非鮮見的例子,畢竟,「亞美利加」( “America”)也有類似的經歷。更重要的,一個小地方的名字(□髮∕吐蕃,似乎一開始只局限於圖伯特高原的東北部邊緣一帶),漸漸轉變成為指涉一個大地區的名字,並非罕見, 另外類似的例子有「亞細亞」(“Asia”,亞洲)與 「阿非利加」(“Africa”,非洲),這兩個名詞的指涉範圍,後來備受擴張,遠超過它們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地中海諸古典語言裡的原始意義。因此,這個帶點地方性質的、在唐代以前出現的名字,「□髮∕吐蕃」,後來在中文裡已經澈底改頭換面,指稱的是它原來的地點以西的廣大圖伯特地區。這個名字,與實際居住在此高原上的原住民所使用的各種名字(如蘇毗、象雄等),並無關連,就如同「亞美利加」與西半球上任何本土名字(如馬雅、阿茲特克等)皆不相關一樣。
值得一提的是,當學者端智嘉與陳慶英把《舊唐書》與《新唐書》中的〈吐蕃傳〉翻譯成博伊時 ,他們肯定知道舊有的Stod-Bod(上博)概念,然而他們似乎拒斥了它,把Tufan翻譯成Thu-Bhod。我們可以想像他們不能全然拒斥已經政治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教條的Tubo,然而他們可以很有技巧地處理它,或許將它翻譯成近似 “Tibet”的名詞,而不是直接了當地將fan/bo 與Bod等同劃一。
簡言之,《舊唐書》〈吐蕃傳〉開頭所提到的中文名字,可以被視為在圖伯特之外、也是現代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普遍所使用的名字──Tibet──的一個雛型。而Tibet,作為普世所接受的一個文化與歷史的畛域,並不是現代的「西藏」。令人欣悅的是,新一代以中文書寫或發表網路文章的作者們已經重新發現、並採納了「圖伯特」,作為這塊他們深深關懷的土地一個清晰明朗、無法混淆的稱呼。
艾略特.史伯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