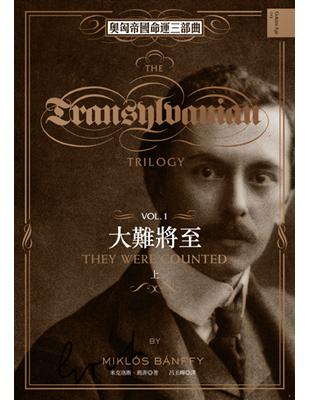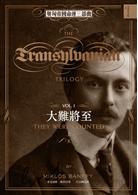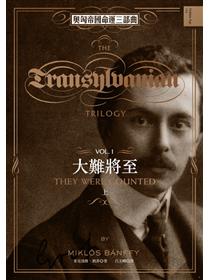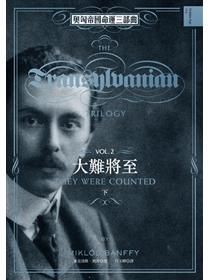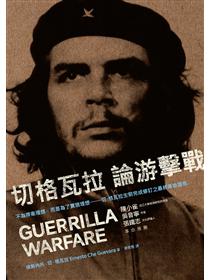媒體推薦:
【國際讚譽】
沒讀過這麼棒的小說,宛如《安娜.卡列尼娜》及《戰爭與和平》的綜合體。性、愛、城市、鄉野、金錢、權勢、美麗以及社會無可避免走上毀滅之路的悵惘──通通都有。──Charles Moore,《每日電訊報》
一般歷史小說很難讓人一口氣讀完,但是《奧匈帝國命運三部曲》不但能讓我們一氣呵成讀下去,甚至成功地將已消失的世界用一種富娛樂性文字表達。──《獨立報》
宛如托爾斯泰的敘事格局,以兩位表兄弟(從政的巴林特及酗酒爛賭的拉茲洛)背馳的命運為主線,敘述走上末路的奧匈帝國,令人不忍釋卷。娓娓描述衰微的布達佩斯宮廷裡的陰謀、沒有明天的戀情、奢華的舞會、決鬥,以及抱著鴕鳥心態面對一己世界即將永遠消逝的特權精英分子。身為匈牙利伯爵的班菲,也以生動逼真的筆觸描繪故鄉外西凡尼亞的大地之美。──《衛報》「1000本必讀小說」
班菲是天生的說故事好手。──英國作家派屈克.利.佛摩(Patrick Leigh Fermor.)
班菲在一九三四年發表《奧匈帝國命運三部曲》首部,獲得極大的讀者回響,可惜最後一部至一九四○年才問世,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自然難以引起戰火中的歐洲人的關注。戰後,匈牙利落入共產黨的統治,班菲出身貴族世家,又是帝國時代的外交官,想當然耳,他的作品刻意受到忽略。幸好,在兩位英譯者的努力(其中一位是班菲的獨生女)下,《奧匈帝國命運三部曲》終於跨越了階級、語言與地理的重重障礙,晉升二十世紀偉大文學作品的行列。從某些角度而言,這是一部老派小說,有一個無所不知的敘事者,帶有當時正蔓延至歐美各地(尤其是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的現代主義的痕跡。在另一方面,班菲似乎精通當代心理學,充分掌握了角色的心理狀態。不過他最大的優勢是能夠不拘篇幅,淋漓盡致描繪優美的自然與奢華的宴會,痛快批判國會的陰險手段,同時掌握住多條情節線與眾多大大小小的角色。──Dennis Drabelle,《華盛頓郵報》(節錄)
另一種規模與類型的閱讀享受,宛若英國名作家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的小說,以一連串的生活事件,描述哈布斯堡王朝的衰亡──十分適合像我這樣懷舊又浪漫的人深夜閱讀。──Jan Morris,《觀察家報》「年度好書」
引人入勝。作者描寫外西凡尼亞古怪狡猾的地主鄉紳、煙嵐雲岫的幽山峻谷,以近似波蘭詩人米洛茲(Czeslaw Milosz)所懷抱的痛楚靜觀這個失落的伊甸園。──《衛報》
躍入一部再度被挖掘出來之傑作的淨化池中吧,因為這部書不管在哪一種語言都絕對是一部傑作。──Michael Henderson,《每日電訊報》
讀來興味盎然,扣人心弦,作者靈敏的政治嗅覺與拒絕自欺的態度增添小說與眾不同的色彩。如果純粹為了享受而快速閱讀,你很可能會一頁接著一頁翻下去,但許多讀者會想再讀一次,放緩速度,品味其中精妙之處,玩味作者的聰敏慧悟。──Allan Massie,《蘇格蘭人報》
太精采了。──Martha Kearney,《哈潑時尚》
細細勾勒人物在光輝燦爛的生活中迴旋沉淪,亦流露出企圖警告匈牙利統治階層改革妥協之必要的政治家的挫折及悔恨。充斥奢靡與浪漫的情景,就其時代背景而言,也滿溢著激進的思想。──《衛報》書評
《奧匈帝國命運三部曲》非常值得購買。故事以奧匈帝國末年為背景,當時整個歐洲正緩緩走向一場天搖地動的戰爭。這部長篇巨作描述目光短淺的政治手法與遊走道德之外的戀情,還有奴僕如何以機智蒙騙主人的情節。作者的技巧讓這一切保持令人屏息的平衡。──《華盛頓郵報》
與奧地利作家羅特(Joseph Roth)和穆西爾(Robert Musil)一樣,班菲擅長描述奧匈帝國。這幾個小說家用才華橫溢的文字技巧,深刻記述一個大世界的衰敗,語氣諷刺,語調哀傷,他們早已發現階級和國族的命運會在二十世紀初開始變天。奇怪的是,他們沒有一個在世時就得到應有的評價,這大概是因為中歐人在一九一八年茫然若失,帝國在一夜之間崩潰,之後的中歐如同正在沉沒的大船,一陣下沉的強大氣流吹走了一個世代的理念與緊密聯繫。班菲親眼見證了自己的時代,在這幾本回憶錄中描繪一段親身經歷過的人絕對難忘的非凡歲月。──Julian Evans,《每日電訊報》
雋永有味。──Simon Jenkins,《衛報》
充滿精彩的描寫刻劃、優美的景色再現與睿智的政治道德見解。──Francis King,《觀察家報》
班菲深情描繪一種生活之道,這種生活之道在他書寫之際早已黯然,也注定在他死亡之前徹底消失。班菲目光犀利,不可能只顧著眷念往昔,但失落之痛無疑存在文字之間。拉茲洛從小是個無家可歸的孤兒,巴林特的父親在他幼時身故,整個國家承受失去自尊的痛苦。難免有人拿這部書與西西里作家蘭佩杜薩(Lampedusa)的小說《豹》(The Leopard)作比較,不過班菲的作品在氛圍上應該更接近羅特(Joseph Roth)的小說《拉德茨基進行曲》(The Radetzky March),畢竟兩部作品都為同一位皇帝的垮臺而感到哀痛。──Ruth Pavey,《新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