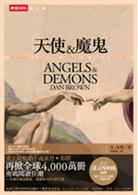一部手稿,隱藏著一間飯店大火奇案,一串價值連城的珠寶竊案和兩位女子的死亡之謎。
愛麗絲為了著手寫一部她作家母親──凱瑟琳──的回憶錄,而回到卡斯基爾山區偏遠的秋分飯店──凱瑟琳生前工作的地方查訪。沒想到這趟懷舊之旅,竟無意間揭開了糾葛兩代的疑雲。她發現幼年時,母親在床邊說的愛爾蘭童話中,隱含著一場謀殺的真相。而這樁謀殺引起了凱瑟琳生前的文學經紀人關注,深信凱瑟琳卅年前死於那場離奇的大火之前,曾寫下最後一部手稿,手稿中不僅隱藏著凱瑟琳的身世之謎,還有一串價值連城的珠寶失竊懸案。
一個個糾結已久的謎團,在親情和愛情的牽引下,即將真相大白…… 優美細膩的文筆,奇情浪漫的故事,一出手便屢獲大獎,令人激賞。
本書特色
★暨南國際大學教授李家同、推理評論家陳國偉、博客來圖書部經理喻小敏聯合推薦!
★被認為是「推理界的珍.奧斯汀」,耽美派藝術懸疑小說之最高成就。
★結合純文學書寫厚度、詩意語言、哥德氛圍和女性心理驚悚,在童話故事中展開充滿藝術氛圍的一段追尋。
★融合古典∕奇情∕懸疑∕推理∕浪漫∕童話元素的精彩小說。
★以緻麗的文字,幽迴迷暗的氛圍,結合愛爾蘭的海豹神話和繁複謎團與動人的愛情故事。
★已售出英國、德國、法國、荷蘭、義大利、日本(早川書房)、挪威、瑞典等國版權。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卡蘿.古德曼(Carol Goodman),作品曾發表在《格林斯布落評論》、《文學拿鐵》、《中西部季刊》,以及《其他聲音》。她於威沙學院主修拉丁文,畢業之後,在美國德州奧斯丁市教了數年的拉丁文。之後在新學院大學拿到藝術碩士(MFA)學位,主修小說。古德曼現在教授寫作,並且是教師與作家組織的常駐作家。目前住在長島。
譯者簡介:
譯者簡介 賴俊達,出生於馬來西亞,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曾擔任中央社和華視新聞部國外組編譯。現為自由撰稿人。)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2005年IMPAC都柏林文學獎提名◆2004年達許‧漢密特獎◆結合純文學書寫厚度、詩意語言、哥德氛圍和女性心理驚悚,在童話故事中展開充滿藝術氛圍的一段追尋。◆被認為是「推理界的珍.奧斯汀」,耽美派藝術懸疑小說之最高成就。
得獎紀錄 ★2003年三月《時人雜誌》評選為最引人入勝的小說 ★2004年達許.漢密特獎(The Dashiell Hammett Awards)(2001年得主為瑪格麗特.愛特伍《盲眼刺客》) ★2005年提名為IMPAC都柏林文學獎 媒體推薦 ★一本充滿藝術氛圍的驚悚小說,佈局高明,高潮迭起。──紐約雜誌
名人推薦:
◆暨南國際大學教授李家同、推理評論家陳國偉、博客來圖書部經理喻小敏推薦!
媒體推薦:
★真正引人入勝……從第一頁起就緊抓住了讀者的興趣,直到最後。──丹佛郵報
★最好的懸疑小說之一,《海之魅惑》滿佈謎團和曲折離奇的情節,但也富於人情趣味。──波士頓環球報
★一本驚悚小說……卡蘿.古德曼的另一次全壘打……《海之魅惑》把民間傳說、中世紀哥特派恐怖故事、以及十足現代化的男歡女愛融於一爐……這是本會讓你挑燈夜讀、愛不釋手的小說,但別讀得太快而忽略了作者優美的文筆。──布林頓自由報
★古德曼簡練、優雅的寫作技巧,讓讀者墜入了撲朔迷離的情境。書中的主人翁愛麗絲活潑風趣,用第一人稱講述故事,娓娓道來,令人喜愛。讀者閱讀時,從頭至尾,經常會處於緊繃狀態,一方面急切想知道故事的後續發展,卻又不禁浸淫在相關的場景和人物中……。──波士頓環球報
★扣人心弦……迷人……一個錯綜複雜的懸疑事件,巧妙的跟好幾個童話故事結合在一起。──書目 ★中世紀哥德派懸疑作品……《海之魅惑》以童話為軸心,藝術氛圍濃郁,令人為之著迷。──時人雜誌
得獎紀錄:◆2005年IMPAC都柏林文學獎提名◆2004年達許‧漢密特獎◆結合純文學書寫厚度、詩意語言、哥德氛圍和女性心理驚悚,在童話故事中展開充滿藝術氛圍的一段追尋。◆被認為是「推理界的珍.奧斯汀」,耽美派藝術懸疑小說之最高成就。
得獎紀錄 ★2003年三月《時人雜誌》評選為最引人入勝的小說 ★2004年達許.漢密特獎(The Dashiell Hammett Awards)(2001年得主為瑪格麗特.愛特伍《盲眼刺客》) ★2005年提名為IMPAC都柏林文學獎 媒體推薦 ★一本充滿藝術氛圍的驚悚小說,佈局高明,高潮迭起。──紐約雜誌名人推薦:◆暨南國際...
章節試閱
第一部份
破碎的珍珠
第一章
我小時候最愛聽、而且每晚都央求母親講的故事,就是《海豹女郎。》
「那個老掉牙的故事,」母親總會這樣說。她的聲調跟父親讚美她的服裝時一模一樣。哦,這件舊東西,她說,淺綠色的眼睛洩露了她心中的喜悅。「來點新鮮的吧?」她舉起蘇菲姨媽買給我的那本光鮮亮麗的書《波西雙胞胎》,或是我長大一點後送我的《南西德魯》。書中盡是些教人上進、以及敘述女英豪事蹟的美國故事。
「不,我要聽你的故事,」我說。這故事竟變成了她的故事,因為她把它默記在心,最初是從她母親那裡聽來的,而她母親卻又是從她的……聽來的。我腦海中泛起了一連串的母親和女兒,就像我陪著她,站在飯店大堂裡的許多面鏡子前看到的疊影。
「好吧,如果這樣能讓你入睡……」
我點點頭,更深的窩在毛毯中。那是我執著的少數要求之一,也許是因為母親開始時半推半就,已成了她說故事的慣例。我們在玩這個遊戲,因為我知道她喜歡我愛聽她講故事,而不喜歡買來的故事書。即使在她打扮停當準備外出、或只是過來跟我道一聲晚安時,她總會坐在我的床沿,脫掉肩上的外套,黑色的毛皮領子落到腰際,於是我依偎在烏黑、香噴噴的厚皮草上。她準備講故事了,撫摸著脖子上的一長串珍珠,珠子發出輕柔的喀嗒聲,她閉上了雙眼。我猜想她閉上眼睛,是因為故事就在她體內某個地方,藏在眼皮後的隱形捲軸上,她夜復一夜的講,每個字都跟昨晚講的一樣。
「當河流被大海淹沒前,在太陽和月亮之間的某塊土地上……」
這時她會睜開眼睛,撫摸我的床頭板上的把手。這些把手原已破損,由飯店園丁約瑟修復好,並雕刻成新月和太陽的形狀。我們用的是已過度磨損、不能再供客人使用的床墊和家具 ─ 邊緣綻開的毛毯、抽屜嘎嘎作響的梳妝台,以及粗心的城市婦女不拿碟子墊著,就把熱茶杯擱在上頭而留下圓形痕跡的桌子。我們住的房間是剩餘物資,是飯店北側翼的服務生新宿舍蓋好前女傭們住的頂樓,也是母親在飯店當女傭時的住所。她嫁給我父親(飯店經理)後,仍會對他說,她喜歡高高在上。從頂樓的房間,你可以飽覽大河南流到紐約市,然後匯入大海的美景。
「在祖先居住的那個地方,漁夫們談到某個男子愛上了其中一個海豹女郎的故事,這些海豹每年蛻皮一次,變成了女人……」
「那是女人假裝成海豹,或是海豹假裝成女人囉?」
母親輕易的化解了我的插話,因為我經常提出同樣的問題,她把答案融入了故事中。
「沒人知道是先有海豹,還是先有女人,那是他們的一部分神秘。當你注視海豹的眼睛時,你看到人在向外張望,但當你聆聽女人歌唱時,你能聽到她的歌聲中有大海之音。」
海豹女郎究竟是海豹還是女人的成分居多,我對答案仍不滿意,於是更深的縮進被窩裡,閉上雙眼,表示要母親繼續說下去。我知道母親正要外出,這個故事只能耽擱她這麼久。如果她覺得我還不會入睡,故事就可能嘎然而止。
「……於是有一天,有個農夫來到海邊……」
「是去撿貝殼來鋪他的花園小徑嗎?」我問。「約瑟說他們在法國時都是這樣做的。」大戰後,約瑟曾在歐洲所有最好的飯店工作過。當他捲起他那件已褪色的藍色工作服的袖口時,可以看到他的右前臂上,刺了一組模糊的號碼,跟他穿的襯衫同一顏色。
「正是,貝殼小徑聽起來真不錯。」她微笑著說。她喜歡我在她的故事中加油加醋。「農夫希望通往他那棟房子的小徑,像破碎的珍珠在月光下閃亮。當他抬頭看見一位肌膚像珍珠、頭髮烏黑如漆的女郎坐在岩石上晒太陽時,心理不禁這麼想。」
黑頭髮。像我母親。也像我。最近我發現母親那本包含了《海豹女郎》的愛爾蘭民間故事的舊書。故事中的海豹女郎卻是金髮碧眼。一定是我母親決定讓她故事裡的女中豪傑留著一頭黑髮,就像我們一樣。
「那位黑髮、珍珠色肌膚的女郎唱的歌,只能在夢裡聽到,比你在劇院、卡乃基音樂廳、甚至……聽到的任何東西更甜美。」這時,如果我偷窺,就會看到母親仍然閉著雙眼,露出傾聽音樂的神情。她默不作聲一陣子,我也不會發問打破靜默,因為我在想,如果我仔細聆聽,也能聽見她聽到的東西。然而,我只聽到低沈的腳步聲、夜班女服務生的細語、以及老舊電梯搭載宵夜客人回房歇息時發出的呻吟。如果有人歌唱,那必定是在夏天租下頂樓房間的其中一個退休音樂老師。一看到母親睜開眼,我立刻把眼睛閉上。
「於是農夫愛上了黑髮女郎,並決定娶她為妻,但當他試圖靠近她坐著的大石時,她聽到他的腳步聲,馬上潛入水中。農夫站在海濱張望,深信她無法在水中待太久。後來他看見浪花間冒出了一個烏溜溜的頭。但她已不再是女郎,她變成了 ── 」
「海豹!」我說,興奮中忘了把聲音裝著愛睏的樣子。
「不錯。農夫站了很久,望著大海,忖量他剛看見了什麼,或自以為看見了什麼,但最後,他記起了還要擠牛奶,要餵雞,於是轉過身來,背向大海回家去了。」
「但他忘不了那個黑髮女郎和她的美妙歌聲。」
「不會。他忘不了。你能嗎?」
我母親常向我提出同樣的問題,但不管她問過幾次,我始終不知所措。這不僅是因為我擔心自己會像農夫那樣,被黑髮女歌手擊潰,也是因為母親的發問方式有點特殊,讓我覺得自己的回答必須與眾不同,還必須抗拒得了海豹女郎的歌聲。總之,瞧瞧那個可憐農夫的下場……
他為海豹女郎害了相思病,無法入睡,而誕生以來一直聽到的海洋之音,開始侵擾他的神經。不管他抖動床單多少次,總覺得床上有沙子,即使窗戶全部打開,他仍覺得小屋裡令人窒息。
每當故事講到這個段落時,我都聽得出母親的聲音有點高亢。我小時認為這跟床單上的沙礫有關。畢竟母親曾當過飯店女傭,她常告訴我,客人把餅乾屑弄得到處都是,很不禮貌,留在床上更糟。但後來我猜想,她患了失眠症才是聲音高亢的更主要原因。
事情就這般過去,直到農夫荒廢了田莊才有了變化。他的母牛沒擠奶,母雞溜進鄰居的庭院覓食。在絕望中,他求助於一位住在海邊懸崖上小屋中的聰明老婦人。她看著農夫深陷的眼睛、穿孔小船似的破衣裳底下突出的肋骨、像海草一樣糾結成一團的頭髮,她立即知道了問題所在。
「你看見海豹女郎有多久了?」她問,請他坐在火爐邊,端給他一杯味道很苦的茶。
「明天就滿一年了,」他告訴她。「我至今仍然記得,因為那是春季的第一天。」
老婦人微笑。「你好像要靠它才記得起來。」她罵他,但沒叫他忘掉海豹女郎。她告訴他喝完那杯能讓他一夜安眠的茶。「然後,明天回到你當初看見她的那塊巨石去。你必須游過去,小心別讓她聽到。她身旁放著一捆皮,你必須把它搶過來。一旦你有了她的皮,她就別無選擇,只好跟你回家了。」
「她會留下來做我的老婆?」
「她會留下來做你的老婆。」
「給我生小孩?」
「她會給你生小孩。」
「也許有一天她會愛上我?」
老婦人聳聳肩,不知是表示不知道,還是認為他問得太多,農夫永遠無法知道答案。茶使他的眼皮逐漸下垂,雙手和雙腳變得沈重。他蹣跚著離開老婦人的小屋,從她的住所到他的前門都是下坡路,他總算回到了家。他顧不得找床,就倒在火爐前的地毯上睡著了。
早上醒來,他擔心睡過了頭──他覺得好像已經睡了一年──接著他聽見海洋的咆哮中夾著歌聲。那是她的歌聲。
他跑向大海,最後一刻記起了他必須悄悄溜下海邊,滑入水中,盡量壓低聲音。幸好浪濤的沖擊聲,掩蓋了他笨手笨腳、游近巨石時激起的水聲。他看見了黑髮女郎和她身旁的一捆皮 ─ 她的皮 ─ 既滑又亮,在夕陽下閃閃發光,像悶燒中的一塊煤。正當他伸手拿那捆皮時,黑髮女郎轉過頭看他一眼,幾乎凍結了他的血液。她那漆黑睫毛下的眼睛,呈浪濤般的淺綠色。他張開嘴巴,吞下大量海水,如果不是胸前緊抱著那捆皮,就可能立即沈入海底。它發揮了救命功能,浮力很大。他轉身游回岸邊,試圖忘掉女郎投給她的那一眼。他想,一旦她習慣了他以後,就會改變對他的想法。
泅回海岸比他料想的還要困難。一陣突然而來的風,掀起驚濤駭浪。那捆皮雖然讓他浮在水面,卻也把他拖向外海。纏繞著雙腿的潮水似乎長了肌肉,像條大鰻魚把他箍得快要斷氣。當他拖著身子到達沙灘時,已疲弱得站不起來了。他曾幻想自己抱著那捆皮,像個驕傲的征服者站在女郎面前,其實他卻緊抓著柔軟的毛皮,貼在臉上,像個口銜毯子尋求慰藉的小孩。那捆皮摸起來仍很溫暖,似乎每根纖維都吸收了陽光。他抬起頭,看見那位黑髮女郎,坐在海灘隆起的沙丘上,離他只有幾尺遠。她的膝蓋屈到胸前,長髮垂到腿上,像布幔一般遮住了她裸露的身體。她碧綠色的眼睛平靜的注視著他。等著看我是否已經溺斃,他想。當她看見他還沒死,便站起來,從大海緩緩的走向他的房子。其實,是他跟隨她回家的。
故事講到這裡,母親會停下來,看我睡著了沒有。我必須小心應對。如果我顯得太清醒,她會認為故事沒有效果,便會很嚴肅的要我去睡。若她認為我快睡著了,就會不發一語的溜出去,關燈,把門帶上。這一來,我就留在黑暗中,未說完的故事在我腦海裡縈繞,徹夜難眠,正如海豹女郎的歌聲令農夫無法入眠一樣。那種感覺就像你把沒吃完的三明治放下,後來卻忘了放在那裡;我孤零零的躺在黑暗中,飯店的各種聲音漸漸沈寂,像唱完了的音樂盒。我知道母親同樣害怕失眠,而如果我用恰到好處的慵懶聲音,央求她再講一些,她就會嘆口氣,彷彿感到寒冷,把毛皮綑邊的外套往胳臂勒緊一點,然後繼續講下去……
有好一陣子,農夫和他的海豹女郎新娘處得很好。她替他生了五個小孩:頭胎是個女兒,接著是四個兒子,全都有著一頭黑髮,淺綠色的眼睛。她學會了做飯打掃,還照顧農夫的牲口和花園。她碰觸到的每樣東西都變得很美。她在窗前掛上貝殼和海草,風吹動時會發出樂音。她的聲音能安撫懷孕的牝馬,誘哄羊兒乖乖站著讓人剪毛。
她唯一學不會的是編織、刺繡或補破網。儘管村婦們費盡心機教她,她卻連打個結都不會。她甚至不懂得怎樣給女兒辮髮,或在自己的衣服上綁根飾帶。事實上,婦人發覺到,每當她加入編織小圈子時,他們全都放下針線,於是他們正在編織的毛衣的邊緣就綻開了。不久,村婦們經常叫她去跑腿,使她無法加入小圈子,因為編織正是他們東家長西家短的時光,而她被排除在外。
她一點也不在乎。
她在操持家務時唱歌自娛,歌聲甜美,連陌生人也站在路邊傾聽。但有時她的歌聲十分淒涼,引得村民莫名其妙的哭泣,晚上睡不著覺。在每年的春分和秋分這兩天,更是如此。在那些日子裡,她從黎明直唱到太陽沈入大海的那首歌(其實只有一首)是那麼的悲傷,以致沒人能好好幹活。稀飯煮焦了、漁網丟失、大拇指被鎚子敲到、乳酪變餿壞掉、墨水溢漏出來、毛衣綻開而成了一坨坨油膩膩的毛線。
幾年來都是如此,於是村民要求農夫禁止他的妻子在那些日子裡唱歌。
「我還可以叫地球別再轉動,」他告訴他們。「也可以叫春別跟隨冬,冬別跟隨秋呢。」
年復一年,他的回答總是這樣,但當他最大的兒子十歲時,他厭倦了那些婦人的臉色,以及男人在他背後訴說他不懂得怎樣管教自己的老婆。
「這是為你好,」他告訴妻子。「唱歌只會讓你更憂傷。還睡不著。替孩子們想想吧。你想要他們感染你的憂傷嗎?」
她看了他一眼,露出那天他搶走她那捆皮時,她在大石上的同樣眼神。從那天起,他沒再看到那種眼神,現在又看到了,他的嘴裡彷彿灌滿了海水,覺得自己在下沈。但她聽從了他的話,始終不發一語。春季的第一天,她待在屋內,一直沒開口。她取下了掛在窗前的鈴噹,關上煙囪的排煙管,以免聽到海風的呼嘯聲。她責罵女兒在跳繩時哼著歌。她以前從未因任何事情責罵過她。
春分過後,農夫心想情況將會恢復正常,但並沒恢復。她像石頭人似的操持家務。她煮稀飯,卻煮焦了。牲口不願讓她觸摸。當她凝望著兒女時,好像透過一泓清水看他們。
整個夏天就這樣過去。農夫原希望她會改變,但她沒變,於是對她變得很冷漠。她晚上離家出走了,女兒跟著。她發現母親在棚裡的牛群間縮成一團,或是卡在海濱的巨石間,試圖找個地方,克服近來常患的失眠症。晚上天氣轉冷,她看見母親穿了件薄睡衣,在戶外瑟縮發抖,她暗想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母親准會凍死。
九月間的一個夜晚,也就是秋分前的晚上,氣溫好像預知了地球會傾斜到太陽的另一邊,降到很低,小女孩看到母親呼出來的氣,在四週岩石上化成了冰。海面升起的濃霧,在母親的頭髮上變成水晶,她彷彿聽到濃霧在寒冷的海風中哀鳴。如果他不想個辦法,母親準會在黎明前凍成冰塊。
她跑回家裡,打開毛毯櫃,但農夫已把剩餘的被子全堆在兒子的床上。她雙手在櫃底猛抓,粗礪的木板碎片割傷了手指,開始流血。她把指甲插入木板,體會痛的感覺。令她驚異的是,櫃底竟然鬆開了,她的雙手摸到了一樣溫暖、絲一般柔軟的物件。
她以為是個活東西。
當她拎起厚重的皮草,看見獸皮時,仍不敢相信那是個死東西。那張皮鼓動著,散發出溫暖,像燃燒中的媒在發光。她把臉頰湊上,聞到了海洋氣息。她聽見了每根毛髮間的海洋鳴響,就像貝殼的螺紋深處隱藏著海洋之音。
她把皮草圍在肩上,奔向海濱母親躺著的巨石之間。皮草披肩並沒使她腳步沉重,反而卻像飄浮在風中,把她輕輕托起。
當她找到母親時,還以為回來太遲,已經凍死了。但海面湧來的霧,一碰到她母親的皮膚,就凝結成柔細的冰紗,把她裹在像用水晶珠子編織成的網裡。但她知道母親的氣息也已結成了冰,不過仍然活著。她把皮草蓋在母親身上,爬到底下,夾在母親和巨石之間。她立刻感覺到母親的皮膚暖了起來,冰網融化,水滲入柔軟、厚重的皮草中。
母女倆同睡在沙灘上皮草披風底下,但在睡夢中,小女孩仍感覺到母親的手指在撫弄她的頭髮,想消除她心裡的恐懼。
有時在這當兒,我也會睡著。我的毯子的一角已經綻開,用一小塊絨布縫補。母親離開後,我喜歡把它塞在頰下,假裝它是海豹女郎的皮,或是母親的外套的毛皮領子,每當母親出席特別的場合,例如:本地大學為她舉辦的派對、與萊貝克河對岸的主編共進晚餐、或是在市內朗讀小說時,她都會穿上那件外套。直到她完成了最後一本書多年後,這些活動仍在持續;她寫的其中兩本書,銷路愈來愈差,最後停止出版。
母親擁有一些書迷。她那套敘述提拉˙格林虛幻世界的三部曲,只寫了其中兩本。第一本在我誕生前五年完成,書名叫破碎的珍珠。第二本淚之網是她胎裡懷著我時寫的(她常對我說,我和那本書的構想同時孕育出來,而且都花了整整九個月才問世)。沒人知道第三本書的名字,因為它始終沒有出現。還記得在我六歲生日前後,我的一年級老師問我,是否看過母親寫東西。我把話轉述給母親聽,她就要我離開公立學校,轉學到包吉西的一所私立學校。兩年後我被送回公立學校。母親的書銷路直線下降。如果三部曲的書不出第三本,還有誰願意去讀前兩本?
旅館業生意也因不景氣而衰退。那是六十年代,美國人發現了航空旅遊和歐洲大陸。在我們南方和西方的大飯店,一間接一間倒閉。如果不是那些忠誠的顧客(祖父母曾住過秋分飯店的家族,或是前來畫風景的畫家),我們也會關門大吉。誰會願意開三小時的車到度假村,在冰凍的湖裡游泳?秋分飯店高據哈德遜河岩架上,距離大路很遠、式樣太古老,當母親離去時,更顯得淒清。
我十歲那年,她一去不回頭。有人邀請她在紐約大學的兩天會議上,擔任婦女科幻小說家的委員。她原定清晨前往那個大城,但因為她無法入睡,便請約瑟開車送她過河,去搭乘夜間列車。我聽到她和父親在我臥房外面的客廳裡爭論不休。「你打算住那裡?」他問,「你預定的是明天的房間。」
「今晚應該會有房間,」她說,聲音裡帶著笑。我想像得到,她的手放在他的額上,把他的頭髮攏到腦後,她也經常這樣做來紓解我的恐懼。「班恩,你顧慮太多了,我不會有事的。」
然後她走進我的房間吻我、道聲晚安,我把頭緊貼著她那件外套毛茸茸的領子。外套一直扣到她的喉嚨上,她沒脫下,也不像她從前要講故事時那樣,讓它溜到腰間。
「講海豹女郎的故事給我聽,」我央求她。他的手按在我的額上,像在測試我是否發燒,拂掉我臉上的髮絲,用手指梳理糾結的亂髮。我等著她的回答,那件老東西?但她卻說:「今晚不行。」她叫我閉上眼睛睡覺去。我才閉上眼睛幾分鐘,就聽到她頸上的珍珠和外套鈕釦的碰撞聲,她俯身吻我道晚安。然後她就走了。
她到了紐約,卻沒住進主編替他訂下的艾康金飯店,不過我們後來查出,飯店當晚仍有房間。我的母親根本沒去那裡。她住進了夢境飯店 ─ 康尼島上一家
破落的飯店,就在夢境樂園的舊址附近。那是1973年九月的最後一個週末,也正是樂園燒成灰燼的週末。過了好幾個星期,我們才確知母親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她登記時用的名字,不是婚後的名字凱兒˙葛林費德,不是筆名拉佛爾,也不是婚前的名字凱瑟琳˙莫莉賽。她和那個跟在身旁的男子,是登記在約翰˙麥格林夫婦名下。調查警員看了登記簿,就猜到她是什麼人,因為警員的太太是我母親的忠實讀者,曾讀到母親失蹤的消息,她還記得麥格林這個名字,因為我母親把她的夢境樂園取名為提拉˙格林。
警員從城市老遠跑來,把一隻護身手鐲拿給我父親看,父親認出那是他前一年送給母親的聖誕節禮物。他們在圖書館碰面,我躲在圖書館外面的庭院裡,偷聽他們的談話。父親問他是否查出跟她在一起的男人是誰,但警員說,他還沒找到那個男人的屍體。我母親死時是孤單一人。
此後許多年,我非得聽著海豹女郎的故事才能入睡。母親離去後,照顧我的是姨媽蘇菲,我請她講這個故事。
「那件老東西?」她說,用詞跟我母親的一樣,但意義完全不同。「那個恐怖的故事?」她說恐怖這字眼時的神情,正如我小時想吃掉在地板上的菜、或某個房客吃剩擱在碟子邊緣的糕餅,而她說骯髒時的神情。其實令我恐怖的,是當我做完雜務,迅速爬上床,以便她也能做雜務的那一刻。恐怖的是母親離去前的情況。但姨媽就像我母親一樣,如果認為講故事能催我入眠,她就會順應我的要求。我摺起絨布毯子,緊貼著臉頰,把它想像成母親的外套皮毛領子,我還想像母親的手在撫弄我的頭髮,就像海豹女郎的女兒入睡後,仍感覺到她母親在撫弄她的頭髮。我姨媽逐字逐句的講故事,因為我當時就知道,那是我母親寫的《破碎的珍珠》的第一章,但如果我緊閉雙眼,我仍聽得出講故事的聲音,是出自我的母親。
「早上,海豹女郎的女兒醒過來,孤零零的躺在沙灘上。她在睡夢中聽到她母親感謝她把皮膚交還。『現在我可以回到海裡,跟我的五個海豹兒女團聚了,我在陸地上也有五個人類兒女,而他們現在必須由你照顧了。別為我哭泣,當你想念我的時候,就來站在大海邊緣,傾聽浪花裡我的聲音。每年春季的第一天和夏季的最後一天,你會看見我現在的樣子,一個有著女人皮膚的女人。』
「女孩回去她父親的房子,決心信守對母親的諾言,不過,從大海往回走的每一步,都覺得十分沉重,彷彿網子絆住了雙腳,隨著退潮把她往外拉。甚至昨晚凍結的頭髮,也好像要把她拖下去。但她終究回到了家,點起爐火煮稀飯,當弟弟醒來後,她向大家說明,雖然母親已經離去,現在由她來照顧他們,而且每年兩次,她會帶他們去看媽媽。
「直到後來,她依然覺得頭髮重得像結了冰,她照鏡子,發現了母親臨別時送給她的禮物。她還記得母親整晚在撫摸她的頭髮。她母親不會縫衣、不會編織花邊、甚至不會打結,但她卻用凍結成鮮豔石子的浪花,串成一個花環:像顆被網住、呈現出海水般碧綠顏色的淚珠。」
然後,姨媽關了燈,把燈罩弄直,拂掉我臉上的髮絲。我感覺到她乾燥的嘴唇擦著我的前額,接著,我孤單的在黑暗裡,聽那老舊的飯店漸趨安靜。在刮風的夜晚,木樑和地板嗶啪作響,像篝火中的木頭,我想像成飯店在燃燒。但在寂靜的夜裡,如果我仔細的聽,我似乎依稀聽見我們下方大河的流水聲。我想到母親那天晚上沿著大河往南走,我想像河流盡頭處的海洋在呼喚她──她並沒死在夢境飯店的那場大火中,而是回去了她在海底的另一個家──現在輪到他們跟她團圓是公平的。我只要耐心的等待,等到他們的團聚期限屆滿時,她就會回到我的身邊。
第一部份破碎的珍珠第一章我小時候最愛聽、而且每晚都央求母親講的故事,就是《海豹女郎。》「那個老掉牙的故事,」母親總會這樣說。她的聲調跟父親讚美她的服裝時一模一樣。哦,這件舊東西,她說,淺綠色的眼睛洩露了她心中的喜悅。「來點新鮮的吧?」她舉起蘇菲姨媽買給我的那本光鮮亮麗的書《波西雙胞胎》,或是我長大一點後送我的《南西德魯》。書中盡是些教人上進、以及敘述女英豪事蹟的美國故事。「不,我要聽你的故事,」我說。這故事竟變成了她的故事,因為她把它默記在心,最初是從她母親那裡聽來的,而她母親卻又是從她的……聽...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