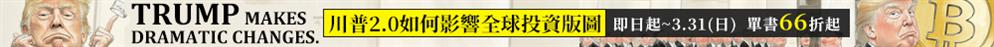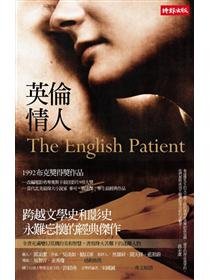名人推薦:
成英姝:這是我看過最恐怖的小說!
究極虐待調教之愛情哀歌 最華麗SM帝國暴行史!
《家畜人鴉俘》是我看過最恐怖的一本書了。
是比薩德侯爵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和《茱麗葉的故事》還要可怕的書。以四十世紀由地球白人建立的宇宙帝國的科技文明為背景,在白人為統治階級、黑人是奴隸、黃種人(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後,除了日本人以外的黃種人全部滅絕,所以這裡說的黃種人,其實就是日本人)被視為牲畜的階級制度下,被稱作「鴉俘」的黃皮膚日本人被製作成各種活體工具器物,《家畜人鴉俘》可以算是高科技未來版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
從地球移居天狼星系的白人建立邑司帝國後,經過女權革命,邑司人以女人為貴,男女的身分與當今二十世紀完全顛倒,女人穿長褲,男人著裙,結婚以女為夫,男為妻,子女當然從母姓,男人重視童貞,女夫外出男妻都要戴上貞操帶,即使是自慰也不可以。為了改造成各種器物,鴉俘被任意切割肢體,甚至以鴉俘作為便器,吞下主人的糞尿。除了各種活體家具,做成活體雕刻、皮被活剝製成衣服,活體解剖之類的就更不用說了。狗或者馬等各種動物也是由鴉俘改造,雌鴉俘作為生產工具,雄鴉俘被迫必須不停地與自己的妻子、女兒、姊妹交配,生產更多鴉俘以用作邑司人生活不可或缺的材料。鞭打、當作動物凌虐、吞食糞尿是最典型的SM情節,至於諸如割斷肢體、燒烙、強迫亂倫等,也是常見的殘酷式SM虐待,將所有傳統SM全面性架構起來予之最大化,《家畜人鴉俘》是以「從被虐者受到最極致的痛苦達到快樂的最高境界」為宗旨的SM精神最登峰造極的表現。
我和朋友J起了一番爭執,自認可以理解嗜好性虐待者心理的J,視《家畜人鴉俘》為滿足日本人長久固有的SM喜好,將之發揮到極致的產物。「看慣了性虐待A片的人不會像你這樣大驚小怪啦,」J以泰然的口氣說:「雖然格局和敘事或許不同,但SM還不就這麼一回事哩!不過就是提供會從施虐和被虐中得到快感的人一種想像。」
我認為不能僅如此看待《家畜人鴉俘》。薩德筆下的種種SM表演,挖人眼珠、截肢、輾碎、用鋼鐵刺穿、火燒炮烙,若與之相較,不過只是競技,《家畜人鴉俘》更重要的部份不可輕忽的,是虐待調教。「那個男主角麟一郎最後不是也對被視為鴉俘感到快樂嗎?」J說:「SM的樂趣就是在這裡嘛!」最可怕的就在此,原生鴉俘原本也以「人類」(鴉俘不被白人認為是人類)的型態生活,有職業、社群和家庭,一但被送到白人世界進行改造,就被教育身為鴉俘是以犧牲自己來服侍白人為榮耀,在這個過程裡,鴉俘是毫無反擊能力的,不管是思想上的洗腦,或是運用肉體折磨訓練學習能力的技巧設計,鴉俘到最後必會無條件接受、徹底依循這一套思考模式:自身越是痛苦、越是能取悅主人,越是無上的快樂。「如果鴉俘自己都甘之如飴,又何必替他們操心」的邏輯是很危險的,受虐者的「自願」成為一種「必然」,這個過程是施虐關鍵的一部份,卻沒有引起任何矛盾的質疑,最後將鴉俘視為非同類,喪失同理心。
在SM影片裡常見的訓練奴隸對自己被卑賤化的凌辱產生快感反應,這不只是角色扮演的遊戲而已,而是人類真實生活的重要元素,來自階級制度。SM俱樂部裡,扮演施虐者的女性色情服務者自稱為女王,扮演被虐者的男客自貶為奴隸,正是以階級落差的位置來達到威權凌駕與服從受辱的相對關係。更值得玩味的是一離開SM俱樂部,不,遊戲一停止,男客馬上便恢復現實社會裡男尊女卑、花錢者是大爺的思維模式,那才是真正的階級制度。階級區分在現實裡確實存在,平等則是神話,只能當作口號作為鬥爭的依據和工具(這就是平等並不存在的證明)。階級化對社會結構有其必要性,人類文化的歷史進程中,階級高者以其身分為尊榮,視己身的特權為理所當然,階級低者則充分明白自己的身分較前者卑屈,並對前者的尊貴和權力心悅臣服,這種心理是促進階級分化穩定的依據(這個精神與虐待調教是無異的),正因這種心理根深蒂固已經內化,才能用來當作SM的角色扮演的重要元素。
《家畜人鴉俘》的作者在書中提到日本人的民族性裡就有較強的慕主性,事實上在東方國家裡無條件服從、犧牲一己之獨立性而成就群體利益(因為君王及國家的利益就是所有人的利益)被視為重要的美德。男人服從上司,女人服從男人,這一點,即使邑司文化已經發展到女權至上,鴉俘的世界卻沒有變。日本人戰敗以來崇洋之心未減弱過,認定白皮膚較黃皮膚更高一等,作者提及當今日本女人(其實《家畜人鴉俘》成書很早,是40年前的事了)迷戀白人,不,連黑人也比日本人高一級,年輕女孩因為迷戀白人,淪為玩物也在所不惜,鴉俘的悲劇是一個拉到最大格局的象徵。與性遊戲一樣,階級分化的調教也預期兩種結果,一是被調教者徹底降服(自我意識喪失,從內心深處認同自己的卑屈),一是保留自我意識,藉由踐踏其自尊使其感到恥辱而得到樂趣。喪失個體性思考的鴉俘,成為以肉體承受痛苦的機器,仍然保存著獨立意識與思考能力的鴉俘,更是備受折磨,正是因為可從這一點得到虐待的快樂,智商超高的鴉俘更是白人貴族喜愛的玩物。
主張愛好性愉虐並非變態者強調SM是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進行不真正傷害到任何人的性虐待,這樣的說法雖然有道理,但這是僅就狹義的角度去看SM這回事(換言之,僅就單純的性行為互動、一種床第遊戲來討論SM),然而SM的本質,其實是人性裡共通的黑暗角落。普通人一但嚐到特權的滋味,超越自己同類之上的威儀、豪奢或者魄力,初始會驚訝,其後卻無法失去。當然在邑司文明的發展過程裡,也曾有人不茍同鴉俘的待遇,然以一人之力無法抵擋整個世界共同的價值觀,這價值觀無關是非良善,純粹是方便而已,因為這個方便形成了人類文明。我認為《家畜人鴉俘》不僅是鋪陳一個最壯觀華麗的SM帝國史,它是關於終極階級的形成,歸功於人面對殘酷的事情,剛開始或許感到悲哀和憤怒,接著會覺得無奈和不忍,逐漸就會習慣,到最後不只是麻痺,甚至認為理所當然了,這是對人天生所具有(假如有的話)的同理心(感同身受)予以消滅的過程,是這一概念最不厭其煩的具體陳述。
《家畜人鴉俘》的女主角克萊兒原本深愛著日本男友,對鴉俘遭受的待遇感到不平而發出正義的抗議。但當被帶到未來的時空、享受女神般驚人優渥的特權後,不但渴望留在未來以白神的身分受廣大下位者膜拜,且樂見昔日男友經歷種種非人痛苦被改造成性具。薩德的小說裡,誦揚邪惡是美德,善良是沒有好下場的,歌頌罪惡,使別人痛苦會得到最大的快樂,讀者會把自己和「薩德那樣的變態」區隔開來,但《家畜人鴉俘》裡,邑司人(未來的白人)的殘酷卻好比人類使役、食用家畜、將動物的每一部份拿來使用一樣,別說是敗德,根本是與道德無關的問題。人類行為依據的道德標準是什麼呢?認為自己的人格情操符合最高標準的道德觀,並且以此自傲的人,其口中的道德依據是什麼呢?也不過是方便建立秩序、使各人順從服膺自身位置、被植入人心無條件被全盤接受卻漏洞百出的工具罷了。薩德挑戰、攻擊道德,《家畜人鴉俘》則根本無所謂「挑戰」或者「攻擊」,因為道德這一次元原本就是空洞的。
如果書中虛擬的歷史真正發生,在邑司統治的社會裡,黃皮膚的我,恐怕也會變成命運悲慘的鴉俘,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我卻開始把自己視為邑司女人來看待(雖然是黃種人,但畢竟是女人嘛,在邑司的世界裡,統治者可是女人,這時候我已經把膚色之事拋諸腦後,只想到性別而已),如果被身邊的年輕俊美的男性冒犯,心中竟然便冒出「這個鴉俘真是沒有教養」的念頭來。《家畜人鴉俘》這部奇書也許真的只是作者為了滿足自己或同好者對SM的終極幻想,但卻精準點出以人類這樣恐怖的生物造就的社會演進最駭人的部份,我不認為是巧合,階級分化的達成仰賴潛意識SM精神的調教,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下位者也有機會晉級,反而不希望特權神話破滅,使這一套結構更牢不可破。若說SM是人類文明的核心,可一點不為過!
【專家解說】
反烏托邦的榮耀與悲慘
前田宗男
I
讀尚‧惹內(Jean Genet 1910-1986)的作品如《鮮花聖母》時,我感受到無與倫比的溫柔。「飛累了,停在電線桿上,風一吹,吹落到蕁麻草溝中。就算是兩位天使,應該也沒有如此純潔。」雞姦行為之後,慵懶無力地躺著,這是投落在這兩人身上的花束。如果在令人做噁的醜陋與侮辱之後,出現如此純潔無垢的色調,可以稱為「溫柔」的話,那麼惹內就可以用他的筆,將充斥著乞丐、男妓、女妓、小偷、殺人犯的社會所發生的所有侮辱與悲慘,全部轉化成詩,惹內稱此為「將糞便變成黃金之術」。
話雖這麼說,但我並不是為了排遣無聊,而選擇惹內來談。他是個私生子,一出生就被丟在療養院裡,十歲開始偷東西之後,就一直過著告密、竊盜、賣淫等犯罪生涯,生活在罪惡與羞辱之中。可是,他用他唯一的武器──筆,重現這些深入他靈魂的悲慘與侮辱。這位將罪惡整個轉換成「神聖性」的惹內,正好可以做為即將談到的這篇反烏托邦故事的前言。
像惹內這種身陷污辱泥沼中,卻又把泥沼變成黃金,擁有如此稀有詐術的人物,確實還是有。但是,這個世界的習慣,就是當人對現實世界產生敵意與厭惡時,迫使人們脫離現實世界,朝向想像世界而去嗎?波特萊爾(Charles-Pierre Baudelaire)「何處容身?此世之外!」的深切嘆息與哀鳴,響起催促出發的聲音時,脫離現實的願望,宛如一個氫氣球般,輕飄飄地往上飛到夢想的天空。然後,對現實世界的不滿,變成對另一個世界的憧憬,當不滿如此熾烈的時候,就不得不虛構另一個相反的世界。氣球漸漸上升到人類無法居住、空氣稀薄的大氣層,用一種不同於形成現實世界的布料,織就另一個球體,就像白天的月亮一樣,漂浮在那裡。綻放出烏托邦式夢想的美與虛幻!虛幻?不,說不定那顆球體的光輝,會朝著我們居住的大地,反射出非常尖銳的批判之毒!
柏拉圖的亞特蘭提斯、莊子的無何有之鄉……十六世紀初葉,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寫出一卷《烏托邦》以前,烏托邦的夢想,似乎就一直持續刺激著人類的想像力。一直到現在所產生出的烏托邦,或是可以稱為烏托邦式的產物數量,龐大而驚人。因此,這些烏托邦的傾向與型態,也是形形色色,令人難以預料。不只是「漂浮在未知海上的理想鄉」這樣簡單而天真的看法。
大概也具有實踐家靈魂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在革命後的法國中心,以「情念引力」的類比為工具,描寫出整個社會由情色體系控制的雜交構圖。西拉諾貝爾吉拉克(Cyrano De Bergerac)前往外太空旅行,格列佛漂流到小人國。H‧G‧威爾斯幻想著駕駛著時光機,顛覆時間的座標軸。赫胥黎(Aldous Huxley)夢想著完全的蟻塚式社會……。要舉例下去,將會無止無盡,說得極端一點,就連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在我的眼裡都可以稱之為偉大世界落日的烏托邦式夢想的產物。
所謂的烏托邦,往往違反社會一般的常識,採取反烏托邦的形式。用影像式的簡單比喻來說的話,就像是在一座被慵懶逸樂的大氣包圍下的田園中,就連獸類、鳥類、魚貝類,甚至更低等的菇菌類,都會彼此有反應與感覺,無數的裸體男女,重複著懶散的渴望,這一幅波希(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的「悅樂之園」,如果是在描寫烏托邦的話,那麼描寫著堅固大氣與岩石山、以及噴出有毒的火焰之中,迪里克‧鮑茨(Dieric Bouts 1415~1475)那一幅被異形怪物折磨消瘦的裸體的「地獄」,一定也是烏托邦的情景。不是嗎?在荒涼的西特爾島上,聳立著黑影重重的絞刑台,眼球被烏鴉挖了出來,罪人的屍體、腐爛的內臟遭到啄食,這些正完全將波特萊爾的靈魂所渴求的東西,用影像表現出來了。那絕對不是充滿甜美氣息、妝點著桃金鑲花與薔薇、山鳩的鳴叫聲四處迴盪的愉悅島嶼(《西特爾島之旅》)。
我還必須說一句話,真正的烏托邦,必須是系統化方法的精神,是汲汲營營地將一塊塊磚瓦往上堆積,具有散文式、建構式精神的人才行的。因為要塑造出一個反世界,一個世界的完整迷你形象,為了住在那裡的居民,建立出政治、經濟、法律、教育、軍隊等社會基礎不可或缺的東西,就需要一位烏托邦者。就這個意義而言,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可說具備了真正烏托邦的骨架,可稱之為烏托邦故事的始祖。
在日本,明治十五年出版井上勤翻譯的摩爾的《烏托邦》,是最早的介紹。很早就輸入了最正統的範本,可是我國的烏托邦歷史卻很貧乏。仔細思量之下,也許日本人的體質,本來就很難符合一個烏托邦者應具備的那種體系式的、方法式的、建構式的、散文式的精神。沈迷於日常生活中瑣事的私小說精神,本來就與烏托邦式的想像無緣,不過,偶爾會出現異種或變種。另一個世界的消息,或觀想、或幻想,這些東西具有特殊而濃厚的詩的性格,是一個迷你世界,可是卻只是瞬間出現,或只是片斷呈現。比如芥川龍之介的《河童》以及《不可思議之島》都只不過是為了諷刺而做的即興舞台。江戶亂步川的《帕諾拉瑪島奇譚》就像是在夏夜夜空中,瞬間即逝的五彩繽紛煙火,美麗而脆弱。即使腦中浮現出極端烏托邦者風貌的稻垣足穗的臉龐,也只有一幅《一千一秒物語》的影像而已。要把《黃漠奇聞》稱為烏托邦故事,又有點抗拒。結果,足穗只是不斷訴說著對遙遠烏托邦的鄉愁而已。
可是,到了六零年代,我們終於有幸得到一本藉由真正的烏托邦者的方法式精神,建構出來的真正烏托邦故事。
那就是沼正三的《家畜人鴉俘》!
舊文庫版有六百多頁的這本小說,網羅了烏托邦者的主要原則:(1)與現實世界的空間隔離;(2)導入異次元的時間座標;(3)與現實世界的秩序(理念)完全顛倒;(4)統一式原理的控制;(5)排除實現的可能性。猶如三島由紀夫所讚嘆的,其架構性可謂稀有之至。
前言就說到此為止了,我們立刻進入「鴉俘」們居住的奇怪超現實世界吧!
II
一九六X年的某一天,日本青年瀨部麟一郎與其未婚妻,美麗的德國女孩克莱兒,因為偶然的機緣,坐上了因故障而臨時降落,來自未來世界的時光機。載著兩個人的時光機,回到了存在於二千年後未來空間的邑司宇宙帝國。而這座邑司宇宙帝國,位於什麼樣的地方呢?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第三次世界大戰後,在世界毀滅的混亂中,白人(英國人)駕駛著太空船,逃到人馬座星圈的一個行星上,在那裡建設了這一座宇宙帝國。
帝國的版圖遍及無數行星,行星上的居民駕駛著時光機,可以自由進出各個時間帶。他們擁有高度文明,形成完全的女權制社會。這個帝國用嚴格的階級制度來統治。等級最高的是由王族、貴族、平民組成的白人階層,接下來是有義務對白人無條件服從,並服侍白人的黑人階層。然後,還有比黑人更低等的階層,與其說他們是奴隸,還不如說是家畜。他們是被道具化的生物,也就是「家畜人鴉俘」。白人以神的身份,高居於黑人與鴉俘之上,他們受到無上的尊崇,被當作是絕對信仰的對象。白人、黑人、鴉俘之間的順序有多嚴格呢?看他們的攝取物與排泄物的連鎖關係就可以一目瞭然了。
白人的排泄物變成黑人的酒或營養來源,而黑人的排泄物則變成鴉俘的營養來源。千萬不要笑言其荒誕無稽,筆者為了說明這個部分,〈第六章2 三色攝食連鎖機構〉就用了二十張稿紙,甚至連卡路里計算或化學式都有。
未來文明中,生體科學發達到令人害怕的程度。可以自由自在改變、修正生物的型態或器官的形狀。配合各式各樣的用途目的,被畸形化的鴉俘們,棲息在怎樣的屈從與侮辱之中呢?舉例來說,職稱為「舌人形」的鴉俘,他們擁有畸形長大化的舌頭,為白人女性的性做服務,他們是專為了慰藉白人女性的無聊而存在的人形。為了不損壞白人女性的肌膚觸感,他們被脫毛,消除鼻子或耳朵等不必要的凸起,剝奪視力,又考慮到在服侍的時候,不會漏接到湧出的「Juice」,在嘴唇上植入海綿質的人工皮膚癌。而職稱為「肉便器」的鴉俘,他們就是活生生的便器,要吞下白人的糞尿,並舔拭排泄物。(他們不准直接吃下白人的糞便,這些排泄物事後會被回收,做為黑人的糧食。)此外,還會用生體糊將幾個(幾隻)鴉俘黏在一起,做成白人用的活浴缸。也有的鴉俘被矮小化,變成在金魚缸裡游泳的寵物,或是放在抽屜裡的迷你樂團中的樂師。有的還要鑽進內褲裡面,參與生理期的清潔工作。只要舉出其中一部份,就大概可以想像他們身處的情境了吧!
「牠們的腸道都住著一條鉤頭蛔蟲,蟲頭刺入腸胃之間的幽門,有鉤固定,蟲尾則長達肛門,像絲蟲一樣在腸道中蜿蜒行走。進食時,蟲尾從肛門伸出,插入營養液中,由蟲尾末端的開孔處吸取汁液,直到內部中空,狀似囊袋的蟲體漲滿為止。接著,再從緊鄰幽門下方的細孔徐徐噴出營養液,滋潤腸壁,為宿主省去進食的麻煩,同時以易於吸收的型態給予腸部養分。然而蛔蟲本身的營養卻非來自這種汁液。隨著汁液從腸內排放出去,蟲體也失去了養分,待汁液化成廢液,就在排泄的前一階段,蛔蟲的下半身會將之吸收,做為本身的養分。由於蛔蟲攝取營養的能力十分卓越,無論多麼難以消化的養分,都能被同化吸收到最後一分子,不留一絲無用的廢物,但是,正因為尾節些微硬化是正在進行新陳代謝的特徵,所以不需排泄。既然蛔蟲本身如此,當然天馬也不需要排泄行為……」
除此之外,邑司帝國發展出來超乎想像的奇特風俗或怪異科學技術,不勝枚舉,詳情請看原書內文。
想想我們加諸在人類以外的生物身上的種種殺戮與畸形化(我們屢屢稱之為改良)的歷史,我們實在沒有資格批評邑司世界的居民對等同於畜類的鴉俘的對待。不過,有一些事情對日本人來講,很難等閒視之。位於黑奴之下的黃畜、智慧型猿猴,這些支撐著投射在二千年後未來空間中的烏托邦的「家畜人鴉俘」,正是日本人二千年後的模樣。
「鴉俘(yapoo)會讓人想起《格列佛遊記》中,居住在『小人國』中的醜陋生物『雅虎』。當然,也會令人聯想到『Jap』。」沼正三脫離了史威斯特那股悲觀主義的陰鬱,使他自由而毫無所懼地為鴉俘們說出了下面這段話:
「為使白人樂園邑司的文明開出繁華的花朵,而以肥料為名被生產、被愛用,即為日後鴉俘的命運。若以鴉俘人類觀視之,等於成為他人永無止盡的禁臠,陷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卻無可奈何。認為這是一齣悲劇的人,是站在錯誤的鴉俘人類觀的角度;假設站在正確的鴉俘家畜觀,就不會有哀慟的感覺。正因為隸屬種族的個體增加以及多樣性的分化變種,充分展現了生物的繁榮,在幾百個太陽下,現階段沒有任何一個種族能如simius sapiens那般繁盛,只要有人類的地方,便能與之共同發展,這種智慧家畜的生物學前景,將是無可限量。」
III
但是,讀者一定會問:白人把鴉俘虐待到那種程度,難道他們沒有罪惡感嗎?我們先說結論:他們一點都沒有罪惡感。鴉俘人猿說被當作最初的政策性神話,流傳下來。雖然那是為了堵住人權論者的嘴,透過媒體流傳開來的。在那個階段,還是有一些人無法排除疑惑,不過,鴉俘家畜化的「事實」,降低了人們的懷疑,給予強化信念的力量。而且,二十三世紀出版盧森勃的大作《家畜人的起源》,讓整個狀況有了決定性的發展。他在那本書中,用豐富的例證與巧妙的人類學理論,論證鴉俘只不過是疑似人類的生物而已。人們連一點點良心之痛都沒有,推動了鴉俘的非人類化。我們可以從邑司帝國的人種序列中,讀出納粹人種理論的微妙投影。但是,書中還補充說明這位盧森勃是具有「在前史時代末期,著有《二十世紀的神話》的納粹戰犯哲學家奧佛雷‧盧森貝格的血統」的一位偉大生物學家。
那麼,讀者一定會再問:白人給予如此的污辱,黑奴或鴉俘對白人都毫無憎惡或敵意嗎?面對這樣的壓制,毫無反抗嗎?這一類不祥的徵兆,也許會撼動邑司帝國嚴格的階級制度,可是,卻一點也看不到這類不祥的徵兆。原因應該很明顯吧?不用說也知道,那就是白人所施予的周到而巧妙的各種馴致策略。首先,應該可說是一種意志去勢的方法,叫做腦葉剔出手術。藉由這種手術,可以剔出令自由意志發達的大腦局部,使他們的腦子只留下服從本能。另外,也有極度利用條件反射的洗腦的方法。可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徹底進行的宗教教育,也就是白神崇拜的信仰心,對白神絕對俯首跪拜。比如說,生來就是做為白人用狩獵目標的黑奴,直接用嘴巴承接克萊兒的聖水(尿),做為臨死之水,在極致的幸福恍惚中嚥下最後一口氣。另外,還有生來專為負責擔任白人女性的妊娠檢查器的矮鴉俘,能夠進入女人最內部,為女神的生理期服侍,是他們最值得驕傲的事情,他們懷抱著聖職者的意識,全心全意,充滿熱情地執行她們所告知的受胎使命。將死的他們口中,又會吐露出對女主人多麼熱烈的讚仰言詞呢?「女神啊!我將死在這裡。我再也無法蒙賜您的聖水,可是,女神啊!您教導我酩酊的滋味,瞭解沈醉的信仰之喜,我很幸福,謝謝,謝謝您的恩惠,白晰女神寶琳,萬歲!」「肉便器」們不止不避諱自己的職務,甚至覺得嘴巴可以直接接觸神體,承接神體的神酒或神糧,他們覺得自己的地位具有特權,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這份工作本身,就會帶給他們無可言喻的法喜。
「利用信仰,他們對其實很難吃的東西產生錯覺,這不是使用者的狡猾智慧嗎?」充滿批判的質問,那位提倡慈畜主義,給鴉俘們帶來福音的安娜‧泰勒斯會這麼回答吧!「不,味覺沒有真假,若沒有信仰,不好吃的東西,也會因為信仰的比例,而變得好吃。你怎麼能說美味是虛假,不美味是真實呢?」這些話可以代換成以下這種虐待狂理論:「鞭子或繩子,一開始會覺得痛苦。可是,一旦加以訓練,以後就會覺得可以用鞭子或繩子來疼愛他。這兩種方式,就會變成愛的表現。所以,反過來就可以對訓練中的鞭子或繩子,加以肯定了。」
各位讀者應該已經瞭解了吧?要適當對應虐待狂的理論,就必須要有受虐狂。是的,所謂的邑司宇宙帝國,對鴉俘們而言,就是一個巨大的受虐狂王國。從這個觀點來看,白人給予的勞役或服侍,越是苛刻,黑奴或鴉俘感受的歡喜就越大。在如此完整而充足的關係中,憎惡或敵意是永遠都不可能產生了。
白人們受到高度文明的恩惠,位於階級的最高處,享受著黑奴或鴉俘們的服侍,當然一定處於極為舒適的狀態中。可是,卻與鴉俘們那種深入靈魂的極端幸福感相差甚遠。在這部小說中,最大的反論,就是感受到真正的恍惚,真正極端幸福感的人,不是統治階層白人,而是受統治的黑奴或鴉俘們。
明白地說,這是完全反烏托邦的。主體是被虐待的鴉俘們,我們不能被揮鞭者與跪拜者這樣的圖像外觀所矇騙。是受虐者把鞭子拉過來的,作者沼正三把自己放在鴉俘這一邊,是無庸置疑了。西蒙波娃(Simonede Beauvoir)以前曾將受虐狂的本質,定義為「身為一個無生氣的物體,努力想拋棄自己的時候,又回歸到自己的主觀性」。但是,家畜化、道具化、機械零件化的鴉俘群,完美地達成了受虐狂想要物化的願望,必須說他們是處於理想的狀態中。
屈服的擴大與幸福的擴大,都與一般的價值觀及理念相反、倒錯,在邑司的世界中,也完全成功地融入了惹內所說的「將糞便變成黃金之術」。寫到這裡,使我不得不想起馬庫色(Marcuse Herbert)這個名字。
在動物身上看到的單純生殖活動,是屬於大自然的,可是,所謂的情色主義,是對大自然的挑戰。而且,那也是想要侵犯脫離動物性的自然之後,人類所獨有的領域(勞動、生產)。當社會生活基礎的勞動或生產性負面運作的時候,情色主義就必然會變成反社會性。佛洛伊德認為這種對立,是「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各執己見,互不相讓。現代的文明,不用說也瞭解,是建立在「現實原則」佔優勢之上。人類生活的價值標準,是以汽車、電視、拖拉機等來制訂,把物質的生產性做為神聖的理想這一點,資本家與克里姆林宮的主人都一樣。
馬庫色以社會科學的方式,將精神分析擴大,可是,結果他對於新佛洛伊德派一直「將壓抑的生產性,當作人類的自我實現,而加以讚美」似乎無法忍受。馬庫色的主張是,拋棄壓抑才是新文明努力的方向。其主張的具體內容,援引希臘羅馬神話,構想著性衝動的全然解放、個人全體的情色化。在「現實原則」的壓抑下,長期以來,性慾侷限集中在肉體的一部份(性器),肉體的其他部分,則被賦予了勞動工具的意義。但是,在拋棄了壓抑的新世界中,所有的性感帶都復活了,性器的優越性將會消失。整個肉體都是性的對象,都將成為快樂的手段。肉體停止成為勞動工具,工作變成遊玩,於是人類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節日……。馬庫色在《性愛的文明》中的構想,就是放棄「現實原則」與「快樂原則」,放棄所有的壓抑,這麼一來就會出現烏托邦的世界。
但是,馬庫色的世界,與邑司可怕的反烏托邦之間,不覺得有點一脈相承嗎?一邊是知名哲學家,另一邊是荒唐故事作家,但是,受虐而產生的性滿足=性衝動的解放(快樂原則)以及完成社會性的職務(現實原則),兩者在此確實合而為一,至少勞役變成快樂,服侍變成愉悅這一點,兩者都是相同的。邑司帝國面對整個邑司帝國社會的要求,能夠有性愛式的反應,這些鴉俘們無疑就是「性愛人類」,站在鴉俘這一邊來看時,根本就可以把邑司帝國文明稱之為「性愛的文明」。
IV
想要顛覆長久以來保持的觀點,打開一個新局面,是需要不顧一切的轉換,但是,馬庫色的構想是以在歷史的過程中,他對消失的、過去的神話時代的回憶做為基礎。那麼鴉俘幸福的泉源,也可以說是現在的我們已經完全失去,卻被奇異擴大的畫面吧!
老實講,想起馬庫色的同時,我腦海裡還浮現出另一個人物。就是寫《莫諾斯與烏納的對話》的愛倫坡。
《莫諾斯與烏納的對話》是採取與死者對話的形式,這個奇妙故事的前半段,是在沈痛地批判文明。詩人的預見力真是可怕,身處於十九世紀中葉,正確洞察我們現代正在逐步失去河川、海以及大氣等大自然,詩人的慧眼在他對人道主義與「進步」的天真信仰下,西歐文明的合理主義,隨著無可救藥的自我繁殖結構,會走到多極端的地步呢?詩人的慧眼似乎已經透視了以上的動作圖式必然導向滅亡了。愛倫坡這麼寫著:
「啊!我們在最受到詛咒的那一天斷氣。偉大的『運動』──這是暗號──沒有停止。精神、物質兩方面都生病了,病態的混亂。一旦技術至上興起,掌握主權,我們被知性逼到權勢的地位上,技術至上的鎖綑綁了我們。人們將不得不承認大自然的主權,因此,面對自然的領域,我們認為我們已經獲得了統治權,並擴大這種統治權,陷入宛如孩童般的瘋狂中。就連懷抱著任性的幻想,把自己比喻為神的時候,都是孩子氣的愚蠢在引導他們。就像我們可以從人們混亂的起源來想像一樣,他們感染了系統與抽象這種病。他們將自己禁閉在普遍性之中──在他們的奇特觀念中,萬人平等的觀念佔據一席之地。而且,無視於類比,蔑視神。無視於在天地萬物之間,清楚明白的秩序規則,無視於嘈雜的警告聲。瘋狂追求著絕對普遍的萬人平等,話雖這麼說,如此之惡弊,形成其母胎的惡弊,是從知識中必然會衍生出來的東西。人類不能同時並行知道之事與屈從之事。於是,興起無數吐著煙的巨大都市,綠色的樹葉面對融鐵爐熾熱的氣息而顫抖,美麗的大自然容顏,有如罹患可怕職業病一般地扭曲了……。」
透過這段引用自愛倫坡的文字來眺望邑司的世界時,會呈現出什麼樣的樣貌呢?
當諷刺之箭從預期之外的方向飛來,深入人肉時,總會刺入最深最嚴重的要害。《家畜人鴉俘》隱含的尖銳批判之毒,就交給各位讀者去品味吧!
V
話題再回到邑司帝國裡面。被時空機綁架到邑司帝國的麟一郎與克萊兒遭遇到的命運,輕而易舉就可以預測出來吧!屬於畜類的黃色人種與屬於神的白人女性,竟是未婚夫妻,這對邑司世界的居民來講,應該是難以置信的事情。克萊兒受到熱情的款待,漸漸學會了身為神的權威。另一方面,麟一郎則接受各種訓練與教育,漸漸變形成完美的鴉俘「麟」,把新地球腸蟲插進腸內、施行皮膚強化處理、被去勢、訓練他喜好白人的排泄物、鍛鍊其對白人產生敬神式的忠誠……。於是,他逆向攀登顛倒的金字塔階梯,在污辱、奴隸、痛苦之中找到快樂,漸漸變成受虐國度名符其實的居民。這部小說應該可以當作一種教養小說來讀吧!
本來,在烏托邦的描寫中,詩的文體是最不適合的。從他一開始述說時,就有的烏托邦資質來看,當然不適合詩的文體。但是,沼正三很堅持將幸福編織進文體裡面。重要的是述說的內容,不是文句。從我們至今節錄出來的幾段,就可以瞭解,可以說是無味而枯燥的散文式文體貫穿了整本書,就我來看,整本書唯一沈溺於字句之中的段落,就是第二十四章第三節最後那一段例外而已。而彼此朝相反方向成長,麟一郎與克萊兒唯一交會的那一瞬間,卻只有以下幾行優美的文字:
「她就這樣在空中列車的客房中,過了三個小時。在馴致椅子的表皮上面,是美女一邊在夢裡學完了人類與鴉俘的興亡歷史,一邊沈睡的三個小時,而在表皮下面,卻是鴉俘支撐著她的身體,把主人搖得很舒適,專心致意地向她祈禱的三個小時……。」
閱讀著這本書的舊文庫版,約六百多頁,我的腦子裡忍不住浮現出薩德的書,他描寫可怕如夢魘的情景所用的文體,與這本書相同,是一種無味而乾燥的文體。
但是,第二十五章開始不斷出現某種文字遊戲,閱讀這些文字遊戲,就可以瞭解作者有多愉悅了。比如說,有關「神嘗」、「新嘗」在語源學上的文字遊戲,就可以看出他的黑色詼諧。所謂的「神嘗」,就是被賦予成為肉便器命運的鴉俘,在開始調教時的一種「發誓成為品嚐神(白人)之物的存在物,一口一口品嚐液體固體的儀式」。而所謂的「新嘗」,就是在調教結束之後,一種「身為新的廁所,第一次品嚐的儀式」。又比如下面提到這一首和歌,是歌頌負責生理時清潔工作的矮鴉俘的一首歌,不需要作者細心的解說,就可以瞭解其中趣味了。
「望著與聖孔接唇的極小畜,只留下了紅色的經水。」
(譯注:以上所呈現是作者玩文字遊戲後的意思,和歌原意是:原以為聽到了杜鵑啼叫,轉頭看去,卻什麼也沒看到,只看到一輪明月殘留在破曉的天空中。)
再節錄一首吧!
從今而後,不再回顧過往。
將以區區護衛之身立足。
(護衛的另一種解讀,就是「想喝妳的尿」。接獲賜飲命令的時候,要採取站立姿勢,所以才說「たつ(立足、站立)」。這是新捕獲、將被變成肉便器的土著鴉俘,歌頌在邑司世界中新生的決心。)
這是歌頌著被肉便器化的鴉俘,在邑司世界決心重生的詩歌。能夠把日本傳統的和歌,硬是掰到這麼奇怪的領域中,全天下大概也只有沼正三一個人了。
同樣的趣味,在書中到處都是。如「天之岩戶」變成是「Amen in heart」之訛;「天照大神」則是白人女人的名字「安娜‧泰勒斯」;「淤能碁呂島」變成「Honoured goal」;「高天原」變成邑司的巨大飛行島「塔卡拉馬漢」。沼正三把「伊邪那岐」與「伊邪那美」二位神,當作是白人從邑司世界搭乘時光機,飛到原始時代的Japan各島,他們來的目的是要做考古學上的實驗,把未施行畜化處理的雌雄兩隻原鴉俘「邪那岐」與「邪那美」放到日本,而「伊邪那岐」與「伊邪那美」這兩位神就是被放到日本各島的兩隻原鴉俘。
但是,作者真正的用意,並不只是要用這些黑色幽默來博讀者的苦笑。沼正三使用這些文字遊戲,順著日本書紀與古事記的文脈,想要一舉顛覆日本歷史文獻中所記載有關日本開國的狀況。這些日本人的後裔,如上所述,處於遙遠的未來空間,將走到降為比奴隸還不如的可憐家畜人的命運。而回顧過去,萬世一系的首長,在世界史上居冠的民族歷史的起源,被聖化的發祥源頭,竟是家畜人鴉俘悽慘的容顏。作者深層的企圖,顯而易見。他不止要關上日本民族的未來,甚至也要剝奪日本過去的榮耀。於是,這本書完成了可怕的一貫性,就像咬著尾巴的蛇一樣。
VI
為了探尋其一貫性的意義,我們就必須把目光轉移到寫了這本怪書的作者沼正三。
與出版社的交涉,全部委託代理人,甚至有一段時間,死亡說甚囂塵上。對於這位謎樣的作家,我一無所知。因此,只能相信他自己在都市出版社單行本中所寫的〈後記〉了。在那篇後記中,他這麼寫著:「戰爭結束的時候,我當時是學徒兵,人在外地。俘虜生涯中,在某種命運的安排下,我處於被迫接受虐待的處境下,對白人女性產生了被虐的性快感,成為一個性異常者回來……」從這些話裡,讀者可以自由想像,白人女軍官與被派去女軍官房間打雜的年輕俘虜之間,所發生的種種刺激畫面。。(為什麼作者一定要把邑司帝國建造成女權制社會,看到這裡應該瞭解了吧!)總之,沼正三變成一個「性異常者」,踏上了遭到白人佔領,已經變成一片焦土的祖國土地。所有人為了活下去,都需要有一些可以抓住的東西時,年輕的士兵看著廢墟,眺望著地平線那一端的未來,過去一切的權威或秩序,在戰敗後帶給他的,是內心某種官能上錯置的騷動。
內在的飢渴,無法輕易療癒,為了發洩這些飢渴,沼正三在《奇譚俱樂部》雜誌上,以《某個夢想家的手帖》為題,連載有關虐待狂的散文。後來,結合科幻手法與偉大的虐待狂夢想的《家畜人鴉俘》,也在這本雜誌上連載。從昭和三十一年的十二月號開始,連載了二十回。
過去在軍隊內部,以天皇為最高階級所建立的完美虛假階級秩序,因為戰爭失敗而崩潰瓦解。保證民族優越性的神話露出破綻,顯現不動先驗的價值泉源枯竭了,全部的黃金在瞬間變成瓦礫。僅存的是什麼呢?只有屈服在白人統治下,變成被佔領的日本。沼正三在外地接受虐待狂洗禮的體驗,與這種狀況產生的精神結構,難分難捨。在小小的八疊大房間裡面,不斷發生的SM劇,無法醫治他的飢渴。自己所夢想的隸屬狀態,需要奴隸制、俘虜狀態等某種制度的契機,我們必須在這本書裡面,讀出他內在想告白的這些想法。俘虜時代的體驗,成為他寫這本書的直接動機。當時所產生的生理、心理上的倒錯傾向,在被佔領的日本這樣的精神結構支撐下,被放大、加倍。
前面提到文字遊戲,在文字遊戲的材料中,看到「靖國」、「九段」的時候,我覺得我似乎看到了作者那個年代,被迫遭受到的內在傷口的深度,一時無語。因為利用文字遊戲嘲笑、揶揄的對象,可以藉由企圖讓價值、權威失落,反向證明隸屬於高價值體系,是不值得期待的。這本小說在連載的時候,是戰爭結束後,已經過了十年了。那時候,「靖國」、「九段」竟然還盤據在沼正三內心的陰暗處,看到這種情景,令人怎能不黯然啊!看到「邪蠻」這種笑話,會笑的人就笑吧!請不要誤解,我並不是說沼正三在戰敗以前,是皇國史觀的忠實奉行者。但是,有誰能夠完全擺脫青春期的意識型態呢?當我們正在面對死亡,而且死亡是如此確實的事情時,我們除了摸索死亡的意義之外,還能關心哪些精神上的事物呢?在最慘澹的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浪漫派強烈吸引著無數年輕人的心,在那與死亡直接接觸的危險場所中,卻得以散發咒語般的勢力,為什麼呢?只要回顧這整件事情,不用我說,大家也能瞭解吧!意識型態的虛妄性,就讓歷史學去斷罪吧!但是,因為這些虛妄性而受到傷害的心,當他們打開黑暗的口時,文學的領域就從那裡開始。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既有價值體系與秩序瓦解後發生的事情,到底是什麼呢?在一片廢墟的灰色之中,從消失的神話裡,找到了民主主義的神話,真正的黃金就隱藏在這裡,使整個日本遺忘了屈服的現實。想想「奉進駐軍之命」這句話的魔咒般的效能吧!戰敗後那幾年,日本人親美的態度,是過去與未來都不曾有過的強烈。的確,同時具有令人聯想到魔術的出色手法與陰險氣息。但是,當時沼正三僅僅抓住屈服與隸從,徹底活在被佔領的日本這幅構圖中,然後,甚至把這幅構圖塑造成一個反世界。
在沼正三的眼裡,他看到因為戰敗的屈辱,日本的歷史過程全部遭到腐蝕。這就是V章最後所說的一貫性的意義吧!
VII
在寫這篇小文章時,我覺得我似乎太過賣弄學問了。但是,最後還是必須請沙特出場。透過沙特對想像力的龐大現象學論證,所得到的結論,大略如下:
知覺作用與「影像」喚起的功能,所出現的想像力,是將人類的意識世界一分為二,所佔有的極為重要的要素。可是,「知覺」會與目前的事物連結,以現實世界為主。相對的,「影像」總是遠離眼前的世界,總是以非現實的世界、虛構的世界為主。若要簡單敘述兩者的關係,那麼可以說「想像界」是成立於「現實界」的空無化之上,而「現實界」是成立於「想像界」的空無化之上。當意識在某種型態中,完全不包含否定現實的契機時,也就是說,藉由知覺到的眼前事物,意識被完全佔據的時候,想像力是無法啟動的。意思就是說,必須脫離與現實事物的緊密連接,且受到拘束的狀態,當意識獲得自由的時候,才有可能產生富有想像力的創造。沙特說:「非現實的東西,藉由孕育在世界之內的意識,誕生在這個世界之外。人類能夠想像,為什麼呢?因為人類天生就是自由的。」
純粹的想像力的產物,而且聚集了所有不存在的要素,所創造出來的烏托邦景致。若照沙特式的說法,這就證明人類意識的自由性,達到了最大的程度。但是,沙特所說的「狀況」,在這裡又有另一個狀況介入。借用平井啟之的話來說的話,就是「所謂狀況(situation),一方面是隨著『影像』,以否定現實為想像力的絕對條件,另一方面,是指從裡面否定自己的現實,所支持的事實。比如『夢』,作夢者的意識,很明顯是處於對現實性的知覺完全喪失的特權狀態中,可是,就『夢』的內容,事實上嚴格而言,那位做夢者是活著的。而且,又同時活在現實中的時間、空間中,也就是說,受到這個世界的限制。」若依照這篇文章開頭時所舉的例子來講,離開現實的地面,本來應該緩緩上升,升到遙遠虛空盡頭的氣球,卻被一根繩索,紮實地繫在地面上。
漂浮在遙遠天空中的,是一幅令人驚訝的反烏托邦風景。這幅風景是藉由想像力的作用,建構在「無」之中,是證明人類的自由性的「影像」的巨大集合體。但是,看著這幅反烏托邦以及聯繫地面的那一根繩索的根部,就會發現黑色的情色受虐狂陰影。漂浮在夢想的天空中時,不管想綻放多妖豔的光彩,色情受虐狂在「現實界」,依舊受到「疏離」,依舊受到「挫折」。在這篇文章的標題中,揭諸出「榮耀」與「悲慘」兩個詞,就是我對這些被自由與宿命糾纏在一起的人,所表達的感慨。
三島由紀夫得意洋洋地提出忠告說:「不可對這部作品的諷刺與類比,評價過高。」(《小說是什麼?》)但是,若將「諷刺」與「類比」從這本小說中拿掉,就好像失去辛辣味的芥末。無限刺激讀者的想像力,讓「類比」與「諷刺」如亂箭到處飛,不就正是一本書的真正價值嗎?我也希望各位當作是一個小小的嘗試,來閱讀這篇小文章。也就是說,發諸於個人生理深深的必然,以性的倒錯這種宿命,所妝點出來的世界,能夠做到什麼程度的基本原理(metaphysics)的普遍性呢?作者沼正三在舊都市出版社單行本的〈後記〉中告白說對於這部作品「再版,被超過萬計的讀者選上,這件事實」,「令他為難」。但是,既然花錢買了這本書,讀者應該有正當權利,可以漠然扼殺掉作者的「為難」吧!
(撰文者為當代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