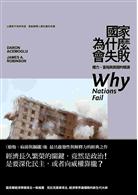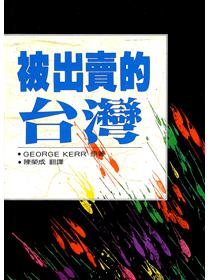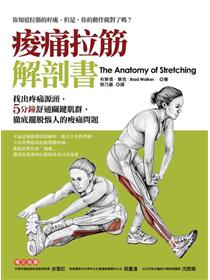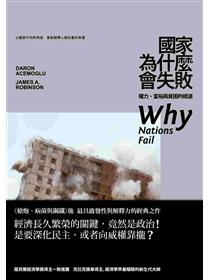章節試閱
第一章 美國在雅爾達的歷史錯誤
︽雅爾達協定︾與︽大西洋憲章︾,代表兩種對立的哲學與戰略觀。
︽大西洋憲章︾的哲學,是以自由力量的聯合,戰勝法西斯奴役制度,實現有利於全人類自由發展的和平。
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他的一篇演講︿人類四大基本自由﹀︵浣our Essential Human Freedoms荂`︵註 1 ︶中提出,反法斯西斯戰爭勝利後,﹁我們將看到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言論自由與表達意見的自由。
第二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方式的自由。
第三是免於匱乏的自由,保證每一個國家的居民都能過著健康的和平生活。
第四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解釋免受恐懼自由時,羅斯福指出:﹁從全球角度來講,這意味著在世界範圍內全面徹底裁軍,使世界上一切地方,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對任何鄰國發動武裝侵略。﹂︵註 2 ︶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停泊於大西洋紐芬蘭海面的奧古斯塔巡洋艦︵USS Augusta︶上會晤,簽署著名的︽大西洋憲章︾,重申這﹁四大自由﹂,還增加了民族自決條款,即在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後,﹁被強制剝奪主權和自治的人民,得以恢復主權和自治﹂;這個劃時代的重要文獻,它的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動員了從民主國家到殖民地、附屬國的廣大人民,奠定了反法西斯聯盟勝利的基礎。二○○二年九月,美國小布希總統簽署︽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所提出的﹁有利於自由的力量平衡﹂概念,事實上已經包含在六十一年前的︽大西洋憲章︾之中。︵註 3 ︶
然而,當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的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一起出席了雅爾達戰時會議。﹁雅爾達﹂的哲學,是對︽大西洋憲章︾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的背叛。﹁雅爾達﹂確立的自由制度大國與奴役制度大國共同瓜分全球勢力範圍的﹁力量平衡﹂,是對﹁有利於自由的力量平衡﹂的反動,使戰後蘇聯共產奴役制度的版圖,擴展到歐洲的柏林圍牆與亞洲的蒙古和北韓。在雅爾達戰時會議上,羅斯福同意史達林把波蘭國界西移,蘇聯佔領波羅的海各國和波蘭的一部分,﹁美國和英國都不會出現﹂。羅斯福說,他﹁樂見波蘭東邊國境線向西推移,西邊國境線也自奧得河再推移﹂。邱吉爾和羅斯福在雅爾達只獲得史達林簽署的一紙聲明,表示蘇聯同意戰後在所有被佔領的前軸心國內舉行民主選舉;但事實上,這些國家將毫無例外地落進蘇聯的勢力範圍,邱吉爾與羅斯福根本無法使其實現。︵註 4 ︶
對亞洲,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簽訂了︽雅爾達密約︾。照毛澤東的說法:﹁雅爾達會議上,一個史達林、一個羅斯福、一個邱吉爾,三家子就把歐洲分了,把世界分了。中國分給了美國,蘇聯要老沙皇佔的旅順口和中東路,把外蒙古佔為蘇聯的殖民地,老沙皇在新疆的利益,也都要分給蘇聯。﹂︵註 5 ︶
︽雅爾達協定︾取代︽大西洋憲章︾,導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自由民主制度世界與共產極權制度世界的大分裂。而處於中間地帶的國家,成為這兩個對立世界爭奪的戰場。這就是世界現代史上許多荒唐故事的根源。台美中三國演義,則是這些荒唐故事中歷時最久,至今還在繼續荒唐下去的一個。
假如遵循︽大西洋憲章︾的哲學,台灣與中國,就都會面臨成為像美國與印度一樣的自由民主獨立國家的歷史機會。
戰前的台灣,是﹁被強制剝奪主權和自治﹂的日本殖民地。隨著日本戰敗放棄台灣,台灣人民理所當然有權建立自己的自由獨立國家,如同羅斯福曾經承諾:﹁我不相信我們能夠一方面反抗法西斯奴役,同時卻不去努力,讓全世界人民自落後的殖民制度中解放出來。﹂︵註 6 ︶
同樣,蔣介石的中國是反法西斯的戰勝國,當時顯然是具備了走向自由民主國家的充分條件。
中國國際地位在二戰後達到歷史高峰,上升為戰勝法西斯的﹁四大強國﹂之一。當時政治、軍事、經濟實力均居於絕對優勢的國民黨政府,擁有四百三十萬軍隊,其中三十九個旅是由美國軍械裝備齊全的精銳部隊,在兵力和機動性上佔絕對優勢。戰爭結束時,國民政府的財經狀況甚佳,國庫黃金、外匯存儲達到歷史最高點。一九四五年底美元存底超過九億,包括一九四二年的五億美元貸款大部分都未曾動支,以及戰時美國政府支付給中國政府約四億美元左右,作為償還中國政府為美軍所墊的費用。︵註 7 ︶
中國最大的反對力量——中國共產黨處於相對弱勢。毛澤東不是一開始就準備打內戰的,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從延安赴重慶﹁國共和談﹂之前起草的︿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判斷﹁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承認國民黨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走上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中國的主要鬥爭形式由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議會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面來解決,因此黨的全部工作必須適應這一新形勢﹂。︵註 8 ︶在九月二十七日於重慶,毛澤東接受路透社︵Reuters︶記者甘貝爾︵Doon Campbell, 1920-2003︶訪問時,毛澤東提出﹁自由民主的中國﹂概念。
甘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它將實現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大西洋憲章︾的四大自由。﹂︵註 9 ︶
一九四六年元月,蔣介石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時發表﹁四項諾言﹂:
一、人民的自由。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司法與警察以外機關,不得拘捕、審訊及處罰人民。
二、政黨的合法地位。各政黨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並得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
三、普選。各地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
四、釋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漢奸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為者外,分別予以釋放。
在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的集會上,演說者把蔣介石的﹁四項諾言﹂與︽大西洋憲章︾的﹁四大自由﹂相提並論,認為這﹁四項諾言﹂將揭開中國歷史新頁。︵註10︶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1880-1959︶,專為調停國共兩黨實現和平民主來到中國,允諾和平民主實現之時,將援助中國經濟復興。顯然馬歇爾若調停成功,馬歇爾復興計劃將在中國先於歐洲實現。︵註11︶
從一九四五年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到一九四六年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前後,約半年期間,在中國興起了自由民主浪潮,這表明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所到之處,︽大西洋憲章︾的自由價值觀已深入人心,連毛澤東、蔣介石這樣的獨裁者,也不能不順應歷史潮流與人民意志,作出相應的表示。當時的﹁力量平衡﹂,的確是﹁有利於自由﹂︵Favors Freedom︶的。
然而大國強權﹁力量平衡﹂的﹁雅爾達﹂體制,終於壓倒︽大西洋憲章︾的自由潮流。馬歇爾調停使命注定失敗的一個根本矛盾,就是﹁雅爾達﹂體制與︽大西洋憲章︾的衝突。馬歇爾要完成調停的使命,必須使國共雙方,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接受︽大西洋憲章︾的自由原則,不但結束國共兩軍的敵對狀態,而且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使中國成為現代民主憲政國家。但﹁雅爾達﹂體制卻決定了無論蔣介石是選擇民主與和平,或是選擇獨裁與戰爭,美國除了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之外,別無選擇。這就使馬歇爾不得不一手敦促蔣介石和談,另一手幫蔣介石運兵到前線打仗。而當時國民黨倚仗其軍事、財政的優勢,傾向以武力消滅共軍的主張。陳誠誇口﹁三個月解決關外共軍,半年全國解決﹂。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南京軍事會議上宣佈﹁全面進攻﹂、﹁五個月打垮共軍﹂。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底,正好五個月,國民黨軍隊從共產黨手裡奪得十七餘萬平方公里土地、一百六十餘城。同年三月初,蔣介石趕走中共駐重慶、上海、南京的談判代表,命令胡宗南進攻陜甘寧邊區,三月十九日佔領延安。蔣介石打電報表揚胡宗南﹁延安如期收復,為黨為國雪二十一年之恥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報之也﹂,並親率中外記者到延安慶祝勝利。︵註12︶
蔣介石的勝利是中國悲劇的開始,因為他未能順應中國的民意所向,停止內戰,走上民主憲政之路。他當時有足夠的力量,又有美國支持。假如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不是選擇戰爭,而是如他在政協開幕式上許諾的選擇和平與民主,中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將改寫,毛澤東帝國將不會出現,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民主中國政黨政治中一支較強的競爭力量而已,像二戰後法國的法共與義大利的義共一般。
然而蔣介石卻選擇了戰爭,軍事力量佔領絕對優勢的國民黨,在全面內戰中只取得短暫的勝利。軍事上劣勢的共產黨轉敗為勝。毛澤東打敗蔣介石的決定因素是政治,他舉起﹁反內戰、反饑餓,要和平、要民主﹂的旗幟贏得了民心。內戰的結果,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力量自中國撤至台灣。共產黨佔有中國全部政治、經濟資源,失去了制衡它的反對力量。共產黨對國家權力與國家資源的壟斷,超過它取代的國民黨。毛澤東在﹁民主﹂旗幟下贏得了戰爭,戰爭卻使中國建立民主憲政的歷史機會失掉了。
毛澤東是世界上第一個挑戰﹁雅爾達﹂體制的歷史人物。他不接受以美、蘇為首的兩個對立陣營主宰世界的﹁力量平衡﹂,並且試圖打破這種﹁力量平衡﹂。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概念,即世界上存在著獨立於美、蘇兩個陣營之外的廣闊的﹁中間地帶﹂與﹁中間力量﹂。
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史達林在莫斯科一個選民大會上發表演說,提出﹁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要求蘇聯人民對此有所準備。接著在三月五日,邱吉爾於美國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以﹁鐵幕﹂︵Iron Curtain︶︵註13︶一詞聞名於世的演說,號召﹁所有講英語的民族結成兄弟聯盟﹂,對抗共產主義。這兩篇演說被看作是東西方的兩篇﹁冷戰宣言﹂。那時世界和中國都擔心美蘇戰爭。︵註14︶
毛澤東否定了當時的流行觀點。他說:﹁美國和蘇聯之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裡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在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他又說:﹁美、英、法同蘇聯的關係,不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的問題,而是或者較早妥協或者較遲妥協的問題。所謂較早較遲,是指在幾年或者幾十年,或者更長時間。﹂︵註15︶毛澤東的﹁中間地帶﹂戰略概念,可以概括為:
第一、美蘇戰爭的危險並不存在;
第二、美蘇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爭奪中間地帶;
第三、中間地帶的國家應爭取獨立自主,擺脫美蘇控制;
第四、中國應聯合中間地帶力量,制衡美國和蘇聯。
從反對︽雅爾達協定︾到形成中間地帶戰略概念,毛澤東強調的是獨立自主,不依賴任何外國。他說:﹁在中國掌舵,首先要有不聽指揮棒的精神,自己能獨立把中國這個舵掌好,不能讓外國人指揮中國人,不管你那個外國人是什麼共產國際,是哪一國,是哪個人。你發號施令,我不聽。﹂︵註16︶
所以當一九四九年四月共軍渡江佔領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之後,毛澤東設法同時與美國和蘇聯雙方接觸,試探建立並行關係的可能性。他派黃華在南京拜會美國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同時派劉少奇到莫斯科會見史達林。
共軍渡江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蘇聯大使羅申︵Nikolai Vasilievich Roscin︶卻跟著國民黨遷都,去了廣州,使毛澤東察覺到史達林比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更遵守﹁雅爾達﹂遊戲規則。﹁雅爾達﹂把中國︵除了東北與西北部分權益分給蘇聯外︶劃歸美國的勢力範圍,使得史達林始終跟著美國承認的國民黨政府,甚至跟得比美國更緊,美國跟到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淪陷,就停下來不跟了,蘇聯還繼續跟孫科︵蔣介石隱退後的國民黨政府之行政院長︶到廣州。毛澤東注意到這一點,就派黃華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長,去同司徒雷登會面。
黃華是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學校長時代的燕大學生。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黃華與司徒雷登首次會面時,向他轉達了中共中央的意見,希望美國承認新中國政府,表示新中國需要與外國建立商務關係。司徒雷登表示他想以到燕京大學過生日為由,訪問北平,並與中共領導人會晤。六月十五日,中共領導人透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寫信給司徒雷登,邀請他來燕京大學慶祝他七十三歲壽辰。六月二十八日,黃華再訪問司徒雷登,向他轉達中共領導人的邀請,告訴他在北平期間一定能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在北平將像一位許多中國共產黨人的老朋友一樣受到歡迎﹂。︵註17︶
司徒雷登日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六月二十六日
周雨康從北平返回。得知黃華是因為我而被派到這裡來的——匯報了我去北平的請求——毛表示我可以作為許多中共黨員的老朋友受到歡迎——沒有瞞著美國人的東西,等等。
黃華顯然匯報了我去北平的請求。
六月二十八日
傅︵係傅涇波,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黃華在燕京大學的同班同學︶訪問了黃華。告知收到陸志韋︵燕京大學︶的一封措詞強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訪問。他說毛、周衷心地歡迎我去。但明顯重申這信息的是他下午來時帶來的另一封電報——黃華來了,帶著那封電報,待了大約一個小時。︵註18︶
司徒雷登立即向美國國務院報告,力促國務院批准他的北平之行。報告指出:﹁此行或可加強中國共產黨內不滿意蘇聯的自由主義傾向。﹂︵註19︶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1893-1971︶在接到司徒雷登報告的當日,便與杜魯門總統磋商,然後於七月一日向司徒雷登下達總統訓令:﹁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艾奇遜的理由有三條:第一、會遭到美國國內的批評;第二、損害西方的反共團結;第三、提高中國共產黨的聲望。︵註20︶
司徒雷登透過傅涇波將此決定轉告黃華。︵註21︶
與這一幕同時並進的,是劉少奇、高崗、王稼祥在莫斯科會見史達林。毛澤東派去莫斯科的這三個人,是精心挑選的,因為毛澤東知道史達林不相信他,也不贊成渡江。史達林認為渡江會引起美國出兵干涉,那時上海、青島等地都駐有美軍軍艦和海軍陸戰隊。所以共軍一渡江,史達林就讓蘇聯大使跟著國民黨政府離開南京。史達林還想著﹁雅爾達﹂和他支持國民黨政府的︽中蘇友好條約︾︵註22︶。
現在毛澤東派的這三個人,劉少奇是站在毛澤東一邊,反對過﹁王明路線﹂,即史達林路線的。另外兩個都是史達林信任的:王稼祥是史達林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內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高崗在東北,接近蘇聯,每年八月八日都打電報給史達林,感謝蘇軍出兵東北,很會討史達林歡心。
毛澤東沒有料到,從莫斯科來的好消息,比從華盛頓來的壞消息要快。六月二十六日,劉少奇、高崗、王稼祥抵達莫斯科。二十八日晚間,史達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Georgy M Malenkov, 1902-1988︶、米高揚︵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 1895-1978︶等,會見劉少奇、高崗、王稼祥,祝賀中國革命勝利。史達林一反過去對中國共產黨的輕蔑,承認中國革命的勝利超出他的預料。在宴會上,史達林舉杯向劉少奇敬酒時說:﹁為學生超越老師乾杯!﹂劉少奇婉謝了。他說:﹁這杯酒我不能喝,學生要永遠向老師學習。﹂劉少奇向史達林報告中共建國的步驟:第一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第二步再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建國,並爭取東西方的共同承認,準備於一九五○年宣佈新中國成立。
史達林建議提前,下半年就可以成立︵指一九四九年的下半年︶,蘇聯會帶頭承認。︵註23︶
同一九四九年四月共軍攻佔南京時相比,兩個月來美國與蘇聯的立場,正好對換了位置。
原來史達林看到共軍渡江,美國不但沒有絲毫軍事動作,還讓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同共產黨代表頻繁接觸;他擔心美國可能拋棄國民黨拉攏共產黨,毛澤東可能做鐵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他不能讓毛澤東倒向美國。
而杜魯門呢?既讓司徒雷登待在南京不走,不要跟孫科的行政院長到廣州,表示與國民黨政府拉開距離;又不敢讓司徒雷登去北平見毛澤東、周恩來。結果是兩頭都落空。此時杜魯門、艾奇遜想的,已經不是如何因應中國變化的新形勢,而是如何推卸美國的責任。他們正在用全部精力編纂那本︽美國與中國關係白皮書︾︵The U.S. State Department:the White Paper on U.S. relations with China︶︵註24︶,來表明國民黨的失敗不是美國政府援助不力,而是國民黨自身腐敗無能所導致。如果司徒雷登到了北平,難道不是正好給認為美國政府對共產黨妥協導致﹁丟掉中國﹂的批評者找到藉口?
毛澤東察覺出美國與蘇聯對中共態度的微妙變化,看來同時與美國和蘇聯雙方建立並行關係的可能性已經消失,與其等司徒雷登走了才被動靠攏蘇聯,不如在史達林表達善意時主動靠攏。毛澤東一得到來自莫斯科的消息,趁劉少奇還在蘇聯時就親自寫出的那篇︿論人民民主專政﹀,以回應挑戰的語調道:
﹁您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註︶
毛澤東當時曾向鄧小平說明選擇這樣的時刻提出﹁一邊倒﹂的用意,毛澤東說:﹁這樣是主動的倒,免得將來被動的倒。﹂︵註︶
同時,毛澤東透過陳銘樞,交給司徒雷登一份備忘錄,概括了毛澤東、周恩來對陳銘樞的如下談話:
一邊倒絕對不能被誤解為是依附他人的表示。用這種方式來理解此說法將是一種侮辱。必須認識到,我們的政治路線完全是我們自己的。還必須進一步認識到,就我們的民族獨立而言,絕不存在依附於他人的問題。︵註︶
按照毛澤東的構想,在中國打敗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府,是突破﹁雅爾達﹂大國強權﹁力量平衡﹂的重大歷史事件。毛澤東的戰略是要讓中國成為美、蘇兩大強權之間﹁中間地帶﹂的﹁中間力量﹂,不依附任何一邊。毛澤東的﹁一邊倒﹂,是對美國試探碰壁、對蘇聯及時伸出援手之後別無選擇的選擇。
毛澤東原來不信任史達林,史達林也不信任毛澤東。史達林迷信﹁雅爾達﹂,認為美國一定幫蔣介石打敗毛澤東,所以才反對共軍渡江,作出﹁打下去中華民族要毀滅﹂的荒謬判斷。最後毛勝利了,美國不但沒有干預,還讓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等候﹁解放﹂。這時史達林才察覺美國準備拋棄國民黨,趕緊把及時來到莫斯科的劉少奇拉到自己一邊。
美國當時可以有多種選擇:
第一、同毛、蔣兩邊保持平衡關係,承認毛澤東的新中國,使之成為美蘇之間﹁中間地帶﹂的﹁中間力量﹂;同時支持蔣介石政權在台灣的統治。
第二、承認毛澤東的新中國,支持台灣人民自決成為獨立的自由民主國家,讓蔣介石選擇留在台灣或同宋美齡一起留在美國。
第三、不承認毛澤東的新中國,全力援助蔣介石反攻,打敗毛澤東。
第四、既不承認毛澤東的新中國,拒絕同毛政權往來;又想從國民黨政權脫身,無所作為,推卸責任,坐等毛澤東拿下台灣。
杜魯門、艾奇遜編纂那本︽美國與中國關係白皮書︾,表明美國政府作出的,正是那第四種最荒唐的選擇。它背棄自由價值、背棄自決原則、背棄當時的現實,是對美國、對中國、對台灣的最壞選擇。他們一心想的,只是如何在﹁丟掉﹂雅爾達戰時會議上瓜分給美國的那個﹁中國﹂這件事上推卸責任。他們像鴕鳥一樣,完全無視當時中國和台灣的現實,完全放棄美國該為中國和台灣人民的未來做些什麼的責任。他們不但徹底背叛了︽大西洋憲章︾對世界的自由承諾,而且從﹁雅爾達﹂劃下的那條大國強權﹁力量平衡﹂線上,作出不利於自由、有利於奴役制度的後撤。 那時的台灣,處於動盪不定的狀態。
台灣原是反法西斯戰爭的戰敗國日本的殖民地,戰後理應遵循︽大西洋憲章︾的自由價值與自決原則,由台灣人民自行選擇自由與獨立。然而按照羅斯福、邱吉爾與蔣介石的︽開羅宣言︾︵The Cairo Declaration︶,和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的︽雅爾達協定︾,日本戰敗後,台灣劃歸美國勢力範圍內的中國,由中國國民黨政府派員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受降、佔領,剝奪了台灣人民建立自由國家的權利和機會。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中國打敗國民黨,於十月一日宣佈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掇 Republic of China︶成立,取代了﹁舊中國﹂︵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舊中國的代理總統李宗仁託病去了美國。早在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一日已經引退的蔣介石,從成都飛到台灣,以國民黨總裁身分實際上控制了流亡到台灣的舊中國獨裁政權,再次剝奪了台灣人民建立自由國家的歷史機會。
於是在台灣海峽兩邊,誕生了這個孕育於﹁雅爾達﹂大國強權﹁力量平衡﹂的荒唐故事。
第一、按照﹁雅爾達﹂大國強權的﹁力量平衡﹂,中國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然而在美國支持下由國民黨統治的那個﹁舊中國﹂,被共產黨打敗,被共產黨統治的﹁新中國﹂取代。﹁雅爾達﹂平衡在中國已經被打破。
第二、毛澤東打破﹁雅爾達﹂平衡,本來打算讓中國成為中間地帶的中間力量,打算同美、蘇兩大陣營建立平行的合作關係。然而當毛澤東同時對美、蘇雙方進行試探之時,美國突然對毛澤東關閉了大門。史達林的大門及時敞開,迫使毛澤東﹁一邊倒﹂向﹁社會主義﹂。
第三、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政權,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已經瓦解。蔣介石於元月二十一日宣佈引退總統職位,回溪口故居,副總統李宗仁宣佈成為代理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派國民黨政府代表團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竤、章士釗、劉斐、李蒸等六人,於四月一日同共產黨談判︿和平協定﹀,內容包括﹁廢除中華民國憲法﹂等八條二十四款,實際上是投降協定。李宗仁拒絕簽字,派專機去接代表團回來時,代表團八人已自行決定投降,留在北平,一個也不肯回。李宗仁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後飛抵香港,託言胃疾,十二月五日飛往美國。十二月十日,蔣介石偕子蔣經國飛往台北,﹁以國民黨總裁身分協調軍政事務﹂。
第四、那時的美國政府,既不承認毛澤東的﹁新中國﹂,又準備從它支持過的﹁舊中國﹂國民黨政府脫身;對海峽兩邊的台灣和中國,都採取﹁不介入﹂的觀望政策。美國一面忙於推卸﹁失去中國﹂的責任,一面靜靜等待台灣落入共產黨手中。為此,杜魯門在一九五○年元月五日公開聲明:
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現在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國捲入中國內爭中的途徑。同樣地,美國政府也不擬對在台灣的中國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註28︶
第五、最後阻止台灣落入中國共產黨手中的,是史達林。一九五○年六月,史達林支持金日城發動韓戰入侵南韓,把毛澤東拖下水。從而導致美國第七艦隊︵Seventh Fleet︶進入台灣海峽,毛澤東的﹁中國志願軍﹂在朝鮮半島同美國為首的聯合軍作戰。從此,﹁新中國﹂被孤立於聯合國與自由世界之外達二十一年︵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一年︶之久。反過來也可以說,是史達林迫使美國不得不介入台灣海峽,幫助蔣介石鞏固了在台灣的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
第六、美國﹁失去了中國﹂︵蔣介石的﹁舊中國﹂︶,也就是﹁雅爾達﹂的力量平衡事實上已經被打破。但美國對此長期採取的是不承認事實的鴕鳥政策。美國起先不承認海峽西邊共產中國的存在,達二十二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一年︶之久。一九七一年季辛吉到北京,第一次﹁看到了﹂一個﹁新中國﹂存在的事實,但沒有建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卡特同共產中國建交,又反過來不承認台灣的蔣經國政府存在的事實。直到今天,台灣已經是自由、民主、獨立的現代先進國家,美國政府竟然仍不承認這個重大事實,甚至無視海峽西邊那個奴役制度的共產中國對民主台灣的軍事威脅與吞併陰謀。這種有利於奴役制度的力量平衡戰略的長期延續,正是這個世界現代史上最荒唐故事的根源。
註1:F. D. Roosevelt, 浣our Essential Human Freedoms? January 6, 1941, The Public Papers of F. D. Roosevelt, Vol. 9, p.663.
註2: Ibid.
註3: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7, 2002, p. iii, on-lined resource: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pdf
註4:︵英︶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著,周啟朋等譯,︽二十世紀世界史︾︵西安: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年︶,下冊,第二卷,頁七一四。
5:王力,︿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註6: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著,林添貴、顧淑馨譯,︽大外交︾︵Diplomacy︶︵台北:智庫文化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上冊,頁五二八∼五二九。
註7: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二○○一年︶,頁五九一。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台北:一九六五年︶,第三卷,頁五三一∼五三二。
註8:︿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四卷,頁一一五二∼一一五五。
註9:︿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四卷,頁二五。
註10: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三卷,頁四九四∼四九六。
註11:在一九四七年,美國為了早日重建歐洲經濟,由國務卿馬歇爾提出歐洲復興計劃,也就是俗稱的﹁馬歇爾計劃﹂︵涆he Marshall Plan荂`。由美國政府主導並提供相關的協助,以早日繁榮歐洲經濟。參閱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15 June 1947, pp. 1159-60.
註12: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一九九九年︶,頁四七。
註13:﹁鐵幕﹂一詞在當時並不十分流行,但是隨著冷戰情勢的升級,這個詞開始被廣泛採用來形容歐洲的分裂。鐵幕限制了人員與資訊的流通,這個比喻在西方世界獲得廣泛接受。另一個與﹁鐵幕﹂相似的詞是﹁竹幕﹂︵Bamboo Curtain︶,被用來形容共產中國的情況。
註14:︵英︶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著,周啟朋等譯,︽二十世紀世界史︾,下冊,第二卷,頁八○七。
註15:︿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一一九三∼一一九四。
註16:王力,︿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
註17:袁明、何漢理︵Harry Harding︶主編,︽中美關係史上沉重的一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九二。
註18: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司徒雷登日記︾︹美國華埠:傅氏︵傅涇波︶印行,一九八二年︺。
註19:Stuart, J. L. Edited by Kenneth W. Rea and John C. Brewer,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333-334.
註20: FRUS, 1949, vol. Viii, p. 769. 轉引自袁明、Harry Harding︵何漢理︶主編,︽中美關係史上沉重的一頁︾,頁九二。
註21: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司徒雷登日記︾。
註22:︽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簡稱︽中蘇友好條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國民黨的王士杰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 Molotov, 1890-1986︶於莫斯科簽訂,該約廢於一九五一年,其因是蔣介石政府以蘇聯未能履行︽中蘇友好條約︾中相關承諾為由,宣佈中止︽中蘇友好條約︾的履行。
註23:︿一九四九年劉少奇秘密訪蘇﹀,︽中共黨史資料:伍修權回憶錄︾︵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四輯。
註24:US State Department, White Paper on U.S. relations with China, Aug. 5, 1949.
註:︿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一四七二∼一四七三。
註:︿打破帝國主義封鎖之道﹀︵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頁一三五。
註:FRUS, 1949, vol. Viii, p. 773-774. 轉引自袁明、何漢理︵Harry Harding︶主編,︽中美關係史上沉重的一頁︾,頁四二三。
註28:浣or the remarks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t his press conference on January 5, 1950? see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22, p. 79.
第一章 美國在雅爾達的歷史錯誤︽雅爾達協定︾與︽大西洋憲章︾,代表兩種對立的哲學與戰略觀。 ︽大西洋憲章︾的哲學,是以自由力量的聯合,戰勝法西斯奴役制度,實現有利於全人類自由發展的和平。 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他的一篇演講︿人類四大基本自由﹀︵浣our Essential Human Freedoms荂`︵註 1 ︶中提出,反法斯西斯戰爭勝利後,﹁我們將看到一個建立在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言論自由與表達意見的自由。 第二是在世界的一切地方,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方式的自由。...
推薦序
美國目前扮演的角色不但助長中國共產主義、傷害中國人民並威脅其鄰國之自由,但這卻非特例。正如阮銘書中指出,從《雅爾達密約》開始,美國在亞洲一直是說一套、做一套。雖然滿口理想主義,但行為卻完全相反。在阮銘眼中,美國的軟弱是造成中國共產黨崛起並與蘇聯結盟的主因,而美國並非弱在資源不足,而是弱在缺乏意志力及理解力。若非美國示弱,慘烈的韓戰或許可以避免。蔣介石對台灣獨裁統治,卻受華府支持。但當這個獨裁者的兒子蔣經國及其繼任者開始實行民主化,美國不但沒有給予支持,一九七九年號稱美國「人權總統」的卡特政府甚至企圖強迫台灣人民接受中國統治。如果美國勢單力薄,以上種種雖然不可原諒,但或許可以理解。但美國並非弱國。依阮銘之見,這是一個理念上的問題。某些像季辛吉、布里辛斯基之流的美國人以堅定的「現實主義者」自居,他們認為國際關係取決於金錢與武力。從漢彌爾頓、傑佛遜兩位總統時代至今,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兩套價值觀之間拉扯。它若支持自由,則自由必定得以伸張;相反的,它若縱容強權暴政,像它在中國及對台政策中的作為,則自由在全世界將愈趨式微。中國及台灣都須細讀這本書,並汲取其中精義。美國人也該讀此書,因為阮銘也是寫給美國看的。——賓州大學歷史系羅德國際關係講座教授、華盛頓國際評估及戰略中心副總裁林蔚
美國目前扮演的角色不但助長中國共產主義、傷害中國人民並威脅其鄰國之自由,但這卻非特例。正如阮銘書中指出,從《雅爾達密約》開始,美國在亞洲一直是說一套、做一套。雖然滿口理想主義,但行為卻完全相反。在阮銘眼中,美國的軟弱是造成中國共產黨崛起並與蘇聯結盟的主因,而美國並非弱在資源不足,而是弱在缺乏意志力及理解力。若非美國示弱,慘烈的韓戰或許可以避免。蔣介石對台灣獨裁統治,卻受華府支持。但當這個獨裁者的兒子蔣經國及其繼任者開始實行民主化,美國不但沒有給予支持,一九七九年號稱美國「人權總統」的卡特政府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