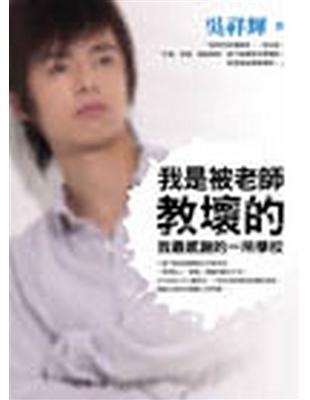(一)
這個十四歲又五個月大的少年,向我回憶他五六七年級的往事。事隔三兩年,他已能用輕鬆的心情描述。我摘要他的「口述歷史」:
「同學不乖,叫去屋頂罰曬太陽。不必上課,一次一小時。連下課時間。」
「發考卷邊走邊叫同學名字,同學要馬上站到他前面。成績好的,他把考卷給他。成績差的,他就不給。直接把考卷扔在地上。叫學生自己撿。」
「還有更過分的,我們教室在三樓,他會走到走廊,把考卷或連絡簿丟到一樓。發完考卷或連絡簿,他才說:沒有發到的,自己到樓下撿。」
「全班太吵,被罰跪著考試。有家長向學校反應,老師知道後,對全班說:『是你們自己要跪著寫的。我又沒叫你們跪?你們怎麼怪到老師頭上?』」
他說的是五年級的男性班導師。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對孩子說話的語氣很直接:「排好!」「站好!」「不要講話!」「聽到了沒有!」
非常明顯地,他的功課一落千丈,朋友激增。敢嗆老師的,被老師憎厭的同學都成為他的「好朋友」。他們那夥孩子如此稱呼自己的班導師:「屁」一個。「那個屁啊!」
現在他已經會苦笑地說:
「他是個敢做不敢當、會撒謊、喜歡侮辱學生的老師。」
「現在我學會了。自己不乖,不要把錯怪到別人身上。」
五年級下學期,家裡替他轉學,遠離不再讓他快樂的學校。新學校接手的林老師兢兢業業,卻得面對一個「總是抱怨和遷怒」的孩子。沒想到,老師也會成為上一位老師的受害者。
真正的惡夢從七年級開始。故事發生在宜蘭一所著名的私立住宿學校。事隔一年,遷地為良後,他已能坦然面對。
「我問他,我戴個戒指也不行?事情就這麼大?」他頂撞學務處江主任,學務處當年稱為訓導處。
「誰叫你是一○八的。」主任說。
「一○八是怎樣啦?就不是人嗎?」他直接嗆回去。
這私立學校按入學考試成績分班。雖然,對外都說常態分班,但是,校長、老師和同學,都知道真相。私下裡也互不隱瞞。數資班、英資班和全資班都有。
「我們學校現在很多人讀,寧缺勿濫。你們一○八的幾個問題學生,給我小心點。我會天天盯著你們,找到機會就會讓你們走。」
「幹你娘!」十三歲的孩子當場發飆。結局是小過兩支。這是「念在初犯,從輕發落。」按校規,侮辱師長記大過一支。
這樣的反應很不成熟。但是,面對這種可惡的師長,十三歲的孩子還能有什麼成熟的反應?他媽媽說的話最經典:「兒子,你這樣反應,讓我很擔心。但是,你如果不反應,媽媽會很傷心。可以讓我不要擔心、也不要傷心嗎?」
我請他把過去七年學生生活中的「惡師」,列個「排行榜」。他說只有兩個。連五年級的班導他都淡淡地略過。這位學務處江主任被他評為首惡;排名第二的惡師叫禿頭,他總管教室和宿舍之外的地盤。
他舉一個和他同夥的崔姓學生,在餐廳遇到禿頭的例子。
「安靜,不要講話,不要走動。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禿頭說:「在餐廳我最大。叫你們做什麼,你們就照著做。」
「需要這麼臭屁嗎?」崔同學小聲說,卻被禿頭聽到。
「站起來。」禿頭咆哮著,「你不服氣嗎?你想怎樣?」
崔同學拿起餐盤,往禿頭砸過去。餐盤上的食物散落滿地。記大過一支。
當然,這都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早已冰凍三尺。師生之間互相憎惡已久。
現在,他說著說著,毫無怨氣或怒氣。神態和語調都很輕鬆。
「學校大,又漂亮,制服也很好看。籃球場很多,籃框都是新的。教室開冷氣,桌椅很新。他們給學生最好的讀書環境。」
「可是,我們的心裡什麼也沒得到。」
「高段班有錯,大事可以變小事。高段班當然沒有小事。低段班小事絕對是大事。他們看人處理事情。」高段班是成績好的班。低段班是成績差的。成績歧視是這個學校的體制運作本質。
「有別班的老師這樣跟全班說,沒辦法,既然在這學校教書,就要遵照學校的規定。希望大家能夠配合老師,給老師一個面子,賞老師一口飯吃。」他還補充說,這種老師會獲得同學認同,至少這種老師很誠實。
他把「寧缺勿濫」「表裡不一」擺在一起,烙下這個學校在他心靈的深刻印記。
七年級沒讀完,他又被家長轉學。轉到您們手上。他是我最小的兒子,培正。
感謝您們,讓他擁有一個不錯的新開始。 「這是我為你轉的最後一個學校。」
從學校帶培正回家「停學」後,我讓他知道,他和我共同面臨一個既殘酷、又有希望的事實。他必須認明清楚。用不同於過去的心,珍惜這個特別的學校。
「這個學校如果你還待不下,台灣就沒有你能讀的學校。你只有出國一條路可走。」培正說他不想出國念書。
「從現在開始,我走到哪裡,你跟到哪裡。直到秋假結束。」他同意這個處置。他知道自己惹出大禍。媽媽笑笑地對他表達強烈不滿:「培正,請你幫媽媽一個忙,好不好?」他說好。「照鏡子的時候,幫媽媽看看鏡子裡面的人,是不是還是我兒子?拜託你囉。」
「安琦事件」很意外。因為,培正一直都很有「女生緣」。從小學開始,就不斷地有許多異性的「追求者」。滿抽屜不同筆跡的「情書」,證明他不是在吹牛。
「情書」是他的隱私。我們只能看信封。偶爾,不堪我的拜託,他才會網開一面,讓媽媽和我分享一二。「讓我了解你們小孩子怎麼告白嘛!拜託啦!」這是通常我博取同情的方式。「告白」是我聽他講電話時,學來的青少年流行用詞。
「情書」是隱私。「情話」是家事。孩子有講電話的充分自由。只是,房間裡不裝分機,要講就不要偷偷摸摸。全家人都公平,講電話誰都能聽。講大哥大?請便,自己付錢。
國中新生訓練才結束,培正就接到幾個女同學寫信給他,包括學姊。據他說,其中一個「品學兼優」。他是她的「初戀情人」。他們的交往被班導師發現,但沒有遭受處分。
「為什麼沒有被記過呢?」我問培正。這學校很特別。男女同校,男女同班,卻禁止男女同學私下交往。
「她跟我交往,功課也沒有變壞。還是好學生嘛。」培正說:「我的功課本來就很壞,也沒有變好。」
「可是,她很可憐。老師總找她麻煩。」他補充說。本來班上同學按程度不同,設有「標準分」。培正六十分就OK。她是八十分才可以免挨打。少一分打一下。
「妳成績很好嘛,」老師笑笑地損她,「提高到八十五分好了。不夠的罰雙倍。」
舉例來說,她考八十一分,過去是安全過關。現在少四分,加倍變成打八下。
每當她挨打時,許多同學看不下去。培正的幾個同夥都當場直接對老師嗆聲:
「老師妳太過分!」「不公平!」「不公平!」「老師,妳怎麼可以這樣!」甚至還有的小聲罵三字經。培正是「當事人」,也是「害人精」,不敢說什麼。
「看到她被打得那麼慘,我的心很痛。」培正說,「所以,我就跟她說,我們不要再交往了。」
「她喜歡你什麼?她不知道和男同學交往、寫信會被記警告,甚至記過嗎?」媽媽問他。
「她知道我是怎樣的人。我一定不會讓她的信被學校看到。」培正說。
不守校規,終要出事。學務主任突擊檢查一○八教室,搜出違禁品。項鍊、手環、耳環、化妝品、手機、PDA、MP3、PS2都是「違禁品」。但,大家都知道,「信」才是真正搜查的第一目標物。
她寫給培正的信被搜出。學務主任不懷好意地笑看培正,一副人贓俱獲的得意之情。培正不斷地被激怒。
就在學務主任慢條斯里,信封即將被打開的剎那間,暴怒聲驚動四座:
「你敢看我的信。那是我的隱私!」培正咆哮著。他憤怒地重拍桌面:「有種你就拆開來看!」
按校規,這是「大過兩支」。「頂撞師長」一支。「男女不當交往」一支。培正在這學校念不滿一年,已經累計將近七支大過。沒被趕出學校,是一位好心的教官看不慣,暗中幫他「槓過」。故意不把記過單送出,放在抽屜存查了事。一直到重現微笑之後,他才主動對我全盤托出。
唉,我只知道他不適應,卻不曉得他的日子過得這般屈辱,榮譽感完全喪失。不過,他還是很勇敢。不會哭。不會訴苦。他還是我記憶深處中的那個孩子。
(二)
半年裡,我為他直接付出已超過一萬個小時。只覺得父子之情已不是我們感情的最核心,卻也整理不出什麼頭緒,才能說盡。「量變而質變」的父子關係,好像一種綿密的柔性壓力,把我們越綁越緊。
我請問培正的感覺。他也跟我一樣,說不出個明確觀點。
「對爸爸是一種隨性和尊重。再來是對兄弟,兄弟只有隨性,沒有尊重。再來是朋友,朋友不會載我去上學。最後才是男女朋友。」
反正,我說他聽。他不見得都認同。他說我聽,我也一樣不必凡事都認真。就像他排名第四的親密關係,很快就會爬升到第一位。誰會笨到去點破?
當天他說出「打球像吃稀飯」後,我問他:「信邪了吧?」
「信了。」他笑著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這個人就是不信邪。可是,我有個優點,看到後,我就會相信。不會像有些人,看到後,還不信邪。不過,在沒看到之前,不管誰怎麼說,我都不會相信。」
他倒是很準確闡明自己的特性。說教對他完全無效。其實,這情境我早就對他舉證過很多次:「沒發現嗎?有時候,你打一整晚爛球。最後十顆、二十顆才打得出上帝的傑作。為什麼?」「沒感覺嗎?你每天練球都是越打越好。後面打的一定比前面打的好。有例外嗎?」
「當然有。」他馬上會說出一兩次後面打得很差的練球天。
現在的台灣小孩,哪個不是像他這麼聰明的?當爸爸或媽媽的如果不認分,氣死了只是提早消費一具棺材。我還算認分,說歸說,卻知道非得等到「驗明正身」,他才會相信。他終於覺悟「量變就會質變」的道理。
「你比較像是我的老師。」培正總算對我們的父子關係做出結論,「你是我最好的老師。」
「我比老師有說服力?是不是?」我問。
「對,一般老師懂得不多。你比老師懂太多東西。」培正說。
「拋開父子關係。你從我這個大人身上看到或學到什麼?」
「我學到想法。你的很多想法都讓我能想得更多,對我的思考幫助很大。」
「人呢?你覺得我是個什麼樣的大人?」
「只要認為對的,你就會堅持下去。」
「舉個例?」
「就像你認為我打高爾夫是對的,你就一直堅持陪我打下去。」培正說,「其實,你不要認為打高爾夫球是我自己選擇的,你沒給我壓力,我就沒有壓力。你這樣挺我,陪我,我怎麼可能會沒有壓力呢?」
「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說過一句話:教育之道無他,愛和榜樣而已。」我慢慢地重複兩次「教育之道無他,愛和榜樣而已。」然後問培正對這句話有什麼看法。
車子剛從「美城」出來,在蘭陽平原黑暗中的小路上緩緩而行。培正沒有馬上回答,直到我們準備要上五號國道的平原段。
「我想不出有任何角度可以反駁這句話。」培正說,「這就是為什麼我想了很久,才回答你。」
「現在的國中小校長水準和以前的比起來怎樣?」我曾私下請教一位教育科班出身,負有培育校長和師資重責的當令教育機構主管。
「現在校長成績考得再好,也比不上以前考上的。優秀的先錄取,剩下的才留給後來的。」您有沒有被他的說法嚇到?
這位教育學博士從教育實務看問題,所以,不了解自己滿腦子反進化、反常識。人類當然一代比一代優秀,才有文明進化這回事。知識越新越進步,台灣的溝通和表現平台越來越開放多元。怎麼可能現在的校長比過去的差?
我還聽過一種門戶之見,師範系統的和非師範系統的私底下互罵:「以前師範畢業的學有專長,現在的老師沒受正規訓練,師資水平一落千丈。」
「師範系統的最反動,程度最差。師專入學考試不必考英文,因為教小學生用不到,所以,英文程度特別爛的會去考。教小學會算術就行,考師專的數學題目,好像在做國小算術的期末考。師範有公費,窮人子弟排隊去,就只想捧鐵飯碗而已。」
何必呢?台灣教育體制出問題,哪個系統出身的老師都得乖乖就範,在體制下討生活。同是天涯淪落人,沒什麼好互臭的。現在的師範生已經不一樣,沒有公費,沒有鐵飯碗。體制大計都還沒個準,也沒什麼教育實務好急著爭論的。就「行業性格」而言,台灣的老師從來就是相對穩定性最高,服從性最強的職業。不然怎可能會讓「萬世師表」「孟母三遷」教到今天?
威權解構才可能有教育改革。教改要發揚多元智慧,主流體制就必須是多元。師資培育也必須多元,才能勝任不同價值取向的體制。「多元智慧」對一個運作體系而言,說了等於沒說。到底要幾元?不先明定,如何做「組織設計」和師資培育?誰當教育部長也不知道幾元才好。也許,旺盛的台灣民間活力才可能破解這個難題。何不讓台灣的教育法令徹底鬆綁?讓所有對教育有想法,想辦學校的人都能夠有機會試試看實踐個別的教育理想。市場法則或許終會讓到底是幾元的答案,自然浮現。
「有自由的地方就是故鄉。」這是文學上的說法。用這樣的精神意涵,「能快樂學習的地方就是學校。」「沒有快樂的地方就不是學校。」「不能帶領學生快樂學習的就沒有資格當老師。」多元智慧當然要有多元的量表。用同一種量表評鑑不同教育價值的學校,必然失真可笑。這種學習快樂指數的新教育評鑑量表,有哪幾個台灣老師願意合作去創造?
學校是天真孩子相聚的地方,卻一直是個不快樂的大磁場。學生不快樂,家長和老師會快樂嗎?學生身心不健康,台灣怎麼會和諧?哪個校長去參加遴選時,不都把「提高升學率」做為主訴求?全部都是這樣的校長候選人,教改怎麼會有希望?家長卡校長,校長卡老師,老師卡學生,關關相卡,卡到現在,還出不了一個敢拍胸脯保證教改一定成功的教育部長。
多元智慧不會成就於以既有學校為主體的教育體系。給予各種教育價值相等的法律地位,多元價值才會普遍體現。「同等學力」就是教育歧視下的救濟。如果,國小畢業和高中畢業都一樣可以考大學,文官考試和任用沒有學歷歧視,「同等學力」做什麼?
每個機構的人才進用,各展神通。要用博士的,就考博士程度的題。要用碩士的,就考碩士的程度。考試的學歷資格限制為什麼不能取消?政府用人起薪為什麼要帶頭做學歷歧視?博士就比學士更會當稱職的公務員?還是因為,大權在手的人都是博士?
什麼士都跟培正無關。他幸運地否極泰來,找到學習的快樂。他早已回復到過去那個快樂小培正的樣子,只是內斂許多。
春假過後,星期三的夜間課程,培正選擇上美髮課。老師是同學的媽媽。在頭城經營「喬伊髮舖」。第一堂上「毛髮的知識」;第二堂教「頭部的穴道」;第三堂要去老師開的髮舖,實際洗頭。他和可麗餅互洗。家族裡連他共有三個人選修美髮課。他還預約,假日回家,我和媽媽都要讓他練習洗頭。
陳教練也傳達一個好消息。蘭陽地區「第一志願」的宜蘭中學,請他推薦球打得好的國中生。宜中想要延攬高爾夫球手進學校,大力發展高爾夫運動。
「早上上課,下午就練球。」我在一個場合碰巧遇上宜中的吳校長,他跟我證實學校的新政策,並略做細節說明。
要靠高爾夫推薦入學,陳教練的第一高徒非培正莫屬。
「宜中如果不給獎學金,你就不要去讀。」培正媽媽對他說。他說真的有獎學金嗎?母子一搭一唱,至少演得很像吳校長非捧獎學金,登門拜訪不可的模樣。
快樂,好像讓人在冥冥之中,走上更開闊的命運磁場。
練習場一位從美國回來的球友,看他打球,跟他「保證」:「小弟,你的球技,美國的好高中都會給你獎學金。你再繼續努力,只要打入七十幾,美國的好大學隨你挑。你當然可以挑獎學金最多的那一間。」
我和培正相視微笑。我知道他的表情顯示著:「聽聽就好,不一定是真的。」走出練習場,我對培正說:「你繼續努力打,國中畢業前,打不出七字頭,我頭砍給你。」
「不要砍啦。」他笑著說:「你砍頭,誰陪我練球?」
這傢伙越來越貼心。幾乎所有過去認識他的人,都讚美他越來越有禮貌。我才不跟他神經病,陪他打了半年球,還不夠嗎?
「破八十有多少把握?」我舊話重提,提醒他別忘記自己立過的第一階段目標。
「不難。」培正說。
他接著補充說,他不喜歡兩種極端的說法:
「很簡單」就是極端的說法。如果很簡單,為什麼我現在做不到?人家會說我自大。「很困難」也是極端的說法。如果很困難,我幹嘛還要繼續打?講不難比較不極端。對自己有信心,也不自誇。
這樣的孩子,我再不放手讓他獨自奮力一搏,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和媽媽開始商量要如何漂亮地「下車」。孩子的列車開向人間,我們的列車卻要從人間開往天國。父子同車總會彼此耽誤點什麼。
培正將來要念什麼高中,只有他自己心裡曉得。我不想猜測,更不會干涉。孩子能「獨立」就好,就是「成材」。就不會成為家庭的負擔,就是社會的正數,不是負數。看著他半年來的蛻變,我相信他終會「成材」。我和媽媽還有同行天涯的旅程要走。
(三)
擔心也可以是表現愛的一種形式。就像從台北到高雄,不坐高鐵,非要踩著快要解體的拼裝三輪車,並不犯法。擔心是一種心靈疾病,患者以父母占最大宗。疾病可能痊癒,但病人最難自主獨立。獨立的先決條件是健康。不健康連基本生活行動都需要人幫忙。擔心是傳染病,不只自己生病,還會感染最親近的人。擔心的可怕是:甜美的家庭變成病房。
擔心不是真愛的核心。愛是對人付出,擔心是自我恐懼。擔心別人往往只是恐懼自己的期待落空。擔心只是愛的初階出場情境。就像演唱會之前,擔心這擔心那。但是,真的走上舞台,任何一個擔心都可能破壞心念的專注和純淨,毀滅精彩演出的初衷。
擔心的人永遠品嚐不到獨立自主的滋味。獨立經濟是獨立的開始。獨立思考是獨立的成熟。物質面和精神面難以切割,同時進行著。培養孩子獨立的能力,是在他們還沒獨立之前,我最想做好的一件事。當然,過程中孩子屢有嘗試錯誤。但也正因為如此,更堅定我一試再試的信念。我寧願他們早早犯錯。人生的錯誤犯得越晚,會越不可收拾。
從孩子們還在蹣跚學步,他們就都學會「買單」。在餐廳吃過飯,只要現場盡在我的眼底,沒什麼救不得的危險,我就會跟孩子說:「看到沒有?櫃檯那個阿姨?去跟她說要結帳,把帳單拿回來給爸爸。」
孩子一走出,我的眼睛就盯著廚房出菜口到他將走過的路。等他拿回帳單,我數了錢,叫他拿去付帳找錢。他們任何一個都做得跟大人一樣好。培正小時候比兩個哥哥都更「肥軟」。可愛到不行。有時,付完帳我們還必須再坐著等。因為,餐廳的阿姨和姊姊不放人。一個轉手過一個:「好可愛喔,借我們抱一下,玩一玩。」熟的餐廳還更會「做人」。「你們先去逛街。逛完再來抱。這麼可愛的小孩,不玩會受不了。」「乾脆你們直接回家。小孩今天跟我回家睡,明天你們再來吃飯,再抱回去。」生意做到如此瘋狂,難怪台灣錢淹腳目。
等到孩子稍大。當然一以貫之,不洗碗就沒有權利吃飯。五年級開始,他們每一個人都開始洗自己的衣服。「能做的就自己做」,這種家教下,孩子的思路根本難以「控制」。
他們從念幼稚園開始就老是覺得別人「很幼稚」。小學放學的校門口,看到許多讓媽媽拿書包的孩子,或是讓菲傭跟在身後提便當袋的學生。他們幾乎都快到完全厭惡,深以為恥的程度。早熟讓他們容易「不適應」台灣的學校環境,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也沒辦法,我又不是故意的。誰教他們生為我的兒子?
孩子是否「卓越」?我真的「不敢」在乎!人生是他們各自的。一個父親能夠教養一個「獨立的孩子」,社會責任已了。有多大的成就,是孩子自己的造化。我唯一不可取代的角色是「父親」。不管孩子是否「卓越」,他們永遠是我的孩子。卓越或不卓越的都一樣是,哪個孩子也都享有相同的父親之愛。人生的親子真相不就是簡單如此?
說感傷點,誰在奉養老父老母?往往不都是那個「最沒出息」的孩子?他沒那麼忙,沒很多產業和事業要操心勞碌或國內外奔波。他甚至覺得自己沒成就,最對不起父母,所以,最孝敬。
親子是天底下唯一不可取代的關係,沒有任何價值或成就或榮譽能夠改變我的這項認知。這樣的信念,大概我會成為幸福的父親。無論孩子終將如何,他們都會知道,他們的父親不踰越應有的角色,只是幫助和支持他們摸索自己的人生。
三教九流、販夫走卒、達官顯要,我這半生多所結交。中低收入戶、小康之家、富豪巨室的悲歡離合我也略有見識。人格特質才是幸福或快樂的真正秘藏之處。
學校教育的成績,跟人一生的成就或財富基本上無關。成就和財富都是個人經過長期的奮鬥或機緣所得。學校最重要的角色是在形塑一個孩子的人格特質。這正是台灣的常態學校最不在乎的。
如果教育是為了升學考試,可以確定,台灣常態的公立學校是最壞的選擇。一些私立學校已經證明。他們一、二年級就趕完三年的教學進度,三年級就是復習和考試。公立學校的教學效率差人三分之一。
私校還是要教許多和升學考試無關的科目。通學或住校也都要浪費許多交通時間或應付群體生活的必要之惡,像集合、聽訓,因某個人或某事件造成的耽擱。最有效率的上學選擇是:在家自學。
如果我是現在的孩子,我也許會這樣做:先把過去歷年來的基測試題全做一遍。不管考幾分,先掌握出題的型態、方向和關鍵處。然後,開始在家「讀書」。我相信給我一年時間,三年的進度,我最多用一年就能讀完。因為,在家讀書的一年時間,等於去學校讀書的兩年。而且,我只讀「可能會考」的重點。
把學校比喻成「教育便利商店」,恐怕也太侮辱便利商店。因為,校長和老師都沒有接受過以客為尊,笑臉迎人的「店長講習」。便利商店的貨品當然任由消費者自己選。學校的體制,核心價值,服務品質和服務態度遠遠比便利商店不如。
便利商店的全國連鎖成為行銷通路壟斷的怪獸,學校也扮演教育壟斷的怪物角色。只是,不上便利商店是省錢儉樸。不上學校卻是驚天動地,自毀前程。
有一次我對全國的「消保官」演講,開玩笑請他們管管學生的消費權。
「教育部的位階比消費者保護高,我們管不到。」大家嘻嘻哈哈一番。哪個消保官沒有孩子?不知孩子疾苦?可是,官再做得比「消保官」千百倍大,事到臨頭,才知道「孩子的爸」或「孩子的媽」都沒有「孩子的老師」大。
過去,我偶爾會想主動去學校跟老師談談,但終究是想歸想,從來沒行動。心想,老師也只是個「升斗小民」,都在盡「照表上課」「照章行事」的本分,又能要求他們什麼?根據家長們私下聊天,只要孩子有問題,老師的最大共同特點就是:自己和學校都沒錯,都是學生的錯和家長的疏忽。
「如果學生受到老師不當的待遇,家長應該怎麼辦?」我繼續利用培正沒用完的四分鐘。
「家長一定要趕快去學校罵。」培正說。
「罵有用嗎?」
「罵當然沒用。但是,罵過以後,小孩在學校會比較好過。老師知道他爸媽會到學校罵人,就不敢欺負學生。」
「罵誰?罵校長或老師?」
「被誰欺負就罵誰。」
「怎麼罵?」
「越大聲罵越好。」培正還描述幾個家長到以前的學校罵老師的情境,說好遠好遠就聽得到,最難聽的三字經、四字經、五字經、六字經、七字經、八字經都有人罵過。
「這樣公然侮辱人是犯法的耶?」
「那就不要罵難聽的。但是,一定要罵得很大聲,讓別班,最好全校都聽到。這樣子老師才會怕。」
「老師被罵過以後,不管這學生了。學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沒人管,怎麼辦?」
「這樣說太誇張。罵老師是為了讓老師怕。」培正糾正我,「爸媽罵老師,學生最多只會不怕那個老師而已,學生該怕的自己會怕。家長罵老師會讓孩子在學校人緣很好。」
「為什麼人緣會好?」
「不是所有的老師大家都想罵。很多老師大家都很喜歡。但是,想罵的老師也很多,又不敢罵,學生家長也都不來罵,我們多可憐啊。有家長來學校開罵,大家當然都會很高興,都會感謝那個同學請他家長來學校罵。」
「為什麼要趕快罵?」
「不趕快處理,問題就一直會發生。因為老師有問題,學生通常不會說。會跟家長說,就表示事情很久、很嚴重了。當然要趕快去罵。」
「兒子,所以我和媽媽從來沒去罵過老師,很不盡責囉?」我笑問他。
「不會啦。罵也沒用,學校不會改的。而且,我自己有錯,你怎麼去罵老師?」
「至少有三種人。」我對培正說。經過一段不好的遭遇後,每個人因為發展不同,會有不同的心靈氣質。有人會記住過去的種種不愉快。有人會覺得過去已經過去,也沒什麼,還不是走過來了。有人會心存感恩,沒有那段不堪的經歷,就沒有現在的甜美和深刻。
我問他:「你是三種中的哪一種?」
「最後面那一種。」培正說,「我現在對人都很感恩。」
我沒問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變化。只是在心裡琢磨,一個充滿感念的孩子,為什麼會希望爸媽要「趕快去學校罵老師」?
「如果現在要你總結讓你變壞的經驗,你會怎麼說?」
「我們只是個小孩子,怎麼能夠給我們那麼大的壓力呢?」培正說。
「通常大人會說,孩子變壞都是交到壞朋友。你的經驗呢?」
「我有交到壞朋友。」培正說,「可是,老爸,我真的告訴你,我不是被朋友帶壞的。我是被老師教壞的。」